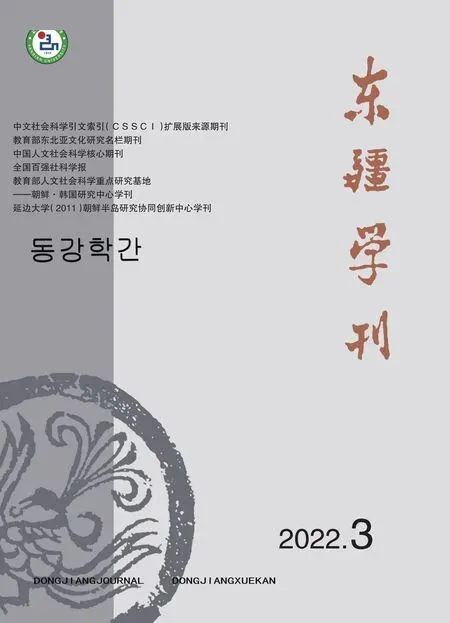日本萬葉時代家訓文化構建中的中國元素溯源
——以《喻族歌》為例
閆秀,冉毅
“家訓,顧名思義,是齊家之訓、家內之訓。中國的家訓是父祖輩對子孫、家長對家人、族長對族人通過文字形式向子女晚輩進行的訓誨。”[1](98)家族,“在中國,表現為由同姓同宗的多個家庭集合而成的宗族。”[1](1)在日本,“家族”的內涵不僅包括中國“家族”的含義,還進一步擴展到主從關系之成員的家和宗族。因此,日本家訓的訓誡對象包含有血緣關系的家族成員以及服務于該家族的非血緣關系成員,如武士的家臣、商家的用人等。李卓在《日本家訓研究》中提出,“日本的第一部家訓是吉備真備(695—775)所撰的《私教類聚》,成書于奈良時代(公元769年左右)。之后,日本家訓不斷繁榮發展,逐漸形成公家家訓、武家家訓、商家家訓、農家家訓、儒家女訓等各種類型。”[1](52)
《萬葉集》①本文所引《萬葉集》出自《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 萬葉集4》,東京:巖波書店,2003年。該組歌群出自于卷4:461。所引譯文出自兩套中譯本,分別是楊烈譯:《萬葉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金偉、吳彥譯,《萬葉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楊烈先生用五言古詩的形式來譯和歌,故譯文內容比原文豐富。金偉 、吳彥夫婦則采用口語化的語言翻譯和歌,比較精確地把握了和歌中要表達的含義和氛圍,但無法兼顧和歌中嚴格的形式美。因此,在研究和歌內容等方面時,為更全面、更準確地把握作者的原意,部分參考了金偉、吳彥版;在研究和歌格式等方面時,為保留原詩的格式之美,較多引用了楊烈版。中的《喻族歌》(卷20?4465-4 467)是萬葉時代著名詩人大伴家持(后稱家持)的作品。嚴格說來,《喻族歌》并不屬于家訓,但其標題中的“族”與“家”的含義相近,“喻”又含有教喻、訓誡的含義,與“訓”相似。伊藤博《萬葉集釋注》引用《萬象名義》的定義“喩暁也、諷也”,稱“喩す”為“訓誡之意”。[2](706)“喻族”意即“家訓”,其內容體現了日本萬葉時代的家訓文化。左注顯示該作品的創作時間是756年。因此,《喻族歌》可看作日本第一首蘊含家訓意義的和歌。
《喻族歌》是《萬葉集》中唯一一首告誡族人的作品。由于作品的特殊性和唯一性,《喻族歌》在日本學界備受關注。學者們主要從作品背景、教諭對象、文學地位、詩歌理念等角度全方位加以論述,《代匠記》中略有提到部分詩詞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尚未見《喻族歌》與中國文學的比較研究。在中國學界,《喻族歌》相關的研究成果更難覓其蹤跡,僅有寥寥數篇偶有一提,更無深層次研究。殷曉星在《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對明清圣諭的吸收與改寫》中提到了《喻族歌》的詩名,但未進一步展開。[3](58)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為頻繁的時期之一,同時又是思想極度開放的時代,學說百家爭鳴,文壇百花齊放。家訓在這一時期蓬勃發展,形成了我國傳統家訓創作的第一個高峰。《顏氏家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系宏大的家訓,影響巨大,亦曾傳入日本。業界有學者認為,《喻族歌》的創作可能受到了中國家訓文化的影響,因此,《喻族歌》與《顏氏家訓》之間的關系很有研究的必要。經過考察,筆者還發現晉朝陶淵明的《命子》在諸多方面與《喻族歌》有相似之處,值得深入探究。魏晉南北朝止于589年,而萬葉時代始于629年(舒明天皇即位),理論上存在魏晉南北朝中國文學向萬葉時代日本文學浸潤的可能。因此,本文擬將體現萬葉時代家訓文化的代表作《喻族歌》分別與《顏氏家訓》和《命子》做比較,探究日本萬葉時代家訓文化的源流。
一、大伴家持的《喻族歌》
《喻族歌》的創作背景如下。日本天平勝寶八年(756)2月2日,左大臣橘諸兄因承擔誹謗太上皇之責辭官。4月14日,圣武太上皇病危。橘奈良麻呂策劃謀反。5月3日,圣武太上皇駕崩。5月10日,大伴古慈斐因誹謗朝廷被捕。6月17日,家持作《喻族歌》。《喻族歌》歌頌了自神代以來大伴氏族的榮光,頌揚大伴之名的尊貴,告誡族人要揚大伴之名,不要輕舉妄動。窪田空穂指出,“家持所追求的是忠孝兩全,既表明了對朝廷的忠誠,又表達了自己作為名門后代要繼承祖先遺志的孝心。”[4](348)
二、《喻族歌》與《顏氏家訓》的比較
北齊顏之推(531—594)的《顏氏家訓》是中國第一部內容完備并以“家訓”為名的家訓專著,也是中國家訓的典型代表,被后世奉為家教規范。顏之推生活在南北朝至隋朝期間,深知各朝政治,洞悉南北學識,是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是當時最博學的學者之一。其編纂的《顏氏家訓》記述了個人經歷、思想、學識,目的是告誡子孫,使子孫成為國家棟梁之才,反映了其名門士族的政治立場和“學而優則仕”的人生價值觀。
《顏氏家訓》是家訓專著,約四萬字,用語平實卻寓意深刻。全書分為七卷,二十篇,每篇圍繞不同的中心來展開,或談治家,或論道德,或議交友,或說學習,或曰仕宦,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各篇篇幅不一,短則幾百字,長則數千字,如《勉學》一篇就長達六千余字,而《止足篇》僅四百余字。
《喻族歌》屬于典型的日本和歌,在長歌之外還附有兩首反歌和左注,文筆優美,辭藻華麗。在楊烈所譯《萬葉集》中,《喻族歌》為250字(包括長歌、反歌及左注,不計標點符號),篇幅不到《顏氏家訓》字數的百分之一,不在一個數量級。
其次,在創作背景和主旨方面,顏之推生于官宦人家,一生經歷南北兩朝,侍奉四朝天子,親身體會歷次朝代更迭,三次被俘,數次險遭殺身之禍,生活閱歷極其豐富。站在人生臨近終點的地方,他回首往昔,自省“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其根本原因在于“無教,以至于斯”。[5](3)于是,顏之推于花甲之年著《顏氏家訓》,把自己一生中刻骨銘心的體會傾注其中,“以為汝曹后車耳。”[5](3)他在《序致篇》明確了這篇家訓的主旨是“整齊門內,提撕子孫”,[5](1)希望子孫后代能以此為鑒,從而“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5](114)
家持祖上曾任右大臣、大納言、大將軍,官階從二位。然而延續到家持這一輩,家族逐漸式微,地位威望不復往日。家持作《喻族歌》時任兵部少輔、山陰道巡察使,官階從五位上。《喻族歌》的左注提到家持作《喻族歌》的直接原因:“上,緣淡海真人三船讒言,出云守大伴古慈悲宿禰解任。是以家持作此歌也。”[6](817)家持出于約束族人、保全家族的想法而作此歌。值得一提的是,作歌前一月余,親厚大伴家族的圣武天皇駕崩。因此伊藤博認為《喻族歌》“表述了對圣武天皇駕崩的深痛悲切,是緬懷圣武朝代的挽歌。和歌體現了失去圣武天皇這一精神支柱后,家持的空虛落寞、無依無靠的危機感”。[2](681)
在教諭內容方面,顏之推希望子孫像自己一樣步入仕途。所以《顏氏家訓》不僅包含教子篇、兄弟篇、勉學篇等常見教諭內容,還包含誡兵篇、涉務篇、雜藝篇等入仕為官的相關內容。顏之推要求子孫不僅要讀儒家經典,還要學習琴棋書畫等技藝,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這些不但是為官為宦的必需技能,也是士大夫生活的重要內容。后世形容《顏氏家訓》曰:“該括百行,貫穿六藝”,[7](543)說明《顏氏家訓》包羅萬象,涉獵廣泛。
相較而言,《喻族歌》篇幅短小,內涵單薄。大半篇幅追述祖上榮光,最后寥寥幾行教諭族人“珍惜清令名”“凡事心思量”。[6](816)反歌是對長歌的強調和重復,沒有更多的教諭內容。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作者經歷、創作背景方面,還是在文章體裁、篇幅、結構、主旨、內容等方面,《顏氏家訓》與《喻族歌》都存在較大差異,難以想象兩者具備相互借鑒的可能。
三、《喻族歌》與《命子》的比較
存世的陶淵明訓子詩文中,有三篇最為著名:《命子》《責子》及《與子儼等疏》,分別作于陶淵明仕宦前期、歸隱前期和歸隱后期。聶言之(1985)考證該詩反映了陶淵明仕宦思想由強而弱直至完全消釋的變化過程。其中《命子》是陶淵明的第一首家訓詩,作于陶淵明長子降生之時。聶言之指出“該詩追述先祖功德,激勵兒子勿負祖輩榮光,要成為一個品德高尚、有所作為的人。”[8](45-50)袁行霈在《陶淵明集箋注》中提到,“《命子》猶教子,其大要在追述祖德以教訓之”。[9](43)
《命子》共分十章,每章八句,每句四言,共320字(不計標點符號)。前文提到,《喻族歌》為250字,與《命子》的數量級相當。《喻族歌》和《命子》在結構上都可分為兩部分,上半部分為追憶祖先功績,下半部分為教諭內容,上半部分皆占整體篇幅的大半。《喻族歌》從開篇“高千穗岳上”到“極盡事皇方”屬于上半部分,余下為下半部分,上下部分的比例約為2:1。《命子》共分十章,前六章和后四章分屬上、下半部分,比例約為3:2。兩者均為蘊含家訓寓意的詩歌,且體量相當,結構相近,具有較大的相似性。
其次,從作者身份和家世背景來看,陶氏家族是中國典型的士大夫家族,祖上頗有功績。“邈焉虞賓,歷世重光”“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9](40-41)論文治,陶青曾任丞相;論武功,陶舍曾跟隨漢高祖劉邦征戰四方;論分封,陶侃曾因功封長沙郡公。陶淵明作《命子》時,正任江州祭酒。
大伴家族是輔佐歷代皇族的重要家族,長期掌管國家的軍事大權。從圣武天皇時代起,“手持櫨木弓,又執鹿兒矢”“掃清寰宇內,奉仕長如此”。[5](816)家持的曾祖父大伴長德鼎盛時官拜右大臣,祖父大伴安麻呂官至大納言兼大將軍、贈從二位,父親大伴旅人曾任大納言、從二位。《喻族歌》作于756年,當時家持任兵部少輔、山陰道巡察使。
由此可見,陶氏家族和大伴家族都是輔佐當權者的重要世族,歷史上都曾經位高權重、顯赫一時,擁有傲人的家族歷史。陶淵明和家持創作作品時都是朝廷的中下層官吏,距離祖上的榮耀地位還有不小的差距。兩名作者的家世狀況、當時身份相近,產生相似的感情亦情有可原。
在創作背景以及教諭對象方面,《命子》作于陶淵明初得長子之時,教諭對象自然是陶淵明剛出生的兒子陶儼。古人結婚生子都較今人早,陶淵明年近而立之年方有子嗣,猶今人之中年得子,自是喜不自勝。彼時,陶淵明初入仕途,出任江州祭酒,正是青春年少、揮斥方遒、大展宏圖之時。“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夙興夜寐,愿爾斯才。”[9](42)詩中充滿了對孩子的期望、對家族振興的憧憬。
圣武太上皇駕崩、橘諸兄辭官、大伴古慈斐被捕,一系列噩耗給整個大伴家族帶來極大動蕩。而敵視大伴家族的橘奈良麻呂蠢蠢欲動,意圖謀反。大伴家族在內外交困、撲朔迷離的政治環境中風雨飄搖。家持內心深感惶恐不安,于是作《喻族歌》,教諭族人謹言慎行,遠禍消災。關于作歌主旨為何,藤井一二論析有以下三點:“①告誡與家持關系特別密切的大伴池主以及堂兄弟大伴古麻呂等人。②對外表明作為一族之長的態度,具有儀式感。③家持自身的感悟”。[10](155)考慮家持當時所處的境遇,教諭的對象應是全族。
此外,從教諭重點來看,《喻族歌》和《命子》都從言行、品性上對族人、后代提出了嚴格要求和殷殷期望。《喻族歌》告誡族人要謹言慎行,“凡事心思量”“戲言起禍殃”,更要珍惜祖上傳下的好名聲,“珍惜清令名”“勿絕祖宗名”“勿負大伴氏”“古來清白族,永享好家聲。”[6](816)《命子》要求孩子學習祖先“穆穆”“亹亹”“直方”“惠和”“淡焉虛止”的德行操守,勤奮不懈,“夙興夜寐”,通過“名汝曰儼,字汝求思”傳達了“溫恭朝夕”“尚想孔伋,庶其企而”的殷切希望,并諄諄教導居安思危,“福不虛至,禍亦易來”。[9](41-42)
《喻族歌》和《命子》的教諭重點都是謙虛謹慎。家持審度當時動蕩的政治形勢,告誡族人宜低調行事、韜光養晦,度過家族的至暗時刻,以求自保延續。陶淵明則是因本身淡泊名利,對子孫后輩亦不強求步入仕途,只求君子修身,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志向高潔。
在遣詞用句方面,兩篇作品多處使用不同語句表達了相似含義。如:《命子》的“世歷重光”[9](40)、《喻族歌》的“相繼世世王”[6](816)都強調了世世代代一直追隨著君王。《命子》的“御龍勤夏,豸韋翼商”[9](40)、《喻族歌》的“赤心豪不隠,極盡事皇方”,[6](816)表達了對君主的忠心赤膽。《命子》的“撫劍風邁,顯茲武功”,[9](41)《喻族歌》的“手持櫨木弓,又執鹿兒矢,丈夫有武雄”[6](816)分別通過“撫劍”“持弓執矢”的動作細節描述祖上的勇武形象,用“武功”“武雄”來形容祖先的功績。《命子》提到陶氏譜系“爰自陶唐”,[9](40)起源于遠古的堯舜時代,《喻族歌》說到大伴氏“自從神代起”,[6](816)都因家族歷史源遠流長而自傲。《命子》說“運當攀龍”,[9](41)意即追隨帝王建功立業是時運注定的,《喻族歌》則曰“仕奉是祖職”,[6](816)都是表述家族使命是為君主效命,是上天注定、從一而終的。“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9](41)“赤心豪不隠,極盡事皇方。”[6](816)《命子》強調寵辱不驚的“斯心”,《喻族歌》強調“極盡事皇方”的“赤心”,本質都是一心輔佐君王、不求任何回報的“誠心”。
另外,土屋文明在《萬葉集私注》中指出左注中的“緣”并非緣由的緣,而是緣坐。[11](397)“緣坐”與“連坐”相同,是正犯本人和相關親屬、家族連帶受罰的一項特殊歸責原則。日本律令沿襲了唐律令的用法,家持作為律令制下的官員,必然熟知該詞,才得以在《喻族歌》中進行化用。
在創作手法方面,《命子》使用的敘述手法是虛實結合,偏重于贊揚祖先的德行。“邈焉虞賓,世歷重光。御龍勤夏,豸韋翼商”[9](40)是對祖先功績的虛寫。對家族“渾渾長源,蔚蔚洪柯”[9](41)的悠長興衰歷史,則是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時有語默,運因隆窊”[9](41)一語略過。《命子》把一些歷史上名聲隆盛的祖先作為重點實寫對象,如擁有顯赫官職的“穆穆司徒”陶叔、“斖斖丞相”陶青,如創下了不世功績“啟土開封”的陶舍、“業融長沙”的陶侃,如品行修養高尚的“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的祖父陶茂和“淡焉虛止”“寄跡風云”“冥茲慍喜”的父親陶丹。[9](41)
《喻族歌》則以虛寫為主,偏重于宣揚祖先的功績。整篇和歌中沒有出現某位祖先的具體名諱,只是籠統提到“名曰大久米”。將祖先的功業抽象概述為“事神務太平,遠人亦和喜,掃清寰宇內,奉仕長如此”[6](816),描述祖先志得意滿的時候濃墨重彩,對家族時運不濟的時期簡單帶過。
在感情基調方面,《命子》的前六章從帝堯之世開始回憶祖先,陳述家世淵源,氣勢磅礴、意氣風發,“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啟土開封。”[9](41)但從第七章起,感情突趨低沉。“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只立。三千之罪,無后為急。”[9](41)回憶長子的降生,文字色彩變為明亮。“卜云嘉日,占亦良時。”[9](41)嘉日、良時表達了陶淵明內心的欣喜和憧憬。“厲夜生子,遽而求火。”[9](42)陶淵明此處用夜半求火的典故來形容等待孩子降生的焦慮和惶恐。“名汝曰儼,字汝求思。”[9](42)《禮記·曲禮上》曰:“毋不敬,儼若思。”“儼”即恭敬莊重。“溫恭朝夕,念茲在茲”為人待物要溫和恭敬。“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希望兒子能夠像孔子之孫孔伋那樣出色。可見,陶淵明對長子抱有極大期望。“爾之不才,亦已焉哉”[9](42)又展現了父親對待孩子的寬容和豁達,也反映出了陶淵明樂天知命的人生態度。“凡百有心,奚特于我”“人亦有言,斯情無假”[9](42)強調這種厚重的父愛和殷切的感情是普遍、真摯的。
《喻族歌》上半篇追述祖上功績,并忠肝義膽地袒露了對天皇“豪不隠”的拳拳“赤心”,鄭重其事地表達了“仕奉是祖職”的殷殷決心,慎而重之地立下了“子孫長相繼,世世當延長”的錚錚誓言。下半篇家持更是以一族之長的身份訓誡族人,要求“凡事心思量”,嚴厲告誡“勿負大伴氏”“勿絕祖宗名”“戲言起禍殃”“珍惜清令名”。[6](816)4470左注中寫道:“以前歌六首、六月十七日大伴宿禰家持作”。[6](817)“歌六首”就包括了這首《喻族歌》。在這里家持使用的是“大伴宿禰家持”。提到“宿禰”這個天皇的賜姓也有強調家族歷史榮耀的意味。左注中還寫道:“出云守大伴宿禰古慈斐遭三船陷害被解任。”家持這一說法與《續日本記》記載不同。關于左注與史料不同的原因,窪田空穗推測源于“家持遠離政治中樞,不清楚事件詳情,難以預料事件走向這一不安的心情。”[4](347)由此可見,家持認為大伴家族已到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當時的心情既有惶恐,又有焦慮。因此《喻族歌》的基調是嚴肅緊張的,亦有風聲鶴唳、驚弓之鳥之感。
總體來說,《喻族歌》通篇的整體感情基調是嚴肅莊重的,一字一句、鏗鏘有力、入木三分。而與此不同的是,《命子》下半部分呈現出濃厚的親子之情,感情豐富,筆觸細膩。
《命子》中陶淵明既不強求孩子對朝廷、對天子忠心耿耿,也不要求子孫成為達官顯貴,光宗耀祖,而是在德行操守上對其寄予厚望。首章提到“穆穆司徒,厥族以昌”“亹亹丞相,允迪前蹤。”[9](41)“穆穆”,儀容美好、舉止端莊恭敬。“亹亹”,勤勉。陶淵明就將“厥族以昌”的原因歸功于“穆穆”“亹亹”。在談及曾祖父陶侃時,強調“功遂辭歸,臨寵不忒”,[9](41)高度贊揚陶公在榮寵面前不貪戀迷惑的高風亮節。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時“直方二臺,惠和千里”,[9](41)其正直嚴明使朝廷內外官員傳頌,恩惠澤陂全郡百姓。父親陶丹“淡焉虛止”,不因做官與否而患得患失。《命子》講述家族光輝歷史的目的,不是為了炫耀,也不是像《喻族歌》為了激勵后人延續祖上榮光,而是強調祖上的功績來源于高尚的德行操守。
大伴氏被天皇賜姓宿禰,是日本飛鳥時代天武天皇八色賜姓中第三等,可稱得上是名門望族。但從家持的父輩起,大伴家族逐漸沒落。《喻族歌》正是反映了家持對每況愈下的家族狀況焦急的心情。《喻族歌》上半部分追述祖先功績,通過高貴出身來表達對家族重興的渴望。“赤心豪不隠,極盡事皇方,仕奉是祖職,立言永不忘,子孫長相繼,世世當延長”,[6](816)強調對天皇的忠心,并教諭族人“凡事心思量”“戲言起禍殃”,最終目的都在于“勿絕祖宗名”“勿負大伴氏”,激勵族人要延續祖上榮光,保持大伴家族的威名不墮并發揚光大。
盡管在創作背景、教諭對象、寫法側重、感情基調、教諭目的等方面,《命子》與《喻族歌》存在不少差異,但是他們的體裁、篇幅、結構、教諭重點、遣詞用句多有不謀而合之處,而且其作者身份、家世背景極其相近,很難用巧合來解釋。
四、《喻族歌》的中國文學溯源
隋唐時期,中國是東亞世界的中心,燦爛的文明廣被四鄰,中日文化交流頻繁。日本多次派遣使者,學習中國的制度與技術,全方位、系統地汲取唐朝先進文明。飛鳥和奈良時期,中國文學成為日本貴族間的風雅。《萬葉集》是在吸收中國文學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關于《萬葉集》與中國文學的交流,小島憲之指出,“雖說交流,但萬葉集處于下游,不會向處于上游的中國文學逆流。”[12](892)考慮到當時的國家實力和文化輻射能力,中國文化更有可能是“源”,《萬葉集》是“流”。
神龜四年(727),家持之父大伴旅人兼任大宰帥,赴任筑紫。大伴旅人就職的大宰府是國家外交部門,負責接待外賓和管理商品交易。漢籍是中國向日本出口的重要物品,所有漢籍皆需通過大宰府審查方可交易。作為大宰帥的大伴旅人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漢文化底蘊,再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接觸到數量眾多的漢籍,漢文化修養更是日益精進。大伴旅人與筑前守山上憶良幾乎同期作為官吏出使九州,他們共同創建了筑紫歌壇,翻譯了大量漢籍的詩語,并加以創新,創造了特色歌語,成為當時流行的風潮。隨父滯居筑紫期間,家持耳濡目染父輩對中國文學的追求,受到中國文化的熏陶。作為大伴家族的棟梁,家持接受了當時貴族子弟的教育,從中國文化中汲取到了豐厚的養料,逐漸具備了深厚的中國文學素養。
藤原佐世于891年奉敕撰寫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本朝現在書目錄》),是日本現存最早的一部敕編漢籍目錄。這部目錄所著錄的圖書大
都來自中國,所以,它還具有“輸入”目錄的性質,可作為研究中國文化在日本傳播的依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里明確記載《陶潛集十》,表明有十卷陶淵明作品集傳入日本。吳春燕也認為“陶淵明詩文早在奈良時代(710-796)便經由《文選》《藝文類聚》等書一起被傳入日本。”[13](93)孫猛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亦論證了李善注《文選》的流布,即“早在奈良時期就盛行于日本。”[14](1499)可見,陶淵明對日本文學的影響從奈良時期開始便已形成。《喻族歌》作于756年,家持作為萬葉時代崇尚熱愛中國文學的詩人,本身具備較高的中國文學素養,有受容中國文學的基礎,應是接觸、學習到了陶淵明的《命子》,并在《喻族歌》創作中融入了中國元素。
五、結語
《喻族歌》是日本萬葉時代家訓文化唯一的代表性作品,與中國魏晉南北朝士大夫家訓的代表作《顏氏家訓》相比,在作者人生經歷、創作背景、文章體裁、篇幅結構、主旨內容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因此,二者難以具備相互借鑒的可能性。但《命子》與《喻族歌》在體裁結構、作者身份、家世背景、教諭重點、遣詞用句等方面多有相似之處,應有借鑒關系。根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記載,曾有十卷陶淵明作品集傳入日本。因為父親旅人和筑紫歌壇的關系,家持蒙學即浸淫中國文化,具備深厚的中國文學素養。前文提到,《命子》著于399年前后,而家持生于717年,顯然只有可能是家持借鑒《命子》、融入中國元素,創作了《喻族歌》這一作品。因此,考慮到當時的國家實力和文化輻射能力以及成書年代,日本萬葉時代家訓文化的中國元素源頭可以追溯至陶淵明的《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