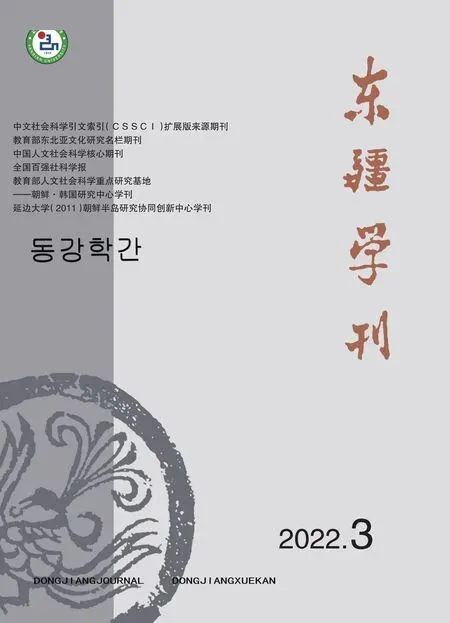論日本歌曲漢譯中的等值與改寫
——以《我只在乎你》為例
金 華,胡冰玥
歌詞即歌曲的唱詞。歌詞蘊(yùn)涵著整首歌曲的宗旨與靈魂,訴說歌曲表達(dá)的思想和情感,使音樂藝術(shù)和文學(xué)藝術(shù)緊密相連。從古至今,歌詞與詩歌都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詩歌用高度凝練的語言,抒發(fā)作者豐富的情感,并具有一定的節(jié)奏、韻律和較強(qiáng)的文學(xué)性。因此,雅克布森認(rèn)為詩歌是不可譯的[1](135),同樣,歌詞的翻譯也具有較強(qiáng)的“抗譯性”。歌詞的翻譯主要有以下兩種形式:即歌詞翻譯和歌詞譯配。前者注重對源語歌詞意義的翻譯,對格式、韻律沒有要求,因此往往出現(xiàn)多種譯法;而后者不僅要呈現(xiàn)源語歌詞的意義,還要實(shí)現(xiàn)入曲演唱,這就需要譯者在譯詞與源語歌詞之間實(shí)現(xiàn)“等值”,而且還要發(fā)揮譯者的主體性作用,對譯詞進(jìn)行一定程度的“改寫”,使之匹配曲調(diào)。因此,一首歌曲往往只有一種譯配詞。
改革開放初期,流行歌曲的風(fēng)潮從中國香港、臺(tái)灣地區(qū)(以下統(tǒng)稱為香港、臺(tái)灣)吹向中國內(nèi)地,鄧麗君是20世紀(jì)80年代華語樂壇最耀眼的歌星之一,也深受日本民眾的喜愛。她從1974年開始,以テレサ テン為藝名在日發(fā)展,憑借《空港》《つぐない》《時(shí)の流れに身を任せ》等歌曲,多次斬獲“日本有線大賞”和“全日本有線放送大賞”。歌曲《時(shí)の流れに身を任せ》發(fā)布于1986年,由荒木とよひさ(Araki Toyohisa)作詞,三木たかし(Miki Takashi)作曲,漢譯歌詞由慎芝譯配。慎芝是臺(tái)灣知名詞作家,具有較深厚的日文和漢學(xué)功底,曾擔(dān)任過多首經(jīng)典歌曲的詞作和譯配者。她的譯文不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日語歌詞的原意,還進(jìn)行了語法、內(nèi)容和文化等方面的改寫來貼合旋律。本文將結(jié)合等值翻譯理論和勒費(fèi)弗爾的改寫理論對譯配詞進(jìn)行分析和探討。
一、歌詞譯配中的等值理論
等值屬于西方翻譯理論范疇。卡特福德指出,“翻譯實(shí)踐的中心問題在于尋求等值成分,翻譯理論的中心任務(wù)在于界定等值的本質(zhì)和條件……為了建立翻譯等值關(guān)系,源語和譯入語文本都必須與功能上相關(guān)的語境特征相聯(lián)系”,[2](93)這強(qiáng)調(diào)了翻譯與語言功能之間的關(guān)系。由此,翻譯中的等值可以基于語言功能劃分為語言等值、文化等值和藝術(shù)等值三個(gè)層次。[3](103)在歌詞譯配中,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實(shí)現(xiàn)語言等值,此外,歌詞中的每個(gè)詞語、每個(gè)句子都承載著自身的文化信息,所以好的譯配詞應(yīng)當(dāng)自然易懂,盡量不出現(xiàn)由文化差異導(dǎo)致的理解障礙,還要搭配旋律,在語音方面實(shí)現(xiàn)藝術(shù)等值。
(一)語言等值
著名語言學(xué)家奈達(dá)主張“形式對等”和“等效原則”。形式對等強(qiáng)調(diào)忠實(shí)原文,使譯文最大限度地體現(xiàn)原文的內(nèi)容和形式。這就是語言等值的第一個(gè)層次,表層意義的等值,即源語和目的語表層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換。如果要保留源語語言形式,就不能改寫內(nèi)容,保持字面意義的等值。在歌詞中,達(dá)到表層意義的等值并不容易。日中兩國語言的表達(dá)結(jié)構(gòu)存在較大差異,既滿足歌曲韻律節(jié)奏,又保留日語語法結(jié)構(gòu)十分困難,以歌詞中的第一句“もしもあなたと會(huì)えずにいたら”為例,該句是假定條件句,譯成中文是“如果沒有遇見你”。這句日文歌詞有14個(gè)音節(jié),但直譯成中文只有7個(gè)音節(jié),如果不做擴(kuò)充則很難配曲演唱,因此在譯配時(shí)譯者增譯了“我該會(huì)是在哪里”。由于歌詞對文字?jǐn)?shù)的嚴(yán)格限制,在譯配中實(shí)現(xiàn)表層意義等值難度較大,因此本首歌的譯配詞中只能找到一處比較符合表層意義等值的句子,即“思い出だけじゃ生きてゆけない”,其大意為“只憑借記憶我無法活下去”,慎芝譯配為“我不能只依靠/片片記憶活下去”。譯配詞中增譯的“片片”屬于對原詞“だけ”的強(qiáng)調(diào),與“只”形成呼應(yīng),生動(dòng)地描繪出戀人對主人公的重要性,實(shí)現(xiàn)了雙語形式和內(nèi)容上的對等。
語言等值的第二個(gè)層次是深層意義等值,即不拘泥于原文的結(jié)構(gòu)和形式,又可以挖掘源語表達(dá)的真實(shí)含義和目的語的相同含義。這與奈達(dá)在后期主張的“等效原則”非常相似。在“等效原則”中,信息可以裁剪以滿足目的語讀者的語言文化上的需要,同時(shí)還要保證源語讀者與目的語讀者所得到的信息一致。實(shí)現(xiàn)這種等效須滿足四原則,即“譯文要有意義;傳遞了原文的精神風(fēng)貌;自然流暢的表達(dá);與原文產(chǎn)生相同的反應(yīng)”[4](146),這種主張解放了譯本形式。這種深層意義的等值在譯配詞中有較多體現(xiàn)。例如原詞“平凡だけど/誰かを愛し/普通の暮らし/してたでしょうか”的大意為“雖然很平凡,但會(huì)愛上某個(gè)人,過著普通的日子吧”,慎芝譯配為“也許認(rèn)識(shí)某一人/過著平凡的日子/不知道會(huì)不會(huì)/也有愛情甜如蜜”。
這句譯配詞雖然未能實(shí)現(xiàn)表層意義等值,但在深層意義上與原詞實(shí)現(xiàn)了等值。在表層意義層面上來看,譯配詞和原詞有多處相異點(diǎn)。一是原詞中“誰かを愛し”是指會(huì)愛上某人,并不是譯配詞中的“認(rèn)識(shí)某一人”。二是原詞中修飾“暮らし”的是“普通”,而譯配詞用的是“平凡”。三是譯配詞中的“也有愛情甜如蜜”無法與原歌詞相對應(yīng),但原詞想要表達(dá)的深層意義卻在譯詞中非常巧妙地傳達(dá)了出來。理由如下:首先,結(jié)合整首歌詞不難看出,詞中主人公對歌詞中的“你”有著深厚的感情,甚至歌頌成“あなたしか愛せない/見えない”。譯者并未將原句“誰かを愛し”翻譯為“會(huì)愛上某一人”,而是譯為“認(rèn)識(shí)某一人”,這就巧妙地把“你”和“某一人”區(qū)別開,也與之后的歌詞中表達(dá)的“你”對主人公的重要性形成呼應(yīng)。譯者增譯的句子“不知道會(huì)不會(huì)/也有愛情甜如蜜”,則是對“誰かを愛し”的發(fā)問,隱藏答案是否定的,實(shí)際上表達(dá)了對“你”以外不會(huì)有甜如蜜的愛情之意。這種深層意義上的增譯不僅滿足了音節(jié)上的不足,還很好地傳達(dá)了原詞的深層含義。此外,譯者將“普通”一詞譯成“平凡”的巧妙之處在于充分考慮到歌曲的易唱性。漢語詞典《漢典》上對“普通”的解釋為“平常、一般”,對“平凡”的解釋為“沒有值得注意的事件、具有通常或重復(fù)的特點(diǎn)”等[5],二者都表示平常的意思。但“普通”側(cè)重于“一般人的水平”,“平凡”側(cè)重于“不突出”。而且“普通”二字的聲母為“p”和“t”,均為爆破音,在這首溫婉的情歌中的適應(yīng)性不如聲母為“p”、“f”的“平凡”。簡言之,上述譯詞雖然做了順序調(diào)換或增譯,且表層意義有所不同,但在深層意義上和原詞實(shí)現(xiàn)了等值,而且達(dá)到了奈達(dá)規(guī)定的翻譯四原則。
(二)文化等值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的載體。不同語言具有不同的文化內(nèi)涵,且會(huì)受到社會(huì)背景、社會(huì)發(fā)展的影響。因此,翻譯活動(dòng)不僅僅是語言層面的,更多時(shí)候是一種源語文化到目標(biāo)語文化之間的轉(zhuǎn)換。要把源語中包含的文化信息等效轉(zhuǎn)換成目的語的文化信息,不僅需要譯者深厚的語言功底,還需要具備對特定語境下的詞語敏銳的文化嗅覺。例如原詞“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直譯為“被你的色彩染上”,慎芝譯配為“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氣息”。
在這個(gè)例子中,譯者并沒有將原文的“色”直譯成“顏色”或“色彩”,而是譯為“氣息”。先來分析原詞,日語中可以見到用原詞中的“……の色に染める/に染められる”來表達(dá)戀人之間相處模式的情況,例如,日本“セキララセクシィ”戀愛網(wǎng)站中一篇標(biāo)題為“彼色に染まる?自分色に染める!?どっち派?”[6]的一文,這里的“彼色に染まる”表示“受到男友的影響,女子的穿搭風(fēng)格和興趣愛好都會(huì)改變(彼氏に影響されて、服裝や趣味などを変える女子)”之意。可見原詞想表達(dá)的意思有以下兩種可能:一種是原詞作者用了唯美表達(dá),即用“色”的原意,意為染上色彩,給讀者描繪了一個(gè)“染上戀人顏色”的唯美場景,但這究竟是什么樣的色彩,什么樣的場景,是非常抽象的,要靠讀者的自我想象來理解。另外一種是,可以認(rèn)為原詞作者想要表達(dá)的是上述網(wǎng)站標(biāo)題中的意思,即主人公受歌詞中“你”的影響很深,從主人公身上能看到“你”的喜好和習(xí)慣。但無論原詞詞作的意圖屬于上述哪一種,譯為“氣息”都會(huì)比譯為“顏色”或“色彩”等詞更能吸引目的語聽眾。其原因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如果是對個(gè)體印象、記憶等的表達(dá),中文一般不會(huì)用“顏色”,而用“氣息”,具體參見表1。表1是北京大學(xué)中國語言學(xué)研究中心語料庫(CCL現(xiàn)代漢語語料庫)中的兩種表達(dá)相關(guān)結(jié)果,在表達(dá)對某個(gè)人的印象、記憶,或通過某個(gè)事物聯(lián)想到本人的時(shí)候,用“你的氣息”表達(dá)有4例,“你的顏色”只有1例。

表1 使用“你的氣息”“你的顏色”的例句
不難看出,如果不是上下文中提到過具體條件,中文一般不會(huì)通過顏色來聯(lián)想到某個(gè)人,而更多是通過氣息來聯(lián)想。例如“你的顏色”中唯一符合條件的例句是由于前文提到了“指磨踵接”所以才出現(xiàn)了后文“筋骨都怕涂上了你的顏色”。但本歌歌詞中并沒有對“你”的性格、行為等進(jìn)行描述,也就缺乏前文具體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譯為“你的色彩”,聽眾就很難對這種色彩產(chǎn)生基本認(rèn)知,例如無法判斷這種色彩屬于冷色系還是暖色系,這種理解障礙使聽眾難以展開想象或產(chǎn)生共鳴。如果譯為“氣息”,則變得生動(dòng)具體,且能做到押韻。因此,此處譯配為“你的氣息”,既消除了文化上的差異,又能讓聽眾沉浸在歌曲中,增強(qiáng)了藝術(shù)感染力。
其二,如果原詞作者并沒有采用上述的唯美表達(dá),只是用日文中的固定搭配“…の色に染める/に染められる”來表現(xiàn)主人公在戀愛中受到“你”的影響很大的話,那么譯詞中的“心甘情愿”就形象地表現(xiàn)出主人公完全傾心于“你”,與固定搭配的含義形成呼應(yīng)。“感染”則體現(xiàn)出主人公此刻的狀態(tài),即主人公生活中都帶有“你”的習(xí)慣、喜好和痕跡,似乎這些已經(jīng)變成自己的一部分,與自己共生。因此,“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氣息”一句譯配得頗為巧妙,一個(gè)詞能涵蓋原詞兩種含義,既消除了文化理解障礙,又實(shí)現(xiàn)了文化等值。
(三)藝術(shù)等值
作為音樂藝術(shù)的語言載體,譯配詞不僅要傳達(dá)原詞信息,還要配合旋律和人聲,才能入曲演唱。因此,與原詞的節(jié)奏、韻律實(shí)現(xiàn)等值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只在乎你》的譯配歌詞雖然并非每一句都和日文原詞字?jǐn)?shù)對應(yīng),但并未影響演唱,并且由于中文譯配詞比原詞音節(jié)少,搭配這首情歌顯得更細(xì)膩綿長。例如“だからおねがい”的譯詞“所以我求求你”,演唱過程中“らお”和“我”屬于同一個(gè)音符,漢字雖然比日文少了一個(gè)音節(jié),但不影響演唱,且演唱時(shí)可以做到一個(gè)音節(jié)對應(yīng)一個(gè)音符,比兩個(gè)音節(jié)對應(yīng)一個(gè)音符的原詞更加悠揚(yáng)、放松。
綜上,《時(shí)の流れに身を任せ》的中文譯配不僅在語言、文化和語音三個(gè)方面實(shí)現(xiàn)了等值,還進(jìn)行了恰當(dāng)?shù)母膶憽?/p>
二、歌詞譯配中的改寫理論
20世紀(jì)70、80年代,西方翻譯學(xué)家的研究重點(diǎn)從文本轉(zhuǎn)移到文化、社會(huì)、政治等因素上。學(xué)者們放棄一味地追求等值,開始從社會(huì)學(xué)、哲學(xué)、人類學(xué)等跨學(xué)科的角度,用新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翻譯,使翻譯研究的重點(diǎn)轉(zhuǎn)向文化方面。文化學(xué)派重視翻譯與文化之間的互動(dòng),主張?jiān)谡Z境、歷史、政治等更廣的社會(huì)層面上研究文化對翻譯的制約,是翻譯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勒費(fèi)弗爾是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他在《為什么要費(fèi)周折談改寫?另類范式中改寫角色的困境》中提出了翻譯“改寫”的概念。他認(rèn)為翻譯即改寫,哪怕最忠實(shí)的翻譯,也是一種改寫。改寫是為某種意識(shí)形態(tài)服務(wù)的,必然會(huì)受到目的語環(huán)境中的主流詩學(xué)、意識(shí)形態(tài)、贊助系統(tǒng)的影響。基于勒費(fèi)弗爾的主張,筆者判斷《我只在乎你》的中文譯配主要受到主流詩學(xué)和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的影響。
(一)委婉化改寫——主流詩學(xué)的影響
歌詞與詩歌存在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中國詩歌講究含蓄,詩歌中蘊(yùn)含的情感與韻味常常不直接言明,而是以一種隱隱約約,似可見又似不可見的表達(dá)方式來達(dá)到雋永的效果,使讀者回味悠長。同樣,歌詞也能體現(xiàn)委婉含蓄的特點(diǎn),徐開彬指出,“80年代的情歌大多婉轉(zhuǎn)悠長,雖常見男女情感的描寫,但多為內(nèi)斂的內(nèi)心感受而少見熱烈的直接表達(dá)”。[7](171-189)這種委婉表達(dá)在譯配詞中也有所體現(xiàn)。例如原詞“今はあなたしか愛せない/見えないの”,可直譯為“現(xiàn)在除了你我無法愛上別人/看見別人”,慎芝譯配為“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絲絲情意”。
中文文化圈對愛的表述相對委婉,一般不會(huì)直接說出“愛”這一動(dòng)詞。歌曲要通過大眾傳媒傳播,如果在歌詞中直接用“愛”這一動(dòng)詞表達(dá)的話難免會(huì)讓聽眾覺得不夠文雅。因此慎芝將原詞“除了你我無法愛上別人”的意思改寫成了“在別人那里我感受不到情意”。筆者認(rèn)為,這樣的處理方式將歌詞中的主動(dòng)示愛處理為被動(dòng)接受,原詞中的“愛”也含蓄地用“情意”替換。另外,《時(shí)の流れに身を任せ》的中文譯名《我只在乎你》同樣體現(xiàn)出了一種委婉,此句在原詞中并沒有對應(yīng)的句子,是由譯者自主增譯的。譯者沒有用意義相近且同樣押韻的“我只會(huì)愛你”或“我只愛上你”來翻譯,而是增譯為“我只在乎你”,同樣體現(xiàn)了一種點(diǎn)到為止的委婉之情,達(dá)到了讓聽眾用心靈去感悟的境界。
(二)女性依附性形象的改寫——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的影響
二戰(zhàn)以后,被稱為女性主義“第二浪潮”的婦女運(yùn)動(dòng)在各國興起。各國女性主義者主張兩性平等、兩性平權(quán)、兩性同格,同時(shí)要求女性在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等方面的平等。著名女權(quán)主義者波伏娃認(rèn)為“婦女必須把命運(yùn)掌握在自己手中”,逃離“客體”“他者”的形象[8](161-165)。她的觀點(diǎn)促進(jìn)了20世紀(jì)后期婦女運(yùn)動(dòng)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女性在社會(huì)規(guī)則下與“美”作斗爭,反對選美比賽,拒絕成為觀賞品。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臺(tái)灣地區(qū)經(jīng)濟(jì)水平的騰飛和社會(huì)轉(zhuǎn)型為女性意識(shí)的覺醒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其間,女性的就業(yè)率和受教育程度不斷提升,但并未得到相應(yīng)的尊重。因此女性呼吁社會(huì)消除對女性的歧視和偏見,強(qiáng)調(diào)女性自身的覺醒,呼吁不要依附男性、從被支配的客體角色中徹底解放出來。此外,中國主流傳統(tǒng)文化將女性美定位為自然和諧、清新脫俗,通常認(rèn)為美是一種綜合氣質(zhì),是由內(nèi)而外散發(fā)出來的,并不是可以像東施效顰那樣輕易學(xué)來或者改變的。傳統(tǒng)文化還講究氣節(jié),女子不應(yīng)為了男女之情尋死覓活,而應(yīng)具備家國情懷等崇高的追求精神。本文中的歌詞譯配完成于婦女運(yùn)動(dòng)高漲的20世紀(jì)80年代上葉,在女性解放思潮和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下,譯詞中也出現(xiàn)了對原詞女性依附性形象的改寫,例如,原詞1“一度の人生それさえ/捨てることも構(gòu)わない”,直譯為“就算是只此一次的人生丟掉也無所謂”,原詞2“綺麗になれたそれだけで/命さえもいらないわ”,直譯為“只要能變得美麗/生命都可以不要”。這兩句對應(yīng)的樂句旋律相同,因此慎芝均譯配為“人生幾何能夠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原詞2表達(dá)的意思是“只要能變得漂亮,生命都可以不要”,這種行為體現(xiàn)了主人公為了容貌可以拋棄生命、迎合他人審美的“客體”角色。這不僅不符合中國的傳統(tǒng)觀念,還與倡導(dǎo)女性活出自我而非委身于異性的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相悖。因此,在對這一句進(jìn)行譯配時(shí),譯者放棄了原詞的意思,采用了原詞1的譯配詞“人生幾何能夠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在原詞1的譯配詞中,譯者也對男女感情做了模糊化處理。原詞1“一度の人生それさえ/捨てることも構(gòu)わない”一句雖然未說明究竟是為了什么可以“丟棄只此一次的人生”,但結(jié)合前后歌詞可以知道是為了這段愛情。譯者在這里將愛情改寫成“知己”,譯配為“人生幾何能夠得到知己”容易讓聽眾聯(lián)想到“人生能得一知己,足矣”的感慨,從而認(rèn)為是主人公在追求一生難求的友情。后句并沒有使用更加貼近原詞意思且押韻的“即使丟失了生命也不可惜”,而是改寫成“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這樣一來,一方面對“丟失生命”之行為做模糊化處理,將原詞中體現(xiàn)主觀意志的他動(dòng)詞“捨てる”轉(zhuǎn)化為不以個(gè)人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失去”,另一方面結(jié)合前句的“人生幾何能夠得到知己”,轉(zhuǎn)移了該句的重點(diǎn)。展現(xiàn)出來的不再是原詞那個(gè)為了愛情情愿放棄生命的消極形象,而是一個(gè)要窮盡一生力量尋求知己的積極形象。這種精神面貌的改變,使其更符合現(xiàn)代社會(huì)女性追求人格獨(dú)立的價(jià)值觀。慎芝在譯配詞中降低了原詞的負(fù)面傾向,將消極的情感平淡化。這種改寫更貼合目的語的受眾人群,展現(xiàn)出一個(gè)用情至深,卻不失自我的主人公形象,自然也就更容易廣泛流傳。
三、結(jié)語
歌詞譯配涉及音樂、語言、文學(xué)等諸多方面,是一項(xiàng)極其特殊的翻譯工作。譯者不僅要追求語言、文化、語音等藝術(shù)性等值,還要進(jìn)行符合音樂旋律和時(shí)代潮流的改寫。對歌曲譯配來說,等值和改寫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既是相互對立、相互分離的矛盾體,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誰也離不開誰的統(tǒng)一體。一首歌曲的譯配不僅能傳達(dá)原曲的思想,還能使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訴說譯者對語言文化現(xiàn)象的理解。分析研究歌曲的譯配,不僅能提高譯者自身翻譯水平、加深對源語文化的理解,還能提高文學(xué)素養(yǎng)和審美水平,獲得多維度的鍛煉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