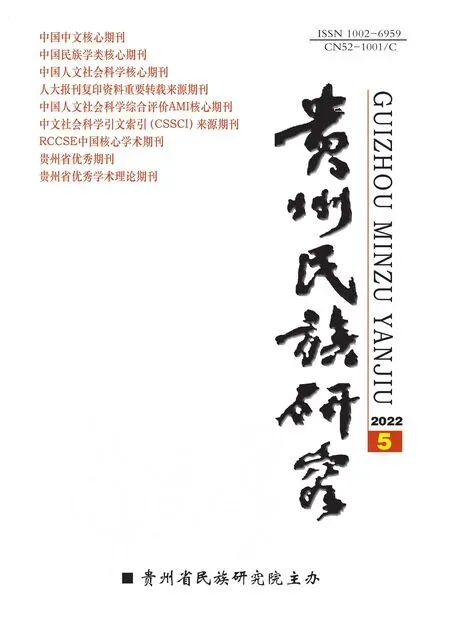土司文化遺產的復合性、多元價值及其實現路徑
李 然
(中南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湖北·武漢 430074)
土司文化遺產是土司制度運行所產生的系列歷史遺跡和歷史記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不斷加深對中華文明悠久歷史和寶貴價值的認識”“讓文物說話、把歷史智慧告訴人們,激發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1]。土司制度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制度創舉。它體現了中華民族處理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和諧共處的歷史智慧,是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貢獻。但土司文化遺產的內涵、內在結構與要素、價值和保護利用方式有待更深層次的提煉和總結。本文對中南地區湖北咸豐唐崖土司城址、湖南永順老司城;西南地區四川馬爾康卓克基土司官寨、云南梁河南甸宣撫司署;西北地區甘肅連城魯土司衙門(永登土司府) 等進行田野調查和比較研究,以期對土司文化遺產的復合性特征、多元價值及其實現路徑進行總結與闡釋。
一、土司文化遺產的復合性
土司文化遺產是土司文化在當代的遺存。李世愉先生提出:“土司遺址與長城、故宮、布達拉宮、大運河等不同,它是中國文化遺產中獨特的一種類型,土司文化遺產與其他各項文化遺產共同構成了燦爛的中華文明”[2]。但“學界還未對土司文化遺產基本概念進行界定”[3]。“遺產既指那些有形的遺存,包括自然和文化的環境、景觀、歷史場所、遺址、人工建造的景物;亦指無形的遺產,包括收藏物、與過去相關的持續性的文化實踐、知識以及活態化的社會經歷”[4]。但在實踐操作中,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系列土司文化遺產以土司城址作為申報主體,遮蔽了土司文化遺產的豐富內容和深刻內涵。鑒于土司制度運行中王朝國家、民族首領、各族民眾的多主體參與,漢文化、非漢族群文化的交融并置,土司文化遺產具有鮮明的復合性特征。所謂文化復合性,是指不同社會共同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內部結構生成于與外在社會實體的相互聯系,其文化呈雜糅狀態。文化復合性的構成表現為“內外上下關系”。所謂“內外”,即指社會共同體與文化界線兩邊的聯動;所謂“上下”,則是指由于歷史中的社會共同體與文化通常存在規模與影響不一或“尊卑”不等的“差序”。因此,跨社會或跨文化關系通常也具有深刻的等級內涵[5](P9)。借助文化復合性的理念,可以達成對土司文化遺產形態、結構和內涵的深入認識。
(一) 遺產形態多樣
土司文化遺產是一個整體,但在遺產保護社會語境中,會涉及遺產形態分類和理解。“這與確認、創造和產生遺產背景的差異有關,也與反映在遺產中的關系和對遺產的認知有關”[6](P52)。土司文化遺產形態涵蓋了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土司文化遺產物質樣態多樣,包含土司相關的城址、官署建筑、碑刻牌匾、墓葬、印章、譜牒文獻、用具、禮器、兵器、服飾等歷史遺存。現存土司城址及官署已大多被確立為文物保護單位。全國現有土司城(官寨) 19處,土司衙署建筑群(莊園) 50處,土司墓葬(群) 23處,單獨建筑群6處,其他3處,共計101處。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9處,其中土司城、官寨9處,土司衙署建筑群或莊園7處,土司墓葬(群) 1處,單獨建筑2處;另有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處,縣市級文物保護單位62處[7]。
武陵山區的唐崖土司城址、永順老司城、貴州遵義海龍囤,川西地區的卓克基土司官寨和甘青地區的魯土司衙門,滇西南的甸宣撫司署等堪稱土司城址和衙署的代表。墓葬是土司禮制的重要物證。如永順老司城墓群集中于司城紫金山、雅草坪、帕桶湖三處,共有土司及其貴族墳墓109座。碑刻牌匾是土司功勛和德行的標志性遺存。唐崖土司城址的“荊南雄鎮”功德牌坊、張王廟“公頌重新”碑;老司城翼南牌坊、宣慰使彭泓海德政碑、紫金山彭公德政碑以及20處石刻,連城魯土司明代牌坊等,記錄了王朝對土司的旌表和土司的自我夸耀。土司印章是王朝授予土司權力的歷史物證。如唐崖長官司印、卓克基長官司印、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印、清南甸宣撫司署方形銅印、木制官銜牌及民國印章等。譜牒等文獻是土司對自身歷史的書寫,如唐崖土司的《覃氏族譜》,南甸土司署的“三大款”底冊、《南甸司刀龔氏世系宗譜》等。
土司生活用具、禮樂宗教用具和軍事器械是土司身份和地位的彰顯。如南甸土司的土司座椅御扇牌、“萬民傘”等;永順老司城的朝廷“回賜”金銀器,帶有“永順司置”“宣慰使司佳器”等官職銘文的瓷器;卓克基土司官寨收藏的寶劍、矛、頭盔、土槍、戰袍、馬鞍等武器裝備。土司服飾是土司官制的文化表征。唐崖土司夫人服飾以五品誥命夫人使用的品紅為底色,繡有明朝流行的纏枝蓮。
土司文化遺產還表現為土司歷史文獻、傳說故事、信仰、民俗、飲食等非物質形態文化遺產。土司歷史文獻一是明代以來的官修正史、文人筆記、方志的文獻記載。二是碑刻銘文、牌匾和楹聯的自我表達,如南甸宣撫使司署的“衛我邊陲”“南極冠冕”匾額,橫梁題刻“欽賜花翎三品衛世襲南甸宣撫使司宣撫使刀定國暨閣司紳民重建”,楹聯如體現土司治理思想與愿景的“宣化萬民群省咸遂,撫綏四境百姓為心”“偃武修文唐虞盛世,此矛彼盾叔季人情。”三是圖片等影像記錄,如南甸土司刀定國拍攝的修筑橋梁,開墾農田,修筑道路的照片。土司遺產地留下許多有關土司的傳說。如永順老司城彭翼南抗倭傳說、卓克基土司改“桑”姓傳說、“瓊部大鵬卵生嘉絨先民”神話傳說、神山傳說故事等。
散布于各地的土司文化遺產表現為不同的文化內在結構、遺產景觀和文化符號。它們是王朝國家、民族首領與各族民眾長期互動中形成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的物質遺存和歷史記憶,其表征自會呈現為多樣態。土司文化的物質文化遺產或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文本化的物”也是“物化的文本”[6](P17),體現出物質、制度和精神多種形態的混融性。
(二) 地域性與民族性并置
土司文化遺產是區域文化的經典。土司文化遺產因其自然生態,與中央王朝和轄地內各民族的內外關系,以及發展歷史軌跡不同,物質遺存和歷史記憶存在著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土司城址及相關建筑形態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土司制度推行地區涵蓋了西南山地、青藏高原、云貴高原等地區,受地理環境、人文歷史、地緣政治、區域族群關系等因素的影響,文化各具特色。西南山地的唐崖土司城、永順老司城等土司城池普遍因山采形,就水取勢,建筑依山而建,鱗次櫛比,氣勢恢宏。青藏高原東部的卓克基土司官寨建筑的高寒地域文化特征明顯。官寨選址朝向上坐東北朝西南;建筑材料采用片石壘砌而成,墻體厚,留小窗,減少屋內熱量損失,抵御寒冷氣候。南甸土司官署建筑和用具帶有濕熱多雨熱帶特征。官署建筑群用石頭等材料墊高,內部鋪設石板,保持清涼與干燥;椅子多用藤蔓制作,中間布滿空洞,便于散熱。連城魯土司地處西北河谷地區,夏季降水豐富冬季寒冷干燥,衙門內部建造了一套獨特的供暖系統與排水系統。
土司文化遺產作為民族首領集團行動的歷史遺存,又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如南甸宣撫司署保留了傣族和白族文化特色。土司署飛檐頂端飾有傣族傳說中龍頭魚尾的瑞獸,會客廳后方有傣族特色“太陽門”及白族特色的“三滴水”照壁。
土司相關民俗文化也是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結合的產物。如青藏高原東部川西卓克基土司服飾以嘉絨藏裝為主。官寨周邊地區嘉絨文化和土司節日深度交融。斯古仁欽波就是由一個宗教節日變為一個慶祝土司受封的節慶。官寨各式茶壺是嘉絨地區飲“馬茶”的習俗和“茶馬貿易”的歷史見證。
(三) 多元民族文化融會
土司群體為了處理好與中央王朝和治下各民族民眾的上下關系以及周邊各民族的內外關系,一般持包容開放的文化心態,所以土司文化遺產具有多元民族文化融會的特點。南甸宣撫司署衙門表現出漢族、白族、傣族三個民族的建筑特點,同時也有現代西方文化元素。宣撫司署是土司邀請劍川白族工匠依照漢式布局修筑而成,卻又留下了劍川特有的飛檐裝飾“三滴水”形白族照壁。土司印章多鐫刻多種民族文字,如兩枚南甸宣撫官印為漢滿兩種文字銘文,世襲鎮康州印除用滿漢兩種文字外,另有一行字體較小的少數民族文字,疑是蒙古文或藏文[8](P117)。永順老司城遺址周邊佛道廟宇林立,彭氏土司既供奉彭氏“先祖土王”,也供奉關帝、城隍廟、五顯祠、祖師殿等道教神靈。土司文化遺產的多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融會,體現了土司群體處理與中央王朝和各民族的上下關系和內外關系的文化智慧。
(四) 大傳統與小傳統互滲
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和邊疆民族所形成的一種有中華帝國自身特色的上下關系。他們都有一個需要面對的共同問題,即,既要跟遠方強有力的帝國形成關系,又要跟更遠的那些相對軟弱的比他們還要“蠻夷”的“蠻夷”形成關系[5](P409-410)。處于“中間圈”的土司必須熟練采納與駕馭大傳統與小傳統、中原正統文化與邊疆邊緣文化,來維持這種“上下關系”。如土司城或衙署建筑大多遵循王朝禮制營建,但又保留地域特征。聚落形態上通過對國家“正統”的認同來強化土司在地方社會的權威。南甸宣撫司府衙正堂上懸“德馨邊圍”牌匾,正殿選用栗木,左廂用椿木,右廂用楸木,取諧音“正立春秋”,寄寓土司希望江山永固的美好心愿。土司“四院”與側房懸掛的牌匾與楹聯,為宣撫司署漢族師爺與深得土司信任的熟識漢文化的傣族文人所做,寓意深遠。中堂雕刻著中原文化特色的王羲之愛鵝、陶淵明愛菊、周敦頤愛蓮、葉公好龍、伯樂相馬、何靖愛梅、隱公釣魚、明皇愛月“八愛圖”。公堂懸掛“衛我邊陲”牌匾,彰顯“附輯諸蠻,謹守疆土”的保衛邊疆的權力與義務,會客廳懸掛“十司領袖”牌匾,凸顯自身在滇西土司中的領導地位;家堂中央設神龕,掛天地君親師牌位,香案桌既供有光緒皇帝,也有刀定國及兩位末代土司龔綬及龔統政畫像。卓克基土司官寨整體為漢式四合院布局,但屋頂采用漢式三角桁架構成的懸山式屋頂和嘉絨傳統的密梁式黏泥夯筑平頂兩種結構形式。
土司群體仰慕漢文化,又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形成一種地域特色的治理方式,使得土司文化遺產根植于當地文化傳統之中。如南甸土司“一手尊孔,一手倡佛”。南甸土司崇尚漢族文化,不但司署按照漢式風格打造,自身也積極學習儒學。因轄地與東南亞相接,而又深信南傳上座部佛教。唐崖土司將土司城四周山峰以中原傳統文化中的“四象”命名:西為玄武山,東為朱雀山,北為白虎山,南為青龍山;建筑格局遵從“坐北朝南”“中軸對稱”原則,表達對儒家文化中“禮”的傾慕與效仿。中央王朝對土司及子弟進行儒家文化教育,土司既通過對中原文化觀念的習得來宣揚文化優越性,也借機彰顯土司權力。牌坊上雕刻著體現漢文化思想的槐蔭送子、漁樵耕讀、魁星踢斗、獨占鰲頭,也鐫刻著展示地域特色的“土王出巡”。卓克基土司索觀瀛熟讀“四書五經”,“蜀錦樓”土司書房收藏有大量的漢文和藏文典籍,但官寨的文化元素和符號多源于嘉絨文化,官寨“壘石而居”“厚墻小窗”,白藍紅黃綠五色裝飾、藏式家具具有濃厚的嘉絨文化氛圍。
(五) 傳統與現代交融
遺產屬于歷史時態的延續紐帶,一些土司存續于古代王朝國家和現代民族國家,經歷了20世紀上半葉系列戰爭、革命以及經濟社會變革,土司文化遺產體現出傳統與現代交融的特點。滇西南甸宣撫司一直延續到民國末年,宣撫司署建筑不但具有漢族、傣族和白族傳統文化特色,還有近現代西方文化元素。南甸土司府公堂現存有土司家族購買的德國央絲相機與美國奧古斯相機、英國銀制咖啡壺等,土司生活的二院、三院內也安裝有英國彩色玻璃。清末民國時期南甸土司日常中式長袍馬褂與西洋裝并穿,現還存有身穿西洋服與官服的第二十八代土司龔授照片。
部分土司還為近現代中華民族抵御外侮和獨立解放作出了獨特貢獻。抗日戰爭中,卓克基索觀瀛與大頭人們向省政府捐獻白銀和鹿茸、貝母等中藥材,表達支持政府抗戰的決心。國民政府“中央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為其親自題寫“獻金抗日”匾額。卓克基土司官寨見證了藏族地區紅色革命進程。1935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在土司官寨居住一周,并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通過《告康藏西番民眾書——舉行西藏民族革命運動的斗爭綱領》,為卓克基土司官寨遺址打上了紅色烙印。
二、土司文化遺產的多元價值
(一) 普遍價值
土司制度是古代中華民族處理不同民族、多元文化和衷共濟、整合凝聚的制度創新,屬于人類創造精神的杰作。土司文化遺產是中華文明這一超大文明共同體超長持續的見證和記憶。《保護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公約》 認為,文物古跡、建筑物和遺址必須從歷史、藝術或者科學、審美、人類學等角度上觀察,具有普遍價值。遺產需要人類精神的附會,人類情感的滲透,人類審美的參與,以及人類認知的體驗[6](P33)。土司文化遺產的整理詮釋、保護與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也是一種政治表述。每種遺產都屬于特定民族群體的集體表述與記憶。遺產認知和認定過程也是一個社會動員和凝聚共識的過程。經世界遺產委員會認定、列為土司系列世界文化遺產的唐崖土司城、湘西老司城和貴州海龍囤,在歷史時段、地理環境、族群屬性、行政級別、功能構成、聚落形態、建筑風格等方面表現出特有的共性特征和內在關聯,顯著地體現出系列遺產具有的整體性特征,具有普遍性價值[9]。在政治層面上,土司文化遺產與中華民族認同以及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相關聯,反映了古代中國在多民族聚居地區“齊教修政”“因俗而治”等治理思想和兼容并包、和衷共濟的政治智慧。如“荊南雄鎮”牌坊反映了唐崖土司與中央王朝的文化互動,體現了“土司對中央王朝國家權威的理性接納,進而上升為國家認同”[10]。文化層面上,多元一體的土司文化遺產也體現了漢文化、少數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既是中國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也為當今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和諧共處之道提供了歷史借鑒。因此,土司文化遺產是元明清時期“大一統”政治思想與尊重不同文化價值的“因俗而治”理念在中華大地協調運行的產物。存留的文物古跡、建筑、遺址、景觀及其相關知識與實踐,為土司制度建立到改土歸流土司消逝的歷史過程提供了獨特的見證。
(二) 歷史價值
土司文化遺產“具有見證、證實、反映元明清時期中央王朝經營邊緣族群以及邊緣族群社會文化生活的歷史價值”[11]。土司制度是土司文化遺產的核心。土司制度之下,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傳統文化、生活習俗得以保留發展,邊疆民族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也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得以培育,實現了多民族文化的共處與包容,是王朝國家與土司集團的雙向認同。這樣一種將國家統一與少數民族自我治理相結合的國家治理手段,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獨特貢獻。每一處土司文化遺產都是土司制度興衰和區域社會與國家互動的歷史見證。如滇西南甸土司文化遺產保留了元明清至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邊疆民族共同開發、治理滇西的重要遺存與歷史記憶。湘西老司城始于唐末五代,經歷了“羈縻制度”“土司制度”和改土歸流的完整過程。卓克基土司經歷了元、明、清、民國、新中國之初五個時期,成為消失最晚的土司之一。完整的土司成長與消亡史使其成為研究土司制度的重要對象。這對于研究中央王朝邊疆治理政策、中華民族共同體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有重要歷史意義。
土司文化遺產是土司轄區經濟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老司城遺址中的衙署區、苑墅區、宗教區、墓葬區等和周圍烽火臺、軍事設施、石碑銘刻都是探尋土司社會結構的重要線索。南甸土司署“三大款”底冊等契約文獻,記錄了土司治下德宏地區封建經濟運行模式,老傣文“貝葉經”對于研究土司宗教信仰與上座部佛教在西南地區的傳播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南甸土司所攝照片是西南邊陲清末與民國初年的生產生活狀況的珍貴影像資料。永順老司城墓地出土的彭世麒、彭宗舜、彭翼南及其眷屬的墓志銘、出土瓷器是研究土司社會生活史的珍貴史料。
土司文化遺產是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重要史料。唐崖土司城址的藝術物象的藝術觀念、藝術形制與儒家文化和漢地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儒家文化的物化和對漢地藝術的仿象[12]。甘肅連城魯土司文化遺產有蒙、漢宗教信仰表述,有滿、蒙、漢生活習俗的交織,有明清官署建筑與民族地域特色建筑的結合,是研究漢族文化、滿蒙文化在甘肅地區交織傳播的重要例證。
(三) 藝術價值
土司城遺址是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城市營建藝術理念和技藝的結晶。唐崖土司城遺址“在整體選址、整體布局、土王墳墓營建、排水系統設計等方面均體現了土家族的獨特智慧,反映了土家族人敬畏自然、順應自然、巧妙借用自然的自然觀,以及追尋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營造智慧”[13]。唐崖土司城選址上“負陰抱陽”,山水環繞,表達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建筑格局的“圍合內向”“序列關系”“中軸對稱”展現了中國古代建筑的禮制之美;石刻、牌坊、墳墓的建筑形制與雕刻藝術呈現了技藝之美。老司城周圍地勢峻峭,但功能分區齊全、布局科學,體現了土家族城市營建中注重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核心價值,體現了西南山地在城市規劃、建筑技術和藝術創作上漢文化與土家族文化的結合,是西南山地城市的優秀范例。
“土司文化遺產具有讓人認知和體驗美的藝術價值”[11]。卓克基母官寨的修筑方式、布局、裝飾都體現了嘉絨文化獨特的審美觀念,被美國著名作家索爾茲伯里贊譽為“東方建筑史上的一顆明珠”。母官寨由一座石砌五層藏式民居和一座石砌五層碉樓組成,官寨坐西北朝東南,是一座仿漢式的四合院建筑,西面碉樓高聳。因其采用了漢藏結合的建筑風格以及嘉絨地區獨特的建筑方式,為當代建筑、藝術、藏文化等專業愛好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點。南甸土司建筑將漢族、傣族與白族傳統文化與西洋玻璃裝飾結合,體現出中西合璧、傳統與現代交融之美。
(四) 教育價值
土司文化遺產可以樹立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價值。土司文化遺產的挖掘整理和宣傳弘揚,有利于深刻認識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4]重要論述。如“唐崖土司遺址的牌坊作為中央政府與地方土司交往互動的產物,是國家權力施于地方社會治理方略的文本書寫。在地方社會的牌坊建造以及民間傳說敘事中,通過朝廷征調、協助平叛等重大歷史事件,唐崖土司的牌坊表達了對國家權威的理性接納,成為西南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典范”[10]。
土司文化遺產為愛國主義教育提供了好素材。湘鄂西土家族土司、廣西壯族土司明代抗倭保家衛國的故事廣為流傳。抗日戰爭后期,南甸土司龔授投身抗日,成立軍民合作站供應軍需品支持抗日。龔授還曾致電李根源表達抗日之決心:“我司世受國恩,同仇敵愾,當師體德意,死抗戰,與疆土共存亡”[15](P114)。盈江土司刀京發表了《滇西土司否認企圖獨立》[16](P116)的聲明。紅色文化扎根于卓克基土司官寨,使其兼具歷史教育與紅色教育雙重教育功能。上述歷史記憶和歷史遺存是增強各民族國家認同教育的好案例。
(五) 資源價值
土司文化遺產所反映的國家與地方、土司與各民族共同開發建設家園的歷史經驗和智慧,是當下民族地區治理創新的歷史源泉。土司制度體現了古代中國大國治理的政治智慧,顯示了中央王朝“齊政修教、因俗而治”的民族治理理念。這種民族治理理念是對“大一統”的追求、對少數民族權利與文化的尊重,保護了多元文化,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促進了當地政治、文化、經濟、文教的發展。土司制度對民族地區政治建設有借鑒意義。南甸土司與元明清三代王朝和現代民族國家均保持了良好的關系。民族地區因土司制度賦予了極大的權力,同時也承擔了守衛疆土,建設家園的義務,并保持了對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的高度認同。卓克基土司。觀瀛索鼓勵漢地商人來此經商,保護過往川西商旅商民。當地立有漢藏雙文功德碑,紀念索觀瀛為卓克基地區商貿的繁榮作出的貢獻。
土司文化遺產的多元性、豐富性、民族性和不可再生性,決定了其極高的旅游資源價值。通過對遺產的參觀,對遙遠的空間與悠久的時間的文化遺存的感知,滿足人們懷舊的情感需求,是全球遺產旅游的重要動力。永順老司城遺址與咸豐唐崖土司城址、貴州遵義海龍囤土司遺址等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使其成為最權威、最有公信度的一個旅游品牌,并已全部建成為國家AAAA 級旅游景區。
土司文化遺產是培育民族團結進步、宗教和諧的重要載體和平臺。卓克基地區所在的川西地區歷來都是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地區,古代有茶馬古道相連,藥材貿易繁榮一時。這里的藏族、羌族、回族、漢族等多個民族相互交往,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土司官寨融合了多民族的文化元素,是各民族和諧相處的最好見證。整體采用了四合院式的建筑風格,藏漢結合,還包括一些羌族建筑的文化元素。如“碉樓”“壘石而居”等都是藏羌兩個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魯土司文化遺產蘊含了蒙古族、滿族與漢族等多元文化因素。土司府內修筑儒家學堂,學漢文化;又修建藏傳佛教寺廟,積極推崇道教文化。飲食文化既有清廷官署風格,宴席菜肴也為蒙古與內地風格相融,婚嫁中有諸多漢地婚俗習慣,喪葬保留了蒙古族特點也吸收了漢地喪葬禮儀。這些反映各民族相互交融、宗教和諧發展的文化遺產是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的重要資源。
三、土司文化遺產價值實現的多重路徑
(一) 土司文化遺產價值再認識
土司文化遺產文化內涵與價值的再闡釋是增強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覺的重要手段,是一切保護和利用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強古代遺址的有效保護,有重點地進行系統考古發掘,不斷加深對中華文明悠久歷史和寶貴價值的認識。”[1]遺產與人們對其認知、審美和崇敬有關。遺產語境中的遺產敘事是一個遺產地社會文化再生產的過程。土司文化遺產是一個復合的文化遺產體系,其保護與開發尚存諸多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司文化遺產的現代價值尚未充分挖掘。當前應結合遺產學的理論,與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展開對話,加強土司文化遺產現代價值的挖掘與闡釋。第一,充分認識土司文化遺產對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價值。土司制度及其實踐,體現了少數民族自我管理與國家統一行政管轄的有機統一。土司制度實施過程中,土司及其民眾促進了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中央政府以及土司區外通過朝貢、商貿發生了密切的經濟往來,以及文化上的互動與采借、交融。土司制度的實施鞏固了邊疆統一和地方穩定,促進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土司制度促進多民族國家內各民族的和諧相處,體現中華文明的智慧,要利用土司文化遺產向世界講好中國民族團結好故事。土司既是本民族文化代表,也積極吸收、傳播漢文化,各地土司文人輩出,既是凝聚民心,促進地域認同和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典型案例,也是國家認同教育的重要資源。第二,土司文化遺產見證了土司制度的興衰成敗。通過遺產反思土司制度和土司集團的封閉性、保守性、割據性等問題,可以為今天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歷史鏡鑒。第三,發掘土司文化遺產中蘊含的優良傳統,促進家風教育。如鄂西《鄂西卯洞司志》的《向氏家訓》,利川土司《覃氏族譜》等保持清白家聲、忠信、敬祖先、孝父母、敦手足、正家室、勤耕讀、睦族鄰、擇師友、維風俗、戒淫行、崇禮讓等優良傳統道德的崇尚與訓導,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極具啟示意義。
(二) 創新土司文化遺產保護理念、模式與措施
土司文化遺產要素多,分布地域廣,應吸收“文化景觀遺產”“文化線路遺產”等前沿遺產類型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遵循主題性、整體性、綜合性、動態性、生態性保護原則,實行文化遺產保護與民生改善相結合的策略,打下文化遺產創造性轉換的基礎,引導和培育各族群眾對土司文化遺產的自信。
鑒于土司文化遺產的整體性,遺產持有者及其社區、社群的主體性、遺產的可持續性,遺產管理部門、旅游企業應探索與遺產地社區與民眾共建共享的遺產開發利用模式。土司文化遺產保護要堅持政府主導、人民主體的基本原則,重視發揮多元參與主體功能,提升參與能力,創新參與方式,樹立多元主體協同合作理念,建立激勵融入與規范退出機制,滿足多元利益主體訴求,提升遺產保護管理績效。
土司文化遺產的保護還應利用數字化技術提升保護措施的科學性和傳播的智能化。對兼具物質形態和非物質形態的復合性土司文化遺產,采取靜態保護和動態保護相結合的方式,如文物保護、博物館保護、土司遺址公園建設等保護模式,并借助虛擬技術、數字化技術、3D打印技術應用于土司文化遺產的保護、修復與再現,如制作土司朝貢、商貿、征戰、交游、官署營建等數字電子地圖等,探尋數字人文時代土司遺產的數字平臺建設及其可視化和智能化呈現。這些也是確保文化遺產所具有的突出的普遍價值以及完整性和真實性得到保持或提升的關鍵。
(三) 文旅融合,遺產保護與社區發展共贏
土司文化遺產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打造區域旅游文化品牌,是實現遺產保護與遺產地社區共贏的關鍵。我國遺址旅游開發多采用遺址博物館、遺址旅游區、遺址公園、創意產業和考古活動參與等五種模式[17]。發揮土司文化遺產的文化資源價值,促進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轉化,發展旅游、影視和文化產業,可以實現土司文化遺產價值的最大化。當前土司文化遺產旅游一是將遺址游整合于縣域特色旅游路線之中,二是復原再造土司城遺址,三是新建土司文化商業街、土司文化小鎮,四是注重土司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的整合,豐富旅游產品與服務。如卓克基是阿壩藏羌文化走廊上的重要節點。當地政府將整個土司官寨與西索村規劃為紅色文化感悟區、土司文化鑒賞區、民俗文化體驗區、游憩休息區,使其成為全國藏族特色民居集中展示區和嘉絨藏族文化旅游最佳目的地。
土司文化遺產需要進行創造性轉化,提升旅游開發品質。一是創作一批如《塵埃落定》 《唐崖夫人》等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深厚底蘊的土司文化小說、詩歌、戲劇、影視作品。二是緊扣現代審美情趣和消費特色,研發土司文化相關歌舞、文化節、民俗、服飾、婚嫁、餐飲、工藝品等文創產品,增強土司文化遺產旅游、文創產品的觀賞性和可體驗性,滿足觀光與深度旅游訴求,適應人們日益增長的娛樂、教育、探奇和審美的體驗需求。三是豐富土司文化遺產的表現形式。通過改造、復原土司遺產周邊人文和自然景觀風貌,塑造特色土司文化景觀,賦予遺址及其周圍村寨、古鎮以文化意義,增強土司文化遺產景觀的“可讀性”,創造一個“會說話的環境”。這種景觀空間需要現實場景中的遺址、村落、雕塑、圖片、民俗和技藝的展演,以及虛擬空間的數字化產品共同營造。四是細分游客市場需求,創新旅游產品主題、方式,內容,建設差異化的遺產旅游景區。如將土司遺址景區建設成研學旅行、夏令營、冬令營等,作為青少年國情教育、民族團結進步教育的研學旅行基地。遺產地發展旅游是實現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文旅融合既能激發遺產地社區、遺產持有者保護土司文化遺產的積極性主動性,增強文化自信和社區認同,也能為他們增加收入,脫貧致富。如永順老司城所在司城村村民普遍參與旅游開發,共享遺產紅利,也體現了“原居民利益保障第一”的原則。
(四) 遺產賦能,文化惠民
地方政府要合理定位土司文化遺產的功能與地位,應尋求遺產有效保護與社會發展“雙贏”的途徑。第一,利用土司文化遺產開展傳統文化教育。如編制地方校本課程,建立研學基地、傳承基地等,培養青少年的家國情懷。第二,利用土司文化打造地方文化品牌,將土司文化遺產樹立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如圍繞土司文化遺產打造文學作品、演藝劇目、文化創意產品等。第三,利用土司文化遺產促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如建設遺址公園和博物館,為地方民眾提供休閑娛樂、科普、美育服務。第四,利用土司文化遺產促進特色村鎮建設。大多土司遺址與所在的鄉村和集鎮相互嵌入,在土司文化遺產的保護開發過程中,培育特色產業,建設遺產小鎮,可以使所在村寨或城鎮的特色風貌得到有效維護和修復,文化底蘊得到彰顯。遺產地通過文化遺產的申報、保護與利用,培育和帶動遺產地村落民眾的文化自覺意識、社區自我組織自我服務能力和市場經濟經營管理能力,將形成一個新時代的鄉村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與利用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