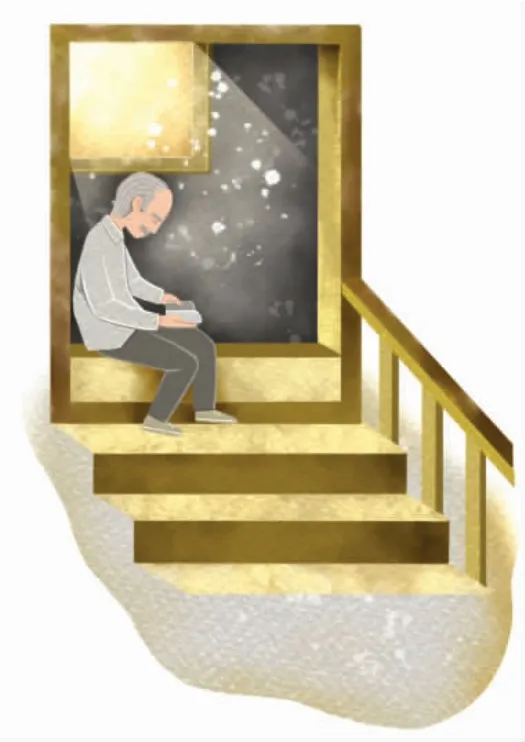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傳奇
文 龍游縣第二高級中學 夏 天

從我記事起,曾祖父就好像總在小院里——小院很簡陋,但不破敗,干干凈凈,樸素得很。除了那間老式的閣樓,只有一棵參天的棗樹陪著曾祖父,或許它以前并沒有那么高的樹冠、那么粗的枝干,只是歲月陪伴著它長大,就像曾祖父陪伴我的祖父,陪伴我的父親,陪伴我長大一樣。
閣樓的小門底下有道門檻,那是曾祖父最喜歡待的地方,他一向不愛走動,于是坐在門檻上讀書成了他最喜歡做的事情。老花鏡、透過棗樹的枝葉灑下來的光、清晨帶著濕意的空氣、一本泛黃的舊書,就是曾祖父每天的伊始。“他年紀那么大,哪里看得清。”家里人都這么說,但是他們知道什么呢!“這些字啊,阿公早放進這里了。”曾祖父看著一臉稚嫩的我,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心口,笑意從嘴角氤氳到眉梢——“阿公”是我老家對曾祖父的稱呼,他很喜歡在年幼的我面前這樣自稱。
曾祖父還很喜歡書法,小院的空地上放著一張烏木桌,那是他的寫字臺。筆、墨、紙、硯,最簡單的文房四寶,到了曾祖父的手里,卻如水般的自由,幾滴墨暈染開,宣紙上綻放出烏黑的花。曾祖父常常在院子里一坐就是一個下午,曾祖母喊他吃飯,不聽;祖父找他說話,不理;小孩繞著桌角跑,他不聞不問。一個字寫不好,他就練到星斗漫天、素月清輝。夏日的蟲鳴擾不到他,秋夜的風霜吹不動他,他像一張掛在墻上的弓,那么堅韌,那么鏗鏘,小院就是這堵墻,除了他自己,好像就沒有什么能撼動他。
曾祖父出生在一個普通的佃農家里,家里兒女多,他自然沒法去上當時的私塾。聽祖父說,曾祖父是天天蹲在人家教書先生的房檐下學的讀書寫字。除了打草喂豬、背水下山,曾祖父還得下田幫忙,那個時代的男孩總要辛苦些,多干點體力活。一天忙忙碌碌,汗流浹背。晚上空下來,曾祖父就趁著星星、月亮的微光費力讀著向別人借來的書,白日里稍微有點空照例去蹲著聽課。就這樣,曾祖父成了家里的第一個“讀書人”。憑著一股闖勁,曾祖父剛滿二十那年便進城去了。在城里打拼自然不容易,是一段啃硬饅頭、睡破房的艱苦日子。妻子是山上老家送下來的,第一個兒子是在城里生的,夫妻倆為了兒子勤勤懇懇打拼,生活終于有了起色。可惜也可恨,世事不遂人意,那一年日軍打到了東南方,為了保護家人,曾祖父風風火火地帶著妻兒趕回了老家。還是愣頭青的年紀,曾祖父卻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一夜長大。我們家沒人知道曾祖父的父母有沒有熬過去,只知道為了讓妻兒和家中長輩有一條生路,曾祖父讓他們抄小道先走,自己單槍匹馬抵住了被砸得哐哐響、搖搖欲墜的門板。門被砸開的時候,他順勢滾進了一旁厚厚的草垛里,狡猾狠心的鬼子自然不會放過這明顯的隱蔽物,年輕的曾祖父趴在里面大氣都不敢出,閃著寒光的刺刀就這么刺進草垛,劃開稻草,他一動不動。所幸蒼天有眼,老天也見不得鬼子虐殺這個勇敢又堅強的年輕人,刺刀只劃開了曾祖父左手小臂的外側,留下了長長的傷口就撤走了。等曾祖父從草垛里爬起,老舊的泥屋已經燃起了熊熊烈火,黑煙嗆人,曾祖父踉踉蹌蹌沖出家門,在遍野哀鴻里找到了幸存的家人。
沒人知道曾祖父是怎么把病弱的妻子、年幼的兒女從那個食不果腹衣不蔽體,隨時面對刀槍的深淵里拉扯出來的。在戰火熄滅、社會安穩后,曾祖父一家才得以安寧度日。過去所有的苦難,最后都被澆筑成一張弓,澆筑成曾祖父這個人,上面浸透著他的汗、他的淚、他的血,浸透著一個平凡男人的一生。
有人會說,曾祖父不過是一個從戰亂中活下來的普通人,但在我的心里,他就是一個無法重塑的傳奇。小時候我喜歡摸著曾祖父左臂上的疤痕睡覺,在我眼里,那是勛章,是記錄著他保護家人英勇事跡的標簽,是讓我無比欽佩的勇敢者的象征。我熱愛文字,我堅信文字的神圣不容褻瀆,這都離不開我的曾祖父的熏陶——打小他就愛抱著我看書。作為家里這一代唯一的女孩,親戚們都覺得我不需要怎么讀書,只要好好學家務,將來嫁個好人家就好了。曾祖父就常常同他們大吵,自顧自地給我講劉關張桃園三結義,講司馬遷如何寫就《史記》,講李白寫詩被稱為詩仙,講那些我聽得懂或者聽不懂的故事和歷史。于是,他又成為我心中一個新的傳奇,就仿佛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滄海桑田世事變遷都已經裝在他那年邁的身體里,在他的一呼一吸間沉淀成難能可貴的珍寶。祖孫倆坐在小院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他也不過是一個疼愛晚輩的普通長輩而已,他曾一個人步行十里地去買一塊海綿,就為了給我釘一張不會硌人的板凳;他曾在深夜坐在那熟悉的門檻上,等待著第二天才會歸家的兒孫;他也曾捧著好不容易在小院里打下來的棗,步履蹣跚地拿去遞給我出生不久的表弟。“傳奇”也會老去,曾祖父的背一點點弓下去,真正成了一張“弓”,他的眼睛,也終于成了深邃悲傷的井,井里倒映出他曾經的意氣風發,倒映出遠去的記憶,倒映出他孑然一身的孤獨。曾祖父是在一個平靜的夜晚離開的,他像平時一樣起夜,碰到同住的女兒,擺擺手,“沒事,今天不用扶我”。然而等他再回來躺在床上,就再也沒起來。第二天早上,大家甚至沒感覺出他的逝去,按部就班地做了早飯去喊他起床,這一次,曾祖父沒再睜開眼睛。
葬禮上我一滴眼淚都沒掉,大家都說小孩子不懂事,但“頭七”的時候,我一個人留下來守了最后一晚,咬牙沒讓眼淚掉下來。就像沒人知道曾祖父曾悄悄帶我去爬樹、下河一樣,沒人知道我和他約好了:“阿公走的時候,囡囡一定不哭。”午后的陽光照在我們身上,明明逆著光,我卻覺得曾祖父眼睛里的那口井前所未有地溫暖起來,不再孤獨,沒有悲傷。
曾祖父和他的小院,就那樣永遠留在了我和家人的心中。他的臉一點點被時間的潮水沖刷,輪廓不再堅硬,眉眼不再清晰,一點點淡出我的視線,但只要我還熱愛文學,只要我還銘記歷史,只要我還在學著勇敢,曾祖父就永遠留在我的身邊,他所書寫的傳奇,就永遠不會消失,且會同我身上的血脈一起,歷久彌新地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