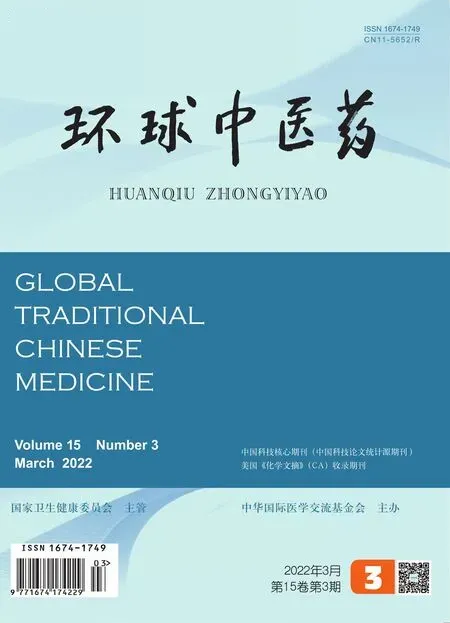中藥“香臭腥臊”四氣理論溯源及現代應用
吉靜 張迪 邵奇 徐甜 厲贏 馬重陽 程發峰
傳統中藥四氣理論,是指“寒熱溫涼”四性,反映了藥物對人體陰陽盛衰、寒熱變化的傾向,是藥性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然而,北宋醫家寇宗奭[1]明確提出四氣之“氣”為“香臭腥臊”之氣,而非用于概述藥物的寒熱溫涼性質。這種說法在當時雖然沒有掀起很大的波瀾也沒有達到糾正的目的,但現在看來,其在指導臨床用藥、中藥炮制與鑒別等方面仍具有重要意義。本文現對中藥四氣理論的歷史源流進行梳理,闡明四氣與四性的不同,為拓寬四氣理論的臨床運用提供參考。
1 “香臭腥臊”四氣源流
中藥藥性理論定義“氣臭”為憑借嗅覺可以感知的藥性,即直觀感受到的藥物揮發的氣味。在文獻記載中,或稱為氣,或稱為臭,或稱為氣味。不過后世又將氣味作為中藥屬性概念中四氣和五味的統稱。中藥學理論是在生產實踐中不斷積累得到的經驗,氣臭的概念最初也是來自古代社會生活,如《周禮》中提到食物的“香臊腥膻”。《素問·金匱真言論篇》將“臊焦香腥腐”分別與五臟相對應,這是與醫療相關的最早“氣臭”文獻,同時也是最早的“氣臭專入說”。《神農本草經》首次提出藥物有“寒熱溫涼”四氣,諸家奉為圭臬,直到北宋中期,寇宗奭首次提出:“藥凡稱氣者,即是香臭之氣;其寒、熱、溫、涼,則是藥之性。論其四氣,則是香、臭、臊、腥……如蒜、阿魏、鮑魚、汗襪,則其氣臭;雞、魚、鴨、蛇,則其氣腥;腎、狐貍、白馬莖、裩近隱處、人中白,則其氣臊;沉、檀、龍、麝,則其氣香。”至此,香臭腥臊“四氣”被正式提出,且獨立于“四性”存在。楊守敬[2]評價為:“《本草衍義》蓋翻性味之說,而立氣味之論。本草一學,自此一變。”《宋徽宗圣濟經》[3]在此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氣臭學說”并加以運用,“腥臊羶香不獨可食,而亦可以已疾”;“蘭草治脾癉,其氣足以除陳氣也,鮑魚利腸中,其臭足以通瘀血也,凡此皆以氣臭專達”。明末的《藥品化義》[4]則是第一部系統論述“氣臭學說”并將其歸入藥性理論的本草著作,在中藥藥性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縱觀本草及各類醫學專著,“氣臭學說”形成于北宋,明代廣為應用,后諸典籍中雖有涉及但未成主流,現將歷代醫史文獻中的“氣臭”記載進行歸納,見表1。

表1 歷代醫史文獻中關于“氣臭”的記載
2 四氣與四性之辨
中藥藥性理論是中醫藥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中藥學》[11]認為藥性是指藥物性質與功能的高度概括,研究藥性的形成機制及其運用規律的理論稱為藥性理論。狹義的藥性理論主要包括四氣五味、升降浮沉、歸經、毒性等內容。其中四氣被定義為藥物的寒熱溫涼四種不同的藥性,現又與四性劃等,不過查閱文獻可知,二者概念的混稱一直存在。
《神農本草經》最早提出“寒熱溫涼”四氣,并提出“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的臨床指導用藥思想。《內經》雖有寒熱溫涼之名,卻沒有明確提出四氣或四性的概念。北宋中期以前,醫家在描述各具體藥物寒熱屬性時很少冠以“氣”字,因此并沒有直接對這一含義的“四氣”提出異議。后寇宗奭提出:“《本經》序例中‘氣’字,恐為后世誤書,當改為‘性’字。”至此,后世一些文獻也開始用“四性”來描述藥物的寒熱溫涼性質,如《泰定養生主論》“大抵百藥之性,不外溫涼寒熱”等[12]。至清代徐靈胎觀察到藥物作用于人體之后的反應提出“入口則知其味, 入腹則知其性”;王學權[13]也提到因個人體質不同,藥物發揮作用的效果也不同,言“可見藥有定性而體臟不同,則性亦隨之而變矣”。明清時期的很多本草著作的成書體例也是依據四性進行藥物分類。然張元素《醫學啟源·用藥備旨》雖提到“藥有寒、熱、溫、涼之性,但又采用“氣熱”“氣溫”“氣平”“氣寒”等表述法。可見從古至今一直存在對于寒熱溫涼的四氣、四性概念混用。
李時珍[14]則認為“寇氏言寒熱溫涼是性,香臭腥臊是氣,其說與《禮記》文合。但自《素問》以來,只以氣味言,卒難改易,姑從舊爾”。他主張《內經》著書立論在先,后人無法輕易推翻,這樣的觀點有失偏頗。原因如下:首先,《內經》中并沒有明確給出“四氣”或者“四性”這樣的概念;其次,《內經》中雖有“寒者熱之、熱者寒之”但并未特指是藥物屬性,更多的是指治則治法;最后,以《素問》原文為例:“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如果這里的氣指寒熱溫涼,氣厚是指寒涼之氣厚還是溫熱之氣厚?溫熱之氣厚者為陽尚可解釋,但寒涼之氣厚者為陽有悖常理。結合“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與“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可知《內經》所言的氣是指附于味而離于味的一種物質,符合“臊焦香腥腐”的氣臭本質。因此,筆者認為,對比“四性”的單一內涵,“四氣”是一個總括性的概念,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遵循《本經》所述,指“寒熱溫涼”四種藥物的寒熱屬性;其二,參考寇氏所言,指“香臭腥臊”四種藥物的氣味屬性。基于此,建議在論述中藥屬性時應將四性與四氣分而論之。
3 “香臭腥臊”四氣臨床應用
3.1 “氣香”之品
由于藥物“氣臭”中的“香”為人所喜,故臨床運用主要以香為主。《說文》云:“香,芳也。”現代中藥學中也多“芳香”并稱,四氣之中,芳香藥物的應用最為廣泛。最早在《內經》“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中就論述了芳香藥物的使用禁忌。有學者[15]曾對芳香藥物的應用歷史發展進行考證,發現早期對于芳香藥物的使用大多是以佩戴或焚燒的形式來達到辟穢消毒、防治疾病的目的,這種方法對于任何時期都有實際應用價值,如在民國時期的《增訂通俗傷寒論》[16]記載有:“暑穢尤為繁重,輒致悶亂煩躁、嘔惡肢冷,甚則耳聾神昏,急用芳香辟穢藥,輕則蔥、豉、菖蒲、紫金片錠,重則蒜頭絳雪,而鮮青蒿、鮮薄荷、鮮佩蘭、鮮銀花,尤為清芬辟穢之良藥。”南北朝時期,一些外來的香藥被引入,但也僅是作為外用,后來才逐漸發現了這些香藥內服的臨床價值,因此在《本草經集注》中不僅補充了大量的本土芳香藥物,也收入諸多外來香藥。發展至隋唐時期,大量內服香藥達到鼎盛。宋代以后,芳香藥物的應用已經極為普遍,甚至出現了濫用,故朱丹溪在《局方發揮》中指出《局方》中許多辛香燥熱方劑下所附的疾病并非其所宜。清代醫家靈活化裁使用芳香藥物,對于溫熱疾病收效顯著。
在現行《中藥學》教材中,芳香藥物多歸類于化濕藥、開竅藥、理氣藥、解表藥及溫里藥中。這些藥物歸脾胃經為主,正如李東垣所言:“芳香之氣入脾胃。”《藥品化義》:“香能通氣、能主散、能行脾陰、能透心氣、能和合五臟”,結合現代臨床應用,筆者認為芳香藥物具有護正辟穢、化濕醒脾、健胃助運、解表散邪、通達走竄、去腐消腫、通經止痛等功效[17]。
3.2 “氣臭腥臊”之品
現代社會,常香、臭對舉使用,臭取“難聞的氣味”義,因此可將氣臭分為香、臭兩氣。在實際臨床應用中,根據藥物所占比例,所謂氣“臭”的藥物實際也指“臭腥臊”的集合,以“臭”統稱。《韓非子》記載:“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原始社會對于火的應用尚未出現時,人類就察覺到了生用瓜果肉食的腥臊臭氣,這也是氣味判定食物屬性并指導醫療的早期記載。本草學涉及的“臭腥臊”之品以動物藥(包括動物糞便、動物臟器、動物病理生理產物)、貝殼類或地衣類藥物為主。“心脾之氣得芳香則運行,得臭惡則壅滯”,以上諸品皆不為臟腑所喜,因此在炮制過程中多將其祛除。如酒炙烏梢蛇、醋炙五靈脂、麩炒僵蠶、米炒斑蝥、滑石粉炒水蛭、水漂昆布等。同時在藥物煎煮的過程中應避免使用鐵鍋作為容器,因鐵制品易與中藥中的鞣質、苷類成分發生化學反應,使湯劑藥味澀而腥,影響服藥口感。也有一些方劑其配伍及服用精當巧妙,不僅增強療效,也兼顧藥味,如《局方》失笑散其方后注有以釅醋調服,這不僅可以增強原方活血止痛之力,還可以矯五靈脂的腥臊之氣。《金匱要略》當歸生姜羊肉湯中羊肉具溫補之力,雖其氣腥膻,但有生姜矯其味且可以增加溫補的協同作用,同樣臨床常見的具有溫中功效的花椒因含有多種揮發油和芳香物質,也可以用于祛除腥臊臭氣。
“臭腥臊”之品雖不似“香”藥應用廣泛,但經炮制后投入臨床仍具備重大意義。《本草綱目》記載的“鹽之氣味咸腥,人之血亦咸腥……從其類也”與《醫學衷中參西錄》記載的“鮮小薊根氣微腥,為其氣與血同臭,故善入血分”皆是利用藥物與血液二者共有的腥氣來進行藥理闡釋的。同時,“腥臊臭”也可以用于疾病的輔助診斷,多用于描述瘀血、痰飲、帶下、二便等分泌物。在臨床應用上,常選擇帶有臭氣的魚腥草、敗醬草來治療肺癰之咳吐腥臭膿痰,用帶有糞便味的雞屎藤治療消化不良所致瀉痢惡臭等,這些都是依據“同氣相引”來進行臨床選藥的,又稱“以臭辟臭”。所謂“腥臭填下”,是指具有腥臭之氣的藥物多為動物類藥材,因下焦肝腎所藏多為脂膏精液,“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因此這類物質的補充常以腥臭重濁的血肉有情之品為主,如鹿茸、龜板、紫河車等。臭阿魏取自傘形科植物的樹脂,具有強烈而持久的大蒜樣二硫化合物氣味,古籍記載其善殺諸蟲,能消積利諸竅,除穢惡。這正是“ 極臭通竅”之義,誠如《本草備要》中所記載的“凡極香極臭之物,皆能通竅”。同時,臭還能“辟惡氣”“解瘟疫”,如藥食同源的胡荽、大蒜之品。
4 “香臭腥臊”的現代研究
4.1 “香臭腥臊”的應用研究
關于“氣臭”的現代研究較少,又因其臨床的實用性,對于香臭之氣一般更集中于芳香藥物的研究。近年來,國內外時興的自然療法——音樂療法、水療法、氣味療法等引發了中醫“芳香療法”的又一陣熱潮。臨床研究表明,利用薄荷、白芷、金銀花、菊花、蘇葉等散發的芳香氣味可顯著改善多種呼吸道疾病,如普通感冒、鼻炎、咽炎、支氣管哮喘等[18]。有報道稱,貓咪產后抑郁在治療時可采用氣味療法,即通過類似主人衣物等貓咪可以聞到的、熟悉的、讓它覺得安全的味道可以明顯安撫貓咪抑郁情緒。其實利用氣味舒緩身心早有記載,宋代連文鳳有詩言:“坐我以靈室,爐中一纂香,清芬醒耳目,馀氣入文章。”古人常用熏香的方法寬胸理氣、開竅醒神。多項研究也表明,芳香藥的代表組分揮發油具有抗焦慮、抗抑郁、鎮靜安神、神經保護作用等藥理活性,經嗅覺、皮膚等途徑可達到緩和情緒、調節神志的作用[19],還有研究表明其配合音樂療法可緩解癌癥患者的不良情緒[20]。以上足以證明氣臭對于防治抑郁、焦慮、失眠等情志疾病有著獨特的優勢,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具有中醫特色的健康資源。用藥取其氣者,“香臭腥臊”四氣對于中藥的煎煮方式以及給藥途徑也存在重要意義。例如類屬解表藥、芳香化濕藥之品不宜久煎,久煎其“氣”揮散,藥效大打折扣。“氣”之無形特質決定了此類藥物多經鼻、皮膚腠理等孔竅進入人體,因此在臨床應用上,主要經鼻嗅、口服、外用等方式給藥,但未見不同的給藥途徑是否有不同的作用效果等文獻報道。此外,對于“香臭腥臊”現代研究還有部分集中在鑒定易混中藥、正品與偽品、質量評判上。如薄荷與墨旱蓮,兩者外形極其相似,然薄荷氣香,可加以辨別,川芎和當歸亦是如此。
4.2 作用機制及物質基礎
“氣臭”是以嗅覺來辨認,而作為嗅覺感受器的鼻卻存在生理差異,不同的人對于嗅覺的感知有異。近年來雖然有電子鼻的仿生技術,但對于香味的判定卻沒有統一的標準,此外芳香藥物的氣還會受到炮制及各種儲存條件的影響。關于藥的物質基礎,但許多辛味藥物其氣不香反臭,如胡荽、大蒜等,并且一些具有同樣物質基礎的藥物功效卻有差異。因此有關“香臭腥臊”四氣的現代定性定量研究尚有一定難度。冬蟲夏草是一種具有強烈腥味的傳統名貴中藥,有經驗者可根據其散發的“腥氣”濃烈程度評判其質量優劣。譚鵬等[21]建立并應用了一種基于頂空—固相微萃取—氣相色譜—三重四極桿質譜聯用技術的冬蟲夏草“腥氣”分析方法,成功篩選出冬蟲夏草真偽鑒別的標志性成分并為其他中藥材的特征嗅氣分析提供參考。還有部分學者通過比較生首烏、炆首烏、制首烏的揮發性成分,化學計量學分析表明炮制方法對于中藥氣味的顯著影響[22],至于是否“氣味優勢”越明顯,其補肝腎、烏須發的藥效越顯著還需進一步研究。正所謂“凡藥之用,或取其氣,或取其味……各以其所偏勝而即資之療疾,故能補偏救弊,調和臟腑”,不同藥物甚至同一藥物經過不同的炮制方法,其“氣味”的作用機制及物質基礎不同,臨床作用范圍也隨之不同,至于其具體關聯尚待研究。
5 小結
“氣臭學說”在中藥藥性理論占有重要地位,但提及四氣或四性的概念,大多醫家只知“寒熱溫涼”,忽視“香臭腥臊”,主要原因是對于四氣運用的不足。醫者在臨床辨病論治時,重視辨別八綱中的寒熱,以確定組方藥物的寒熱溫涼。除了芳香藥物,其余具“臭臊腥”氣的藥物在臨床的應用也并不廣泛,在重視“氣臭學說”的《藥品化義》中也是僅僅討論香氣,并自注“缺膻、臊、腥、臭四氣,有脫簡”,甚至在現代有學者提出應“避用腥臭”。一些藥物如童便、雞屎白、人中黃等不為人接受而主動避用;另一些藥物如甲珠、虎骨、犀角、牛黃等珍稀動物藥材被規定禁用;還有一些如雞子黃、戎鹽等不常用藥材,以上藥物的共同特點都是帶有“臭”氣,因此四氣在藥性理論中的地位逐漸被削弱。但是根據歷代醫家的臨床實踐記載,四氣理論在指導臨床時仍有其重要價值,不僅可以用于內服方劑,也可以外用熏浴、膏摩、塞鼻取嚏等療法,因此應加以挖掘利用,不可輕視。“土愛暖而喜芳香”, 現代研究統計發現, 芳香藥物歸脾、胃經居多, 其次為歸肝、肺等經,且多具有宣散解表、開竅醒脾之功效。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一部)》[23]記載,具有腥味或臭味的藥物共39種,百分之八十為動物藥,如土鱉蟲、烏梢蛇、水蛭等多歸肝、腎二經,多可用于化瘀生血、滋補肝腎。這些都說明“氣臭”對于藥物歸經及功效的重要意義。同時,重視藥物“香臭腥臊”四氣可以幫助醫者更好的理解藥性理論,指導臨床組方用藥。中藥“四氣”指代“寒熱溫涼”刻板印象日久,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醫藥各家學說的發展進程,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醫者臨床用藥的思維模式,筆者提出:在“寒熱溫涼”四性的基礎上,倡重視“香臭腥臊”四氣,以免貽誤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