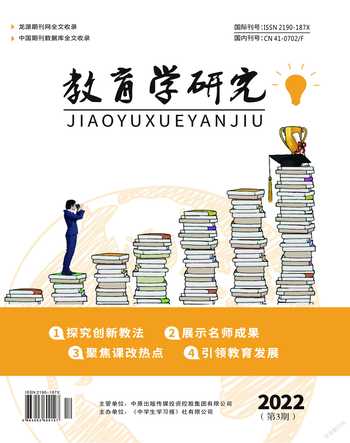藝術(shù)是時(shí)代的影射
李瑩瑩
摘要:羅中立的《父親》和彭偉的《而立之年》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產(chǎn)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和審美意義,是藝術(shù)家將藝術(shù)作品置于不同的審美“語境”之下的藝術(shù)典型形象的結(jié)果。不同的時(shí)代語境孕育不同的藝術(shù)作品,產(chǎn)生不可取代的時(shí)代審美價(jià)值和意義。
關(guān)鍵詞:審美語境;藝術(shù)符號;父親;而立之年
一、藝術(shù)作品的符號化審美載體
羅中立的《父親》獲得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一等獎(jiǎng)。羅中立也因《父親》一畫聲名遠(yuǎn)揚(yáng)。《父親》運(yùn)用“照相寫實(shí)主義”手法描繪了四川大巴山一位普通老農(nóng)形象。其當(dāng)時(shí)備受各界矚目且產(chǎn)生廣泛的社會(huì)影響,羅中立的《父親》繼而成為家喻戶燒的名作。
在2014年第十二屆全國美展上,彭偉的黑白木口木刻版畫《而立之年》奪得金牌榜第一名,由此版畫作品登上全國美展冠軍。《而立之年》刻畫了燙著卷發(fā)、戴著眼鏡的青年。其目光深邃、神情冷峻、精神飽滿、意志堅(jiān)定,自信的眼神中略帶憂郁,睿智的表情里充滿深刻,真實(shí)自然地體現(xiàn)了當(dāng)代中國青年的形象,再次深得人心。
盡管時(shí)代情境與文化語境千差萬別,《而立之年》與《父親》各有千秋。但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兩件作品都是兩位藝術(shù)家在各自生活的年代里,根植于現(xiàn)實(shí)生活又超脫于真實(shí)的生活而創(chuàng)作的極具時(shí)代性和符號化的典范之作。不管是羅中立的《父親》還是彭偉的《而立之年》,我們暫且不看他們創(chuàng)作的形式語言和專業(yè)技法,首先他們給我們呈現(xiàn)的絕不單單是“父親”、“青年”形象本身,而給我們呈現(xiàn)更多是的是一種符號化、典型化了的藝術(shù)形象,是時(shí)代的象征和縮影。它們直擊心靈,引發(fā)思考。《父親》的形象不僅是某一位父親,更是億萬中國農(nóng)民父親形象,是八億人民的“父親”,是改革開放后社會(huì)發(fā)展階段里程碑新時(shí)代。《而立之年》的形象也不單是某個(gè)青年的形象,更是歷經(jīng)改革開放后,億萬中國當(dāng)代新青年的形象,亦是當(dāng)代中國新面貌。80后的“而立之年”也是中國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從發(fā)展到逐步成熟的“而立之年”。《父親》和《而立之年》之所以能夠引起震撼,就在于這兩件作品對時(shí)代內(nèi)涵的表達(dá)最為直接、準(zhǔn)確、鮮明。兩件作品都鮮明的映射著那個(gè)時(shí)期的社會(huì)文化特征。石濤曾提出“筆墨當(dāng)隨時(shí)代,猶詩文風(fēng)氣所轉(zhuǎn)”的論斷,這兩件作品既如此。“藝術(shù)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藝術(shù)創(chuàng)作就是要把這些分散的素材從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找尋、提煉、歸納,然后進(jìn)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還原成一個(gè)具有典型性、代表性、象征性的藝術(shù)形象。欣賞者之所以會(huì)被這個(gè)作品打動(dòng),是因?yàn)樗麄儚淖髌分锌吹搅苏鎸?shí)的生活和真實(shí)的自己,形成自己的符號化語言。
二、歷史時(shí)代語境下藝術(shù)符號的審美關(guān)照
曾景初的《畫什么?怎么畫? 美在哪里?》一文對《父親》所塑造的“父親形象”給與充分肯定:“他不是某一個(gè)農(nóng)民的父親,而是當(dāng)代中國農(nóng)民的形象。這個(gè)形象所體現(xiàn)的力量,是支撐我們整個(gè)民族、整個(gè)國家從過去走向未來的偉大力量。但他生活在最底層,過著不聲不響的勤勞艱苦的生活,從他身上,可以看出我國農(nóng)村的縮影。”彭偉創(chuàng)作《而立之年》時(shí),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后,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正走向強(qiáng)起來。作者憑借敏銳的洞察力和超強(qiáng)的表現(xiàn)力,精準(zhǔn)刻畫和反映了新一代中國青年的嶄新形象和精神面貌。“吾十有五而志于學(xué),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而立之年”是彭偉作為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而立之年,也是作為青年的他和他的同齡人的而立之年,更是經(jīng)歷改革開放三十年后朝氣蓬勃走向未來的中國的而立之年。這個(gè)“而立之年”是美術(shù)的希望、國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羅中立《父親》的成功決非僅僅是表面一個(gè)農(nóng)民形象帶來的視覺沖擊。而應(yīng)該是《父親》背后的審美意蘊(yùn)和審美關(guān)照。換言之,我們不應(yīng)把《父親》簡單當(dāng)作一件現(xiàn)實(shí)主義美術(shù)作品看待,這將導(dǎo)致我們忽略了《父親》一畫的當(dāng)代和劃時(shí)代的審美意義。羅中立說他的《父親》“表達(dá)的是一個(gè)民族對過去歷史的反醒:一個(gè)瘋狂的時(shí)代結(jié)束了,一個(gè)神話結(jié)束了”。
三、藝術(shù)符號發(fā)展審美價(jià)值
羅中立在后來自己也是這樣闡釋自己的《父親》:“‘文革’結(jié)束后畫了這件作品,突破蘇式寫實(shí)而用了照相寫實(shí)法,采用與主席像完全相同的尺寸,當(dāng)時(shí)要表達(dá)的是一個(gè)民族對過去歷史的反醒:一個(gè)瘋狂的時(shí)代結(jié)束了,一個(gè)神話結(jié)束了,現(xiàn)實(shí)又活生生地回到眼前。”彭偉的《而立之年》采用超級寫實(shí)的圖片技術(shù)和木刻技術(shù),借助燈光和放大鏡精致完成。人物臉部若干條細(xì)如發(fā)絲的線條,沒有一根交叉,通過線條與線條的間距,達(dá)到凹凸、起伏、明暗效果,來傳達(dá)人物的情緒、氣質(zhì),揭示內(nèi)心活動(dòng)。《而立之年》還突破了中國傳統(tǒng)木刻、新興木刻和西方木口木刻的限制,特別是超越了木口木刻版畫一般尺度只有書本大小的禁錮,開創(chuàng)了新的表現(xiàn)形式。作為《父親》典型的繼往開來者和成功的承前啟后者,《而立之年》為重慶美術(shù)樹立了新的標(biāo)桿,點(diǎn)燃了新的火焰。從兩件氣勢恢弘、振聾發(fā)聵的作品中,我們不僅可以清楚地看到時(shí)代的不同、形式的不同、風(fēng)格的不同、面貌的不同,看到所表達(dá)的國家形象的不同,同時(shí)能夠更真切地看到有良知、有擔(dān)當(dāng)、有情懷的藝術(shù)家對生命禮贊、對人性謳歌、對美好憧憬的大愛大同。
當(dāng)人們談?wù)撆韨ズ退摹抖⒅辍疯T就的藝術(shù)輝煌,我則更看重這件作品所體現(xiàn)的人文精神可能給中國藝術(shù)和中國社會(huì)帶來的深遠(yuǎn)影響。和《父親》一樣,《而立之年》所傳遞滿滿的正能量,飽含深情而充滿希望。《而立之年》因其深切觀照現(xiàn)實(shí)、深情直面人心,已經(jīng)定格為一個(gè)時(shí)代的永恒,成為民族精神與民族希望的雕像。在這件黑白構(gòu)成的作品中,我們讀到了黑的深沉、凝重、堅(jiān)硬、剛毅、智慧、寬廣,讀到了白的純真、神圣、單純、簡潔、謙卑、悠遠(yuǎn),這不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底色和原色?
從《父親》到《而立之年》,三十年中國國家形象美術(shù)表達(dá)的蛻變,折射出的是中國、是所有中國人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更是強(qiáng)大的文化自信,是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之所急、之所需。
參考文獻(xiàn):
[1]羅中立:《信》,《美術(shù)》,1981年,2月號
[2]曾景初:《畫什么?怎么畫?美在哪里?》,《美術(shù)》,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