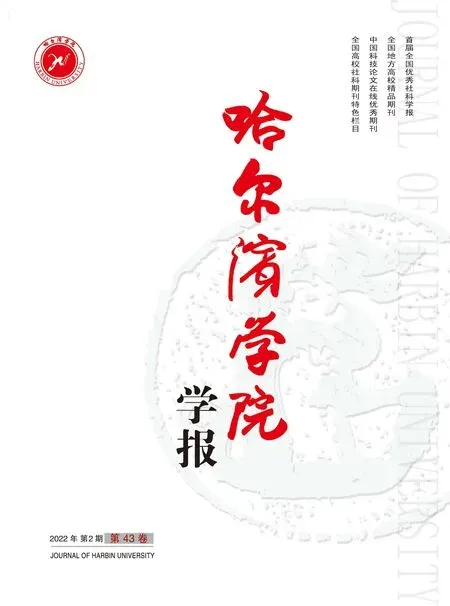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為入罪研究
陳 玲
(鄭州大學 法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國民的生命健康依賴于食品安全,頻頻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威脅到了國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嚴厲打擊食品安全犯罪的呼聲高漲。為此,我國在立法及司法解釋方面對食品安全問題做出了調整,相繼出臺了《刑法修正案(八)》《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并根據《刑法修正案(十一)》細化了負有監督管理食藥安全責任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玩忽職守以及濫用職權行為,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呈現趨嚴的狀況。學界有學者認為,當前我國刑法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規制存在一些問題,提倡嚴密食品安全刑事法網,以完善對此類犯罪的治理。[1]在此背景下,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為應否納入刑法規制范圍,便具有了較大的理論探討空間。
一、持有型犯罪行為方式的理論爭議
持有是指行為人對特定物品或者財產進行支配、控制的一種狀態。持有型犯罪,是以行為人持有特定物品或財產的不法狀態為基本構成要素的犯罪。[2]關于持有型犯罪的行為方式,學界主要存在作為說、不作為說與獨立行為說等三種理論學說。
作為說認為,持有型犯罪違反了禁止行為人取得特定物品的法律規范,處罰重點在于取得行為,不法狀態是先前積極獲取行為的自然延續,實質上屬于事后不可罰。不作為說則認為,持有型犯罪存在一種抽象意義上的法律義務,刑法將持有行為規定為犯罪,表明刑法禁止持有特定物品這種行為的存在。這一規定的隱含內容是當出現持有某種物品的狀態時,行為人具有應將該物品上繳司法機關或其他部門結束該狀態的法律義務。其違反了抽象意義上的法律義務,屬于不作為。[3]獨立行為說認為,持有型犯罪的行為方式,既有先前取得的作為特征,又有違反法律規定的支配特定物品狀態持續的特征,[4]很難將“持有”這一行為方式完全歸屬于作為或者不作為,因此被認為是同作為、不作為并列的獨立行為方式。
筆者贊成持有屬于作為方式,行為人持有特定物品,違反禁止規范屬于不應為而為之。非法持有某種特定物品或者財產的狀態來源通常來講有三種:一是更為嚴重的先前犯罪行為的結果,例如非法持有大量不安全食品往往是生產有毒、有害食品或者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的結果狀態;二是后續銜接犯罪的過渡狀態,例如持有大量不安全食品的后續犯罪行為可能是銷售,持有毒品的后續銜接犯罪行為可能是販賣等;三是可能是其他目的犯罪的預備狀態,例如非法持有槍支可能是故意殺人罪的預備。由于行為人的持有行為往往較為隱蔽不易被發現、行為人故意銷毀犯罪證據等各種原因,司法機關在抓捕犯罪分子、人贓并獲后可能因無法收集到能夠證明非法持有狀態的來源與去處的足夠證據且犯罪分子無法說明其來源,而無法以先前犯罪行為、后續銜接犯罪或者其他目的犯罪對行為人定罪處罰時,可以持有型犯罪定罪處罰。
二、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為的界定
不安全食品是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為的對象,其范圍的明確界定是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為入罪的重要問題之一。我國刑法和食品安全法中均未使用“不安全食品”這一概念。對“不安全食品”做出明確規定的是2007年《食品召回規定》第3條和2015年《食品召回管理辦法》第2條,即不安全食品是指有關食品的法律法規禁止生產經營的食品,以及其他能夠被證據證明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食品。上述兩條規定并未對不安全食品的范圍做出具體的劃定,因而實踐中無法依據此規定確定某種食品是否屬于不安全食品。
2015年《食品安全法》第150條規定,安全食品要求食品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并且不會對人體健康造成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以此條規定的內容為參考反推知,不安全食品應當指的是食品有毒、有害,不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會對人體健康造成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其范圍應該包括兩種:一種是有毒、有害食品;另一種是雖不屬于有毒、有害食品,但不符合應有的營養要求,食用后可能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的食品。第二種不安全食品類型的確定,需要借助食品安全機構的檢測和鑒定。
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為,指行為人客觀上持有一定量的不安全食品,司法機關無法查證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生產、銷售或者其他目的,行為人也無法或不愿說明不安全食品的來源與流向的行為。[5]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為是食品安全犯罪的重要環節,貫穿整個食品的鏈條。對不安全食品的持有可能是生產某種有毒、有害食品前的貯存階段,也可能是食品生產完成后發往銷售點的運輸階段,同樣也可以是銷售前或者銷售中的貯存階段,這種運輸和儲存階段均是對食品的持有行為。食品的持有狀態在食品從生產者到銷售者再到消費者這一完整的流轉過程中是常見、頻繁且持續時間較長的。這意味著,相比于生產、銷售不安全食品的行為,持有行為更容易被行政執法機關發現并查獲。
將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為入罪不能忽略的問題是,如果在我國《刑法》中增設不安全食品的持有型犯罪,該罪名中的不安全食品范圍與第143條和144條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兩個罪名的犯罪對象之間的關系。從不安全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與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這三個概念所涵蓋的范圍來看,不安全食品和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的認定與《食品安全法》銜接,兩者的內涵一致。有毒、有害食品也屬于不安全食品,因為其規制的范圍最小,可視為最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被包含于不安全食品的概念中。在食品安全問題屢禁不止、層出不窮的背景下,有不少學者認為我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法網較為疏漏,犯罪對象范圍較窄。因此,筆者認為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入罪的對象應當以食品行政法規中的不安全食品范圍為參考,以彌補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對象較窄的問題,嚴密刑事法網。
三、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為入罪的必要性
我國食品安全刑法保護的立法趨勢表現為法益保護前置化、幫助行為正犯化、重視風險防控、注重保護民生。回顧我國對食品安全的刑法保護,從《刑法修正案(八)》對“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量刑方面的修改,增設了食品監管瀆職罪,到《刑法修正案(十一)》對食品、藥品監管瀆職罪的細化等內容可以看出,我國食品安全刑法保護呈現出介入時間提前、規制范圍擴大與打擊力度趨嚴等特點。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為入罪具有必要性:
第一,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持有不安全食品的行為是食品行業鏈條上的重要一環,其通常是生產行為的結果狀態、銷售行為前或進行中的貯存狀態抑或是食品安全犯罪中其他目的犯罪的預備狀態。由于多種原因的存在,不安全食品暫時未能進入食品流轉環節。不安全食品是有毒、有害食品或者其他能夠對人體健康造成損害的食品。投入市場流通環節,容易危及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和安全。在工業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食品行業已經成為科學技術含量高、專業性強、操作精細化、鏈條化的領域,現代社會的食品通常是工業化大規模、批量化加工制造的。當含有不能食用的化工物質或者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劑制成的不安全食品經生產者、銷售者流轉到消費者手中時,通常會導致一定的不良后果,會對廣大消費者造成傷害。例如我國曾出現的三聚氰胺事件,在該事件中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而生產出來的嬰幼兒食用奶粉流入市場,對眾多嬰幼兒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嚴重損害,給無數家庭本來幸福的生活蒙上了揮之不去的陰影。食品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其種類繁多,既包括不需要精細加工,從農田便直接進入市場的初級農產品,同時也包括了經過細致復雜的工業生產技術加工而成的食品。隨著物流網絡的大規模鋪開,網絡銷售食品行業不斷發展壯大,通過網絡渠道銷售的食品也日益成為國民日常生活離不開的存在。從農產品的種植、養殖、銷售到食品的生產、加工、運輸、貯存、銷售,鏈條上的每一環節都可能存在不安全因素。犯罪行為人在任一環節施加影響,都容易造成食品安全事件,損害廣大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和安全。因此,將作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或者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的先行行為或者后繼行為的持有行為犯罪化,能更好的維護國家對食品的管理秩序,保護公共安全,嚴密我國食品安全刑事法網,發揮刑法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防線作用,意義重大。
第二,我國食品安全法網存在疏漏。首先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為方式范圍較窄,其他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相關行為未納入刑法規制范圍。例如,與食品生產、銷售行為相關的產品進出口、相關記錄制度的維持、產品召回以及持有相當量不安全食品等環節,尚未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其次是,根據我國目前《刑法》的規定,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行為方式限于社會危害性較為嚴重的生產、銷售兩種方式。而《食品安全法》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為的規定則覆蓋了農產品的種植、養殖、供應等環節和食品的生產、加工、包裝、運輸等一系列從“農田到餐桌”的相關活動。由于二者范圍不一致,因而“兩高”出臺司法解釋,針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補正:除食品的生產、銷售環節以外,對于其他環節如提供資金、貸款、賬號、證明、許可證件,生產、經營場所或者運輸、貯存、保管等行為的依照幫助共犯論處,擴大了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圈,算是對現有規制不完善的一個彌補。再次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規制的對象與作為其前置行政法的中食品的范圍不一致,食品安全法將規制的范圍擴展到用于食品生產銷售的工具、設備,例如食品添加劑、食品包裝所用材料等諸多與食品相關的產品,而刑法中所規定的食品犯罪的行為對象不能囊括上述與食品生產經營相關的產品。最后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主觀罪過限于故意,事實上很多食品安全事故的發生并不是由于行為人的故意行為所致,行為人的過失行為導致食品安全事故,同樣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危害性,其對人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所造成的影響不低于故意行為。因此,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增設持有型犯罪,能在有毒、有害食品和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銷售流入市場之前截斷犯罪,保護法益,防止造成更嚴重的危害消費者身體健康的后果。
第三,符合我國食品安全刑事政策的要求。現代化不斷發展給國民日常生活和出行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制造了風險。不安全食品導致的食品安全問題往往不能立即被發現,具有潛伏性和隱蔽性等特征,工業社會的風險性決定了側重積極預防成為我國食品安全刑事政策的重要體現之一。食品安全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的是,行政執法機關查獲行為人運輸或者儲存了一定量不安全食品,當行政執法人員、司法人員能夠查明或者行為人能夠說明不安全食品的來源與去向時,可以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相關罪名定罪處罰;但當無法查明或行為人不能(愿)說明不安全食品的來源與流向,且無相關證據能夠證明行為人有生產、銷售的目的時,在此情況下難以用先前犯罪行為、后續銜接犯罪或者其他目的犯罪對行為人定罪處罰。在此情形下,因為持有型犯罪一般可以從持有的現狀推定行為人具有持有的故意,適用持有型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公訴機關的證明責任, 有利于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將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犯罪化符合嚴密我國食品安全刑事法網,以及我國食品安全刑事政策保障人民健康、側重積極預防的要求。
四、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為罪名歸屬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侵害的是雙重客體,哪一個客體是主要客體關系到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犯罪化后在我國刑法分則罪名體系中的歸屬。
學界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歸屬存在爭議,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主張將食品安全犯罪歸入我國刑法分則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此觀點認為,食品是國民的生活基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為的影響波及不特定多數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應當將公眾的健康與安全作為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客體。而且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歸入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利于實現刑法保護人民利益的目的,并有效規制犯罪。另一種觀點主張,將食品安全犯罪規定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此觀點認為刑法分則中的罪名體系放置,既要考慮侵犯的客體,也需要兼顧罪名間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問題。現行的立法模式,不僅考慮到了危害食品安全行為的經濟屬性,而且也是因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主要規制生產、銷售環節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犯罪存在相似之處。[6]就此爭議,高銘暄教授認為,曾有刑法修擬版本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設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下。現行刑法最終將該罪名歸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專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該罪的刑法立法價值取向偏重實現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維護,也是對廣大消費者生命健康權利的保護。
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主張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罪增設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罪名體系上歸屬于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在此僅對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罪的構成要件做出假設,宜參考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中銷售金額的設置,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構成本罪,銷售金額不滿五萬元的,屬于行政違法行為,由行政機關予以處罰,實現刑行有效銜接。在該罪的法定刑方面,宜設置短期自由刑和罰金。
至于增設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罪后,如何在立法層面上規定該罪的罪狀,該罪的立案標準是以貨值金額還是以銷售金額為標準,該罪的法定刑該如何設置等問題較為復雜,需要結合我國食品安全司法實踐、刑法分則罪名體系、國際食品安全犯罪刑罰輕緩化的特征以及其他持有型犯罪的規定進行深入研究。
五、結語
近年來我國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呈現趨嚴的形勢,但在司法實踐中未取得明顯效果,食品安全問題仍有增無減。非法持有不安全食品行為是食品安全犯罪鏈條中的重要一環,通常銜接先前的生產行為以及后續的銷售行為。大量的不安全食品流入市場,容易影響消費者的正常生活和市場經濟秩序。我國食品安全犯罪行為方式范圍較窄,缺少對持有行為的刑法規制,考慮將其納入刑法的規制范圍,也是食品安全刑事政策的需要。食品安全問題是食品市場的監督管理機制不完善、企業盲目追逐利益缺乏行業自律和底線等諸多方面的原因綜合造成的。刑法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線,無法以一己之力解決由行為人逐利、企業管理不足等諸多原因導致的犯罪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需要政府監管、食品的生產經營者自律、公眾監督等多方共同參與、共同努力,刑法最終應回歸謙抑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