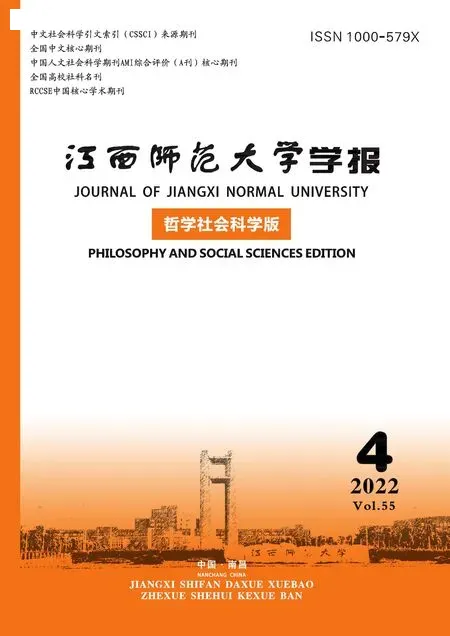試論中華美學“詩性寫意”精神的當代價值
何世劍, 袁軼凡,2
(1.南昌大學 藝術學院,江西 南昌 330031;2.江西科技師范大學 音樂學院,江西 南昌 330038)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精辟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1](114)他的講話啟示和引領我們與時俱進地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美學精神的學理研究與傳承弘揚。
著名美學家葉朗先生承續朱光潛、宗白華等先生的美學思想,強調“美在意象”,有力地揭示了中華美學精神的真諦。與西方古典美學精神重視“理性寫實”不同,中華美學精神更側重“詩性寫意”,在中國書畫、建筑園林、樂舞、戲曲等文藝創作與表現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孕育出情、象、境、神、妙、逸、品、氣、韻、趣、味等諸多具有民族文化內涵、學理特質、詩性品格的美學范疇。列寧《哲學筆記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中指出:“思維的范疇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和人的規律性表述。”[2](p75-78)人類思維的發展和結晶,通過概念、范疇、精神等得以展開和表達。這些概念、范疇、精神等相互關聯,互相影響,它們統攝力大、生命力強、影響深遠,其傳承、發展、嬗變、創新,是我們把握思維演進、文化及文明發展的重要支點。張岱年先生指出:“民族精神乃是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集中體現,是一個民族價值目標、共同理想、思維法則和文化規范的最高體現。”[3]就中國文化、美學而言,其根基在詩學。不管是張揚政治—倫理型功能,還是強調藝術—審美型功能,早期中國先人的詩性智慧結晶《詩經》、“楚辭”,已經表現了這一點,奠定了中國詩性文化發展的基礎。劉士林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本體是詩。其精神方式是詩學,其文化基因庫就是《詩經》,其精神峰頂是唐詩。總括起來說就是: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4](p2)從文明的分野和地域文化的傳承、發展來看,以齊魯文明為代表的北方大地(黃河流域)詩性文化,強調禮樂教化的功能,走向以“善”為核心的詩學大道。而以湘楚文明為代表的江南水鄉(長江流域)詩性文化,強調藝術體驗的功能,走向以“美”為核心的詩學大道。當下,我們有必要深入具有通貫互滲性、有機整體性的中華美學“詩性寫意”精神范疇“潛體系”中進行考察和探討,尤其是把握和激活其當代價值,為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繁榮發展貢獻新的思想智慧,為社會生活的團結穩定和諧美麗開出新的美學良方。
一
從藝術生發論,“詩性寫意”精神的起點與基礎在于“詩興”。“興”是古典詩學、美學的核心。元朝楊載在《詩法家數》中認為“賦比興”是“詩學之正源,法度之準則”[5](p758)。朱自清先生稱“比興”是中國古代詩論的“金科玉律”[6](p144)。劉勰《文心雕龍》:“比者,附也;興者,起也。……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7](p601)劉勰從情理關系闡述了比、興的區別,肯定了“興”對于詩歌情采生成、意象生成的發生意義。鐘嶸《詩品序》:“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馀,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8](p111)鐘嶸首次系統地論證和闡釋了詩“興”精神,鄭重其事地強調了“興”的首要之意義。至此,無論是從詩歌創作還是從理論上講,詩“興”精神作為藝術生命的激活功用已經得到了深入的認識和強調。之后,唐皎然《詩式》說:“取象曰比,取義曰興。”[9](p281)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余言外。”[10](p215)王夫之言:“興在有意無意之間。”[11](p463)這些論斷立足不同的文體,從各個側面補充完善了對詩“興”精神的認識。“詩興”精神在中國古典美學、文藝學領域具有重要的價值。袁濟喜先生強調“興”是藝術生命激活的重要中介,是實現現實人生向藝術人生、審美人生躍升的津梁[12]。“興”作為中國古典美學的核心范疇,它融會了文藝和審美的許多根本性問題,溝通和涵括了心物、情景、情志、形神、情理等諸多對立關系,同時又具有獨立的中華民族精神文化創造特質。葉嘉瑩先生曾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形象與情意之關系例說》一文中說:“至于‘興’之一詞,則在英文的批評術語中,根本就找不到一個相當的字可以翻譯。”[13](p33)揭示了“興”作為中華審美文化創造、詩性精神生發的典型特性。“興”源發于中華民族的原始生命沖動,保留了遠古生民天人感應、觀物取象、譬諸擬議、托物寓意等文化觀念[14]。“興”,較早作為詩教用語,屬于讀者接受層面,春秋賦詩的借詩比喻、托喻之辭可以為證。后來逐漸向表達、創作領域發展,魏晉時期的“物感說”“感興說”成型是重要代表,內涵得以拓展。唐宋以迄,被美學家、文論家爭相闡發,從批評鑒賞層面進一步充實了“興”的內涵,融會了藝術創作中如情景、心物、意象等其他許多范疇。從“比興”“感興”“興象”“興喻”“興寄”“興托”“興味”“興趣”“興會”“意興”等相傳遞降、演化豐富,創造了輝煌燦爛的華夏文藝。而“跨領域的解讀,使‘興’成為更廣泛意義上的藝術范疇”[15]。沒有生命之興,就沒有藝術之美,興激活了生命活力、創造欲望,點燃了外物風采、境象光輝,讓人生不普通,讓生活更豐富,讓藝術更精彩,讓審美更深邃。
從藝術語言論,“詩性寫意”精神的要義與表達在于“隱秀”。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云:“詩無達詁。”[16](p35)詩之所為詩,正在于詩性語言的模糊性、多義性,造就了詩意的豐富性、復雜性,激活了想象的維面,拉大了闡釋的空間。“復義”是優秀詩作的基本特征。它激活了文本的審美內涵。“復義”一定時候通過“隱秀”的手法表現出來,起到“雙關”的審美效應,給人以“話外重旨”“弦外有音”的感覺。劉勰《文心雕龍·隱秀篇》指出:“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7](p632)范文瀾先生注釋說:“重旨者,辭約而義富,含味無窮。陸士衡云‘文外曲致’,此隱之謂也。獨拔者,即士衡所云‘一篇之警策也’。”[7](p633)周振甫先生箋注時也指出:“秀:秀出,高出,指警句。隱:指含蓄。”[17](p350)也就是說,好的詩歌作品,語詞既要勁爽曉暢,又要含蓄委婉。正是這種矛盾的內在統一,才彰顯了意蘊的深度和豐富。英國詩人、文論家燕卜蓀(William Empson,1906—1984)在其1930年出版的《復義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A Study of Its Effects on English Verse)中指出,“任何語義上的差別,不論如何細微,只要它使用一句話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應”[18](p296),就會造成“復義”。燕卜蓀所說的“復義”和中國文藝美學中的“隱秀”有近似之處。譬如,中國戲曲創作非常注重“詩性寫意”。在結構敘事方面,喬吉曾提出過“鳳頭、豬肚、豹尾”[19(p95)之說,言下之意是“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19(p95),此外,“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19](p95)。到后來,發展為王驥德、李漁等有關戲劇結構的“有機整體說”。以中國戲曲之經典《西廂記》來說,其中開頭有一折“張君瑞鬧道場”,就做到了“起要美麗”,京劇、昆劇、黃梅戲等劇種改編演出時稱為《驚艷》。內中一個細節片段很是“詩性寫意”,崔鶯鶯初見張君瑞時“臨去秋波一轉”,既彰顯了女子的柔情萬種,“回媚一笑百媚生”;同時又為后文兩人生發情愫、衍生故事埋下了伏筆。清代毛西河評此節,揭示了它的寫意之“妙”,指出:“于佇望勿及處又重提‘秋波’一句,于意為回復,于文為照應。”[20](p144)明代萬歷八年(1580)徐士范刊本題評:“‘秋波’一句是一部《西廂》關竅。”[21](p1945)可見,藝術家的匠心獨運,平添了一部劇的豐富意蘊,給受眾留下了無窮遐想。戲曲美學中的這一“詩性寫意”細節,成了許多影視劇爭相模擬的橋段。譬如《湄公河大案》中第十集“高野與葉香初次相見”一節,面對不明來歷的匪徒的暗殺,高野奮不顧身地搶救了葉香性命。葉香離開前,同樣也是通過“回眸一笑”,充滿好感地對視高野,為高野進基洛調查葉香父親秘密制毒及之后兩人之間的故事的生發埋下了伏筆。在這里,“秀”的是當時緊張刺激、驚心動魄的暗殺現場“英雄救美”,“隱”的是今后兩人感情的跌宕起伏,為“恩怨情仇”劇情的展開安了一條伏線,給人以無限遐想,讓人心生余味曲包之感。
從藝術關系論,“詩性寫意”精神的彰顯在于講求“形神”兼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1](p114)張晶先生指出:“習近平同志這里所說的三個‘講求’和一個‘強調’,是對中華美學精神的最為精準的表述。”[22]“形神”是中國古典美學、文藝學中具有辯證統一關系的核心范疇。形,是外表、外相、外貌;神,是內涵、內蘊、內情。形,被創造出來,可直觀感受;神,被涵養其中,需理性把握。形神是辯證統一的,又是矛盾存在的。只有亮麗的外形,沒有內在的神韻,那么將失去生氣活力。如果沒有合適的外形,僅有內蘊的精神,也難以迅捷引發受眾的注意力。經過了長期的實踐和理論的探索,逐漸形成具有我國民族特色的“形神論”。陳良運先生曾指出:“中國詩學的體系結構有一個合乎‘美的規律’的程序:發端于‘志’,重在表現內心;演進于‘情’與‘象’,注意了‘感性顯現’;‘境界’說出現和‘神’的加入,使表現內心與感性顯現都向高層次、高水平發展。”[23](p28)從較早的重形論發展到重神論,再到形神兼備論,強調以形寫神、象外傳神,形神論逐漸走向全面、豐富、辯證和精細,成為中國古典詩學、文藝美學的重要精神傳統。
從藝術品格論,“詩性寫意”精神的最高形態是營構“意境”之美。在中國古典美學、文藝理論中,“意境論”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既抒發、表現和寄托審美主體的思想情感、心理感受,也集中反映和再現審美客體的美學特性、內在品格。意境的生發,是審美主客體交融統一的產物,情景相融后的形象、氛圍,將欣賞者引入一個充滿想象的藝術空間、審美化境。“意境”這一美學范疇,萌芽、孕育于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演進成型于唐宋,在明清時期至近代獲得深入發展。中國文藝美學重視“意境”,與藝術創作注重“意境”的營造有密切關聯,王國維曾揭示了《詩經》的審美創境表現,指出“《詩·蒹葭》一篇,最得風人深致”[24](p73)。相比而言,西方人更重“典型”論。一般來說,典型重再現,意境重表現。典型重寫實,意境重抒情。典型重描繪鮮明的人物形象,意境重抒發藝術家的內心世界[25](p332)。中國的文藝,譬如詩詞歌賦、散文、戲曲、音樂、舞蹈、書法、繪畫、建筑、園林等,都重視創造審美意境,把創造美學意境視為藝術追求與表現的理想極致,彰顯了中國文藝重表現、尚抒情、主寫意的美學傳統。值得指出的是,情、意在意境創造中起主導作用,它決定了對景(對象)的審美認識和創造。宗白華論“意境”時指出:“藝術家以心靈映射萬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現的是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成就一個鳶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26](p358)又說:“就中國藝術方面——這是中國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貢獻的一方面——研尋其意境的特構,以窺探中國心靈的幽情壯采,也是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26](p356-357)就美學品性而言,總體來講,意境具有意與境渾、境生象外、自然之美等特點[27](p282-308)。
二
中華美學“詩性寫意”精神,有助于通過生命體驗,對大自然審美認知,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詩性智慧。
中華美學“詩性寫意”精神具有“人文關懷”的品格。在人與自然的對待性向度上,它引領我們體驗自然風物,關心人文生態,在詩歌的視界中構建人與物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孔子曾引導兒子和弟子多學習《詩》,他強調詩具有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等功能[28](p557),肯定了詩歌創作的“感物”傳統,揭示了《詩經》的“感興”精神。學習《詩經》是一種審美認知的行動,可以認識自然風物的品性,掌握自然的知識和變化規律。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又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7](p65)《文心雕龍·物色篇》說:“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又說:“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7](p693)劉勰強調主觀情志與客觀物象自然融合。人有七情六欲,受到外物的感染,內在的心志就通過詩性想象、詩歌寫作自然抒發。鐘嶸《詩品序》:“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8](p111)鐘嶸認為在大自然中游歷、陶冶、體驗,感于春秋代序,受自然萬物的刺激,必然興起詩歌創作的沖動,詩歌自然而然生發出來。特別是生命中遭際了種種痛苦、悲怨體驗,更是寄托于詩歌中,詩歌是最好書寫心志、寄托情感、平復心理、回歸生命和諧狀態的一種藝術形式。中國人與大自然之間很早就形成了一種和諧共存的理想關系。大自然與人的生命息息相關,大自然的變化成就了藝術家的敏感心靈和萬千創造。中國藝術家根基于大地,自然而然地將情感、心志書寫在大自然之中。
在對待大自然的向度上,中國人選擇了詩性寫意的方式來體驗自然,在自然的世界里書寫生命本真,激活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與大自然形成了一種生命共存、和諧共處的關系。海德格爾以前的西方人多選擇了科學分析的方式來考察自然,自然雖然也進入藝術家的創作視野,但更多的是一種“主客二分”的關系,呈現對立的、緊張的、分裂的、局限的、間斷的狀態,未能走向“主客相融”“天人合一”。英國學者勞倫斯·比尼恩在《亞洲藝術中人的精神》一書中指出:“如果說有一點最值得我們向東方藝術學習,那就是這種持續性。在那里,我們看不到‘美術’和‘裝飾藝術’之間的分家,整個藝術乃是一個整體。”[29](p141)他論中國山水畫時指出:“大自然的生命并不是被設想為與人生無關的,而被看作是創造出宇宙的整體,人的精神就流貫其中。”[29](p54)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表現,乃在于“中國人從來也沒有與這個生活的中間世界斷過聯系;他們不斷地在探討它,這不是出于歐洲人的那種科學的好奇心,而是似乎出于——可以這樣說——一種作這個宇宙的公民的欲望,因此,不僅獵獸而且小鳥和昆蟲,還有比這更深遠一層的、我們稱之為無生命的東西,也都被包括進他們關于宇宙的生命這一意識之中”[29](p13)。他還強調:“這是我對中國的藝術所要強調指出的一點,它與原始人的聯系,以及對于有生命之物的那種慢慢擴大、所無不包的同情。這種藝術把自己的根深深植于大地上。”[29](p13)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離不開詩性寫意精神,需要激活和弘揚中華美學的“詩性寫意”精神。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是生命共同體、生產共同體、生活共同體、生態共同體,最終體現為以人民為中心的命運相連,休戚與共。面對日益嚴峻的全球氣候變暖、生態環境污染、生活食品安全等問題,我們必須深入反思過往的發展理念和實踐行為。不堪重負的地球用頻發的地震、海嘯、狂風暴雨、變異氣候等現象警示我們,地球生態危機問題已經到了極限程度了。非理性的生產,無節制的消費,不可持續的發展,地球人的種種“異化”表現,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改變,勢必毀滅整個地球。詩性寫意的精神,引領我們親悅自然,體驗大自然的悲歡,認識大自然的苦痛與快樂。激活“詩性寫意”精神,讓我們“道法自然”,關心大自然,書寫大自然,與大自然命運共存。老子說:“道生萬物,天人合一”,“福禍相依、物極必反”[30](p105);莊子說:“與人為善,與物為春”[31](p169);《禮記·中庸》:“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2](p1198)……這些激活中國人“詩性”智慧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正視現狀,破除主客二分思維,調節心物失衡關系,堅持“綠色發展”理念,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三
中華美學“詩性寫意”精神,有助于引領當代中國人超越生活俗常,掙脫功利束縛,過一種詩意化、審美化的人生。
中華美學“詩性寫意”精神具有“審美超越”的品格。如果說通過“人文關懷”,構建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的和諧關系,那么“審美超越”,則在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對待性向度上引領人解放自我,詩意棲居。南宋陸游在《澹齋居士詩序》中說:“蓋人之情,悲憤積于中而無言,始發為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詩為百代法。”[33](p399)優秀的詩人能結合自己的悲苦生命體驗,點燃自己的創作詩情,通過詩歌書寫來發泄內心痛苦,通過藝術審美來超越俗常困頓。他們所創作的詩歌,因為情感真摯、體驗深刻,故而感人至深。在世俗人生中不得志、不快意,卻成就了他們的創作,這些詩人,在詩歌世界里面,掙脫了現實的、物質的、功利的、目的的束縛,去尋找和追求藝術的、審美的、精神的自由和超越,他們富有才情,又有現實體驗,往往唱出時代的最強音,最終成為后世詩歌創作的楷式。
較早的時候,蔡元培、林語堂、宗白華曾揭示,中國人缺乏純粹的信仰,而通過詩歌、藝術等來超解生活苦難、人生痛楚。藝術、審美的理想追求,培育和成就了中國文化的“詩性”維度,在詩歌的、藝術的世界里,人們得以解放自我,卸下心理抱負,超越現實俗常功利追求和遭際的人生痛苦。劉小楓、張法、王一川、劉士林、金雅等學者均曾指出,中國文化美學的理想,不是科學實證的,也不是宗教幻想的,而是藝術審美的。的確,中國人在人生不得志時,選擇獨善其身,或隱逸林泉、躬耕田畝;或游山玩水,窺情風景;或寄情于琴棋書畫,怡情養性,追求人格解放和心靈自由。不同于西方信仰上帝、基督,寄希望于天堂;亦不同于印度佛教,游心于來世。他們追求當下性、現實性,在詩歌、藝術的世界里來解決人生問題,達到藝術、審美與人生的貫通,回歸自由、和諧、完滿的狀態。
品讀中國古人的詩歌,我們仿佛聽到了來自古老遠方的音響。謝靈運《七里瀨》說:“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34](p143)一代又一代優秀詩人的創作,滋養了后來人的生命。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杜甫曾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又說:“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跡五首》)繼承了“詩可以怨”傳統的庾信,在入北之后寫下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思鄉文字、隱逸文字、悲怨文字。這些文字激活了杜甫的詩興,成就了杜甫的詩境。可以說,沒有庾信在之前的積淀和鋪墊,就沒有杜甫在后來的成就和影響。鮑照之于李白,陶淵明之于蘇軾……我們可以開列一長串名單。直至今天,我們依然以他們為楷模,引他們為精神導師和人生知己,從他們的詩歌中汲取學養,激活心靈,收獲智慧。陳炎《中國“詩性文化”的五大特征》一文從詩性文化特殊地位、精神主宰與影響、古人的行為方式、信仰方式、語言特性等五個方面考察中國“詩性文化”的特征,揭示中國詩歌的“彌補宗教信仰”功能,強調詩歌具有可以令人解放的精神品格[35]。“詩性寫意”精神的承傳,讓中國人活得不再沉重,走向了超脫與逍遙。區別于西方人通過耶穌基督的上帝之愛而得拯救,中國人因詩歌的審美救贖而卸下了人格心靈包袱,活出了真我的風采。
四
中華美學“詩性寫意”精神,可以為建構當代“民族化”“本土化”藝術創作理論體系提供精神學養。
中華美學“詩性寫意”的精神還具有“涵養創化”的品格。在人與藝術的對待性向度上,其所涵養的精神可為后世的藝術創作提供精神學養。譬如:影視劇創作領域,有學者感于“取悅世界電影節、模仿外來大片、迎合所謂世界潮流、做作式的西方視點”導致中國影視“獨特性”被淹沒的狀況,倡導中國影視藝術應該走“民族化”的道路,建立起“中國民族化的影視劇美學理論體系”[36]。黃會林先生指出:“中國古典戲劇、詩詞、繪畫等藝術作品,在處理時間和空間的技巧上,常常與蒙太奇鏡頭語言處理畫面的方法神似;細加分析也常有運用特寫、遠景、中景等畫面和畫面組接的技巧,這為我們影視藝術創作和發展,提供了美學的啟示。”[37](p10)的確,中華美學“詩性寫意”精神涵養的藝術構思論(如虛靜、神思、感興、物化等)、藝術創作論(虛實、動靜、有無、法度、體勢等)、藝術表現論(情理、理趣、情景、情采、文質、通變等)、藝術形象論(形神、真假、意象、意境等)、藝術風格論(自然、風骨等)中均有值得我們檢視、整理和傳承的學養,這些富有中華民族文化特色、品格的思想智慧,也對當下的影視劇創作具有啟示作用。
早期中國優秀的影視人自覺地、較好地傳承了中華美學詩性寫意精神,創作出來的作品至今仍然是經典,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啟迪了一些新生代的影視人向之學習和看齊。臺灣著名導演李行曾說:“我自己受到大陸三、四十年代電影的影響很深,如《漁光曲》《小城之春》《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關不住的春光》《新閨怨》以及昆侖影業公司等一系列的影片。那時是在高中的時候,覺得當時的中國電影太好了,以致于我連西片都不看的。那些電影對我的影響非常深。”[38](p15)柯靈評蔡楚生的電影創作時指出,《一江春水向東流》直接引用了李后主《虞美人》里的詞句,他說:“這些古詩的意境,推陳出新,都溶入了膠卷。”[39](p318)黃會林先生指出:“在中國新時期電影中,中國美學傳統同樣發揮著它的獨特作用。她舉例說,謝晉導演的《天云山傳奇》中有一個著名場面:女主人公馮晴嵐在風雪彌漫中,用板車拉著病重的羅群,在冰天雪地間漸行漸遠的瘦小身影……那分明是蘇東坡特有的意境:‘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其蕭瑟惆悵之意,盡在不言中。通篇整體的精心營構,使這部洋溢著民族文化氛圍的作品,列入了中國電影精品畫廊。”[37](p8)
人,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上。詩意點亮了我們的生活,藝術寫意讓生活詩化。雷內·克萊爾說:“攝影機的鏡頭把它碰到的一切東西都染上神話色彩,把它視野以內的一切都搬到現實之外的一個由表象、幻影和夢境所統治的天地之中。”[40](p17)電視劇創作,通過鏡頭塑造,浸蘊了許多詩意。品賞體味詩性寫意的電視劇,掠過觀眾頭腦中的鏡頭、映像、畫面,肯定還少不了杏花春雨、雨夜小巷、小橋麗人等江南風光意象。江南水鄉的橋千姿百態,各顯其美。更有數不盡的茶樓,飯館,手工作坊,紅花綠樹,曲園回廊,樓閣亭榭……江南風光秀麗,氣韻氤氳,本身就極像一首首詩歌。江南水鄉的詩性寫意,自然離不開搖曳多姿的美麗女子。黃健中導演曾在導演《美麗無聲》日記中寫道“拍年輕梳頭女孩,注意抓群體細節,很有特點,木屐在石階上,上上,下下,是很有些味道的,下雨時再捕捉一些有雨傘、木屐的特寫”[41](p57-58)。中國電視劇史上,《大明宮詞》《新白娘子傳奇》《桃花扇》《瑯琊榜》等古裝劇是體現詩情畫意的最好證明。此外,還有一些電視劇如《青青子衿》《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寂寞空庭春欲晚》《人間至味是清歡》《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年花開月正圓》《香蜜沉沉燼如霜》《小樓昨夜又東風》等,僅從劇名就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的詩情畫意。又,一些電視劇中人物的名字充滿了與角色性格、命運等相吻合的詩意文采,寓意深刻,意味深長,讓受眾久久難以忘懷,譬如:《天龍八部》中的木婉青、《七劍下天山》中的練霓裳、《天涯明月刀》中的南宮翎、《仙劍奇俠傳三》中的夕瑤和紫萱、《古劍奇譚》中的芙蕖、《蜀山戰紀》中的玉無心、《雪花女神龍》中的歐陽明月、《香蜜沉沉燼如霜》中的旭鳳、《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的顧廷燁,不贅述。
綜上可見,“詩性寫意”精神是中華美學精神的重要構成。從藝術生發論,“詩性寫意”精神的起點與基礎在于“詩興”;從藝術語言論,“詩性寫意”精神的要義與表達在于“隱秀”;從藝術關系論,“詩性寫意”精神的彰顯在于講求“形神”兼備;從藝術品格論,“詩性寫意”精神的最高形態是營構“意境”之美。中華美學“詩性寫意”精神具有“人文關懷”“審美超越”“涵養創化”等品格,當下,大力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詩性寫意”精神,能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詩性智慧、為建構“民族化”“本土化”藝術創作理論體系提供精神學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