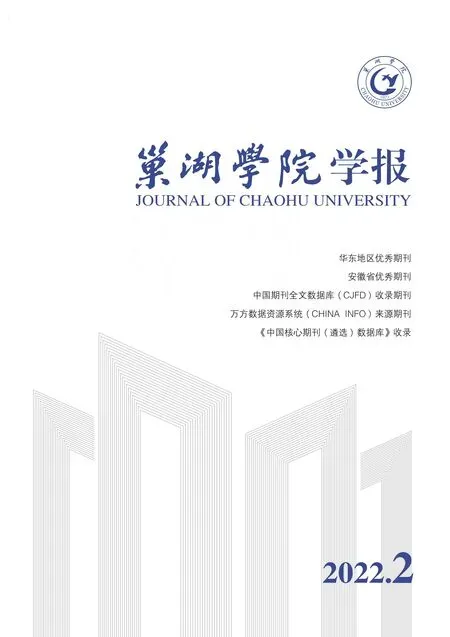阿倫特與馬爾庫(kù)塞現(xiàn)代性批判的比較研究及啟發(fā)
張 潛
(上海師范大學(xué) 哲學(xué)與法政學(xué)院,上海 200234)
引言
現(xiàn)代性批判在不斷涌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和新問(wèn)題中發(fā)展出了很多條脈絡(luò),其中阿倫特與馬爾庫(kù)塞兩位哲學(xué)家的現(xiàn)代性批判構(gòu)成了值得進(jìn)行比較分析的兩重維度。阿倫特與馬爾庫(kù)塞都是20世紀(jì)西方杰出的政治哲學(xué)家,二人的經(jīng)歷也有許多相似之處,那么,他們的現(xiàn)代性理論中是否存在對(duì)話的可能性呢?在阿倫特的現(xiàn)代性批判中,公共領(lǐng)域的衰落是政治領(lǐng)域現(xiàn)代化問(wèn)題的核心,而“惡的平庸性”是發(fā)生在人身上的最普遍的危機(jī),她希望人們鼓起勇氣去行動(dòng);馬爾庫(kù)塞痛斥技術(shù)理性消除了人的否定的向度,壓抑了人的愛(ài)欲,鼓勵(lì)人們從拒絕中尋找救贖。從現(xiàn)有研究來(lái)看,國(guó)內(nèi)理論界尚未有將他們直接進(jìn)行比較研究的文獻(xiàn),但是常有將阿倫特與馬爾庫(kù)塞分別同馬克思進(jìn)行比較研究的文獻(xiàn),其中“勞動(dòng)”成為了最主要的關(guān)鍵詞。因此通過(guò)“勞動(dòng)”這一條隱秘線索,并嘗試跳過(guò)馬克思這一中介,直接探究阿倫特與馬爾庫(kù)塞現(xiàn)代性批判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是可行的。
阿倫特認(rèn)為在現(xiàn)代,勞動(dòng)的范圍不斷擴(kuò)大,取代了行動(dòng)與工作的地位,使得世界異化成為消費(fèi)的世界,造成人的復(fù)數(shù)性與公共領(lǐng)域的消失,阿倫特因此“批判”了馬克思的勞動(dòng)觀。在關(guān)于阿倫特勞動(dòng)話語(yǔ)的研究中,呈現(xiàn)出兩極分化的特點(diǎn),一方試圖論證阿倫特與馬克思在勞動(dòng)話語(yǔ)上具有相同的內(nèi)核,另一方則批判阿倫特是對(duì)馬克思的歪曲。持相同論的學(xué)者有的從手段上論證,“馬克思對(duì)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條件下異化勞動(dòng)的批判與阿倫特對(duì)從‘資本統(tǒng)治’到‘技術(shù)控制’展開(kāi)的批判殊途同歸”[1];有的從目的上論證,“阿倫特對(duì)馬克思的挑戰(zhàn)并非否定勞動(dòng)本身的意義,而是為了揭示西方現(xiàn)代實(shí)踐思想用勞動(dòng)代替行動(dòng)的危機(jī)”[2]。持批判論的學(xué)者又分為誤解論和分歧論,誤解論認(rèn)為,阿倫特“不理解馬克思勞動(dòng)觀的研究對(duì)象和宗旨,也就遮蔽了它的科學(xué)性”[3],且阿倫特 “忽略了馬克思的勞動(dòng)解放這個(gè)重要思想,因而不能全面的批判技術(shù)社會(huì)”[4];分歧論的觀點(diǎn)是從阿倫特的理論本源出發(fā),認(rèn)為阿倫特“對(duì)勞動(dòng)和技術(shù)及二者關(guān)系的理解是抽象的、非歷史的,因此阿倫特對(duì)馬克思的批判是不成立的”[5]。馬爾庫(kù)塞作為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論受到馬克思勞動(dòng)異化理論、盧卡奇物化理論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響,他試圖將心理學(xué)分析與馬克思主義結(jié)合,從新的角度解釋勞動(dòng)異化,認(rèn)為勞動(dòng)是最基本的愛(ài)欲活動(dòng),勞動(dòng)的解放與愛(ài)欲的解放密不可分。對(duì)馬爾庫(kù)塞勞動(dòng)話語(yǔ)的研究呈現(xiàn)出驚人的一致性,即普遍認(rèn)為“馬爾庫(kù)塞將現(xiàn)代社會(huì)對(duì)人心理與靈魂的奴役擺上臺(tái)面,是對(duì)資本主義發(fā)展新現(xiàn)象的合理解釋,但仍有不成熟之處”[6]。馬爾庫(kù)塞在《單向度的人》中對(duì)技術(shù)理性的批判與一個(gè)世紀(jì)前馬克思的《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相比,反而入了馬克思沒(méi)有陷入的“人本主義陷阱”[7],而“《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中馬克思對(duì)勞動(dòng)‘積極的方面’和‘消極的方面’作出的區(qū)分也被馬爾庫(kù)塞所忽視,致使他關(guān)于愛(ài)欲解放的理論成為了現(xiàn)代烏托邦”[5]。
前人的研究中揭示出阿倫特與馬爾庫(kù)塞之間存在共同的話語(yǔ)——?jiǎng)趧?dòng),因此勞動(dòng)可以成為二者現(xiàn)代性批判理論比較研究的基點(diǎn)。從勞動(dòng)批判的比較出發(fā),再延伸到政治領(lǐng)域的批判和人自身的批判的比較,可以全面厘清他們?cè)趯?duì)“勞動(dòng)”的觀點(diǎn)產(chǎn)生分歧的基礎(chǔ)之上是如何發(fā)展成兩重維度的現(xiàn)代性批判,并探究阿倫特的公共領(lǐng)域理論與馬爾庫(kù)塞的愛(ài)欲解放理論能否形成互補(bǔ)。這對(duì)于更好地理解現(xiàn)代性以及理解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科技、勞動(dòng)與政治的關(guān)系,從而避免走向資本主義國(guó)家所面臨的現(xiàn)代性困境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
一、勞動(dòng)話語(yǔ)
“勞動(dòng)”是阿倫特與馬爾庫(kù)塞的政治哲學(xué)中共同具有的隱藏話語(yǔ),也是把他們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一條紐帶,二者的現(xiàn)代性批判都以勞動(dòng)為基礎(chǔ)。他們的主要矛盾也在于對(duì)勞動(dòng)的看法:阿倫特否定勞動(dòng),批判勞動(dòng)侵入公共領(lǐng)域造成人類公共性和政治生活的消失;馬爾庫(kù)塞將愛(ài)欲與勞動(dòng)結(jié)合,批判技術(shù)理性和操作原則造成的勞動(dòng)異化,提出勞動(dòng)的解放就是愛(ài)欲的解放。對(duì)勞動(dòng)的不同理解體現(xiàn)出阿倫特與馬爾庫(kù)塞不同的思考向度,也在政治學(xué)上產(chǎn)生了兩種不同的現(xiàn)代性批判路徑。要理解阿倫特與馬爾庫(kù)塞現(xiàn)代性批判各自的特點(diǎn)以及他們之間的分歧,需要先理解他們的勞動(dòng)話語(yǔ)。
阿倫特是以亞里士多德關(guān)于人類活動(dòng)的劃分法為理論依據(jù),展開(kāi)了她自己的勞動(dòng)話語(yǔ)。亞里士多德在柏拉圖思考與行動(dòng)二分的思想基礎(chǔ)上,將人類活動(dòng)分為從事生產(chǎn)、治理等活動(dòng)的積極生活與專職思考真理的沉思生活,又將積極生活分為行動(dòng)、工作和勞動(dòng)。在西方政治哲學(xué)傳統(tǒng)的語(yǔ)境下,沉思生活要高于積極生活,因?yàn)槌了际请x真理最近的活動(dòng)。在積極生活中,行動(dòng)是人脫離了生產(chǎn)活動(dòng)和私人領(lǐng)域,在公共領(lǐng)域中勇敢展現(xiàn)自己,用言語(yǔ)說(shuō)服他人的活動(dòng),也是最具有政治性的活動(dòng);工作是技藝人制作物品的活動(dòng),技藝人工作的目的是制作“有用的物品”,使人在世界上更好地生活下去;勞動(dòng)是必然性的、為了維持生命必需品進(jìn)行的生產(chǎn),勞動(dòng)的產(chǎn)品就是消費(fèi)品,很快就會(huì)被消費(fèi)掉。勞動(dòng)對(duì)工作的同化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消費(fèi)的世界。“技藝與勞動(dòng)的區(qū)別在于,技藝體現(xiàn)了世界的持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體現(xiàn)了物本身的物性。技藝生產(chǎn)出的物體現(xiàn)了人與世界的相互熟悉,人與物之間的關(guān)系是親切的,而不是消費(fèi)性的”[8]。現(xiàn)代化無(wú)序發(fā)展的后果是工業(yè)越發(fā)達(dá),生產(chǎn)力越提高,工作向勞動(dòng)的蛻化就越明顯,隨著勞動(dòng)動(dòng)物進(jìn)一步擴(kuò)大勝利果實(shí),私人領(lǐng)域的勞動(dòng)逐漸占據(jù)公共領(lǐng)域,必然導(dǎo)致公共領(lǐng)域的衰落。在阿倫特看來(lái),人類公共性和政治生活的實(shí)現(xiàn)有三個(gè)必要條件——誕生性、復(fù)數(shù)性和交往性,那么勞動(dòng)是如何破壞這三個(gè)條件從而破壞公共領(lǐng)域的呢?首先,誕生性意味著人能從偶然中開(kāi)端啟新,而勞動(dòng)是一種只能在消費(fèi)中體現(xiàn)自身意義的活動(dòng),勞動(dòng)動(dòng)物一直生活在必然性之中,被循環(huán)往復(fù)的勞動(dòng)和消費(fèi)所掌控,因此他們雖然人丁興旺,卻缺乏誕生性。其次,復(fù)數(shù)性要求每個(gè)人可以自由表達(dá)自己的獨(dú)特性和與他人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來(lái)源于人類思想和靈魂的自由,需要通過(guò)行動(dòng)和言說(shuō)來(lái)表達(dá)。在消費(fèi)社會(huì)中勞動(dòng)取代了行動(dòng)和言說(shuō),人的靈魂被同質(zhì)化,所展現(xiàn)出來(lái)的差異是在消費(fèi)主義控制下的差異,從而人類失去復(fù)數(shù)性,成為原子化的人。最后,交往是人們?cè)谄降鹊幕A(chǔ)上表達(dá)復(fù)數(shù)性的活動(dòng),在交往的過(guò)程中產(chǎn)生著政治權(quán)力——維持公共領(lǐng)域的權(quán)力。在勞動(dòng)者社會(huì)中,人類差異性被抹平,由此帶來(lái)的只是空洞的法律上的平等,而不是平等交往的權(quán)利,因此交往性的權(quán)利也被阻斷,維持公共領(lǐng)域的力量日漸衰弱。
馬爾庫(kù)塞提出,在發(fā)達(dá)資本主義社會(huì),勞動(dòng)呈現(xiàn)出新的特征。隨著自動(dòng)化的發(fā)展,工人的勞動(dòng)效率提升,必要?jiǎng)趧?dòng)時(shí)間減少,與此同時(shí)對(duì)智力性生產(chǎn)和分工合作的要求越來(lái)越高。這樣的趨勢(shì)一方面通過(guò)減少工人的痛苦掩蓋了剝削的事實(shí),另一方面通過(guò)將工人與工廠形成更緊密的依存關(guān)系削弱了工人反抗的意愿。在一些地區(qū),工廠給予工人參與生產(chǎn)決策的權(quán)力,工人為此感到自豪。技術(shù)進(jìn)步縮減了勞動(dòng)時(shí)間,改變了勞動(dòng)形式,由此削弱了工人階級(jí)的否定地位。資本家的面孔從兇惡的剝削者變成了和善的管理者,工人階級(jí)意識(shí)到自己的利益已經(jīng)與社會(huì)和企業(yè)綁定在一起,并且為自己得到的利益感到滿足,因而不再追求否定與自由,失去了革命的力量。馬爾庫(kù)塞擴(kuò)展了馬克思的勞動(dòng)異化理論。他將弗洛伊德的愛(ài)欲理論運(yùn)用到對(duì)勞動(dòng)的分析上。在原始狀態(tài)或在未來(lái)理想狀態(tài)的社會(huì)中,未異化的勞動(dòng)(工作)是一種消遣,是對(duì)人體愛(ài)欲能量的自然釋放,滿足了人自由發(fā)展的條件。在發(fā)達(dá)工業(yè)社會(huì)中,資本不斷要求增加勞動(dòng)的時(shí)間,而且使用迫使人們“自愿”的、用美好生活的愿景來(lái)誘惑人們的方式。勞動(dòng)時(shí)間的增加暴露了這種美好生活的虛偽,這種異化的勞動(dòng)只是在不斷增加對(duì)人類正常本能和否定性向度的壓抑,進(jìn)而阻礙人的自由與升華。
阿倫特對(duì)消費(fèi)社會(huì)的批判和馬爾庫(kù)塞對(duì)技術(shù)理性的批判的共同點(diǎn)在于,他們都意識(shí)到科技發(fā)展為理性的統(tǒng)治鋪平了道路。現(xiàn)代人“墮落”、失去自由的根源在阿倫特那里是“生命為至高善”,在馬爾庫(kù)塞那里是“免于匱乏的自由”,都代表了將物質(zhì)生產(chǎn)與消費(fèi)作為根本追求的一種價(jià)值觀。也就是說(shuō),人類本性中對(duì)消費(fèi)的需求和現(xiàn)代科學(xué)技術(shù)對(duì)這種需要的滿足構(gòu)成了這兩種批判的理論基礎(chǔ)。阿倫特對(duì)勞動(dòng)持否定批判的態(tài)度,并且她認(rèn)為馬克思誤將“工作”與“勞動(dòng)”混為一談,為了維持生命活動(dòng)必然性的勞動(dòng)是在削弱人的政治性;馬爾庫(kù)塞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對(duì)勞動(dòng)和工人階級(jí)的態(tài)度是肯定的,他批判的是技術(shù)理性造成的異化勞動(dòng)和工人階級(jí)在舒適的生活中對(duì)資本主義的妥協(xié)。因此從勞動(dòng)這一點(diǎn)出發(fā),阿倫特與馬爾庫(kù)塞分別從不同的方向上為我們帶來(lái)了現(xiàn)代性批判的兩重維度。
二、現(xiàn)代性的批判
阿倫特認(rèn)為政治領(lǐng)域現(xiàn)代性危機(jī)的核心問(wèn)題是公共領(lǐng)域的衰落。公共領(lǐng)域衰落的理論原因是傳統(tǒng)的斷裂和世界的異化,“現(xiàn)代對(duì)于我們的世界和人類一般狀況的改變已經(jīng)到了這樣一個(gè)程度,對(duì)傳統(tǒng)理所當(dāng)然的依賴已經(jīng)變得不再可能了”[9]。柏拉圖將真理世界與現(xiàn)象世界二分,創(chuàng)造了西方政治哲學(xué)的傳統(tǒng),這個(gè)傳統(tǒng)就是以哲學(xué)作為政治的尺度,把“理性”當(dāng)作政治統(tǒng)治的目的,阿倫特認(rèn)為這是最早的權(quán)威概念。現(xiàn)代科學(xué)的發(fā)展和笛卡爾的懷疑主義哲學(xué)使人們發(fā)現(xiàn)了阿基米德點(diǎn),并將阿基米德點(diǎn)植入人們自身,導(dǎo)致了沉思生活與積極生活的倒轉(zhuǎn)以及傳統(tǒng)信仰和權(quán)威的消失。導(dǎo)致公共領(lǐng)域衰落的第二個(gè)大事件是世界的異化。哲學(xué)的轉(zhuǎn)變使“思”成為了“做”的奴仆,理論開(kāi)始為實(shí)踐服務(wù)。這種思想層面的轉(zhuǎn)向與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相結(jié)合,促進(jìn)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傳統(tǒng)政治領(lǐng)域的邊界開(kāi)始崩潰,社會(huì)取代了公共領(lǐng)域。人與人之間自由平等的交往轉(zhuǎn)變成為了積累財(cái)富而工作以及為了生活需要而勞動(dòng),傳統(tǒng)的“政治”從概念上被抹除了,取而代之的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權(quán)力政治,這是政治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急速衰落的原因。
公共領(lǐng)域衰落的現(xiàn)實(shí)原因是民族國(guó)家的異化與資本主義的擴(kuò)張。民族國(guó)家是在主權(quán)和人權(quán)原則下建立起來(lái)的,但是當(dāng)資產(chǎn)階級(jí)取得政權(quán)之后,民族國(guó)家很快成為了資本擴(kuò)張的工具。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西方進(jìn)入帝國(guó)主義時(shí)代,民族國(guó)家體系便在20世紀(jì)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瓦解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shí)期,在以納粹德國(guó)為代表的極權(quán)主義國(guó)家中,民族主義已經(jīng)異化成了對(duì)外擴(kuò)張、對(duì)內(nèi)維護(hù)統(tǒng)治的工具。帝國(guó)主義發(fā)展到極端所產(chǎn)生的極權(quán)主義與古代的一切暴君、獨(dú)裁者的統(tǒng)治不同,它的恐怖之處在于沒(méi)有人能為它所犯下的罪行負(fù)責(zé)。“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沒(méi)有人有罪”[10]。在壟斷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階段,人和人之間的差異被逐漸抹平,逐漸變成了千人一面的大眾。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迫使人們走出原先的小共同體,加入社會(huì)的大家庭。社會(huì)不是一個(gè)可以用言說(shuō)和行動(dòng)展示自己獨(dú)特性的公共領(lǐng)域,在社會(huì)中人們做的是原先在私人領(lǐng)域中做的事——因?yàn)樾袆?dòng)和沉思都不再有意義,人們關(guān)注的只有勞動(dòng)與消費(fèi)。資本主義社會(huì)還把財(cái)產(chǎn)的概念偷換為財(cái)富,在古代,擁有財(cái)產(chǎn)是一個(gè)人參與政治生活的資格,它使得一個(gè)人不受生命必然性的制約而得以參加公共生活,是具有政治性的;而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jí)憲法保護(hù)的“財(cái)產(chǎn)”實(shí)質(zhì)上是財(cái)富,財(cái)富追求的是不斷的擴(kuò)張,只關(guān)心自身增殖而不關(guān)心公共生活,是反政治的。這樣一個(gè)無(wú)政治社會(huì)的統(tǒng)治者不是某一個(gè)人,而是整個(gè)官僚機(jī)構(gòu),每個(gè)人,包括官僚本身都只能按照指令活動(dòng)。在這個(gè)社會(huì)里沒(méi)有公共領(lǐng)域,只有“私人領(lǐng)域中的公共面孔”,任何人,除非完全逃避政治,都會(huì)受到政府行為的牽連。在一個(gè)富有煽動(dòng)性的惡人引導(dǎo)下,人越想做一個(gè)好公民,就越會(huì)做出可怕的惡行。只有當(dāng)每個(gè)人都行動(dòng)起來(lái)時(shí),才有可能擺脫這種恐怖,然而不幸的是,在這個(gè)社會(huì)中沒(méi)有公共領(lǐng)域,也就沒(méi)有了行動(dòng)的空間。知道如何擺脫卻又不能去行動(dòng),這是納粹式極權(quán)主義最恐怖的地方,也是阿倫特的現(xiàn)代性批判要解決的問(wèn)題。
在馬爾庫(kù)塞看來(lái),現(xiàn)代科學(xué)技術(shù)既能給人以自由,又能限制人的自由。“一種舒舒服服、平平穩(wěn)穩(wěn)、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發(fā)達(dá)的工業(yè)文明中流行,這是技術(shù)進(jìn)步的標(biāo)志”[11]。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理論認(rèn)為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能增加人的自由,促進(jìn)人從必然王國(guó)向自由王國(guó)的過(guò)渡。“節(jié)約勞動(dòng)時(shí)間等于增加自由時(shí)間,即增加使個(gè)人得到充分發(fā)展的時(shí)間,而個(gè)人的充分發(fā)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chǎn)力反作用于勞動(dòng)生產(chǎn)力”[12]。自由時(shí)間的增加使人有更充分的條件實(shí)現(xiàn)全面自由的發(fā)展。但馬爾庫(kù)塞認(rèn)為,發(fā)達(dá)工業(yè)社會(huì)實(shí)現(xiàn)生產(chǎn)效率的極大提高之后,卻使得自由無(wú)法被實(shí)現(xiàn)。這是因?yàn)樵谖镔|(zhì)匱乏的年代人們所呼吁的各種自由,如思想、言論與信仰的自由,實(shí)質(zhì)上是通過(guò)對(duì)社會(huì)的批判來(lái)達(dá)成建立一個(gè)更好的社會(huì),建立更好的社會(huì)則是為了解決物質(zhì)的匱乏。“免于匱乏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具體實(shí)質(zhì)”[11],一旦社會(huì)有能力解決物質(zhì)匱乏的問(wèn)題,那么傳統(tǒng)的自由訴求便喪失了它的本質(zhì),一切批判性的理論也失去了意義。在這個(gè)社會(huì)中只需要服從和同意,維持現(xiàn)存的秩序就可以讓每個(gè)人過(guò)上富足安定的生活,與此相比,對(duì)政治權(quán)利、人的自由的追求會(huì)破壞這一社會(huì)的穩(wěn)定,成為不利因素。通過(guò)與人的擺脫物質(zhì)匱乏的需求的綁定,技術(shù)理性在這里粉墨登場(chǎng)并成為了支配一切的霸主。技術(shù)理性對(duì)人的控制不僅在于控制了物質(zhì)的生產(chǎn),更是在于它“創(chuàng)造了”并不存在的需求。馬爾庫(kù)塞把人的需求分為自由需求和抑制性需求,技術(shù)理性的統(tǒng)治壓制了要求自由的那些需求,發(fā)展了抑制性的需求,這一類需求要求不斷延續(xù)人們的過(guò)度生產(chǎn)與消費(fèi),并且不會(huì)提出反抗。技術(shù)理性抹去了人的否定與超越的向度,造就了“單向度的人”和“單向度的社會(huì)”。單向度的人除了肯定和順從,沒(méi)有其他的選擇。技術(shù)理性巧妙地利用科學(xué)消滅了反對(duì)的聲音,一方面技術(shù)進(jìn)步帶來(lái)了更富足舒適的生活,另一方面,技術(shù)理性標(biāo)榜自己為“科學(xué)的”,通過(guò)掌握一切話語(yǔ)的解釋權(quán)來(lái)控制人們的行為。在發(fā)達(dá)工業(yè)社會(huì),技術(shù)本身就是意識(shí)形態(tài),“在發(fā)達(dá)資本主義社會(huì),技術(shù)合理性在生產(chǎn)機(jī)構(gòu)中得到了具體化(盡管對(duì)它的使用是不合理的)。這不僅適用于工廠、工具和資源開(kāi)發(fā),也適用于按‘科學(xué)方式’來(lái)安排的、適應(yīng)并管理著機(jī)械加工進(jìn)程的勞動(dòng)方式”[11]。意識(shí)形態(tài)是技術(shù)統(tǒng)治的重要工具,樹立一個(gè)外部的敵人讓人們感到恐懼,迫使人們認(rèn)同發(fā)展科技、經(jīng)濟(jì)、軍事的重要性,技術(shù)便有了理由讓人們安分待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并且由于人們不敢想象也無(wú)法想象有超越意識(shí)形態(tài)的更好的社會(huì)的存在,批判和否定的聲音也被壓制。
在文化領(lǐng)域上,單向度社會(huì)用低俗的大眾文化擠壓了精英文化,阿倫特在《文化的危機(jī):其社會(huì)和政治意蘊(yùn)中》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他們都認(rèn)為是消費(fèi)主義和商業(yè)秩序在攫取傳統(tǒng)文化,制造供大眾消費(fèi)的娛樂(lè)品。馬爾庫(kù)塞認(rèn)為低俗文化流行的后果是消除了存在于藝術(shù)之中的否定向度,產(chǎn)生了一種調(diào)和性的多元主義,這是文化領(lǐng)域中的新極權(quán)主義。技術(shù)統(tǒng)治中的人們也受到操作主義話語(yǔ)的控制。統(tǒng)治者使用一套由“自明的分析性命題”組成的術(shù)語(yǔ)來(lái)命令、組織、引導(dǎo)人們?nèi)プ觥⑷ベI、去接受。“這樣一套術(shù)語(yǔ)能把意義封閉在規(guī)制所給出的條件范圍內(nèi)”[11]。如同“戰(zhàn)爭(zhēng)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wú)知即力量”的奧威爾式語(yǔ)言,將對(duì)立的概念強(qiáng)制統(tǒng)一,具有強(qiáng)大的反否定能力。在這種語(yǔ)言的管理下,人們對(duì)一般問(wèn)題的不滿被分解成具體問(wèn)題加以解決,人們會(huì)感謝具體問(wèn)題的解決而忽視背后根本的社會(huì)矛盾。這種因技術(shù)理性發(fā)展到極端而產(chǎn)生的極權(quán)主義并不恐怖,反而是以需求滿足者、問(wèn)題解決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人們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技術(shù)的奴役。
阿倫特與馬爾庫(kù)塞在政治領(lǐng)域的批判上的主要分歧是阿倫特強(qiáng)調(diào)人們失去了政治生活的空間與條件,馬爾庫(kù)塞強(qiáng)調(diào)的是人們失去了從事政治活動(dòng)的意愿。阿倫特更擅長(zhǎng)于從政治性的角度分析社會(huì)問(wèn)題,馬爾庫(kù)塞則是從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的角度分析政治問(wèn)題。這體現(xiàn)了他們?cè)诂F(xiàn)代性批判中的兩種視角,因而也帶來(lái)了兩種不同的結(jié)果。相比較而言,阿倫特更重視歷史研究,對(duì)公共領(lǐng)域衰落和西方極權(quán)主義形成的原因做出的解釋更符合我們對(duì)于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rèn)知;馬爾庫(kù)塞的理論更多的基于發(fā)達(dá)工業(yè)社會(huì)的現(xiàn)實(shí),對(duì)現(xiàn)代性的種種弊端試圖用技術(shù)理性的統(tǒng)治能力完全解釋,但是技術(shù)理性本身不是原因,而是人們?cè)谇艾F(xiàn)代的行動(dòng)留下的后果。“歐洲民族國(guó)家體系的衰落,地球在經(jīng)濟(jì)和地理上的萎縮,以至于繁榮和蕭條成為了世界范圍內(nèi)的現(xiàn)象,人類變成了一個(gè)真正的實(shí)體……所有這些都標(biāo)志著這一發(fā)展已經(jīng)開(kāi)始達(dá)到了它的最后階段”[13],通過(guò)阿倫特的描述,我們能看到一幅清楚的現(xiàn)代政治社會(huì)畫卷,她詳細(xì)描繪了世界異化的過(guò)程;而在馬爾庫(kù)塞那里,更多的是對(duì)技術(shù)統(tǒng)治的批評(píng),過(guò)度夸大了科技本身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作用,造成一種對(duì)科技的恐懼情緒,這是較為片面的。但馬爾庫(kù)塞的理論相對(duì)于阿倫特,也有一定的優(yōu)點(diǎn)。他從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的角度出發(fā)來(lái)研究政治的現(xiàn)代性問(wèn)題,體現(xiàn)了他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chǎng),并對(duì)發(fā)達(dá)資本主義國(guó)家如何掩蓋階級(jí)矛盾的事實(shí)做了詳細(xì)的觀察與闡述,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新時(shí)代做出了與時(shí)俱進(jìn)的補(bǔ)充。
三、現(xiàn)代性的救贖
阿倫特在總結(jié)并重構(gòu)康德判斷力批判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自己的“判斷”理論用以解釋在極權(quán)主義之下人們應(yīng)當(dāng)負(fù)起什么樣的責(zé)任。納粹戰(zhàn)犯艾希曼是一個(gè)犯下十惡不赦罪行的人,但是阿倫特在他的審判過(guò)程中卻看不到所謂的“邪惡”。是什么促使一個(gè)看上去不邪惡的人犯下罪行的呢?阿倫特在他身上看到了反思性判斷能力的缺乏。康德將判斷分為“規(guī)定性判斷力”和“反思性判斷力”,前者是在給定普遍規(guī)則的情況下判斷一個(gè)特殊案例的能力,后者是從特殊案例中總結(jié)出一般規(guī)則的能力。艾希曼對(duì)他接到的命令毫無(wú)保留不加質(zhì)疑地執(zhí)行,他只是按照規(guī)則來(lái)判斷,因此他不缺乏規(guī)定性判斷力。他犯下罪行是因?yàn)槿狈Ψ此夹耘袛嗔Γ@種判斷力是在沒(méi)有給定規(guī)則或現(xiàn)有規(guī)則無(wú)法明辨是非的時(shí)候讓人知道什么是對(duì)的、什么是錯(cuò)的。反思性判斷依賴的是人的想象力與共同感。想象力為人們?cè)炝艘粋€(gè)判斷的空間,讓不在場(chǎng)的事物“在場(chǎng)”,通過(guò)再現(xiàn)某一種場(chǎng)景,獲得“美與丑”“快樂(lè)或不快樂(lè)”的基本感受,康德將此稱為“反思的運(yùn)作過(guò)程”[14]。反思運(yùn)作過(guò)程的基準(zhǔn)是“可交流的品味”,這就是一種“共同體感覺(jué)”,區(qū)別于“私人感覺(jué)”,必須有賴于他者的在場(chǎng)才能實(shí)現(xiàn)。因此判斷只有在人的復(fù)數(shù)性條件下才可以實(shí)施,在政治的公共空間中實(shí)現(xiàn)。“它不是為那些拒絕判斷、拒絕爭(zhēng)論我的判斷的合法性的人做出的”[10]。
阿倫特在《論道德哲學(xué)的若干問(wèn)題》中寫道,現(xiàn)代社會(huì)中最危險(xiǎn)的是對(duì)道德的冷漠,即一個(gè)人完全不在乎和什么樣的人做同伴,這種人身上的惡是人類公認(rèn)的極端之惡。但現(xiàn)實(shí)中更為普遍的是完全拒絕判斷,這就是“惡的平庸性”。從個(gè)人行為上來(lái)說(shuō),這種平庸之惡往往脫胎于普通人平凡的“想做個(gè)好公民”的愿望,但因?yàn)樗麄兙芙^判斷,好的愿望會(huì)在極端惡的引導(dǎo)下蛻變?yōu)閻盒械膸蛢矗创蟊姟⒕⑴c暴徒之間的聯(lián)合。阿倫特的政治現(xiàn)代性批判在這里出現(xiàn)了一個(gè)悲觀的閉環(huán):世界異化導(dǎo)致了公共空間的消失,公共空間的消失造成了人們無(wú)法通過(guò)共同感進(jìn)行判斷,進(jìn)而大范圍出現(xiàn)“惡的平庸性”,這又使更多人淪為暴露在極權(quán)主義統(tǒng)治下的“赤裸生命”,使得公共空間復(fù)興的可能性越來(lái)越渺茫。為了拯救這種絕望,阿倫特提出了行動(dòng)和判斷兩方面的補(bǔ)救措施,為了恢復(fù)行動(dòng)的能力,需要寬恕和承諾,行動(dòng)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可預(yù)見(jiàn)的特征,寬恕使人擺脫行動(dòng)的后果,承諾能約束人,使人保持同一性,這都需要在復(fù)數(shù)性的條件下完成。康德說(shuō),“典范是判斷的助步車”,因此阿倫特重視樹立道德典范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人的政治參與,只有鼓起勇氣參與正確的政治活動(dòng),才有創(chuàng)造奇跡的可能。而那些不關(guān)心公共生活,只關(guān)心自身靈魂救贖的人,無(wú)法在政治的現(xiàn)代性危機(jī)中參與挽救共同體的行動(dòng)。
馬爾庫(kù)塞通過(guò)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論說(shuō)明愛(ài)欲的退化與單向度社會(huì)之間的聯(lián)系。弗洛伊德認(rèn)為愛(ài)欲是人的“生的本能”,基于愛(ài)欲建立的共同體是人們對(duì)抗攻擊性的“死的本能”的基礎(chǔ)。愛(ài)欲是人類性本能的壓抑性升華,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愛(ài)欲”與“性欲”常常是一回事。馬爾庫(kù)塞在吸收弗洛伊德理論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進(jìn)一步的升華。對(duì)馬爾庫(kù)塞而言,性欲是低等的、動(dòng)物性的,愛(ài)欲是高等的、文明的。發(fā)達(dá)工業(yè)社會(huì)通過(guò)解放性欲和壓抑愛(ài)欲的方式,阻礙了升華的過(guò)程。“由于降低了愛(ài)欲能量而加強(qiáng)性欲能量,技術(shù)社會(huì)限制著升華的范圍。同時(shí)它也降低了對(duì)升華的需要”[11]。俗化的性欲和快樂(lè)充斥著發(fā)達(dá)工業(yè)社會(huì),技術(shù)的進(jìn)步使這種俗化的需求更加容易被滿足,人們也更自覺(jué)地順從于技術(shù)合理性的統(tǒng)治。弗洛伊德認(rèn)為性(力比多)的釋放會(huì)導(dǎo)致攻擊性本能的減弱,但馬爾庫(kù)塞察覺(jué)到,如果性本能的釋放是偏狹的,只釋放性欲而不是愛(ài)欲,那和限制愛(ài)欲本能沒(méi)有什么區(qū)別。“俗化趨勢(shì)也將與既粗俗又高尚的攻擊性形式的發(fā)展步調(diào)一致,后者正蔓延于當(dāng)代工業(yè)社會(huì)”[11]。阿倫特指出,技藝人的工作始于對(duì)自然的暴力破壞,與此觀點(diǎn)類似,馬爾庫(kù)塞認(rèn)為破壞性的本能(死亡本能)是對(duì)人與自然進(jìn)行技術(shù)征服的能力的一部分。科技發(fā)展“創(chuàng)造性的”滿足了人類這一本能,使得社會(huì)的凝聚力竟空前加強(qiáng),人們面對(duì)暴力與戰(zhàn)爭(zhēng)不是恐慌,而是欣喜若狂地接受,資本統(tǒng)治下極權(quán)主義的恐怖面孔在快樂(lè)與滿足之中被淡化了。更進(jìn)一步的,馬爾庫(kù)塞將文明分為壓抑性文明和非壓抑性文明。為了建立文明,人們不得不對(duì)一些本能進(jìn)行壓抑,這是文明的基本壓抑,而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hù)秩序?qū)Ρ灸苓M(jìn)行過(guò)多的、不必要的壓抑稱為額外壓抑。操作原則是壓抑性文明的運(yùn)行規(guī)則,也是異化勞動(dòng)形成的原因之一。馬爾庫(kù)塞在《愛(ài)欲與文明》中認(rèn)為操作原則是現(xiàn)實(shí)原則對(duì)快樂(lè)原則的壓抑,發(fā)達(dá)工業(yè)社會(huì)將人的解放與更高水平的生活畫上了等號(hào),這里更高水平的生活指的是被各種越來(lái)越先進(jìn)的科技產(chǎn)品圍繞的生活,為了這樣的“高水平”,不得不增加人們的勞動(dòng)時(shí)間,這種勞動(dòng)的增加其實(shí)使人離解放越來(lái)越遠(yuǎn),因?yàn)樗皇遣粩嘣黾尤说膲阂郑嗽谶@樣的“高水平生活”中只能滿足被壓抑的本能與被控制的需求。
馬爾庫(kù)塞樂(lè)觀地認(rèn)為隨著技術(shù)發(fā)展,人類勞動(dòng)效率大大提高,當(dāng)人們可以實(shí)現(xiàn)按需分配時(shí),勞動(dòng)的壓抑屬性會(huì)消失,變成完全是滿足自身快樂(lè)的消遣活動(dòng),人也將得到解放和升華。馬爾庫(kù)塞認(rèn)為這樣的一種烏托邦在理論上是可行的,“在成熟工業(yè)文明的理想條件下,勞動(dòng)全部實(shí)現(xiàn)了自動(dòng)化,勞動(dòng)時(shí)間減少到了最低限度,勞動(dòng)技能可以相互交換,所有這些便結(jié)束了異化狀態(tài)”[13]。此外他還提出了著名的“大拒絕”,但需要注意的是,馬爾庫(kù)塞的“大拒絕”與20世紀(jì)60、70年代西方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提出的口號(hào)略有不同,他不是要拒絕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一切,也不是要實(shí)現(xiàn)性欲的無(wú)限制解放,而是拒絕那些增加了額外壓抑、維護(hù)技術(shù)理性統(tǒng)治的“糖衣炮彈”,拒絕虛假需要,拒絕俗化的欲望和快樂(lè)。馬爾庫(kù)塞把實(shí)施“大拒絕”的任務(wù)交給了社會(huì)最底層的流浪漢、妓女、大學(xué)生等“局外人”,他認(rèn)為只有擺脫發(fā)達(dá)資本主義的商業(yè)文明和消費(fèi)主義的人才能反抗這個(gè)社會(huì)。馬爾庫(kù)塞不信任工人階級(jí),因?yàn)槲鞣降墓と穗A級(jí)已經(jīng)與資本主義社會(huì)共生共存,無(wú)法代表革命的、否定的、進(jìn)步的力量。
相對(duì)于馬爾庫(kù)塞烏托邦以及“大拒絕”式的救贖之路,阿倫特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態(tài)度較為理性。阿倫特并沒(méi)有把整個(gè)發(fā)達(dá)資本主義社會(huì)當(dāng)作自己的批判對(duì)象,她雖然也批判過(guò)所在的美國(guó)社會(huì),但她一直將獨(dú)立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美國(guó)革命者當(dāng)作一種典范,她所希冀的,正是將典范用于判斷,并鼓勵(lì)人們依據(jù)正確的判斷去行動(dòng)。馬爾庫(kù)塞的烏托邦有一個(gè)內(nèi)在的矛盾,他認(rèn)為隨著勞動(dòng)時(shí)間的減少,自由時(shí)間的增多,壓抑的愛(ài)欲就會(huì)得到解放,人就會(huì)追求非壓抑性的升華,但是阿倫特反駁了這一前提假設(shè),“勞動(dòng)動(dòng)物的空余時(shí)間只會(huì)花在消費(fèi)上面,留給他的空閑時(shí)間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貪婪越強(qiáng)烈……最終沒(méi)有一個(gè)世界客體能逃過(guò)消費(fèi)的吞噬而不被毀滅”[13],因此阿倫特得出自由時(shí)間的增加并不必然導(dǎo)致人的自由發(fā)展的結(jié)論。此外,馬爾庫(kù)塞把希望寄托在“局外人”身上,無(wú)異于一場(chǎng)吃飽了再鬧的革命,他們本身作為離開(kāi)技術(shù)社會(huì)就無(wú)法生存的人,是沒(méi)有能力推翻技術(shù)統(tǒng)治的,想要實(shí)現(xiàn)人的全面而自由的解放還是要依靠作為工業(yè)社會(huì)主體的工人階級(jí)。馬爾庫(kù)塞揭示了工人階級(jí)向發(fā)達(dá)資本主義妥協(xié)的現(xiàn)象,但是如何讓工人階級(jí)重新具有革命性,他的理論還不能夠自圓其說(shuō)。阿倫特的判斷理論為解決這個(gè)矛盾提供了一個(gè)可能的思路,判斷對(duì)于任何愿意進(jìn)入公共領(lǐng)域的人都是有效的,當(dāng)更多的人有勇氣進(jìn)入公共領(lǐng)域,判斷就足以改變?nèi)藗兊男袆?dòng),進(jìn)而自覺(jué)地進(jìn)行“大拒絕”并且追求愛(ài)欲的解放。同時(shí)馬爾庫(kù)塞也填補(bǔ)了阿倫特理論中存在的空缺,一方面,擺脫勞動(dòng)、進(jìn)入公共領(lǐng)域的勇氣是罕見(jiàn)的,而技術(shù)進(jìn)步卻可以提供擺脫必然性的條件,因此必要的勞動(dòng)和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是實(shí)現(xiàn)公共空間復(fù)興的基礎(chǔ);另一方面,阿倫特沒(méi)有意識(shí)到感性在反抗極權(quán)主義中的重要性,馬爾庫(kù)塞批判了理性對(duì)感性的壓抑,感性的合理釋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抗理性統(tǒng)治的作用,阿倫特的“惡的平庸性”本身具有理性統(tǒng)治的色彩,在理性的框架內(nèi)反抗“惡的平庸性”是行不通的,需要感性的力量來(lái)補(bǔ)充。
四、啟示
阿倫特與馬爾庫(kù)塞的現(xiàn)代性批判都基于對(duì)“勞動(dòng)”的批判,然而走向了兩種不同的維度。阿倫特從政治和哲學(xué)的維度進(jìn)行批判向我們揭示了現(xiàn)代極權(quán)主義恐怖的一面,馬爾庫(kù)塞從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維度進(jìn)行的批判則提醒我們警惕披著和善外衣的新型極權(quán)主義。對(duì)于他們的現(xiàn)代性批判,可以結(jié)合起來(lái)看待。一方面,阿倫特的理論啟發(fā)我們反思性判斷的重要性,我們應(yīng)當(dāng)在正確典范的模板下思考和判斷并有勇氣付諸行動(dòng);馬爾庫(kù)塞則啟發(fā)我們審視自身的真實(shí)需求,不被低俗的文化和潮流左右,不被消費(fèi)主義控制,適當(dāng)釋放自己的本能,保持批判性的思維。另一方面,我們也應(yīng)當(dāng)看到他們理論中的局限性。阿倫特否定勞動(dòng),但是只有勞動(dòng)生產(chǎn)力的提升能幫助更多人擺脫必然性束縛,有勇氣進(jìn)入公共領(lǐng)域;馬爾庫(kù)塞批判技術(shù)的統(tǒng)治,但是技術(shù)發(fā)展本身是中立的,只有在人的手里才能發(fā)揮統(tǒng)治的作用,他缺少了對(duì)政治的批判,因此突顯出了自身的矛盾性。
在如何救贖現(xiàn)代性難題上,阿倫特與馬爾庫(kù)塞的觀點(diǎn)可以互補(bǔ)。“惡的平庸性”是人在思維領(lǐng)域中 “獨(dú)在”時(shí)的不作為,而“單向度的人”是人作為共同體一員時(shí)的不作為,這兩種狀態(tài)同時(shí)存在于每一個(gè)個(gè)體身上。要想從現(xiàn)代性中拯救這些個(gè)體,也必須結(jié)合這兩種維度。阿倫特公共領(lǐng)域理論為馬爾庫(kù)塞的“單向度的人”提供了判斷和行動(dòng)的模范,使他們不會(huì)偏離正確的道路;馬爾庫(kù)塞對(duì)愛(ài)欲與感性力量的發(fā)掘?yàn)榉纯埂皭旱钠接剐浴碧峁┝伺械奈淦鳌_@些觀點(diǎn)對(duì)于更好地理解現(xiàn)代性以及理解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科技、勞動(dòng)與政治的關(guān)系,從而避免走向資本主義國(guó)家所面臨的現(xiàn)代性困境具有一定的啟示。
從國(guó)家層面來(lái)說(shuō):第一,不僅要建設(shè)物質(zhì)文明,更要建設(shè)精神文明。解放勞動(dòng)不是為了消費(fèi)與享樂(lè),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適度的消費(fèi)和享樂(lè)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種手段,但如果沒(méi)有精神上的升華,人們會(huì)很容易迷失于消費(fèi)主義陷阱,背離馬克思解放勞動(dòng)的初衷。第二,要合理運(yùn)用科技手段。科技的使用是以增加人民生活的幸福度為目的,而不是單純的擴(kuò)大生產(chǎn)、增加GDP,尤其要警惕資本借助科技的力量滲透進(jìn)人們的生活。第三,貫徹落實(shí)全過(guò)程人民民主。全過(guò)程人民民主不同于西方式選舉民主,它是全過(guò)程的民主,有力保障了人民的參與空間和參與時(shí)間。全過(guò)程人民民主的實(shí)施,有助于提高人民的政治參與意識(shí)、共同體意識(shí),構(gòu)建起公共生活的空間,是我國(guó)避免政治現(xiàn)代性危機(jī)的強(qiáng)大制度優(yōu)勢(shì)。第四,將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整體主義、和而不同的精神與馬克思主義相結(jié)合。汲取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智慧,發(fā)揮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制度優(yōu)勢(shì),使社會(huì)在整體的和諧中又多元包容,幫助人民抵抗資本的腐蝕,避免人民蛻變?yōu)樵踊膫€(gè)體。
從個(gè)人的層面來(lái)說(shuō):第一,要平衡物質(zhì)與精神在生活中的關(guān)系。儒家先賢孔子說(shuō):“君子食無(wú)求飽,居無(wú)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xué)也已”[15]。現(xiàn)代人不需要像古人一樣不顧生命的求“道”,但“道”所蘊(yùn)含的智慧與理想不應(yīng)當(dāng)被忘記。第二,作為生活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一個(gè)個(gè)普通個(gè)體,我們不能做一個(gè)獨(dú)善其身的旁觀者,也不能在沒(méi)有判斷力的情況下盲目行動(dòng),應(yīng)當(dāng)明確自己在共同體中的責(zé)任,并且有勇氣付諸行動(dòng)。第三,依法積極行使參政議政的權(quán)利,在全過(guò)程人民民主制度優(yōu)勢(shì)的保障下,共建平等交往的共同體。第四,對(duì)現(xiàn)代文明的成果要審慎、批判地思考。了解自身真實(shí)的需要,而不是在資本的蠱惑下忘記初心。我們要理性地思考,感性地行動(dòng),在現(xiàn)代性的浪潮中做一個(gè)敢于說(shuō)“我拒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