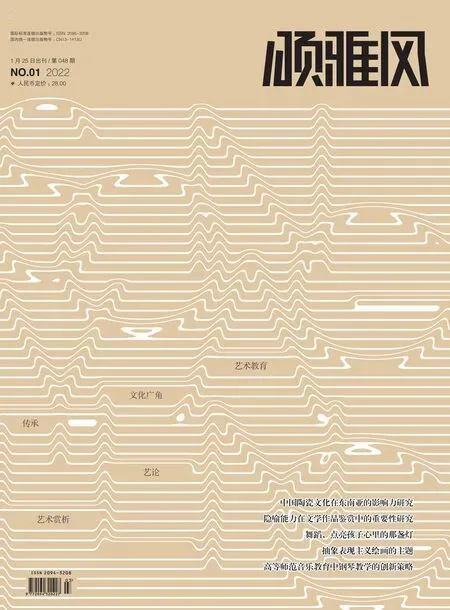抽象表現主義繪畫的主題
——讀《閱讀抽象派大師杰克遜·波洛克》
◎馬銘涵
羅莎琳·克勞斯的《閱讀抽象派大師杰克遜·波洛克》一書,從藝術史學家和藝術批評家的不同研究方法是否會得出不同結論的這一問題開始論述。盡管藝術批評界和藝術史學界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但針對具體問題,比如對杰克遜·波洛克作品意義的解讀,有些理解方式的確會將人們引向歧途。為此,克勞斯樹立了她重點批判的靶子——卡米恩對波洛克黑白畫的論述。克勞斯指出其中的漏洞,并明確表示這種解讀“不僅歪曲了波洛克的工作方法,也誤解了作品的意義”。克勞斯由此以對卡米恩觀點的細節考察和批判為線索,考察了“創作動力說”的批評和藝術史方法,并探討了波洛克作品的主題問題。
波洛克在1951年到1952年間創作了一系列的黑白繪畫,這些繪畫看起來與其之前和之后的作品似乎存在著斷裂,這些畫不僅僅是黑白的,同時還是高度形象化的。這一系列作品的確會使人產生疑問,為何在這短暫時期波洛克的作品會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這些畫面的意義又是什么?在卡米恩的理論中,這些黑白作品是為教堂的玻璃窗做裝飾,由于是為了宗教目的而設計,所以回歸了具象,具有比喻義。然而無論是從時間上,還是從波洛克留下的文本資料敘述中,都能夠找到推翻卡米恩這一假設的證據。根據波洛克信中所述,他構思這些黑白畫作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將其理解為這是波洛克對長期以來人們對他抽象作品主題誤讀的某種反抗。由于滿幅繪畫過于抽象,人們總是誤認為其畫面沒有主題,而僅僅追求視覺上的絕對抽象。但波洛克似乎對這種解讀有所不滿。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抽象繪畫隱藏在抽象之下的某種具象主題是波洛克非常關注的重點,也就是說,也許黑白畫時期的作品可以作為我們解讀波洛克作品主題的一把鑰匙。在此,克勞斯用極長的篇幅事無巨細、毫不留情,并且極有耐心地指出卡米恩教堂假設的種種不合理之處,推翻了從這一角度對波洛克黑白畫時期創作目的的解釋。那么,克勞斯對黑白畫以及波洛克長期以來的創作主題是怎么理解的呢?
克勞斯緊接著論述了她對抽象主義與作品主題之間的關系的思考。“沒有混亂,該死的”這一部分是我認為本文中最為精華的章節,她指出“抽象主義和主題在本質上是矛盾的”這一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抽象主義畫家最大的恐懼就是僅僅創造出連主題都無法表達的抽象主義……最終淪為裝飾”,這一點可以由與波洛克同時期的抽象藝術家紐曼的話佐證——“主題才是繪畫最重要的部分,我們這一代人開始直面‘畫什么’這一問題。”且波洛克本人也曾經表達過這種被誤解“沒有主題”的苦惱。這種誤解來自人們“非此即彼”的思維,因為人們認為藝術作品“所畫即所有”,這種所指才是畫面的主題,而如果一幅畫是抽象的,且無法和任何具象之間掛鉤,那么這幅畫就什么都沒描述,也就是沒有主題。克勞斯在接下來談到實際上與形式相同,抽象繪畫的主題也可以是抽象的,比如虛無,“虛無是指用某種方法被剝奪了一切物質化或是限定性質的存在”。在畫面中,這個“無”的概念可以借由對立構造來體現,在對立中,對立的兩方并不是作為獨立的實體存在的,而是一種對立關系,即a意味著非b。波洛克的作品中就存在著這樣的對立結構,比如說色彩和線、區域和輪廓等,這些二元對立的a和b同樣也是非b和非a,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是同等且可以相互轉化的,色彩也是線條,區域也可以轉化為輪廓。關于這一點我理解為像蒙德里安的作品那樣,線條同樣也可看作一個細長的色塊。這種可以相互轉化的動態對立在克勞斯《看的沖動/令人看到的脈沖》這篇文章中也有提到,在那里的例證是杜尚的《循環器》系列作品,“不斷溶解圖像的脈沖,完全摧毀了我們認為的‘形態’。”在波洛克的作品中,除了探討抽象的二元對立現象,還存在著心理學上的主題,像是夢境,或者波洛克將其稱為“被空間拘捕的記憶”,這也就是波洛克作品中一些非具象形象的來源,我理解這些碎片化的沒有圖像的夢境就像是一種潛意識。由此可見,黑白畫時期的創作仍然遵循了波洛克一貫以來的主題,而非突然轉變了創作思路。可以說,這個時期的作品為了對抗大眾的誤讀,反而更加強調了波洛克的創作主題,抽象繪畫的主題不是空缺或者必須呈現一個相對具體的形象,而是具有在這兩極中間更加復雜而細膩的過渡區域。

在沢山遼《抽象表現主義與繪畫,或者繪畫之上》中也探討了這個“更加復雜而細膩的過渡區域”。根據他的觀點,“二戰”后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展現出的是對“被稱為‘無意識’原始‘神話’的,對作為人類存在、社會基礎的原始和起源領域的關注”,以及對超現實主義中展現夢和潛意識的方法的關心。關于這種展現方式,他提到了自動筆記。超現實主義中的自動筆記是在半睡眠狀態下的又述和超高速寫作的實驗,實驗者要處于半夢半醒、意識模糊的狀態,被要求在規定時間內用文字填滿草稿紙,完全不需要思考內容,憑借下意識去寫作。結果是我們看到了實驗者寫出的不受審美或道德意識約束的、令人驚訝的文本。由此產生的句子和詩歌,反映了無意識和有意識的世界,表現出被隱藏在我們身處現實背后和內部的更高度的現實,即為 “超現實”,我們可以借這樣的“超現實”來審查自己的現實。而波洛克的潑灑畫的作畫方式,同樣依賴一定程度上的即興和顏料的自動運行,藝術家在創作中處于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狀態,由此似乎能看到一點自動筆記的影子。自動筆記和潛意識的主題更加接近所謂的表現具體形象,因此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從這個角度上說,波洛克的繪畫并不是完全在追求“非再現性”,而是具有“非再現性的傾向”。也就是說,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們在創作時并不是為了抽象而抽象,而是因為他們所表現的主題本就是具有抽象的性質,為了表達這個帶有抽象性質的主題(潛意識中的某些內容無法與現實中的具象形態對應),才呈現出抽象的畫面。順著這一主題,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們走上對自己本性和自我的探尋之路。如果說這之前的藝術家展現的是對外部世界的熱情,那么波洛克們則是轉向了自己的內心深處。
紐曼針對畫家與作品的關系有這樣一個比喻:畫家是主語,畫板是目的語,繪畫過程是動詞,而畫好的畫作是整個句子。也就是說,最終呈現出來的作品是包括畫家、作畫過程在內的全部,畫家被卷進了作品當中。在一般的認知當中,作品是由畫家創作并控制的,在這里,這個關系完全顛倒了,作品成了一切的主體,作品證明了畫家的存在,甚至觀者通過在作品前佇立而感知到自己的存在。作品成了一個場域,處于其中的人成了誤入引力場的原子,被其影響,受其控制,這種關系在面對波洛克的巨幅繪畫作品時可以切身感受到,這種場域作用同時也適用于一些沉浸式影像作品。而波洛克創作的獨特性在于,他的巨幅潑灑畫在創作時就已經將自己卷了進去。這一概念下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活了過來,它不僅僅是被操縱的,它還是獨立于作者的、可以進行對話的對象。從這一角度上看,波洛克的繪畫主題更是與再現性或是非再現性毫無關系,幾乎像是一種創生或是禪修,“波洛克和紐曼創作出來的,并不是關于某種東西的繪畫,而是這畫作就是某種存在本身”,也就是原文題目中所說的“繪畫之上的某物”。
哲學家伽達默爾這樣說道:“對一個文本或一部藝術作品里的真正意義的汲舀是永無止境的,它實際上是一種無限的過程,這不僅是指新的錯誤源源不斷被消除,以至真正的意義從一切混雜的東西中被過濾出來,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斷產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義關系展現出來。”找到新的切入點去理解波洛克的作品,也并不意味著之前的理論就被完全否認了。盡管我認為波洛克的作品中從來都沒有完全拋棄與現實世界的關聯性,但格林伯格和弗里德等形式主義批評家的理論仍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對波洛克作品主題的闡釋,二元對立、潛意識、場域等,都是不斷突破現代主義理論范式、揭示新的意義、為今后的創作帶來啟發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