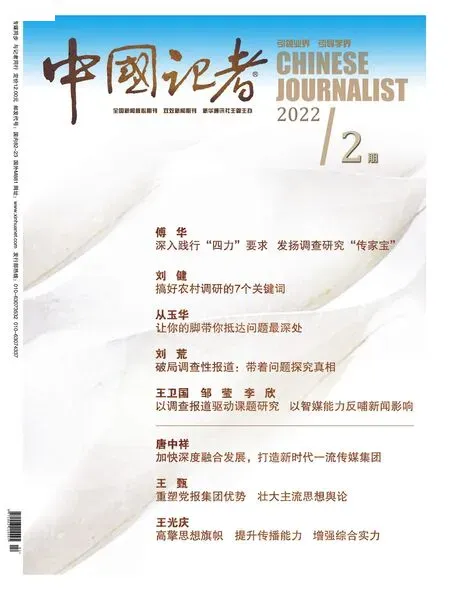破局調查性報道:帶著問題探究真相
劉荒
新華每日電訊特稿部主任
巴爾扎克說,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遇事問個為什么。話雖簡短,分量并不輕,越回味越有嚼頭。換而言之,記者的職業天性是質疑,問題便是最好的老師,調研更像做不完的功課。
調查研究是記者的看家本領。新聞界老前輩穆青指出,“離開了調查研究,我們的新聞就會失去光彩,就沒有了生命力,指導性、思想性、戰斗性也會喪失”。
問題是調研的前提,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以輿論監督、突發性事件和重大社會議題為主要題材的調查性報道,因旨在挖掘新聞事實背后的真相、揭示復雜隱蔽的內在關系,更能彰顯新聞價值、媒體責任和記者使命。
在構建全媒體傳播格局的新形勢下,堅持問題導向,注重調研實效,提升專業水準,拓展報道空間,破除調查性報道“選題難”“要求高”“易流產”“不解渴”等困局,對于加強傳統主流媒體傳播力、公信力和影響力至關重要。
研究真問題,找出好選題
相較于日常新聞報道,調查性報道更強調問題意識,圍繞當前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做文章。如何從紛繁復雜的問題中發掘選題,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如因報道“水門事件”而名聲大噪的調查記者伍德沃德所言,“做新聞的主要困境在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
一些年輕記者常為選題所困:有的人天馬行空又無從下手,有的人信手拈來但缺乏價值,有的人驚曝猛料卻信源存疑,還有的人偶然覓中一個選題,細究卻發現已有報道,再寫又難有新意。
現實生活中并不缺少選題線索,缺少的是發掘真相的問題意識和調研能力。
調研本身就是面向問題的,既要“帶著問題下去”調查,又要“帶著問題回來”研究。這個提煉選題的過程猶如剝洋蔥,要剝掉層層干碎的表皮,直到露出新鮮光亮的“內核”。
通過學習發現問題,將知識點變成新聞眼。這樣既有知識點,避免報道淺嘗輒止,問題研究不深不透;又有興趣點,了解讀者關注什么、需要什么,而不僅僅是記者知道什么,想說什么。
另外,根據媒體報道追蹤選題線索,提煉富有報道價值的好選題——選擇全新的視角,追問更深的問題,提供增量的信息,使調研報道更具厚度與深度。
好問題自然引人入勝,有時甚至比答案還重要。建立問題意識源于獨立思考,堅持問題導向需要擔當精神。唯有如此,記者才能練就敢于正視問題,善于分析問題,最終解決問題的“真功夫”。
記得2013年6月,筆者采訪全國唯一的“高考專列”,從這個公益性運輸典型案例中,挖掘出鐵路政企分開后如何推進改革的真問題。
當年,國務院大部制改革撤銷鐵道部,鐵路客貨運輸市場化改革提速。這趟已在大興安嶺林區開行11年的高考專列,每年高考期間往返共270公里,運送近千名考生高考。為此,鐵路部門已累計虧損40多萬元。
此時,深陷經營困境的原哈爾濱鐵路局,全年政策性虧損高達百億元。他們私下里抱怨虧損嚴重的支線客車屢遭各方抵制“停不起”,表面上仍邀請媒體高光宣傳“高考專列”的社會效益,難免有些“賠本賺吆喝”的味道。
一位鐵路人士向記者反映,與哈鐵當年百億虧損相比,即使把“高考專列”“插秧專列”的虧損都算到一起,連續十幾年還不到1000萬元,如此“小題大作”或有逃避行業經營性虧損責任之嫌。
為了追蹤公益性運輸虧損的真相,筆者針對如何厘清公益性運輸的邊界、各類公益性運輸虧損該由誰來埋單、怎樣建立相應的財政補貼機制等問題,采寫了《“高考專列”虧損該誰埋單》的調研報道,一時間引起各方熱議和思考。
時隔多年,這趟“高考專列”仍在開行,雖然考生逐年減少,但宣傳報道陣勢依舊。記者偶然看到它的“最新成就”報道時,如同撞上一個巨大的問號:相比每年運送一千名考生及家長,運送一千份考卷是否更加溫情而有效率?!
剔除那些似是而非的理由,這又何嘗不是一份考卷呢。
記者也是問題的一部分
調查性報道的深度,取決于記者的思想深度及專業程度。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社會生活瞬息萬變,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元宇宙和碳中和等新技術、新概念層出不窮,對記者的知識結構提出挑戰,一味追求全知型記者或已無可能。
記者需要長期跟蹤一個或幾個領域,才能成為厚積薄發的專業性人才。隨著認知水平的提升,記者關注問題的類型、層次和維度也會發生變化。
一位名記者說過,“新聞業充滿了自我膨脹的人,但你必須花一切代價避免自我膨脹。”這種觀點或許有失偏頗,卻值得媒體同行警醒,真正領悟自身也是問題的一部分,避免沾染“聞功則喜”、起哄自嗨的陋習。
記者要有“自以為非”的自知之明,多在“專”和“新”上下功夫,避免由于認知模糊不清,生搬硬套概念來解釋專業問題,掩蓋專業性不足的報道缺陷。
例如在經濟調研報道中,有的記者喜歡用詩意化的語言概括復雜的經濟現象,譬如描寫企業打贏反壟斷官司或克服產業升級困難時,引用“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詩句,或“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抒懷就給打發了,既說不清貿易規則背后的邏輯沖突、價值沖突和利益沖突,也道不明產業轉型升級“路徑依賴”與“低端鎖定”之間的邏輯關系,自然也不會被專業人士所認可。
而在輿論監督報道中,容易給個別高價格的產品或服務,貼上“天價”標簽后窮追猛打。殊不知,市場競爭發現價格,價格是調節市場的信號。在非特殊管制時期或壟斷條件下,只要不存在強行買賣或惡意欺詐,不要隨便給人家扣上“天價”之類的大帽子。
如果媒體總是用道德的大棒,抨擊形成價格的市場機制,而不是從品牌溢價、供需變化、市場競爭等角度分析問題,就會壓縮正常討論的空間。
有些報道在解決問題的建議導向上,喜歡呼吁行政政策出臺,而不是完善法治環境建設,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上,因迷信行政權力往往開錯了藥方。
還有醫保藥品談判的報道中,經常會出現“靈魂砍價”等過度褒獎之詞,忽視商業談判互利互惠的基本原則,這都不是客觀平實的報道語言。
新聞報道有時難以抵達真相,還在于無法打開采訪對象心扉說真話。比如,由于采訪問題過于簡單,導致對方沒有深入交流欲望;交流缺乏同理心,難以獲得對方的信任;喜歡斷章取義,歪曲采訪對象的真實意圖。
經濟社會生活的復雜化,要求記者具備一定的法治思維、科技知識和人文素養等,對報道選題形成專業認知和判斷。比如,個別地方政府不用法治的思維辦事,打著“畝均稅收”“有機更新”之類的口號,侵犯企業合法權益。記者在采訪中應分辨是非,從法治角度出發,理性分析政府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有的媒體記者,由于長期不做調查性報道,逐漸丟了看家本領,難免心虛發慌,重新撿起來手生了、筆鈍了,只能“為賦新詞強說愁”,做些不痛不癢的報道;有的記者則習慣引用專家觀點,濫用所謂“借嘴說話”的“技巧”,以掩飾采訪不扎實、內容缺乏干貨硬料的不足;還有的記者錯把幼稚當簡單,遇到問題不知所措,索性不碰這類報道了。
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我們的個別員工做事憑慣性,看到負面消息第一時間就想著去處理掉消息,而不是把事情討論清楚,這非常不好。”這封網易CEO丁磊的道歉信,終于平息了與自媒體公眾號“魚眼觀察”的輿論爭議。
日前,丁磊以政協委員身份提交一份關于“統一智能電子設備充電器標準端口”的提案,引起“魚眼觀察”的公開批評質疑。網易方面通過微信平臺投訴其侵權,還發出一份措辭強硬的法律函要求刪稿和道歉,引發雙方爭議。
對于這種難容異見的現象,圍觀的網友早已司空見慣。高管因其言論或行為引發輿情,很多公司的反應大同小異:首先將質疑文章定義為負面消息,不是組織公關灌水刪稿,就是發出律師函相威脅。
一些大企業雖對主流媒體有幾分忌憚,總是以繁雜的流程為由,對媒體采訪設置重重障礙。有位年輕記者采訪一家上市公司,對方要求說報道意圖,再讓記者列出采訪提綱,刪除幾條“敏感”問題后,還再三要求不能超出采訪提綱。
記者還沒開始采訪,先被對方“采訪”個底朝天,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
相比企業來說,有的地方政府和權力部門,面對質疑或批評時的反應更為激烈。一些地方在突發事件中,一旦發現調查記者進入所轄地區,便先禮后兵,用遍各種招式向記者贈送貴重的禮品,試圖留下記者收禮的把柄,被拒絕后又使出各種手段暗中阻撓采訪。
記者采訪結束后,當地還會疏通層層關系,請求媒體領導把報道摁住,或者稿件播發后,要求刪除新媒體版本,降低網絡傳播力。
筆者曾當面批評一位省級外宣部門負責人,在突發事件現場使用通信技術手段屏蔽記者手機信號,限制記者手機拔打北京的區號。盡管當時手里沒有實錘的技術證據,對方亦對“妨礙公民通信自由”“侵害新華社記者耳目喉舌職能”的指控狡辯一番,可現場記者的手機卻很快恢復正常了。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客觀中性的正常報道,也令一些地方官員猶如驚弓之鳥。記者完成采訪工作后,受訪部門要求提前審閱稿件,并隨意刪除稍有些問題導向的語句,大段地補充宣傳地方政績的內容,跟記者反復“打太極”。
有一位縣委宣傳部門負責人私下說,除了對縣委書記的正面報道外,其他報道都屬于負面報道。這句話雖然說得極端,可見怕跟媒體打交道惹麻煩的成見之深。
何謂正面報道,何謂負面報道?界定的尺度在哪里,由誰來定義呢?各地紀委網站上,幾乎每天都在發布干部被調查的信息,對那些干部來說當然是負面的,但從反腐倡廉和公共利益角度來看,公布這些信息必然有其正面效果。
如前所述,調查報道的邏輯與之完全相通。如果一篇報道觸動了某些地方或某些人的利益,但站在貫徹落實中央大政方針的高度、有利于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角度,推動了實際工作和問題的解決,產生了正面積極的效果,誰又能說這是負面報道呢?因此,報道是正面還是負面,不能簡單取決于報道對象的感受和利益,應該用社會效果來界定。傳統主流媒體不能甘于陷入這種非黑即白的話語陷阱,更要避免被這種包裝成“大帽子”的“偽命題”牽著鼻子走。
“成績不說跑不了,問題不說不得了。”記者帶著問題意識挖掘真相的報道,并不是要跟誰過不去,更不是故意找茬、挑刺和抹黑。對調查性報道尤其輿論監督,隨意貼上“負面報道”的標簽,動輒處理提出問題的人,甚至發生跨省抓捕記者的違法行為……個別地方和部門領導的錯誤認知和慣性做法,不僅危害黨的新聞宣傳工作正常開展,也壓縮了媒體的報道空間,更不利于問題的解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是統一的。新聞媒體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直面社會丑惡現象,激濁揚清、針砭時弊”。這為做好新時代主流媒體輿論監督報道提供了根本遵循和依據。
內部要有激勵機制
調查性報道一直是主流媒體的核心能力和競爭利器,也是衡量一個記者業務能力的重要標志。若因自我身份認知上存有偏差,長期在熱點事件或重大事件中失語缺位,就會喪失主流價值,逐漸被邊緣化。
當下的輿論場,新興媒體的傳播優勢顯著,淺閱讀、碎片化和泛娛樂的閱讀習慣漸成主流。網絡社交媒體上的熱點事件,更容易形成巨大的影響力,當事人或官方一條長微博或公眾號文章,就可能引發社會輿論關注。
近年來,在一些熱點或重大事件中,主流媒體失語失聲的現象時有發生。輿論監督功能蛻化,導致對“房間里的大象”視而不見,甚至不敢觸碰相關選題。西安疫情期間,發生孕婦因被醫院拒收而流產的悲劇,主流媒體就缺少像樣的調查性報道。
現在很多主流媒體,都在推動傳播方式和渠道創新,但如果從業者思想依舊老化,即便從紙媒轉移到新媒體,內容上也不會有本質的改變,很難吸引年輕受眾,難言再有主流影響力。
一些法治報道中調查味道不足,看似情節豐富、過程曲折的報道,細究則發現信源過于單一,記者大量援引公安機關的辦案資料或法院的判決書。亦有記者隨行各級督察組、督導組明查暗訪,報道更像是受權發布而非輿論監督。
調查性報道的主體是媒體記者,通過獨立采訪調研發現問題,追尋事實背后的真相,最終以獨家報道的方式呈現出來。如果只是跟著有關部門后面打打“死老虎”,沒有進行扎實的調查,如何稱得上是調查報道呢?難怪有同行調侃,如果記者專挑“死老虎”,永遠也成不了“真武松”。
一段時間以來,帶有“無名氏”特征的調查報道模式流行,即故意隱去人物、地點等核心要素,區域或行業全部以“某”字代替。這種調查報道現象化,雖可緩沖地方政府或部門的干擾,卻因新聞要素不完整,只是“找到板子看不見屁股”,也會帶來個別記者拼湊報道事實的道德風險。

▲ 2020年1月3日,重慶市渝北區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人員(左)在渝北區洛磧鎮長江碼頭向群眾介紹“長江禁漁”相關知識。(新華社記者 王全超/攝)

▲ 一級飲用水源保護區內的福州市長樂區三溪水庫周邊山體被大量墳墓覆蓋(2019年3月27日無人機拍攝)。2019年清明節前,“新華視點”記者在福州長樂、福清、連江等地發現,雖然地方政府不斷整治墓葬亂象,但偷建豪華墓、活人墓的情況依然多發。(新華社記者 姜克紅/攝)
盡管這樣欠專業性的操作實屬無奈之舉,但也可見調查報道空間之逼仄。相比那些面對假丑惡現象而無動于衷的媒體人,我們仍然要向這樣的媒體和記者致敬,畢竟他們一直在堅持和努力。
調查報道有時弄錯一個數據,被監督對象就可能找上門來,追究記者報道失實責任。做調查性報道往往費力不討好,很容易自縛手腳、自我設限。有時發現一個調查線索,卻止步于選題策劃階段,調查性報道的習慣性“流產”,難免會帶來調查記者的職業倦怠,甚至產生孤獨的挫敗感。
堅持做調查報道的記者,應該得到支持和激勵。近年來,新華社加大輿論監督報道力度,新華每日電訊、經濟參考報和半月談等社辦報刊,都堅持做調查性報道,涌現出一批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調查記者,推出了一批激濁揚清、匡扶正義的輿論監督報道,如經濟參考報首席記者王文志采寫的《青海“隱形首富”:祁連山非法采煤獲利百億至今未停》《多年拆違巋然不動 數千棟“堅挺別墅”野蠻侵蝕濟南泉域保護區》、新華社福建分社鄭良采寫的《大建豪華墓活人墓陋習難改——福建墓葬亂象調查》、新華社重慶分社記者韓振、何宗渝、劉博偉采寫的《晝伏夜出、派人盯梢、地下交易……長江禁漁數年,“貓鼠游戲”仍上演》等調查性報道,都得到了中央高層重視,推動了問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