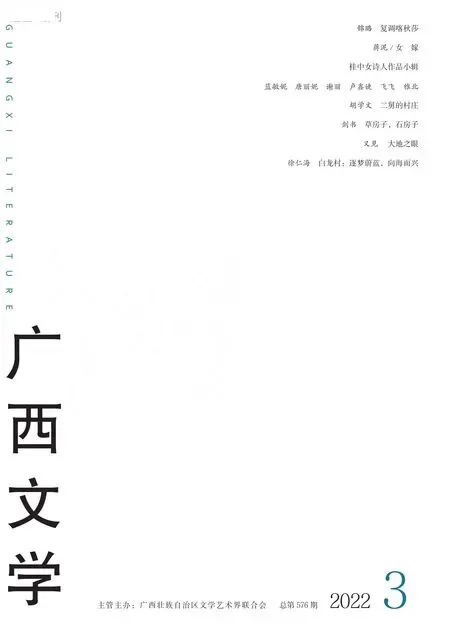恍然書(shū)
一
這是林書(shū)海今年第七次夢(mèng)見(jiàn)大火了,夢(mèng)見(jiàn)大火燒掉了整個(gè)書(shū)店。他如臨深淵,沒(méi)有驚慌與驚恐,而大火最終淹沒(méi)了他的靈魂。夢(mèng)醒后,他的身上似乎仍帶有灰燼的氣息。打開(kāi)手機(jī)上的搜索引擎后,他特意查了這個(gè)夢(mèng)的含義。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解讀:一種說(shuō)是兇兆,預(yù)示著即將而來(lái)的災(zāi)難;另一種說(shuō)是吉兆,預(yù)示著將會(huì)來(lái)財(cái)。他對(duì)著屏幕苦笑,于是打開(kāi)了藍(lán)牙音箱,整個(gè)房間回蕩著馬勒的《復(fù)活交響曲》。多年過(guò)去了,這部交響曲仍舊是他最愛(ài)的音樂(lè)作品。這部關(guān)于重生的作品無(wú)數(shù)次照亮了黑暗中的他。
像往日一樣,他騎上電動(dòng)車,約莫十分鐘后到了書(shū)店門(mén)口。把車子放好后,他便去了不遠(yuǎn)處的老馬家餐館,點(diǎn)了自己最愛(ài)的胡辣湯,搭配黃燦燦的金絲餅。這原本是他一天中最愜意的時(shí)分,如今卻帶了某種哀傷的鄉(xiāng)愁色彩。這個(gè)店的胡辣湯,他已經(jīng)吃了十多年了,卻從未厭倦。世界變樣了,很多事情也變味了,但這胡辣湯卻從來(lái)沒(méi)有變過(guò)味,是時(shí)間的恒遠(yuǎn)味道。或許這也是他鐘情于這家店的緣故。
店里的老板和他大致上是同歲,每次見(jiàn)到他,都會(huì)說(shuō)同樣的話:你來(lái)了啊,快到里面坐。臨走的時(shí)候,也是同樣的話:慢走啊,再來(lái)。這兩句話仿佛時(shí)間的針腳,在他的體內(nèi)有規(guī)律地運(yùn)轉(zhuǎn)。今天臨走時(shí),他對(duì)老板說(shuō),不知道還能在你們這里吃幾次了。老板說(shuō),這周末,我們就搬走了。他說(shuō),太可惜了,這么多年的老店了,說(shuō)沒(méi)就沒(méi)了。老板說(shuō),人也一樣,說(shuō)沒(méi)就沒(méi)了,這也是天意吧,之后會(huì)開(kāi)新店的,有機(jī)會(huì)了來(lái)坐坐。他說(shuō),是啊,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你的名字。老板笑道,我叫馬遠(yuǎn)航,從我爺爺?shù)臓敔斈禽呴_(kāi)始,我們家就做胡辣湯了,從河南做到了陜西。他也說(shuō)了自己的名字,之后便離開(kāi)了這家店,回到了書(shū)店。
打開(kāi)書(shū)店門(mén)后,光也隨之灑了進(jìn)來(lái),帶來(lái)夏日的最后溫情。天氣預(yù)報(bào)說(shuō)接下來(lái)的半個(gè)月都是陰雨天,而他再也不用為接下來(lái)的雨季發(fā)愁了,因?yàn)檠巯碌臅?shū)大部分已經(jīng)有了各自的出路。他打開(kāi)手機(jī),拍了書(shū)店的一角,先后上傳到微博與豆瓣,配上了但丁《神曲》中的名句——我看到了全宇宙的四散的書(shū)頁(yè),完全被收集在那光明的深處,由仁愛(ài)裝訂成完整的一本書(shū)卷。他又登錄孔夫子舊書(shū)網(wǎng),看到了新接的六個(gè)訂單,于是去了地下室,把所需要的書(shū)一一找出來(lái),擺好在前臺(tái)。他叫來(lái)了快遞,按照地址幫顧客把這些書(shū)寄走。每次和不同的書(shū)告別,他都有某種不舍,畢竟有或深或淺的交情。再過(guò)一個(gè)月,這個(gè)書(shū)店就要消失了,而整個(gè)幸福堡也將會(huì)化為灰燼,從城市中消失。這里將變成新的商業(yè)區(qū)。
半年前,他就聽(tīng)到了幸福堡將要被拆遷的消息。那時(shí)候,他還沒(méi)有做好離開(kāi)的準(zhǔn)備。畢竟在這里干了十五年了,身體與靈魂已經(jīng)扎進(jìn)了這個(gè)城中村,仿佛門(mén)外繁茂的梧桐樹(shù)。他用了很長(zhǎng)時(shí)間才慢慢消化了這個(gè)事實(shí),卻依舊不敢想象沒(méi)有了書(shū)店的日子。如果沒(méi)有了這個(gè)書(shū)店,他可能會(huì)再次過(guò)上那種被罷黜的漂流生活。他把自己的困惑講給了好友周洲聽(tīng),周洲回道,你這個(gè)書(shū)店也不怎么掙錢(qián),這剛好是個(gè)機(jī)會(huì),你可以出去謀個(gè)事情。他苦笑道,這么多年都不上班了,早都不適應(yīng)那樣的活法了。周洲說(shuō),沒(méi)啥適應(yīng)不適應(yīng)的,你當(dāng)年可是咱們班的大才子啊,要不我在我表哥的公司給你謀個(gè)職務(wù)。他說(shuō),以后再說(shuō)吧,這種事情也只能說(shuō)給你聽(tīng)了。和周洲說(shuō)話,就像與另一個(gè)自己交談。他們約好了下次見(jiàn)面的時(shí)間。
周洲是他的大學(xué)舍友,也是他至今唯一聯(lián)系的大學(xué)同學(xué)。大學(xué)畢業(yè)后,周洲去了縣城的政府部門(mén)做公務(wù)員,三十二歲被調(diào)到了市里,三十六歲又被提到了省城,一步步穩(wěn)扎穩(wěn)打,如今是處級(jí)干部。與周洲的扶搖直上相比,他卻平淡無(wú)奇,一直都在經(jīng)營(yíng)這家舊書(shū)店,旱澇保收,沒(méi)什么大的起伏,是世俗意義上的普通人。周洲每次來(lái)找他,什么掏心窩的話都會(huì)告訴他,說(shuō)得最多的是自己枷鎖般的生活。自從工作后,周洲幾乎就沒(méi)有了讀書(shū)的心境,只有與他相處的短暫時(shí)間里,才能脫離俗世的束縛,看見(jiàn)自由的幻象。有一次,周洲說(shuō)自己厭倦了牢籠般的日子,說(shuō)自己羨慕他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也想把自己心中的苦水倒給對(duì)方聽(tīng),但話都到了嘴邊又咽了回去,只能點(diǎn)頭苦笑。直到書(shū)店面臨倒閉,他才把自己的難處告訴了周洲。對(duì)于他而言,周洲更像是鏡子中的自己。或者說(shuō),周洲是自己的另一個(gè)分身。
十點(diǎn)半,周洲來(lái)到了書(shū)店,帶來(lái)了黃金芽。他說(shuō),來(lái)就來(lái)了,每次來(lái)都帶茶葉,這么生分的。周洲說(shuō),我在你這蹭吃蹭喝,也不能空手來(lái)嘛,再說(shuō)茶葉也是別人送我的。他說(shuō),公家的飯不好吃,你可要把碗端平啊。周洲說(shuō),我在里面摸爬滾打十幾年了,知道其中的分寸。說(shuō)完話后,周洲自己下了樓,去了地下室,而林書(shū)海繼續(xù)寫(xiě)那篇關(guān)于《過(guò)于喧囂的孤獨(dú)》的書(shū)評(píng)。編輯已經(jīng)催過(guò)兩次了,今天一定要完成這篇約稿。上午來(lái)買書(shū)的顧客不多,這是最寶貴的寫(xiě)作時(shí)光。到了下午,他就會(huì)被各種事情分神,只能用零碎的時(shí)間來(lái)啃噬這些無(wú)盡的書(shū)。對(duì)于像他這樣的人而言,這是無(wú)言又苦澀的快樂(lè)。他已經(jīng)無(wú)法想象沒(méi)有書(shū)的生活了。書(shū),是他的親密伙伴,也是他的隱蔽戀人。
半晌過(guò)后,周洲從地下室走了出來(lái),帶著莫里森的《所羅門(mén)之歌》。他問(wèn)林書(shū)海是否讀過(guò)這本書(shū),林書(shū)海點(diǎn)點(diǎn)頭說(shuō),非常喜歡,我還為這本書(shū)寫(xiě)過(guò)書(shū)評(píng)呢。周洲說(shuō),太羨慕你了,我已經(jīng)沒(méi)心讀書(shū)了,或者說(shuō),我已經(jīng)被各種煩瑣事挖空了心。林書(shū)海說(shuō),你這是瓤我呢,你們當(dāng)官才是正道,我們普通人就是混口飯吃。周洲說(shuō),你這才是諷刺人哩,對(duì)了,剩下這么多的書(shū)以后咋辦啊?林書(shū)海說(shuō),能賣就賣了,賣不掉的我就拉回家,再不行就當(dāng)垃圾處理了。周洲說(shuō),那你也很心疼吧。林書(shū)海說(shuō),我倒是沒(méi)什么,這些書(shū)在很多人眼里連垃圾都不如。周洲沒(méi)有再說(shuō)話,而是坐在沙發(fā)上,翻讀手中的書(shū)。
十二點(diǎn)半,他們?cè)趯?duì)面的餃子館吃飯,要了半斤韭菜蝦仁餃子、半斤豬肉茴香餃子、一盤(pán)素拼盤(pán)和兩瓶干啤。吃飯期間,周洲突然說(shuō),哎,告訴你一個(gè)事情啊,我估計(jì)也快離婚了,我們已經(jīng)分居三個(gè)月了。林書(shū)海沒(méi)有說(shuō)話,而是看著對(duì)方的神情。周洲又說(shuō),這次是我的不對(duì),對(duì)玲花沒(méi)感覺(jué)了,不知為啥,不想回那個(gè)家了,那里就是牢籠。林書(shū)海說(shuō),哎,都不容易啊,那娃以后咋辦?周洲說(shuō),玲花要養(yǎng),就讓她養(yǎng),我每個(gè)月給他們生活費(fèi),哎,活著有啥意思啊,活著活著,最后連心都沒(méi)有了。林書(shū)海沒(méi)有再說(shuō)話,突然發(fā)現(xiàn)朋友眼中的星辰墜落了。他在他眼中看見(jiàn)了另外的自己。他總是在他身上瞥見(jiàn)自己的幻影。
吃完飯后,他們又在書(shū)店里拉了一些閑話。分別時(shí),周洲再次叮囑道,書(shū)店沒(méi)了就沒(méi)了,你可要好好地,心放寬,不要走極端啊。林書(shū)海說(shuō),你今天看起來(lái)有點(diǎn)古怪,是不是有啥話沒(méi)有告訴我。周洲說(shuō),就是之前說(shuō)的,如果你想上班,我?guī)湍阒\個(gè)職位,如果不想上班,我?guī)湍阏覀€(gè)新書(shū)店。他感謝了他,并且要把莫里森的書(shū)送給他。周洲搖了搖頭,說(shuō),你也知道,出了你這個(gè)書(shū)店,我是不讀書(shū)的,我們下次再約。
周洲離開(kāi)后,林書(shū)海很快就寫(xiě)完了書(shū)評(píng)的剩下部分。交給編輯后,他坐在了沙發(fā)上,泡了一杯黃金芽。看著在水中舒展的茶葉,他沿著記憶的河流,回溯到了他們的大學(xué)時(shí)期,回溯到了第一次見(jiàn)到周洲的情景。
二
1998年的9月,林書(shū)海去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報(bào)到。有個(gè)手續(xù)需要交六十元的現(xiàn)金,而他恰好忘記帶錢(qián)包。正當(dāng)他準(zhǔn)備返回宿舍取錢(qián)時(shí),后面有個(gè)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說(shuō),我這里有零錢(qián)啊,你先用上。他轉(zhuǎn)過(guò)頭,看了看這張陌生的臉,說(shuō),謝謝同學(xué),可你不認(rèn)識(shí)我啊。同學(xué)說(shuō),我是周洲,我們是舍友啊。這個(gè)名字突然間涌向了眼前,于是他點(diǎn)點(diǎn)頭,從周洲那里借來(lái)六十元,現(xiàn)場(chǎng)交了手續(xù)費(fèi)。等忙完所有的事情,他們一起走出了行政樓,繞著秋日的學(xué)校散步。那一天,他們說(shuō)了很多的話,走了很多的路,也由此對(duì)學(xué)校的各個(gè)建筑有了最初印象。這是他來(lái)大學(xué)后認(rèn)識(shí)的第一個(gè)人。讓他意外的是,多少年后,周洲成了他大學(xué)時(shí)代的唯一朋友。
轉(zhuǎn)完圈之后,他們一起回到了宿舍,也由此認(rèn)識(shí)了另外四個(gè)舍友——來(lái)自廣東的安迪、來(lái)自福建的胡凱、來(lái)自黑龍江的吉慶與來(lái)自寧夏的馬曉濤。他和周洲來(lái)自本省,他是西安本地人,周洲是渭南人。和舍友們寒暄了幾句后,宿舍陷入了可怖的沉默,之后便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他從書(shū)包里取出一本尼采的書(shū)捧著讀。周洲喊了他的名字,說(shuō),你看我手里是什么書(shū)。他轉(zhuǎn)過(guò)頭,發(fā)現(xiàn)周洲拿著的是同一本書(shū)。也就是那個(gè)瞬間,林書(shū)海覺(jué)得自己遇見(jiàn)了真正的知己。以前上中學(xué),他從來(lái)不敢和任何人提自己讀尼采這件事情。父母也禁止他讀這位哲學(xué)狂人的作品。他們交換讀尼采的心得,好像也由此交換了彼此黑暗的心。
后來(lái),周洲就拉著林書(shū)海一起加入了本校的文學(xué)社團(tuán)。這個(gè)社團(tuán)每周都有一個(gè)主題活動(dòng),或是文學(xué)講座、或是讀書(shū)會(huì)、或是創(chuàng)作競(jìng)賽、或是觀影會(huì)。自從創(chuàng)社以來(lái),中文系的領(lǐng)導(dǎo)就特別支持這個(gè)文學(xué)社團(tuán),不僅僅為其提供資金、場(chǎng)地以及人力方面的支持,而且為其辦了一個(gè)名為《花冠》的文學(xué)月刊。盡管只是學(xué)校的內(nèi)部刊物,但《花冠》在學(xué)校里擁有很高的知名度,據(jù)說(shuō)師范大學(xué)每三個(gè)學(xué)生中,就有一個(gè)是《花冠》的忠實(shí)讀者。能在上面發(fā)表作品,是他們這些文學(xué)愛(ài)好者的最初夢(mèng)想。
11月末的某日午后,周洲回到了宿舍,對(duì)正在讀里爾克詩(shī)集的他說(shuō),今晚咱們?nèi)ネ饷娉曰疱伆桑艺?qǐng)客。他轉(zhuǎn)頭笑道,是不是有啥好事情要分享啊。周洲把書(shū)包放在桌子上,拉開(kāi)拉鏈,取出了兩本《花冠》雜志。他把其中的一本遞給他,說(shuō),請(qǐng)你從這期雜志中找一找亮點(diǎn)。打開(kāi)目錄后,第一眼便看到了周洲的名字。林書(shū)海沒(méi)有說(shuō)話,而是直接翻到了這篇名為《夏之旅》的散文。他把這篇文章認(rèn)真讀了一遍,是一篇偶有佳句的旅行散文,記錄了作者游玩南京城的所見(jiàn)所聞與所思。讀完后,林書(shū)海說(shuō),祝賀你啊,周同學(xué),文學(xué)事業(yè)邁出了如此重要的一步。周洲笑道,你可別瓤我了,就是瞎寫(xiě)呢,不過(guò)還領(lǐng)了一小筆稿費(fèi)。林書(shū)海的臉上掛著笑容,但心里有點(diǎn)失落,畢竟他也給雜志投過(guò)三次稿子了,最終都是落了大海,沒(méi)了回響。
第一學(xué)期很快就結(jié)束了,周洲邀請(qǐng)林書(shū)海去他的老家玩幾天,順便可以去渭河岸邊散散步、談?wù)勑摹A謺?shū)海剛好也想借此機(jī)會(huì)出門(mén)逛逛,便接受了周洲的邀請(qǐng)。回家的前一天,他們?nèi)チ藢W(xué)校的圖書(shū)館。周洲借了一本托馬斯·曼的《魔山》,林書(shū)海借的是但丁的《神曲》。看見(jiàn)彼此所借之書(shū)之后,他們相視一笑,明白了彼此能成為朋友的真正原因。那個(gè)夜晚,林書(shū)海陷入但丁構(gòu)造的地獄世界。他以前只在課本上讀過(guò)這本書(shū)的概括,原本以為是距離自己非常遙遠(yuǎn)的宗教書(shū)籍,如今發(fā)現(xiàn)卻是但丁的心靈史。但丁所遇到的人生困惑與他的人生困惑其實(shí)并沒(méi)有本質(zhì)的差別。重新發(fā)現(xiàn)了但丁,就像重新發(fā)現(xiàn)了大海。當(dāng)然,這本書(shū)里也有很多他并不熟悉的歷史典故與宗教知識(shí)。那個(gè)夜晚,他夢(mèng)見(jiàn)了但丁所看見(jiàn)的黑暗森林,也夢(mèng)見(jiàn)了那三頭野獸。在夢(mèng)中,他與周洲交換了彼此的身份。
林書(shū)海在這個(gè)縣城待了三天,獲得了全新的生活體驗(yàn)。臨走前,周洲把一袋椽頭饃和一份八寶辣子交給了他,說(shuō),這是我媽帶給你家的,是我們這里的特產(chǎn),咱們寒假后再見(jiàn)。林書(shū)海上了車,回頭和周洲說(shuō)了再見(jiàn)。雖然只有三天,但林書(shū)海覺(jué)得自己的內(nèi)心經(jīng)歷了某種平靜的風(fēng)暴,獲得了某種微小的成長(zhǎng)。車啟動(dòng)后,他看了看戶外的零度風(fēng)景,隨后繼續(xù)將目光放在手中的《神曲》上。在某個(gè)瞬間,他突然意識(shí)到但丁的世界與此刻的世界,其實(shí)是兩個(gè)共存的平行世界。
自從周洲有了戀情后,林書(shū)海和他相處的時(shí)間也變短了。除了日常的課程,林書(shū)海將大量時(shí)間放在了圖書(shū)館,而文學(xué)借閱室和社科借閱室成了他的人間天堂。按照?qǐng)D書(shū)的序號(hào),他一本接著一本翻,有的書(shū)看看簡(jiǎn)介即可,有的書(shū)則需要深入閱讀。他會(huì)做讀書(shū)筆記,甚至?xí)橄矏?ài)的書(shū)寫(xiě)簡(jiǎn)短的評(píng)論。只有與書(shū)相處時(shí),他才能夠獲得深刻的平靜。對(duì)于書(shū)的上癮,讓他想戒也戒不掉。閱讀之外,他開(kāi)始寫(xiě)日記,只不過(guò)是浮光掠影般的記錄,卻也是內(nèi)心的真實(shí)圖景。
5月的最后一個(gè)周末,他在閱覽室讀紀(jì)德的《田園交響曲》,抬眼時(shí)瞥見(jiàn)對(duì)面有人看著他。他迅速挪開(kāi)了目光,半邊臉燃起了火焰,心中的荒野著火了。他將書(shū)放進(jìn)書(shū)包,起身離開(kāi)了圖書(shū)館。圖書(shū)館外,他聽(tīng)見(jiàn)有人在背后呼喊他的名字。他轉(zhuǎn)過(guò)身,看到了對(duì)面的那個(gè)女生,于是問(wèn)道,你好啊,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呢。女生說(shuō),你的筆記本上寫(xiě)著你的名字和學(xué)院,我也是無(wú)意間瞥見(jiàn)的,對(duì)了,我也喜歡紀(jì)德的書(shū),《窄門(mén)》打開(kāi)了我新世界的大門(mén)。之后的情節(jié)像是很多浪漫小說(shuō)那樣,兩個(gè)人因書(shū)結(jié)緣,成為書(shū)友,成為朋友,后來(lái)成了戀人。
女生名叫楊梅,也是西安人,是同年級(jí)的哲學(xué)系學(xué)生。楊梅也是一個(gè)書(shū)迷,只不過(guò)她并不想成為作家,而是想成為學(xué)者。成為戀人后,他們會(huì)交換彼此的讀書(shū)筆記,而他也會(huì)把自己的文章拿給她去讀。她成了他的第一個(gè)讀者,也成了他唯一的評(píng)論者。大二下半學(xué)期,他把楊梅介紹給了周洲和陳舒,當(dāng)天下午四人便去看了伯格曼的電影《假面》,晚上又一起吃了火鍋。回到宿舍后,周洲問(wèn)他和楊梅發(fā)展到了哪種地步。他說(shuō),就是牽牽手,也親過(guò)她。周洲說(shuō),只有睡過(guò)了,才算是真戀人哦,書(shū)海君,請(qǐng)繼續(xù)加油吧。他笑了笑,沒(méi)有繼續(xù)說(shuō)下去,而是打開(kāi)了手中的黑色筆記本。不知為何,他感覺(jué)自己和周洲站在了同一個(gè)平臺(tái)上,又有了更多的生活與藝術(shù)的交集。
大三上學(xué)期,他去學(xué)校對(duì)面的書(shū)店買了些專業(yè)參考書(shū)。在一家名為“是夢(mèng)”的書(shū)店里,他很快便找到了所需要的書(shū)籍。他又在書(shū)店里轉(zhuǎn)悠,打量著書(shū)架上的書(shū)籍。書(shū)店老板對(duì)他說(shuō),這個(gè)同學(xué),你也可以去地下室看看,那里或許有你想要的書(shū)。書(shū)店老板指了指地下室的方向。他點(diǎn)頭感謝了他,于是沿著階梯一步步往下走,有種下地獄的錯(cuò)覺(jué)。地下室仿佛另外的世界,擺放著形形色色的舊書(shū),其間可以聞到時(shí)間的塵味。他自認(rèn)為讀過(guò)很多書(shū),卻在這里迷了路。在書(shū)籍森林中,他發(fā)現(xiàn)了1990年版本的《神曲》,譯者為朱維基,而之前在圖書(shū)館所借閱的是王維克的譯本。他翻看了其中的前兩頁(yè),是完全不同的閱讀體驗(yàn),便毫不猶豫地買下了這本書(shū)。回到宿舍后,他把這本書(shū)放進(jìn)了自己的抽屜,時(shí)不時(shí)會(huì)拿出來(lái)翻讀兩三頁(yè)。他在這本書(shū)中發(fā)現(xiàn)了更為陌生卻更為本真的自己。他沒(méi)有把這個(gè)發(fā)現(xiàn)說(shuō)給任何人。
自此之后,他每隔一些日子便去是夢(mèng)書(shū)店淘書(shū)。有時(shí)候,他寧愿成為隱身人,因?yàn)槟抢锸撬牟厣碇Hサ拇螖?shù)多了,和老板漸漸也熟絡(luò)了,從淺到深,從少到多。他們說(shuō)得最多的就是書(shū),各種各樣的書(shū),多彩多樣的思想。老板名叫夏河,五十多歲,以前是國(guó)企的車間工人,因?yàn)橐馔馐鹿识鴮?dǎo)致肋部骨折,出院后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了,于是選擇從工廠內(nèi)退,拿到了一些經(jīng)濟(jì)補(bǔ)償。后來(lái)因?yàn)楦鞣N機(jī)緣巧合,在師范大學(xué)對(duì)面的幸福堡開(kāi)了這家舊書(shū)店,生意不溫不火,卻也基本上夠日常生活的開(kāi)銷。夏河說(shuō),自從開(kāi)了書(shū)店后,我才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義,以前算是白活了。林書(shū)海問(wèn)他為何有這樣的想法。他說(shuō),以前在工廠,就像機(jī)器一樣,沒(méi)有任何精神生活,還以為世界就像自己想的那么大。等熟了之后,林書(shū)海也會(huì)把心事選擇性地講給這位長(zhǎng)者,而夏河的回答總能說(shuō)進(jìn)他的心坎。他沒(méi)有把到是夢(mèng)書(shū)店的事情告訴周洲和楊梅,因?yàn)槟抢锸菍儆谒粋€(gè)人的秘密花園。
轉(zhuǎn)眼間便到了畢業(yè)季節(jié)。周洲如愿地考上公務(wù)員,陳舒則去了南方的某個(gè)報(bào)業(yè)集團(tuán)做社會(huì)新聞?dòng)浾摺K麄儍蓚€(gè)和平分手,并相約做一生的好朋友。林書(shū)海通過(guò)了教師考試,即將成為西安市某重點(diǎn)中學(xué)的語(yǔ)文教師,楊梅則選擇繼續(xù)留在本校攻讀哲學(xué)碩士學(xué)位,兩個(gè)并沒(méi)有說(shuō)分手的事情,但彼此都明白已經(jīng)不是同路人了。畢業(yè)前夕,他們四個(gè)人又去了那一家火鍋店,吃了散伙飯。那天晚上,周洲喝了很多的酒,一會(huì)兒哭一會(huì)兒笑,最后林書(shū)海和陳舒把他扶回了宿舍。在學(xué)校的最后一個(gè)晚上,他失眠了,往事像書(shū)頁(yè)般在他眼前翻過(guò),沒(méi)有留下文字。他想到了第一次住學(xué)校的那個(gè)夜晚,也是失眠,也是惶恐,只不過(guò)心中還有些許期待。四年過(guò)去了,期待已經(jīng)褪去色彩,迎接自己的將是未知的命運(yùn)。半夜,他聽(tīng)到了周洲的夢(mèng)話,夢(mèng)話中出現(xiàn)了楊梅的名字。恍然間,他明白了很多事情,他哭了,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已經(jīng)失去的日子。
三
畢業(yè)后,他去了明光中學(xué)做語(yǔ)文教師。父母也滿意他的這份工作,畢竟是有編制的鐵飯碗。他也為自己制定了比較詳盡的人生規(guī)劃——比如說(shuō)工作之外保持閱讀與寫(xiě)作的習(xí)慣;比如說(shuō)寒假的時(shí)候去哈爾濱與海南島,暑假的時(shí)候去臺(tái)北與東京;再比如說(shuō)去健身、去游泳、去爬山、去看燈塔,等等。然而,工作并沒(méi)有想象中那么輕松自在,相反,大量與教學(xué)無(wú)關(guān)的事情拖著他、纏著他、磨著他、耗著他,甚至常常以噩夢(mèng)的形式控制著他。夏至的晚上,他夢(mèng)見(jiàn)自己死去了,夢(mèng)見(jiàn)了活著的自己將死去的自己火葬,看見(jiàn)了升入天空的縷縷青煙,最后,活著的自己把骨灰撒進(jìn)了大海。醒來(lái)后,他盯著戶外的黑夜,仿佛看見(jiàn)了在海中溺水的自己。如此活著,常常讓他有種溺水感。
在經(jīng)歷了一次短暫的崩潰后,他選擇把自己的困境講給父親。聽(tīng)完后,父親說(shuō),你這剛進(jìn)入社會(huì)不久,再熬一熬就習(xí)慣了。他說(shuō),不想熬了,現(xiàn)在看見(jiàn)書(shū),看見(jiàn)字,我就惡心。父親說(shuō),你這就是太矯情了,要是你經(jīng)歷過(guò)我們那個(gè)時(shí)代,你就知道你有多幸運(yùn)了。他說(shuō),你們有你們的痛,我們也有我們的難處,這不是時(shí)代的問(wèn)題,是每個(gè)人的問(wèn)題。父親說(shuō),你就是太脆弱了,多經(jīng)歷些社會(huì)的毒打是好事。他看著父親陌生的臉,沒(méi)有再說(shuō)話,而是回到了房間,繼續(xù)批改那看不到盡頭的作業(yè)。將近十一點(diǎn)半的時(shí)候,他才完成了當(dāng)天的工作。臨睡前,他想翻一翻身邊的閑書(shū),卻發(fā)現(xiàn)自己沒(méi)有了任何閱讀的興致。關(guān)掉燈后,在黑暗中,他覺(jué)得自己的靈魂與肉身都被這日常煩瑣的事情慢慢掏空了。他開(kāi)始想念自己的大學(xué)生活,想念周洲和楊梅,卻發(fā)現(xiàn)和他們已經(jīng)失去了聯(lián)系。無(wú)法入睡,于是打開(kāi)臺(tái)燈,敞開(kāi)筆記本,想要在上面記錄心事,卻寫(xiě)不出一個(gè)字了。眼前的稿紙讓他感到害怕,如同步入了黑茫茫的森林。他的心生病了,又找不到醫(yī)治的方法。看著眼前的《神曲》,他突然想到了那個(gè)在舊書(shū)店夢(mèng)游的人。
周末,他去了是夢(mèng)書(shū)店,見(jiàn)到了夏河。自從林書(shū)海畢業(yè)后,他們有三年多都沒(méi)有見(jiàn)面了,甚至連電話也沒(méi)有打過(guò)。看到他后,夏河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握著他的手說(shuō),你這家伙,還以為你消失了呢。他說(shuō),再不見(jiàn)你,我就感覺(jué)自己快要死了。他給林書(shū)海泡了一杯茶,兩個(gè)人之間并沒(méi)有什么生分,開(kāi)始聊起了各自的生活。夏河說(shuō),今年冬天,我就要離開(kāi)這里去成都了,老兩口要去那里幫忙看孫子了。林書(shū)海問(wèn),那這個(gè)書(shū)店咋辦啊?夏河說(shuō),看能不能找到下家,要不就得把書(shū)全處理掉,太可惜了,這些書(shū)也都是我的命啊。林書(shū)海想了半晌,說(shuō),其實(shí),我很想接手這個(gè)書(shū)店,就是不知道具體的情況。夏河說(shuō),這個(gè)書(shū)店每月盈利還可以,也自在,不看人臉色,就是要常守在這里,比較消耗人,不能和你鐵飯碗相比。林書(shū)海說(shuō),我感覺(jué)自己被那里困住了,就像籠子里的鳥(niǎo),再這樣下去我會(huì)瘋掉的。夏河說(shuō),這個(gè)你可要好好思索,和家里人好好談?wù)劊皇撬腥硕寄艹陨蠂?guó)家飯。之后,他們又閑談了其他的事情。臨走前,夏河送了他一套博爾赫斯全集,叮囑他要好好讀讀這位阿根廷的文學(xué)大師。
讀完博爾赫斯全集的那個(gè)夜晚,他終于可以寫(xiě)出屬于自己的文章了,不是散文隨筆,不是小說(shuō)詩(shī)歌,而是辭職信。第二天,他把辭職信交給了校長(zhǎng)。校長(zhǎng)說(shuō),小林老師,你可是咱們學(xué)校的骨干教師啊,我非常看重你,你再好好想想,要慎重一點(diǎn),這么多年來(lái)都沒(méi)有人辭過(guò)職。林書(shū)海說(shuō),感謝校長(zhǎng)這么多年對(duì)我的照顧,這個(gè)決定,我已經(jīng)想了很久了。校長(zhǎng)搖了搖頭,沒(méi)有再說(shuō)話,而是在辭職信上簽了名。之后,他走了離職的正常手續(xù),蓋了好幾個(gè)章子,與學(xué)校慢慢地剝清了所有關(guān)系。走出大門(mén)后,他轉(zhuǎn)過(guò)頭,給學(xué)校搖了搖手,說(shuō)了聲再見(jiàn)。
當(dāng)他把這個(gè)消息告訴父母之后,想象中的暴風(fēng)雨并沒(méi)有發(fā)生,取而代之的是更為可怕的平靜。晚餐時(shí),父親突然開(kāi)口道,哎,不管你做怎樣的決定,都是我們的孩子,我們都會(huì)給你托著底。母親說(shuō),如果我們都不理解你的話,怎么可能會(huì)讓別人理解你呢。聽(tīng)完父母的話后,眼淚從臉上滾進(jìn)了湯面里,他沒(méi)有作聲,而是悶頭吃完了飯。
和計(jì)劃中的一樣,他從夏河手中接管了這家舊書(shū)店。維持舊書(shū)店的運(yùn)轉(zhuǎn),并沒(méi)有想象中那么簡(jiǎn)單。不過(guò)在夏河的指導(dǎo)下,他慢慢地掌握了其中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如何選書(shū)、如何進(jìn)書(shū)、如何擺書(shū)、如何售書(shū)等,所有的細(xì)節(jié)最終都化為生活的日常習(xí)慣。10月中旬,夏河正式離開(kāi)了是夢(mèng)書(shū)店。離開(kāi)前夜,林書(shū)海請(qǐng)夏河去湘菜館吃了晚飯,并相約以后要保持聯(lián)系。
夏河離開(kāi)后,他獨(dú)自來(lái)打理這家書(shū)店,父母偶爾也會(huì)來(lái)幫忙照顧。在他二十八歲的時(shí)候,父母給他全款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并一再督促他結(jié)婚,而他總會(huì)找各種理由搪塞過(guò)去。畢業(yè)后,他先后談過(guò)三次戀愛(ài),最后的結(jié)果都是不了了之。所有問(wèn)題都在自己身上——他對(duì)感情很容易就厭倦了,他對(duì)戀人缺乏持久的熱情,他不懂得挽留,也不會(huì)哄人。更可怕的是,當(dāng)戀人們離開(kāi)之后,他沒(méi)有遺憾,沒(méi)有傷心,也沒(méi)有愧疚,有的只是擺脫重負(fù)后的自由與自在。他覺(jué)得自己不適合戀愛(ài),更不適合組建家庭。為了避免更多的傷害,后來(lái)的他,幾乎不和異性發(fā)生微妙的情感糾葛。更可怕的是,他對(duì)于書(shū)的迷戀,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對(duì)于人的迷戀。
有時(shí)候,他會(huì)睡在地下室,側(cè)著身子看著眼前的書(shū)籍。他喜歡被群書(shū)環(huán)繞,有種踏踏實(shí)實(shí)的安全感。夜深之時(shí),他甚至能聽(tīng)到從書(shū)籍內(nèi)部發(fā)出來(lái)的聲響。有個(gè)夜晚,他夢(mèng)見(jiàn)周洲從山上跳了下去,以飛翔的姿態(tài)。夢(mèng)醒后,他渾身盜汗,有種不祥的預(yù)兆。凌晨三點(diǎn)鐘,他撥打了周洲很久之前留下的電話。對(duì)方并沒(méi)有接,自己也只好作罷。清晨八點(diǎn)鐘,他接到了周洲的電話:你這家伙,大半夜給我電話,是不是夢(mèng)見(jiàn)我死了?他說(shuō),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周洲說(shuō),我之前也夢(mèng)見(jiàn)過(guò)你死了,是從山上跳下去的,我當(dāng)時(shí)也想給你打電話。他說(shuō),我也做了同樣的夢(mèng),可能太久沒(méi)有見(jiàn)面了,在彼此心里已經(jīng)死了。周洲笑道,咱們都好好的,什么死不死的,我這周去西安,到時(shí)候一起吃火鍋。
從這個(gè)夢(mèng)開(kāi)始,他更堅(jiān)信周洲就是另外一個(gè)自己,過(guò)著自己的另外一種人生。后來(lái)讀黑塞的《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突然覺(jué)得這本書(shū)就是關(guān)于他和周洲的另一種現(xiàn)實(shí)寫(xiě)照。第二天,他就把這本書(shū)寄給了周洲。
四
2009年春天的某個(gè)下午,他打開(kāi)豆瓣網(wǎng),收到一條私信,上面寫(xiě)道:林書(shū)海先生,您好,我是《青年文藝報(bào)》的編輯李曼童,讀到了您寫(xiě)的關(guān)于庫(kù)切小說(shuō)《等待野蠻人》的評(píng)論,很喜歡,希望可以在本報(bào)刊發(fā),并附有一定的稿費(fèi),是否同意,期待您的回復(fù)。林書(shū)海將這條私信反復(fù)讀了五六遍,隨后回復(fù)道:同意,感謝關(guān)注。之后,他打開(kāi)自己的豆瓣讀書(shū)的頁(yè)面,發(fā)現(xiàn)這幾年來(lái)已經(jīng)標(biāo)注了兩千多本書(shū),寫(xiě)過(guò)一百多篇書(shū)評(píng),總計(jì)有五萬(wàn)三千多人的關(guān)注。他原本只想將這里作為自己的秘密花園,沒(méi)想到卻開(kāi)出了可以供人觀賞的花朵。無(wú)論是他人的贊許或是批評(píng),他都會(huì)認(rèn)真回復(fù)每一條網(wǎng)友的留言,這讓他覺(jué)得自己并不是一座孤島。他渴望成為海,而不是成為島。
自從在報(bào)紙上發(fā)表了文章后,又有其他編輯通過(guò)豆瓣陸陸續(xù)續(xù)找到了他。他的書(shū)評(píng)文字變成了報(bào)紙上的鉛字,這讓他有了某種微不足道的成就感。豆瓣上,關(guān)注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而他也珍惜每一次表達(dá)的機(jī)會(huì)。后來(lái),他在幾家報(bào)紙先后開(kāi)了專欄,把自己喜歡的書(shū)籍通過(guò)文章傳達(dá)給更多的人。除了書(shū)評(píng),他有時(shí)候也會(huì)寫(xiě)點(diǎn)散文與詩(shī)歌,記錄自己的所思所想。與此同時(shí),他也把舊書(shū)曬在了豆瓣上,會(huì)有網(wǎng)友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來(lái)購(gòu)買這些書(shū)籍。有時(shí)候,父母也會(huì)過(guò)來(lái)幫他搭把手,看著兒子的精神狀況與經(jīng)濟(jì)收入都還不錯(cuò),他們懸著的心才有了一絲絲安慰。
2014年,有個(gè)出版公司的編輯表示愿意幫他出一本書(shū)評(píng)集,問(wèn)他是否有出版的意向。他很開(kāi)心地接受了這個(gè)邀請(qǐng),并且與對(duì)方簽署了出版合同,書(shū)名就定為《是夢(mèng)》。過(guò)了一段時(shí)間,書(shū)便順利出版了,雖然首印只有八千冊(cè),稿費(fèi)也不多,但對(duì)于他而言,這是一種莫大的榮幸,也是生活的新路標(biāo)。可能因?yàn)樵诙拱晟嫌幸欢ǖ挠绊懥Γ@些書(shū)不到三個(gè)月就告罄了,隨后又加印了三次。豆瓣上對(duì)這本書(shū)的評(píng)價(jià)也不錯(cuò),有八點(diǎn)五分,出版社的編輯自然也很滿意,表示愿意長(zhǎng)期與他合作。他感覺(jué)自己打開(kāi)了那道窄門(mén),看見(jiàn)了新天新地。在經(jīng)歷了地獄和煉獄之后,他仿佛進(jìn)入了天堂。他又重新讀了《神曲》,并盡可能收集《神曲》的各個(gè)版本與中文譯本。對(duì)于他而言,《神曲》就是自己的啟示錄。他已經(jīng)寫(xiě)了足夠多的書(shū)評(píng),但仍舊找不到評(píng)論《神曲》的道路。
隨著自己在書(shū)評(píng)圈的影響力越來(lái)越大,是夢(mèng)書(shū)店的聲名也跟著水漲船高,很多文學(xué)青年會(huì)慕名前來(lái),借著買書(shū)的名義和他閑談幾句。在好幾個(gè)中文系男生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當(dāng)年的模樣。有幾個(gè)常來(lái)書(shū)店的男生,最后也成了他的朋友。他偶爾也會(huì)想到夏河,想到曾經(jīng)和他深談的那些個(gè)午后。如果沒(méi)有夏河,自己也許不會(huì)走上這條路。從某種意義上講,夏河就是為自己領(lǐng)路、幫自己穿過(guò)地獄之旅的維吉爾。然而,他始終找不到給夏河打電話的理由。
2015年冬天的某個(gè)上午,面對(duì)著文檔,他往上面敲打著文字,是一篇關(guān)于斯坦納《語(yǔ)言與沉默》的書(shū)評(píng)。寫(xiě)到收尾處,他收到了一條來(lái)自夏河的短信,內(nèi)心有點(diǎn)驚詫。短信上寫(xiě)道:家父夏河先生已于今年十月因病去世,感謝您曾經(jīng)和他有過(guò)交往,人生海海,萬(wàn)事如煙,家父的這個(gè)手機(jī)號(hào)碼將于近期注銷,再次祝您生活順?biāo)臁A謺?shū)海不敢相信眼前的話,又反復(fù)讀了好幾遍,才確定這并不是夢(mèng)。他回復(fù)了那條短信:感謝您,夏河先生,我們還會(huì)見(jiàn)面的,我也會(huì)照顧好是夢(mèng)書(shū)店的。發(fā)完短信后,他重新面對(duì)著文檔,而眼淚已經(jīng)淹沒(méi)了眼前的荒野。
又過(guò)了幾日,雪停了,太陽(yáng)從陰霾中探出了頭,是夢(mèng)書(shū)店的顧客也多了起來(lái)。手上的稿子完成了一大半,心情也舒暢了一大半。除了書(shū)店的生意,他白天大多數(shù)的時(shí)間都是用來(lái)閱讀新到的著作。這里的每一本書(shū),都是他嚴(yán)格意義上的朋友。他珍視與每一本書(shū)的情誼。這一天,是夢(mèng)書(shū)店迎來(lái)一位獨(dú)特的顧客。他從聲音中聽(tīng)出了她,經(jīng)過(guò)確認(rèn)后,才喊出了她的名字,楊梅,你怎么來(lái)這里了?楊梅轉(zhuǎn)過(guò)頭,眼神中的疑惑瞬間消散了,笑道,原來(lái)是書(shū)海啊,這是你開(kāi)的書(shū)店嗎?我還以為你一直在中學(xué)教書(shū)呢。林書(shū)海說(shuō),早都不教書(shū)了,你這些年過(guò)得很好吧?楊梅點(diǎn)了點(diǎn)頭,說(shuō),好著呢,這是我的老公王晨宇,我倆都在師大中文系教書(shū),你媳婦也還好吧?林書(shū)海搖了搖頭,苦笑道,我還沒(méi)結(jié)婚的。短暫的沉默后,楊梅說(shuō),這么多年了,你還是這么愛(ài)書(shū),你給我們推薦幾本書(shū)吧。他原本想把自己的書(shū)送給他們,然而轉(zhuǎn)念又把話咽了下去,給他們推薦了幾本外國(guó)小說(shuō)。臨走前,楊梅和他又交換了手機(jī)號(hào)碼,并邀他下次去他們家吃飯。他點(diǎn)點(diǎn)頭,明白那些都是客套話,因?yàn)樗麄冊(cè)缫呀?jīng)不是同一類人了,不可能會(huì)再見(jiàn)面了。在她丈夫的眼神中,他已經(jīng)讀出了那種想要掩飾的輕蔑。某個(gè)瞬間,他開(kāi)始懷疑自己當(dāng)初的選擇是否正確。不過(guò),這樣的自問(wèn)轉(zhuǎn)瞬即逝。他已經(jīng)厭倦了沒(méi)有意義的追問(wèn),只有真正的行動(dòng)才能讓他體會(huì)到深刻的快樂(lè)。
臨近年關(guān),他帶著父母去海南島過(guò)年。那是父母第一次見(jiàn)到大海,他們久久地站在海邊,看著一艘輪船起航,慢慢地消融于天海盡頭。父親說(shuō),你也大了,我們也陪不了你幾年了,我們還是希望你能找個(gè)陪你過(guò)后半生的人,哎,不過(guò)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路。母親說(shuō),看著海,人變小了,心卻變大了。隨后,他們?nèi)齻€(gè)人在海邊散步,唯有大海知道他們各自的心事。夜間,他聽(tīng)到了海的嘆息。
五
這么多年過(guò)去了,是夢(mèng)書(shū)店已經(jīng)成了他的精神避難所。他在這里讀過(guò)各種各樣的書(shū),見(jiàn)過(guò)形形色色的人,也做過(guò)多彩多姿的夢(mèng)。在這個(gè)人間方舟上,他理解了自己與世界的關(guān)系,也看清了意義的幻象。如今,幸福堡即將要消失了,書(shū)店也跟著要消失了,而他乘著海上虛舟,還沒(méi)有找到未來(lái)的棲息地。然而,他已經(jīng)不害怕時(shí)間了,也不害怕存在了,那些讀過(guò)的書(shū)已經(jīng)為他建造了堅(jiān)不可摧的精神王國(guó)。
再過(guò)三天,他就要離開(kāi)這個(gè)書(shū)店了。書(shū)店里的書(shū)基本上都處理完了,只剩下了最后的三四十本,其中的五本是不同版本的《神曲》。他把這五本《神曲》放進(jìn)自己的包里,晚上帶回了家,與其他三本《神曲》擺在了一起。他打開(kāi)了筆記本電腦,打開(kāi)了空白文檔,面對(duì)眼前的盈盈綠光,再看看眼前的《神曲》。忽然間,他找到了通往這本巨著的道路。在寫(xiě)這篇評(píng)論的時(shí)候,他仿佛先后又經(jīng)歷了地獄、煉獄與天堂,在敲完最后一個(gè)字時(shí),他看見(jiàn)了真正的榮光。寫(xiě)完文章后,已經(jīng)到了午夜時(shí)分,他長(zhǎng)時(shí)間地凝視窗外的黑暗,恍然間領(lǐng)悟到了生活的奧義,那是無(wú)言卻又豐沛的永恒沉默。打開(kāi)其中的一本《神曲》,他重新念出了最初的篇章——就在我們?nèi)松贸痰闹型荆以谝蛔璋档纳种行盐蜻^(guò)來(lái),因?yàn)槲以诶锩婷允Я苏_的道路。那瞬間,他突然理解了但丁,也突然理解了自己。
他又去吃了老馬家胡辣湯,馬遠(yuǎn)航告訴他這是最后一次營(yíng)業(yè)了,明天就要離開(kāi)這里了。林書(shū)海把自己的《是夢(mèng)》從包里拿了出來(lái),送給了他。馬遠(yuǎn)航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道,你是我們這里好多年的老顧客了,沒(méi)想到你居然是個(gè)作家。林書(shū)海說(shuō),不,算不上是作家,就是隨意寫(xiě)的文章。馬遠(yuǎn)航說(shuō),等我們找好新店了,到時(shí)候把地址發(fā)給你。林書(shū)海點(diǎn)了點(diǎn)頭,隨后便離開(kāi)了這家店。他站在路口,看著眼前的廢墟景象。幸福堡往日的繁華已經(jīng)不在了,剩下的只是人走店亡后的荒涼。但他的心并不荒蕪。要不了多久,這里將成為一片廢墟,這里的故事將化為塵土,而我們所有人終將會(huì)被時(shí)間所掩埋。
最后一天,周洲來(lái)書(shū)店幫忙。林書(shū)海摘掉了書(shū)店的牌匾,摸了摸上面的四個(gè)字,是時(shí)間的觸覺(jué),也是夢(mèng)的觸覺(jué)。他對(duì)周洲說(shuō),做了這么多年的夢(mèng),也是時(shí)候醒過(guò)來(lái)了。周洲問(wèn),接下來(lái),你要做什么呢?林書(shū)海說(shuō),好久之前編輯就向我約了書(shū)稿,現(xiàn)在我終于知道該寫(xiě)點(diǎn)什么了。周洲問(wèn)道,寫(xiě)什么呢?林書(shū)海說(shuō),就寫(xiě)關(guān)于這個(gè)書(shū)店的故事。周洲點(diǎn)了點(diǎn)頭,幫他打理好了書(shū)店剩下的事情。在關(guān)掉書(shū)店大門(mén)前,他又轉(zhuǎn)過(guò)頭來(lái)看了看這個(gè)空蕩蕩的空間,而他的心卻被往事與未來(lái)共同填滿。他不再害怕任何事情了,包括在夢(mèng)中出現(xiàn)的那場(chǎng)大火。
【丁小龍,1988年2月生,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碩士。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魯迅文學(xué)院高研班學(xué)員,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huì)簽約作家。作品發(fā)表在國(guó)內(nèi)多家文學(xué)雜志,被多種文學(xué)選本轉(zhuǎn)載。另有譯作三十萬(wàn)字,翻譯并發(fā)表了包括托妮·莫里森、科爾姆·托賓、薩曼·拉什迪與珍妮特·溫特森等人的中短篇作品。入選陜西省“百優(yōu)人才”。著有長(zhǎng)篇小說(shuō)《世上的光》,小說(shuō)集《世界之夜》《島嶼手記》。曾獲陜西省青年文學(xué)獎(jiǎng)等多種獎(jiǎng)項(xiàng)。】
責(zé)任編輯? ?李約熱
3433501908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