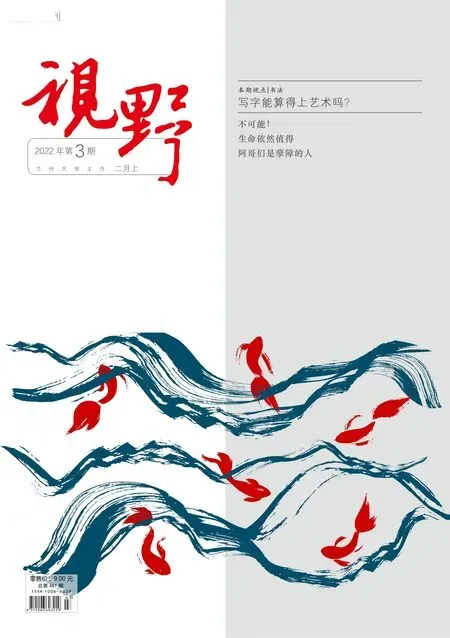宋代書法:經典的一種尺度
2022-03-14 07:39:10張銳
視野
2022年3期
關鍵詞:書法
/張銳

自東漢至初唐,支配書法史的強大藝術傳統,在幾百年間逐漸確立,中國傳統社會的精英文人由此正式進入該系統,并以此自辯——“每一個士大夫都可以根據共同的標準(這也是他自己學書時需遵循的)來判斷一件書法作品,哪怕兩人地隔數千里、時隔數百年。書法卻成了加強統治階級聯系的有力手段。”德國漢學家雷德侯因此稱書法是一種“精英藝術”。
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北宋中期文人,將書法改革看作其政治與文學改革的重要部分。歐陽修行書《自書詩文稿卷》現藏于遼寧省博物館,卷中包括《歐陽氏譜圖序》和《夜宿中書東閤》兩件作品。后者寫于宋英宗繼位不久出現的一次政治危機,曾任遼寧省博物館研究室主任的劉中澄評價此詩:“耿耿忠介之心,昭示無窮。”
作為與政治、道德關聯的關鍵節點之一,宋朝的書法樣貌明顯開始發生轉折。復旦大學文博系教授沃興華說:“楷書在唐代經歷了正反合的發展過程,各種風格形式已得到充分表現,猶如一朵盛開的鮮花,精華泄盡,難以為繼了。因此,到宋代,書法家開始把全副精力投人到行草的創作和研究之上。”
以蘇、黃、米(蘇軾、黃庭堅、米芾)為代表的北宋書法家,從唐人“尚法”的天花板中,開“尚意”書風,倡導書法注重意趣和個人情感宣泄,行草書體也為這種書風提供了便利。暨南大學書法研究所所長曹寶麟曾不無遺憾地說:“以‘尚意’為特征的宋代書法所代表的尺牘書風,在唐人‘尚法’的豐碑巨制的映照之下,只覺得像蘭苕翡翠,而唐代,則無疑是碧海鯨魚。……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大理文化(2022年8期)2022-09-27 13:38:02
大江南北(2022年9期)2022-09-07 13:13:48
求知(2022年5期)2022-05-14 01:28:58
娘子關(2022年1期)2022-03-02 08:18:42
娘子關(2021年6期)2021-12-16 01:18:44
娘子關(2021年5期)2021-10-20 03:16:06
中老年保健(2021年3期)2021-08-22 06:53:18
娘子關(2021年3期)2021-06-16 10:56:32
少林與太極(2020年11期)2020-03-25 01:27:34
吐魯番(2018年1期)2018-06-12 07:1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