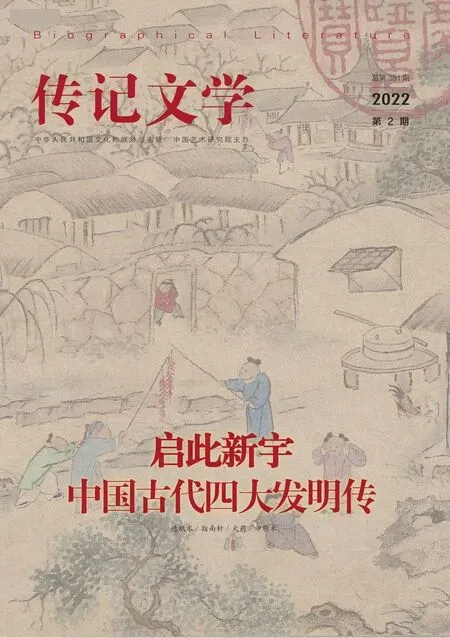記汪蔚林先生二三事
緩 之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由一組詩說起
1983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主任汪蔚林先生因病去世。三個月后,《羊城晚報》(1983年6月4日)刊發了文學所老人荒蕪先生(1916—1995)的《挽汪蔚林》詩,前有引言:“汪蔚林同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主任,學識淵博,性情樸厚,不幸因病去世,我們共事將近三十年,一同坐牛棚,下干校,艱苦共嘗,良友云亡,深感悲痛,爰草二律,歌以當哭。”其一曰:
原期朝夕敘家常,誰料天人各一方。
座上談詩“雙右派”,館中結伴“四人幫”。
清晨南畝收棉子,午后西園起菜秧。
傍晚偷閑瓜地坐,聽君續話孔東塘。
據作者自注,“雙右派”是指徐懋庸和作者荒蕪本人。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聯”成員。魯迅曾為其作品《打雜集》作序,對他多有肯定,后來一篇《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則又表現出對他的強烈不滿。徐懋庸晚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四人幫”是詩人自封的,當然是戲稱,指文學所的四位老人:陳友琴(1902—1996)、吳曉鈴(1914—1995)、汪蔚林和荒蕪。孔東塘,是《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自稱云亭山人。汪蔚林先生曾輯校《孔尚任詩文集》,是孔尚任研究的專家,故有“聽君續話孔東塘”之說。
該詩其二曰:
牛棚得句共推敲,偷送藏書慰寂寥。事到臨頭裝土蒜,時逢佳節啃豬骹。明知歪理非真理,蔑視熱嘲與冷嘲。長憶達摩克利劍,愁聽鄰笛過松郊。
作者自注:“裝土蒜”,指“文革”中逼供者專講歪理,他們都只好裝蒜。汪蔚林先生說,蒜也有兩種,錢鍾書(1910—1998)、吳世昌(1908—1986)他們裝的是洋蒜,他自己裝的是土蒜。錢鍾書畢業于牛津大學,吳世昌曾在牛津大學任教,1962年回國。兩位都是文學所的研究員,后來一同下“干校”。“時逢佳節”是指每逢年過節,那些被集中起來的“牛鬼蛇神”們不許回家,幸好食堂尚有醬豬蹄出賣。“達摩克利劍”(The Sword of Damocles)用的西方典故。汪蔚林先生老兩口住一間小屋,屋頂上有一個破洞,承以紙板一方,以防磚瓦灰塵下墜。作者就把它叫作“達摩克利斯頭上的劍”。文學所發布的《汪蔚林同志悼詞》中專門提到:“汪蔚林同志一向生活儉樸,艱苦奮斗,他識大體,顧大局,體諒國家和組織的困難。七二年,文學所從干校回京。他長期身居陋室而無怨言。”“陋室”指的就是這間小屋。“松郊”指勁松地區。汪蔚林先生去世前一年,才遷居勁松地區,這里當時還屬于北京近郊,故云“松郊”。
荒蕪,本名李乃仁,安徽蚌埠人,與汪蔚林先生為安徽老鄉。20世紀30年代畢業于北京大學,參加過“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1949年,擔任外文出版社圖書編輯部副主任。1956年,他進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57年被劃為“右派”,到黑龍江農場勞動改造。1961年又回到文學研究所做資料員。當時,汪蔚林先生為圖書室主任,他倆成為同事。1969年,整個“學部”一起下放到河南信陽羅山“五七干校”。這就是兩首詩所寫的背景。荒蕪先生在中學期間就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創作了很多詩歌。他還翻譯過賽珍珠的小說和惠特曼的詩歌,是著名的文學翻譯家。下放“干校”時,這些文學家常常“牛棚得句共推敲”。悼念汪蔚林先生的詩歌寫好后,荒蕪先生曾請俞平伯先生(1900—1990)指正,于是引來了平伯先生的一段評議:
舊體詩歷千年,敝矣。推陳出新,自是當然,方向正確,不待言。做法不妨各異,古言殊途同歸。今日百花齊放,即如用典,圣陶以為密碼,比喻極佳。我們是欲不用或少用。我近來作詩,用典極少,尤其避僻典。
兄意要用新舊中外之典而多作注,目的同而方法異也。作注,多則妨詩,少則不達,即如此次惠詩有云“長憶達摩克利劍”,雖注明原文,但若不知一發系千鈞之義,仍不能知比喻之妙也。同詩末句“松郊”不醒豁,鄙意不妨逕作“愁聽鄰笛勁松郊”,表詞可省,即可省注。
這里討論的是詩歌用典問題,俞平伯先生主張盡量不用典,荒蕪先生的詩歌喜用新舊中外之典而多作注。譬如“鄰笛”,用的是竹林七賢的“古典”。嵇康被殺后,向秀路過其舊居,聽到鄰人的笛聲,聯想到嵇康當年彈琴之事,于是寫下《思舊賦》,舉目有山河之感。這個典故用的比較貼切,如果不用解釋,也無妨。“達摩克利劍”用的是“洋典”,更多的是用“今典”,盡管非常活潑,但不加注釋,讀者還是不懂。最后一句“愁聽鄰笛過松郊”中的“松郊”二字,俞平伯先生認為比較生硬,不如徑改為“愁聽鄰笛勁松郊”,準確、顯豁,不失典雅。
在文章的最后,俞平伯先生又特別加了一段話:“蔚林遽逝,為之驚惋。猶憶東岳一夕,偕兄同過我茅屋,四人今余其半,而故人千古矣。牛棚陳跡可復道哉。”東岳是指東岳鎮。1970年,文學所和經濟所的“五七干校”就坐落在這里。俞平伯先生的文字,簡短意長,不勝今昔之感。查《俞平伯全集》第十冊所載1983年6月17日《致俞潤民信》:“我有三文寄出:一港《大公報》,二《文匯報》,三廣州《羊城晚報》。”這里提到的給《羊城晚報》文章,就是這篇《致荒蕪》。從書信看,作者的身體狀況非常不好,蕭然寒暑,心緒落寞:“自三日發病后,雖無恙,但對于一切均無甚興味,空空洞洞不想什么。”但汪蔚林先生的去世,還是叫俞平伯先生深感驚惋。
在一般人看來,汪蔚林先生的名氣不大,但是文學所的老人都很感念他。
圖書資料工作的默默耕耘者
在文學所的檔案文件里,簡單地記述了汪蔚林先生早期的工作經歷。
汪蔚林(1912—1983),字履實,原名裕麟,安徽黟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因家境貧寒,他長期為衣食生計奔波,大部分時間從事中小學教學工作。1936年,在全國抗日愛國熱潮的感召下,在生活書店杜重遠同志的支持下,他與幾位朋友在安慶開辦了求知書店,從事抗日愛國的進步宣傳活動。為此,他遭到國民黨特務的迫害,曾被捕入獄。1949年4月參加革命后,他在黟縣教育科工作,同年8月加入民主同盟,后任黟縣中學教導主任、貴池中學教導主任。1951年,他由安徽省民盟送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結業后被分配到馬列學院(中央黨校的前身)任教員。
1952年下半年,馬列學院語文教研組組長何其芳(1912—1977)奉中宣部指示,組建成立文學研究所。他首先召集語文組的著名詩人力揚(1908—1964)、教員汪蔚林以及通訊員馬世龍(現為文學所離休干部)等協助他做籌備工作。范寧(1916—1997)、汪蔚林負責圖書室工作。鄭振鐸、何其芳對于圖書資料建設高度重視。1957年,在鄭振鐸的提議下,文學所成立了圖書資料管理委員會,錢鍾書任主任,范寧、吳曉鈴、汪蔚林等任委員。當時,圖書室和資料室是分開的,圖書室負責圖書的購買、進書、編目和典藏等事宜。資料室負責采集報刊資料,剪裁分類,裝訂成冊。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研究所編輯出版了若干種研究論文索引的工具書,主要依據的就是這些報刊資料。這些資料類編成冊,迄今尚有五六千種,現已做了數字化處理,將來可以發揮更大作用。此后一段時間,圖書室與資料室分分合合,人員變動很大。只有汪蔚林先生一直在圖書資料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年。不僅如此,1981年,《中國文學研究年鑒》創刊,汪蔚林先生還兼管《年鑒》工作,從工作班子的組建、編輯及最后定稿出版,他都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些背景材料,在我主編的《文學研究所所志》一書中有比較詳盡的記載。
很多人認為,從事圖書資料工作既無名又無利,一天到晚鉆到資料堆里,為他人作嫁衣裳,沒有成就感。汪蔚林先生卻不這樣看。1980年,他在中國人民大學主持的全國資料工作科學討論會上做了題為《范例和啟發》的發言,很有針對性。他認為做好資料工作,首先,要認認真真地把它當作一項事業來做,要有一種很強的責任心和事業心,不計較自己的名譽,不計較個人的利益;其次,圖書資料工作者必須端正思想,擺正位置,要有為科研服務的意識。
據老人們回憶,三十年來,汪蔚林先生在工作中事無巨細,一絲不茍,熱心為研究人員的工作提供方便,解答各種參考咨詢問題,因而令人記憶深刻。《王伯祥日記》1955年11月22日有這樣一段記載:“余開各書,蔚林云正力求中,一俟收到,隨即送來也。”可見,汪蔚林先生通常把科研人員需要的圖書親自送到家中。這樣的事例,在文學所的老人中多有傳誦。我在《記憶中的水木清華》一文中提到,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清華大學圖書館也提供這樣的服務,還是讓人羨慕的。
在汪蔚林先生看來,這樣的服務工作理所當然。何其芳先生明確要求他們做好圖書資料工作,必須兼顧科學性、系統性和準確性,尤以準確性最為重要。汪蔚林先生在《范例和啟發》中回憶,何其芳先生在撰寫《論〈紅樓夢〉》這篇長文時,閱讀了大量資料,對清代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和戴震等人的著作做了深入研究。在《論紅樓夢·序》中,何其芳先生曾寫道:“《論〈紅樓夢〉》是我寫議論文字以來準備最久、也寫得最長的一篇。從閱讀材料到寫成論文,約有一年之久。”這篇論文長達十萬字,何其芳先生經常引用到一些經典著作,有時對俄譯本也不輕信,還會找懂德文的同志對譯文進行核校。因為有堅實的資料做支撐,何其芳先生所持的論點基本上是站得住的。汪蔚林先生還舉例說,何其芳先生有一篇論述農民起義歷史背景的文章,說到當時農民的悲慘生活,有這樣一段話:“安寨城西,有一個糞場,每天早晨都有兩三個嬰兒扔在那里。那些嬰兒有的哭,有的叫,有喊父母的,有吃糞土的。”這條材料見于一本有關農民起義的資料書,“糞場”原來作“翼場”。何其芳先生覺得“翼場”不好理解,就和汪蔚林先生討論起來,認為“翼場”如果不是地名,就是有訛誤,叫汪蔚林先生協助找一找原始材料。很快,汪蔚林先生就在《陜西通志》卷八十六查到了馬懋才《備陳災變疏》,改正了“翼場”的錯誤。這是正面的例子,在《范例和啟發》中,汪蔚林先生還舉了一個反面的例子。幾年前,人民文學出版社要出一本《紅樓夢》的資料集,有一份征求意見的選目,讓提意見,他馬上想到一篇發表在50年代《大公報》上論《紅樓夢》四大家族的文章,論點很新。資料來源注明很清楚,有年、有月、有報紙,按理說查找這些資料應該問題不大,但是50年代的《大公報》有好幾個,上海有一個,重慶有一個,漢口有一個,桂林、香港也各有一個,查了數個,都沒有這篇文章。如果當初在那條資料上注明是什么地方的《大公報》,問題就會簡單得多。可見,收集資料不僅要全,更要準確。資料不準,就會給研究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

《中國文學研究年鑒(1981)》《文學研究所所志》
圖書資料工作的科學性和系統性同樣重要。文學所館藏圖書之所以具有今天較為完備的規模和體制,是與汪蔚林先生的努力工作分不開的。從現存文件看,建所之初,文學所圖書室藏書主要由北京大學劃撥一部分副本,數量不多。現存古籍,多數都是多方采購而來的。1954年,鄭振鐸先生促成購買了近代重要藏書家張壽鏞(1875—1945)的約園藏書,約兩千余種。1957年,受所領導委托,錢鍾書先生代表文學所擬函向周恩來總理求助,爭取到一大批價值極高的善本古籍,其中包括2008年《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收錄的幾部珍稀善本。此外,還有一些捐贈的古籍,如王伯祥(1890—1975)先生贈書,現在業已專架庋藏。

《紅樓夢稿》抄本
作為圖書室負責人的汪蔚林先生,他最初的主要工作就是四處搜購古舊書籍,走訪書肆,深入民間,拜訪文人墨客。河北省社科院劉月教授還記得汪蔚林先生曾提及,他去過中國戲曲學校校長蕭長華(1878—1967)家看書,還去過北京師范學院教授王古魯(1901—1958)家買書。文學所圖書館善本書庫確實還保存著一部分王古魯的藏品,主要是戲曲小說善本古籍的攝影復制本,大概是汪蔚林先生從王古魯家征集來的。1958年,吳曉鈴先生介紹了在中國書店看到乾隆時期百廿回《紅樓夢稿》抄本,根據抄本上的“蘭墅閱過”“蘭墅太史手訂紅樓夢”等字樣,當時專家鑒定,確認是程、高在修訂《紅樓夢》過程中的一個稿本,屬楊繼振舊藏本。但之后的研究發現該抄本旁改、貼改和補配部分存在諸多版本問題,遂使該抄本的抄寫時間和底本問題成為長期爭論的焦點,而未有定論。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是目前已知十二個《紅樓夢》脂本中非常重要的抄本,極富價值。當初購回時,這部珍貴的孤本已殘破不堪,沒有目錄,經張中興先生修補裝訂,那延齡先生增寫目錄,呂其桐先生做好函套,至今仍完好地被文學研究所圖書館善本書庫珍藏。
文學所圖書館有很多這樣的古籍,購藏時已有破損,需要經過技術人員的修補才能入藏使用。遺缺的部分,汪蔚林先生還會設法抄配補齊,臻于完璧。例如,彈詞寶卷是文學所圖書館的特藏之一。1957年,汪蔚林先生在上海溫智書店購得清光緒年間的《荷花寶卷》,同年在杭州和合橋東首文藝齋購得清光緒甲午年間的《繡像韓湘寶卷》。1958年,他又在溫州古舊書店購得清光緒三十年“溫州府前街墨香簃發行”的《升仙寶卷》等,都是比較珍貴的本子。迄今為止,文學所共收藏了六百多種彈詞寶卷,其中不乏珍稀善本,甚至孤本。譬如明萬歷年間的刻本《破邪顯證鑰匙寶卷》和康熙年間的抄本《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寶卷》等,都曾經歷了三四百年的滄桑,彌足珍貴。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古籍善本書目》

文學所圖書館成為國務院頒布的首批51 家“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之一
到1964年,文學研究所圖書館的藏書已達二十四萬冊。其中善本書就有近三千種,兩萬多冊,孤本有三十種以上。根據當時的藏書情況,汪蔚林和趙桂藩兩位先生編輯了《文學研究所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1978年,“全國善本書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會議決定編輯《全國善本書聯合書目》(后更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汪蔚林先生代表文學研究所參加了會議,文學所因此成為了《全國善本書聯合書目》的合作單位之一。經過四年的時間,《聯合書目》編成初稿。在此工作基礎上,1993年圖書資料室又編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古籍善本書目》,這是對汪蔚林先生和所有為文學所藏書作出貢獻的同志們的一份紀念和志謝。

宋刻本《五代史記》(宋歐陽修撰)

葉夢得:《石林奏議》十五卷(明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
據統計,文學所圖書館收藏普通古籍一萬三千余種,善本古籍四千余種,合計十三萬余冊。其中以明清詩文集、古典戲曲、古代小說為館藏的三大支柱。詩文集方面,如陶淵明詩文集就有六十多種(其中善本四十余種),明代詩文集一千多種(其中善本六百多種),清人詩文集三千多種(其中善本五百多種),晚清及民國初年詩文集一千多種。館藏戲曲小說六百多種,其中孤本三十多種,如《鎖海春秋》《五更風》《美人書》《蕉葉帕》《鳳凰池》《集詠樓》《閃電窗》等。此外,文學所館藏中還有大量不被人注意的晚清警世小說、社會小說。五四運動前后及“左聯”、抗戰時期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出版物也是文學所圖書館收藏的重要文獻。如魯迅、周作人、沈從文、郭沫若等著名作家的早期印本就多達四百余種,其中善本一百多種。

1.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四十二卷(錢曾藏宋寶祐年刊本)(局部)

2.朱熹:《資治通鑒綱目》五十九卷 (宋刻元修本)(局部)

3.《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元刻本)(局部)

4.《莊子內篇》不分卷(明王寵手書抄本)(局部)
從版本方面看,宋元版書十四種,如宋刻本《五代史記》(宋歐陽修撰)、元延祐間刻本《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宋黃履翁撰),明刊本兩千一百多種,其中一百多種為清代禁書,鈔本三百余種,稿本一百多種,另有稀見明版家譜數種。2008年3月,文學所圖書館成為國務院頒布的首批51 家“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之一,有6 部館藏古籍入選第一批、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包括《莊子內篇》不分卷(明王寵手書抄本)、葉夢得《石林奏議》十五卷(明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袁樞撰《通鑒紀事本末》四十二卷(錢曾舊藏的宋寶祐年刊本)、鄭樵《通志》二百卷(元大德三山郡庠元明遞修本)、朱熹《資治通鑒綱目》五十九卷(宋刻元修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元刻本)等。這些善本古籍非常珍貴,就是放在國家圖書館,也是一級文物。
上述這些圖書收藏,均凝聚了汪蔚林先生的心血。可以說,他把自己大半生的時間和精力都撲在文學所的圖書資料工作上,并以自己的工作成果有力地支持了文學所的科研工作。
“聽君續話孔東塘”
和文學所那些大家、名家相比,汪蔚林先生沒有名牌學校文憑,沒有顯赫的家世和光輝的經歷,但是他的學問、他的工作、他的成績得到全所領導、專家、同事的認可。他是熟悉圖書工作的專家,學有專長。《王伯祥日記》1965年1月19日有《致吳曉鈴書》,作者寫道:“《西諦書跋》……汪蔚林先生所簽各條皆精確,似可照改,其所提總意見一紙,鄙見亦復從同。”學問淵博的王伯祥先生說汪蔚林先生的意見“各條皆精確”,這樣的評價是很高的。汪蔚林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潛心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對吳敬梓、孔尚任、曹雪芹等都有專門研究,并發表過論文。《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五輯刊發的《紅樓書話》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汪蔚林先生原打算在離休之后全力以赴參與編輯《古本戲曲叢刊》《古本小說叢刊》的工作。隨著他的遽然離去,他本人未能如愿參與這項工作,不無遺憾。可以告慰汪蔚林先生及其他文學所前輩的是,文學所同仁并未放棄理想,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并充分利用了文學所的珍貴藏書,最終完成并出版了這兩套卷帙浩繁的叢書。

《紅樓夢研究集刊》

汪蔚林輯校:《孔尚任詩》《孔尚任詩文集》
汪蔚林先生的孔尚任詩文研究在當時居于學界前列。1958年10月,汪蔚林先生輯校的《孔尚任詩》被列為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資料叢刊”第二種,由科學出版社出版(2006年又列入文學研究所學術叢書第一輯,交由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1962年,中華書局又出版汪蔚林先生修訂的《孔尚任詩文集》,增加了散文部分,并補入不少新的資料。在當時,這是一部比較完備的孔尚任詩文集。
當然,學術研究永無止境。新的資料不斷涌現,新的問題也不斷地被提出來。劉輝等先生從張潮《友聲初集》等書札中就發現了若干孔尚任集未收的佚文,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我初到清華大學任教時,在圖書館里讀過一本清鈔《滄浪唫》,卷首有孔尚任序,汪蔚林先生編《孔尚任詩文集》未曾輯入。后來看到徐振貴先生主編的《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齊魯書社2004年版),也沒有收錄。出現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或是未見,或是認為不可靠。《〈滄浪唫〉序》如下:
舟來維揚,兩寓蕭寺。言詩之客,常滿于座。所謂舊游者百不一存矣。天寧方犬,鐘版屢更,偶赴主僧之齋,邂逅靜庵劉公,知為內府近臣,欽其豐范,遂與久談,和平溫厚,頗露風人之趣。兩次過從,漸窺蘊抱。頃于幾案間得鈔稿一卷,則公南來游吳之作,袖歸細讀,知公于此道精熟已久。凡登山臨水,過都歷市,遇其境之士女,交其邦之逸老大夫,莫不抒寫贈答,信口披胸,如其景,如其事,如其人,詞達理暢,令人玩味吟誦,有無窮之意。古人詩歌,被于樂懸,朱弦?越,一唱三嘆有遺音者,不仿佛近是乎?蓋公侍從內廷,常居清穆高華之所,賡歌元音,鈞天雅奏,觸于耳而會于性,不待習學,較之隱流學士,已高數等,況其心虛氣下,每不自信,常就予詢四始之源流,究三唐之變遷,偶得于心,即書紳不忘。杜子美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從此引而伸之,更入妙詣,無俟予津津推許,當有自信之名矣。
康熙乙未孟夏曲阜弟孔尚任撰于維揚客舍。
康熙乙未為康熙五十四年(1715),孔尚任67 歲。序文“玄”字闕筆。下有朱文、白文印各一方,分別為“孔尚任印”和“東塘”。卷首署:“靜庵劉士瑤英石氏著,闕里孔尚任東塘父閱。”序中提到的“蕭寺”“天寧寺”等時常見諸孔尚任的筆端。提及蕭寺的,如《答何蜀山》:“足下作士不第,作吏不終,落魄揚州蕭寺,遇亦窮甚。”《與朱天錦》:“別來移居蕭寺,吟詩送老。”《答黃仙裳》:“別來仍居蕭寺,以餓腹而陪閑話之賓,空囊而養久居之眾。”《答汪柱東》:“蕭寺雪夜,共話窮愁。”論及天寧寺,如《與蔣玉淵》:“天寧寺內,僧居也;寺外,丐居也。我兩人寓館,處僧丐之間,其孤寂饑寒相似者,居相似也。”《與黃仙裳》:“仆在天寧寺,忍饑抱病,千愁萬苦,皆于兩月內包之。”可見這兩個地方,給孔尚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滄浪唫》收錄了好幾首作者與孔尚任的唱和之作,如《贈別孔東塘先生》《送孔東塘登舟約于淮陰再會》《送東塘先生歸石門》等,多是孔尚任辭別揚淮回到故鄉曲阜時,該書作者所寫的送別之作。石門,是曲阜附近的名山,孔尚任有《游石門山記》記之,傳為佳作。這個抄本除《滄浪唫》外,還有《竹西唫》《魯游紀事草》等。卷尾分別有“仝里嚴錫璋僣評”及“康熙庚子中秋后二日夏邑曹裕嗣敬跋”。康熙庚子為康熙五十九年,即公元1720年。其時,孔尚任已去世兩年。因此,這兩則題跋可以暫且按下不表,還是回到孔尚任的序文上。
徐振貴先生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所附《孔尚任年表》,從康熙五十一年(1712)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孔尚任去世,前后七年,完全空白。其實這幾年,孔尚任的行跡還是可以推知一二的。《長留集序》說“甲午臘月,薄游江南,舟維袁浦,遇先生為淮、徐觀察”,云云。這里交代得很清楚,康熙五十三年(1714)甲午臘月,孔尚任泛舟南下,在淮南與劉廷璣等多有交往,并在淮南過冬,直到初春,羈留時間長達三個月之久。在這期間,兩人商議盡搜時賢詩稿,用存真詩。他們先從自選作品開始,分別編成《長留集》和《在園雜志》,孔尚任還為這兩部集子各寫了一篇序言。《長留集》題下有“孔劉合刻”四字,作者題署:“曲阜孔尚任東塘著,遼海劉廷璣在園選。”《長留集》序言的落款為“康熙乙未仲春曲阜弟孔尚任撰于袁浦之云跡館”,《在園雜志》序言落款為“康熙乙未初春,云亭山人孔尚任撰”,兩序都作于康熙乙未春,《在園雜志》序在初春,《長留集》序在仲春。有意思的是,《滄浪唫序》也作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只不過作于孟夏。這三篇序言的寫作時間正好可以銜接起來。據此推測,作者編好《長留集》后又有一次南游,或者根本就沒有回到家鄉,而是從淮南直接到了揚州,并與當地文人唱和。孔尚任有很多作品描寫到江淮湖海的風土人情,他甚至說“生平知己,半在維揚”(《答張諧石》)。即便是在六十七、八歲的高齡,依然游走于曲阜、淮南和揚州等地,可謂流連忘返。
孔尚任晚年雖罷官在家,仍不時登山臨水,訪親拜友。對他來講,這既是一種慰藉,也是寫詩的需要。他在《酣漁詩序》中說:“求友之道多端,惟詩為最近。詩也者,性情之音,唱予和汝,而性情各見。”他在很多詩文中都談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對于詩人創作的重要性。這篇《滄浪唫序》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他說,靜庵劉公“凡登山臨水,過都歷市,遇其境之士女,交其邦之逸老大夫,莫不抒寫贈答,信口披胸,如其景,如其事,如其人,詞達理暢,令人玩味吟誦,有無窮之意”。如果序文可靠,這兩條淮南、揚州之行的材料是可以補充到《孔尚任年表》中的。
我到文學所工作時,汪蔚林先生已經去世多年,無從求教有關東塘的故事。為了求證這篇序文的真偽,我曾抄錄給專家學者,請他們指點迷津,可惜至今也沒有得到答復。歲月不居,一晃四十年過去了,我的學業沒有多少進步,對于孔尚任這篇序文的真偽和價值還是不能甄別論析,只好借此機會,再次過錄如上,以就教于專門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