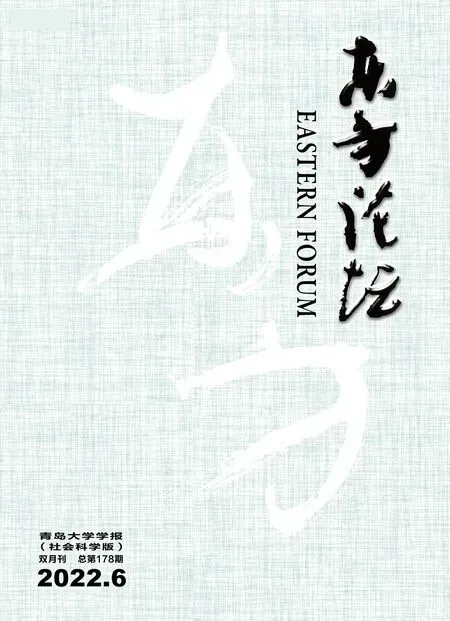論夏目漱石《心》中K的“自我本位”
梁 懿 文
山東大學(xué) 東北亞學(xué)院,山東 威海264209
一、夏目漱石的“自我本位”思想
生于明治維新前一年的夏目漱石,受時(shí)代的影響,一直懷有“立身出世”的信念。在《處女作追懷談》中,夏目漱石曾寫(xiě)道,“我既然生于此世,就必須有所作為”①[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三十四卷』,東京:巖波書(shū)店,1957年,第162頁(yè)。。1914年11月25日,夏目漱石在學(xué)習(xí)院輔仁會(huì)上做了題為《我的個(gè)人主義》的演講。在演講中,夏目漱石談到他“自我本位”思想產(chǎn)生的起源。夏目漱石曾在東京帝國(guó)大學(xué)文科大學(xué)的英國(guó)文學(xué)專業(yè)學(xué)習(xí)了三年,可是對(duì)英國(guó)文學(xué)卻不得其解,關(guān)于“文學(xué)是什么”這一問(wèn)題也找不到答案,這是他煩悶和不安的根源。“我懷抱著這種不安從大學(xué)畢了業(yè),又帶著同樣的不安從松山到了熊本,又把同樣的不安埋藏于心底遠(yuǎn)渡重洋。”②[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二十一卷』,東京:巖波書(shū)店,1957年,第138頁(yè)。1890年夏目漱石進(jìn)入東京帝國(guó)大學(xué)文科大學(xué)英文科,1893年從英文科畢業(yè),1895年赴愛(ài)媛縣尋常中學(xué)校任教,1896年輾轉(zhuǎn)去熊本第五高等學(xué)校執(zhí)教,1900年奉命去英國(guó)倫敦留學(xué)。在這期間,同樣的煩悶和不安始終縈繞心間,使他常感內(nèi)心空虛。留學(xué)期間,他在倫敦的住所冥思苦想,發(fā)覺(jué)自己不論讀多少書(shū),也無(wú)法填滿腹中空虛,甚至對(duì)自己讀書(shū)的意義也開(kāi)始感到困惑。他突然醒悟:“除了從根本上憑借自己的力量構(gòu)建起關(guān)于‘文學(xué)是什么’的概念,我別無(wú)救贖之途。我漸漸意識(shí)到,正因?yàn)槠駷橹沟奈彝耆撬吮疚坏模缤瑹o(wú)根浮萍一般,不著邊際地漂來(lái)漂去,所以才貽誤至今,無(wú)所建樹(shù)。我在這里說(shuō)的他人本位,指的是模仿他人的行為,是讓別人替自己飲酒嘗味,聽(tīng)其品評(píng)后不假思索地全盤(pán)接收。……比如,當(dāng)我讀到一個(gè)西洋人評(píng)價(jià)另一個(gè)西洋人的作品時(shí),完全不去思考其評(píng)價(jià)恰當(dāng)與否,自己是否能夠信服,而輕率地散布其言論。換句話說(shuō),說(shuō)是囫圇吞棗也好,生搬硬套也罷,到底不是我自身的血肉,只是將陌生的東西當(dāng)作自己的所有物一樣到處宣揚(yáng)。但時(shí)代如此,人們會(huì)贊賞這種行為。然而,無(wú)論怎么被人贊賞,終究是穿著借來(lái)的衣裳裝自己的威風(fēng),內(nèi)心不得安寧。因?yàn)檫@就如同毫無(wú)抵抗地把孔雀的羽翅插在自己的身上逞威風(fēng)一樣。我開(kāi)始意識(shí)到,如果不下一番‘去浮華,就摯實(shí)’的功夫,自己永遠(yuǎn)不會(huì)感到安心。比如,即便西洋人說(shuō)‘這是很優(yōu)秀的詩(shī)作’,‘語(yǔ)調(diào)非常優(yōu)美’,那也是西洋人的意見(jiàn),雖然未必不能成為我的參考,但如果我不是真心那樣認(rèn)為,終究不應(yīng)對(duì)其觀點(diǎn)現(xiàn)學(xué)現(xiàn)賣。既然我是一個(gè)獨(dú)立的日本人,決不是英國(guó)人的奴婢,那么作為國(guó)民的一員,必須得有這點(diǎn)見(jiàn)識(shí)。再者,從重視世界共通的正直之德義這一點(diǎn)來(lái)看,我也決不能違心歪曲我的意見(jiàn)。”①[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39—140頁(yè)。
夏目漱石在這里闡述的“自我本位”包含了個(gè)人和國(guó)家兩層含義。
首先,“自我本位”體現(xiàn)了夏目漱石對(duì)自身人生意義與價(jià)值的思考。在這個(gè)意義上,“自我本位”意味著完全依靠一己之經(jīng)驗(yàn)與意志決定自身道路。結(jié)合夏目漱石自身的經(jīng)歷來(lái)看,他自幼愛(ài)喜漢學(xué),他曾說(shuō)“余兒時(shí)誦唐宋數(shù)千言喜作為文章”②[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二十三卷』,東京:巖波書(shū)店,1957年,第25頁(yè)。。他11歲時(shí),便用漢文寫(xiě)下了歌頌楠木正成忠誠(chéng)勤王的《正成論》,發(fā)表在《回覽》雜志上。14歲時(shí),從東京府立第一中學(xué)退學(xué)進(jìn)入專門(mén)教授漢學(xué)的二松學(xué)舍,專心研學(xué)漢學(xué)。在二松學(xué)舍學(xué)習(xí)漢學(xué)的經(jīng)歷,鞏固了他的漢學(xué)基礎(chǔ),并形成了他的文學(xué)觀。他在《文學(xué)論·序》中這樣寫(xiě)道:“我少時(shí)好讀漢籍,學(xué)時(shí)雖短,但于冥冥之中也從‘左國(guó)史漢’里隱約感悟出了文學(xué)究竟是什么。我曾以為英國(guó)文學(xué)亦應(yīng)如此。若果真如此,我將義無(wú)反顧地終生學(xué)習(xí)文學(xué)。……我在漢學(xué)方面雖然并沒(méi)有那么深厚的根底,但自信能夠充分玩味。”③[日]夏目漱石:《文學(xué)論》,王向遠(yuǎn)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4頁(yè)。他由衷地感受到漢文學(xué)的魅力,并且從中受到啟發(fā),產(chǎn)生了創(chuàng)作的欲望。“十五六歲時(shí),我讀了漢籍和小說(shuō),對(duì)文學(xué)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產(chǎn)生了自己也想寫(xiě)點(diǎn)什么的想法。”④[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三十四卷』,第163頁(yè)。因此,對(duì)于漢文學(xué)之于夏目漱石的根本性的意義,學(xué)界基本形成共識(shí)。如李光貞認(rèn)為:“夏目漱石自小深受漢文學(xué)的熏陶,有雄厚的漢學(xué)基礎(chǔ),雖然他大學(xué)里學(xué)的是英語(yǔ),又有過(guò)留學(xué)英國(guó)的經(jīng)歷,但都沒(méi)有動(dòng)搖過(guò)他的根基。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是把他引上文學(xué)之路的最初最根本磁場(chǎng)。”⑤李光貞:《夏目漱石與漢文學(xué)》,《聊城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5年第6期。王勇萍、趙驕陽(yáng)認(rèn)為:夏目漱石身上有一種由漢學(xué)構(gòu)筑而成的文化自信,“作家窮其一生所追求與執(zhí)著的‘自我本位’文化觀蘊(yùn)藏的是‘漱石’這一名號(hào)所強(qiáng)調(diào)的不畏強(qiáng)權(quán)、不流于世俗、堅(jiān)持自我的精神品質(zhì),體現(xiàn)了作家對(duì)‘漱石’文化意象的深刻理解與認(rèn)同,彰顯的是作家由漢學(xué)構(gòu)筑而成的文化自信”⑥王勇萍、趙驕陽(yáng):《由漢學(xué)構(gòu)筑而成的文化自信——“漱石”名考及“自我本位”文化觀》,《東北亞外語(yǔ)研究》2018年第4期。。但是,在明治日本“脫亞入歐”“文明開(kāi)化”的大背景影響下,夏目漱石還是決定改變初衷,選擇英國(guó)文學(xué)。立志要“通達(dá)英語(yǔ)英文,以外語(yǔ)著述偉大之文學(xué),以震驚西洋人”①[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三十四卷』,第165頁(yè)。。“我在英語(yǔ)知識(shí)方面雖然不能夠說(shuō)深厚,但自認(rèn)為不劣于漢學(xué)。學(xué)習(xí)用功程度大致同等,而好惡的差別卻如此之大,不能不歸于兩者的性質(zhì)不同。換言之,漢學(xué)中的所謂文學(xué)與英語(yǔ)中的所謂文學(xué),最終是不能歸為同一定義之下的不同種類的東西。”②[日]夏目漱石:《文學(xué)論》,王向遠(yuǎn)譯,第5頁(yè)。通過(guò)學(xué)習(xí)英國(guó)文學(xué),他認(rèn)識(shí)到英國(guó)文學(xué)具有的與漢文學(xué)不同的異質(zhì)性,這種異質(zhì)性的發(fā)現(xiàn)開(kāi)闊了他的視野,但也質(zhì)疑了他通過(guò)漢文學(xué)得出的關(guān)于“文學(xué)是什么”的定義,驅(qū)使他憑借“自我本位”的進(jìn)一步努力,親自解答出“文學(xué)是什么”這一重要課題。可見(jiàn),在進(jìn)入一高之前,夏目漱石拋棄鐘愛(ài)的漢文學(xué)、選擇英國(guó)文學(xué)專業(yè),作此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跟風(fēng)。然而結(jié)果卻是他連自己所學(xué)的英國(guó)文學(xué)究竟是什么都不甚明了。“既然自己連自己所學(xué)的英國(guó)文學(xué)專業(yè)究竟是什么都弄不清楚,那就不可能真心認(rèn)同這門(mén)學(xué)問(wèn)的價(jià)值,將其作為值得奉獻(xiàn)一生精力的事業(yè)了。這就不難理解他此后為何認(rèn)定,在選擇自身道路時(shí)絕不應(yīng)受社會(huì)潮流與他人觀念束縛了。”③彌生屋:《夏目漱石〈我的個(gè)人主義〉譯稿(一):煩悶和個(gè)人主義之起源》,2022年3月25日,https://mp.weixin.qq.com/s/5JV_WC2vhDtxJzGx96aUiQ.
其次,“自我本位”中包含著作為日本人的夏目漱石對(duì)西洋復(fù)雜扭曲的感情。在這層含義上,“自我本位”意味著對(duì)日本文化不同于西洋文明的獨(dú)特價(jià)值的宣示。對(duì)夏目漱石來(lái)講,他一生與“明治日本”密不可分。他于明治維新前一年的1867年出生,曾言“在和明治維新同時(shí)出生的我看來(lái),明治的歷史即是我的歷史”④[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二十卷』,東京:巖波書(shū)店,1957年,第232頁(yè)。。英國(guó)自18 世紀(jì)60 年代開(kāi)始了工業(yè)革命,在19 世紀(jì)40 年代前后,工業(yè)革命基本完成。夏目漱石赴英國(guó)倫敦留學(xué)是在世紀(jì)之交的1900年,此時(shí)英國(guó)工業(yè)革命已經(jīng)完成了約60年,西洋文明在物質(zhì)和精神層面繁榮鼎盛的局面,使他感受到了西洋文明對(duì)日本社會(huì)的全方位碾壓。他處處發(fā)現(xiàn)有時(shí)也過(guò)度解讀了歐洲人對(duì)日本人的歧視和敵意,從而受到劇烈的精神刺激,在深感自卑之余,“開(kāi)始尋求建立日本文明獨(dú)特價(jià)值的論說(shuō),試圖以此重建自己的身份認(rèn)同與自信心”⑤彌生屋:《夏目漱石〈我的個(gè)人主義〉譯稿(一):煩悶和個(gè)人主義之起源》,2022年3月25日,https://mp.weixin.qq.com/s/5JV_WC2vhDtxJzGx96aUiQ.。
二、K “自我本位”的生存方式
夏目漱石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心》中的一位主人公K,其“養(yǎng)子”的身份帶上了夏目漱石本人的影子。他的“求道”行為,也體現(xiàn)了夏目漱石以一己之經(jīng)驗(yàn)與意志決定自身進(jìn)路的“自我本位”思想。
(一)K的身世:對(duì)家督制度下“養(yǎng)子”命運(yùn)的抗?fàn)?/h3>
李卓關(guān)于中日家族倫理的比較研究顯示:受儒家“均平”觀念影響,中國(guó)歷史上的財(cái)產(chǎn)繼承制度遵循諸子析產(chǎn)的原則,保證了同胞兄弟在家中地位的平等。而在日本,由于祖孫一體、家族永續(xù)是日本人家族觀念的核心內(nèi)容,家督繼承制是實(shí)現(xiàn)這個(gè)目的的具體保證,在數(shù)個(gè)子女當(dāng)中,只能由長(zhǎng)子繼承家業(yè)與家產(chǎn),繼承人之外的人自出生之日起便被入了另冊(cè)。同胞兄弟之間存在明顯的上下尊卑之別乃至主從之別,家中的所有不平等便因此而起源。長(zhǎng)子和非長(zhǎng)子在家中的待遇和經(jīng)濟(jì)地位截然不同。家族成員之間的不平等,從根本上決定了家族成員不同的生活道路。殘酷的命運(yùn)迫使那些無(wú)緣繼承家業(yè)的次子、三子們不得不在以下出路中作出選擇:第一,終身不娶,寄長(zhǎng)子及其后繼者籬下,如下人一般苦度人生。第二,外出當(dāng)雇工、當(dāng)傭人,江戶時(shí)代町人和商家的“奉公人”大多數(shù)都是農(nóng)家的次子、三子。第三,給別人家當(dāng)養(yǎng)子①李卓:《“儒教國(guó)家”日本的實(shí)像》,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第252—253頁(yè)。。
《心》中的K身為次子,自出生之日起,他的人生道路就被限定在以上三種情況之內(nèi)。而他的父親為他選擇了第三種——給別人家當(dāng)養(yǎng)子。家督制度在日本經(jīng)歷了一個(gè)過(guò)程,14世紀(jì)中后期,日本家族制度中長(zhǎng)子的家產(chǎn)繼承權(quán)及其統(tǒng)率庶子的家長(zhǎng)權(quán)合為一體,各地相繼確立了家督制。財(cái)產(chǎn)單獨(dú)繼承以及家督制的確立,迫使長(zhǎng)子之外的諸子不得不尋找新的求生之路,他們就成了養(yǎng)子的后備軍②官文娜:《日本歷史上的養(yǎng)子制及其文化特征》,《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正如有的學(xué)者所說(shuō),中世紀(jì)以來(lái)的養(yǎng)子制度成了一個(gè)一個(gè)家庭“兒子再分配”的戰(zhàn)略手段,也是整個(gè)社會(huì)“人的資源的再分配”的戰(zhàn)略手段③[日]黑須里美、落合惠美子:《人口學(xué)的制約和養(yǎng)子——幕末維新期多摩農(nóng)村中的繼承戰(zhàn)略》,見(jiàn)速水融編:《近代移行期的家族和歷史》,京都:米內(nèi)路巴書(shū)房,2002年,第129頁(yè)。。既然如此,那么“養(yǎng)子”就是“兒子再分配”戰(zhàn)略中的棋子,是“工具人”,被剝奪了憑自己意志主宰自身命運(yùn)的可能性。
K是新瀉地區(qū)本愿寺派的真宗和尚之子,但不是長(zhǎng)子,而是次子,因而K被送給一個(gè)醫(yī)生家當(dāng)養(yǎng)子。原本K的生父家里比較富裕,父親卻將他送給別人當(dāng)養(yǎng)子,說(shuō)明將次子送作養(yǎng)子與家庭經(jīng)濟(jì)條件關(guān)系不大,更多的是源于一種思想觀念。K的生父是僧侶,“但在講究義理這點(diǎn)上,可能更近乎武士”④[日]夏目漱石:《心》,林少華注譯,北京:中國(guó)宇航出版社,2013年,第494頁(yè)。。武士般的道德感決定了他在面對(duì)兒子“背叛”時(shí)的絕決態(tài)度,他以“勘當(dāng)”(斷絕父子關(guān)系,逐出家門(mén))這種懲罰作為事情的解決方式。父親是封建社會(huì)武士道德的捍衛(wèi)者,兒子“自我本位”的行為構(gòu)成了對(duì)傳統(tǒng)道德的違逆和反抗,是破壞“秩序”的行為。K被過(guò)繼給醫(yī)生當(dāng)養(yǎng)子這一事實(shí),是在生父和養(yǎng)父之間達(dá)成默契的前提下成立的,即K要給醫(yī)生繼承家業(yè)。這一默契無(wú)視了K作為一個(gè)獨(dú)立個(gè)體的意志,是由父輩安排兒子的命運(yùn)。而K作為一名近代青年,已經(jīng)受到“自由、獨(dú)立、平等”等思想的熏陶,其自我意志已經(jīng)覺(jué)醒,不再接受被安排的命運(yùn)。
(二)K的“自我本位”:積極面和消極面的復(fù)合體
夏目漱石提倡“自我本位”,本意是反對(duì)盲從和模仿西方,強(qiáng)調(diào)自身的主體性。然而因“自我本位”這一詞語(yǔ)語(yǔ)義的模糊性,使其同時(shí)含有積極和消極兩方面含義。積極方面,它意味著獨(dú)立、自主、個(gè)性、自尊;消極方面,則是狹隘、自利、自閉、脆弱。作為踐行“自我本位”的先驅(qū)者,“自我本位”這個(gè)詞所代表的積極和消極兩方面,在K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xiàn)。最終,在近代日本的社會(huì)條件下,“自我本位”的消極方面占了上風(fēng),無(wú)法通過(guò)獨(dú)立、自主來(lái)實(shí)現(xiàn)個(gè)性、獲得自尊的K,陷入自閉和自利,終于只有自決了之。
1.K的自主與精進(jìn)。“出生于寺院的他經(jīng)常使用‘精進(jìn)’一詞。在我眼里,他的所有舉動(dòng)行為均可以此‘精進(jìn)’來(lái)形容。我在內(nèi)心常對(duì)K懷有敬畏之感。K念初中時(shí)就曾用宗教或者哲學(xué)等復(fù)雜問(wèn)題把我難倒。不知是他父親的感化,抑或是其生身之家即寺院那種特殊場(chǎng)所特有的氣氛的影響使然。總之,看上去他遠(yuǎn)比一般僧人還具有僧人氣質(zhì)。”①[日]夏目漱石:《心》,林少華注譯,第491頁(yè)。本來(lái)養(yǎng)父母送其來(lái)東京是想把他培養(yǎng)成醫(yī)生,開(kāi)業(yè)醫(yī)生這一職業(yè)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它意味著優(yōu)渥的物質(zhì)條件和受人尊敬的社會(huì)地位。然而K決意不當(dāng)醫(yī)生,背著養(yǎng)父母私自改了專業(yè),并說(shuō)為道之故,這點(diǎn)欺騙并無(wú)不可。K的住處有《圣經(jīng)》,“先生”問(wèn)個(gè)中緣故,K說(shuō)無(wú)緣無(wú)故,只因《圣經(jīng)》難得可貴,看一看理所當(dāng)然。他對(duì)《古蘭經(jīng)》也有閱讀興趣。大一的暑假K沒(méi)有返鄉(xiāng),而是在一座寺院租了一間屋子學(xué)習(xí)。他的房間很狹小,然而他卻不以為意,反而很高興自己可以在此處盡情學(xué)習(xí)。他的生活逐漸僧人化,手腕掛著一串念珠,一天數(shù)好幾遍。“穿成一串的東西一顆顆數(shù)下去,任憑數(shù)到哪里都數(shù)不完。K將以怎樣的心情在什么地方停下手呢?”②[日]夏目漱石:《心》,林少華注譯,第492頁(yè)。K陷入無(wú)限的自我問(wèn)答的循環(huán)當(dāng)中。水川隆夫評(píng)價(jià):“從K的這種姿態(tài)中,可以看到他真摯的精進(jìn)及其對(duì)于人格完成的焦躁感。”③[日]水川隆夫:『夏目漱石「こゝろ」を読みなおす』,東京:平凡社,2005年,第130頁(yè)。K精進(jìn)的心情得到充分的描寫(xiě),然而K精進(jìn)的目的卻不甚明確。“無(wú)緣無(wú)故”“因?yàn)殡y得可貴所以看一看”等說(shuō)法,反映出K并沒(méi)有明確的學(xué)習(xí)目標(biāo),進(jìn)而言之,他沒(méi)有明確的人生目標(biāo)。即便他能夠在自己所選擇的專業(yè)順利畢業(yè),也沒(méi)有回到家中寺院去繼承家業(yè)的機(jī)會(huì),而K也并無(wú)這一打算。醫(yī)生將其收為養(yǎng)子,供其在東京的大學(xué)學(xué)醫(yī),是為繼承自己的家業(yè)考慮。然而在K的身上,“己”和“家”的沖突無(wú)法調(diào)和,他更加重視自己的意愿,強(qiáng)烈的自我意識(shí)使他反抗了這種既定的命運(yùn)安排。K希望憑借自己的意志決定自身命運(yùn),他的所為符合夏目漱石“自我本位”的主張。然而他的決定是非現(xiàn)實(shí)的,是由一種內(nèi)在的非理性的宗教熱忱支配的,這也為他后來(lái)無(wú)法實(shí)現(xiàn)“自我本位”埋下了伏筆。“他說(shuō)他的第一信條是應(yīng)該為道而犧牲一切。節(jié)欲、禁欲自不消說(shuō),即使離開(kāi)欲的愛(ài)本身也是道之障礙。”④[日]夏目漱石:《心》,林少華注譯,第526頁(yè)。“他有個(gè)壞毛病:動(dòng)不動(dòng)就想把精神和肉體割裂開(kāi)來(lái)。甚至可能覺(jué)得越是鞭打肉體,靈魂才越放光輝。”⑤[日]夏目漱石:《心》,林少華注譯,第498頁(yè)。小森陽(yáng)一指出:一心追求“道”,有“將精神和肉體割裂開(kāi)來(lái)的毛病”的K,其身上殘留的,只有“被肉體的神秘性持續(xù)威脅著的、作為‘頭腦’的‘心’=精神”。在這個(gè)意義上,“‘精神上沒(méi)有上進(jìn)心的人是渣滓’這句話,具有剝奪K生存價(jià)值的力量。這句話,講述了希望解釋人的本源的存在方式、被從身體分離出去的精神的悲劇”⑥[日]小森陽(yáng)一:「こころ」を生成する「心臓(ハート)」,『成城國(guó)文學(xué)』1985年,第51頁(yè)。。
眾所周知,《小倉(cāng)百人一首》和歌集是由生活于日本平安時(shí)代末期、鐮倉(cāng)時(shí)代初期的著名歌人藤原定家精心編撰而成的, 選取飛鳥(niǎo)時(shí)代至鐮倉(cāng)時(shí)代百位歌人每人一首代表作,是日本最廣為流傳的和歌選集。到了江戶時(shí)代,還被制成了紙牌,開(kāi)始在民間流傳,特別是作為新年的游戲而受到人們的歡迎。而K對(duì)百人一首“不大清楚”⑦[日]夏目漱石:《心》,林少華注譯,第516頁(yè)。,對(duì)和歌紙牌游戲也不熟悉,卻對(duì)《圣經(jīng)》《古蘭經(jīng)》、伊曼紐·斯威登堡的思想著迷,說(shuō)明世俗大眾公認(rèn)的文化價(jià)值在K的心中并不具有重要性,他要靠一己之力獨(dú)自開(kāi)辟價(jià)值領(lǐng)域。“先生”和K是“什么都談得來(lái)的”,然而兩人的話題“大多情況下談的都是書(shū)、學(xué)問(wèn)、未來(lái)事業(yè)、抱負(fù)、修養(yǎng)之類”,“兩人只是拘拘板板地親密而已”①[日]夏目漱石:《心》,林少華注譯,第506頁(yè)。,兩人間的友情是“以學(xué)識(shí)交流為基調(diào)”的,K的身上缺少一種平常的生活氣息,用“先生”的話來(lái)形容就是“不像普通人”②[日]夏目漱石:《心》,林少華注譯,第510頁(yè)。。
2.K的自閉與自利。K沉默寡言,獨(dú)來(lái)獨(dú)往,過(guò)著閉塞的生活,除了“先生”,一個(gè)朋友都沒(méi)有。熊野敦子曾指出:“‘自我本位’是一個(gè)充滿豐富個(gè)性的自主自立的世界,在日本的場(chǎng)合,伴隨著陷入狹隘、利己、自閉,招致‘外發(fā)的’脆弱的危懼。至于基于個(gè)性的自尊這一意義層面的‘自我本位’,漱石雖視其為內(nèi)在的必然,然而漱石探求思索近代的路程,注定要經(jīng)歷很多的曲折。”③[日]熊坂敦子:「反近代·日本の漱石」,『國(guó)文學(xué) 解釈と鑑賞 夏目漱石の軌跡』,東京:至文堂,1975年,第27頁(yè)。K是在“先生”租住的軍人遺孀的家里自盡的。對(duì)此,鶴田欣也指出K感受性的欠缺,“如果希望以死來(lái)解決自身的問(wèn)題,那么像‘先生’后來(lái)所做的那樣,在誰(shuí)也不知道的情況下離開(kāi)家去做就好了。如此一來(lái)既不會(huì)給身邊的人添麻煩,也可以達(dá)成自己的愿望。要么,是因?yàn)镵的性格只關(guān)注自己,不僅無(wú)法關(guān)照到‘先生’,連自己的自殺給夫人帶來(lái)的麻煩都不曾考慮。要么,是K故意為之。如果是后者,那么他的死也是對(duì)自己失戀的抗議。自我中心說(shuō)也好,遺恨說(shuō)也好,K的死法對(duì)于他的人格來(lái)說(shuō)決不是加分項(xiàng)”④[日]鶴田欣也:「テキストの裂け目」,『漱石の「こころ」どう読むか、どう読まれてきたか』,東京:新曜社,1992年,第210頁(yè)。。K的自殺體現(xiàn)了“自我本位”的消極方面——自閉和自利。由于過(guò)于強(qiáng)調(diào)自我,造成了他視野的狹隘化,割裂了自我與他人、社會(huì)的關(guān)系,一切從自身的感受和利益出發(fā),欠缺一種處世的協(xié)調(diào)性,結(jié)果走入了極端。
3.K的矛盾與孤寂。K的“自我本位”中,固然包含著只考慮自己、或者只能考慮自己的自私、自閉的一面。然而,K一心求道的行為,又體現(xiàn)了他追求以個(gè)性為基礎(chǔ)的自尊、自立、自強(qiáng)的一面。水川隆夫指出:“K和‘先生’一樣,在‘近乎武士’的父親以及教育敕語(yǔ)發(fā)布前后的小·中學(xué)校教育下,接受了儒教的、武士道的倫理。后來(lái)又逐漸養(yǎng)成了尊重‘自由、獨(dú)立、自我’的個(gè)人主義精神。”⑤[日]水川隆夫:『夏目漱石「こゝろ」を読みなおす』,第124頁(yè)。K固執(zhí)地堅(jiān)守內(nèi)心價(jià)值,“K所以未能拋棄舊的自己而銳意奔向新的方向,并非因?yàn)樗狈ΜF(xiàn)代人的意識(shí),而是因?yàn)樗兄鹳F得無(wú)法拋棄的過(guò)去。不妨說(shuō),他是為此而活到今天的”⑥[日]夏目漱石:《心》,林少華注譯,第528頁(yè)。,“既然沒(méi)有給予足以使之忘乎所以般的沖動(dòng),他就不可能不停下來(lái)回顧自己的過(guò)去。這樣,他就只能義無(wú)反顧地走過(guò)去指引的路。何況他又有現(xiàn)代人所不具有的剛毅與堅(jiān)忍”⑦[日]夏目漱石:《心》,林少華注譯,第529頁(yè)。。 他以“現(xiàn)代人所不具有的剛毅與堅(jiān)忍”,義無(wú)反顧地走“尊貴的過(guò)去”指引的道路。這樣的K,在選擇的努力方向上,體現(xiàn)了“自我本位”的積極方面,他沒(méi)有受到西化的社會(huì)風(fēng)潮的影響,而是堅(jiān)守內(nèi)心信仰,依靠尊貴的過(guò)去給自己的指引前行。他的選擇,彌補(bǔ)了夏目漱石當(dāng)初在專業(yè)選擇上未能遵從內(nèi)心而是跟風(fēng)的遺憾。而K在對(duì)家庭關(guān)系的處理上,也體現(xiàn)了他希望通過(guò)自身努力決定命運(yùn)的“自我本位”思想。小森陽(yáng)一就曾通過(guò)K和“先生”的對(duì)比指出:“‘先生’是被基于血緣的信賴關(guān)系所背叛,而K是為了‘道’而親自背叛了基于血緣的信賴關(guān)系。在這個(gè)意義上,K是更加具有主體性地選擇了‘充滿自由、獨(dú)立和自我的現(xiàn)代’的邏輯。這也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制度下城市生活者的邏輯。和這樣的K不同,‘先生’對(duì)這樣的新邏輯感到‘孤寂’。”①[日]小森陽(yáng)一:「こころ」を生成する「心臓(ハート)」,『成城國(guó)文學(xué)』1985年,第48頁(yè)。如果將K的死和自我(自由、獨(dú)立、自我)聯(lián)系在一起考慮,想要在明治這個(gè)時(shí)代里活出自我的人必須要付出的代價(jià)是“孤寂”這一結(jié)果。而這里說(shuō)的“自我”是帶引號(hào)的自我,換言之,K的自我是過(guò)于閉鎖的、不具有社會(huì)性的、孤高的“自我”。三好行雄指出:“明治的精神”體現(xiàn)了“生活于明治這一和洋折衷的時(shí)代的日本人的精神”,“選擇了禁欲和修行的東洋式的求道,從對(duì)肉體的侮辱中尋找精神的高貴的K”,“無(wú)疑是明治精神的體現(xiàn)者”②[日]三好行雄:「こゝろ」,『鑑賞日本現(xiàn)代文學(xué)⑤夏目漱石』,東京:角川書(shū)店,1984年,第215頁(yè)。。
三、K與明治30年代前后的日本社會(huì)
根據(jù)木村功的考察,“先生”和K的學(xué)生時(shí)代是從中日甲午戰(zhàn)爭(zhēng)之后到明治30年代前半期的大約六年間,處于中日甲午戰(zhàn)爭(zhēng)和日俄戰(zhàn)爭(zhēng)之間。“他們的青春,定位在為與歐美列強(qiáng)為伍而展開(kāi)急速的近代化、同時(shí)具備了帝國(guó)主義態(tài)勢(shì)的國(guó)家的抬頭期。”中日甲午戰(zhàn)爭(zhēng)后的日本政府,“推進(jìn)以軍事的、經(jīng)濟(jì)的、精神上的國(guó)力增強(qiáng)為重點(diǎn)的戰(zhàn)略經(jīng)營(yíng)。為增設(shè)陸軍師團(tuán)、建造海軍軍艦而擴(kuò)大軍事預(yù)算,導(dǎo)入軍事稅制。為確保軍需物資,興建鋼鐵業(yè)”。“物價(jià)不斷上漲,生活水平下降,國(guó)民困苦不堪,然而表達(dá)不滿聲音的爭(zhēng)議運(yùn)動(dòng)也被‘臥薪嘗膽’的口號(hào)抹消了。在民間,‘尚武的氣象’和 ‘武士道’精神被大肆提倡和鼓吹。”金子筑水闡述了明治30年代是認(rèn)同青年群體倫理宗教傾向的時(shí)代,“當(dāng)時(shí)高山樨牛等人最初標(biāo)榜日本主義,后來(lái)又高舉尼采、日蓮主義大旗,風(fēng)靡整個(gè)日本思想界。另外,能看到傳統(tǒng)的、多少帶點(diǎn)革新的傾向,但與其說(shuō)是學(xué)術(shù)的、純粹的哲學(xué)傾向,不如說(shuō)實(shí)際的人生觀的傾向——安心于新的人生觀的倫理的、宗教的傾向是從明治30年代一直到明治末期都很盛行的風(fēng)潮。在以這種傾向發(fā)展的過(guò)程中,宗教的熱情也高漲起來(lái),其熱情相當(dāng)?shù)貎A向于浪漫主義,這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如此,當(dāng)時(shí)的哲學(xué)界,——如果可以稱之為哲學(xué)界的話,在實(shí)際的意義上,處于一個(gè)帶有相當(dāng)單純浪漫色彩的倫理宗教時(shí)代,或者說(shuō)追求實(shí)際的人生觀的時(shí)代”③[日]木村功:「こゝろ」論――先生·Kの形象に関する一考察」,豬熊雄治編:『近代文學(xué)作品論集3』,東京:クレス出版,2001年,第48-49頁(yè)。。根據(jù)生方敏郎的論述:“那時(shí)的學(xué)生埋頭于宗教問(wèn)題、倫理問(wèn)題。即使是不喜歡那方面的學(xué)生或者和宗教并不相稱的人,也經(jīng)常出入教會(huì)。說(shuō)是時(shí)代精神也好,總之那一時(shí)期非常流行。”④[日]生方敏郎:「明治時(shí)代の學(xué)生生活」,『明治大正見(jiàn)聞史』,東京:中公文庫(kù),1987年,第115頁(yè)。
K的形象代表了這一時(shí)代潮流中熱衷于倫理、宗教的青年。與K的求道者形象近似的另一個(gè)人物形象,是夏目漱石在發(fā)表于1907年的小說(shuō)《野分》中塑造的主人公白井道也。白井道也主張:“人除了遵從道之外沒(méi)有其他方法。人是‘道’的生物,因此遵從道是最尊貴的。從道之人神也敬畏。”⑤[日]夏目漱石:「野分」,『漱石全集第四巻』,東京:巖波書(shū)店,1957年,第279頁(yè)。白井道也被推定為和“先生”、K同時(shí)代的人。從其名字即可知道,他是一個(gè)固守“道”之人,和“先生”、K一樣,他也受到了倫理宗教風(fēng)潮的影響。自青年時(shí)代起,夏目漱石就傾心于求道,無(wú)論是老莊的道,還是禪宗的道,漱石都苦心思索追求。在1913年10月5日給和辻哲郎的信中,夏目漱石寫(xiě)道,“我現(xiàn)在時(shí)刻留心入道”①[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三十卷』,東京:巖波書(shū)店,1957年,第213頁(yè)。。結(jié)合夏目漱石的經(jīng)歷來(lái)考慮的話,K的形象上也重合了夏目漱石自身的影子。
隨著生存競(jìng)爭(zhēng)日趨激烈,很多落敗者焦慮于如何自殺,甚至出現(xiàn)了華嚴(yán)瀑布、淺間山的火山口等青年人自殺的名所。1903年,夏目漱石擔(dān)任英語(yǔ)教師的一高的學(xué)生藤村操投身華嚴(yán)瀑布自殺。自殺之前他在華嚴(yán)瀑布旁樹(shù)干上寫(xiě)下了題為《巖頭之感》的詩(shī)作為遺書(shū),表達(dá)了當(dāng)時(shí)青年人的煩悶。其詩(shī)云:“悠悠哉天壤,遼遼哉古今,欲以五尺之小軀裁量此大。霍萊修之哲學(xué),竟終不值任何權(quán)威。萬(wàn)有之真理以一言悉之,曰:‘不可解’。我懷此恨,煩悶終至決死。既及立于巖頭,胸中無(wú)有任何不安。始知極大之悲觀與極大之樂(lè)觀之一致也。”②譯文引自彌生屋:《〈煩悶的青年〉(1908)譯稿:希望的青年,還是絕望的青年?》,2022年4月19日,https://mp.weixin.qq.com/s/op37IyoDx4NzfDwvMywv5A.此后,夏目漱石在《我是貓》(1905年)、《草枕》 (1906年)、《文學(xué)論》 (1907年)等著作中,都曾提及藤村操一事。1907年2月8日夏目漱石寄給弟子寺田寅彥的信,是一首寫(xiě)給藤村操的題為《水底之感》的詩(shī)。可以想見(jiàn)夏目漱石因?yàn)榇耸率艿搅讼喈?dāng)大的刺激,他對(duì)藤村操的死耿耿于懷。藤村操所代表的煩悶、絕望的一代青年的形象,夏目漱石通過(guò)塑造K的形象來(lái)進(jìn)行表現(xiàn)。K的遺書(shū)寫(xiě)得極其簡(jiǎn)單而抽象:“自己懦弱無(wú)能,前途無(wú)望,故而自殺。” 最后似以余墨補(bǔ)寫(xiě)的那句“本該早日死,為何活至今”③[日]夏目漱石:《心》,林少華注譯,第537頁(yè)。卻讓“先生”感覺(jué)最為沉痛,從中可以看出K的厭世求死之心由來(lái)已久。
作為“求道者”的K,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卻無(wú)從求之。“道”這個(gè)詞語(yǔ)無(wú)比高貴,在明治時(shí)代以前,一生作為求道者、悟道者而生存或許是可能的。然而,在生存競(jìng)爭(zhēng)激烈的近代日本,社會(huì)認(rèn)同的不是“道”這種“虛無(wú)”的精神,而是有形的實(shí)際利益。“求道者”被時(shí)代拋在后面,成為“落敗者”。在這樣的時(shí)代背景之下,在憑借一己之力根本無(wú)法與之對(duì)抗的時(shí)代潮流之中,K從根本上選擇了前途無(wú)望的事情。“懦弱無(wú)能,前途無(wú)望”,表明K認(rèn)識(shí)到自己力量的微小,不足以通過(guò)“自我本位”的堅(jiān)持改變時(shí)代潮流,主宰自己的命運(yùn)。視“道”為生命的他,失去了命根。封閉地求道的他,終于迎來(lái)此路不通的結(jié)局。雖然K親手毀掉了自己在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甚至為“道”獻(xiàn)出了生命,但在“先生”心中,K對(duì)“尊貴的過(guò)去”的堅(jiān)持是偉大的,他做出了非凡之舉。然而K的這種堅(jiān)持又是如此孤獨(dú),“先生”揣測(cè),K真正的死因,和自己一樣,是因?yàn)椤肮陋?dú)寂寞得不行才突然采取最后措施的”④[日]夏目漱石:《心》,林少華注譯,第545頁(yè)。。前一個(gè)時(shí)代無(wú)聲地崩潰了,自我也喪失了立足之地,由此產(chǎn)生了不安。明治時(shí)代加諸青年人的巨大思想難題,K和“先生”,終其一生都無(wú)法將其解開(kāi),高坂史朗將其稱之為“近代精神的挫折”⑤[日]高坂史朗:《近代之挫折:東亞社會(huì)與西方文明的碰撞》,吳光輝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5頁(yè)。。最終,隨著明治天皇的逝去,明治的青年們以自己的生命為這個(gè)時(shí)代獻(xiàn)祭了。“先生”自殺前說(shuō)的那句“殉明治的精神”⑥[日]夏目漱石:《心》,林少華注譯,第549頁(yè)。,決非一句戲言,而是處于時(shí)代轉(zhuǎn)折期自身命運(yùn)的真實(shí)寫(xiě)照。
“日本近代以來(lái)幾乎所有成功與失敗都與日本家族制度與家族倫理密切相關(guān)。家族制度不僅是封建時(shí)代幕府統(tǒng)治的支柱,而且是近代以來(lái)日本國(guó)民政治生活、經(jīng)濟(jì)生活、法律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基本紐結(jié)。雖然傳統(tǒng)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適應(yīng)了日本的資本主義工業(yè)化的進(jìn)程,在資本主義勞動(dòng)市場(chǎng)的形成、近代企業(yè)的結(jié)構(gòu)和經(jīng)營(yíng)管理方面都表現(xiàn)出有利的一面,但從政治、道德、法律的角度而言,家族制度帶給日本人的只有不平等。”①李卓:《日本近現(xiàn)代社會(huì)史》,北京:世界知識(shí)出版社,2010年,第89頁(yè)。家督繼承權(quán)賦予長(zhǎng)子財(cái)產(chǎn)單獨(dú)繼承權(quán)和家長(zhǎng)權(quán),造成長(zhǎng)子和其他兒子之間經(jīng)濟(jì)實(shí)力、身份地位差距懸殊,迫使長(zhǎng)子之外的諸子不得不自謀生路或者過(guò)著“寄食”的生活。受到“自由、平等、自我”思想洗禮的K,希望靠一己之經(jīng)驗(yàn)與意志決定自身進(jìn)路,卻在社會(huì)的家族制度的重重束縛之中無(wú)法翻身。K的身上,重合了夏目漱石身為“養(yǎng)子”的身世及其通過(guò)“自我本位”確立自我認(rèn)同的決心。不同的是兩人的結(jié)局:K將他的人生事業(yè)追求局限在自我意識(shí)之內(nèi),因而走進(jìn)了人生的死胡同;而夏目漱石則通過(guò)個(gè)人命運(yùn)與社會(huì)、時(shí)代的融合,實(shí)現(xiàn)了自我的價(ji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