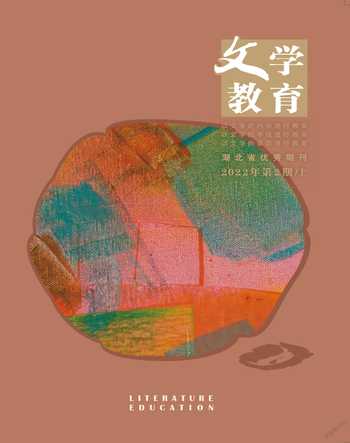艾青:自由體的內(nèi)在音樂性


艾青(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原名蔣正涵,字養(yǎng)源,號海澄,曾用筆名莪加、克阿、林壁等。出生于浙江金華,當(dāng)代文學(xué)家、詩人。1928年中學(xué)畢業(yè)后考入國立杭州西湖藝術(shù)院。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美術(shù)家聯(lián)盟,從事革命文藝活動。1933年第一次用筆名發(fā)表長詩《大堰河——我的保姆》。1935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大堰河》。1985年獲法國文學(xué)藝術(shù)最高勛章。1996年5月5日凌晨4時15分因病逝世,享年86歲。艾青被認(rèn)為是中國現(xiàn)代詩的代表詩人之一。主要作品有《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詩選》。
艾青的詩作將自由體詩推向了音樂性的更高境界。他貼近黑色大地,贊頌火紅陽光,書寫愛國主題中的倔強與抗?fàn)帲詰n郁深沉的詩風(fēng),淳樸自然、簡約明朗的語言,深刻影響了三四十年代和“新時期”以來的新詩發(fā)展。“土地”與“太陽”構(gòu)成了艾青詩歌“紅與黑”的兩大對應(yīng)并列的意象體系。黑色土地是民族苦難歷史和悲慘命運的意象化,凝聚著詩人對土地勞動者深沉的愛,對他們命運的質(zhì)詢與探索。紅色陽光系列意象表達(dá)了詩人對抗戰(zhàn)精神、真理光明和希望的熱情禮贊。艾青以溶化現(xiàn)實的詩家語和對色彩意象的自覺追求,增加了新詩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其內(nèi)在的音樂性和外在奔放的詩行,革新了所謂“自由體”詩歌的藝術(shù)魅力。
一
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中國新文學(xué)詩壇出現(xiàn)了中國詩歌會、后期新月派和現(xiàn)代派相互競爭的繁榮局面。艾青從法國吸納了東西方詩藝的精華,“吹著蘆笛”沉穩(wěn)地步入中國詩壇。其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在1933年1月的獄中創(chuàng)作而成,發(fā)表于次年《春光》第1卷第3期,首次署名“艾青”。艾青出生時難產(chǎn),算命先生說他命相“克父母”,從小便寄養(yǎng)在農(nóng)婦“大葉荷”家中,這一經(jīng)歷使艾青對破敗的舊中國鄉(xiāng)村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同情苦難中掙扎的鄉(xiāng)村農(nóng)民,逐漸形成了“憂郁”的個性。他深情地呼喊:“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兒是在獄里,/寫著一首呈給你的贊美詩”,“大堰河,含淚的去了!/同著四十幾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同著數(shù)不盡的奴隸的凄苦,/同著四塊錢的棺材和幾束稻草,/同著幾尺長方的埋棺材的土地,/同著一手把的紙錢的灰”,他將最誠摯的“圣母之歌”唱給了同大堰河一樣辛勞、貧苦、善良、平凡的中國鄉(xiāng)村農(nóng)人。
整節(jié)詩歌間接反復(fù),前后呼應(yīng)回環(huán)往復(fù),加深了情感的濃度與敘事意象的立體感。排比句式“在你……之后”,鋪陳我的保姆大堰河日常的清苦辛勞,詩句中緩緩流淌著大堰河對兒女家人的深情關(guān)愛,突出了她對“我”的特別呵護。詩中充滿濃郁的生活氣息,舒展奔放的結(jié)構(gòu)和淳樸親切的口語構(gòu)成了《大堰河》《鐵窗里》《夢》《春雨》等為代表的樸素的鋪陳體詩風(fēng)。
1934年3月,艾青創(chuàng)作了《蘆笛》,被“七月詩派”同仁譽為“吹蘆笛的詩人”[1]。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游徙于武漢、西安、桂林、湖南、重慶等地從事抗日文化活動,并堅持詩歌寫作。1938年創(chuàng)作了《我愛這土地》,詩人假設(shè)自己是一只鳥,以嘶啞的喉嚨歌唱土地、河流、林風(fēng)與溫柔的黎明,最后連羽毛也要腐爛在土地里:“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圣經(jīng)》贊歌式設(shè)問句,極寫出對苦難中的中華大地最深沉的愛。苦難的現(xiàn)實不斷強化他的憂郁情緒,“叫一個生活在這年代的忠實的靈魂不憂郁,這有如叫一個輾轉(zhuǎn)在泥色的夢里的農(nóng)夫不憂郁,是一樣的屬于天真的一種奢望”[2]。對底層社會饑餓的老人、蓬頭垢面的少婦、刻滿痛苦皺紋的農(nóng)夫、流浪者、乞丐等的人道主義同情,轉(zhuǎn)化為他筆下憂郁的詩情。
1932至1941年是艾青創(chuàng)作的黃金期,創(chuàng)作出版了詩集《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向太陽》《曠野》《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1941年3月,艾青從重慶到延安,參與發(fā)起成立“延安詩會”,在魯迅文學(xué)藝術(shù)院任教。新的革命環(huán)境逐漸改變了他思考問題的方式,詩歌情感與表達(dá)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創(chuàng)作了《黎明的通知》《給太陽》《獻給鄉(xiāng)村的詩》等作品。
艾青以對現(xiàn)實生活的深入觀察和對民族、人民命運的深沉關(guān)注,加強了現(xiàn)代詩歌的時代感和現(xiàn)實性。他善于將個人的遭遇同民族文化歷史聯(lián)系在一起,從民族文化建設(shè)角度探尋個人創(chuàng)造的深層價值。同時,他又廣泛地汲取世界詩藝的精華。在法國留學(xué)時期,艾青就閱讀了大量的西方作品,接受了象征派、印象派的藝術(shù)觀念,自覺借鑒西方詩藝以創(chuàng)作新詩,許多優(yōu)秀篇什中留有馬雅可夫斯基、惠特曼、波特萊爾等人詩風(fēng)的痕跡,做到了中西詩藝的融合。
二
艾青追求以意象呈現(xiàn)內(nèi)在情思,以意象拓展詩歌張力,通過意象融合現(xiàn)實與藝術(shù),創(chuàng)造個性化的新詩精品。艾青早年旅法學(xué)習(xí)油畫,對光影色彩的關(guān)注直接體現(xiàn)在他對世界的把握和感知體驗上。艾青的詩歌注重畫面感和立體感,意象色彩鮮明。他緊貼大地,抒寫“土地情詩”;追尋真理,呼喚光明。“黑色的土地”與“紅色的太陽”成為貫穿他全部詩作的典型意象[3]。
作為“土地的歌者”、“農(nóng)人的后裔”,艾青詩歌中最具典型、影響最深遠(yuǎn)的就是其土地意象。可以說,艾青的詩在其起點上就與我們民族多災(zāi)多難的土地與人民保持著血肉般的聯(lián)系。黑色的泥土是肥沃豐富的禮贊,也是面對民族苦難時的感情載體。在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詩人就用沉郁的筆調(diào)細(xì)寫了大堰河的生活痛苦,表達(dá)了詩人對中國廣大農(nóng)民遭際的同情與關(guān)切。作為一位心貼著大地的行吟詩人,艾青的很多詩都以土地、鄉(xiāng)村、曠野、道路和河流為中心意象或貫穿著土地、鄉(xiāng)村、曠野、道路和河流意象,形成土地意象群,如《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我愛著土地》《曠野》等。
艾青筆下的黑色土地,既是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具體可感的藝術(shù)形象,又是一組具有浪漫格調(diào)和象征色彩的審美意象。土地意象不但是中華民族的苦難歷史和悲慘命運的藝術(shù)具象化,而且還體現(xiàn)著作者多層的思想情感含義。
首先,它凝聚著詩人對祖國—大地母親最深沉的愛。愛國主義是艾青作品中永遠(yuǎn)唱不盡的主題,如《黎明》《北方》等,而把這種感情表現(xiàn)得最為動人的是他創(chuàng)作于1938年11月17日的《我愛著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鳥,∕我也應(yīng)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這被暴風(fēng)雨所打擊著的土地,/這永遠(yuǎn)洶涌著我們的悲憤的河流,/這無止息地吹刮著的激怒的風(fēng),/和那來自林間的無比溫柔的黎明……”這首詩中的愛國熱忱撲面而來。
其次,土地意象凝聚著詩人對祖國命運深沉的憂患意識。抗日戰(zhàn)爭期間,艾青通過廣泛接觸人民的苦難,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描寫北方風(fēng)、土、人的系列組詩。在《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一詩中,詩人反復(fù)呻吟著風(fēng)雪北國:“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詩人悲憤地講述著:“那些被烽火所嚙啃著的地域,/無數(shù)的,土地的墾植者/失去了他們所飼養(yǎng)的家畜/失去了他們肥沃的田地/擁擠在/生活的絕望的污巷里;/饑謹(jǐn)?shù)拇蟮?伸向陰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顫抖著的兩臂。//中國的痛苦與災(zāi)難/像這雪夜一樣廣闊而又漫長呀!”“中國,/我的在沒有燈光的晚上∕所寫的無力的詩句∕能給你些許的溫暖么?”透過這些反復(fù)、排比、呼告,壓抑的整齊的韻腳,人們所感受的正是詩人對土地的憂郁的深情和墾植者苦難命運的悲憫與哀吟。
再次,土地意象還凝聚著詩人對于生于斯、耕作于斯、死于斯的勞動者最深沉的愛,對他們命運的質(zhì)詢與探索。在其北方組詩里,詩人又以簡潔有力的筆觸刻繪了在這大地上生息的乞丐、驢子、補衣婦、農(nóng)夫、鋤草的孩子和老人。因此可以這樣說,傾注于對被侮辱受損害的勞動者——特別是農(nóng)民的關(guān)懷,是艾青土地意象象征意義延伸的歸結(jié)點。[4]
作為艾青詩歌的主導(dǎo)意象,“土地”類意象與黑色壓抑的韻律,都凝聚著詩人對祖國和人民最深沉的愛,以及對民族危難和人民疾苦的深廣憂憤。早在1940年,馮雪峰就對艾青的歷史地位做了理論的評定:“艾青的根是深深地植在土地上”,是在“根本上就正和中國現(xiàn)代大眾的精神結(jié)合著的、本質(zhì)上的詩人”。[5]
“紅色的陽光”是艾青詩意言說的另一個重要載體。唐弢曾說:“我以為世界上歌頌太陽的次數(shù)之多,沒有一個詩人超過艾青的了。”[6]紅色是暖色調(diào),是光明、溫暖的象征;同時也是戰(zhàn)斗犧牲精神的隱喻。因此,一方面“太陽”意象表達(dá)了詩人對光明和希望的熱烈期盼。《太陽》(1937年春):“從遠(yuǎn)古的墓塋/從黑暗的年代/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震驚沉睡的山林/若火輪飛旋于沙丘之上/太陽向我滾來……//他以難遮掩的光芒/使生命呼吸/使高樹繁枝向它舞蹈/使河流帶著狂歌奔向它去”,他把黑暗與太陽加以對比,用[-a-]元音做韻腳,形成一種內(nèi)在的昂揚的音樂性,盛贊“比一切都美麗”的陽光,深信只有太陽“把我們從絕望的睡眠里刺醒”,“刺醒我們的田野、河流和山巒”;“假如沒有你,太陽,/一切生命將匍匐在陰暗里,/即使有翅膀,也只能像蝙蝠/在永恒的黑夜里飛翔”(《給太陽》),堅信太陽給生命以陽光與力量。
另一方面,“太陽”意象還寄予著詩人對戰(zhàn)斗抗?fàn)幷卟磺竦亩Y贊。《吹號者》“以對于豐美的黎明的傾慕/吹起了起身號”,“太陽給那道路上鍍上黃金了/而我們的吹號者/在陽光照著的長長的隊伍的最前面/以行進號/給前進著的步伐/作了優(yōu)美的節(jié)拍”;《火把》(1940)描述了進步青年知識分子唐尼在抗日民主浪潮的激蕩下,從人民群眾的抗戰(zhàn)熱情中汲取力量,進而從迷惘和徘徊中覺醒,投身追求時代光明的斗爭行列的過程。“讓我們的火把/叫出所有的人/叫他們到街上來/讓今夜/這城市沒有一個人留在家里//讓我們每個人都做了帕羅美修斯/從天上取了火逃向人間/讓我們的火把的烈焰/把黑夜搖坍下來/把高高的黑夜搖坍下來/把黑夜一塊一塊地?fù)u坍下來”,全詩以敘事詩的結(jié)構(gòu)形式表現(xiàn)了作者對抗戰(zhàn)初期如火的民族情緒的謳歌。《向太陽》則塑造了一個支撐著拐杖向前行走的“傷兵”形象,他在“太陽下的真實姿態(tài)/比拿破侖的銅像更漂亮”,在詩人看來,這些平凡而不屈的士兵正是苦難民族的希望。
黑色土地、紅色陽光兩大意象系列,遙相呼應(yīng),并列對舉,融匯成詩人艾青對于現(xiàn)實、生命和自我的深沉吟唱。他將千百年來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于腳下的中國大地,對于普照天地的陽光的深情,轉(zhuǎn)化成為一種跨越現(xiàn)代與當(dāng)代的詩意交響樂,凝練成對比絢爛的綺麗詩篇,這是艾青對于中國新詩內(nèi)涵發(fā)展的貢獻。
三
艾青以來自生活而又詩化了的語言,以對浮泛的喊叫的擯棄和對審美意象的自覺追求,增加了現(xiàn)代詩歌的表現(xiàn)力。艾青曾如此發(fā)問:“一首詩里面,……沒有色調(diào),沒有光彩,沒有形象——藝術(shù)的生命在哪里呢?”[7]在創(chuàng)作中,他總是試圖將對于外在世界諸如土地、光色、風(fēng)、雨、霧、電等的感受與自己的思想情感融為一體,使詩句獲得一種豐厚感,一種情感沖擊力,如“頹垣與荒冢呀/都被披上了土色的憂郁”(《北方》),“呈給你黃土下紫色的靈魂”(《大堰河——我的保姆》),“由瑪格麗特震顫的褪了脂粉的唇邊/吐出蒼色的故事”(《蘆笛》),詩人對于外在世界的感受真實而特別,彰顯了一種崇高的價值認(rèn)同和巨大的語言張力。
艾青的色彩感特別強烈,色彩是他承載詩意的重要元素,色與意融為一體,化為美的意象和詩句。《北方》:“一片暗淡的灰黃/蒙上一層揭不開的沙霧/……村莊呀,山坡呀,河岸呀/頹垣與荒冢呀/都披上了土色的憂郁”;《曠野》:“在廣大的灰白里呈露出的/到處是一片土黃,暗赭/與焦茶的顏色的混合啊”,詩人以色彩再現(xiàn)北方鄉(xiāng)村的破敗,呈現(xiàn)詩人的憂郁。《向太陽》《火把》等詩里,火紅的色彩意象傳達(dá)的是詩人的民族自信心,是一個民族對于生的強烈渴求。
艾青以不受格律拘束、自由流動的詩行,鞏固了自由體詩歌在現(xiàn)代詩歌史上的地位。艾青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富于散文美的自由體詩歌,其特點是形式自由,表達(dá)口語化。形式自由,就是指詩人自由地抒寫所感所思,不求外在形式,只注重詩的內(nèi)在韻律。他認(rèn)為是詩產(chǎn)生格律,不是格律產(chǎn)生詩,他追求詩意的自由表達(dá),不愿意將美的詩意裝進呆板的形式里,而是讓詩情任意揮灑,變幻出美的節(jié)奏與形式,諸如《大堰河——我的保姆》那散文化的排比句,就是詩意自由生成的一種“格律”。艾青倡導(dǎo)詩的“散文美”,在《北方·序》中說:“我是酷愛樸素的,這種愛好,使我的感情顯得毫無遮掩,而我又對自己這種毫無遮掩的感情激起了愉悅。當(dāng)我們熟視了散文的不修飾的美,不需要涂抹脂粉的本色,充滿了生活氣息的健康,它就肉體地誘惑了我們。口語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間味。它使我們感到無比的親切。”他還說,“我說的詩的散文美,說的就是口語美”,“最富于自然性的語言是口語”[8]。口語是美的,大詩人才能挖掘、駕馭其中的富有表現(xiàn)力的音樂性元素,來“自由”地抒寫自己的生命體驗與生活感受。艾青以口語入樂,自由奔放,創(chuàng)造出一種靈動變幻而又具有內(nèi)在音樂性的新詩體。
艾青在繼承與創(chuàng)造、自由與整飭中將自由體新詩推向了“音樂性”的更高境界。正如綠原所說:“中國的自由詩從‘五四發(fā)源,經(jīng)歷了曲折的探索過程,到三四十年代才由詩人艾青開拓成為一條壯闊的河流。”[9]艾青緊貼中國大地,以崇高的價值理念為底蘊,廣泛借鑒中外文學(xué)經(jīng)驗,“綜合”五四以來新詩散文化與格律化的傳統(tǒng),融會貫通,將中國自由詩推向了一個外在情思與內(nèi)化的音樂性完美溶合的新高度。[10]
參考文獻
[1]胡風(fēng):《吹蘆笛的詩人》,《胡風(fēng)評論集》(上),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4年,第416頁。
[2]艾青:《詩論》,《艾青全集》(第3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43頁。
[3]筆者受呂進老師和李冰封同學(xué)論文《由紅到黑:對聞一多詩歌意象的一種闡釋》(《西南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06年第4期)的啟發(fā),從意象色彩上對早期艾青詩歌意象系列進行了概括,特此致謝。
[4]龍泉明:《中國新詩流變論(修訂版)》,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4年,第345頁。
[5]馮雪峰:《論兩個詩人及詩的精神和形式》,《文藝陣地》,1940年4卷10期。
[6]唐弢:《中國現(xiàn)代作家作品欣賞叢書·新版序言》,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
[7]艾青:《詩論掇拾》(一),《艾青全集》(第3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第48頁。
[8]艾青:《詩的散文美》,《艾青全集》(第3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第65頁。
[9]綠原:《白色花·序》,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4年。
[10]本文資料搜集感謝江薇整理。
任毅,閩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武漢大學(xué)博士畢業(yè),福建省寫作學(xué)會副會長,福建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代詩學(xué)和魯迅傳播研究,在《光明日報》《當(dāng)代文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小說評論》《中國文藝評論》《魯迅研究月刊》《福建論壇》《詩刊》《詩探索》等報刊上發(fā)表論文150余篇,出版專著《百年詩說》《0596詩篇》等多部,入選福建省閩南師大新世紀(jì)優(yōu)秀人才支持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