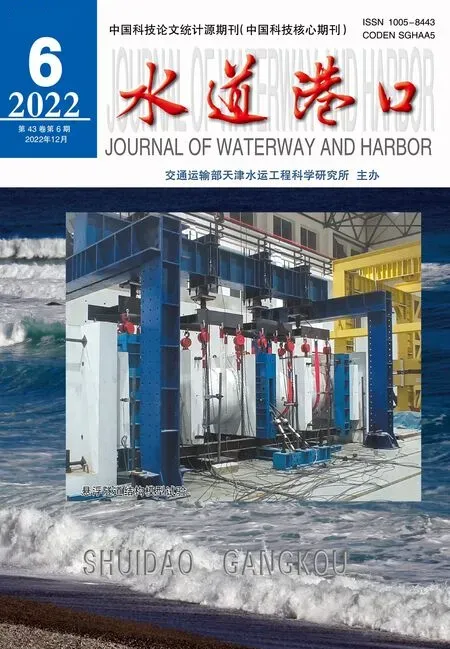帶齒墻基礎與土體相互作用水平承載特性研究
王 蒙,譚慧明*,陳 寧
(1.河海大學 海岸災害及防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南京 210024;2.河海大學 港口海岸與近海工程學院,南京 210024;3.南方海洋科學與工程廣東省實驗室(湛江),湛江 524013)
當擋土(擋水)結構物建于軟弱地基上或抗滑穩定性不足或作為安全儲備時,常常采用設置齒墻(齒坎、凸榫)的方法來滿足防沖抗滲抗滑承載力的要求[1-6]。相關學者采用試驗研究了齒墻的承載特性[7-9],結果表明:齒墻對擋土結構物的抗滑作用較大,設置齒墻可保護易沖刷地基,增強抗沖刷能力。數值模擬特別是有限元法,是研究帶齒墻基礎結構承載特性的方法。阮長青等[10]對有無齒坎的重力式擋土墻進行有限元分析,發現隨著齒長和水平力作用點的抬高,底板下剪切破壞帶深度加深,破壞模式由滑移破壞轉為傾覆破壞。賴允瑾等[11]通過有限元計算得出隨著錨碇位移量加大,齒坎正面承擔的抗力比例越大的結論。劉金龍等[12]基于有限元法考察了齒坎式擋土結構物與墻后填土共同作用下的抗滑特征。但對于帶齒墻基礎而言,在基礎出現失穩破壞前,齒墻基礎通常會對附近地基土造成破壞,地基土會出現較大變形,通常的有限元計算并不能很好地反映這一特點。此外,關于帶齒墻淺基礎與周圍地基土體相互作用的破壞模式研究和齒墻數量對水平承載特性影響的研究也較少,因此本文采用模型試驗和離散元數值模擬相結合的方法分析研究帶齒墻淺基礎水平承載特性和土體破壞模式。
1 實驗設計
1.1 實驗裝置和材料
雙齒墻淺基礎模型如圖1所示,試驗總體圖如圖2所示。模型底板寬度為0.14 m,兩側板間的底板寬度為0.11 m、長度B為0.2 m,側板高度為0.17 m,加強角條尺寸為0.02 m×0.02 m×0.14 m。底板下的齒墻高度為0.04 m,齒墻數量為2個。將雙齒墻淺基礎模型放置在長度0.7 m、寬度0.14 m、高度0.3 m 的土體容器中,通過水平加載裝置對模型施加荷載,同時通過外部拍攝記錄設備記錄實驗過程。

1-a 斷面圖1-b 平面圖
外部拍攝記錄設備由一臺500萬像素工業相機、一對功率36 W色溫5 500 K的長條形補光燈、一塊1.5 m×1 m的攝影吸光布和一臺筆記本組成。在后處理中,使用粒子圖像測速技術(PIV)分析,得到土體應變場。PIV技術是一種模式識別技術[13-14],它對連續的兩幅圖像進行比較計算出其位移場,具體原理是將土體變形前后獲得的圖像分割成大量獨立的圖像塊,將變形前的每個圖像塊與變形后的圖像進行全場匹配或相關計算,根據峰值相關系數確定該圖像塊在變形前后的位置,從而求得每一圖像塊的中心位移,進而獲得整體的位移場。
試驗所用地基土為標準石英砂,其物理力學參數根據室內材料性質試驗確定,如表1所示,顆粒級配曲線如圖3所示。

圖3 顆粒級配曲線圖

表1 砂土物理力學參數
1.2 試驗方案
雙齒墻淺基礎水平加載試驗共分為3組,對比分析不同的力矩和水平荷載復合作用對雙齒墻淺基礎水平承載特性的影響。通過改變模型上的水平荷載作用點的高度,來實現不同的力矩和水平荷載復合作用。試驗分別在0.05 m(0.25B)、0.1 m(0.5B)、0.15 m(0.75B)作用點高度施加水平荷載,且垂直配重壓載均為6 kg。
使用電腦控制工業相機拍攝初始狀態時的照片。采用分級加載的方法,每級荷載為0.5 kg,通過逐級往水平加載裝置中的加載容器輕放秤砣來施加荷載,每級加載后,按間隔5 min測讀一次百分表的水平位移值。當連續10 min內,每5 min的沉降量小于10-4m時,則認為已趨于穩定,記錄當前級荷載值和對應的水平位移值,當水平位移急劇增大,荷載-水平位移曲線出現陡降段時,即終止加載。利用數據繪制得到荷載-水平位移曲線,該曲線上陡降段起點荷載值為該雙齒墻淺基礎模型的水平極限承載力。
1.3 試驗結果
雙齒墻淺基礎模型的荷載-位移/轉角曲線如圖4、圖5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所有作用點高度的模型水平位移、轉角變化趨勢類似,均為陡降型曲線。開始時位移、轉角緩慢增加,隨后位移、轉角增加速率隨荷載增大而逐漸增大,5 cm、10 cm、15 cm作用點高度雙齒墻當荷載分別達到39.2 N、29.4 N、24.5 N時,模型位移、轉角急劇增大,突然失穩,此時荷載即為模型極限承載力。隨著水平荷載作用點高度的增加,模型的水平極限承載力不斷降低,失穩前一級荷載下的極限位移也不斷降低。這是由于雙齒墻淺基礎的基礎深度較低,導致其抵抗力矩性能較低,并且當水平荷載作用點高度增加時,基礎由以水平滑移破壞為主逐漸過渡為以傾覆破壞為主,導致其水平極限承載力大幅降低。

圖4 雙齒墻淺基礎物理模型荷載-位移曲線 圖5 雙齒墻淺基礎物理模型荷載-轉角曲線
使用模型失穩平衡后的實驗照片和失穩前一級荷載時實驗照片進行PIV分析,可得到土體破壞時刻的土體位移場如圖6所示。從圖6可以看出:隨著水平荷載作用點高度的升高,傾覆破壞占主導作用,雙齒墻淺基礎模型圍繞右齒墻轉動的中心上移,右齒墻右側土體的高影響區域變淺變窄,右齒墻右側滑動土體可分為三大區域,右齒墻右側的薄層土體整體斜向下運動,薄層之外的土體運動方向上、下分離的界限點高度增加;右齒墻底部土體受壓斜向右下運動加劇;底板右側轉動下壓加劇,其下方主動滑動土體向底板中部擴張;左齒墻左側的楔形下滑土體因齒墻拔出而下滑;左齒墻右側被動滑動土體范圍變小,運動方向由水平為主變為豎直向上。土體滑裂面由幾乎連續的中間弧形的向右傾斜的W形,分離為兩個窄而陡峭的V形,左齒墻底部右側的高應變區域上移,右齒墻底部右側高應變區域往深部延伸,底板右側加強角處應變值增大。

6-a 0.05 m作用點高度
2 離散元模型
2.1 模型尺寸和土體參數
本文根據雙齒墻淺基礎水平加載試驗模型數據,使用離散單元法來建立二維離散元模型。利用數值模擬雙軸試驗,通過對比數值試驗結果與室內試驗結果確定微觀參數,通過調整試樣參數,使得試樣表現出來的宏觀力學特性與室內試驗結果相符,模擬試驗得到的砂土物理力學參數與實際砂土物理力學參數對照結果見圖7。按照試驗模型槽尺寸生成數值模型槽,使用膨脹法生成地基土顆粒并在自重下平衡,逐級施加水平荷載并在加載過程中記錄模型位移、轉角、荷載、顆粒位置、顆粒位移等參數。離散元數值模擬能夠提供各個顆粒的位移、接觸角、接觸力、摩擦角、骨架結構和力鏈網絡等細觀參數,從而更清晰地認識荷載作用于土體內部所產生的機制。本文建立的雙齒墻數值模型如圖8所示,數值模型按照試驗尺寸建立,帶齒墻淺基礎地基土體的高位移區域遠小于3倍乘1倍的基礎底板長度范圍[15-16],滿足對模型地基土體位移場的觀察需要。具體模型材料參數如表2、表3所示。

表2 地基土顆粒數值模擬參數表

表3 雙齒墻淺基礎數值模擬參數表

圖7 數值模擬與普通三軸試驗對比

圖8 離散元數值模型示意圖 圖9 雙齒墻淺基礎物理模型對比數值模型的荷載-位移曲線
2.2 模型合理性驗證
首先建立離散元數值分析模型,分別對物理模型試驗工況進行模擬,并將數值模擬獲得的結果與實驗結果進行對比以驗證數值模型和計算參數的合理性,對比結果如圖9所示。
從圖9可以看出,數值模擬與物理模型的曲線走勢較為一致,同樣為陡降型曲線,模擬的位移增加速率均呈現出與物模曲線一致的隨著荷載增加而不斷增加的趨勢。在曲線末端,物模和數模曲線的差異略微增加,這是由于數值模擬在每級加載時采用了更加緩慢的加載策略,保證模型在加載時不會因受到沖擊而發生過大位移,而物模對人為操作的加載過程中造成的略微沖擊不可避免,而最終模型失穩是一個快速發生的過程,由此導致位移的略微增加,加大了數模與物模因加載效果不同導致的結果差異,但差異不大可以忽略。由此驗證了所建立的離散元數值模型的有效性。
3 齒墻數量對帶齒墻淺基礎的水平承載特性的影響
為對比分析在水平荷載、力矩復合作用下,不同齒墻數量對帶齒墻淺基礎的水平承載特性以及地基土體破壞模式的影響,采用如圖10所示的結構形式,繼續使用PFC2D顆粒流軟件的離散單元法建立二維離散元模型并對試驗進行數值模擬。

圖10 單、雙、三齒數值模型結構形式正視圖
3.1 荷載-位移/轉角曲線
不同齒墻數量數值模型的荷載-位移曲線如圖11所示,荷載-轉角曲線如圖12所示,淺基礎數值模型的承載特性改變比例如表4所示。從圖11和圖12可以看出,單齒、雙齒和三齒模型的荷載-位移曲線和荷載-轉角曲線均為陡降型曲線,位移和轉角的增加速率均隨著荷載的增加而不斷增加。在5 cm作用點高度時,當荷載分別達到34.3 N、39.2 N、44.1 N時,單、雙、三齒墻模型位移、轉角急劇增大,此時荷載即為模型極限承載力,隨著水平荷載作用點高度的增加,模型的水平極限承載力不斷降低,失穩前一級荷載下的極限位移也不斷降低。總體上,相比于單齒墻模型,在所有作用點高度下,雙齒和三齒模型的水平極限承載力均有所增大,在同一級荷載下三齒模型水平位移和轉角的減小幅度顯著大于雙齒模型。實體基礎模型的位移隨水平荷載增加而緩慢增加,陡降程度較小,變化比三齒墻模型均勻。三齒墻模型的曲線有較為明顯的增加的轉折點,說明三齒墻模型雖然抗水平位移性能較好,但是一旦開始失穩,從失穩到破壞的過程會非常劇烈,而實體基礎模型的抗傾覆性能要略優于三齒墻模型。從水平極限承載力增加比例來看,實體基礎模型與三齒墻模型仍比較接近,從平均每級荷載下水平位移減少比例可以看出,三齒墻模型的抗滑移性能優于實體基礎模型,實體基礎模型的抗傾覆性能優于三齒墻模型。

圖11 單、雙、三齒墻數值模型的荷載-位移曲線 圖12 單、雙、三齒墻數值模型的荷載-轉角曲線

表4 不同齒墻數量對基礎水平承載性能影響對比結果
從表4可以看出,總體而言,相比于單齒墻,隨著作用點高度的增加,雙齒和三齒模型無論在極限承載力,還是在減小位移和轉角方面的性能都有較大提升。隨著作用點高度的增加,總體上兩者承載力提升比例均有上升趨勢,最后均達到25%,兩者的性能比較接近,這表明齒墻數量的增加對模型極限承載力的提升效果不明顯,只在作用點高度較低時能發揮一定的作用。 齒墻數量的增加能有效減小轉角,在所有作用點高度下,平均每級荷載下位移、轉角減小比例的平均增幅達30%、20%左右。實體基礎的荷載位移曲線和三齒墻淺基礎類似,隨著加載高度的增加,實體基礎的水平極限承載能力急劇下降[17-18]。隨著作用點高度增加,雙齒和三齒模型的平均每級荷載下轉角減少比例總體上均呈現上升趨勢。由于中間單齒在低作用點高度時水平滑動特性明顯,模型的垂直荷載直接作用于中間單齒墻之上,抑制其發生向上的拔出運動,因而被強迫水平向運動,而雙齒和三齒模型由于左、右齒墻的存在,左齒墻斜向上拔出和右齒墻轉動下壓的趨勢明顯,比較容易產生較大轉角。而隨著作用點高度繼續增大時,平均每級荷載下轉角減少比例不再明顯增長是因為此時模型傾覆破壞作用逐漸占主導地位,齒墻數量的增加只會將淺基礎的性能逐漸向更加厚實的淺基礎性能靠近。
3.2 土體位移場
在0.05 m、0.1 m和0.15 m作用點高度的情況下,中間單齒墻模型、雙齒墻模型和三齒墻模型的地基土體破壞時刻的位移矢量云圖如圖13、圖14和圖15所示。
對于中間單齒墻模型,從圖13-a可以看出,0.05 m作用點高度時,在土體破壞之前土體的高影響區域依然寬深,外輪廓線仍為底部平緩的U型,但模型以齒墻為支點的轉動增加,底板右端對土體的下壓作用加重,此處原本水平運動的土體大幅度偏下運動,再轉而上拐通往土表。而齒墻右側土體高影響區域有收窄趨勢,土體緊貼加強角處斜向上運動。由于底板右端過于單薄而輕易向土體刺入,使得模型的水平承載力大幅度降低。從圖14-a和圖15-a可以看出,中間單齒墻模型在0.1 m和0.15 m作用點高度時,底板右端的下壓作用已經非常明顯,土體高影響區域集中在底板右端,高影響區域的土體被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向下擠壓,并往土體深處大幅度延伸,隨后轉而向上通往土表。此時模型主要發生傾覆破壞,齒墻對右側土體影響范圍進一步收窄,以齒墻右側附近為中心的土體回轉運動逐漸顯著,加速了模型的失穩。
對于三齒墻模型,從圖13-c、圖14-c和圖15-c可以看出,隨著作用點高度的增加,模型傾覆破壞比例增大,土體高影響區域變淺上拱,左齒墻向上拔出趨勢加重,對其右側土體的影響大幅減小,右齒墻轉動下壓運動加劇,中間和右齒墻間的土體高影響區域外輪廓由直線變為拱形。右齒墻右側土體斜向下推出較遠距離后轉而斜向上運動至土體表面,比雙齒墻模型對右側土體的影響范圍稍大。土體弱影響區域也有一定程度的加深。三齒墻模型的土體破壞模式結合了中間單齒模型和雙齒墻模型的特點,其承載性能也比前兩者略勝一籌。

13-a 0.05 m作用點高度單齒墻位移矢量云圖 13-b 0.05 m作用點高度雙齒墻位移矢量云圖13-c 0.05 m作用點高度三齒墻位移矢量云圖

14-a 單齒墻位移矢量云圖 14-b 雙齒墻位移矢量云圖 14-c 三齒墻位移矢量云圖

15-a 單齒墻位移矢量云圖 15-b 雙齒墻位移矢量云圖 15-c 三齒墻位移矢量云圖
4 結論
(1)帶齒墻淺基礎的荷載-位移/轉角曲線為陡降型曲線,水平極限承載力隨水平荷載作用點高度的增加而降低,當水平作用點高度為0.75B時,帶齒墻淺基礎以轉動破壞為主,當水平作用點高度在0.25B至0.5B時,帶齒墻淺基礎滑動、轉動混雜且轉動比例逐漸增加。
(2)隨著水平荷載作用點高度升高,當作用點高度達到0.5B時,右齒墻右側土體影響寬度縮小,帶齒墻淺基礎轉動破壞比例增加;當作用點高度達到0.75B時,左右齒墻兩側對土體產生影響,兩齒墻中間土體影響區域較小,帶齒墻淺基礎轉動破壞明顯。
(3)隨著齒墻數量增加,模型的水平極限承載力顯著增加。和單齒墻相比,當作用點高度為0.25B時,雙齒墻、三齒墻的水平極限承載力分別增加了14.29%和28.57%;當作用點高度為0.75B時,水平極限承載力均增加了25%。作用點較高時,齒墻過密相互影響使極限承載力增加不明顯。
(4)隨著齒墻數量增加,水平荷載作用點較低時,帶齒墻淺基礎抗力主要由齒墻右側和底板右側承擔轉變為主要由中間齒墻右側和左、右齒墻右側承擔;水平荷載作用點較高時,帶齒墻淺基礎抗力主要由底板右側承擔轉變為主要由右齒墻底部和底板右側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