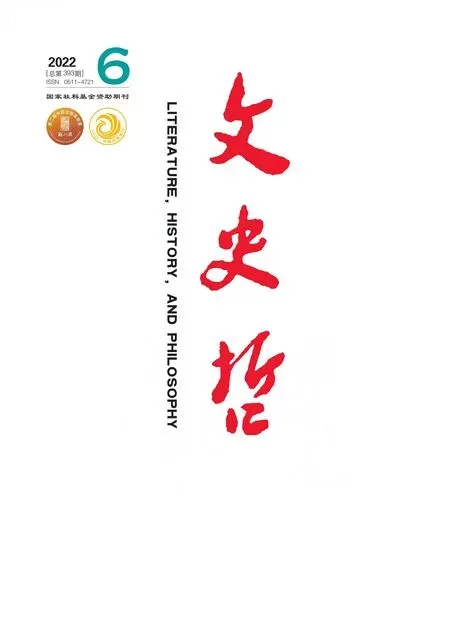古禮今學:吳承仕禮學思想略論
吳 飛
一、古禮今學
吳承仕先生,號檢齋(又作絸齋),出身于清代皖派學術的重鎮歙縣,曾整理其鄉賢程瑤田《儀禮經注疑直輯本》,對程瑤田研究功莫大焉。他身為章太炎先生弟子中的“北王”,不僅非常熟悉章門學術的小學功夫,更精通三禮之學,有書信與太炎先生非常深入地討論禮學問題。吳先生最后又成為中國共產黨特殊黨員,系統研讀了馬克思主義著作,支持學生運動,于1939年逝世于北平。吳承仕先生在1934年由其主編的《文史》創刊號上,發表《五倫說之歷史觀》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者對于喪服應認識的幾個根本觀念》二文,自覺運用社會科學方法和唯物史觀研究禮學,堪稱今人研究傳統禮學的典范,對包括筆者在內的當代禮學研究者啟發巨大。其弟子與當代學人關于他的研究,很強調他如何從一個經學家成長為一位革命戰士(1)弟子回憶如王西彥《從學者到戰士——記我所接觸到的吳承仕先生》、陸宗達《從舊經學到馬列主義歷史哲學的躍進》,參見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42-63、116-120頁。,但對吳承仕先生的禮學研究如何將這兩個方面熔于一爐,大多僅有涉及,而很難深入。之所以如此,當然首先是因為吳承仕先生留下的著作不多,特別是其將禮學傳統與唯物史觀理論結合起來的研究成果更少,其學術研究的最終形態并未完整呈現出來。不過,從吳承仕先生現存的著作中,我們仍能找到蛛絲馬跡,據此在新舊交融的民國學界給吳承仕先生一個大致的定位,并為今天禮學與經學研究的范式探索提供借鑒。
根據相關人士的回憶,吳承仕先生正式接觸馬克思主義應該是在1930年,他從范文瀾處讀到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與《共產黨宣言》(2)佟冬《對于吳檢齋先生的片段回憶》、榮孟源《悼念吳檢齋先生》,以及胡云富、侯剛《吳承仕傳略》均有所述及,分別見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第88、101、202頁。。在深入閱讀了這些著作之后,吳承仕先生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有了系統的反省與規劃。陸宗達先生說:“為什么檢齋先生要從‘三禮’入手來探討中國某一時代的歷史發展呢?因為他認為,在古代典籍中,‘禮’是直接表現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的,因而也就最足以反映當時的經濟基礎。從這點出發,他認為研究‘三禮’應自喪服始。”(3)陸宗達:《從舊經學到馬列主義歷史哲學的躍進》,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第119頁。此說較為清楚地表達了吳承仕先生后來看待禮學的思路。實際上,吳先生曾明確講過自己的研究規劃:
我自從對于經學即史學,史學有史學的哲學與方法,并有它的時代任務與作用,這一系列的命題有了明了認識以后,三四年來,擬將所謂“三禮名物”——即古代社會下層的基礎以及上層的意識形態之表顯于三禮中者——中各部門,先整理材料,考訂真偽,作成有系統的敘述,名之為文獻檢討篇;次比較異同,求得其通性與異性,而確定某時代之經濟形態相當于歷史公式之某一階段,名之為史實審定篇。(4)吳承仕:《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與井田制》,原刊于《文史》一卷三號(1934年8月),收入吳承仕:《吳承仕文錄》,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72頁。他也曾將這一規劃講給陸宗達先生,參見陸宗達:《從舊經學到馬列主義歷史哲學的躍進》,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第119頁。
這里說的研究工作,吳承仕先生大部分沒有來得及完成,但從中也可以看到他治學的基本思路和總體規劃。黃壽祺先生認為,吳承仕先生的《三禮名物》等著作“是屬于文獻檢討篇的范疇”,而《文史》上以及以后發表的若干篇文章,“則是屬于史實審定篇的范疇”(5)黃壽祺:《略述先師吳檢齋先生的學術成就》,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第141-142頁。。
吳承仕先生的思想發展,給我們帶來了一個疑問:他前后期的學術研究,特別是禮學研究,究竟是截然分開的新舊兩段,還是有著內在的關聯?如果有的話,這種關聯是什么,又如何區別于同時期其他學者的研究?
很多吳承仕先生同時代的師友認為其前后期有一個重大變化。章太炎先生就是這樣看的。吳承仕先生自己說:“太炎先生對他的老師表示決裂,寫過‘謝本師’。我的老師不同意我現在走的路,我不會做出他那樣的表示。”他的老朋友孫人和也認為,他“忘了老朋友,不要老朋友了,也不搞學問了”(6)均見張枏:《永難泯滅的記憶》,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第81頁。。呂振羽先生在吳承仕先生去世后不久也提道:“《文史》雖然獲得大多數青年的愛護,然對于從來的國學‘道統’自亦不免有所冒犯。這卻招致檢齋先生的舊同道對他個人的攻擊和謾罵。他因此被推出北大和師大的國學‘王座’;據說其業師太炎先生也不免慨嘆于‘檢齋的退步’。”(7)呂振羽:《悼吳檢齋先生》,原刊于重慶《新蜀報》1940年1月20日,第4版,收入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第153頁。這些說法都顯示,在其昔日的師友看來,吳承仕先生有個重大的思想轉變,甚至是背叛。他自己也曾對學生說:“我們鉆了一輩子故紙堆,沒有用,希望你們不再鉆故紙堆。你們首先要學社會科學,懂得社會發展規律。理論和實踐統一起來,才能夠成為真正有用的人。”(8)張枏:《永難泯滅的記憶》,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第79頁。這一說法,似乎是否定了此前研究故紙堆的學問。
但對章、吳師弟子都有深入研究的王銳先生指出,“‘故紙堆’及其背后的思想傾向與價值判斷,與‘社會科學’所代表的要求,二者之間雖有矛盾之處,但也并非截然相反”(9)王銳:《從經史之學到馬克思主義史學——吳承仕的學術旨趣及其古代社會論》,《福建論壇》2022年第5期,第157頁。。王銳認為,“章太炎雖然表面上恪守古文經學的治學之道,但他的思想內涵絕非僅限于中國傳統學術。深受章太炎學術思想影響的吳承仕,自然也不會排斥新學”(10)王銳:《吳承仕——從經生到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歷史評論》2020年第3期,第120頁。。當時的楊樹達先生,已經有過類似說法。他在1934年1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訪吳檢齋。見示論五倫文字,根據《禮經》,剖析精微,令人心折。檢齋今日頗泛覽譯本社會經濟學書,問者群以為怪,交口詈之。一日,一友為余言之。余云:‘君與余看新書,人以為怪,猶可說也;若檢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參合新舊起家,檢齋所為,正傳衣缽,何足怪也?’友人語塞,無以難之。”(11)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5-56頁。
從西方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中國傳統學問,本就是民國以來的學術潮流,章太炎先生自身就已經有所吸收,更不必說同時代的其他許多學者。誠如吳承仕先生所言,章太炎之于俞曲園,吳承仕之于章太炎,雖均有很大變化,但在思路上仍有繼承之處。至于從唯物史觀理解傳統學問,特別是禮學,在民國學界,尤其是社會史大論戰前后,已經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思想傾向,不僅郭沫若這樣的左派學者,即使被吳承仕先生痛批的陶希圣,也同樣受到了唯物史觀的影響。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任何號稱以唯物史觀的態度對待中國傳統材料的做法都是可取的。盲目地以西方觀念裁割和解釋中國材料,難免武斷與附會之弊,可能流為機械論的妄言。只有對兩種思路都有深入的了解,并找到恰當的契合點,解釋才有力量,才能夠真正推動學術的進步。這是無論民國學人還是當代學人,都同樣面臨的問題。章太炎先生的學問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不僅有非常扎實的舊學功底,而且曾廣泛閱讀西學著作,不僅可以恰當運用,而且有相當深入的反思與批判,甚至運用起來不見痕跡。當然,他所接受的并非唯物史觀。
當年運用唯物史觀解釋中國歷史,影響最大的無疑是郭沫若先生,但今日看來,其對中國歷史的解釋不免多有牽強之處。相較而言,社會史論戰中很多學者對唯物史觀的運用,未免“生吞活剝”之嫌。那么,精通經學的吳承仕先生在做類似的解釋嘗試,特別是在批評陶希圣的時候,他的思想特點在哪里,何以區別于郭沫若等其他學者?特別地,他前期的經學研究,除了自己所說的“文獻檢討”之外,還在什么意義上影響了其后的“史實審定”?這是我們尤其關心的問題。
吳承仕的一位回族學生楊明德先生說,他本來對漢族傳統禮制并不熟悉,但“經過吳先生給我們講喪服期、五服,讓我們思考,同時讓我們讀墨子的節喪、短喪,我才深知了檢齋先生的進步思想。我的畢業論文題目就選了《儒家厚葬墨子節葬論》,長達幾千字,很得檢齋先生的賞識”(12)楊明德:《檢齋先生在師大》,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第114頁。。這位楊先生是1929年畢業的,還在吳承仕先生真正接觸唯物史觀之前,而在那時候,楊先生就覺得他有“進步思想”了,并受他的影響研究了喪服制度。可惜的是,現存吳承仕先生的著作很少涉及墨子,而楊明德先生的論文筆者也未能見到。可以想見的是,吳承仕先生在當時講喪服學的課堂上,已經有了一些現代思想,而這些思想并沒有使他否定喪服研究,反而推動著學生去做這方面的研究。
二、職在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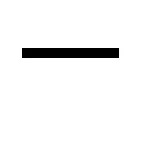
在1929年致太炎先生書中,吳承仕先生就提到了自己打算寫的一部大書:
承仕頗欲撰《三禮辨名記》一書,以事為綱,列封建、制祿、井田、宮室、車服、時祭、間祀等數十題,首引經、記明文,次鈔鄭說,次摘賈、孔要義,而翦其緐蕪。后儒駁正之說,且置不錄。如是乃能窺《三禮》之概要。是書若成,似較《通故》為善。(14)參見吳承仕:《吳絸齋上余杭先生書》,《制言》1926年第8期,第4頁。
《三禮辨名記》就是后來的《三禮名物》。定海黃元同先生,太炎亦以師禮事之,曾為黃先生作傳,而吳承仕先生欲作一部較黃先生《禮書通故》更好的禮學著作,其志誠不在小。隨后他也說明了自己的具體想法:
承仕亦知鄭君說《禮》,于記、傳違經之處,多以異代法通之,似為完密,而實滋糾紛。清儒頗糾正鄭君,而實陰用鄭法,猶之糾紛也。今且先通賈、孔申鄭之義,本基既立,乃論后儒之是非,實治《禮》之要術也(江氏《禮書綱目》,意亦如是。與彼異者,并列疏文,且附以圖表耳)。(15)吳承仕:《吳絸齋上余杭先生書》,《制言》1926年第8期,第5頁。
這段話里包含了《三禮辨名記》最重要的學術思路,即對鄭學“以異代法通之”這一做法的評價。鄭氏“以異代法通之”的做法,包括兩方面,一是以夏、殷禮與周禮比較互證,二是以漢時之禮解禮經之說。在回復中,太炎先生一言即指出其要害:“既以禮為鄭學,而又不滿于鄭氏傅會之說,則用思益不易。”吳承仕先生在信中舉出《王制》的例子,認為其中所言封建與三監制度不合周制,而鄭氏則附會為殷制。對此,太炎先生做了更加審慎的討論。他首先同意吳承仕先生的判斷:“至夏、殷文獻,本無可征,鄭說原非有明據。”隨后筆鋒一轉:“然如封建地域之事,亦不能謂其盡誣。”對于禘祫禮,他認為鄭氏糅合今古文為說,五冕之制,鄭則附會《虞書》十二章。文末又略略涉及以漢制推想周制者:“《戴記》多雜漢初著作,非獨《王制》一篇,如《大戴記·公冠》篇且明著孝昭冠辭矣。”(16)章太炎:《答吳絸齋書》,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8頁。
從師弟子之間的信函往復可以看出,雖然在具體問題上大有討論余地,但對《三禮辨名記》的基本思路,二人是高度認同的。吳承仕先生忠實地繼承了章門六經皆史的基本思路,治禮學更希望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歷史實情。其所理解的“禮是鄭學”,就在于鄭學更接近史實。而他認為唐代義疏學更有價值,就在于它是本于鄭學的疏釋;清人學術的成就,如江永、戴震、凌廷堪、金榜諸人,亦在于其對鄭學的補充,而其瑕疵則在于對史實過于主觀的獨斷:“若金鶚之《求古錄》,每每自出新解;孫仲容作《周禮正義》,大抵崇信金說,以為折衷。黃以周《通故》,引舊說既不具,每事皆有獨斷。后學執是數家,欲窺鄭學之本真,難矣。”(《三禮名物》)正是基于對經學史的這一判斷,他規劃自己的著作時,準備于經文之外,僅列鄭注,摘錄孔、賈之疏,唐疏中的繁蕪之處尚且刪去,后儒駁正之說,更因增加糾紛而不征引。吳承仕相信這一做法將使他自己的著作優于《禮書通故》。蓋《禮書通故》本非史學著作,其目的不在考證史事,而在建構經學體系。喬秀巖教授曾對比《周禮正義》與《禮書通故》二書,認為《禮書通故》因建構經學體系而成為一部經學著作,黃氏為成全其經學體系,不惜歪曲語法,而《周禮正義》則以“析義平實”為特點,不會有這樣的曲說,因而也就較少主觀判斷,不構成一個經學體系。而經學之為經學,正是因為有經學體系,而不僅僅是文字典制的考證,鄭學作為最重要的經學體系,正是如此(17)喬秀巖:《〈周禮正義〉的非經學性質》,喬秀巖、葉純芳:《學術史讀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第359頁。。但喬先生的判斷與吳先生顯然不同。在吳承仕先生看來,《周禮正義》的問題在于崇信金鶚而有折中之說,《禮書通故》之病正在獨斷,孫氏之學似較黃氏為優。其之所以獨與《禮書通故》對比,是因為《三禮辨名記》與《禮書通故》的內容更接近,都是禮學通書,而非《周禮正義》那樣的新疏。不過,太炎與吳承仕二先生之看重史實與孫氏不同,他們并不滿足于考證文字與制度,雖然這些是他們的起點和重要基礎。說《周禮正義》沒有經學體系則可,說吳承仕沒有理論體系方面的考慮則不可。雖然其理論體系未能完整呈現,但其史學態度并非僅限于收集史料,而有一種基于經學的史學理論。將《三禮》放回到歷史中,再以唯物史觀來解釋這種歷史的發生,是吳承仕先生接受了唯物史觀之后其禮學研究的發展路徑,而這一態度實與其對待《三禮》的學術態度一脈相承。在接受唯物史觀之前,他既對過于主觀的經學體系不滿,也不滿足于僅僅從事史料考證。這應當就是他對鄭學持兩種態度的原因,只是他尚未找到一種理論視角來解說自己的經史思想。在1930年以后,這個理論視角漸漸成熟,《文史》中的小文章里呈現出的歷史觀,與《三禮名物》中的禮學態度,實是互為表里。
吳承仕先生對鄭學傳統“以異代法通之”有較大意見,更拒絕過于主觀的理論體系。這一點,在他的《尚書》與《易》等經學研究中,也有透露。盡管從史學角度看待經學,以重新講述中國的經史傳統,特別是《三禮》之學,在晚清民國時期是一個非常強勁的趨勢,如王國維、顧頡剛、郭沫若等皆是,但他們之間還是有相當大的不同。吳承仕先生代表的方向,雖來自章門的史學態度,卻是現代治經學者應有的一個學術出發點。正如在經過19世紀以來的學術洗禮之后,西方學者必須遵循基本的客觀性才能進行學術研究和思想表述,在經歷了清代考據學的流行和民國時期現代學術的確立之后,過于主觀的附會在中國已經無法被學術界接受了。偏主觀附會的思想傾向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可能有很大影響,但生命力終究是短暫的。如康有為以西式烏托邦思想附會大同、太平世之說,以托古改制說講《春秋》公羊學,其思想余波雖仍有巨大影響,但其猜想往往沒有根據,在學術上是無法成立的。顧頡剛的疑古思想本身則代表著一種現代學術的批判精神,其方法在學術上是成立的,其論證與結論是具體可驗證的,所以在大量考古發掘和出土文獻面世之后,很多結論是可以修正的(18)張京華:《古史辨派與中國現代學術走向》,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3頁。。吳承仕先生的研究與王國維先生更類似一些,在受過現代學術思想的洗禮的同時,其學術基礎卻是對中國史實的精密考證,有理論的旨趣,但并沒有過于牽強的附會,因而也就不會隨著新史料的出現和新理論的產生而被輕易淘汰。
在完成于1933年的《三禮名物略例》中,吳承仕先生比較清晰地講了他寫《三禮名物》的思路,將與太炎先生討論的成果落實在了著作中。其言《三禮名物》一書的宗旨云:
《三禮》名物之學,職在考古,一以實事求是為歸,整比成文而斷之以律令,齊此則止,師說同異,非所宜問也。今不用此術者,以禮為鄭學,不明其條貫,則始基不立,一也;后儒新說,尋覽未周,意為取舍,轉多疏失,二也;立破二家,各于其黨,非淺學所能折衷,三也;是故今所撰述,一準鄭義,鈔次注疏,不加裁斷,蓋為己之意少,而為人之意多,誠欲傅于焦氏《便蒙》之班,為后生開發頭角。非偷取漢學之名以自賁飾也。學者既明鄭義,次取群經史傳之文以相證明,次取宋、清諸儒攻難之言而觀其得失,以是持論議禮。其庶乎蹈諸大方矣!
誠如王銳先生指出的,“職在考古”乃是吳承仕先生對自己治禮學之宗旨的基本概括,也是他對太炎先生“六經皆史”說的繼承(19)王銳:《從經史之學到馬克思主義史學——吳承仕的學術旨趣及其古代社會論》,《福建論壇》2022年第5期,第164頁。。在這段陳述中,他也相當清晰地講出了其“職在考古”宗旨下的一些具體考慮和做法。“職在考古”應以實事求是為歸,而不能僅僅限于漢、宋師說家法。所以,他反對盲目崇漢的鄭學學者,但又以“鄭義”為準,不加裁斷。這一態度并非佞鄭,而是因為鄭學更接近歷史真相,而不似后之新說,“尋覽未周,意為取舍,轉多疏失”。其他經史典籍,以及宋、清諸儒之論,不是用來為鄭學辯護的,而是為了與鄭學相印證比對,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從中發現鄭義之誤,但鄭學之主體應是最接近古史真相的,所以他說,“而《三禮》則通尊鄭氏,自爾迄今,更無異論。疏家皆謂《三禮》為鄭氏一家之學,良有以也”(《三禮名物》)。
尊鄭而又自稱職在考古,這在無論當時還是今天的許多史學學者看來,恐怕都很難算是“實事求是”。而且,吳承仕先生于《三禮名物略例》開篇即言:“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授之成憲,俾施于邦國。”他仍然篤守古文經學家法,深信《儀禮》《周禮》為周公所作,這顯示了吳承仕先生作為一個尊鄭的禮學學者的基本立場。在1930年代,仍然相信這一點的現代學者可謂少之又少。
與此同時,吳承仕先生又接受臣瓚之說,以“三百”“三千”為《儀禮》之目,而不接受鄭氏以“三百”指《周禮》,“三千”指《儀禮》之說。鄭氏此說的主觀附會色彩自不待言,鄭氏之所以對“三百”“三千”做出這樣的詮釋,正是基于以《周禮》統攝《三禮》,復以《三禮》統攝群經的經學體系考慮。吳承仕先生不接受這一點,即不接受鄭學的經學體系。但對《周禮》《儀禮》為周公所作的接受,表明他至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接受了鄭學的歷史觀。陳壁生教授指出,“禮是鄭學”一個相當深刻的學術后果,表現為鄭氏確立了理解三代歷史的一個基本模式(20)陳壁生:《經史之間的鄭玄》,《哲學研究》2020年第1期,第66頁;《經學詮釋與經史傳統的形成——以殷周爵國問題為例》,《哲學動態》2021年第2期,第73頁。。對三代歷史的分期與判斷,本是經學理論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章、吳師弟子雖然努力辨析鄭氏對三代歷史的敘述,但只是否定了其中過于牽強的一些說法,仍然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其歷史觀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他們不會像胡適、郭沫若、顧頡剛那樣,將古人的歷史敘事徹底打散為史料,重建對歷史的一套新表述。吳承仕先生在《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與井田制》中也提到其對三代歷史的基本態度:“現在所存的文獻,當然以周代的為最多而又比較可靠。周人每言及夏殷制,大抵是據周而上推的,甚至如鄭玄又是據他個人意見而上推的。我們在沿革比較上,不得不涉及唐虞夏殷,而大體總以周代為本。”(21)吳承仕:《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與井田制》,《吳承仕文錄》,第73頁。他對周代以前的史料雖不很確信,但對唐虞夏殷的沿革并無懷疑,對現存周代史料更是認為大部分可靠。這里有意無意地繼承了傳統經學的一些基本理念。
可見,吳承仕先生的“職在考古”,固然不會如古人那般以經為常道,但也并非將經學僅僅化約為史料,而是力圖為進一步的理論解釋打下基礎。他說:“禮之事類有四:曰禮意,曰禮制,曰禮器,曰禮節。”(《三禮名物》)這應當是其禮學研究的一個非常基本的分類方式。若是僅將經學當作史料,恐怕就不會將“禮意”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吳承仕先生之所以將名物當作自己的主要研究對象,并非真的如清代漢學末流那樣,以訓詁、器物、制度為主要關心的內容,而是因為“夫禮意易推而多通,禮器難言而有定,然形體不存,則制作精意,即無所傳離以自表見,故考跡舊事者,應以名物為本”。禮意當然是禮學的最終落腳點,所以他將它列在第一位,但是禮意過于空泛玄虛,很容易陷入相對主義的狀態;至于器物,后人不得見實物,因而就不好理解,但一旦明白了,那就是確定的,禮器確定了,其中的禮意也就確定了。通過考證禮器以明禮意,這是《三禮名物》的真正旨趣,實與其鄉賢戴東原的說法非常類似:“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22)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東原集》卷一一《戴氏雜錄》,戴震撰,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第6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第498頁。這一態度甚至可以追溯到朱子的格物窮理之論。在乾嘉學術初期,考證之學本有義理追求,只是因為考證煩瑣,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而學者往往未能走出考證階段、達致義理層面,或是義理之學的深度遠遠不及其考證之學之精,其義理之學遂湮沒不聞;民國時期的很多學者同樣如此,其治史學本有理論的規劃,但理論未能得到充分展開,考證部分反而更為人重視,吳承仕先生便是其例。而今我輩研習其學說,當更深入體會其總體規劃,既為理解其人其學,更為我輩今后之學能更上一層樓。
吳承仕先生由名物以求禮意的學術路徑,與宋學、清學皆有相似之處,只是其所理解的“禮意”與之有所不同。此時已經接觸歷史唯物論的吳承仕先生說:“言不虛生,事不空作,制度有廢興,器數有隆殺,必有其廢興隆殺之故,此禮意也。”后文又說:“事勢異則法度有變更。”這無異于以文言文轉寫了“人們因受了某種客觀條件的拘束或某種客觀條件的需要,即規定了人們應該作的工作”(23)吳承仕:《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與井田制》,《吳承仕文錄》,第72頁。。事實上,在同時期寫作的語體文中,吳承仕先生更加明確地講過,他研究《三禮名物》的目的,就是要從中發現周代的意識形態。他談道:“我是浸淫于所謂‘正統派經學小學’的很小范圍中費時甚多而心得較少的一人,雖企圖著將舊來研究所得的材料,用一元論的歷史哲學,從事于中國社會發展史中之某一部分工作,從實踐來證明理論,這當然是我們責無旁貸的‘歷史任務’。”(24)吳承仕:《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與井田制》,《吳承仕文錄》,第70頁。他還這樣表達對鄭學的態度:“漢儒如鄭玄等,當然有很多牽強拘泥之處;然而并不如近人所說‘豆腐干塊式’的井田,絕無可行之理。”(25)吳承仕:《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與井田制》,《吳承仕文錄》,第73頁。
三、作為意識形態的禮意
吳承仕先生究竟會如何更系統地闡釋其對古代社會的總體理解,我們不可得而知。細讀吳承仕先生的文稿可知,對如何運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特別是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他有相當深入的思考。雖然吳承仕先生僅將禮意當作某一時期的意識形態,但由于他非常深入真切地體會禮意,對過于牽強的現代解釋,他是非常反對的。他對同時代學者的一些研究,也是很不滿意的:
當新興社會科學風起水涌大行其道的現在,對于中國古代歷史,有多數學者正應用新的利器,努力從事于“自己的園地”的工作。這工作的收獲怎么樣,在藏身于另一“象牙之塔”之內的我們,當然沒有批判這些問題的資格;但是,據我一瞥所及:很有用一定的理論方式,作為下層基礎,而建筑起彈指即現的空中樓閣來的,這種建筑物,怕不見得有金城湯池那么穩固罷。……對于用新方法來講中國古史的學者,不幸發現了它的援引不當或解釋錯誤,不待看完全書,對他總不免要起一種“不信任”的反感。(26)吳承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者對于喪服應認識的幾個根本觀念》,《吳承仕文錄》,第11-12頁。
最為遺憾的是:中國人以不成熟的作品去欺騙外國人,又將外國人雖努力研究,因為根據不甚可靠的材料,以致產出“似是而非”的作品,轉譯為中文以欺騙不成熟的中國人,不問其為意識非意識的,似乎對于現代學術界,皆應負相當責任。(27)吳承仕:《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和井田制》,《吳承仕文錄》,第72頁。
徐協貞的《殷契通釋》,就屬于他尤其反對的一類研究。徐著認為,殷代前期是舊石器時代,混亂部落社會,兩性雜交血族群婚,過著游牧生活,屬生食人時期,后期則是新石器時代,王朝部落社會,亞血族群婚,農業萌芽,屬熟食人時期。吳承仕先生諷刺他說:“然而他老先生最得意最精彩的發現,卻完全在殷朝是由生吃人進化到熟吃人的一個六萬年前原始野蠻社會這一點,較之亞血族群婚諸說之拾人——郭沫若——牙慧者,真是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成績呵!”(28)吳承仕:《介紹天下第一奇書——徐協貞先生新著殷契通釋》,《吳承仕文錄》,第57頁。筆者未見吳承仕先生對郭沫若著作的直接評價,但從這兩處來看,他應該是認為郭著雖不像徐著那么荒謬,但同樣是向壁虛構。太炎先生在答復吳承仕先生論喪服的書信中,曾提及母系社會;吳承仕先生從范文瀾處最早讀到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即《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而且應當是受到過很大的影響,但在自己的著作中,他從來都謹慎對待這些理論資源。就在批判徐著的這篇文章中,他也并未否定摩爾根和恩格斯的理論,只是認為以此來解釋殷代歷史是不合適的。
徐協貞、郭沫若算是比較極端的例子,對陶希圣等人,他同樣有非常深入的批判。《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者對于喪服應認識的幾個根本觀念》就是針對陶希圣而發的。在民國學者中,陶希圣先生也是對喪服比較重視的,但在吳承仕先生看來,他在《婚姻與家庭》和《中國古代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對喪服制度的討論,充滿了錯誤。正是為了糾正這些錯誤,他才在文章中詳細梳理了喪服制度的一些基本原理。
徐協貞、郭沫若等的問題,在于粗暴地用外來理論解釋中國歷史;陶希圣等的問題,則在于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常識有錯誤理解。兩種錯誤截然相反,卻同歸于謬。那么,吳承仕先生自己所服膺的研究方法,應該是怎樣的呢?我們看他的幾項研究。
在刊于《文史》一卷二號的《語言文字之演進過程與社會意識形態》一文中,作為章門弟子的吳承仕先生,特別展現了其文字訓詁的精深功底。以語言文字來展現意識形態之形成與演進,這在當時的左派學者中是獨樹一幟的關于這一研究進路,吳承仕先生表示:“世界上現有的一切文化,無疑的建筑在工作與語言這個歷史進程上面;同時我們研究我們列祖列宗的工作成績與其反映于上層的意識形態,除古物遺留及地層發現而外,自然以語言文字為唯一而可靠的材料。”(29)吳承仕:《語言文字之演進過程與社會意識形態》,《吳承仕文錄》,第45頁。語言文字作為為社會發展變遷之遺存,因而是研究歷史過程與意識形態的寶貴資料。他將太炎先生《語言緣起說》與摩爾根的人類學理論相結合,在研究過程中大量借助中國古代文獻中關于語言文字的論述。吳承仕先生說:“語言文字的名與實在時間空間兩方面,無一處不存在著它的辯證的矛盾性;我們恰好應用社會科學的條例,去發現、研究、說明這些矛盾性,作為‘幫助認識社會階段’的一支效率最大的生力軍,這是現代語言文字學家的歷史任務。”(30)吳承仕:《語言文字之演進過程與社會意識形態》,《吳承仕文錄》,第55頁。在他自己的許多文章中,吳承仕先生非常關心語言問題,注意從文字訓詁的角度檢討事物和制度的緣起與發展,自覺將這一方法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如《我所認識的大眾語運動的路線》,是對語言文字現代化的思考(31)吳承仕:《我所認識的大眾語運動的路線》,《吳承仕文錄》,第84-101頁。,《從〈說文〉研究中所認識的貨幣形態及其他——‘中國語言文字與社會意識形態’之一》和《從〈說文〉研究中所認識的交換形態之史的進展》都是基于扎實的文字訓詁所做的社會經濟史研究(32)《從〈說文〉研究中所認識的貨幣形態及其他——“中國語言文字與社會意識形態”之一》《從〈說文〉研究中所認識的交換形態之史的進展》,分別見于吳承仕:《吳承仕文錄》,第139-148、218-222頁。。
唯物史觀的出發點是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分析。吳承仕先生《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與井田制》一文,即著眼于此,并嘗試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中國古代史中的這對關系。這篇文章并非成熟的研究,而是對未來研究課題的一個設想。他辯證地接受了兩條理論原則:首先,承認“在某種生活階段中,即形成與某種生活階級相適應的上層意識形態;于是乎奠定了我們所確信的一元論的歷史哲學的基礎”,但又認為,“在統一歷史階級中的社會,不妨因她的種種特殊的客觀條件,而顯示出她的種種特殊形式”。考慮到人類社會發展史的普遍規律和特殊情況,他更愿意接受亞細亞生產方法的說法,而對李季、郭沫若、胡秋原等解釋中國社會史的理論,則都持保留態度。在檢討了中外許多相關研究之后,他將自己課題的內容限定為四個方面:“一,經學家對于唐虞三代之封建沿革的傳說與批判;二,《周禮》中所見的與孟子所說的封建制的異同;三,井田制;四,溝洫制。”(33)吳承仕:《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與井田制》,《吳承仕文錄》,第69、74頁。雖然這項研究未能完成,但在兩篇關于《說文》的文章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他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問題思路的展開。
此外,其《士君子——中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論之一》一文,既充分運用其語言學知識并結合歷史考證,考察士的地位,更以唯物史觀的階級分析思路,將士理解為封建社會的剝削階級(34)吳承仕:《士君子——中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論之一》,《吳承仕文錄》,第124-132頁。。
在以上這些研究中,吳承仕先生堅持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立場,這在其關于經濟問題和論士君子的文章中尤其明顯。同時,他的研究因為基于其對文字、文獻、經學的深入理解,所以都緊緊扣在禮學的基本問題上。他很少將外來理論中的一個命題強行套在中國材料上,所關心的問題也往往是傳統禮學本就重視的問題,而只是采取了另外一種解讀方法和理論解釋,他的結論或許皆可商榷,但他的研究都是鮮活而有力的。
四、檢齋喪服學
在吳承仕先生對古代社會的所有研究中,喪服人倫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是中國禮學傳統中最核心的內容。在“五四”之后,青年學生對倫常一類說法往往不屑一顧,但吳承仕先生說:“我以為五倫這個概念,是我們歷史上的精神文化,也就是某時代的社會意識形態;既把它認為社會的上層建筑,當然有它的緣起、演進、變遷,種種過程,以及它與當時社會適應的緣故。”(35)吳承仕:《五倫說之歷史觀》,《吳承仕文錄》,第1頁。
而這也是其遺著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今天仍然會影響到我們的研究,我們因而也特別需要認真對待。這類研究包括《三禮名物》的主要部分和在《文史》創刊號上發表的那兩篇文章。雖然吳承仕先生自己說過前者只是文獻檢討篇,而后者被黃壽祺先生歸入史實審定篇,但這更多是就寫作方式而言,而非在實質上將兩者判然二分。如前所述,這兩部分的最后完成是在同一時期。如果假以時日,吳承仕先生一定會完成更系統的“史實審定篇”,而非僅僅這樣幾篇小文章。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將這兩類內容交互對照,以理解他的這部分研究。
在1929年致太炎先生書中,吳承仕先生談到,《三禮辨名記》將會包括“封建、制祿、井田、宮室、車服、時祭、間祀等數十題”,黃壽祺先生也談到,其《三禮名物筆記》已列出了46個門類(36)黃壽祺:《略述先師吳檢齋先生的學術成就》,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周年紀念文集》,第133-134頁。。但在我們今天見到的《三禮名物》中,卻只有車輿、布帛、弁服、喪服、親屬五題,宮室名物則僅見存目。這距離他的計劃還差了很遠,但應該也能體現吳承仕先生最核心的關切。除較早完成的《釋車》和僅有存目的《宮室名物》外,與喪服相關的布帛、弁服兩部分,可以說是討論喪服的形制基礎;親屬部分,則是由喪服部分推展出來的人倫網絡。在體例上,除《釋車》廣引清儒之說外(37)據其《釋車自序》說,《釋車》是首先寫的,由講義修改后,于1936年正式刊于《國學論衡》。《釋車》與其他部分體例有異,或即因為寫作較早。,其他部分都盡可能只摘錄孔、賈二疏。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者對于喪服應認識的幾個根本觀念》一文,雖為批駁陶希圣而作,卻也簡明地講出了吳承仕先生所理解的喪服理論的基本原則:一,喪期之單位,指出以期為基本單位的五服等差;二,至親以期斷,明確以至親期服為基本單位的原理;三,外親之服皆緦,因父權社會而來;四,親親與尊尊,喪服六術的基礎;五,至親以期斷加隆為三斬衰,即三綱服;六,同姓從宗與異姓主名(38)以上內容分別構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者對于喪服應認識的幾個根本觀念》的第三至八節,為方便論述,筆者在此將其另標號為一至六。。《五倫說之歷史觀》更是突出討論了至親以期斷與加隆的問題,將五倫與三綱歸于喪服制度。這兩篇文章的內容,是對《三禮名物》中的《喪服要略》十章之內容提綱挈領的概括,而《喪服要略》則是吳承仕喪服學一個更系統、更專業的闡釋。
《喪服要略》雖非《三禮名物》中完成度最好的,卻也是精心撰述的部分,呈現了吳承仕先生長期思考喪服問題的成果。其十章分別是:第一,明喪服緣起;第二,明《喪服》經傳誰作;第三,明五服等差;第四,明喪服為上下通禮;第五,明降、正、義衰服精粗;第六,明正服绖帶差數;第七,明衰裳之制;第八,明五服變除;第九,明服術有六;第十,明降服條例(39)較早期的《禮服要略》(收入鉛印本《絸齋講義》,藏于北京大學考古學院圖書館)分章略有不同:五服等衰分第一;降、正、義衰物精粗分第二;五服绖帶差數分第三;衰裳制度分第四;服術有六分第五;明降服條例第六。這是一個過渡性的形態,十章的分法顯然更成熟。。此中討論的,都是非常傳統的喪服學問題,甚至其體例和語言,都是模仿賈公彥《喪服疏》中的七章而來:
第一,明黃帝之時,樸略尚質,行心喪之理,終身不變;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樸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為限;第三,明三王以降,澆偽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第四,明既有喪服,須明‘喪服’二字;第五,明《喪服》章次,以精粗為序;第六,明作傳之人,并為傳之意;第七,明鄭玄之注,經傳兩解之。
這段話是賈公彥喪服學,或其所繼承的魏晉喪服學的理論提綱,其核心是前三章,建構了黃帝以來的喪服發展史,以說明三年喪的道理(40)參見吳飛:《人道至文——〈禮記·三年問〉釋義》,《史林》2016年第3期,第41-49頁。。吳承仕先生從他的史學觀念入手,自然認為這段歷史沒有根據,因而以“喪服緣起”一章取代之。他的看法是:“唐、虞、夏、殷,雖有三年之制,而文獻無征。然則親疏之等,族姻之辨,齊斬升降之衰,歲月變除之節,至周世而大備,可知也。”吳承仕先生并沒有全然否定上古有三年喪的可能,但仍然堅持喪服制度至周代才完備而確定。至于《三年問》中取象于天之說,他的評價是:“象天地,法五行,乃秦漢間老生之常談,制法本意慮不在是。”
第二章對應賈疏中的六、七章,討論《喪服經傳》的作者問題。其開篇云:“《記·明堂位》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崔靈恩、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等,皆云《儀禮》周公所作。”對周公作《儀禮》,吳承仕先生仍然堅持,故并無辨析;只是對《喪服傳》是否子夏所作,論之稍詳,但言辭間仍不愿否定此說。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者對于喪服應認識的幾個根本觀念》中,他又提了一句:“我們且不管周公作經子夏作傳的正統傳說是怎么樣。”(41)吳承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者對于喪服應認識的幾個根本觀念》,《吳承仕文錄》,第13頁。這只是暫不爭論的意思,而對照其多處說法,吳承仕先生應該是并未否定周公作經、子夏作傳的說法。
第三章具論五服差等,以親親為其基本原則:“五服之等,本于親親,而婚姻之好、君臣之義,皆準是以為隆殺。”他尤其否定了心喪之說:“后人不滿于父在為母之制者,則以心喪彌厭降之闕。欲為世主文短喪之過者,則以心喪為諒闇之實,蓋皆晚世之飾說,非隆周所宜有。”
第四章以天子至庶人之服皆在《喪服》篇。第五章接受鄭學降、正、義服的區分。第六、七、八章言喪服绖帶衰裳之制、喪服變除之制,皆從鄭義。
第九章詳論鄭學所謂喪服六術,強調親親、尊尊是喪服最基本的原則,特別是在至親以期斷與加隆之服問題上,從鄭珍之說。這正是《五倫說之歷史觀》與《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者對于喪服應認識的幾個根本觀念》中的基本思想。
第十章論降服,主要內容曾以《降服三品說》發表于《師大國學叢刊》,應當是吳承仕先生禮學思想與鄭學的最大不同所在。鄭注謂降有四品:尊降、厭降、旁尊降、出降。敖繼公將旁尊降并入尊降,而為三品;閻若璩增余尊降與殤降,而為六品;鄭珍不承認余尊降,將殤降稱為年降,故有五品;黃元同先生反駁他們,認為余尊降即厭降,年降在殤服,恢復四品說。而今,吳承仕先生復論此事,以為降有三品:尊降、殤降、出降。其中,尊降來自喪服六術之尊尊,包括本尊降、尊厭降、余尊降、旁尊降四目;殤降來自喪服六術之長幼;出降來自喪服六術之出入。此說是以新的方式為降服重新歸類,以后又總結出不降的若干原則,雖不盡合鄭義,卻仍是對鄭氏喪服六術的發展。
此十章構成檢齋禮學更完備的學術框架。鄭氏喪服學的基本原則是喪服六術,至親以期斷、加隆構成其喪服推演的基本算法,而對期喪與三年喪所根據的天道之理解,則構成其哲學基礎,賈疏中推演的歷史演進,則是根據這一哲學基礎上形成的歷史敘事。與之相較,吳承仕先生非常完整地接受了喪服六術,也接受了鄭珍所闡釋的至親以期斷與加隆之說,但放棄了天道之說與歷史演進,而是將鄭氏禮意放在唯物史觀之下,認為這是周代封建制的意識形態。
五、檢齋之學對現代經學的啟示
在現代學術體制建立的過程中,中國的傳統學問都要經歷現代化重塑。如何在現代化過程中恰當地切中并詮釋傳統學問的真問題,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作為傳統學問制高點的經學,至今還未能完成這一重塑,就是因為它很難被系統地納入現代學術體制當中。現代學術中以六經皆為史料的做法,雖然看上去是對乾嘉樸學傳統的繼承,其實卻是對西方實證主義的嫁接。實證研究雖然看上去只關注具體問題,但經史研究是不可能沒有理論預設的,而只是隱藏得更深而已。乾嘉樸學背后,有在漢宋學統之間的理論權衡;現代樸學往往沒有這方面的考慮,卻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西學的理論預設。不過,優秀的學術研究自有其獨立的價值,即使承載著沉重的理論前提,仍有不可忽視的貢獻。現代學術對古代文明的研究,特別是對文獻與出土文物的發掘整理,使用樸素可靠的科學方法,為我們重新理解上古歷史及其文化,提供了豐厚的史料和文獻。正是這些方面的學術推進,為我們今日研究禮學與經學,打造了全新的學術與文化背景。
《禮記·中庸》有言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4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6頁。關于現代語境下的經學研究,筆者的基本態度是,一方面充分接受現代學科的治學原則與基本態度,另一方面盡可能從傳統學問的內部體會其思想精義,只有將兩方面融會貫通,才會有現代經學的真正成立。在這方面,吳承仕先生的做法正是我們的先聲。
太炎門下諸賢從史學的角度理解經學,既接續了經學史上的固有傳統,也與現代學術思潮相融合,是一個比較成功的做法;吳承仕先生進而以唯物史觀繼續了這一工作,并特別集中在對喪服人倫的研究上,接引我輩后學窺見禮學研究之門徑,厥功甚偉。且不說其對祧的釋義、喪服變除表、降服三品說等本就對傳統喪服學有所推進,他的理論態度和治學方式更是能為現代人所接受,可以被有效納入現代知識體系。
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回頭看吳承仕先生的研究,我們已經未必能接受他的全部結論和理論解釋,但應該沿著他的思考方向進一步推進。比如,吳承仕先生從客觀歷史的角度,而非顧頡剛式的疑古態度對待古史,卻仍相信周公為《周禮》《儀禮》的作者,子夏為《喪服傳》的作者,認為三代皆行三年喪之制,今天的學者大多已不再能接受(43)參考吳飛:《三年喪起源考論》,《文史》2020年第3期,第217-233頁。。我們根據現有的考古學和歷史學成果,盡管不再輕易否定古史,相信夏商周三代創造了偉大文明,六經即為這一文明的記錄和理論提升,卻不能再不加檢討地接受三皇五帝皆為圣王的價值判斷,這便是對吳承仕先生現代立場的進一步推進。
此外,吳承仕先生根據鄭珍之說,考證喪服制度的原理,特別是對《三年問》中“至親以期斷”和“加隆”之說有精深的討論。對此,我們認為,鄭珍與吳承仕先生恐仍未能窮盡期之喪與三年喪的理論深意,我們還需要更深入地體會鄭注、賈疏中體現的經義。吳承仕先生的藏書中有《喪服鄭氏學》一書,《三禮名物》亦頗引其說,可算是現代學者善用《喪服鄭氏學》的典范,但對其中《正尊降服篇》的義理闡釋卻未能充分重視,我們則可以有更深的發掘(44)吳飛:《點校重刊〈喪服鄭氏學〉序》,張錫恭撰,吳飛點校:《喪服鄭氏學》,上海:上海書店,2017年,第21-27頁。。
總之,吳承仕先生的禮學研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在接受現代學術體制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我們仍然可以在傳統經學的脈絡中梳理和推進,從而推陳出新,甚至使鄭學之義也能呈現出時代新義。這應當是現代經學研究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