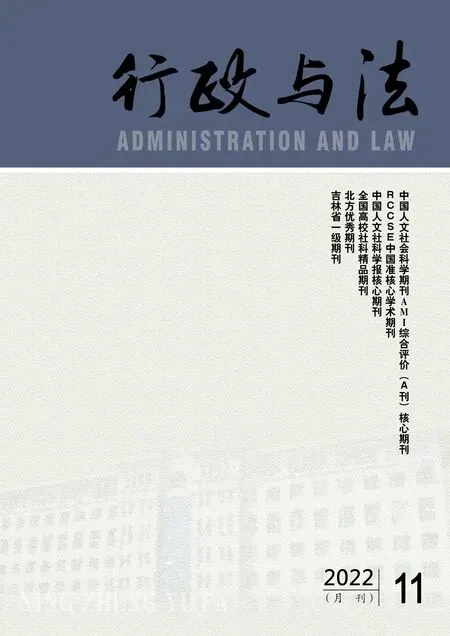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的多重嵌構與協同治理
——基于W市H街道的現實考察
□柳青
(中共武漢市委黨校,湖北 武漢 430070)
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是社會矛盾在基層社區的具象表現和集中反映。城市社區類型多樣,社區物業由于其特殊的商品屬性,涉及業主、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企業、社區“兩委”、街道辦事處及相關政府職能部門等多重利益主體。物業管理領域矛盾點多面廣,存在服務質價不符、行業監管乏力、居民自組織能力不足等問題,物業糾紛已逐漸演變成“任何單一主體都捉襟見肘的復雜問題”。[1]據不完全統計,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呈逐年增長的態勢,給基層社會治理和社區健康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的有效化解也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訪制度,完善各類調解聯動工作體系,構建源頭防控、排查梳理、糾紛化解、應急處置的社會矛盾綜合治理機制。”[2]這種綜合治理機制是協同治理理論在社會治理領域的重要體現。當下,原有的社會矛盾“大調解”①“大調解”最早源于2009年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位一體的‘大調解’工作體系”,是指通過分流機制、運用疏導手段來化解矛盾糾紛。參見熊征:《“大調解”中的司法:表達與實踐的悖論》,載《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9期。機制聯動不足,基于全周期、多主體、寬領域、全要素對基層社會矛盾化解提出了新的要求,綜合治理機制為現實中復雜的物業糾紛化解提供了宏觀指導。
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是基層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觀察窗口。本文結合我國中部W市H街道2021年物業糾紛的主要分布領域、矛盾頻次強度及關聯性要素進行分析,試圖厘清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的多重結構及主要特征,以期為物業糾紛全周期協同治理提供一個可能的分析框架并尋求制度化的解決路徑。
一、問題的提出: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治理的現狀
社區是城市的“細胞”,社區物業服務作為市場化運作、個人權利表達和基層社會自治的交互點,無疑具有復雜性,它既要體現基層社會治理的公共屬性,又要遵循市場規律、體現效率,更要巧妙地在這二者之間謀求平衡。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業主權利意識不斷增強,物業服務企業相對單一的服務供給難以滿足多元化的物業服務需求,由此產生了大量的物業糾紛。
從矛盾的特征來看,一方面,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反映了人們對美好居住體驗的向往,具有普遍性特征;另一方面,物業糾紛又與社區類型、服務規模、居住人群、心理預期等特殊因素密切相關,呈現高分化性特征。[3]物業糾紛涉及的部門和行業眾多,有市場主體(物業服務企業、開發商等)、自治主體(居民、業主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社會組織等)、行政主體(行業主管部門、相關職能部門、街道辦事處等),每一方都可能是具體矛盾事件的直接當事人,他們“集體在場”。[4]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是各種社區沖突的直接和集中反映,“現實性矛盾”與“無直接利益沖突”相互交織,[5]這就導致看起來較為單一的物業糾紛極易演化甚至容易發生“角色轉換”,[6]處理起來難度較大。
在我國的治理體系中,對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的處理是被納入到基層社會矛盾治理的“大調解”框架之中的,按照“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綜治協調、社會自治,充分發揮各職能部門作用”的原則來進行。但長期以來,與其他社會矛盾和沖突相比,城市住宅小區的物業糾紛常常被視為“對國家與社會進步具有普遍性、彌散性和基礎性作用的事務領域,也就是‘小事’治理”[7]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不同小區、各類調解主體由不同的主管部門管理,信息不暢、條塊分割的現象時有發生,表現出“碎片化”傾向。首先,物業糾紛治理的組織體系和工作機制是“碎片化”的,各種民間性、行業性、專業性的物業糾紛調解隨機性很強,效率不高。其次,組織體系與工作機制的“碎片化”必然導致糾紛處理程序、內容上的分散混亂。在處理一些復雜的物業糾紛時,由于工作的側重點不同和依據規則的差異,統籌協調難度較大。究其根本,在于物業糾紛多元治理主體之間并未實現真正的協同,大家往往滿足于表面的沖突“平息”而非矛盾“化解”,“單打獨斗”、互相推諉的局面還未真正破解。
如本文所觀察的H街道所在的W市在矛盾糾紛化解領域建立了“五駕馬車”的組織架構——社區化解、人民調解委員會、警調對接機制、行調對接機制和司法訴訟程序,但這些工作機制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獨立,并未形成系統有機整合、前后程序連貫的協同治理體系。[8]表現之一是各種矛盾訴求受理平臺并未有效整合,同一投訴被多個平臺(社區網格員、微鄰里平臺、市區長專線、城市留言板、數字城管、行風評議等平臺)反復接收,由于信息不對稱而無法有效整合調動資源,造成公共資源被重復占用,解決起來耗時耗力。表現之二是各種工作機制之間并未形成閉環,難以發揮共享、互聯、共治的優勢,導致物業糾紛處理的無序化、無效化。
由此可見,在社區類型極其多樣的復雜情境下,“碎片化”的治理結構只會把各個治理主體陷于各自繁雜的事務性領域,難以形成系統化的行動方案。由于“社區物權沖突是當代城市社區治理中最為棘手的沖突類型之一,其往往是集社區利益沖突、權力沖突、權利沖突、文化認同沖突、結構沖突、變遷沖突等于一身的社區復雜性沖突,”[9]因此,必須結合實際努力尋求治理方案。
二、樣本描述:W市H街道物業糾紛的典型案例分析
(一)W市H街道的基本情況及社區類型
W市位于我國中部腹地,是長江經濟帶核心城市和區域性中心城市,城區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正處于城市化發展的加速期,社區類型豐富多樣。本文選取觀察的H街道位于W市中心城區,地處長江南岸,是濱江文化商務區的核心區域和城市更新改造的重點區域。H街道轄區面積共14.6平方公里,現有居民近6萬戶,常住人口16萬余人,轄16個社區,劃分為82個小區(或管理區域),其中實施市場化專業化管理的物業小區44個、41238戶,老舊小區38個、16306戶。
之所以選擇H街道作為觀察樣本,是因其社區類型多樣,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H街道所轄的82個小區(管理區域)中,既有單一的單位式社區,又有新型的商品房社區;既有傳統的街坊式社區,又有混合式綜合社區;既有過渡型社區(城中村、城鄉邊緣社區),又有較為成熟的新建社區。可以說,H街道是W市的一個縮影,更是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的集中體現,為分析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的結構和作用機理提供了窗口。
(二)H街道物業糾紛的分類和主要特點
H街道作為城市社區發展的復合形態,社區類型和層次多樣,物業糾紛也經歷了從早期單純的物業費爭議到多主體間復雜多變的利益糾紛的演變歷程。據不完全統計,2021年H街道全年通過各種渠道共收到各類物業糾紛投訴1164件,較2020年增長21.4%。2022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影響,僅前三季度就收到涉及物業的投訴件1032起①相關數據來源于W市房管局物業科及H街道網格中心。,增長幅度較為明顯。與此同時,伴隨著一批新建住宅小區的交付和部分老舊小區業主委員會任期屆滿,小區業主委員會的籌建與換屆工作更成為物業管理矛盾糾紛的集中爆發點。根據2021全年的數據,H街道物業糾紛所反映的問題類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物業服務糾紛,共289件,占2021年全年投訴總量的24.83%。主要反映物業服務企業未按合同履約、費用收取不合理、設施設備維護不及時、服務態度不佳、公共收益不透明、物業費漲價等問題。二是物業管理糾紛,共377件,占投訴總量的32.39%。主要反映小區內違法建設、改造施工、噪聲油煙擾民、“膠囊房”、高空拋物、無證辦學開店等問題,大多源于小區自治與職能部門執法銜接不暢,業主多以拒交物業費方式表達不滿。三是業主自治問題,共144件,占全年投訴總量的12.37%。主要涉及業主大會的召開、業主委員會成員的選舉、業主委員會履職和運作不規范、公共維修基金管理和使用而引發的業主委員會與業主之間、業主委員會內部、物業服務企業和社區居民委員會之間的矛盾。四是開發建設遺留問題,共354件,占全年投訴總量的30.41%。主要反映房屋及配套設施存在質量問題,如墻體開裂、樓頂漏雨、外墻脫落,電梯、水箱等設施設備故障,停車位、架空層及垃圾轉運點等設施規劃建設不合理。
整體來看,H街道物業糾紛是城市基層社會矛盾的一個反映,呈現出點多面廣、多發頻發、主體多元、處置復雜的特征。根據對H街道物業糾紛與不同社區類型之間的關聯性分析發現,住宅小區物業糾紛的問題分布、發生頻次、矛盾強度、焦點領域與社區類型呈高度相關。首先,在社會關系相對單一的社區,如傳統的街坊式小區和單位式社區,由于相對熟悉的人員結構及政府兜底思維的影響,[10]此類社區的物業糾紛問題較為單一,矛盾主要聚焦在服務質量、收費標準等方面,數量和頻次相對較少,剛性化程度不明顯。其次,在社會關系較為復雜的混合型社區,如拆遷后的在建小區和城中村等,由于人員流動性大、利益訴求多元、社會分層明顯,此類小區物業糾紛燃點較低,呈高發頻發態勢,剛性化趨勢明顯,解決難度較大。[11]再次,對于新型的現代商品房小區,物業糾紛則呈現兩端極化的現象。物業服務企業實力較強、口碑較好、資源較多的小區運轉相對順暢,物業糾紛投訴的數量、頻次和強度都不高;而那些交付時間較長、沒有物業服務企業入駐或者物業服務企業更迭頻繁、治理難度較大的小區利益結構復雜,物業糾紛剛性化程度明顯,而且極易發生演化和矛盾轉移。
由此可見,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起源于日常生活,但已經不局限于現實的利益沖突表達形式,已成為集主體重疊、權利碰撞、結構嵌套、文化沖突于一體的復雜性沖突。正如有學者說:“傳統社區共同體,……那種不分你我的共同體感情,被各利益主體的經濟理性和權利理性取代,使商品房住宅區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利益場’和‘訴訟的’社會。”[12]
三、治理的難點:H街道物業糾紛治理面臨的多重困境
(一)主體重疊——“易轉換”的糾紛主體
社區是社會的縮影,廣義的社區物業糾紛涉及的微觀主體眾多,包括市場主體、自治主體和行政主體,任意雙方或多方的矛盾沖突都可能引發物業糾紛。在H街道的社區生活中,最為明顯和常見的物業糾紛是業主與物業服務企業或開發商之間的矛盾,而其他的第三方治理主體作為觀察方、干預方或調解方參與其中。從理論上講,政府要發揮監管作用,行業要發揮規范作用,社會組織要發揮協調作用,大家各司其職共同化解物業糾紛。但現實情況卻遠非如此,各治理主體由于權利、義務關系不明晰,矛盾焦點極易轉移,糾紛主體容易發生角色轉換。
如H街道下轄的B小區一期于2019年6月交付入住,合同約定的物業管理公司為前期開發商的下屬分公司。物業入駐前期,企業急于收繳物業費,而對小區公共服務的提供、公共設施的管理維護不夠盡責,業主普遍存在不滿情緒。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更加劇了這種矛盾。2020年6月,企業入駐滿一年后,小區業主因小區安全保障、共有產權部分房產管理混亂等問題,對物業公司的不滿情緒達到頂峰。為了“奪回”主動權,小區部分業主推舉代表會同小區居民委員會組織了“B小區業主大會籌備小組”,擬成立業主大會重新選聘物業公司,通過“鄰里互助”微信群商討相關事宜并征集聯名申請的業主簽名。但由于小區二期尚未交付,征集簽名人數未能達到法定人數要求,更換物業公司的計劃未能實現。很多業主便將行動未果的原因歸咎于居民委員會不作為、房管部門懶政以及其他業主漠不關心,矛盾焦點迅速轉移,“鄰里互助”群內矛盾迅速激化。
糾紛主體的重疊與轉換是物業糾紛復雜化的開端,復雜情境下業主真正的利益訴求被“稀釋”,業主與物業服務企業或開發商的雙邊矛盾也逐步擴展為業主、業主委員會、社區、職能部門間的多邊矛盾,處理起來更為棘手。
(二)自治困境——“被異化”的業主委員會
作為一種新型的社區自治組織,業主委員會是社區廣大業主利益的集中代表與體現。從功能上看,“業主委員會執行業主大會的決定事項,代表和維護全體業主在物業管理活動中的合法權益,并監督和協助物業服務企業履行服務合同。”[13]但在現實的社區生活中,業主委員會的籌備和成立卻是各方利益角力和博弈的結果。一方面,在一些新建住宅小區業主委員會籌建過程中,有的物業服務企業或開發商擔心成立業主委員會影響自己的利益,總是有意無意地拖延,不愿主動配合申請甚至人為設置障礙,從而引發業主的對立情緒。另一方面,從業主角度來看,召開業主大會、成立業主委員會的初衷并不是為了民主管理、民主決策,維護良好的社區環境,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業主維權或更換物業服務企業,這就增加了物業糾紛產生的可能性和矛盾化解的不確定性。
通過對H街道居民的調查走訪發現,只有39.2%的受訪居民表示其所居住的社區成立了業主委員會,27.8%的受訪居民表示還未成立業主委員會,還有33%的受訪居民表示“不清楚”。而在被問及“是否知道本社區業主委員會的組成人員”這一問題時,多數受訪居民表示“并不清楚”。一些受訪居民表示只見過業主委員會成員名單,并不知道他們的具體職責。還有一些居民質疑小區業主委員會與物業公司一起損害業主利益。由此可見,現實中的業主委員會并非是理想中的溝通業主、社區、物業公司的“橋梁”,廣泛存在著成立難、結構松散、運行虛化等問題,甚至異化為謀利型業主委員會或者業主與物業公司對立的“工具”,其自治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發揮。
(三)過程漏洞——“未封閉”的處理程序
復雜性物業糾紛的有效化解、就地化解,需要基層社會具備解決糾紛的制度性“閉環”。從管理學角度看,只有管理閉環才能真正保證矛盾“不上交、不外溢”。而在現實的物業糾紛場景中,社區作為一個基層自治空間,并不具備單獨的糾紛裁判和解決能力,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調解和移交機制。而當前物業糾紛的多樣化程度十分明顯、對抗化程度較高,有時候調解和移交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一旦調解不成,就需要具有更高權威的力量和更有效的機制介入才能解決問題。因此,物業糾紛治理要破除“碎片化”傾向,形成流程有機銜接的管理閉環,必須要有社區自治之外的制度性糾紛解決力量的引入。在自治困境難以突破的情況下,“一個基層的自治結構要在制度上形成封閉循環,國家的在場必不可少。”[14]但是,物業糾紛治理中一些行政主體卻在居民自組織程度不成熟的前提下“提前離場”,奉行“進了小區的門,便是物業的事”的做事態度,相互推諉責任,物業糾紛處理鏈條被無限拉長,居民的訴求難以得到及時有效的回應。
如H街道轄區內C小區2020年因化糞池堵塞導致多棟居民樓一樓住戶被淹,受災居民要求物業公司進行清理并賠償損失,但物業公司認為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市政管網的老化,不愿承擔全部責任。在區房管局、建設局、城管執法局等多家單位參加的協調會上,物業與業主就賠償問題進行調解,但最終因賠償金額未達成一致而導致調解失敗。而后,受災業主停繳物業費并采取圍堵物業公司、扯橫幅、貼標語甚至是暴力對抗等行為進行抗爭。雖然有部分業主選擇訴訟途徑維權,但卻因舉證困難而導致維權效果不理想,雙方矛盾不斷升級。此后,業主們通過集體上訪、重復信訪、越級信訪、網絡信訪、新聞媒體曝光等多種途徑向政府部門和物業公司施壓,希望政府出面解決問題。
現階段,物業糾紛的處理還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管理閉環流程,“未封閉”的處理流程也體現了物業糾紛演化和彌散的內在機理。究其根本,在于社區和各職能部門并未就這一問題建立有效的協同機制,導致物業糾紛很容易出現外溢或擴大化的傾向。在未建立有效的協同機制之前,行政力量的退出并不會自動提升社區的自組織能力,因而必須進行流程的整合和重塑。
(四)結構失衡——“不對稱”的權利義務關系
對H街道物業糾紛的持續觀察表明,物業糾紛的多重主體共同構成了一個復合的治理結構和多邊的權利義務關系,市場主體、自治主體與行政主體間既有合作、也有沖突,他們共同在物業行業領域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動態平衡。從市場的角度看,物業服務企業與業主之間以正式的物業服務合同設定了彼此的權利義務關系,形成了一個雙邊的治理結構。從社會的角度看,業主與業主委員會、居民委員會之間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形成了正式的委托代理關系,是一種正式的社會自治結構。從政府的角度看,行業主管部門、相關職能部門、街道辦事處與物業服務企業、居民委員會之間存在一種隱形的權利支配關系,也可以說是一種潛在的非正式治理結構。三種治理結構存在的差異性較大,并不能有效地契合并嵌入到基層復雜的社會結構當中,各主體之間基于不對等的權利義務關系相互博弈,由于結構匹配度較低極易產生摩擦,由此產生變形失衡、約束軟化的現象在所難免。[15]
在H街道表現出的物業糾紛中,業主與開發商、物業服務企業之間的矛盾占絕大多數,糾紛中行政主體、自治主體與市場主體之間的力量與關系并不均衡。總體來說,行政主體因其行政權力的強制性具有天然優勢,在治理結構中居于支配地位,但其規模最小。無論是物業服務企業、開發商等市場主體還是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等均要受行政權力的支配和影響。其中,業主規模最大,但由于其高度松散的原子化結構并不能與組織化的市場主體相抗衡,在復雜的治理結構中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多重治理主體能力與結構的錯位導致物業這一微觀治理空間權利義務的不均衡,發生糾紛在所難免。
四、解決的路徑: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協同治理的發展趨勢
通過對H街道物業糾紛的持續觀察可以基本了解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產生的原因、演變邏輯及治理難點。作為城市微觀治理的重要領域,住宅小區物業糾紛的有效化解是城市社區建設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要將物業矛盾防患于未然,將風險化解于無形,必須破解“碎片化”治理困境,堅持源頭治理、預防為主,將多重治理主體有效嵌入到規范的治理框架中,形成有機協同的治理結構。
(一)發展方向
⒈注重前后銜接,把握矛盾發展的全周期性。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的產生發展演變有其內在規律,它是伴隨我國社會轉型和深度變遷而出現的新的問題,重疊性強、異質性高。只有把物業糾紛的產生發展視為一個動態、開放、演變的生命體,強調系統治理和源頭治理,注重從系統要素、結構功能、運行機制、過程結果等層面進行全周期統籌和全流程整合,才能創新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的治理思路,為治理方案提供科學指引。
⒉聚合各方力量,強化糾紛化解的多協同性。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的有效化解需要多元主體的參與協同,遵循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則,構建一體化、程序化的多元解紛機制。當前,由于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治理存在“碎片化”傾向,基層組織、行政機關、行業協會等力量分流化解矛盾的作用相對弱化,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聚合各方力量,將各矛盾化解主體納入統一平臺,構建多維度、立體化的協同網絡,充分發揮多重矛盾化解機制的協同作用,尤其是要突出基層黨組織在糾紛化解中的重要作用,打通矛盾糾紛化解的“最后一公里”,形成層層分流、源頭化解的良性運行機制。
⒊堅持多方聯動,突出治理機制的系統性。破解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是一項多元協同的系統工程,需要立足頂層設計和源頭系統建設,把現有的隸屬多個部門的矛盾化解機制整合起來,調動多個主體的積極性,共同面對新矛盾、解決新問題。充分運用依法治國和基層自治的思維,始終堅持法治、德治、自治相結合,不斷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形成管理閉環,扎實做好物業矛盾糾紛的事前預防、事中處置和事后反饋工作。
(二)具體路徑
解決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關系到社會建設和民生保障,其關鍵在于重構物業糾紛領域行政主體、市場力量與自治力量的關系,探索建立政府職能部門、行業主管部門、社區、業主、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企業、開發商共同參與的協同治理機制。逐步建立物業糾紛長效常態化解機制,力爭以小區業主委員會為樞紐,以居民依法自治為前提,構建涵蓋開發商、業主、物業服務企業、社區等各方力量的糾紛處理框架,提高基層社會治理能力,及時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從而營造和諧、平安的社會環境,切實提升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⒈完善物業領域法律體系,進一步細化權利義務。化解城市住宅小區物業糾紛的關鍵在于對業主這一規模大而又相對松散的權利主體予以賦權,以實現對物業服務企業等強勢市場主體的制衡。我國《民法典》將物業服務合同從無名合同轉化為典型合同,極大程度上增加了業主權利。[16]這一規定有效平衡了自治主體與市場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為物業糾紛從源頭上減量奠定了基礎。為有效化解物業糾紛,各地還應根據實際制定并修改地方性物業管理條例,對各利益主體的權利義務進行細化。一是對相關法律中概括性、原則性的規定進行細化,進而充分合理分配權利歸屬和規范權力行使方式,如明確規定“住改非”的程序和共有產權的管理權限等。二是按照《民法典》所規定的物業服務合同標準,進一步優化物業服務的合同樣本和相關條款,平衡業主與物業公司之間的關系,明確雙方的過錯舉證責任,確保業主的權益切實得到保障。三是明確業主自治的組織結構、運行規則和操作流程,如進一步細化業主委員會職能及其內設機構、允許業主委員會代表全體業主提起訴訟、允許業主大會產生對業主委員會的監督機構等,使業主自治實現真正的職能回歸。
⒉強化業主自我服務意識,進一步提升參與水平。物業服務與其他服務行業相比具有服務的綜合性和持續性、受眾的廣泛性和差異性、消費的即時性與無形性等特點,這就需要廣大業主樹立正確的質價相符理念和自我服務意識。社區居民和廣大業主既是物業糾紛產生的直接利益主體,同時也是矛盾化解的重要力量,具有主客體的同一性。要降低物業糾紛的發生率,必須從業主參與實現自治入手。一是通過各種方式如街道、社區和基層司法行政部門開展以案說法、釋法析理等多樣化的活動提升業主的法律意識、房屋管理意識和共有財產意識,切實提升業主自治意識和自治能力。二是注重社區共同體意識的培養,強化居民的公共意識及對社區的認同感。通過參與社區規劃、社區決策共謀等活動來引導業主對社區公共事務的關注與參與,進而提升居民的共同體意識。三是引導居民中公道正派、熱心公益的“意見領袖”參與社區治理,建立物業糾紛“微治理”機制,排查和處理“小糾紛”“小矛盾”。
⒊落實物業行業標準規范,進一步規范物業服務。在物業糾紛處理中,物業行業協會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物業行業協會要發揮行業自治作用和市場擠出效應,規范物業服務企業的行為。一是引入物業服務企業市場準入標準及清退機制。對前期開發商引入的物業服務企業要建立考核評價標準,并根據評價標準對物業服務企業進行分級管理。二是建立服務質量“紅黑榜”,完善物業服務企業誠信檔案。通過建立物業服務企業誠信檔案并公開相關排名的方式實現對物業服務企業的動態監管。三是要求物業服務企業加強崗前培訓,加大履職培訓力度,切實提高員工素質和服務水平,不斷改進工作方法,提高服務質量。四是推行行業市場公開評級制度,引導物業服務企業貫徹落實信息公開制度,將物業管理服務項目、服務標準、收費細則、財務收支等內容向廣大業主公示,接受業主監督。
⒋政府加強監督管理,進一步促進有效協調。要真正實現物業糾紛管理閉環,基層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必須找準自身定位,充分發揮行政主體及相關職能部門在物業管理中的協調和監督作用。相關職能部門要對不同類型的社區開展分類指導。一方面,在具備物業服務條件的小區引導業主與物業公司審慎訂立合同,組織司法所、社區公益律師組成專門的法律工作團隊,定期針對社區、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進行專業問題解析、答疑。另一方面,在不具備物業服務條件的老舊小區,社區居委會應當在街道的指導下組織成立居民自治“議事會”“群賢會”,定期召開會議,商討居民業主提出的問題,能在社區內解決的就“自我消化”,社區解決不了的“吹哨”協調解決,從而實現社區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有效避免糾紛的擴大化。同時,引導居民積極理性維權,推動“多方聯席”制度常態化落實,為業主、業主委員會、社區、物業公司、行政部門搭建溝通平臺,有效防范和化解物業糾紛。
⒌整合問題受理信息平臺,進一步實現數字治理。各種智能服務平臺的“碎片化”必然導致物業糾紛治理的低效化,因而整合各類信息平臺勢在必行。一方面,要做“加法”,加強統一平臺建設。以多元共治、分層遞進為思路,建設具備人工咨詢、智能咨詢、調解、仲裁、訴訟、司法確認等群眾側線上服務功能的統一平臺。通過線上身份驗證、遠程視頻、文字OCR等人工智能應用為支撐的平臺建設實現事項工單與各單位現有系統的銜接耦合,形成遞進式、漏斗型的分層處理機制。另一方面,要做“減法”,歸集數據采集,簡化采集程序,提升共享程度,加強數據的分析應用。通過智慧城市建設加強數字治理,持續研發數據分析模型,對不同類型物業糾紛進行分析比對,探索不同應用場景下化解物業糾紛的智能化運用。借助大數據分析建立風險研判預警機制,提前對可能發生的、涉及面較廣的物業糾紛進行預警,排查風險隱患。同時,還要對各類物業糾紛及化解方案進行智能整合應用,形成關鍵知識庫和工具庫,構建矛盾糾紛化解的知識生態體系,為物業糾紛化解和決策制定提供依據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