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選擇與照顧負擔
劉捷玉
無論生育政策如何調整,它所對應的生育服務配套措施如果不能及時跟上,不僅無法緩解生育率下滑,而且很難得到中國職業女性及其家庭的普遍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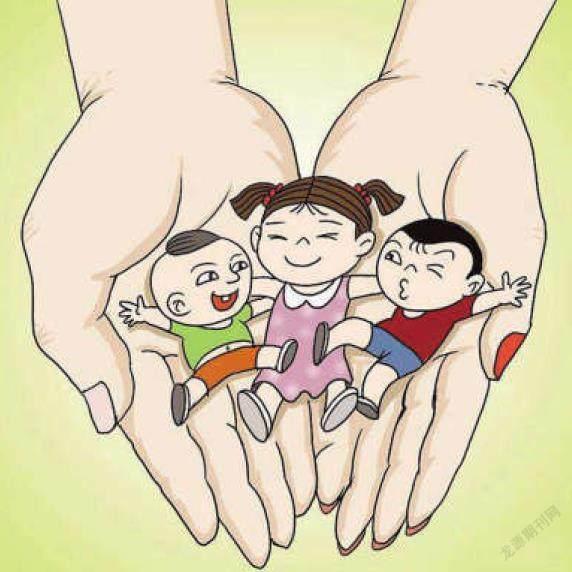
“三孩”政策實施后,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緩解中國不斷下滑的生育率,依然是尚存爭論的話題。但唯一能確定的是:無論生育政策如何調整,生育政策所對應的生育服務配套措施如果不能及時跟上,不僅無法緩解生育率下滑,而且很難得到中國職業女性及其家庭的普遍歡迎。
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目前引起了社會上下廣泛的擔憂。誠然,人口老齡化是全球各國所面臨的共同挑戰,但中國的情況尤為嚴峻且特殊。
一方面,中國人口基數龐大,人口總量占全球總人口將近五分之一,這意味著老齡人口的規模將極為龐大。根據2021年5月11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國60歲及以上的人口規模已經達到2.6億,占總人口的18.7%,而這一數據估計將在2050年達到5億。
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依然是一個人均收入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正如李克強總理指出,中國目前依然存在6億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如果不采取措施,“未富先老”的人口格局將不利于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 雖然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了中國居民的預期壽命,但“一孩化”的獨生子女政策是導致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這項于1979年正式出臺的計劃生育政策,通過超生罰款、上環避孕等舉措在城鎮地區得到嚴格而有效的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出臺,無疑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反映了當時的中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對人口不受控制增長的擔憂。
對獨生子女政策的評價至今眾說紛紜,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最早一批的獨生子女也開始為人父母。他們同時肩負著照顧子女、父母甚至是祖輩的責任。
為了應對這種倒金字塔的人口結構,中國2015年開始實施全面兩孩政策(這項政策主要面向城市人口,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家庭被批準在第一胎生女兒的前提下生二胎)。? ? 但是,像在北京、上海這種超大城市,由于托育服務不足以及生活成本的增加,只有5%-6%的家庭選擇生二孩。
生育選擇的城鄉之別
哪些家庭可能會選擇三胎?
根據筆者一項對中國城鄉家庭生活長達五年的田野研究,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城市第一代獨生子女夫婦,即使符合二孩的生育資格前提,也僅有少數的家庭選擇二孩。因此,“80后”家庭不太可能去享受三孩的政策紅利。
而出生于上世紀90年代的已婚受訪者更加適應獨生子女文化,他們本身對二孩已采取觀望的態度。其中一個受訪者(1991年生)曾與筆者分析在二孩決策過程中的猶豫:
“我們可能會選擇生二孩,但不會做最后的決定。如果我妻子在帶孩子的過程中辛苦又受罪,那我們肯定不會選擇生二孩。我很多朋友在第一個孩子出生前都對再生一個充滿信心,直到孩子真的生下來了,卻開始猶豫退卻。我覺得是否生二孩還是要取決于未來的經濟狀況,以及我們的父母是否健康。”
如果說城市家庭的生育決策更多出于經濟成本與時間精力上的考慮,那么在農村中,文化習慣依然發揮著影響。筆者的田野材料觀察到,城市地區的年輕夫婦沒有表現出對兒子的強烈偏好,但是在農村,雖然對女孩的教育投資有所增加,但“重男輕女”的文化偏好依然存在。
許多農村已婚的“80后”“90后”夫婦已經有了第二個孩子,他們是否會對新的三孩政策有積極的回應,更多取決于現有兩個孩子的性別——如果一對夫婦的兩個孩子都是女孩,那么他們極有可能想要第三個孩子。
此外,中國南北地區間的文化差別可能帶來特定的生育偏好。相比北方,中國南方一些地區擁有濃厚的宗族文化傳統。筆者在福建南部地區的農村調研中發現,為了生一個男丁延續香火,這些“90后”村民已經生了三到四個孩子。
當前,“三孩”政策在互聯網上引起討論的熱潮。一些觀點開始反思計劃生育政策,尤其是上世紀末期在廣大城鄉地區嚴格執行的計生舉措。
而另一些觀點則熱議新人口政策對就業、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尤其就職業女性而言,育兒依然被認為是女性的天然責任,三孩政策很可能產生非預期的性別不平等效應。例如,為了照顧“接二連三”的子女,職業女性只能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轉向無薪的家庭主婦角色。
而對女性生育的預期,也會影響到未生育女性的職場權益。當前,性別歧視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上深深地制度化了。文化創意企業泡泡瑪特,近日就被曝光在職場面試中僅要求女性填寫近期是否有生育計劃,并填寫計劃時間。
在筆者的訪談中,當被問及是否計劃要第二個孩子的時候,一些受訪的職業女性表示,受雇企業不愿承擔她們的生育成本(例如,產假所產生的崗位空缺),這使得她們很難做出二孩的生育決定。
以上材料說明,除非能系統性地解決勞動力市場上的性別歧視問題,否則選擇生三個孩子將對婦女的就業權益產生負面影響。
除了女性可能面臨額外的照顧壓力,老年父母也面臨同樣的壓力。三孩政策的出臺是為了緩解社會人口老齡化負擔,但在個體層面,中國城市當代雙職工家庭的兒童照料往往離不開家庭長輩的代際支持——三孩反而成為老年群體的負擔。
尤其是當前城市三歲以下的兒童托育市場化服務嚴重欠缺,當新媽媽的產假(四個月左右)結束后,她的母親或者婆婆(男方的媽媽)需要承擔起新生兒的照顧責任。不僅如此,由于缺乏充分且高質量的養老服務,這些處于60歲初段的老年人還需要同時親自照顧自己的父母。
正如一個網絡段子里寫道:“63歲的清晨,7點的鬧鐘響起,去三個房間看了看三個孩子是不是都乖乖在家睡覺,幫九個孫子孫女做好早飯,再去兩個房間看一眼四個老人是不是還在好好地睡覺,安心地擠地鐵去上班。”
而在農村,隨著子女外出務工,農村老年群體往往需要幫忙照顧留守農村的童年孫輩,在農村缺乏充分社會福利的背景下,這種照料負擔只會隨著數量的增加而遞增。
簡而言之,在沒有充分的生育配套措施支持下,生三個孩子,很可能只會增加城鄉各代人的照顧負擔。而面對三孩政策在生育決策、性別和代際上所產生的影響,更意味著國家需要在就業、住房、教育、醫療、老年照料政策上進行特定的干預,提供行而有效的生育配套措施,從而實現“敢生、能生、想生”的政策目標。例如,西方發達國家在兒童托育、養老照料以及家政服務上運作良好的市場化經驗,或者是我國早期計劃經濟時期在兒童托育保育事業上取得的成績,都是可以參考、摸索與總結的經驗。
但遺憾的是,針對這一方面的討論,至少目前在公共討論中依然不足。而更重要的話題是,如何調適“計劃(生育)”與“(自由)生育”之間的內在張力,還需要更多的思考。
(摘自《中國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