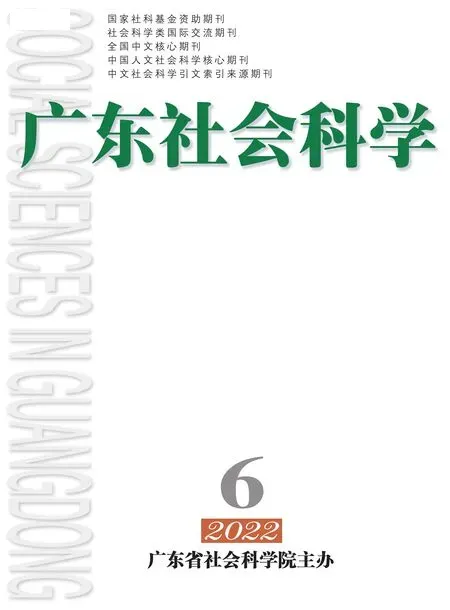空間正義的主體性闡釋
——基于馬克思空間正義思想*
張青蘭 李育林
“在所謂‘現代’社會中,空間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①[法]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齋藤日出治譯,東京:青木書店,2000年,第558頁。,全球化背景下空間重組與規劃和資本權力的結構關系日益凸顯,資本邏輯正以一種更為隱秘的方式實現對人們空間實踐的操縱,使人們自覺或不自覺中遵從資本的空間配置,造成現實生活中空間非正義事態持續泛濫并走向全球化。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根本上超越資本邏輯的社會發展形式,是馬克思空間正義思想的理論證明,但仍未達到“自由人聯合體”的空間正義的理想境界。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續推進引發了社會空間結構的調整與重塑,從而呈現出并置與交織的復雜場景。其中城市化的浪潮所帶來的住宅擁擠化、環境污染化等空間非正義事態,引發了人們對空間正義問題的理論吶喊和實踐訴求。“空間正義危機的本質是人的存在危機。”②熊小果:《空間正義的存在論闡釋——基于馬克思的勞動視角》,《思想戰線》2019年第6期。從主體性視角來看,社會主義空間正義的實現要求社會主義空間的生產與規劃應破除以資本的增殖為核心的取向,堅持以滿足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空間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根本價值追求,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空間幸福感、獲得感及安全感,使空間成為人們“詩意的棲居地”。
一、空間正義的出場:主體空間實踐的價值訴求
對空間本體的回答是解決空間正義問題的理論前提。馬克思空間理論的出場語境源自對唯心主義空間觀以及費爾巴哈機械唯物主義空間觀的批判。前者將空間視為“外在的抽象普遍”或經驗式的“先天直觀”,把空間從人們現實的感性活動中抽離,因而在他們看來空間是在“頭腦的天國”中,其發展“總是遵照它之外的某種尺度來編寫”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頁。,進而將空間解放以及空間正義的實現訴諸思想觀念的運動或絕對精神的自我揚棄,而不是現實的人具體的歷史的活動。后者雖然立足于客觀世界本身將空間視為一種感性對象,但卻只是從“直觀的形式”出發將空間視為“與人無關的自然”或者“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28頁。,從而忽視了空間與主體能動性的內在關聯,看不到空間是主體客體化的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從“實踐的、人的感性的活動”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01頁。出發,馬克思的空間理論突破并揚棄了以往傳統的空間觀,既尖銳地指出舊唯物主義“客體的或直觀形式的”空間局限性,又揭示了唯心主義只是“抽象地發展了”人的能動方面的本質,將空間的活動擱置于純粹抽象的精神家園,把空間“當作實踐去理解”,將空間的社會本質視為主體的感性實踐活動,從而找到實現空間解放的正確道路。具體而言,一方面空間作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總是以物質的形式呈現出來,脫離了物質運動的空間,是空洞的荒謬的,也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主體通過有意識有目的的實踐活動使得空間從“自在之物”轉變為滿足主體需要的“為我之物”,成為人本質力量的展現和確證。“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96頁。在這一過程中,空間這一客觀的存在物通過主體能動的實踐,不僅是以實體形式存在著,更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內涵,以關系形式、意義形式存在著,蘊含著人們某種價值取向與理念主張。其中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空間生產對人們物質資料和社會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有著無可取代的作用。
在明確空間的社會本質與主體的實踐活動的密切關系后,馬克思并非單純停留在對空間本體的思辨中,而是把空間視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要物質條件,將其放在社會歷史領域進行具體考察。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在資本邏輯的影響下,空間逐步成為資本增值的新的工具,空間的生產過程變成了資本主義實現“自我生產”的過程。空間的生產不僅是空間自身的生產,也是生產關系的生產,同時充斥在空間里面的社會關系,也在這一過程不斷得以延續。在這重復不斷的空間生產循環中,資本憑借對物質空間的占有而實現對上層建筑空間的統治,進一步加強對人生存與發展空間的操縱,人的主體性逐漸喪失,“資本主義就是通過對空間加以征服和整合來維持的。”①[法]勒菲佛:《空間與政治》,李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3頁。基于此,馬克思以資本批判作為切入點,論證了資本邏輯的空間非正義產生的社會根源,并指出應通過自由自覺的主體空間實踐來實現人的空間與自由解放。空間正義正是在馬克思進行批判資本的實踐過程提出的,是馬克思在揚棄資本主義空間生產方式的過程中,對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進行空間維度的理論思考與正義審視。從這個意義上看,空間正義思想的提出實則是馬克思在空間維度上拓寬了對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認識,對空間正義的理解離不開對主體的考察。
在馬克思看來,主體并非停留在思辨領域的“絕對精神”“自我意識”“唯一者”,也絕非脫離社會關系的抽象的純粹自然的存在物,而是從事一定活動的“現實的人”。這種“現實的人”在一定社會關系下進行空間實踐的過程中,也是其按照自身意愿對空間進行占有的過程,其中必然包含對空間資源與空間權益的正義訴求。從主體性視角來看,作為空間本身中蘊含著屬人的倫理價值,空間正義是一定社會形式下人們進行空間實踐過程中形成的關系性存在,本質上是主體空間實踐過程中的價值訴求與倫理表達,強調的是對空間資源的平等占有和對空間權益的平等享有。同時,空間正義的實現與主體的生存與發展狀態密切相關。從理論上看,作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頁。,人能夠通過“自由自覺的活動”實現對空間生產與布局進行合乎規律地建構。然而在現實中“人占有自己全面本質”是一個歷史過程,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空間在資本的支配下成為外在于人的客體,空間的物化使得人們親手創造的空間反過來卻成為統治人們的工具,空間正義伴隨著人的主體性喪失而遭到衰落。只有到“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主體真正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空間成為人的發展的現實條件,空間正義才得以真正實現。
在傳統的哲學中,空間一直湮沒在時間的歷史敘事之中,空間正義被用來強調對具體空間形態形塑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雖然在馬克思著作中并沒有對空間正義思想進行專題論述,但這并非意味著空間正義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缺場”。在剖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程中,馬克思關于資本的空間生產、資本全球化的空間擴張、資本邏輯下的空間異化等問題的論述,蘊含著豐富的空間正義思想。從主體性角度來看,空間作為主體存在和發展的先在性統攝,是主體本質力量確證和展現的基本前提。同時正義作為主體生存和發展的價值訴求,是符合主體倫理精神的社會關系表達。而作為二者的有機耦合,空間正義實際上是主體進行空間實踐過程中所蘊含的價值訴求,“是包含著對空間資源進行合理合法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一種綜合性正義”③王文東:《《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空間正義思想解讀》,《哲學研究》2016年第4期。,旨在通過對空間的使用和占有方式的改變,來調整和規范主體在空間資源上的不平等關系,強調的是空間實踐活動對主體的終極關懷。然而空間正義問題,在表象上是空間資源及空間權益的差異性問題,實則是凸顯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空間的非正義現象正是主體實踐在資本的束縛和支配下引起這些關系矛盾激化的外顯。在這個意義上空間正義的實現強調是使現實的個人從資本邏輯的空間統治中解放出來,實現空間的物化到空間解放的轉化,最終邁向空間正義的自由王國。
二、空間正義的衰落:資本邏輯對主體生存與發展空間的操縱
人類歷史的前提“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頁。一方面勞動作為人的本質活動,是個人“生活的第一需要”,另一方面人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一定的客觀物質基礎,外在的地理環境要素是人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同時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在本質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人既在勞動中確證自己的存在,同時作為一種關系性存在深深依賴于外在的地理環境。勞動空間、關系空間及地理空間是人生存與生活的基礎空間,空間正義與否很大程度表現為主體對這三大空間的占有。然而作為一種“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資本不僅表現為對自身增殖的無限需求,同時“資本顯然是關系,而且只能是生產關系”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8頁。,其在追求資本“量”的增殖的同時,也在進一步維護和繼續生產關系,從而實現對上層建筑的抽象統治。根源于資本內在的逐利性,資本邏輯為了在空間層面上最大程度掠奪利潤,從而“力求超越一切空間界限”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頁。,不斷壓縮工人的自由勞動時間,實現“用時間去消滅空間”換取剩余價值的增殖。在這一邏輯的操縱下,空間成為資本逐利的新的經濟工具,主體生存及生活空間遭到無限壓縮,空間正義由于主體實踐自主性的淪喪和生存與發展空間的異化而面臨衰落。
(一)作為根本前提的勞動空間
勞動空間是主體勞動在空間上的集聚與呈現,從內容上看包括空間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是構成人生存與發展空間的根本前提。在資本邏輯下,“最重要的勞動操作是按照投資者的規劃和盤算來調節和指揮的。而投資者所有這些規劃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潤。”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2頁。主體的勞動空間成為資本的增殖空間,人們在勞動中感受到的不是幸福、舒暢和自在,而是不幸、折磨與摧殘,勞動成了主體否定自身本質的異化活動。
首先,表現在空間生產上。空間生產作為主體勞動空間最主要的實踐方式,是其構建個體發展空間,實現空間正義的基本方式。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使得空間生產背后隱匿著資本邏輯的支配。“由于這種工廠手工業把原來分散的手工業結合在一起,它就縮短了制品的各個特殊生產階段之間的空間距離”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2頁。,使得“不同的階段過程由時間上的順序進行轉化為空間上的并存”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53頁。,并通過這種“以空間換時間”的方式實現“龐大的商品推擠”,資本得以迅速增殖。然而從協作到手工場再到機器大生產,技術的發展并未改變工人空間生產的悲慘現狀,相反“主觀的分工原則”的消失意味著勞動空間規劃原則的改變,主體的空間生產被一種“單向度”的生產模式所代替,取代以往時間支配的是一種更深的空間奴役形式。主體空間生產隸屬于資本邏輯,其生產的產品不僅不屬于主體本身,反而成為加劇其主體性喪失的“利器”。異化程度之深使得一旦強制停止,主體便像“逃避瘟疫一般逃避勞動。”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頁。
據了解,Link Turbo技術突破了以往智能手機網絡技術中蜂窩數據與Wi-Fi網絡無法并行的技術瓶頸,實現兩路鏈接同時收發數據,并可依據網絡狀況自動將即時應用切換到蜂窩數據通道。網宿科技解決了云-端最后一公里的加速問題,完成端云協同的網絡聚合,令部分榮耀V20用戶能率先體驗到屬于5G時代的流暢感受。
其次,作為連接空間生產與消費的中介環節,空間分配與交換成了資本邏輯對操縱主體勞動空間的主要手段。空間正義實現的必要條件是主體能夠以合乎自身需要以及社會發展要求實現對空間資源和權益的占有,而空間分配與交換直接關涉到主體空間利益實現的程度和水平。“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頁。,同樣“交換顯然也作為生產的要素包含在生產之內”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0頁。,二者無論是在對象還是形式上都取決于生產。然而由于受到資本邏輯的支配,主體的空間生產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抽象繼續。這一生產關系的持續生成實現了對主體空間分配與交換的操縱。資本家憑借著對財富和特權實現對空間資源的最大化占有,而夜以繼日辛勤勞動的無產階級不僅不能享受與其勞動相匹配的空間權益,反而還要承擔資本家濫用空間資源的代價,被迫“為他人創造財富,為自己而痛苦。”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4頁。“破落的茅屋”與“富麗堂皇的宮殿”的差別反映的不僅是財富的差異,更是資本邏輯下空間分配與交換的非正義事實,因此恩格斯才會發出“向宮廷宣戰,給茅屋和平”這一戰斗口號。
再次,作為空間生產的最終目的,空間消費的操縱是資本邏輯實現對主體勞動空間操縱的邏輯必然。與空間生產所擁有物質生產與關系生產的雙重特性,空間消費同樣具備物質消費與關系消費的雙重特性。一方面作為空間生產的對象化,空間產品只有通過消費“才證實自己是產品”,并“使產品最終完成”,整個空間生產的環節才得以繼續,資本才得以循環并實現自身在空間上的增殖;另一方面空間消費的不僅是有形產品,更是對背后生產關系的“消費”,準確來說空間生產的社會關系在主體的意識中得以不斷強化,從而達到對主體意識形態的統治,只有同時滿足這兩個環節,空間消費才算完成。“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頁。,空間生產的性質和內容決定空間消費的形式與對象。資本空間邏輯下空間生產無休止追逐利潤的特性使得空間消費與人們的實際空間需求嚴重脫節,造成空間資源過度消費、揮霍浪費的非正義問題。同時空間生產對社會關系再生產的支配使得主體空間消費逐漸服從于資本邏輯的空間配置。在消費方式和對象在資本空間邏輯支配下呈現“單向度”態勢的消費社會里,“顧客是上帝”的稱謂表面上抬高了人實則是貶低了人。
(二)作為外在依托的地理空間
“現實的個人”離不開物質生活條件。現實中的地理空間構成了人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的外在依托和客觀條件。“資本的積累向來就是一個深刻的地理事件。”⑥[美]大衛·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3頁。資本邏輯下,地理空間成為資本增殖及危機轉移的實體場域,人為的區域分工與等級劃分造成了不均衡地理發展的全球蔓延。
首先表現為城鄉空間的二元對峙。城市與鄉村是主體通過實踐對空間中各要素進行重新排列聚成的一種新的“人化的自然”空間,在本質上主體對象化活動的產物。然而在資本空間邏輯的支配下,城市淪落為“資本主義大工業所必需的基本生產條件的空間集合體。”①高鑒國:《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上海: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78頁。憑著強大的“聚集效應”以及高效的生產方式,城市對鄉村空間進行“剝奪性積累”,最大限度以鄉村的資源來滋養自身,其結果是鄉村淪為城市的“勞動力蓄水池”和“產業后備軍”,成了依附于城市“中心”的廣闊“邊緣”。隨著資本在城市的空間聚集,一方面棲居于城市空間的主體愈加被資本空間邏輯所支配,“城市愈大,搬到里面來就愈有利”宛如一個魔咒使得大量的人員往城市擠,造成城市空間資源高度緊張;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資源被掠奪,農村的居民對空間資源的平等享受的訴求日益高漲。“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圍內才能存在”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4頁。,只有在超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這種城鄉的二元對立才能得以解決。
其次,這種不均衡也表現在城市居住空間的碎片化與等級化。居住空間是個體進行物質能量交往與意義建構的最直接場所,也是與個體生存與發展關系最為密切的空間形式。城市住宅的規劃本意是使居民居住擁有更好的幸福感、獲得感和滿足感。然而現實是“每一個大城市都有一個或幾個擠滿了工人階級的貧民窟”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7頁。,高等的和中等的資產階級憑借著財富和特權占有著“郊外房屋或別墅”、“空間流通的高度”及“華麗舒適的住宅”,而工人階級“為了一筆微不足道的錢”不得不“居住在骯臟的區域”,甚至“最污穢的豬圈也經常能找到租賃者。”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7頁。這種明顯分化的城市居住空間背后折射的是不同主體的社會權力和地位,它服從于資本積累的需要,是資本家榨取高額房租的有意規劃。在這種分化和隔離的演變下,不同的住宅等級成為一種人工識別的意義符碼對不同的主體進行等級劃分,“住在貧民窟的工人被看成一群骯臟和道德墮落的人,是沒有尊嚴的人;而住在豪華社區的人則被看成高貴的人,體面而有尊嚴的人”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7頁。,這種劃分背后折射的是資本空間邏輯下的空間物化與階級沖突。資本邏輯塑造的畸形的居住空間成為壓抑人的“鐵籠”。長時間處于異化空間的主體,其身體素質和個性發展遭到嚴重扭曲,淪為“狹隘人群的附屬物”。
最后,這種不均衡還表現在全球空間的分裂。“資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財富的兩個原始要素—勞動力和土地,它便獲得了一種擴張的能力。”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7頁。這種能力驅使著資本不斷躍出自我存在的空間,打破束縛自身“增殖”的狹小地域,穿透各種空間障礙,實現資本在全球空間的布展與擴張,同時也間接促進了世界的全球化進程。然而全球化絕非意味著各國具有平等享有全球空間資源與權益的機遇,相反,資本推動全球化恰恰是為了制造這種不平等,其目的在于對其他地區進行“剝奪性積累”,迫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東方從屬于西方”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頁。,從而實現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統治。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大量資源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空間集聚以及殖民掠奪,導致全球地理空間結構的重組,形成了“中心-邊緣”的不平衡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
(三)作為社會內容的關系空間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性關系的總和。”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5頁。作為人的社會關系在空間上的集合體,關系空間構成了人生存與發展空間最本質的內容,同時也是資本邏輯操縱人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的最終對象。
對關系空間的操縱首先表現在對人與自我的關系上。空間對主體的建構作用表現為它提供人的主體性生成與個性化發展的場域。然而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空間內所蘊含的環境因素和社會文化力量反而成為阻礙個體發展的異己力量。一方面私有制下資本家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最大限度榨取工人的勞動時間。“時間是人的發展的空間”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2頁。,隨著自由時間的縮短,個體發展的空間也遭到壓縮;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社會關系,資本憑借對物的占有實現了對社會權力的支配,這在空間層面上表現為對個體空間產權與空間人權的剝奪。“所有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個小小空間里,每一個人在追逐私人利益的時候的這種可怕的冷淡、這種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難堪。”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4頁。資本空間邏輯下,個體棲居場所結構的合理性和生活空間需求的正義性的喪失“致使人像野獸而不像人”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9頁。,個人發展空間被無限壓縮,“資本主義使人類社會空間成為資本的權力場。”⑤李春敏:《資本積累的全球化與空間的生產》,《教學與研究》2006年第6期。
其次,這種操縱還表現在人與他人的關系上。人作為一種社會性存在,在有限的空間資源下進行空間實踐必然與他人發生關系。“正義包含的首要義務是不損害他人”⑥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第1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3頁。,空間正義要求個體進行空間實踐過程中與他人保持平等共享、和諧共處的友好關系。然而資產階級“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頁。資本的本質是對他人的統治,資本空間邏輯的確立使得現實中人與人不平等的關系在空間中得到進一步延伸。現實中的財富差異上升為空間享有的以富壓貧、剝削關系造成空間占有的倚強凌弱,權力失衡引發空間上的權責不當。“資本主義的積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狀況就越悲慘”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57頁。,空間資源配置的嚴重不均反過來加劇現實中的階級對立和社會矛盾,人與他人的空間關系隨著資本邏輯的滲透成為了一種對抗性的關系,現實中空間革命、空間沖突就是這一關系的生動反映。
再次,這種操縱還表現在人與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上。主體通過否定性的對象性活動將整個自然界分為“自在自然”與“人化自然”。前者在人的生成過程中獲得人的屬性,不斷被改造為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和展現。后者作為自然的空間的“真正復活”,是個體空間發展汲取養分并在其中確證自身意義的存在。然而在資本邏輯下,作為勞動的客觀條件的空間被“資本化”了,成為資本增值的工具和手段。空間資本化一方面使得社會空間一切內容和結構都為資本增值服務,成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大工廠”和剝削人、壓抑人的“無形鐵籠”,個體空間在社會空間的影響和制約下成了“大工廠”中的“小作坊”、“無形鐵籠”中的“有形方格”;另一方面導致自然的“祛魅”,并成為了資本謀取利益的工具。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與消耗不斷突破自然本身所容納的極限,引發了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態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再遵循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而是遵從于資本邏輯的支配。
三、空間正義的實現:主體超越資本邏輯的空間建構
空間正義與資本邏輯有著天然的悖論。空間的非正義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內在缺陷,只有徹底推翻空間背后的資本關系,建立超越資本邏輯的共產主義形式才能在根本上實現空間正義。而這種建立與復歸絕非“用詞句來反對這些詞句”純粹思想運動,而是“現實的個人”通過能動的實踐“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來完成,具體而言是以主體自由自覺的空間生產為物質性前提,以“真正共同體的個人”為主體性條件,以關系空間的解放為關鍵性內容。
(一)構建的物質性前提:主體自由自覺的空間生產
“歷史的誕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質生產。”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50—351頁。物質生產活動是人們進行一切歷史性活動的前提,是確證“人之為人”的活動方式。在勞動空間的內容中,空間生產作為整個過程中的首要因素“支配著其他要素”。勞動空間的非正義現實根源于主體空間生產的異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主體自主能動的空間生產活動被資本增值的邏輯掩蓋,“勞動采取雇傭勞動的形式,生產資料采取資本的形式”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8頁。,空間生產的結果是資本的生產與增值,生產的形式從個性化、差異化的具體勞動變成同質化、抽象化的總體勞動,生產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否定自身的壓抑過程。任何事物或過程,都包含著相互對立的因素,都是相反的對立面的統一體,主體的空間生產過程一方面是資本增值的過程,是造成人的全面異化的過程,同時又是為自身自由而全面發展創造新的空間的過程。資本的自我增殖與自我解放是具有同質性和共時性進路的過程,其內在邏輯的自反性最終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自我毀滅,取而代之的是“每一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自由聯合體”。到那時,空間生產不再是外在于人的異化勞動,而是主體自由自覺的實踐活動。每個人都能按照自身的意愿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進行空間的建構,空間生產實現了個體性與社會性的統一,空間真正成為確證和展現人的本質力量的積極存在。主體空間生產活動的解放必將帶來空間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從而構成人們解決一切空間問題,實現空間正義的物質基礎。“剩余勞動一方面是社會的自由時間的基礎,從而另一方面是在整個社會發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質基礎。”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7頁。隨著空間生產力的發展,生產效率的提高將大幅度縮短人們的必要勞動時間,人們得以擁有更多的自由時間來拓寬自身的發展空間,空間正義在人們日益開闊的空間舞臺中得到展現。
在當代中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確立克服了空間生產伴隨著空間非正義生成的邏輯悖論,有效解決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問題,從而使人在勞動過程中獲得更多的自由時間和發展空間。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空間生產的方式由原來的混亂的弱組織性到協調統一的秩序性,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資本的增值而是實現空間財富的共同占有,生產過程不再是壓抑人的痛苦過程而是自由愉悅的勞動過程。如今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極大優化了整個上層建筑的空間布局,推動空間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緩解了區域之間空間資源分配不均的困境;國家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實現了對空間生產的總體把控,避免了空間資源的過度開發與浪費;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確立了空間生產的目的在于滿足人們美好生活需要的空間訴求,空間正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合情合理的空間生產與建構的過程中得以實現。
(二)構建的主體性條件:“真正共同體的個人”
“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回歸于人自身。”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頁。個體只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性個人”,空間正義才能具有普遍的世界性意義,而這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性個人”絕非受資本主義影響被動卷入世界歷史的個人,而是超越資本邏輯的狹隘觀念,可以自主掌握自身命運自覺參與全球空間建構的“真正共同體的個人”。資本主義首創了世界歷史,打破了各民族原本封閉的、孤立的隔絕狀態,客觀上促使了個人從原有狹隘依附狀態的地域性存在轉變為相對開放、自由的“世界歷史性個人”,拓寬了個體生存與發展的時空維度。“單個人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頁。這一時期人的世界歷史性是處于一種被動的低層次階段,依附于資本在全球擴張的歷史進程中。隨著世界歷史的發展和人類時空范圍的擴大,“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界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542頁。同時這種全面的生產的能力反過來促進人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人們的實踐活動獲得更為廣闊的空間聯系。隨著“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頁。個體的空間建構不再局限于狹隘的民族地域中,而是具有世界歷史性,成為全球空間建構的一部分。空間建構的理念由原本地域性的狹隘觀念走向以人類的共同利益為核心的價值取向,空間正義得以擺脫階級觀念與資本邏輯的束縛,而真正具有了普遍的世界性意義。
當今全球化的進程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符合資本邏輯的方式對全球進行空間規劃和布局的過程,其本質上是資本在全球空間的布展。資本積累危機與生態環境污染的空間轉移、全球空間生產中政治霸權的介入及普世價值觀念的滲透,成了發達國家建立全球空間統治地位的手段,也是導致局部戰爭與沖突、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環境惡化等全球空間非正義事態的持續惡化的根源。資本邏輯主導下的全球化,空間建構成為資本及人格化的資本追逐利潤的工具,其提倡的具有“普世價值”的全球空間正義只是反映資產階級這一少部分人利益的狹隘觀念。“空間正義研究的起點不是純理論性的構建訴求,而是現實世界中實際存在和日益嚴峻的空間問題。”⑤吳紅濤:《從問題到方法:空間正義的理論文脈及研究反思》,《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當前中國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打破了西方發達國家以抽象人性論為理論假設,主張超階級、超國家正義理念的“普世價值”幻象,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全球空間正義的中國方案。這一思想絕非空洞的理論吶喊,而是具體的構建“真正共同體”現實方案。在構建目標上,它要求規制全球空間生產中的資本邏輯,“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⑥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18日。;在構建內容上,它認為全球空間正義應涵蓋全球政治空間正義、安全空間正義、經濟空間正義、文明空間正義以及生態空間正義,是這五個方面的有機統一;在構建路徑上,它強調要以培育人類命運共體意識作為奠定全球空間正義的思想基礎、以建設公平正義的全球空間治理格局作為奠定全球空間正義的主體框架、以平等對話、和平協商作為奠定全球空間正義的合理方式。簡言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嘗試修復和改造當前資本邏輯主導下不正義的全球空間格局,探索新型的全球空間正義發展道路的中國方案,也是進行全球空間構建的主體由被動的低層次的“世界歷史性個人”擺脫資本邏輯束縛,向“真正共同體個人”過渡的重要理論與實踐契機。
(三)構建的關鍵性環節:關系空間的極大解放
人不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一種關系性的存在。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空間正義不僅表現為人與空間地理環境之間的正義關系,其在本質上是規范與協調人與人、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價值關系的原則,強調的是對關系空間的建構。在共產主義社會,隨著空間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空間生產資源的社會占有,在人與自我的關系上,空間不再是存在于人之外的異化之物而是人實現自身全面發展的條件,人們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空間的建構。在人與他人關系上,空間不再是用于支配和剝削他人的工具。空間資源的極大豐富使得每個人的空間發展需要都得到滿足,人與人之間不再由于空間利益的分歧而導致空間關系的分裂與對立。人與他人的空間關系是一種和諧、平等、公平、公正的友好關系,這種友好關系不僅包含當代人,也包括后代人,是指每一個人;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隨著階級與分工的消亡,社會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劃分與對立也隨之消失,社會空間成為人們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空間形式。社會與個體矛盾的消失,社會空間將個人空間發展提供更加廣闊的舞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隨著資本邏輯從人與自然關系中抽離,為生產而生產的利潤動機不復存在,人們能以合乎自然規律的方式對自然空間進行改造和利用。自然空間將在真正意義上成為“人無機的身體”,人與自然的關系達到動態平衡與高度和諧。空間正義正是在這些關系的解放過程中得以實現。
我們無法回避資本邏輯宰制的時代,但我們必須看到關系空間的解放隱匿在資本邏輯的內在自反性之中,并隨著資本主義的自我否定與揚棄得以實現。作為對資本邏輯的根本超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與發展徹底扭轉了人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相矛盾的局面,使之朝著更為友好和諧的方向發展。同時我們也應當承認,盡管從多個維度提出有利于構建和諧關系空間,實現空間正義的價值理念和實踐方案,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仍存在許多空間非正義的現象。然而這種現象有別于資本邏輯主導下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空間非正義病態,它是不平衡、不充分空間發展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空間需要這一主要矛盾的外顯,隨著社會主義空間生產力的發展而得到解決。這也恰恰說明了關系空間的解放與空間正義的實現是一個螺旋式的上升過程。空間的非正義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定生產方式下人與人的關系問題。當代中國空間正義的構建,應堅持人的解放與空間解放相統一,以自由、和諧、平等作為構建的核心價值,以空間權力結構的優化為重要抓手,通過保持效率與公平的動態平衡來構建安定有序的社會空間格局,實現人與人、人與空間關系的高度和諧統一,使這些非正義現象消逝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進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