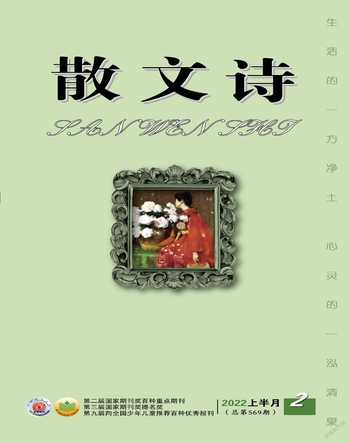那山,在鄉愁中沉默 (外一章)
劉山
那山,高出地平面,高出村莊,高出我的視線。但,它高不出蒼翠與荒蕪。
風沙呼嘯,它沉默。它把一粒粒沙石盡攬懷中,任那些尖銳的、有棱角的石子,在脊梁上恣意切割。
它不語。它把這些肆虐當作養分,揉進四季,揉進骨縫,揉進游子的背影里,用來素描晚霞中的最后一抹余暉。
暴雨傾盆,它沉默。它收集掉落的云朵,也收集思鄉的眼淚。雨水從山頂流到山腳,從山腳滲入大地,再沿著一座山的魂魄,升騰,向上,于陽光普照的地方,開出絢麗的花朵。
山上,鳥兒在飛,銜著游子的思鄉之情在飛。
它們圍繞著這座山在飛,圍繞著山上的朝霞和晚霞在飛,圍繞著村莊的日月星辰在飛。
它們不知疲憊。它們把那山當作故鄉,當作驛站,也當作家,當作有翅膀的夢。夢里,少小離家老大回。夢里,那山開口說話。
山如歲月般厚重。
春天,翠綠如蓋,遠遠望去,那山像少年,有著勃發的生機。是祖輩的鋤禾日當午,是父輩的面朝黃土背朝天。是村莊在第一縷春風中蘇醒過來,緩慢打開一座山的沉默。
夏天,鮮花漫野,那山像母親一樣,挎著一竹籃的鳥鳴和花香,等候一陣陣由遠及近的腳步聲,但是,我從不在鮮花盛開的時候上山。我只是站在山腳下,站在斜陽里,看落日一點點融入山峰,融入樹梢,也融入母親手中的針線。針線密密麻麻的,一個針腳就是一顆種子,一個補丁就是一段歲月,歲月中,父親的目光如山,山如父親般沉默。
秋天的村莊沉甸甸的,稻谷黃,高粱紅,那山披著蒼茫和遼闊,在沉默中,叨念自己的獨白。
把荒蕪鋪成背景,把大雁看成捎信的信使,把鋤頭和鐮刀都掛起來,把糧食堆成山,山山相連,每一座山峰上都飛揚著靈魂之沙。那沙,是山的脊梁,是父老鄉親的筋骨,是我無數次回望時,胸口中的隱隱作痛。
直到一場雪落下來,直到大雪封山,直到進山無路,那山便儼然一尊潔白的雕像,把所有鄉愁都裝進月光里,把所有沉默都裝進靈魂的故鄉。
我們要在第一千次攀登之后,才能貼緊一座山的脊梁,輕輕說出心底的秘密和渴望。
才能說出,一座山在濃密的鄉愁里,所有沉默的理由。
一棵行走的樹
懷揣鄉愁之人,是一棵行走的樹。
背負青蔥與蒼涼,也背負榮耀與孤寂。
風,只從一個方向吹過來,柔婉而薄涼。我移步檐下,攤開掌心月色,緩緩打開最后一朵格桑花的心中之美。
被點燃的,不僅僅是神圣,還有那些命定的淵藪。
粗糙,潮濕,風吹過的地方,更利于一棵樹的成長。它們在河岸留下子嗣,在荒山留下眺望,在一塊石頭上留下萬畝良田。
我開始不停地奔跑。
跑過麥苗的拔節之聲,跑過一只烏鴉和一只喜鵲的爭吵之聲,跑過暴風和驟雨的廝殺之聲,油菜花就開了,到處都是飄零的云朵。
向晚的風里,一棵樹,閃耀著神祇一樣的光芒。
那棵樹高舉著我。我高高舉起一棵樹。
我們緊密相連的部分,流淌著相同的血脈。我們互不接觸的部分,根須蔓延。疼,是千千萬萬行腳印踩下的深谷,谷里,鮮花叢生,枝繁葉茂,我們流著淚,在廢墟里盛開寂寥和荒誕。
慢慢傾斜,一棵棵樹以死亡的方式重新開始。它們繞過江河湖海,把一尾魚種在沙灘上,至此,我看到標本,看到生命的尾音部分,圣潔而永恒。
很多動詞有時候也是名詞。行走與停留之間,互斥,互補,也相互扶持。我握緊一片葉子,在鐵匠鋪的火光里,風沙漫天,淚流滿面。還能說些什么呢?
無家可歸的人們開始奔走相告,告知春天的信息,告知秋天的信息,告知一棵樹如何在第一場雪未到來之前,褪下墨綠色的披掛,著裝荒蕪,繼續行走。直到對岸綠葉如蓋,山泉流響。
是人生的交響曲。
是命運的斷章。
是無數只螢火蟲織就的燈盞,掛在荒野,掛在蒼穹,掛在一棵樹默默無語的靈魂里,逆光飛翔。
愈來愈濃厚,愈來愈淡薄。身后是故鄉巨大的落日,也是李白窗前無垠的月色。是波光瀲滟,也是懷念和淪陷。
有如,永夜的墻上裂出一道美麗的縫隙。
有如,萬家燈火的巷子里,族人們沉浸在秦腔中醉也不歸。
有如,那些失而復得的露珠,正在一朵牽牛花的蕊芯里,耳鬢廝磨。
有如,西山梁于無數棵大樹的庇護下,緩慢地移動著步履,愈來愈接近一壇酒的溫度與醇度。
我懷揣半塊石頭,一次次潛入田野,又一次次浮出水面,接受陽光的撫慰,也接受月光的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