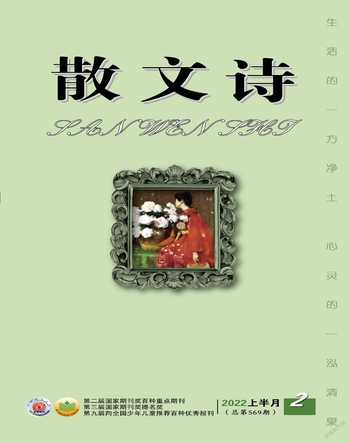一次致敬式的寫作(創作手記)
耿翔
我在馬坊的一個山村里長大。那時,我們很難讀到一些書,但能讀到魯迅。現在想起來,那些囫圇吞棗式的閱讀,根本與魯迅和魯迅的書無關,就像在一個集體里,做著一種無意識的游戲罷了。倒是魯迅那些線條硬朗的肖像,讓一個山村男孩,開始懂得崇拜什么樣的男人了。
我們并不懂得魯迅,但我們熱愛魯迅。
這就是那個時代,塑造出來的我們。至今藏在我的書柜里的,有一本《阿Q正傳》,定價三角一分。這就是說,我曾經用不到半元錢的代價讀過魯迅。現在翻看,我當時讀書的認真程度,還是對得住魯迅先生的。我幾乎在書的每一頁上,都劃出不少的虛線、圓圈、三角等符號,表明我對這些文字的態度,也被那些發黃的舊紙張,作為熱愛魯迅的確鑿的證據,原樣地保留在書里了。
讀書的力量,在于觀己。我不知道我在魯迅的文字里,到底觀看到了自己的什么。但我一直畏懼他的文字,畏懼他文字里的目光,畏懼他文字里的嘆息,畏懼他文字里的冷暖,也畏懼他文字里的結局。那是很多事件的結局,也是很多人物的結局。那些結局,也就是魯迅給一個愚昧年代的結局。我更懼怕的是,沒有活過他的文字的魯迅,那么早地走了,那些被他痛打和同情過的人和事,卻在我們這個沒有他的年代,又活了過來。我們的身邊,有阿Q,有閏土,有祥林嫂,他們活在我們的意識里,也活在我們的行為里,他們是我們很難改變的DNA。
沒有了魯迅的目光,很多事物,我們還看不清楚。
魯迅說過,從來不朽之筆,須傳不朽之人。魯迅走了,留下這么多不朽的文字,我們這些必朽之人,能在他的文字里,呼吸上幾口他的靈魂里的氣息,也就算被魯迅熏陶、滋養、教誨過,也不枉是一個讀過一些書的人。因此,我不敢過多地思想魯迅。為了給自己下臺階,就借用別人的說法,稱自己時不時進入到魯迅的文字里,是一個人在那里私想魯迅。
直到有一天,讀了無場次非歷史劇《大先生》,我才發現,那是李靜的一次文字探險。李靜寫的是李靜的魯迅,正如魯迅寫的是魯迅的中國。因此,只要讀過魯迅的人,每個人的心里,都不同程度地有一個不一樣的魯迅。我從李靜的魯迅中,讀到了魯迅的淚水,讀到了魯迅的血液,讀到了魯迅的骨頭,也讀到了魯迅的笑。這些,無論在李靜的心里,還是與我以前讀過的魯迅,都是很不一樣的。
我也發現,時至今日,魯迅就連身體,也沒有離開我們。
他還坐在那把椅子里。他手上的煙頭,還沒有掐滅。
我還發現,從魯瑞、朱安、許廣平這三個與魯迅生死相連,又命運不同的女人那里,去大膽地讀一讀魯迅,或許因他的文字的不朽,而對很多人顯得遙遠、肅穆的魯迅,距離更近一些,形象也和藹一些。
我也就放下畏懼,寫了《坐在椅子上的魯迅》。
我最想說給魯迅的一句話:“你的文字是一副中藥。”
從最初懵懂地讀魯迅,到第一次寫魯迅,其間的時間跨度接近五十年。
有關魯迅,就是看見了一朵朝花,也只能夕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