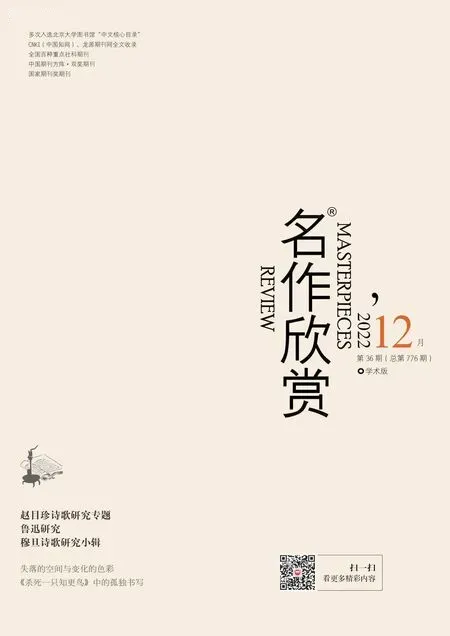現代性:中國文學融入世界文學的出海口
——從魯迅《鑄劍》說起
⊙張有根[蘇州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江蘇 蘇州 215000]
從20世紀初開始,在新文化運動背景下,中國第一次真正地開始擁抱世界,西方文化思潮席卷而至,隨之而來的是大量外國文學名著和文學理論著作被譯介到中國,來自西方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鋪天蓋地,影響了以魯迅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國作家的創作,西方先鋒派思潮也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產生了很多令人震撼甚至驚世駭俗的作品。這種外來文化的快速傳播以及中國作家對新思潮所作的回應,直接將中國文學帶入了世界文學的語境中。現代性是中國文學融入世界文學的最初出海口,從此中國文學開始從幾千年內生式自我循環的狀態脫穎而出,一路浩蕩奔騰,開始融入世界文學的汪洋大海,這是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貢獻,也是中國文學的自我成長和超越。
魯迅的《鑄劍》體現了強烈的復仇精神、原俠精神和人民反抗黑暗的斗爭精神。借由國民性批判,確立了“人”的解放的現代意識;小說以荒誕包孕現實批判,對“復仇”進行了全新的現代性解讀,體現了魯迅小說的現代性追求。《鑄劍》的主題意蘊是繁復而多重的,帶有多重節奏。魯迅并不止于“復仇”,“三頭相搏”把小說情節推至頂點,這個場面無疑是荒誕而令人震撼的,大多數作家往往到此就戛然而止,而魯迅的深刻就在于通過精心安排“復仇之后”情節的新的曲折發展——“辨頭”的鬧劇、“三頭并葬”的滑稽戲和“大出喪”時全民“瞻仰”的“狂歡節”,把小說又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這個魯迅式的結尾,充滿了意味深長的調侃與諷刺意味,既是對強權者的進一步的嘲諷和鞭撻,同時也包蘊著對黑色人乃至作者自身的反諷和自嘲。魯迅給我們揭示了一個殘酷而令人啼笑皆非的現實:一場充滿正義的復仇壯舉業已結束,荒淫虛偽的專制暴君盡管暴斃,但“華老栓”們依然對著暴君的尸體跪拜不已;更有“義民”“忠憤而悲傷,擔心晏之敖者、眉間尺這兩個大逆不道的逆賊的魂靈,此時也和王一起享受祭禮。在此,魯迅謳歌了復仇,又對復仇提出了自己的質疑。此為魯迅的清醒,也是他的深刻。在《鑄劍》中,悲壯與嘲諷、崇高與荒謬這兩種基調相互糾纏而激蕩,互為對峙,彼此消解,集中表現了魯迅深廣之憂憤和靈魂深處的糾纏、痛苦,體現了魯迅小說的現代性追求。
一、強烈的復仇精神、原俠精神和人民反抗黑暗的斗爭精神
《鑄劍》此復仇故事,其本事源于《搜神記》《列異傳》等古籍記載的“三王冢”故事。楚王讓鑄劍名師干將與莫邪鑄劍,劍成之日就是干將被殺之時。十六年后,干將之子眉間尺長大成人,決意復仇。
小說這樣寫道:“眉間尺伏在掘開的洞穴旁邊,伸手下去,謹慎小心地撮開爛樹,待到指尖一冷,有如觸著冰雪的時候,那純青透明的劍也出現了。他看清了劍靶,捏著,提了出來。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驟然失了光輝,唯有青光充塞宇內。那劍便溶在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無所有。眉間尺凝神細視,這才仿佛看見長五尺余,卻并不見得怎樣鋒利,劍口反而有些渾圓,正如一片韭葉。”
眉間尺就這樣開始承擔起家族的重任——復仇。在首次刺王失敗被通緝的情況下,俠士黑色人晏之敖者適時出現向其獻計。黑色人帶眉間尺的頭顱去見楚王,乘機削下了楚王的頭顱,眉間尺和楚王兩頭互相撕咬,難舍難分。晏之敖者繼而拔劍自刎,一時間三頭大戰,最后在鼎中煮成了白骨,難分彼此。作者承續了“三王冢”這一原始故事所承載著十分濃重的復仇精神,并一再渲染了眉間尺的性格成長:為彰顯眉間尺為父復仇的義勇和正氣,作者著力呈現了眉間尺性格成長的兩次轉變:小說開始于眉間尺的“與老鼠的戲斗”的優柔寡斷、怯懦脆弱,當他聽到“母親的埋怨”和“父親被殺”事實后,他“毛骨悚然”,全身燒著猛火”、“毛發閃火星,拳捏得格格響”。這是他性格的第一次重大轉變。繼而寫眉間尺殺王行為的莽撞、與干癟臉糾纏的手足無措,表現了他的涉世不深、經驗不足、能力有限。當黑色人出現,他正確地接受了黑色人的幫助,毅然交出了自己的頭和劍。這是他性格的第二次轉變,在此過程中他日趨成熟。但是魯迅并沒有止步于簡單復仇,而是展開想象的翅膀,站在現代性高處,把“三王冢”的傳說擴展成了一篇驚心動魄的現代小說,賦予其現代審美意識和現代性品格,表現出現代小說的多重意蘊。
從寫作背景角度言,《鑄劍》表達了魯迅強烈的“復仇”精神。從黑衣人的行為表現角度言,《鑄劍》作為一篇武俠小說,體現出一種原俠精神。黑色人的出現是小說情節的轉折點。作為“原俠”,黑色人對眉間尺的幫助是不帶任何功利目的的,并且拒絕一切贊美與感激。魯迅曾說:“中國人總喜歡一個名,只要有新鮮的名目,便取來玩一通,不久連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開,另外又取一個。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樣,放下去,沒有不烏黑的。譬如教授、學者、名人、作家這些稱呼,當初何嘗不冠冕,現在卻聽去好像諷刺了,一切無不如此。”《鑄劍》是神話或傳說,表現了人民群眾反抗專制暴君的斗爭精神。對于宴之敖者而言,他的一舉一動都帶有對于世俗意義的個人生死乃至肉體的擯棄與冷酷的決絕。無疑,魯迅在他身上傾注了他的人格理想與對“理想的人性”的呼喚——復仇乃目的本身,黑色人就是那把青色的復仇之劍鑄就的“精魂”。正是在宴之敖者的身上,魯迅暗置了自己的復仇精神。作為越人后裔,魯迅骨子里激蕩著越王勾踐的精神血脈。魯迅“一個都不寬恕”,乃根源于他對黑暗和命運的根深蒂固的絕望和對絕望的絕地反抗。在此,黑色人就是魯迅。
二、借由國民性批判,確立了“人”的解放的現代意識
魯迅小說的現代性品格,一以貫之的是他深刻幽邃的批判理性精神及其藝術獨創性。魯迅在對我們民族悠遠歷史的深刻觀照及對現實世界的理性而敏銳審視中,揭示并解析了中國傳統文化長期積淀所造成的扭曲的民族心理結構,企圖以思想革命為契機,沖破封建“鐵屋子”,重構民族性格。魯迅第一次在日本留學時發現了看客的存在,《藤野先生》中所記載的槍斃國人的影片,可謂魯迅思想的轉折點。那些面對同胞被殺“酒醉似的喝彩”,徹底改變了魯迅的認知,使他第一次看到了亟待改變的是國民的靈魂。《藥》同樣描繪了一幫看客圍觀革命者夏瑜被殺害的場面。雖然當時已經是“秋天的后半夜”,但是觀者甚眾,“簇成一個半圓”,欣賞著他人的痛苦,時不時還叫上一聲好。“看客們”猶如一面鏡子,使魯迅從根本上看清了中國人的病源。正是魯迅深刻的洞察,看客形象在其諸多小說中愈為經典和鮮明。《鑄劍》中干癟臉的少年和周圍的看客、閑人皆是百無聊賴之人,此無聊之舉正應了眾多國人的表現,活畫出許多國人的嘴臉:無謂地“窩里斗”,那些無聊的看客、閑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判斷力,而醉心于欣賞別人的尷尬與難處,在別人的尷尬中消解自我內心的空虛,排遣自己的無聊。此處情節可以看出眉間尺涉世不深、機智不足,以此隱喻了眉間尺獨自復仇的艱難,也凸顯了一種冷酷的現實——眉間尺是孤獨的,一種不被人理解的孤獨。
七天之后是落葬的日期,合城很熱鬧。城里的人民,遠處的人民,都奔來瞻仰國王的“大出喪”。天一亮,道上已經擠滿了男男女女;中間還夾著許多祭桌。待到上午,清道的騎士才緩轡而來。又過了不少工夫,才看見儀仗,什么旌旗、木棍、戈戟、弓弩、黃鉞之類;此后是四輛鼓吹車。再后面是黃蓋隨著路的不平而起伏著,并且漸漸近了,于是現出靈車,上載金棺,棺里面藏著三個頭和一個身體。
百姓都跪下去,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叢中出現。幾個義民很忠憤,咽著淚,怕那兩個大逆不道的逆賊的魂靈,此時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禮,然而也無法可施。
《鑄劍》的第四部分是狂歡式的大出喪,其荒謬與嘲諷的意味與前文的悲壯、崇高形成強烈反差。這是魯迅曾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幻燈片”中見到過的一張張熟悉的面孔,是他深深愛著而又憎惡的“路人”。他們與為“復仇”而獻身的眉間尺和宴之敖者自然形成了強烈反差與鮮明對比。魯迅借此來表現自己作品中多次出現的一個主題,那就是“國民性”改造的問題,在此,我們又一次看到了改造國民性的必要與艱巨。
《鑄劍》塑造了楚王的貪婪殘忍、喜怒無常、狡猾而老謀深算以及眾看客的麻木奴性形象,在此楚王和眾看客都分別變成了一個符號——惡勢力和閑人的代表,讓小說具有更普遍的意義。魯迅站在時代的制高點,融合歷史和現實,反省歷史,審視現實,挖掘我們民族的絕望與希望、苦難與新生,借由深入的社會、思想革命改造中國,擺脫貧弱和愚昧,并且通過吸取西方先進思想和文化,以改造國民性,實現“人”的解放。魯迅就這樣借由對民族的深愛和時代的敏銳,達成了其小說的現代性品格。
三、以荒誕包孕現實批判,對“復仇”進行全新的現代性解讀
在西方現代派文學那里,荒誕性在作品中往往具體化為生命的虛無、和諧關系的淪喪、異化等主題,從而使荒誕派文學中的審美意象具有了不同于傳統文學的審美特質。魯迅在《鑄劍》中,對現代派文學進行了大膽的具有先鋒性的探索。綺麗的想象、荒誕的情節,賦予這篇神話傳奇以后現代表現主義冷峻奇偉而又驚世駭俗的浪漫主義風格。“荒誕”與“莊嚴”兩種不同的色彩與語調或顯或隱,互相補充、彼此滲透而消解。隨著小說情節的推演,復仇者、被復仇者乃至復仇結果都發生了異乎尋常的顛覆性變化。表面來看,《鑄劍》講述的是一個尋常的子為父復仇的故事,作者用劍與火淬煉出英雄主義的崇高而堅硬的人格力量,但在深層次,人生悖論的荒誕與滑稽卻又撲面而來。
當夜便開了一個王公大臣會議,想決定哪一個是王的頭,但結果還同白天一樣。并且連須發也發生了問題。白的自然是王的,然而因為花白,所以黑的也很難處置。討論了小半夜,只將幾根紅色的胡子選出;接著因為第九個王妃抗議,說她確曾看見王有幾根通黃的胡子,現在怎么能知道絕沒有一根紅的呢。于是也只好重行歸并,作為疑案了。
到后半夜,還是毫無結果。大家卻居然一面打呵欠,一面繼續討論,直到第二次雞鳴,這才決定了一個最慎重妥善的辦法是:只能將三個頭骨都和王的身體放在金棺里落葬。
《鑄劍》的前半部是一個悲壯而驚心動魄的復仇故事,而小說的尾聲于復仇完成“以后”,出現了傾城而出“萬民觀瞻”的“狂歡節”盛景:眉間尺、宴之敖者與王的頭骨混于一處,難以分辨,同被展覽,復仇的神圣和崇高也被消解為無,愚昧的閑人和看客,才是唯一的永遠的“勝利者”。在此魯迅以懷疑的姿態,將在看客面前復仇的無意義和無效揭示給人們看。正是這個無意義,才是《鑄劍》不同于傳統“俠”之意旨的深刻和尖銳之所在。在此,魯迅進行了一場深遠的歷史和現實的對話,從而賦予復仇以重要的認識價值和當代價值。
現代性屬于哲學范疇,現代性與傳統相對立或者說是互相割裂,傳統社會的價值觀與社會風俗在現代性的思潮之下得以解構與重構。自由是現代性的核心,科學與理性是其表征。現代性推進了民族國家的歷史實踐,并且形成了民族國家的政治觀念與法的觀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會組織機制,創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為核心的價值理念。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與現代性的旗手,《狂人日記》的發表,拉開了現代小說不斷推陳出新的序幕,從《孔乙己》《藥》到《風波》《阿Q正傳》的連續發表,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至尊的崇高地位,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到1925年發表《離婚》止,魯迅7年間共創作了25篇小說,后結集為《吶喊》(1923)和《彷徨》(1926),這些作品幾乎每篇都是對現代小說形式的新創造,并成為中國現代各體小說發展的重要源頭.魯迅小說之所以既是現代小說的開端,又是現代小說的成熟的標志,其價值不僅止于文學,更是文化各方位的,它以其現代性體現了“五四”啟蒙運動和思想革命的時代要求,同時還在于它將西方小說的手法技巧與中國傳統小說的藝術精神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在題材、構思、心理描寫以及小說的體式和語言等方面都對傳統小說進行了革命性的突破,實現了中國小說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對后來的現代小說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自此中國文學開始從幾千年傳統文學裂變而出,這是中國文學的鳳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