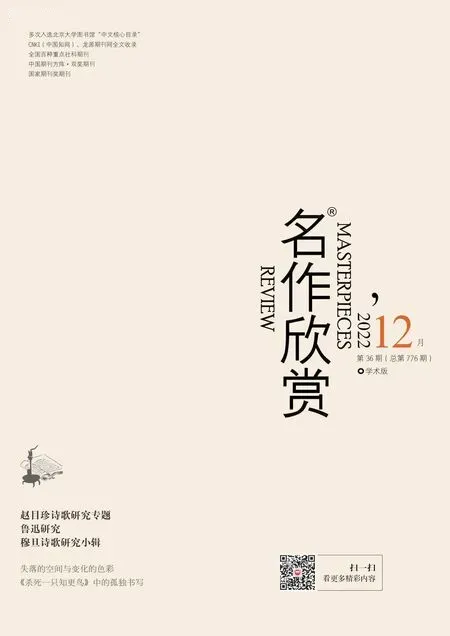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下文人情書演變與大學生群體接受
⊙何梓源 施珂雯[南京師范大學強化培養學院,南京 210000]
新媒體時代日新月異,文學隨之產生劇變。大眾文學與網絡文學異軍突起,強勢地占領了中國當代文壇格局的高地,網絡文學的地位如今不容小覷。新媒體時代中,大眾文學與網絡文學對曾經主流的傳統文學進行著怎樣的翻“新”,究竟“新”在哪里,反映了何種“新”式的文藝接受心理,是許多研究者津津樂道的研究主題。文人情書作為情書文學的集大成者,在新媒體時代下,依然承載了人們社會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身上所具備的,不僅有來自中國傳統文學的底蘊沉淀,也有當代大眾傳媒與網絡文學的影響烙印,使它在文體形式、版式、傳達方式上均產生了一定的變化。
當代大學生群體大多出生于千禧年前后,正是隨著新媒體時代共同成長的一代,受大眾傳媒、網絡文化的影響尤深,其價值取向和審美情趣也時刻影響著大眾文化與時代潮流。對于文人情書,大學生群體也具備相當程度的發言權,甚至不乏切身寫作的經驗。在新媒體時代背景下,文人情書的寫作在大學生中如何被閱讀、如何被接受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一、新媒體時代文人情書演變
文人情書,筆者將其定義為文人創作的,以散文或詩歌為主要文體,溝通雙方情感的書信。書信最早被稱為尺牘,濫觴于戰國時期。由于執筆者大部分為士大夫文人,具備良好的文學修養和書寫技能,又可以將文人尺牘脫胎出普通尺牘來闡發研究。故而,文人情書正是在文人尺牘的基礎上,加以情感的潤色和陶冶,流傳千載,筆墨傳情,為后世留下了無數文學精品。
在紙張問世之前,古代先民將竹簡木牘作為書寫載體,普通百姓多不識字,故唯有文人能夠將心意付諸刻字之上,寫就文人情書。中國古代文學尺牘的成就燦若星河,漢代文人開始了最早的文學書信。這一文體雖然極為發達,卻難免有令人遺憾的空白,即最熱烈的、延續了抒情傳統的書信——情書的匱乏,尤其是女性主筆的缺失。在封建傳統禮教不斷加強升級的束縛控制下,男子尚且遮遮掩掩兒女私情,就更不用提“無才便是德”的女子要如何暗自表情達意了。即使流傳下來,也只有卓文君《與相如書》類只言片語傳世,后偶有女性詩人詞人的閃耀如曇花一現,但更多的還是自古至今由男性代言的情書、情詩創作,無法真實還原女性主筆的情調。這樣的空白直到1917年初發生的文學革命,兼“五四”的思想解放浪潮下才被逐漸填補。
“五四”時期的文學創作潮流服膺于思想啟蒙,在理性批判精神的引領下興起“重新估定價值”的熱潮,對于“人的發現”與“文學的發現”,無一不喚醒了文人具有現代意味的自我認識,其中不可忽視的自然有婚姻與愛情觀念的巨大變革,成為突出文化與文學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現象。接受過現代教育、受“五四”先進人文思想啟蒙的年輕人們紛紛呼吁戀愛自由,將愛情作為“人的覺醒”后理應擁有的基本生存權利,反對傳統封建家長做主下的包辦婚姻、媒妁之言,將心中肝膽肺腑之言、涓涓思慕之情統統付諸筆端,首先用不可壓倒性的文學審美和思想意識引領起這樣的反抗式情書創作的便是功績豐碩的中國現代文人。
反觀現代情書的發展,并未很好地延續這種傳統。“三行情書”是文人情書形式演變中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之一,要求人們以篇幅不多于六十個字、分三行排列的詩歌形式來傳達感情,傳入國內后掀起熱潮,尤在高校中盛行。這類情書在形式上完全突破了傳統詩歌形式的框架,另起爐灶。此前不論是在日本還是中國,傳統的詩歌作品均是以偶數句形式存在,如日本特有的兩句的俳句,中國則經久流傳著四句的絕句。將三行固定為詩歌的形式特征,是中、日傳統詩歌中從來沒有過的。因此,從形式上將“三行情書”視為一種新時代產生的“新文體”并無問題。但在內容的文學性和審美性上,“三行情書”式的情書寫作卻無質的明顯突破,甚至未能延續情書傳統,抒發真摯的情感,新媒體賦予的只是一個剝離內涵的外殼。不妨看看2013年武漢大學第二屆“三行書”大賽中獲獎的幾例:
螃蟹在剝我的殼 筆記本在寫我/漫天的我落在楓葉上雪花上/而你在想我
你說愿在櫻花深處嗅絲縷芬芳/卻留我一人/看櫻頂上盛裝的新娘
偏偏 偏偏/你已在岸上走/我仍舊立在水中候
武漢大學作為教育部直屬的綜合性全國重點大學,其學術淵源和人文素養積淀深厚,始終站在社會前沿,保持對新興事物的大膽嘗試。一所高校的小范圍評選活動,雖然不能全面概括國內“三行情書”創作的整體狀況,但我們仍然能夠以這三首詩為樣本,進行一些分析。不難發現,“三行情書”最直觀的特征即簡潔短小,三行分列,均采取具象化的環境描摹,烘托出“我”對“你”的情思纏綿。但除此之外,這幾首詩無論從主題、意象,還是語言風格、意境方面上,都未表現出明顯超出傳統抒情短詩的氣質。近年來,“三行情書”的創作活動屢見不鮮,與上述三例相比,絕大多數“三行情書”更顯直白淺陋,甚至只是簡單地將一個完整的句子割裂成三行,徒有“三行情書”的形式,而不見“三行情書”的內涵。當然,筆者無意否定“三行情書”作為新文體的進步性,所舉第一首詩的流傳度與影響力至今有目共睹,其將語序顛倒作為隱晦的一種替代技巧也被爭相模仿。筆者意圖強調“三行情書”如果有意謀求文學史的主流敘述地位,仍亟須走出形式翻新的圈套,轉而提升與反思自身的文學審美,爭取從內在革新上逐步合規“新文體”的要求。
另一方面,當代情書創作還面臨著媒介升級、情感流失的情況。中國現代文人情書中的戀人絮語不可勝數,我們不難發現,文人情書中折射出的一些戀愛傳統一直延續。中國現代文人情書中記錄了聚少離多的異地情思,頗能引起新媒體時代下讀者的情感共鳴,而分離的狀態下寫就的文人情書,更顯才華與癡情。《兩地書》踏實地丈量了魯迅和許廣平攜手走過的從相識到相知的寸寸光陰。在一封封平淡又動人的情書中,魯迅把許廣平稱作“害馬”,或用“HM”替代,許廣平在回信時也常常署以此特殊符號。其實,“害馬”之稱最初由女師大校長楊蔭榆所起,因為許廣平求學時期叛逆激進,不是“省油的燈”。魯迅正是欣賞她這一點,便親昵又不著痕跡地“以此為號”。這種親密戀人之間才有的“暗號”或“隱語”,在今天的戀愛男女中也屢見不鮮,甚至成為象征建立起深層次親密關系中的一條“潛規則”。今非昔比,一些親密稱謂,如“親愛的”“寶貝”等,在新媒體時代的背景下,已由戀人之間私密獨有的、展現雙方情感親密的紐帶逐漸模糊、泛化為社會通用稱謂語,甚至成為迅速拉近人際關系的手段。
中國現代文人雖面臨著山海遠、車馬慢的問題,思想卻不會被遙遠的路途阻隔,書信中寄托的是他們契合的靈魂和相同的理想追求。他們將“五四”精神作為思想指導,在情書中表達真切的情感,大膽反抗封建禮教和包辦婚姻。遙遠的距離、世俗的壓力、禮教的束縛,都是他們情感道路中的枷鎖,沖破坎坷、共渡難關才收獲的感情,自然也能引發心靈的共鳴。因此,在這些反映自由精神、崇尚婚戀自主的情書中,有著豐富的內容和復雜的情感,較之于當代青年人附庸風雅,只顧風花雪月的創作形式,顯然更具文化內涵和藝術底蘊。在新媒體浪潮下,通訊發達、媒介升級,迅速發展普及的網絡、交通都為情感交流增添助力,物理阻礙逐漸消除,精神隔閡卻逐漸擴大,在靈魂與肉體的割裂下,現代人的情感世界實在單薄脆弱。
新媒體時代下,通信即時、見面便利,情感溝通易于實現,然而,輕松便捷的方式反而使情感得不到珍視。“電子媒體以電線或電波來傳遞編碼的電子脈沖信息,和書信往來一樣,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延伸了人們‘面對面’交往的時空限度。”①“面對面”的時空限制被新興電子媒介無限拉伸,交流的即時性與可視化不斷削弱著書信的交流功能。在這類媒介的助力下,情感雙方克服了物質阻礙,即使相隔千里,也能通過網絡交換信息。迅速升級的交通體系還拉近了全球的空間,異地見面的可能性大幅提高。這樣的轉變對習慣于快節奏生活的當代人來說異常合適,信息飛速更迭的時代,少有人能真正沉浸在慢節奏的等待中,當代人習慣了隨時隨地獲取關懷和應答,也習慣于情感經營成本的降低,這容易導致情感貶值的情況。依靠網絡等新媒體手段的當代情書文本成為快餐式情感的附屬,文人情書的精神內核難以重現。
因此,當代的情書文本雖然有全新的因子,但未能延續良好的抒情傳統,缺乏時代精神和思想內核,也未能繼承傳統文人情書形式上的優勢。因此,在新媒體時代的背景之下,我們亟須回溯文人情書,重新挖掘其身具備的多元價值,為當今的情書接受與再創作提供支撐和借鑒。
二、對大學生群體文人情書接受情況的觀察和反思
情書文體的演變歷史肯定了傳統文人情書的價值,當代情書不僅要吸收采納其積極因素,更應關注自身的創作情況。在新媒體時代的傳播和文化語境下,可以對當代大學生群體文人情書的接受情況與態度進行如下描寫:綜合調研數據和本項目問卷調查結果可知,總的來看,當代大學生普遍閱讀過中國現代文人情書,并且廣泛通過紙質書籍接觸,對一些知名中國現代文人作品比較熟悉,但多數僅停留在表層,缺乏深入的了解。在閱讀過程中,大部分均已自然接受“三行情書”等新媒體時代下的文人情書的演變產物,并對其前景持樂觀態度,興起一系列模仿創作行為。筆者認為,這一現象正是新媒體經濟下文人情書處境的真實寫照。
信息的圖像化、扁平化、碎片化是新媒體時代的顯著特征,網絡信息成為包括大學生群體在內的現代讀者接觸中國現代文人情書的主要手段,由此對中國現代文人情書的文藝接受產生了不可避免的負面傾向:一是碎片化、媚俗化誤讀,二是閹割交流功能。當代大學生群體更容易受到碎片化信息和圖像的吸引,而非大篇幅的純文本。此類趨勢不利于純文學文本、長篇文本的存在與發展,使現代讀者無法靜下心來體悟作品中蘊含的復雜情感,僅以片面、扁平的只言片語對其下定義。就中國現代文人情書來看,作品往往篇幅較長,文白交雜或以純文言的形式呈現,吸引力式微。與此相悖的是,文人情書又常常在我們的視野里閃現復歸,旋即銷聲匿跡。文人情書保存至今,仍然是等待被理想讀者閱讀的文本,尤其是其中涉及個人情感的部分。作者將自己的情感與特殊的時代背景包裹在審美的文字編碼里,等待著心靈相通的讀者解讀。它們在需要被提及的時刻,如大學里時常舉辦“讀書節”“三行情書”比賽等形式上再次出現在當代大眾視野中,成為被觀看與捆綁消費的對象。在“觀看”與“消費”中,文人情書僅作為純文本形式的材料呈現,以當代大學生為代表的普通讀者,從旁觀者的視角一瞥而過、走馬觀花,因缺乏鑒賞能力、缺少接受機會等種種原因,無法呈現與之匹配的真實價值。這一方面保護了文人情書的相對完整性,另一方面,篡改、誤讀、曲解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損害了文人情書的未來推廣與研究。
誤讀是一種文學接受現象,有根據的誤讀能夠激發讀者的思維、拓展作品的意蘊,反之則會引發許多不利于文本解讀的現象。中國現代文人情書大多含蓄而意蘊豐富,建立在動蕩的時代背景之下,有一定歷史素養積淀的讀者往往能夠合理闡發,但大多數現代讀者的解讀已然徹底偏離。新媒體傳播的信息碎片,或斷章取義,或避重就輕,讀者通過個別字句難以窺見中國現代文人情書的真實原貌。不了解作品的完整內容和復雜意蘊,自然也無從體會其中的深刻內涵,導致作者的原意無法體現,在長時間的誤讀中流失。正如《從文家書》這本現代白話情書典范,其中記錄了沈從文對張兆和的感情波瀾。沈從文追求張兆和,堅持不懈地寫了三年零九個月的情書,愛情長跑收獲的卻是婚后的困惑貧乏,華美虛空的情書文字往往盛開在不堪的生活矛盾中。“你愛我,與其說愛我為人,還不如說是愛我寫信。”沈從文總能在分離狀態下寫出動人的書信:“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單獨時,才會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為一種信仰,一種人格,一種力量!至于在一處,你的命令可把我的頭腦弄昏了,近來,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張兆和“頑固地不愛他”,“不管他的熱情是真摯的,還是用文字裝點的,我總像有我自己做錯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難過”②。文人用才華釀造出極美的情書文字是有誘惑力的,三分的愛意也可以被渲染成七分,不僅張兆和讀來有幻滅的錯覺,我們這些新媒體時代下的旁觀者也時常會陷入文字偽裝的精神交流里,從而迷失在對沈從文與張兆和這一對“璧人”的理想愛情想象里。此般不對稱的情感誤讀或背景缺失,既不利于文人情書的當下解讀,也不利于文人情書的長久研究。
且新興媒介順應快節奏的時代潮流,實現了即時通信功能,人們已經可以隨時隨地傳遞情感、交流思想。與此相比,書信的信息交流功能或許顯得雞肋和滑稽。人們厭倦了等待,等待意味著不安全感、焦慮恐懼的心理發酵,寸寸閹割著情書交流情感的功能。如今互聯網世界的更新迭代甚至觸及瓶頸期,通過郵遞系統寄送的手寫情書仿佛已然成為僅存于“從前慢”的舊時代里不可復刻的神話傳說。大學生群體是新興電子脈沖信息的忠實追隨者,甚至沉迷者。無論身處何種生活場景,隨處可見指尖滑過屏幕的瞬息光影,即時通訊讓書信的交流功能由原來的無可替代,到可有可無。到而今,一封原創手寫情書難求、難得、難覓,觀察大學生群體的情書書寫,或機械摘抄文人情書中散落的精美碎片附庸風雅,或流于空洞的形式模仿,可以說,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中國現代文人情書的文學接受情況都并不理想。
盡管大學生群體在文人情書接受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去中心化、去經典化的傾向,但并不代表中國現代文人情書在大學生群體間失去生命力和創造力。新媒體的誕生或許會將情書的交流功能徹底吞噬,卻實實在在地為中國現代文人情書的傳承提供了適時革新的思路和方法。媚俗的大眾化誤讀如舒斯特曼所言,也并不意味著放逐對審美價值的追求,高雅藝術的通俗化是更好普及大眾的有利途徑,大眾通俗文藝心理中必然享樂與媚俗的傾向與真善美的道德失落間并無直接關聯。當代大學生群體普遍受教育程度高,對文人情書的剖析和解讀也較大眾而言更為良好,具有樂觀積極的意義。適當地鼓勵并發展,可以期待今后文人情書的接受蓬勃復興。首先需要做的是,重視對大學生審美鑒賞力的提升。以基礎課程、社團活動、文化沙龍等方式滲透,結合新媒體、新技術帶來的有趣新穎的優勢,聯動培養興趣熱情,逐漸打造人文精神濃郁的閱讀氛圍;其次,積極鼓勵自發的原創而非單純的模仿。接觸兼具文學審美性與時代先鋒性的中國現代文人情書作品,自覺立正文章寫作的“風骨”。無論是“三行情書”,還是傳統的書信散文、詩歌,都需要避免情感的矯揉造作和流于形式的口水空泛。情書作為個性化和私密化的寫作空間,在保護的前提下讓大學生群體在文本中感受情懷,提升情感素質;情書寫作的進步也有助于引導大學生群體建立親密關系。
三、結語
時代潮流浩浩湯湯,為情感交流提供了更為便捷的渠道,也為情書創作提供了更加豐富的資源。在新媒體時代的背景下,我們必須意識到,文人情書的傳統正在受到沖擊,但以大學生群體為主的當代讀者的接受現狀總體樂觀。唯有正確引導,利用新媒體手段為文人情書的傳承與認可助力,同時剔除媒介更新帶來的媚俗、誤讀等干擾與誤區,才能讓二者巧妙融合,不僅從文人情書內部開出新的絢爛的花來,也從新媒體時代的外部環境中尋得接續花朵新生的活水源泉。
① 徐賁:《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 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頁。
② 沈從文、張兆和:《從文家書:從文兆和書信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