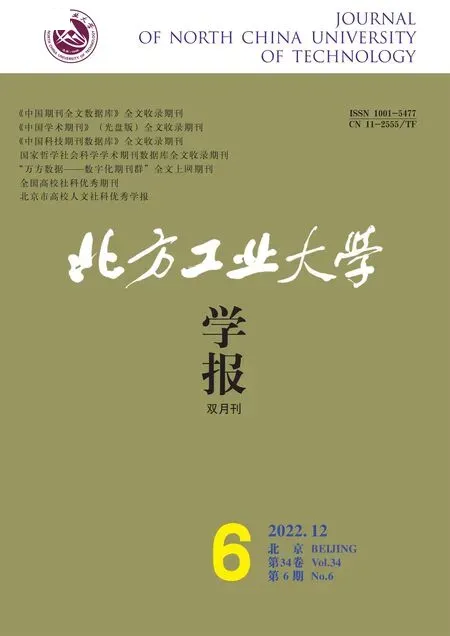典型的全景戰爭小說*
——試論恰科夫斯基的《圍困》
曾思藝
(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300387,天津)
1960—70年代,蘇聯文壇出現了著名的“全景小說”(也叫“全景—史詩式作品”“衛國戰爭史詩”“多層次、多事件的長篇小說”),其特點是:描寫衛國戰爭規模宏大的重大戰役和戰爭過程,既寫普通士兵浴血奮戰的戰壕真實,又寫軍事統帥運籌帷幄的司令部真實,從而構成戰爭的“全景圖”,卷帙浩繁,畫面廣闊,人物眾多,情節復雜,時間較長,具有史詩規模,同時讓真實的歷史人物與虛構的藝術形象相互結合,既有文獻性、紀實性,更有藝術虛構性,代表了蘇聯戰爭文學的新成就,在蘇聯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優秀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有:邦達列夫《熱的雪》(1969)、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三部曲(1959—1971)、斯塔德紐克的《戰爭》(1970—1980),以及恰科夫斯基的《圍困》。
《圍困》(Блокада,1968—1975)是亞歷山大·鮑里索維奇·恰科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исович Чаковский,1913—1994)最有名的戰爭小說,是作家創作的代表作,也是蘇聯戰爭文學中一部著名的代表作品。它是作家“花了七年緊張勞動”(該作品1968年在《旗》雜志發表第一部,1970年第二部,1971年第三部,1973年第四部,1974年底至1975年初第五部)[1]完成的長篇小說,描寫的是蘇聯軍民在德軍圍困列寧格勒時期困苦至極而又英勇卓絕的斗爭。這是全景戰爭小說的代表作之一,而且同其他全景戰爭小說相比,堪稱一部典型的全景戰爭小說。具體地看,這部小說在戰爭敘事方面有以下幾個特點。
1 場面宏大,視角變換,多層次展現全景
《圍困》共五部六卷,是長達近200萬字的巨著,主要描寫列寧格勒從1941年6月蘇德戰爭開始到1943年1月突圍戰役勝利這900多天圍困的一長段史實,展示了列寧格勒被圍時蘇聯軍民的斗爭生活。恰科夫斯基以宏大的場面、變換的視角,多層次地展現了這段史實的全景。
其場面宏大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敵我雙方均從最高統帥寫到普通士兵。蘇聯方面,從大本營最高統帥部斯大林、朱可夫等人,寫到蘇聯司令員、師長、營長,更寫到普通士兵以及平民百姓;德國方面,也從最高統帥部的希特勒及其左膀右臂,寫到圍攻列寧格勒的馮·萊布元帥及其部隊,更寫到其年輕的下級軍官、希特勒欣賞的丹微茨中校等下層官兵。二是小說雖然是以列寧格勒的“圍困”為中心,但卻以描寫重大戰役和蘇德雙方最高統帥部的活動為主,作品中著重描寫了普爾科沃高地爭奪戰、盧加防線的戰斗、涅瓦河“小地”爭奪戰、拉多加湖運輸線的開通、沃爾霍夫守御戰等關鍵性的戰爭場面,而且往往是一個方面軍與敵作戰甚至多個方面軍的協同作戰,戰爭場面頗為宏大。三是描寫了當時蘇聯為了爭取戰爭的勝利,和英國與美國之間相互進行的一些重大外交活動,更是把場面擴大到具有世界性。由此可見,《圍困》“把戰場上的軍事斗爭和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外交斗爭交錯起來寫,從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寫到列寧格勒的斯莫爾尼宮,寫到波羅的海、白俄羅斯、拉多加湖,又從列寧格勒寫到莫斯科,寫到希特勒設在東普魯士拉斯滕堡的元首大本營——‘狼穴’”,[2]還寫到英國與美國。可以說這部戰爭小說從蘇聯最高統帥部寫到平民百姓,又從蘇聯到寫德國,而且也往往是從德國最高統帥部寫到高級軍官和中層軍官,更展示了斯大林與英美的三次斗智斗勇式的外交努力,是一部真正的戰爭全景小說。小說故事情節曲折動人,善于把列寧格勒的圍困與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乃至當時蘇聯整個戰爭局勢甚至世界形勢聯系起來,展示宏大的背景宏大的場面。正因為如此,蘇聯學者西涅利尼科夫認為:“《圍困》在類型上屬于通常稱之為全景性的戰爭文學作品”,在描寫人民的功勛時有一種“規模宏大的史詩般的廣闊。”[3]
與其他全景戰爭小說相比,《圍困》堪稱典型的全景戰爭小說。如前所述,全景戰爭小說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邦達列夫的《熱的雪》、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三部曲、斯塔德紐克的《戰爭》和恰科夫斯基的《圍困》。前面幾部作品盡管既寫了戰壕的真實又寫了司令部的真實,構成了戰爭的全景,但往往以本國高層為主,從師、集團軍到最高統帥部,直至最高統帥斯大林。《圍困》則不僅如此,它還描寫了下層官兵的戰爭生活,甚至描寫了列寧格勒百姓在圍困期間的日常生活,更大量描寫了希特勒陣營高層的活動,從將軍、元帥們的討論、會議到希特勒“狼穴”的種種活動,此外還描寫了蘇聯與德國之間的外交活動,以及蘇聯與英國、美國的外交活動,從而構成了真正的世界性的或者說國際性的大場面,凸顯了蘇聯對德國的戰爭,不僅是這兩個國家之間的一場戰爭,而且是關乎世界關乎人類的世界大戰。正因為如此,諾維科夫指出,恰科夫斯基在全景小說大規模描寫戰爭的基礎上,“還力求表現國際局勢,不僅表現前線的,而且表現兩個敵對陣營的力量對比。因此,他常常采用政論的敘事手法,然而這完全無損于規模宏偉的描寫。相反,倒使畫面更寬廣了”。[4]西涅利尼科夫更簡要地指出,這部小說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宏大廣闊,分析有力,結論分明”。[5]
其視角變換表現為,整部作品總的來說大體采用的是第三人稱上帝式的敘述視角,由敘述者講述蘇聯與德國從最高層到士兵的戰爭故事以及蘇聯的外交活動,但在某些章節又適當地采用了第一人稱有限視角,主要表現在寫到女主人公之一的薇拉時,多次運用第一人稱“我”的有限視角。例如:第一卷第五章寫薇拉離開列寧格勒到小城市別洛卡明斯克的姨媽家去度暑假,而他的戀人阿納托利也緊隨而去;第四卷第六章寫薇拉經常去看望阿納托利的父親瓦利茨基,并從這個老建筑學家身上發現了對勝利的強烈信心;第四卷第八章寫薇拉與負傷住院的蘇羅甫采夫大尉交往;第四卷第十四章寫薇拉終于認清阿納托利自私、膽小、逃避作戰的本來面目并與之分手;第五卷第二部第十章寫薇拉在老院長奧西米寧的要求下,堅持記醫學日記,保留寶貴的歷史材料,第十一章寫薇拉和茲維亞金采夫重逢并相戀,第十三章寫薇拉和茲維亞金采夫遇到蘇羅甫采夫大尉,他們一起埋葬了餓死的瓦利茨基。這幾章都是薇拉以“我”的方式敘述一切,既力破全用第三人稱敘事的單調,同時也與第三人稱敘事形成某種對照:第三人稱多敘述戰爭、外交等大事,薇拉的第一人稱則更多敘述小兒女的情感、思緒,和人民在戰爭中的苦難,以及人民對戰爭勝利的信心等。或運用第三人稱有限視角,如小說一開篇即寫茲維亞金采夫少校和科洛霍夫上校在“莫斯科”旅館里,茲維亞金采夫突然被安排到新的條件很好的房間去住,這使他們大惑不解。后來才知道,這是他在斯大林組織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只有人民委員、元帥們、將軍們才能參加的對剛結束的芬蘭戰爭進行總結的會議上大膽發言說了真話,贏得斯大林的好感而產生的結果。這種第三人稱有限視角一方面讓本來不可能的事情顯得真實可信(蘇聯有讀者指出,一個少校軍官在這種級別的會議上發言根本就不可能。恰科夫斯基本人卻宣稱:“我需要讓能夠講出我們備戰中缺點之人在會上發言。”[6]另一方面也讓敘事人稱有所變化。第二卷第十一章寫丹維茨去見希特勒也采用的是第三人稱有限視角。
由此可見,上述宏大的場面、變換的視角,的確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現了蘇德戰爭的全景,更真實生動地展示了圍困期間列寧格勒百姓的生活與心理。
2 人物眾多,虛實結合,多角度反映歷史
白照芹指出,《圍困》的篇幅龐大,結構復雜,人物眾多。據統計,小說中出場的有姓名的人物達130余人。其中著重描寫、清晰地展現了人物思想面貌的約38人(蘇方29人,德方9人)。在這些人物中,既有真名實姓的歷史人物,又有作家依據生活實際虛構出來的典型人物。作家嚴格遵循歷史真實性的原則,按照實際曾經發生過的事件的本來面貌描寫歷史人物,而把虛構人物穿插于其間,做到虛實結合,不僅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情節更加富于戲劇性,而且也極大地增強了作品的藝術魅力。[7]黃仕榮更具體地談到,恰科夫斯基的《圍困》,刻劃了近300個人物,歷史上的真實人物有百人之多。其中有蘇聯黨政軍領導人和著名的將領: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伏羅希洛夫、朱可夫等等;還有法西斯營壘中的頭目和將領:希特勒、戈林、希姆萊、戈培爾、里賓特洛甫等等,丘吉爾的特使比威爾布魯克以及羅斯福的特使霍普金斯、哈里曼、英國外交大臣艾登等等。對這么一大批歷史上的真實人物,恰科夫斯基都作了生動具體而詳盡的描寫。幾乎對每個人的出身、來歷、外貌特征、性格特點、他們在這場戰爭中的表現,他們的相互關系,他們細微的心理活動等都寫到了,使他們達到典型的高度。[8]陳敬詠更是宣稱,《圍困》中出現的蘇聯反法西斯戰爭中眾多歷史人物是蘇聯文學前所未有的,特別是法西斯營壘中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9]
仔細考察,《圍困》中出現的近三百個人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如蘇方的斯大林、朱可夫、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日丹諾夫、華西列夫斯基、霍津、費久寧斯基、庫茲涅佐夫、沃羅諾夫、杜哈諾夫、沙波什尼科夫、貝利亞、米高揚、柯西金等等,德方的希特勒、戈培爾、戈林、里賓特洛甫、希姆萊、凱特爾、布勞希奇、哈爾德、約德爾、馮·柏克、馮·萊布、曼施泰因、古德里安等等,以及英國的外交大臣艾登、丘吉爾特使比威爾布魯克和美國的羅斯福的特使霍普金斯、哈里曼等等。蘇聯學者奧夫恰連科指出:“《圍困》中使我們一直感興趣的是真實歷史的那部分描寫……交戰雙方都是通過真實人物來表現的(主要關注杰出歷史人物)——這使人對小說的興趣更加濃厚。”[10]一類是虛構的人物,如工程兵少校茲維亞金采夫,老工人老布爾什維克科羅廖夫及其女兒薇拉,老建筑學家瓦利茨基,紅軍基層干部帕斯圖霍夫、蘇羅甫采夫,還有德國黨衛軍少校丹維茨等。
《圍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兩個特點。一是塑造敵方形象不夠成功,主要在于作家意識形態性太強,過于貶低和丑化德軍元首、將領和下層官兵,因而其形象都是模式化的壞人,過于單一;但塑造蘇方形象卻比較成功。二是虛構人物不夠成功,而歷史人物卻塑造得頗為成功。因此,諾維科夫宣稱:“《圍困》中真實的歷史人物比許多虛構人物刻畫得更具藝術技巧。”[11]一般來說,歷史人物不好描寫,因為受制于歷史真實,而虛構人物往往可以放開寫,所以最能出彩。而《圍困》恰恰相反,虛構人物絕大多數塑造得頗為單薄,缺少變化(哪怕是自私自利的阿納托利,經歷了被女友薇拉趕走和父親瓦利茨基的教育,卻依然毫無變化)。限于篇幅,此處僅以最重要的主人公茲維亞金采夫為例,稍加論述。
茲維亞金采夫形象在小說中塑造得不那么成功,關鍵在于作家把他觀念化(正面人物、紅軍優秀軍官的化身)和工具化(串聯眾多場景,溝通上下人物)了。蘇聯學者西涅利尼科夫指出:“茲維亞金采夫是一位在長篇小說中賦有特別功能的主人公”,[12]陳敬詠更是對此有比較具體的分析。他指出,作家試圖通過茲維亞金采夫這個形象表現紅軍軍官的某些優秀品質:高度的思想覺悟、忠于職責、精于業務、善于在任何艱難條件下完成任務……總之,茲維亞金采夫是作者刻意塑造的正面人物。但是,總的看這個人物缺乏完整的藝術性。茲維亞金采夫的活動貫穿于五大卷小說的始終,這個青年軍官經歷了將近兩年的戰斗歷程。可是,我們只看到他在官階上的陡升,卻看不到他在思想上的成長。正是由于作者的主觀“需要”,使茲維亞金采夫形象的藝術完整性受到了損害。[13]
《圍困》塑造歷史人物卻頗為成功,如伏羅希洛夫、戈沃羅夫、日丹諾夫、費久寧斯基、華斯涅佐夫等。朱可夫雖然出場不多,著筆也不多,但作家卻能用不多的筆墨寫活這位人物。如伏羅希洛夫被任命為列寧格勒方面軍司令員后,“面對集結起來的德軍,列寧格勒的防御混亂無序”,[14]只是被動、消極地敵人攻向哪里,就派部隊到哪里去阻擋、抵抗。西方有學者甚至認為:“最高統帥部代表伏羅希洛夫元帥,在負責列寧格勒防務事宜期間與其說是在做貢獻,還不如說是在搗亂。”[15]因此到了1941年9月,列寧格勒已經極端危急。就在此時,朱可夫臨危受命,馬上趕往總參謀部和情報部,不僅了解列寧格勒的局勢,而且了解全國其他戰線的局勢,然后火速飛往列寧格勒,并且雷厲風行,立即開始工作。他沉著冷靜,怒斥報告“極其緊急情報”的驚慌失措的西多羅夫少校,命令他必須守住自己的地段,否則送上軍事法庭;然后聽取報告,具體了解列寧格勒的情況,并且對毫無針對性的防御,指出不能在整條戰線上平均部署部隊,而應該在德軍坦克部隊已經楔入的烏里茨克和普耳科沃高地,調整并集中主力部隊,并馬上根據實際情況,明確而絕對地調整部隊部署。這樣,不僅改變了戰爭的打法,而且讓上下官兵精神一振,有了主動進攻的心理,從而穩定了戰局,守住了列寧格勒。以致蘇聯學者奧夫恰連科認為:“在《圍困》中,這些人物都是在極度緊張的情況下說話和行動的。每一分鐘都飽和到極限。朱可夫將軍剛剛抵達列寧格勒。一小時后他出現在斯莫爾尼宮。把斯大林那像格言一樣簡潔的字條轉給伏羅希洛夫。‘給指揮官搬椅子!’伏羅希多夫大聲吩咐。沒過幾分鐘,朱可夫已經在列寧格勒前線指揮戰斗。他的命令清晰明確,格外大膽,完美而獨立。他的話語也極富特色。這是生活。但這也是《圍困》作者創造的一個傳說。”[16]
由于朱可夫的鎮靜理性,總是從全局考察戰爭,又能根據實際情況,雷厲風行,干脆利索,靈活而果斷地采取對策化解危機,因此,在小說中他幾乎就是一個“救火隊員”,哪里危急,就派他去,而他一去,必定化險為夷:是他,穩定了列寧格勒的局勢,守住了這座城市;是他,贏得了莫斯科保衛戰;還是他,解救了斯大林格勒,并且消滅了德國精粹的保盧斯集團軍。保加利亞學者、批評家葉夫列姆·卡郎菲洛夫認為《圍困》中塑造的朱可夫形象“異常鮮明”。在他看來,小說的另一個優點是:對兩軍司令部及其領導人進行對比時,就會發現蘇軍統帥在道德上的優勢和高度明顯高于希特勒的將軍們。另外,他們的創造力也明顯高于后者。因為與希特勒冷酷而精準的戰略意圖相對立的是高超的戰爭藝術,那恰恰就是創造者的藝術。[17]
盡管有人認為,小說中的斯大林形象塑造是不成功的,如許賢緒認為,《圍困》中的斯大林形象基本上反映了朱可夫對他的看法。他沒有“科學預見的才能”,錯誤估計希特勒發動戰爭的時間,在戰爭的最初幾天里驚惶失措,甚至躲在家里不露面;他沒有軍事指揮才能,在戰爭形勢分析、戰略指導思想、戰役部署等方面總是與朱可夫意見相左,而結果總是證明他錯了。他的固執和絕對權威地位使紅軍大吃苦頭。《圍困》對斯大林的肯定是抽象而又無可奈何的,對他的否定則是十分具體的。只有在外交活動方面,作者對斯大林作了全面的肯定。戰爭初期,外交活動頻繁,斯大林在會見美、英來使時態度鎮定、自信,對國際國內形勢了如指掌,準確及時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使對方有的肅然起敬,有的張皇失措。總之,在恰科夫斯基的筆下,斯大林是個蹩腳的軍事家,同時卻是個出色的外交家。這反映了作者的實用主義立場,因為斯大林在戰時和戰后的全部外交活動,都與蘇聯的新邊界以及整個歐洲政治地理有關,這是不能否定的,而迎合朱可夫的觀點在當時是一種時髦。但這樣把斯大林寫成在軍事上和外交上判若兩人,是不合邏輯的,讀者從中看到的不是斯大林性格中的矛盾,而是作者自己的矛盾。[18]
但在筆者看來,小說中塑造得最為成功的恰恰是斯大林形象(蘇聯學者西涅利尼科夫也認為:“小說中的斯大林是一個有著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弱點的活生生的人”[19]),其成功之處在于通過一系列戰爭和外交事件,寫出了斯大林性格的矛盾復雜性和發展變化,既寫出了他作為最高領導人的優點,也寫出了他在蘇德戰爭初期的失誤,更客觀地描寫斯大林醒悟后的英明決策,還寫出了他的人情味。
小說多處寫到斯大林性格的矛盾性,如他不許別人有或真或假任何虛榮和自滿的表現,可同時又鼓勵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又如當眾對他討好,稱他為“偉大的斯大林”、“領袖和導師”,他可以接受甚至鼓勵,但在談公事時卻不能忍受別人的阿諛奉承。小說進而寫到戰爭初期斯大林變得較為寬容,能夠聽取軍事專家們的意見,而且他在作出某種重大的決定時,通常總是依靠統帥部里的高級軍事首長和黨的領導人的學識與經驗,也考慮總參謀部和各個方面軍司令員的意見。在這特殊時期,斯大林意志靈敏的頭腦、組織才能與軍事才能等都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但在一些大的戰役指揮方面,他有時不免固執己見,甚至為此處罰執不同意見的人(朱可夫就因為不贊成其不切實際的想法而被一度貶職)。但小說最終充分肯定,在贏得衛國戰爭的勝利中,“作為最高統帥的斯大林是作出了重大貢獻的”。
小說進而寫到斯大林的矛盾性格在戰爭中的發展變化,不過,也常常出現反復。小說寫道:戰爭中的每一個月、每一天都在影響著斯大林的性格,使他變得較為寬容,較為喜歡傾聽別人的意見,較為重視人,特別是方面軍和集團軍的司令員了。但是這些變化的產生并不是沒有經過內心斗爭的。時常發生這樣的情況:從前的斯大林,相信自己的智力勝過周圍所有的人,深信多年政治經驗不僅增長了他的才干,也賦予他以作出唯一正確決定的不容置疑的權利,這時從前的斯大林有時就壓倒那個已經深知失敗的痛苦和過于自信所產生的最嚴重后果的斯大林。他熱切地渴望扭轉戰局,渴望戰勝敵人,這是很自然的。蘇軍的英勇抵抗,證明它不僅有能力打防御戰,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還能迫使德國人后退,這就更增強了斯大林的信心,相信他提出的目的立即能夠達到。他熱切地渴望扭轉戰局,加上遠沒有徹底克服的認為自己看問題比任何人都深刻的自負,有時候就促使斯大林作出了以后使他不能不為之后悔的行為,盡管只是暗自后悔。此刻,深信自己掌握了終極真理的從前的斯大林,又與學會了尊重別人意見、認識到自己的不正確、必要時會作出讓步的斯大林,重新展開了斗爭。結果是從前的斯大林占了上風。①
小說還通過斯大林把中學同學、早年的革命同志列瓦茲·巴卡尼澤請到克里姆林宮,表現斯大林的人情味。盡管他們已經分別了40多年,從未聯系,當斯大林看到這個名字,猛然想起中學和早年革命時期的往事后,馬上吩咐把列瓦茲“帶到我這里來”。見面后,他邀請列瓦茲一起共進早餐,關心他的身體,對他戀戀不舍。這樣,小說就寫出了“鋼鐵”般的革命領袖斯大林的人情味。
正因如此,學者潘科夫指出:“小說《圍困》對斯大林的總司令形象塑造比其他或多或少地刻畫過他的任何作品都細致。當然,恰科夫斯基不企望完整地表現斯大林的性格特征。小說中有些情節強調戰爭進程如何對斯大林產生影響,如何改變他對人們的態度,如何提醒他仔細權衡軍事領導人的意見和經驗,這些情節是重要的。……在為數眾多的場景中,斯大林被表現得相當多樣化——有與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官的交流,也有單人獨處的情景(在思考和做出重大決定的時刻)——但無論哪種情景,他都在做要求集中思想、意志、考慮當代現實諸多因素的大事。”[20]
3 縱橫結合,前后呼應,嚴謹而真實地描寫戰爭
所謂縱,是指小說大體采用編年史的方法,從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四天開始,逐年描寫,一直到1943年1月突圍戰役勝利,表現列寧格勒被圍困前后900多天列寧格勒的苦難生活與戰斗場景,對所描寫的歷史事件特別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了幾乎是“編年史”般的真實描寫,從而具有了真實性和深刻性。所謂橫,指的是小說不僅描寫列寧格勒,而且把列寧格勒戰役放到整個蘇德戰爭的全局中去表現,更花了不少筆墨,描寫德軍最高層和將軍們的戰略布局和戰爭會議,進而把蘇德戰爭放到世界性或者國際性的背景中加以表現,描寫了蘇聯與英國、美國等的外交談判,以此說明這場戰爭不僅是蘇德之間的一場戰爭,更是關系到人類前途的一場戰爭,表現出其他全景小說少有的世界視野或國際視野。黃仕榮指出,《圍困》在真實描寫衛國戰爭的廣闊畫面的同時,對敵、我、友三方面在戰爭中的地位、對戰爭的態度、優勢和劣勢、彼此間的關系等方面,都作了詳盡的剖析,從而加強了戰爭描寫的深刻性。就以所涉及的國際關系來說,作品將蘇、美、英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系描寫得入木三分。在《圍困》的五大卷篇幅里,作者對斯大林與英美兩國使節的會見或談判,有三次集中描寫。作者將筆觸深入到事件的深層,深刻剖析和精細描寫了當時的形勢,斯大林本人對形勢的估計,斯大林的內心活動以及這些英美使節本人的身世、政治觀點,對共產主義的一貫態度和他們目前對形勢的估計,甚至對他們此時此刻的心理狀態,他們此行的用意等。通過這些深入的剖析和精細的描寫,將英、美、蘇三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德國法西斯的態度、作用作了真實、深刻和藝術的揭示。這不僅有助于讀者對歷史的認識,也使他們受到藝術的感染。[21]《圍困》的縱橫結合,既使作品因為編年史而顯得真實深刻,又因為國際視野而使小說具有相當的廣度與深度。
前后呼應在小說中運用較多,使200萬字的作品前后勾連,結構嚴謹。
一是通過茲維亞金采夫及與之有關的幾個主要人物進行前后呼應。在小說的結尾,茲維亞金采夫不僅見到曾一同工作過的科洛霍夫,并從他那里得知了自己所深愛的其女薇拉還活著,在列寧格勒對岸的沃爾霍夫方面軍衛生營服役;還寫了茲維亞金采夫似乎看到和他在盧加防線一同戰斗的蘇羅甫采夫大尉領兵從涅瓦河上沖向對岸德軍陣地打破圍困,且知曉了同時和他在盧加防線一同戰斗的帕斯圖霍夫為了救傷殘的戰士而英勇犧牲;更寫到他在掩蔽部門口見到被押送去受審的、曾在盧加附近用望遠鏡看到過的丹維茨。茲維亞金采夫還見到自己曾經給他留下不錯印象的沃爾霍夫方面軍副司令員費久寧斯基,并且這位副司令員還想把他從列寧格勒方面軍要到自己那邊去;還見到華斯涅佐夫——他不僅在第一部里聽他談工事建筑,而且在第四部里幫他尋找薇拉和帕斯圖霍夫;更重要的是,他在相隔一年半后再次見到在盧加防線見到過的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而且元帥告訴他,1941年夏天他在盧加防線所講的那些話對自己很有用,也很必要,就像是一朵火花,與明天代號為“火花”的戰役很有關聯。這種前后呼應,不僅串聯起上層和下層,蘇軍和德軍,而且使作品過去與現在結合,前后勾連,結構嚴謹。
二是其他多位人物構成的前后呼應。費久寧斯基曾跟隨朱可夫到列寧格勒指揮作戰,在朱可夫被召回莫斯科指揮莫斯科戰役后一度還獨當一面指揮列寧格勒保衛戰,最后被調離列寧格勒方面軍,到第五集團軍擔任司令員,但在列寧格勒解圍戰中,他又被調到列寧格勒,擔任沃爾霍夫方面軍的副司令員。而因為最初指揮不力導致列寧格勒危急的伏羅希洛夫元帥曾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在列寧格勒解除圍困的關鍵戰事中,又作為統帥部的代表派往列寧格勒。朱可夫曾在列寧格勒極其危險的關頭一度到這里救火,到解除圍困時,又被斯大林派往沃爾霍夫方面軍協同指揮。阿納托利則在結尾時因為見到由于戰敗被俘的德軍上校丹維茨,而想起自己在第一部曾經被德國人抓住并受丹維茨脅迫而朝自己人克拉夫佐夫開槍,隨即拋棄戀人薇拉獨自逃跑,此時見到丹維茨害怕被其認出從而原形畢露,因此狂奔亂跑,結果被地雷炸死。從第一部開始,青年丹維茨就對希特勒盲目地無限崇拜,然后鐵的事實讓他終于認清了希特勒的真面目,在第五部,他對希特勒的崇拜之夢最終破滅,甚至對他產生了憎恨之情。
這種多人構成的前后呼應,主要作用是讓作品前后勾連,結構緊密,個別也寫出了人物心理的發展變化,如丹維茨對希特勒從崇拜到憎恨。
這樣,盡管《圍困》人物眾多,時而蘇軍時而德軍,時而上層時而下層,時而蘇聯時而英美,大度跳躍,結構復雜,而且篇幅巨大,但由于上述縱橫結合、前后呼應,使得整部作品依然脈絡分明,層次清晰,照應周密,頗為嚴謹。
綜上所述,《圍困》較之其他全景小說場面更宏大,視角也較多一些變換,人物塑造更具立體感,結構雖然縱橫開闔更大,但卻頗為嚴謹,因此,馬家駿等學者認為:“《圍困》反映的時間長,歷史畫面廣闊,情節結構曲折復雜,軍事斗爭與外交斗爭相結合,虛構人物與歷史人物眾多,而虛構人物(如青年軍官茲維亞金采夫)則起著串聯情節和評價歷史人物的作用。恰科夫斯基作為列寧格勒前線記者和圍城情景的目擊者,真實地反映了列寧格勒保衛戰,同時他還利用了大量文件、回憶錄、日記等材料,成功地把藝術虛構和紀實性結合起來,讀來使人倍感親切、令人信服。可以說《圍困》是‘全景文學’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22]而俄國學者西涅利尼科夫則宣稱,由于靈活“運用多種多樣的表現手法,恰科夫斯基獲得了極大的藝術自由”。[23]正因為如此,《圍困》成為1960—70年代“全景戰爭文學”的代表作,并于1978年獲得蘇聯文藝最高獎——列寧獎金。
注釋:
① 本文中所引用的《圍困》中的文字和內容,均出自亞·恰科夫斯基.圍困(第一卷—第五卷)[M].葉雯,江峨,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1979。為節省篇幅,不一一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