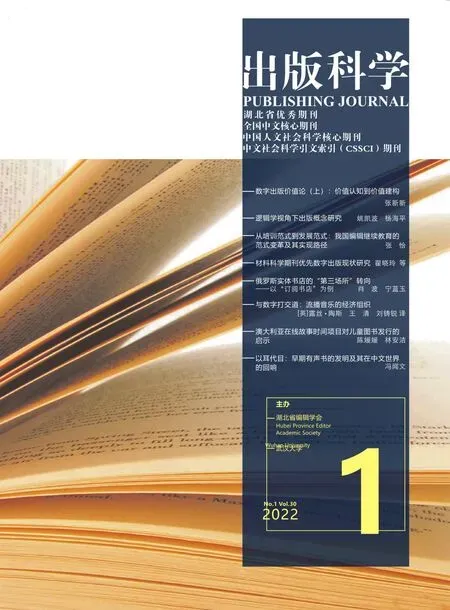出版產業對外貿易政策演進與績效評估
智曉婷 何怡婷



[摘 要] 以規制理論為視角,通過梳理1992—2020年出版產業對外貿易政策,探究其由進入規制向規制改革與重建的演進特征,并根據出版產業進出口貿易總額、進出口數量和版權引進輸出比三項指標評估此階段產業績效,從而檢驗政府規制效益,揭示政府規制與出版產業對外貿易發展的關系。
[關鍵詞] 政府規制 出版產業 對外貿易政策 產業績效
[中圖分類號] G23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5853 (2022) 01-0042-09
The Evolut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Foreign Trade Policy in Publishing Industry: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1992—2020)
Zhi Xiaoting He Yit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207)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u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ts entry regulation to regulation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by combing the foreign trade policy of publishing industry from 1992 to 2020, and evaluates th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mport and export quantity and copyright import and export ratio of publishing industry, so as to test the benefit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in publishing industry.
[Key words] Government regulation Publishing industry Foreign trade policy Industrial performance
1 引 言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放松規制成為中國產業規制改革的主流[1],但由于出版產業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1992年至2001年十年間,政府對出版業的規制仍未放松,期間以加強版權貿易規制為核心。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組織規則和國內出版產業“走出去”戰略共同對政府規制改革提出要求,出版產業對外貿易發展進入新階段。2021年12月28日,新聞出版署印發《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進一步表明在“十四五”時期,中國出版走出去仍是重點。
規制(Regulation)即政府通過權利限制和促進保護兩種途徑對市場進行干預[2]。政府規制包括規制原因、規制措施及規制效益,其中規制效益的評估涉及規制的改革[3]。進入規制是政府規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有學者認為進入規制是政府對企業的進入和退出行為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和監督行為[4]。但是隨著市場背景的變化,政府規制可能存在規制成本大于效益的情況,需要政府通過規制改革來調整政府干預與市場自由競爭之間的關系,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出版產業處于塑造意識形態的特殊地位,歷來是政府規制程度較深的行業。國內部分學者意識到出版產業政府規制的必要性,出版產品的公共屬性和出版產業的雙重效益決定了政府規制和規制改革的必要性。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對外開放背景下,政府規制政策在維護我國文化安全方面發揮了作用[5] [6]。
政策是推動出版產業發展的核心要素,同時出版產業發展的績效為政策的實施與調整提供航標。梳理發現,出版產業政策績效評估主要有建立評估指標體系和經濟模型兩種方法。一是通過經濟模型來評估產業績效,其中成本效益分析法和成本效能分析法是最常用的兩種分析方法[7]。出版物作為文化產品,受到多元外部因素的影響,這也決定了出版產業政策績效評估的復雜性,建立評估指標體系能夠探究多種因素對政策績效的影響。趙禮壽建立了出版產業政策的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出版產業發展指數和相對增長率,分析產業發展狀況與政策之間的關系[8]。徐小傑采用出版產業規模狀況縱向比較分析模型,即通過供給能力、盈利能力和貿易能力三項指標,對我國出版產業政策績效做出歷時性的評估,供給能力指的是圖書出版產業的整體供給水平,盈利能力則反映了圖書出版產業的整體盈利狀況,貿易能力主要體現的是圖書出版產業版權貿易進出口情況[9]。劉大年在徐小傑研究的基礎之上,結合中國出版業大環境添加了數字出版物的發展狀況這一指標[10]。徐小傑所采用的縱向比較分析模型,通過對出版產業市場規模進行連續性考察,從而判斷、評價產業政策制定是否合理,論證進一步提升指標的科學性。結合研究需要,本文借鑒徐小傑的縱向比較分析模型,根據1992—2020年的出版業貿易數據,連續性評估出版產業貿易政策績效,將貿易能力操作化為進出口貿易總額、數量、版權貿易引進輸出比三個指標,并結合中國出版業發展的背景環境,以一定的定性分析和政策依據作為補充。
國內有關出版產業對外貿易政策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整個出版產業政策的宏觀研究之中,而以規制理論為視角的相關研究側重規制和規制改革必要性。產業績效評估是政策調整的重要依據,因此考量政策與產業績效的關系對于產業發展具有指示作用。但目前在出版領域,將二者結合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梳理了出版產業對外貿易政策,并結合國際因素、市場結構、產業特性的背景探究其演進路徑;同時發現政府規制與產業績效之間相互影響。通過對產業績效評估可檢驗規制效益,以期及時調整政策,提高政府規制水平。
2 出版產業對外貿易的政策演進
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之后,國有企業改革進入制度創新階段,“政企分開”繼續深化,但出版產業依然處于“事業單位,企業化運營”的二元體制之中,改革步伐遠遠落后于其他產業,成為“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后一塊堡壘” [11]。直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2003年出版業正式確立以產業化為主導,進入規制的狀況開始發生變化。
2.1 進入規制下的出版貿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2001年我國出版產業對外貿易處于政府的強規制階段,為了對政策文本進行分析和研究,本文按照規制理論的邏輯將出版產業對外貿易政策分成市場進入規制和激勵規制兩個方面,梳理發現,這十年來我國出版產業強調結構轉型與法制化建設,促使出版產業加強進入規制。為適應國際組織的規制需要,加強對外版權貿易規制成為該階段主要特點。
2.1.1 出版產業結構轉型與法制化建設強調進入規制
建立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報告》,其中明確指出,要推動整個出版業的發展從規模數量增長向優質高效進行階段轉變,總的工作方針是:一手抓繁榮,一手抓管理[12]。這表明,我國出版市場結構開始從規模型向質量型轉移。1992—2001年是出版政策法規體系的構建階段,國務院先后頒布了“一法五條例” ,成為指導出版工作最基本、最重要的政策法規[13]。由出版市場結構從“增量”向“求質”的轉型和出版法規體系的完善可看出,加強政府規制成為此階段我國出版產業政策的價值取向。具體到對外貿易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1994)的出臺標志著我國已經進入對外貿易法制化階段。此時期我國圖書進出口機構數量逐年上升,到2000年全國出版物進出口機構數量已達三十多家[14],出版物進出口范圍限制縮小,貿易量迅速增長。同時,在全國范圍內出版業“增質”轉型的推動下,版權貿易領域的政府規制仍然呈現出“強規制”的特征。
2.1.2 國際合作需求與國內政治導向要求版權貿易規制
1992年我國加入《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品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整個出版產業面臨出版市場結構轉型、法制化建設的多重需求,同時受到國際組織規則的制約。版權貿易活動成為這一階段出版產業對外貿易規制的主要對象,具體表現在從事版權貿易的企業市場準入和企業行為管理規制兩個方面。
以“版權”為核心,我國先后頒布了21條政策法規,其中20條屬于對版權引進的管理,僅有1條涉及對出版物出口的激勵,所以該階段體現出顯著的版權引進規制特征。《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狀況白皮書》(1993)中表明了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立場。隨后,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以加強版權貿易規制。企業行為管理方面,通過合同登記的方式對出版物進口進行管理;企業市場準入方面,相關政策限制外資進入我國出版市場并強調涉外版權代理機構的準入條件。政府規制矯正和改善了市場機制的內在問題,形成了規范化的版權貿易體制。此階段對版權貿易進行規制的必要性在于兩個方面:第一,版權貿易所涉及的商品是精神產品,其引進和出口所能產生的影響較一般商品更為復雜。出版物的國際貿易會使不同國家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互相滲透和影響。第二,出版業在對外貿易上不僅指向經濟目的,同時還含有政治目的,即出版業通過圖書、報刊宣傳本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在引進他國文化時必須堅守本國的精神陣地,對出版物進口貿易不得不加強管制。此階段立足于國家版權貿易規制一方面是國際合作的外生需求,另一方面是出版業政治導向的內生需要。
2.2 規制改革與重建下的出版產業對外貿易政策 (2002—2020年)
政府機構是最為核心的規制主體,但隨著新規制實踐的發展,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組織和區域性組織等也被納入規制主體,與政府規制協同作用[15]。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出版產業進出口貿易和知識產權等領域的政府規制日益受到國際組織的影響和制約,要求放寬外資進入我國出版市場的限制。從我國出版產業對外貿易的自身發展狀況來看,面臨文化產業對外發展較大的貿易逆差等現實情況,需要不斷采用激勵規制的手段促進出版產業“走出去”。因此,我國政府對出版產業對外貿易的規制改革是本國出版產業發展與國際貿易組織規則的共同要求。
2.2.1 規制改革:國際組織規則與國內產業需求推動
相對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政府以進入規制為主要手段干預版權貿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政府規制改革主要從兩方面開展:一是為引進外資而放松對出版產業對外貿易進入規制,二是為推進出版產業“走出去”采取規劃布局、財稅等手段進行激勵規制。
放松規制。放松規制指政府取消或放松產業的進入施行的行政和法律規制,包括全面撤銷對受規制產業的限制,使企業完全處于自由競爭狀態;或部分地取消規制,較原來嚴苛的規制條款更為寬松、開明[16]。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我國承諾在出版物分銷和印刷領域允許外資進入,但不允許外資創辦獨資分銷企業,并對外資進入我國出版市場設立了一系列準入條件。隨后相關政策的頒行,拉開了我國出版產業部分領域對外開放的序幕,對接納外資進入我國出版產業分銷企業作出了時間和條件的明確規定。同時,為了對外資進入我國出版市場進行引導,政府出臺了系列配套措施和補充規定,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04)、《關于文化領域引進外資的若干意見》(2005)等。相關措施進一步明確我國出版產業對外開放的領域及準入條件,并根據市場發展情況對政策進行不斷調整和補充。
這一時期,我國關于出版產業對外開放的領域限于書報刊分銷業務和音像制品批發零售、特許經營等方面。相對于市場經濟確立初期政府對出版產業市場化的緩慢探索,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促使政府進行規制改革,出版產業對外貿易借此實現了巨大跨越。除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外,20世紀末全球文化產業的興起也對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軟實力的提升提出了挑戰,而出版產業作為文化產業的主力,必須著眼于全球化的市場背景,加快“引進來”與“走出去”的協調發展。
激勵規制。激勵規制指政府給被規制企業提供相應刺激的辦法,從而誘導其實施某種行動,以實現規制目的[17]。市場經濟確立后,政府規制強調出版產業版權引進與輸出行為的規范性。但這一時期版權引進與輸出卻表現出較大的貿易逆差。單從圖書版權貿易來看,1995年圖書版權引進輸出比例4.7∶1,但1999年上升至15.5∶1,到2001年仍達12.6∶1的高比例。由此看來出版產業在大力“引進來”過程中忽視了版權的輸出。為解決這一問題,借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推動,政府開始布局“走出去”戰略。
關于“走出去”戰略,政府主要通過宏觀產業政策布局和具體的財稅政策相結合來激勵出版產業出口貿易的發展。在宏觀布局方面,政府頒布系列文化產業政策,對出版產業的外向發展進行刺激,強調各部門應當對出口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給予金融、財稅、法律、人才、出入境管理、信息服務等多方面優惠,并對出版單位給予資金支持。從國家層面對出版產業走出去進行規劃布局,財政部、商務部、國家稅務局等部門對出版“走出去”給予金融支持和稅收優惠 。在大量政策激勵下,2011年,出版產業“走出去”經過十年發展,圖書版權引進輸出比降到2.5∶1。
宏觀政策布局為出版產業“走出去”提供了明確的方向指示,但由于宏觀政策的寬泛性導致其落實滯后于產業發展需要,這要求配套政策及時補充和直接推動。財稅政策和獎勵機制彌補了宏觀政策可操作性的缺陷,對刺激出版產業出口貿易產生了直接效益。
2.2.2 規制重建:平衡產業結構與規避文化風險
放松和激勵的協同作用調整了出版產業進出口貿易結構,改善了貿易逆差局面。但放松規制并不是政府完全放松對過去規制行業的規制,而是在引入競爭的同時制定相應的配套措施來規制進入市場的行為。政府在放松具體規制的同時建立起一套更為寬泛的規制體系,即規制改革中的規制重建[18]。放松規制促進了我國出版產業對外開放,并迅速融入全球化,但引進大量外國出版物,對我國文化安全造成威脅,此時,規制重建對于規避文化滲透的風險和維持出版產業進出口貿易平衡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政府對出版產業對外貿易規制的重建可從兩方面理解,一是放松規制與重建規制并重,即在放寬外資進入限制的同時,強調外資進入的條件,放松規制與加強規制在同一政策文件中體現。從具體的放松規制政策可知,政府允許外資進入出版產業分銷、印刷等領域,但在放寬限制的同時,對進入的出版資格(業務能力)、資本、場所、期限等進行明確規定。二是強化具體規制,即頒發專門性政策對進口經營單位市場進入、進出口出版物數量和質量進行規制。對于前者,政府主要采取審批、年檢登記、核發許可證的方式加強進口貿易準入限制;而對于后者,政府通過實施打擊違法進口行為、對進口出版物進行內容審查來加強進口出版物質量的管理;通過目錄備案的方式來規制進出口數量。
3 出版產業對外貿易政策績效評估
出版產業政策評估是根據收集的客觀材料和設定的評價標準,對政策實施過程中的投入與產出、效率與影響進行判斷和評定[19]。政策評估能檢驗政策效果、提高政策水平、促進資源有效配置。出版政策的績效評估對提高出版政策的制定水平和執行效率、促進出版資源的合理配置至關重要[20]。對圖書出版產業的貿易能力進行評估時,采用進出口貿易總額來表示圖書出版產業的貿易能力更加直觀和清晰[21],本文將出版產業貿易能力按照進出口貿易總額、進出口數量、版權引進輸出比三個指標來考量出版產業對外貿易發展情況,以此來體現相關政策的供給水平和規制效益。
3.1 “引進來”導向下的貿易結構失衡(1992—2001年)
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強調資源合理配置與有效利用,僅從產業結構角度看,國內供給與需求出現無法協調的情況時,可以通過進出口貿易進行補充調節[22]。但具體到我國出版產業貿易結構,除了國內出版產業結構因素,還面臨產業特性、國際因素等影響。1992—2001年我國出版產業對外貿易以內向型為主,版權貿易規制占主導。1992年中美達成版權保護的雙邊協議并且加入了《世界版權公約》和《伯爾尼公約》。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升,市場對引進出版物需求擴大。
從政府規制來看,此階段有關版權引進政策共18項,政策出臺數量總體趨勢呈波動上升。反映到出版產業進出口貿易上,進出口貿易差額不斷上漲,圖書版權引進輸出比呈現出逐年增大的趨勢(圖1)。到2001年,我國圖書版權引進輸出比已達12.6∶1,仍處于較大的貿易逆差之中,產業貿易結構嚴重失衡。回溯政策,這一時期政府出臺了大量有關版權引進的政策,且頻率較高,但是有關版權輸出的政策則相對缺乏。由此形成的內向型貿易情況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契機共同推動政府明確實施 “走出去”。
1995年我國制定的“九五”計劃中明確指出:競爭性行業由市場進行配置,基礎性行業也要引入競爭機制,從而使經濟更具活力。相關版權引進政策一方面為了大量引進而放松出版產業的進入限制,從而填補國內圖書資源短缺,激發市場活力;另一方面在大量版權引進時卻引發了行業亂象。市場環境的混亂、圖書結構的不合理以及產業體制的僵化等問題亟待解決。因此,國家在1994—1998年頒布了一系列政策對圖書書號、圖書質量、圖書出版單位進行嚴格限制。尤其是對外貿易中,大量外國出版物的涌進不僅引發了版權紛爭,促使政府出臺了規范涉外機構準入和合理引進出版物的相關政策,這些政策具有明顯的強規制特征,在規制出版對外貿易和維護我國文化安全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引進來導向下的政府規制,首先在放松進入規制中刺激了圖書進口貿易,同時又在治理行業亂象中確立了版權貿易規范,構建了基礎法制體系。與進口規制相比,刺激出口的相關政策缺位使得出版產業結構仍存在不平衡。長期處于失衡狀態的貿易結構為“走出去”路線的確立提供了經濟依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通過激勵和放松規制來緩和貿易逆差、調節貿易結構成為迫切需要。
3.2 “走出去”導向下的協調發展(2002—2020年)
出版產業對外貿易的結構合理化要求進出口貿易結構相對平衡。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刺激出口貿易的相關政策不斷出臺彌補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激勵出口政策的缺失,促進出版產業在“引進來”與“走出去”政策的相互作用下協調發展。通過對相關數據的整理與分析,發現該階段政府規制的改革與重建調整了出版產業對外貿易的發展軌跡,具體呈現出以下兩個特點。
3.2.1 進出口貿易結構趨向協調
世界貿易組織對我國出版產業加大“開放性”的規制要求和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政策需求共同促使我國出版產業對外貿政策進行規制改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國務院、文化部、原新聞出版總署、財政部等部門共出臺約50項相關政策,其中激勵“走出去”規制36條,占比72%。經過政府全面規劃,財稅、獎勵機制等直接激勵的金融配套政策隨之出臺,極大地促進了出版產業出口貿易的發展。總體上,2002年至2020年我國圖書、期刊、報紙進出口總額、數量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出口貿易上升更為穩定,2013年進出口數量持平。2019年全國圖書、期刊、報紙出口總額是2002年的4.2倍,約增長5743萬美元(見圖2)。2008—2013年之間,進出口數量與之前相比縮小,貿易結構開始趨于協調。相較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大量進口政策出臺的偏向,該階段的政府規制不僅大量出臺激勵性政策刺激出口,而且在放松準入限制的同時重建一套規制體系,對外商進入我國出版行業和引進出版物等方面做出條件限制、加大審查力度,努力促進引進與輸出兩方面趨向協調。
2002年至2020年,政府出臺20余項激勵性政策,對文化產業“走出去”進行全局規劃,明確提出開展外向型圖書組織活動的要求;并以大量配套政策具體落實,尤其以財政、金融等手段直接刺激出版物版權輸出。對比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版權貿易逆差不斷上漲的趨勢來看,政府規制從加強準入限制到刺激出口的改革對于調整產業市場結構,縮小進出口貿易逆差,促進我國出版產業“引進來”與“走出去”的協調發展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國出版物版權貿易在進口方面波動曲折中上升,在出口方面整體呈現上升趨勢,出口漲勢明顯高于進口;出版物版權進出口比逐漸降低,出版物版權進出口之間的差距大幅縮小,版權進出口比從2004年8.14∶1降至2020年1.02∶1,縮小近8倍(見圖3)。這說明在國家強有力政策的刺激下,“走出去”實效日益凸顯,對外貿易數量進一步拓展。
3.2.2 協調化進程中的曲折發展
在進出口貿易協調發展的進程中,與進出口數量緩和趨勢相比,進出口總額的差值卻未得到根本性緩解,出口金額不能與數量同幅度上升,這反映了由于我國出版物出口定價過低,導致出版物進出口數量差不斷縮小與進出口總額差擴大相矛盾,這一特征在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的進出口貿易中十分顯著。政府出臺一系列促進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政策,《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2006)、《文化產業振興規劃》(2009)等皆強調加快數字出版發展進程,2010年新聞出版總署頒發《關于加快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指示推動數字出版“走出去”。隨著數字出版物的迅猛發展,其占據進出口貿易的市場份額逐步增大,2020年音像、電子出版物的進口總額為4.33億美元,圖書、期刊、報紙進口總額為3.62億美元,音像、電子出版物進口總額遠遠超過圖書、期刊等紙質出版物,但圖書、期刊、報紙出版物的出口總額仍高于音像、電子出版物,說明中國數字出版仍需繼續發力。伴隨進出口貿易總額和數量的增長,進出口單價漲幅也不斷加強,2002年至2020年進口單價從14萬美元約漲至兩千萬美元、出口單價從2.45萬美元約漲至千余萬美元,各年進口平均單價均維持在出口單價的兩倍以上(見圖4)。音像制品與數字出版物的進出口總額逐年上漲,數量也在波動中上升,但進出口差額卻并未縮小,究其原因在于出版物出口呈現量大價低的局面,出口單價低于進口單價,從而導致我國音像制品、數字出版物等進出口貿易差額巨大,不過值得肯定的是,隨著數字出版產業的發展和完善,數字出版物的出口單價與進口單價之間的差距正逐漸縮小。
從政策原因來看,《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銷企業管理辦法》及補充規定等一系列相關宏觀布局政策激勵著音像制品、數字出版物出口貿易的發展。同時我國對音像制品進口的數量和質量規制較強,《音像制品進口管理辦法》《關于嚴厲打擊違法進口音像制品的通知》《關于音像制品進口管理職能調整及進口音像制品內容審查事項的通知》等政策都明確對進口出版物展開嚴格的內容審查。放松進入規制、激勵“走出去”、加強內容管制多方結合共同促進產業發展,但相關政策仍未落實,圖書、期刊、報紙出口亦是如此,導致出口出版物附加值低,量大價低,不利于我國出版產業對外貿易的發展。
無論是出版物進出口貿易總額、數量的不斷上升趨勢,還是版權貿易逆差的縮小,都離不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政府規制改革的推動。但出版物進出口差額擴大趨勢未得到根本性緩解,特別是音像制品、數字出版物進出口貿易方面,量大價低,差額過大等現象,都反映了我國出版物在出口貿易中內容質量、技術創新方面的不足,有待政府進一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出版產業技術革新,并推動進出口貿易從“數量型”向“數量質量并重型”轉移。
4 結 語
政府規制作為政府干預經濟的一種手段,對彌補市場失靈、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增強產業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作用。在出版產業進出口貿易領域,政府規制在宏觀上調整產業貿易結構,促進進出口貿易,明確主體要求,僅推動產業出口貿易向“質、量并重”轉型,提升國際競爭力,而且利于規避進口貿易所帶來的文化滲透風險,維護我國文化安全。1992年至今,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促使我國出版業的經濟屬性日益凸顯,但“二元體制”的運作方式表明意識形態仍然主導著出版產業,政府規制依舊是影響出版產業發展的關鍵,階段性產業績效為政府規制改革提供了依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強規制下的版權貿易以規范“引進”為核心,版權輸出被忽略,出版產業對外貿易呈現貿易逆差不斷上漲的趨勢;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規制改革與重建以“輸出”為核心,產業貿易逆差趨勢得到緩解。以此來看,政府規制在出版產業發展中是必要的,但理應根據產業階段性發展狀況,及時調整規制方式,促進產業資源合理配置,實現規制效益與產業績效協同增長。
注 釋
[1]李偉.進入替代、市場選擇與演化特征:中國經濟體制轉型中市場進入問題研究[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147-148
[2] [日]金澤良雄著;滿達人譯.經濟法概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45
[3][17][22]干春暉.產業經濟學教程與案例[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173,173,173
[4][19]胡洪斌.中國產業進入規制的經濟學分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9-43,9-43
[5]朱麗琴.出版產業發展需以政府規制變革為保障[J].出版參考,2012(28):12-13
[6]朱丹.從出版產業政策的角度剖析我國的文化安全觀[J].法制與社會,2008(11):195-196
[7]郭劍,徐晨霞.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政策績效評估研究[J].編輯之友,2017(5):21-26
[8]趙禮壽.我國出版產業政策體系研究 1978—2011[M].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4:120-125
[9][21]徐小傑.圖書出版產業評價體系.[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160-199,160-199
[10][11]劉大年.中國出版產業政策研究 社會轉型與價值觀建構[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6:44,55-57
[12]李曉西.中國經濟改革30年1978—2008 市場化進程卷[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8:169-170
[13]包韞慧,何靜.我國出版政策法規40年回顧[J].出版廣角,2018(17):15-19
[14]方厚樞,魏玉山.中國出版通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卷[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361
[15][18]曲振濤,楊愷鈞.規制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33-107,33-107
[16]蘇東水.產業經濟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53
[20]黃先蓉,趙禮壽,阮靜.出版政策的績效評估:基于1979—2002年出版業發展的分析[J].科技與出版,2011(2):74-80
(收稿日期:2019- 09-20;修回日期:202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