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的孤兒《一把刀,千個字》和王安憶的小說創作
陳婧祾
一“凌晨有火車往南去”:沒有傳奇的故事
王安憶喜歡讓她的人物冒險:或者自愿,或者被迫,她讓他們離開熟悉的原有環境,去往未知之境。新世紀之初《遍地梟雄》寫上海的一個乖寶寶小名毛豆,幾番擇業后成為出租車司機旋即遭遇打劫,毛豆卻也便半推半就成了劫匪的兄弟,落草為寇。被打劫而冒險的情節,十年后在另一部長篇小說《匿名》中再次出現,這次輪到一個中規中矩的上海老爺叔,誤遭綁架,綁匪車開千里發現綁錯了人,便就地一扔了事,于是老爺叔——后來被叫做老新——為本能為意志驅使,從廢棄的山村野外開啟一段魯濱遜漂流記。
這個走出去的過程,對《遍地梟雄》里的出租車司機和《匿名》里的老爺叔,都帶有不可逆的性質,走出去了,就回不來了。毛豆當劫匪的日子才一年,被警察抓回來的時候,只能依稀還記得自己的大名,而他長大的地方已經辨認不出。老爺叔的經歷寫得更辣手,一個人平白失蹤了,妻兒鍥而不舍尋找,但悲傷也好絕望也罷,最終了斷,注銷戶口;另一方面,老爺叔其實還活著,離開上海也不遠,并且奮力求生,這過程中,又有外力助他慢慢尋找在荒野里丟失的記憶,尋找回家的路,可是就在曙光出現的時候,溺水身亡,終于坐實了戶口被注銷的結局。這溺水有天降神靈(ex machina)的意味,也不得不如此。且不說毛豆一腳踏入黑道,結局不出意料地被牽扯進殺人命案,少年人的游戲于是成為對人類禁忌的觸犯;老新當然沒法回去。《匿名》中,老新因為被綁架而斷成兩段的人生,王安憶隱約借用了《紅樓夢》的神話框架,比如,把老新送入荒野的“一麻一啞”,小說里說那是“一僧一道”;在他恢復記憶的過程中認出妻子的姓,老新說那個字“似曾相識”,并且還加了一個評語“三生石上”。自老爺叔被綁走的剎那起,就是另一世了,又如何回到前世——其實還是會回去的,我們下文再談。這里要說明的是,冒險的本質就在于打破生活原有的步調,從人生里分出一段,它讓這被分出的一段,構成與既有生活的張力——所謂張力,就是危險,一不小心,橡皮筋就斷了 。
王安憶小說中的冒險也并不是每一段都成為真正的危險。它可以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為了解決一個小小的或者并不小的困局,比如《長恨歌》里的王琦瑤,作為金絲鳥的愛麗絲公寓生涯被迫結束之后,有過一段鄔橋的歲月,這是一段隱居的時光,不過也帶點冒險的意義,離開上海——也許就不回來了?談一段并不現實的戀愛——談成了也許后來的人生就不同了?而當王琦瑤再次回到上海,這段小小的冒險就成為她的療傷,撫平之前的傷痛,讓她接續前緣,回到弄堂,開始新的生活。冒險還可以就是隨性而起,只因為心中一動,當事人并不覺有異樣。好像2018年的《考工記》,主人公陳書玉年輕的時候,跟著一群朋友同學甚至說不上誰是誰的人離開上海,有一點緣由是為了躲避迫在眉睫的婚姻前景,但更多是年輕人的“人來瘋”,盡管事到跟前頗覺蹊蹺,但也不經多想就跟著走了,事后才知道竟無意中被納入革命的行動,一番順遂之下其實驚心動魄,并以目睹年輕的死亡為整段冒險的終結。
與死亡擦身而過之后,陳書玉不等學業完成,就回來了。《考工記》開篇第一句:“1944年秋末,陳書玉歷經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這個開頭有一種莊嚴的氣質,因為它讓我們想到最古老的文學傳統,那些從遠方歸來的旅行者和他們的故事,比如奧德修斯的海上歷險,希臘的游吟詩人在《奧德賽》起始召喚繆斯,請求告訴他“那個多謀的人【如何】在洗劫了神圣的特洛伊城之后四處游蕩”。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里說,“德國有老話,‘出門遠行,就有東西可說了。’人們想象,講故事的人來自遠方,古老的代表就是商船上的水手們”。遠行,或者冒險,當它制造出與按部就班的生活的張力,就是制造出了生活中的故事時刻。冒險的結果是創造故事,創造傳奇。《遍地梟雄》和《匿名》的主人公都在不同的意義上回不去了,但作者兢兢業業寫下他們的故事,成為兩部小說敘事的主體。我們甚至可以說,寫冒險,寫冒險中的經歷,是王安憶鐘愛的小說“模型”,“模型”是她本人的說法,指的是“敘事的基本構成法則”。這個模型甚或還能裝下想象中的冒險,或者就是想象在冒險,以想象建立的敘事在冒險。我們記得她最驚人的寫作表演之一,在《紀實和虛構》中,那個在上海淮海路長大的敘事者“我”(當然也包括了幕后的作者),在想象中為母親少見的姓氏,構架起她的祖先們從內陸亞洲的草原到江南兩千年的沉浮、遷移、掙扎。這跨越時空的冒險,也提醒我們,本雅明筆下的“遠行”本來就含有在歷史、時間尺度上的“旅行”,強調時間的進程帶來的故事,并強調時間和空間的互相穿透。但是,相比上面這些作品,寫《考工記》的王安憶卻顯然有不同的考慮。傳奇的故事幾頁紙就講完了,接著便是日復一日里主人公和他的老宅,在戰后,在后來的時代,一步步老去。
1944年之后的幾十年,中國歷史風云變幻,可謂驚心動魄,自帶傳奇的氣度。寫時代風云下的云淡風輕,也讓熟悉王安憶的讀者想起《長恨歌》里王琦瑤的共和國經驗,一個舊時代的上海選美小姐、國民黨高官外室,如何藏身弄堂,用她的麻將牌、小籠包化開時代革命的熱浪,在一個禁欲的時代未婚生下一個女兒。但是,如果冒險的意義在于偏離常規,那么,《長恨歌》的第二部看似對日常生活的敘述,恰恰是整篇小說中最傳奇的,在革命的時代置身時代的浪潮之外,過一種鴛鴦蝴蝶風味的民國遺民生活,且在與革命遺孤的攪合中嵌入革命時代的世界主義浪漫,本身就帶有戲劇化的冒險。這種冒險卻與陳書玉在共和國的生活風馬牛不相及,《考工記》一開始就劇透得一清二楚,“因為這一行,日后新政府納他入自己人,得以規避重重風險”,再一句話概括,就是沒有故事,沒有傳奇。如果王安憶如王德威所說是張愛玲的傳人,這一次她寫的,也許就類似于《傾城之戀》結尾處的范柳原白流蘇、香港歷劫之后才聚在一起的那對平庸的男女和他們日后的白米飯蚊子血。張愛玲以戲謔的筆調,在傳奇的旗幟下寫現代男女的互相算計蠅營狗茍,由此為現代中國人重新定義傳奇。寫《考工記》的王安憶卻更進一步,要寫的是曾經滄海難為水的那片水,與古典意義上大風大浪的傳奇相比,這是距離最遠的了無詩意。
《考工記》單行本的封面上,這部小說被稱為“上海別傳”。別傳當然與正史對立,它和《長恨歌》大體上旨趣相近,都以普通人的境遇寫出歷史的紋理。文學理論家盧卡奇討論19世紀初年歷史小說的興起,首先要說明它與史詩的區別,標志之一是歷史小說創造了一種異于史詩的英雄。法國大革命及其后的拿破侖戰爭風云詭譎,堪稱史詩的時刻,可是,即使在歷史小說最近于史詩的時刻,兩者仍然有根本上的不同。在歐洲歷史的關鍵時刻,大批民眾在前所未有的社會動員中成為戰爭的主體,由此理解歷史,并接受歷史的召喚,故事的中心隨之就從史詩中太陽般光彩照人的領袖、高貴完美的英雄,轉變為平淡、了無詩意(prosaic)、卻不失尊嚴的普通人,在他們身上展開歷史在關鍵時刻的種種矛盾和爭斗。這些人物“總是在他們的心理和命運中,再現社會的潮流和歷史的力量”,而偉大的歷史潮流就“在典型的人的概念里具有了觸感……”這種帶著史詩遺韻、卻不同于史詩的歷史小說,在1980年代以后的很長時間里,是中國當代文學、文化的最愛。現代中國的風云變幻不啻拿破侖時代的歐洲。回顧這樣的時代,講述驚心動魄的故事,從傳記到小說,以至電影電視劇,都偏愛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的經歷,以此反映歷史的變遷以及普通人在歷史中的命運,在個體與歷史的對應里,同時兼具歷史的反思和個體的關懷。這一點上,《考工記》和《長恨歌》都仍可歸于歷史小說的譜系。


但是,兔子的母親才具有真正的傳奇性,是歷史小說求之不得的主人公。美麗的少女出生于一個舊時代基督教家庭,在新的共和國長大成人,成為一個忘我的革命理想主義者,她在歐洲古典音樂中養成的浪漫氣質,她與生俱來的孩子氣和認真勁,她執著的思考和最后的逆流而上,都讓她具有19世紀俄羅斯經典小說中女主人公的特質,甚或與《戰爭與和平》的皮埃爾也有相似性,在某個角度甚至可以說,她不惜以自己的前程甚至生命狂賭、冒險,而她無端的犧牲和日后的平反,更可見出共和國歷史的曲折。可是她的故事在一個長篇中只占到了五六十頁,總共十一章正文章節的兩章。從這一點上,這是一部作為英雄的主人公退場的小說。甚或是她的退場,也才為兔子的人生觸發了冒險的模式,使他的人生有了最經典的冒險的開頭。父親失魂落魄之時,母親大學時代的女同學突然來訪,在家里吃了一頓飯。然后,小說寫道:
兩人默坐一時,女同學說:凌晨有火車往南去,我帶孩子走。他倒沒想到,眼睛亮了亮,說:我有個妹妹在上海。女同學思忖了一下,要了姓名地址。他又問一句:買得到車票嗎?女同學回答:我們學校屬軍隊系統,我有軍官證。說罷站起身,自行去到里屋。他還要找孩子的衣物,女同學說:什么都不必!動手推大的起來,被他攔住:這一個留下,知道人事了!女同學目光移到小的身上,點頭道:也好,出來一個是一個!從被窩里掏出人來,一層一層穿衣服。孩子一直在酣睡中,小身子熱烘烘,軟綿綿。女同學笑了,問:他叫什么名字?父親說:我們都叫他弟弟。好,弟弟,我們走!穿上大衣,用圍巾裹住懷里的人,推開門走了。
許久未見的女同學,尚不知情的嬢嬢,當機立斷的父親,酣睡未醒的孩子,就像接下來小說里的評論,“從進門到出門,前后不過一個鐘點,就像做一個夢,雪夜里的靜夢”。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在這個驚心動魄的、戲劇性的夜晚之后兔子顛沛流離的人生,尤其是他的幼年和少年,當母親尚未平反的時候,他被拋出了一個孩子正常的按部就班的生活軌跡,再也回不去了——以后即使重返哈市,他也堅持認為回去的是父親的家而不是自己的家。但是,隨著“母親”的退場,我們也不再看到,比如,火車上的日夜,嬢嬢的驚詫,哈市的后續,不再看到冒險小說津津樂道的那些讓人緊張的關口,我們看到的就是兔子的人生從嬢嬢的亭子間開始了。生活局促卻安穩,戲劇性不過上街采買,或者更不同的是父親姐姐來訪,姐姐和師師吵吵好好,最戲劇性的是一次不成功的讓他改口叫嬢嬢“媽媽”,還有就是跟著“爺叔”去洗澡。接著嬢嬢的亭子間,揚州爺爺家的戲劇性是讓小孩子害怕的老宅的夜晚,進而一句伯母的不滿——可是他為什么從上海去揚州爺爺家呢?換而言之,在小說的敘述中,我們感受不到其中的驚險,也并不被刻意要求去意識到把他拋出去的暴力,以至時代巨變,歷史向“母親”的孩子拋出橄欖枝,他也輕輕地推開,以至后來在美國當非法移民,再拿到綠卡,都平淡,日常,細微,多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細節。相對于兔子人生的那些關鍵/危機時刻,以及在這些時刻被我們所期待的、如同舞臺劇的人生演出,王安憶的敘事相反集中于被通常的冒險敘事忽略的過場。
可是,我們還是要追問,兔子怎么從上海去了揚州爺爺家?怎么就跟著舅公當起了走村串戶的廚子?怎么小小年紀就有了工資請師傅單先生吃館子?怎么到美國的第二天就胸有成竹開始變作黑戶的行動?這些反常的地方,王安憶或者解釋,或者不解釋。解釋與否,我們也許都可以想起一幕小小的過場,嬢嬢為什么要讓爺叔帶著去洗澡?因為那個傍晚,失蹤了一個下午,兔子才從床底臟手臟腳爬出來,“臉上污漬斑斑的……其實是淚痕”,那天晚飯,心急如焚找了兔子一下午的嬢嬢,沒有多說什么,還拿出了待客和生病時才有的餅干。這一段真是再日常不過,可我們作為讀者心中也有了嬢嬢不加解釋的溫柔。我們意識到這段看似平穩的生活底下的驚恐。在小小的兔子的生活里,冒險的可不止是跟著爺叔去一個陌生的工廠洗澡,而是每一天亭子間里的日常。冒險,這個時候,不再是生活里的異數,和生活構成張力,冒險不再是從既有的生活里劃出一段不同或者關鍵時刻的放手一搏。對兔子來說,冒險化入了生活,成為不足為外人——外人包括了嬢嬢——所道的底色。這個底色,簡而言之,就是相冊里那張全家照被拿走后只留下的黑色卡紙,上海嬢嬢有一張他們一家的合影,可是被少年兔子無意瞥見一次后這張照片就被藏起來了,只留下黑色的卡紙。
從兔子回過頭看陳書玉,陳書玉平淡的共和國生活,也有一個底色,就是他的這幢樓。我們喜愛看到一個人有一點敢于違背時代的勇敢,所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王琦瑤讓我們心馳神往,我們也愿意想象陳書玉在革命和后革命時代守護一幢古老的樓。但是寫《考工記》的王安憶比起《長恨歌》時更不浪漫。幾十年里,陳書玉在和這個樓的糾葛中,自然生出對它的情感。可是,這幾十年,王安憶的敘事中,陳書玉的人生實在是被困在了這個樓里。他的堂兄弟們都搬走了,他卻搬不走;他想要和這幢樓有個交割,卻得到“順其自然”的指示;最后以為終于可以走了,卻仍然因為家族間的利益紛爭,被不知時限地拖延下去。小說以周禮舊篇章名為題,“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周禮·考工記》寫百工之德之術,可是小說卻寫了一個樓不斷自然敗壞和人為蠶食的過程,到了最后,許諾的維修也沒有發生,陳書玉得到的就是一塊碑,碑上有樓的名字,而樓在繼續敗壞,“那堵防火墻歪斜了,隨時可傾倒下來,就像一面巨大的白旗”。如此,小說全文完。白旗下一塊刻著名字的碑,讓作為讀者的我們驟然心驚。荒蕪的不只是這個樓,還有被困在樓里的陳書玉的生命。與這幢樓一天又一天的糾葛中,歷史的考驗就像滲透在了每一天。我們如果還是要以橡皮筋作比,歷史或者人生本身就是一條被拉緊的橡皮筋,充滿著危險。
陳書玉的祖上曾是上海灘叱咤風云的人物,到了他這一代,王安憶寫道,“上海的正史,隔著十萬八千里,是別人家的故事”,在她的筆下,陳書玉也成了故事里的人,可是,更要緊的是“故事里的人也渾然不覺”,因為并不覺得這是故事。不是故事,大概才是歷史的原貌,人生呈現的常態。正因為沒有故事,或者渾然不覺自己是故事里的人,所以我們才會那么熱愛傳奇的故事。換而言之,當傳統歷史小說里作為普通人的英雄,那些時代關鍵時刻的弄潮兒,也退場的時候,當歷史小說拋開繼承自史詩的傳奇、故事——在盧卡奇看來,那是人類童年的特質,我們也許就在小說里看到了我們更熟悉的人生和歷史。在歷史中行進,歷史并不劃出什么是關鍵的時刻,什么不是關鍵的時刻——所謂的關鍵,至多不過是我們事后的反省、命名,以圖給予歷史秩序;而在王安憶的小說世界中,我們猛然體悟,與這種時間、歷史、人生中的冒險相比,遠行、出走只是不足道的插曲。
二“穹頂就像天庭”:不能遺忘的記憶





然后,我們看《一把刀,千個字》的結尾。雖然兔子的人生還會繼續下去,可是王安憶又以一幕“那些不能遺忘的涌現出來”結束整部小說,對應的又是兔子人生的起點。此時,嬢嬢已經去世,主人公兔子人到中年,他無意中回到了當年爺叔帶去洗澡的鋼廠:
他仰頭望去,望見上方的吊鉤,原先大約用于行車,連軌道都保留原樣。這地方他來過,就是爺叔帶來洗澡的鋼廠。可不是嗎?那行車里,招娣在向他揮手。隆隆的機器聲遍地起來,只看見招娣攏著嘴對他說話,卻聽不見聲音。火星子四濺,煙花似的,絢爛極了。
小說尾聲這一章題名“后來”,主要寫兔子回上海為嬢嬢奔喪。兔子雖然下定決心回上海,但“想到回去,難免心中打怵。未見得近鄉情怯,甚至相反,感到陌生。那里的人和事與自己有關系嗎?記憶是模糊的,被許多輪替的印象遮蔽了”。尾聲的尾聲,就是認出鋼廠的一刻,“他害怕回來,怵的就是這個,可怵什么,來什么”,于是,我們看到中年的兔子“眼淚像決堤的洪水,傾瀉而下”,我們也大概明白,兔子害怕的不是回一個已經陌生的上海和模糊的記憶,卻是不可遺忘的記憶,是不可遏制的涌現出來的往事。他以為這些事很遙遠了,可是一直就在他的心里。那么,在他的淚水中,他想起了什么?是什么在他人生的初始,等待著他用一生去了悟,并在人生的另一頭突然觸動他的淚腺?
前面已經提到,跟著爺叔去鋼廠洗澡的一天是新奇的,帶著冒險的味道。不過那一天里發生的,不止是新奇。爺叔把他帶到車間,卻不知該如何在車間安頓一個孩子。這時候,就伸過來一只手牽起他的手,“暖和,柔軟,而且調皮”,把他帶進了一個小房子,溫暖又相對安靜。早起的孩子于是在小房子里安心補了一覺,等他醒來的時候,看到陽光將小房子照得透亮。他走出去又回到車間,剛才看著恐懼的嘈雜、龐大,這時則是另一番景象:
仰起頭,穹頂就像天庭,高大和遙遠,充滿光明。一架行車從空中開過,窗口有個人,向他招手。是她,小房子的主人。不用說,就知道。有人朝行車上喊:招娣,你的兒子嗎?上面的人回答,是的!
這個在“天庭”上開行車的姑娘——招娣是年輕的爺叔要好的女同事,一個機靈的姑娘——宣稱是他的母親,還要給他一頓豐盛的午餐,再等著他們爺兒倆洗完澡,目送他們騎上車回家。再說帶他去洗澡的爺叔,澡堂里不僅有親昵,甚至還有性啟蒙——爺叔真有了父兄的意味。
有關鋼廠的一日,事實上當天晚上兔子就開始了某一種遮蔽的動作,他用最簡單的方式回答嬢嬢的詢問,不提那頓“饕餮一餐”,也當然沒提招娣。但另一方面,“招娣”卻似乎成了他心底的牽掛。鋼廠也就只此一回,不久爺叔去了美國。兔子和招娣幾年后還有一面之緣,但再見到,那個快樂的姑娘眼里全是淚,面對兔子問候爺叔,“狠聲道‘爺叔死了!’”招娣走后,兔子吃著她給買的水晶包,“咬一小口,忽然啜泣起來”。王安憶寫兔子,除了嬰兒期的哭包時代,極少寫他哭,有關鋼廠,事后提起兩次,就有兩次眼淚,第一次是在和招娣分別的時候,第二次就是中年時的重返。
我們把前后關于鋼廠的段落放在一起,也會發現,中年兔子想象招娣攏著嘴對他說話,卻沒有聽到的,大概也有關于母子的玩笑。兔子的“記憶是從嬢嬢的亭子間開始的”,在有記憶以后的日子,那一天,也只有那一天,他有了一個母親,還是一個好像仙女的母親。這是他無法遺忘的,也是不愿想起的。
他自己的母親,本來就如同天上人。
三“茫茫然不知其意”:寫在虛空茫然中
我們可以做一個大膽的假設,從童年時鋼廠里的快樂一天,到中年時無意間重返鋼廠的淚流滿面,兔子的故事,也可以寫成一個類似《意外的重逢》的作品,寫一個無辜被牽累的孤兒,在顛沛流離的一生里與一個母親般的仙女的故事,從人生初始的偶遇,到時過境遷,物是人非,只能在記憶的深處追念招娣美好的形象。
與這個被假設的作品比較,《一把刀,千個字》有著遠為復雜的敘事結構和邏輯,與遠為豐富的細節。可是,這些層層的枝葉的掩映下,故事的主干仍不出這個框架的基本。那些復雜的結構和細節,恰是因為這個框架的支撐而獲得可能性,或者說合理性。我們再次想起本雅明所提到的故事的權威性:在故事的終了處,兔子的淚水和他的記憶一起“傾瀉而下”,在他遇到過去自己的剎那,構成洶涌的力量,并借助小說的結構所賦予的終結性,給予整個故事以一種權威。小說的枝葉細節,在某種程度上都被規約在最后的淚水的權威下,從它那里獲得意義,并獲得展現出來的價值;小說更為精細復雜的結構,也呼應著這個權威性,為它服務。換而言之,經過這個漫長的敘事,我們會理解主人公的淚水,和淚水中他對自己的過往明心見性的了悟。

從法拉盛到上海,師師充當了穿針引線的角色,因為師師這個名字是那時候弄堂里的稱呼,她比兔子年長幾歲,幾年的差距下,“師師記得第一次看見陳誠的情形,后窗里的小孩,他卻不知覺”。那么,后窗里的小孩又是怎么有知覺的呢?王安憶在這里有一段話描述了孩子的知覺成型的過程,起初是一些語音,與語音相關有一些片段的畫面,接著:
語音將這些片段連貫起來,抑揚的高低,疾緩的節拍,一些上下滑行,停頓,嘆息似的氣聲。開始不攜帶任何意義,然后逐漸生出,仿佛繁殖似的,越來越盛,陡然間結束,新換一種,于是,從頭來過……起先,幾種語音呈現孤立的狀態,各歸各的,漸漸地,互相滲透,融會貫通。就在語音的更替交疊中,視覺的世界成形,有了初步輪廓。
由此聚焦, “那時候,他大約七歲,住在上海虹口的弄堂里”。時過境遷,聚焦往事的過程,被作為往事的引子、作為往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進入小說的敘述,就此便形成了一個“追憶似水年華”的結構。這也為小說的敘事插入一個特定的角度,去釋放下面的往事。在這樣的結構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在一章的開始,會有這樣的句子,“有一段時間是斷開的,一截一截,一幅畫,一幅畫”——這是在呼應并說明記憶的斷裂。也因此,兩個看似平行的時間線,兔子的童年少年和成年歲月,卻是由后者——更精確地說,是后者的最后幾個月,也就是小說主體部分時間線的終點——作為視角,橫跨1967年以來的歲月。在這個時間線之外,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一個“后來”作為短短的尾聲,王安憶在小說的中途插入了兩章1967年之前的故事(“母親”的成長經歷,以及兔子幼年時和父母姐姐在哈市的生活)補全了前因后果,而這段補全之后,在下一章的開始,王安憶再次提醒我們,“他的記憶從嬢嬢的亭子間開始”。因此,在時間的前后線索上,這個小說寫了兔子的一生;而在敘事的角度上,小說寫的是兔子的記憶。王安憶用看似第三人稱的敘述,其實是緊貼成年后兔子的思緒,寫了一個孤兒的往事追憶。

比如,小說題目《一把刀,千個字》。“一把刀”當然是揚州三把刀之一的廚刀,而“千個字”源出袁枚對聯“月映竹成千個字,霜高梅孕一身花”,這一聯后來成為揚州名園個園的名字由來,在敘事中指向兔子一段零星的記憶,零星到與前后的情節都沒直接關系,它在一段法拉盛敘事結束后突然被提到:“一地月光,恍然中,又來到那園子里。竹枝搖曳,沙啦啦唱歌,無數‘個’字下雨般蓋了層層疊疊。他和黑皮踩著地上的影,嘴里喊道:踏著一個,踏著一個!”小孩子在園子的假山間穿梭嬉戲,從假山走出來的時候,“眼前一片亮敞,石窟陣退去,站在橋上。水面蓋滿浮萍,有個小人影,走動起來,才知道是自己。擊掌聲又響了,一抬頭,太湖石頂也有個小人影,是黑皮呢!一仰一俯,對望著,就像隔了千年萬載,不約而同嘻嘻一笑,橋頭匯合,再‘踏著一個,踏著一個’,出園子去”。黑皮是舅公家的孩子,這個細節,在小說的后半部,寫到兔子十幾歲的時候回到哈市,會又一次出現:
他在姐姐的陽臺,從飯后七八點起,一直坐到夜深,半睡半醒中,耳邊響起小孩子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茫茫然不知其意。頭上腳下,身前身后,全是“個”字,風中搖曳。又變作樹葉間晶亮的小孔,搖曳。再回到“個”字。小孩子的聲音還在,“一個字”“一個字”。他聽出來了,是黑皮!那“個”字,是竹葉,一千個,一萬個……

我們突然意識到,“母親”出事的日子正是梅花盛開而寒氣仍然逼人的早春時分。“霜高梅孕一身花”在整部小說里并沒有被提及,它在題記中的位置,反而在小說的敘事里造成了一個空白。這個空白,正呼應故事里那張消失的全家照。半大的少年回到嬢嬢虹口的弄堂亭子間,在一個歡快的夜晚無意看到自己幼時與父母姐姐的合影,看到自己的母親,“那抱他在懷里的,彷佛認識,卻又不認識”,此后不久,少年一天心有所動,背著嬢嬢翻箱倒柜,卻再不能見到這張照片,“揭到一頁,沒有照片,只余下四個透明膠紙角”在“黑色的相冊底板”上。照片被從相冊里取走了,可是少年也松了一口氣,“危險避開了”。“危險”其實在小說中經常出現,它被用來形容人與人間的交流、談論的話題,或者整個氣氛。從“母親”出事之始,我們的敘述者就不諱言,出事的“母親”成了一個危險:“兩個孩子從開頭第一天,就沒有問過:媽媽到哪里去了。他(父親)猜測大的或許有些許耳聞,小的呢?最粘母親的年齡,卻從此不再提一個字。小孩子就像動物,感知危險的本能尚未在進化中萎縮”。這個危險,被本能地意識到,不僅是年幼的孩子,世故的嬢嬢也一樣,因此抽走相冊里的照片;但是,知道它的存在,處理的方式卻是掩耳盜鈴、一避了之,嬢嬢并沒有補上別的照片來掩蓋抽走的痕跡,而在兔子,沒看到也就算過去了。被避開的危險,作為作者的王安憶卻不能輕描淡寫,視而不見。梅花的缺席,母親在1967年后成為“危險”,且被迫離場,在兔子的人生——也就是在小說的情節上——形成一個黑色底板一樣的存在,一個黑洞般的虛空。這在小說敘事上,實則創造了一個棘手的問題。我們都知道母親對孩子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往往體現在母親參與孩子的成長過程并發揮主導的作用。隨著這種參與被取消,母親的重要性卻并沒有消失。以虛空存在的重要性,又該如何被敘述被表達?小說如何為不存在畫像?


從這個角度來看歷史小說、個人傳記,作為“科幻”,對過去的追索,就不僅僅是對記憶停留之處的考察,不僅僅是追述已知、把碎片拼接成故事。無論記憶如何零碎,零碎的記憶都具有已知的意義。“科幻”的歷史小說,還要再現的是記憶之間的空隙,要把這些空隙也納入文學再現的范圍。在兔子的記憶里出現的揚州園子,以及園子里的竹與影,作為記憶的象征,比起它的零碎,更有意義的是光影交錯、虛實難辨,它涵蓋了明與暗,在光的到與不到之處,見出記憶的呈現與遮蔽、知與不知。這大概也正是招娣的故事給我們的啟示。故事的最后,當兔子回到工廠遺址,招娣從記憶中不可阻止地涌現出來,我們跟隨主人公領悟到的,不僅是這個記憶的重要性,也是它在記憶和認知中的黑洞。當它最后被從黑洞中召喚出來,我們了悟記憶同樣是明和暗的共存,并且了悟兩者彼此間的進退。本雅明所謂“不能遺忘的(人事物)涌現出來”也正是這種共存和進退的寫照。
招娣和招娣的工廠,雖然在兔子成年后隱沒在他記憶的深處,但是,從兔子有記憶以來的七歲起,記憶的真正黑洞仍然是被迫離場的親生母親。人的記憶和意識領域里明和暗的對照,也啟發我們可以借用雕刻的不同手藝,來理解王安憶在小說中的努力。母親的在場,在孩子心中呈現鮮明的記憶,也就是說,她將從記憶中凸顯出來,她的形象、有她參與的種種被保留、被強調,正讓我們想到篆刻或浮雕中的陽刻。但這種強調、凸顯、肯定的藝術,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來表達一個母親的重要性。就像在兔子的記憶里,他的事事件件都沒有母親的參與,我們看到的,是他和嬢嬢在虹口的弄堂里,和揚州的爺爺、伯父一家,舅公還有單先生,這些是他凸顯出來的記憶,甚或也有招娣,這同是記憶的明處。可是,就在記憶明處的另一旁,我們知道還有光影不到之處,在明的對照之下,那黑暗之處同樣可以鮮明。就如同雕刻中的陰刻,借由凸顯出來的部分,那沒有凸顯出來的,也被呈現出來;在否定的意義上,在被去除的過程中,相對于被凸顯的部分,那被否定的、被去除的,才是雕刻家所要展現和表達的。這大概也是王安憶在這部小說的用力所在,是招娣的意義所在、一個孤兒和一個母親般仙女的故事意義所在:招娣不僅是記憶的光影明暗對立、進退的寫照;招娣在小說最后出現,伴隨著天堂一般的光芒,明暗的強烈對照之下,王安憶以否定的再現方式,在一個孤兒的記憶里,為他缺席的母親勾勒出了形狀。

尾聲“沒有‘軟兜’”:異鄉的大廚
《一把刀,千個字》開篇,講兔子的美國大廚經歷。比起兔子陳誠移民美國過程中的胸有成竹、步步為營甚或開掛式的順利,作為大廚,大洋彼岸的他卻捉襟見肘,深有巧婦無米之嘆。陳誠出身淮揚菜一系,由揚州的舅公啟蒙,又師從上海灘遺老單先生,學得傍身的技藝,也獲得開闊的眼界,于是有本錢在紐約開私廚,“為舊人物辦菜”。可是,這堂堂大廚,所能使用的食材多來自朋友一家叫做“上海”的農場,這農場和美國其他農場類似,各種出產全是水土不服,菜不是菜的味道,筍就得了個貌似,所以做菜只能全靠調料湊合。
這開篇的描寫里,時間是舊人物,地點是徒有其名,材料更是有形無神,一切都是不能湊在一起的湊合。我們后來會知道,兔子是一個十幾歲的時候就在適時物資貧乏的上海做出一桌佳肴、驚艷了名廚的天才少年;可是,有關他成年后作為淮揚大廚的人生,他作為 “一把刀”的現實,卻是這樣在各種不對中開始——或者說,他的美國大廚生涯是在對各種否定的對抗下展開了。陳誠做菜,就如同他的作者王安憶寫作,令人生出虛空茫然中的探索之感。
不過,這些都還能忽悠。“唯有一件物事,讓陳誠苦惱了,那就是‘軟兜’”。淮揚地方,鱔魚被叫做軟兜,一道鱔絲,是淮揚菜的當家名菜——至今從揚州到上海的諸多揚州餐館甚或本幫菜館,這都是考驗餐館和廚師實力的靈魂——兔子作為淮揚菜的大廚,在美國卻各種尋訪“軟兜”不得,甚至為了軟兜還專門去探訪一家曼哈頓新開的本幫菜館。有關這段探訪王安憶意趣盎然地閑筆了好幾頁,生生寫出了一家充滿東方主義意味的中餐館如何裝腔作勢、忸怩勢力,而做的幾道上海家常菜,卻又如何不著邊際。最后,“終于,清炒鱔糊登場了,沒動筷子,他就笑了。別的不說,那一條條一根根,看得見刀口,而鱔絲是要用竹篾劃的。也就知道,這食材來自當地養殖,新大陸的水土,所以肉質硬實,竹篾也劃不動。兩個人各要一碗白飯,湯汁拌了劃拉下肚”。菜雖不正宗,他和他的朋友吃起來卻是不失正宗的湯汁拌飯。小說然后寫道:
吃過美國“軟兜”,陳誠得出結論,美國依然沒有“軟兜”。
從“千個字”的過去,到“一把刀”的現在,兔子從一個沒有媽媽的小孩,成了一個沒有軟兜的淮揚菜大廚。而那時,無關痛癢的旁觀者看得明白,從姐弟倆到他們的父親,這一家人 “都是怪胎,爸爸是老干部,姐姐是老小姐——世上有一種人,生來是老小姐,結婚不結婚都是。還有一個呢,看上去沒毛病,可是心里有,病根呢,在第四個人,他娘身上”。
于是,我們想到,雕刻中的陰刻,否定的魅力,正在那些被刻去的部分、不存在的部分才是重要的部分。回頭想想,刀刃所及,皆是傷痕。
? 王安憶,《考工記》(廣州:花城出版社,2018年),1頁。
? Walter Benjamin, “The Story-teller: Observa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 Selected Writings, Vol. 3 (1935-1938), Trans. Edmund Jephcott, Howard Eiland et al., eds. 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44.
? 王安憶,《小說的模型》,《鐘山》雜志2021年第2期。
? 王德威,《海派文學,又見傳人:論王安憶》,《讀書》1996年2期。
? 我們可以舉一個歐洲文學中顯著的例子,拿破侖和庫爾佐夫足以擔當史詩中的英雄,但在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里,他們退為背景,前景則聚焦安德烈公爵和皮埃爾,我們看到兩位俄羅斯青年的不滿和沉淪,猶疑和探索,掙扎和奮起,這種種又都和拿破侖戰爭息息相關,和俄羅斯、莫斯科的命運沉浮與共。
? Georg Lukács, The Historical Novel (London: Merlin Press, 1989), pp.34,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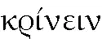
? Georg Lukács, The Historical Novel, p.33.
? 王安憶創作于1990年的作品《叔叔的故事》就以反諷的筆調寫了一個受難歸來的知識分子的故事,寫叔叔的故事如何成為故事,就揭穿了這種對受難的崇拜和受難背后歷史真相的荒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