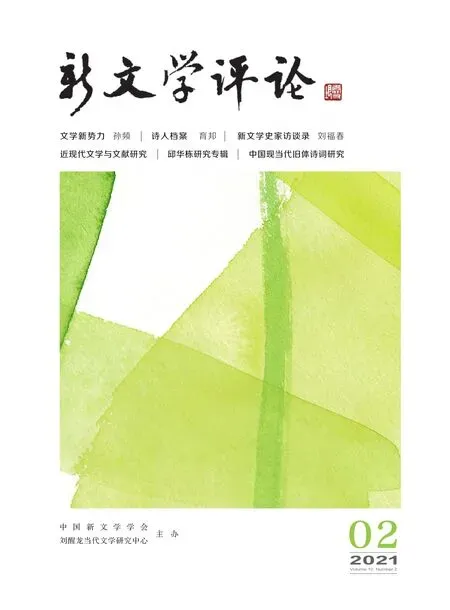一個作家的誕生
——重讀邱華棟20世紀90年代的小說
□ 徐阿兵
邱華棟創作力之旺盛及成果之多,人所皆知。2018年,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推出的38卷、900萬字的《邱華棟文集》,全方位地展現了其文學風姿。如此體量,堪稱中國當代文學園林中一棵枝節縱橫的大樹。長、中、短篇小說眾體皆備,如同挺直向上的主干,始終支撐著這棵樹的高度;散文、詩歌、電影評論和閱讀筆記等,則像旁逸斜出的枝椏,時刻謀求向四周擴展這棵樹的領地面積。與同時代的諸多作家一樣,扎根民族土壤,呼吸時代氣息,沐浴歐風美雨,也是邱華棟快速成長的重要原因。要說邱華棟文學生涯的特殊之處,我想不應忽略其“早熟”:他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嶄露頭角,還不到20歲;進入90年代,發表小說如遍地開花,年齡卻遲遲不滿30歲。當時評論界不無欣喜地將他歸入“新生代”或“晚生代”作家之列,殊不知,他已算得上是年輕作家中的“老”資格了。20世紀90年代,實在是邱華棟創作生涯中最關鍵的時期,其意義值得全盤考量。
一、90年代的“秘密”
重提邱華棟的1990年代,主要是出于以下幾點體會和發現。首先,90年代文學發展的“先鋒”勢頭或許不如80年代,但文學創作的趨新求變已漸成常態。評論界當時對邱華棟作品所作的歸類及命名(諸如“新狀態小說”“新市民小說”“新人類小說”,等等),著意突出其“新”,這在當初或許不失為權宜之計,至今已覺不新鮮。更要緊的是,這種倉促命名所暗含的標簽化的偏頗,在文學傳播和閱讀接受中逐漸放大,留下了無法抹去的痕跡。后來的不少人只知其新,卻不知也不問其何以新。當下,我們回到90年代去重新認識邱華棟小說創作的新質,或能有所發現。
其次,邱華棟在90年代以后一如既往地新作迭出,但我以為,最能體現其個人風格并足以代表其創作實績的,還是他90年代的小說創作。邱華棟對社會現實變化的敏感,文字表達的能力與個性,形式探索的熱情,情感宣泄的方式,在他的中短篇小說創作中顯露無遺。在長篇小說方面,他出版了自稱為“30歲以前的代表作品”的“日晷”三部曲:《白晝的消息》(1996年)、《夜晚的諾言》(1998年)、《正午的供詞》(2000年)。此外,他還發表了取材于歷史上“張汶祥刺馬案”的《刺客行》(1997年)。從小說的題材或主題面向來看,邱華棟此后的長篇小說系列,在90年代已經完成了建基工作:一是注目城市,從《白晝的消息》《正午的供詞》到《教授》(2008年)和《花兒與黎明》(2015年),延續成為“北京時間”系列。《青煙》(2004年)與《后視鏡》(2013年)分別關注造假打假和民工討薪、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也是以城市為敘事空間。二是感悟成長,以《夜晚的諾言》為發端,后續有《夏天的禁忌》(2003年)、《前面有什么》(2004年)和《街上的血》(2005年)。三是回望歷史,《刺客行》寫作所偶然激發的對于歷史的興趣,在后來的《長生》(2013年)中得到呼應。在中國歷史中加入域外元素,則催生了由《賈奈達之城》(2007年)、《單筒望遠鏡》(2007年)、《騎飛魚的人》(2007年)和《時間的囚徒》(2016年)所組成的“中國屏風”系列。
最后,邱華棟本人對90年代的創作也極有感情。他在2001年自編三卷本“小說精品集”時,十分“寧靜地”回顧了自己“成長的秘密”:“這些小說可以說是我在期待著有一天可以理直氣壯地聲稱自己是一個作家的追索過程中寫下的,它們洋溢著青春的激動和憂傷,焦慮和游移,懷疑與確信,絢麗與陰沉,泥沙俱下與精雕細琢——10年間我就是通過寫下這些作品,到今天我終于自信地認為我是一個作家了。”
一個作家就此誕生。不過,邱華棟所描述的創作心理,其實是幾乎所有青年作家共同的成長秘密。另一個眾所周知的“秘密”是,一個作家的創作迅速產生影響,往往得益于積極回應他所處的時代,或者說,呼應了這個時代的文學需求。那么,90年代對文學的吁求是什么?評論家李潔非在90年代末發現,由于市場經濟的全面推行,“九十年代有一種叫做‘城市文學’的東西應運而生,來勢強勁,一下躍升為我們最重要的文學景觀。今天,若翻開各文學雜志,上面所載作品,十之六七要歸在城市文學范圍之內;若統計新生的作家,更是十之八九要歸在城市文學作家的隊列之內”。邱華棟脫穎而出的真正秘密,正在這里。他敏銳地捕捉到新興的城市景觀,全力聚焦城市空間中新奇的人與事,將它們與年輕人的成長記憶及文學夢想加以糅合,不斷地發表新作,從而使自己迅速匯入了“城市文學”的時代潮流。方興未艾的都市化進程,血氣方剛的青年小說家,兩者的脈搏在這個時代達成某種意義的合拍共振,這是屬于邱華棟的機緣,促成他不僅寫出了屬于他自己青年時代的作品,也寫出了屬于這個時代的作品。李潔非當時對年輕作家和城市文學的未來寄予了厚望,認為“盡管他們的寫作如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本身一樣,仍處在初步的階段,但是,從中國的社會發展趨向來預測,新生的城市文學絕不可能曇花一現,它是一座可以深挖的寶藏;從這里,未來二十年內,將產生出可以代表自己時代的作家”。如今看來,他的預判基本得到了印證。我們可以補充說,邱華棟正是90年代城市文學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十幾年后,邱華棟深情回顧來路,說自己是“在書寫著與我的生命共時空的文字,與北京的變化共時空的文字”,所言并非虛夸。他那時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是以城市體驗為敘述對象,而不僅僅是以城市空間為敘述背景。由此,邱華棟90年代的小說創作,成為我們觀察城市與文學相互關系的極佳案例。
二、發現新的“北京”
將邱華棟1990年代的創作放入城市文學的整個脈絡中來討論,必然會遇到如何理解“城市文學”的問題。相比于似乎不證自明的“鄉土文學”,“城市文學”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始終有待辨析。顯然,倘若只是從寫“城市生活”這個角度去理解,“城市文學”就可能被簡化為單純的題材概念。90年代以來,不少研究者主張將作家的“城市意識”視作“城市文學”的內核,但何為“城市意識”仍然值得追問;同時,窮究何為“城市意識”暗含著偏離“文學”的潛在風險,可能導致討論重心轉移到“城市”之上。近些年來,或許是由于親身見證了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以及文學的多元化發展,學者們對“城市文學”概念的理論焦慮有所緩解。以我之見,“城市文學”概念的理論使命不在于定義城市或文學,而是辟出一個理解城市與文學之關系的角度。更具體地說,是為考察作家的城市想象與其文學表現之關系提供一個窗口。如趙園所說,城市文學不僅生動傳達著“對于中國的城市化、城市現代化的文化期待”,還總是“給人以新的藝術形式、新的美學原則在母腹中躁動的消息”。






我們驚訝地發現,邱華棟用以描述城市體驗的語式,竟然與莫言在《紅高粱》中面對鄉村的情感姿態不謀而合:“我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熱愛,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仇恨,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這種語式的背后,無疑是作者表現復雜生活體驗的自覺和自信——不管它是鄉村生活體驗,還是城市生活體驗。不妨推想,即便我們將邱華棟筆下北京“這座城市”的整套地標加以改換,小說中的故事仍然可以在其他新興大城市發生。故事情節具體如何,或許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故事中的人都是城市化進程中的人,都帶著這個時代的氣息和表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邱華棟的寫作,既屬于這個時代的北京,又不僅僅屬于北京——從根本上說,它屬于這個時代。
三、想象城市的方法
以文學的方式理解或想象城市,是城市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說到理解城市,從城市的發展變遷入手,或許是本能反應。但是,邱華棟似乎向來無意于此。他只是在《遺忘者之旅》中提到,“一座城市,總有它的歷史,有它最動人的部分”,總會留下一些古建筑和博物館。但主人公“我”既然連自己的身份、來路和去向都已遺忘,又如何會在意城市的前世?“我”穿梭于各個城市之間,想要尋回自己,重溫刻骨銘心的愛戀,卻發現城市“正是記憶的遺忘中心”。這讓我們意識到,邱華棟所寫的城市,其實是沒有歷史的城市,是無根的城市。
以鄉村作為參照物來理解城市,是現代文學史所傳下來的重要經驗。但邱華棟并不倚重鄉村經驗以反觀城市。在他的城市敘事中,鄉村形象絕大多數時候是缺席的。僅有那么少數幾篇,其中的人物或出身于鄉村,或名字(如“麥香”“麥青”)中透出一絲絲鄉村氣息,但鄉土中國的倫理道德觀念并未構成理解當下城市人事的參照系。《環境戲劇人》以“我”導演環境戲劇“回到愛達荷”和尋找消失的龍天米展開雙線敘事,“我”在龍天米死后發出哀嘆:“只要離開了故鄉,生活在改變一切的城市中我就永遠也回不去了……我們進入都市就回不去故鄉。”這里的城市與故鄉(鄉村?)似乎形成某種對立關系,但小說并未詳細交代“我”和龍天米的故鄉及成長背景,更不可能使故鄉記憶成為當下城市體驗的對立物。邱華棟明確地放棄了以鄉村反襯城市的文學傳承,從而凸顯城市的漂浮狀態。

邱華棟固執地以敘述者或主人公的眼睛觀看城市,由此造成的閱讀效果是:有一種獨特的“城市景觀”始終在場。這種城市景觀,如取景器一般抓取了大量的、物質化的城市要素,同時又彌漫著內在的、情緒化的觀者體驗。邱華棟的許多作品,都以城市景觀開篇,又以城市景觀收尾。例如,《夜晚的諾言》開篇是主人公感到自己像“城市上空偶爾飄過的氣球”,對城市沒有認同感,結尾時則領會了城市“固有的法則和節奏”;《城市戰車》始于“腫瘤”般的城市景觀,終于發現“這座城市清新、友善和慷慨的一面”;《哭泣游戲》始于對城市的“驚羨與欣悅”,終于對城市“感到恐懼又甜蜜”;《手上的星光》以對城市的恐懼與向往開篇,以認識到城市生活的殘酷性而暫告一段落……但我們知道,邱華棟的城市故事還會繼續下去。他要寫的故事,就是人在城中改變的故事,同時也是人對城市發生改觀的故事。


從人與城的關系來看,邱華棟筆下的人大致可以分為六類。一是“闖入者”,以《闖入者》中的呂安、赫建以及《城市戰車》中的流浪藝術家們為代表。他們的特點是在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懷揣夢想但沒有融入感,只能游走在城市邊緣;他們或許一直在受挫,但并不打算放棄夢想。二是已經熟悉城市并適應交換規則的人。如《保險推銷員》中的外省姑娘何佩瑤,迅速適應城市規則,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再如《新美人》中的檀、《手上的星光》中的廖靜茹,她們以自己的美貌不斷與城市交易,從而走向越來越大的舞臺。三是在城市中被生存現實所擠壓,逐漸喪失個性和深度的“平面人”。“時裝人”“公關人”“直銷人”“電話人”“鐘表人”“持證人”也均在此列。四是在城市生活中備受擠壓以致人格晝夜分裂的“午夜狂歡者”,如《午夜的狂歡》中的秦杰和左巖等人。五是在城市中深感壓抑焦慮從而尋求自救的人,如《平面人》中的田暢和何鈴,《天使的潔白》中的袁勁松。《鼴鼠人》中的韓非人更為極端,他既要自救也要救人救世,甚至不惜以破壞行為對抗城市化進程。第六類可以稱為變異人,如《克隆人及其它》中的“橡膠人”“綜合人”“克隆人”以及《化學人》中的“化學人”,他們無不體現邱華棟對城市科技化生存方式及其未來的隱憂。

四、余論


注釋:
①邱華棟:《正午的供詞·后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頁。
②這部小說的“版本”情況有點復雜,值得一說。它最初以中篇小說的規模發表了部分章節,即《白晝的消息》(載《花城》1996年第6期);稍后以“城市戰車”為題,由作家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了單行本。邱華棟在20世紀90年代末寫完“日晷”三部曲時,曾口頭將其恢復為最早的標題“白晝的消息”,但后來的“消息”是:2003年,該書由新世界出版社以“白晝的躁動”為題出版;2015年漓江出版社將其改名為“白晝的喘息”并出版,這個名稱此后在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于2018年打造的《邱華棟文集》和安徽文藝出版社2019年推出的“邱華棟長篇小說精品系列”中被固定下來。
③此書最早由長江文藝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2015年由漓江出版社以“教授的黃昏”為題出版。
④此書最早由長江文藝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題為“戴安娜的獵戶星”。2007年收入“中國屏風”系列,改名為“賈奈達之城”。
⑤邱華棟:《邱華棟小說精品集·自序》,華文出版社2001年版,自序第1頁。
⑥李潔非:《城市文學之崛起:社會和文學背景》,《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3期。
⑦李潔非:《城市文學之崛起:社會和文學背景》,《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3期。
⑧邱華棟:《在那些激情四射的夜晚(自序)》,《白晝的喘息》,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自序第4頁。
⑨趙園:《北京:城與人》,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頁。
⑩理查德·利罕著,吳子楓譯:《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