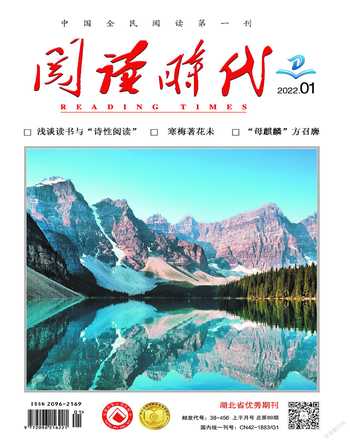徐壽:中國《自然》發文第一人
群學君
01
1878年夏天,剛剛創刊兩年的中國近代最早的科學雜志《格致匯編》第七卷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考證律呂說》的文章。文章不長,研究的也是非常冷門的古代樂律之學。然而正是這樣一篇毫不起眼的小論文,在近代中國科技史上,具有石破天驚的意義——某種程度上,它代表了一個半世紀前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先進科技所能達到的高峰。
中國古代一向采用弦音和管音相合的方式確定音律,以弦定律,以管定音。然而,現代物理學實踐告訴我們,弦的振動和管的振動,有著根本的區別,對于這個問題,漫長的中國古代樂律史根本無能為力。
一直到1878年,一位中國學者開始注意到這個似乎是“細枝末節”的小問題。他用現代科學試驗(盡管很簡陋)的方式,否定了延續千年的“管弦結合論”,寫成了這篇《考證律呂說》:
惟聲出于實體者正半相應,故將其全體半之,而其聲仍與全體相應也。至于空積所出之聲,則正半不應,故將同徑之管半之,其聲不與全體相應,而成九與四之比例。
不久,這位年過花甲的學者讀到了自己兒子的譯作——近代聲學啟蒙著作《聲學》,它的作者是赫赫有名的物理學家、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約翰·丁鐸爾。他驚訝地發現,這本被歐洲物理學界稱譽為19世紀聲學集大成者的著作,卻在管長與音高的問題上,犯了與中國古代音律學者同樣的錯誤。
在創辦格致書院的好友傅蘭雅的幫助下,這位學者將自己的論文翻譯為英文,并謄寫了兩份,一份寄給丁鐸爾教授,用實驗數據與他進行商榷,另一份寄給了歐洲最有名望的科學雜志《自然》。
盡管中國的挑戰者始終沒有等到丁鐸爾的回信,但五個月后,《自然》雜志卻以《聲學在中國》為題,刊發了這篇來自中國的論文。在編者按中,編輯斯通博士寫道:
(這篇論文)以真正的現代科學矯正了一項古老的定律,這個鮮為人知的事實的證實,竟來自那么遙遠的(中國),而且是用那么簡單的實驗手段和那么原始期器具來實現的,這是非常出奇的。
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在《自然》雜志上發表論文,也是中國人第一次正式在國外刊物上發表論文,而這位“以真正的現代科學矯正了一項古老的定律”的學者,名叫徐壽。
美國學者戴維·萊特寫道:徐壽是當之無愧的中國聲學之父。
這篇堪稱里程碑的論文,只是徐壽一生名山事業小小的片段——事實上,他還是中國近代化學啟蒙者、近代造船業的奠基人、化學元素周期表的中文定名人;中國第一臺蒸汽機、第一艘輪船、第一艘軍艦、第一所教授科技知識的學校、第一場科學講座、第一本科技期刊……都與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他與子孫五人,一共翻譯、撰述了科技著作96部,近一千萬字,是中國近代科技文明不倦的“盜火者”。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科學先驅,在晚清保守教條的文化環境下,因沒有科舉功名,終其一生被邊緣化,甚至以匠人身份見用。他的一生,代表了近代最優秀的中國知識人開眼看世界的曲折歷程。
02
1818年2月,徐壽出生沒落望族之家。他五歲喪父,在母親的督促下,也曾“嫻帖括,習舉業”,遵循傳統士人通過科舉求取功名的老路,但是屢次應試,連秀才的功名也沒取得,母親去世后,徐壽自斷科舉之途,“專究格物致知之學”。
不久,徐壽與志同道合的鄉人華蘅芳,在上海讀到了墨海書局刊行的英國醫生合信的著作《博物新編》,這本介紹近代歐洲科學常識的小冊子,為他們打開了睜眼看世界的天窗。徐壽用一雙巧手,驗證了其中許多的科技原理,他把水晶圖章磨成三棱鏡,用來觀察光的折射和分色;甚至常常偷偷跑去西洋人的輪船上,驗證《博物新編》中介紹的關于現代蒸汽機的原理。
22歲那年,徐壽寫下座右銘:
毋談無稽之言
毋談不經之語
毋談星命風水
毋談巫覡讖緯
這種格物致知、求真務實的態度,已隱約可見近代科技文明的精神底蘊,成為徐壽一身奉行不悖的指針。自此以后,他不求功名利祿與個人聞達,將探求西方先進科技作為畢生追求的事業。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徐壽被視為一個鐘情于“奇技淫巧”的異類,只因為他遠遠地走在了那個閉關鎖國、民智不開的時代的前面。
03
1862年,飽受太平天國之亂影響的徐壽,離開家鄉無錫,投奔安慶舉辦內軍械所的曾國藩。此時的曾國藩,因為“眼見洋船上下長江,幾如無日無之……念(洋人)縱橫中原,無以御之,為之憂悸”而常常徹夜難眠。在曾國藩的支持下,徐壽與次子徐建寅等,完全不假西方人之手,僅以三個月時間就造出中國歷史上第一臺蒸汽機,四年后又造出完全國產的中國第一艘蒸汽船“黃鵠號”。1868年8月31日,上海《字林西報》報道:“黃鵠號”所用材料“均由徐氏父子之親自監制,并無外洋模型及外人之助”。
此后,徐壽在上海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先后督辦造出了中國第一艘和第二艘純國產軍艦“惠吉號”“操江號”,這些成就代表了洋務運動中官辦軍事工業達到的高峰。
據說同治皇帝曾親書“天下第一巧匠”厚賜徐壽父子,曾國藩也對徐壽許以厚祿。徐壽也一度備受鼓舞,他曾上述曾國藩,建議朝廷亟辦四事:一是開煤煉鐵,二是自造大炮,三是操練水師,四是翻譯西書,卻遭到曾國藩的一一駁斥。
與其說,曾國藩不認同徐壽的主張,不如說,在曾國藩這樣進士出身的傳統士人心中,“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理念依舊根深蒂固,在技術層面,他們可以將一個沒有任何“科舉功名”的工匠委以重任,然而在價值觀上,他們卻無法打消發自內心的歧視和輕蔑。
直到徐壽去世六年以后的1890年,張之洞創辦湖北鐵政局時,曾千方百計邀請徐壽的兒子徐建寅出山擔任會辦。然而,當徐建寅請求張之洞為父親徐壽立祠,并交國史館立傳,以表彰其貢獻時,張卻大為不悅——他并不是瞧不起徐壽這個人,而是從內心深處無法給予徐氏的名山事業以足夠的體認和尊重。
這恰恰是曾國藩、張之洞之輩的可悲之處:
某種程度上說,徐壽是幸運的——正是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大潮下,他獲得必要的財物支持,得以充分施展才能,在中國近代科技發展史留下自己不可磨滅的一筆;但徐壽也是不幸的——以曾國藩、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大臣,無法脫離自身意識形態與知識結構的根本桎梏,“中體西用”的根本價值觀決定了他們對徐壽只以“匠人”視之,無法體察到徐壽畢生追求中蘊含的文明轉型的深刻內涵。
這樣的矛盾,是一個古老文明在苦苦追尋現代化之路過程中付出的代價。
04
晚年,在熱心國是遇到挫折之后,徐壽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繼續他畢生傳播新知、開啟民智的事業:譯書。
1868年,在徐壽的努力和奔走下,江南制造局成立了翻譯館,徐壽自任總管。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家以翻譯和引進西方的科技類書籍為主旨的學術機構。
在徐壽的擘畫下,翻譯館高薪聘請了九位外國學者參與其事,負責口譯,而徐壽自己,則與徐建寅、華蘅芳等中國學者,負責整理為文字。
在翻譯館,徐壽共翻譯26部西書,共計290萬字。加上次子徐建寅、三子徐華封及兩個孫輩,徐氏家族譯校的西學書籍,幾近800萬字,這其中,72%是科技著作,11%是兵工著作,徐氏父子也因此被尊為“中國近代科學之父”。
徐壽還首創了化學元素漢譯名的原則。他選擇用羅馬音的首音(或次音),找到同音字,加上偏旁,用于化學元素的譯名。今日中國中學生耳熟能詳的元素周期表,也大部分都出自于他的翻譯。如今,我們對比一下日本以片假名直譯化學元素的譯法,就會對徐壽中西合璧的譯法欽佩不已。
到建館40周年時,翻譯館共譯書160種,具體內容,則舉凡兵學、工藝、兵制、醫學、礦學、農學、化學、交涉、算學、圖學、史志、船政、工程、電學、政治、商學、格致、地學、天學、學務、聲學、光學等等無所不涉,西方近現代科學技術,正是從這個機構開始,得以在古老的華夏大地扎根。
在徐壽的嚴格要求下,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的譯書,文字流暢、易懂。據說,日本政府一度特意派人來華求購,以求中日在科學名詞上彼此相通。
05
1874年,徐壽與傅蘭雅聯手創辦格致書院,這是中國第一所教授科學技術知識的學校,開設有礦物、電務、測繪、工程、汽機、制造等多門課程。
傅蘭雅曾說:“徐先生幾乎是集中他的全部精力在募集資金……當他清光緒四年接任司庫職務時,書院負債1600兩銀子,此后,他曾募集7000兩銀子,用以償還了全部債務。”
幾乎是與格致書院成立的同時,徐壽和傅蘭雅也編輯出版了我國最早的科技期刊《格致匯編》。他的那篇影響西方聲學界的文章,最初就是在《格致匯編》上發表的。
1884年,就在格致書院慶祝了它十歲生日后不久,66歲的徐壽在學校里安詳辭世。李鴻章稱贊他:“講究西學,實開吾華風氣之先。”
17年后,在父親身后繼續他科技事業的次子徐建寅,在漢陽鋼藥廠火藥實驗現場殉職,搜救人員多方搜求,只找回他一條被炸斷的大腿。
又過了十幾年,徐壽嘔心瀝血創辦的江南制造局翻譯館,這家中國近代譯書最多、影響最大的翻譯機構,以“既非目前需要,且所譯各書,又不盡系兵工之用,自應一并停辦,以資撙節”,被段祺瑞關閉。
所幸,徐壽生前最后一份事業,格致書院,在歷經一個半世紀風雨之后,被保存了下來,成為今天的上海格致中學。
責編:何建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