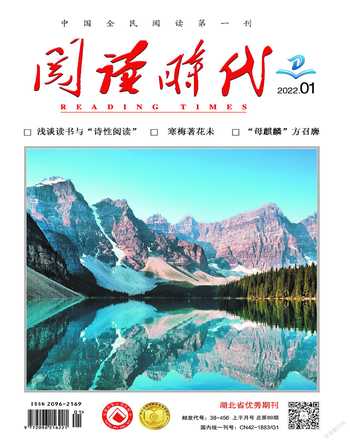仰韶文化是如何被發現的
秋蘭菁
我們在閱讀歷史故事時,常常會發現這樣一個現象:面對現實中存在難以解決的問題,古人們往往會一頭扎進故紙堆中,從過去尋找答案。似乎越是生活在古老時代的人,越會擁有今人缺少的智慧、道德和信念。這樣做的結果顯然是徒勞的。因為經過歷史長河不斷淘洗,這些史料中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湮滅,少部分留存者也被后來的記述者刪改、扭曲。對于后人來說,想要通過歷史記錄完整客觀地還原當時的歷史原貌,似乎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任務。然而隨著現代科學考古學的誕生,這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出現了一絲曙光,人們終于可以不再完全依賴歷史記述者的視角,近距離地與歷史事件發生的時代接觸。
安特生和仰韶遺址
中國現代考古學始于1921年秋,安特生對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
安特生本是瑞典人,1874年出生于謝斯塔,畢業于國際頂尖名校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獲得地質學專業博士學位。1914年,身為地質學家的安特生受北洋政府之邀前來中國,被聘為“農商部礦政司顧問”,與時任地質調查所所長的丁文江一起組織地質調查,并訓練了中國第一批地質學者。1916年由于袁世凱倒臺,地質調查因經費短缺而停滯,安特生調整了工作重心,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一邊進行主業地質調查,一邊滿足自己的愛好——收集化石以及考古發掘。在這期間,安特生獲得了許多足以載入史冊的發現。
1918年,安特生在北京市郊的周口店雞骨山進行過兩次調查,并進行了試掘,但并無大的收獲。
1921年,他和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在當地群眾的引導下在龍骨山北坡找到了一處更大、更豐富的含化石地點,這就是聞名于世的周口店龍骨山遺址。安特生在此進行發掘后發現了兩顆人類的牙齒化石,并在1926年向世界宣布了這兩顆猿人牙齒,隨后更多的北京猿人化石被發現,這些古老人類化石的發現,讓全世界為之轟動。
而安特生最大的貢獻,卻來自一些不起眼的石器和碎陶片。
1920年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劉長山派往河南洛陽以西地區考察。12月,劉長山回到北京,帶回600多件石斧、石刀和其他類型的石器,這些石器均來自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這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并認為仰韶村可能存在新石器時代遺址。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來到仰韶村作地質調查,在村南約1公里的地方,他在一個被流水沖刷露出的斷面上發現了許多石器和彩色陶片,這引起了他的濃厚興趣,并在未來的幾天里不斷擴大他的新發現。此后,安特生回到北京征得農商部及地質調查所同意之后,又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于10月27日正式開始對仰韶村進行發掘,這便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史前考古學以及現代田野考古學的誕生。
隨后安特生的調查又擴展至楊河村、西莊村、牛口峪、池溝寨等多座遺址,他通過對比出土的遺物,認為這些遺址都在一個大體相近的時間,由同一群人創造,因此他正式以最早發掘的仰韶村的名字,將在這些遺址中發現的考古學文化命名為“仰韶文化”。1923年安特生在《中華遠古文化》中提出仰韶文化是由中亞傳播而來的假說,之后動身前往西北尋找史前文化遺址以證明其理論。安特生一行沿著黃河出發,用了一年多時間,途經陜西、甘肅、青海等地,調查和發掘了包括朱家寨、辛店、齊家坪、馬家窯等眾多遺址,這些遺址在后續的發掘中都成為補全中國史前歷史的重要“拼圖”。
這些遺址雄辯地證明,中國也存在著史前史,推翻了世界對中國無石器時代的刻板偏見,也為中國人研究自己的古代文化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民國考古學的發展
自安特生發掘仰韶遺址以后,中國考古學也逐漸走向正軌。當時正值民國期間,雖國家仍風雨飄搖,但在廣大愛國學者的努力下,考古學事業仍緩步前行。
1921年底,北京大學調整研究所結構,其中國學門下設文字學、文學、哲學、史學和考古學研究室,成為較早的考古研究組織,但考古學研究室由于經費受限,未有實際的考古發掘,只收購一些古董商的古器物。1925年,清華國學會成立,清華正式開設“考古學”課。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即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之一,在他的帶領下,清華國學研究院實現了本土考古學由“坐而言”終至“起而行”的轉變。1926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的李濟與地質調查所的袁復禮,在山西運城夏縣西陰村進行了三個月的考古發掘,這也成為中國學者自己主持發掘的第一處史前遺址。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研究部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任第一任所長,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羅常培、李方桂、董作賓、梁思永、勞干、周法高、嚴耕望、石璋如、芮逸夫、全漢升等著名學者先后擔任研究員。史語所集中了一大批英才,一時成為學術界矚目的重鎮,并在殷墟等處考古發掘、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研究、全國各省方言調查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學術成果。
在1928年至1937年共10年中,由史語所組織進行了15次殷墟考古發掘工作。這些發掘采用了當時最先進的考古方法,在發掘之前制定了周密的計劃,重視地層的劃分和遺跡間的相互關系,同時顧及各個遺址之間的有機聯系。殷墟遺址的發掘,為中國考古事業培養了大批人才,也標志著中國考古學走向科學化。
這十年間,由吳金鼎主持對濟南以東的東平陵以及城子崖進行了6次調查,發現了以黑陶為顯著特征的“龍山文化”遺存,并在1930年由李濟、董作賓、郭寶鈞、吳金鼎等人對城子崖進行了一個月的發掘。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國考古事業也走入低潮。隨著中原地區成為淪陷區,殷墟考古發掘也被迫中斷。史語所的田野考古工作逐漸轉移到邊疆地區,但再也沒有恢復到“黃金十年”時的成就,抗戰結束后的三年內戰則完全陷入了停滯。而中國考古事業更大的輝煌要等待新中國成立后由新一代考古人來創造了。
新中國考古學與三大工程
新中國成立后,一度中斷的考古工作又得以重啟。由李濟的學生夏鼐牽頭,中國科學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即后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52年,蘇秉琦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之后很多省份也紛紛成立各自的考古研究機構或文物管理局,其首要任務就是配合新中國轟轟烈烈的大建設,對受建設影響的古代遺跡進行搶救性發掘,中國的考古工作得以在比過去寬廣得多的空間里開展起來。
從1970年代后期開始,豐厚的考古成果開始發酵,學術界已經不再滿足于解讀個別考古遺址,而是逐漸開始重新審視中國原始國家誕生的機制和文明形成等問題,期間多種觀點出現與碰撞,如由美國學者賽維斯提出的酋邦理論傳入后,易建平、謝維揚、范毓周、王震中、陳淳、沈長云等學者曾圍繞酋邦概念及中國早期社會如何與酋邦理論相結合進行過長期論戰;也有學者結合世界考古理論與中國實際,提出自己的觀點,如蘇秉琦擯棄了傳統的“中原中心論”,提出了中華文明“滿天星斗”說、“古文化—古城—古國”說和“古國—方國—帝國”發展模式說;嚴文明提出了相似的“重瓣花朵式”模式;王巍則就中國實際,明確了中國地區文明和國家的定義,并指出文明和國家是不同范疇的概念。各種觀點交織碰撞,進一步提升了人們對史前中國的認識。
隨著國內各項考古工作穩步推進,國家對探究中國歷史真相和提升國民的文化自信有了新的要求,自20世紀90年代起,陸續推出了多個大型考古工程項目。
1995年秋,國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請在北京的部分學者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宋健提出并與大家討論建立“夏商周斷代工程”這一設想。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作為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被啟動。該工程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結合,開設了9個大課題,在這些課題之下設置了44個專題,來自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歷史地理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學等領域的170名科學家進行聯合攻關,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確切年代,為研究中國5000年文明史創造條件。工程于2000年9月15日結題。
斷代工程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是中國古史研究中第一次跨多學科進行的大型研究工程。雖然對最后得出的年表仍存在爭議,但是斷代工程的開創性是無可置疑的。而在此之后,學者們又在斷代工程的基礎上,開展了后續“中華文明探源”“考古中國”等工程,吸取了之前的經驗和教訓,為中國的考古事業開創了新的篇章。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2001年至2004年間進行工程預研究,2004年夏季正式啟動。2016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結項,2018年5月發布相關研究成果。
探源工程成果豐碩,首先是確定了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三個階段:距今5800年前后,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并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然后是探源工程研究團隊從社會分工、階級分化、中心城市和強制性權力等方面,提出了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突出特征,最后是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有了總體認識,實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征。
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豐富且扎實,在此期間如良渚、石峁等大型史前文明遺跡一次次出圈也讓探源工程被人熟知。
探源工程之后,國家文物局又立項“考古中國”,工程項目包括:“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長江下游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長江中游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海岱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夏文化研究”和新疆考古、西藏考古等重大考古項目,隨著考古工作的繼續,之后還將有新的課題納入工程。而早期中國文明的迷霧,也將在考古人共同的奮斗中逐漸被撥開。
責編:何建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