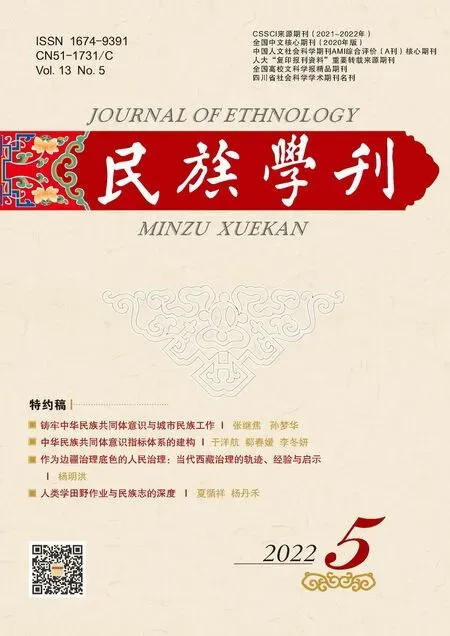互動儀式鏈視角下民族精神培育與學校武術教育的融合與發展
劉 濤 張 艷
在呼吁傳統文化回歸與弘揚民族文化精神理念的推動下,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性逐漸在國人心中獲得了廣泛認同。民族精神作為一個國家欣欣向榮人民團結向上的內在源動力,在歷史的長河下逐漸積累和沉淀,蘊藏和彰顯了民族的特質和本原,表征和描繪了一個民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該民族發展和前進的核心驅動力。自黨的十六大以來便強調堅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且必須把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的重要任務,并納入國民教育的全過程。隨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弘揚民族精神作為工作開展的重要抓手,可見民族精神才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支撐點。民族精神的培育和發展,不僅僅指向個人的覺醒和家庭的進步,更在于強調從青年出發,最大限度發揮青年群體的作用,自覺承擔起新時代使命和擔當,因而學校教育成為了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的重要場域。在此基礎上,除了利用書本等傳統路徑進行民族精神的培育,還可以從情感入手,以互動儀式鏈為理論基礎展開研究和討論。
儀式作為一項維系社會結構與社會秩序的機制,發揮著教化、交流、整合等社會作用,隨著儀式研究的不斷深入,儀式不僅僅局限于宗教體系,而是“擴展到現代社會中的慶典、聚集等社會活動,但儀式的社會功能始終包括對參與者的行為規范和意識形態塑造,”[1]在此過程中必然夾雜著情感在儀式中的作用。情感是中華民族血脈相連的基本要素,影響國人縱向和橫向的情感交織,柯林斯指出,“情感是互動儀式的核心組成要素和結果,是社會動力的來源,同時每個個體在社會中所呈現的行為和觀念的外化是在與他人的社會互動中逐漸形成的。”[2]學校教育本身就是儀式體系的特殊系統,通過樹立青少年正確的人生觀和培育民族精神而進行的各種錯綜復雜關系的形象展示,以特定的場域和情景來闡明其中的道理和文化,更容易使受教者產生情感共鳴。可以說,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揚既是中國文化目前的發展潮流,同時也是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自信與文化轉型的必然選擇,更與傳統文化,民俗體育等傳統學科有著緊密和復雜的內在聯系。武術作為傳統文化傳承的實踐載體和精神載體,分別從技術體系和民族精神的整體層面做出了傳承和對接。本研究試圖以武術教育為切入點,借助互動儀式鏈的文本對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揚進行思考和探索。
一、內在邏輯:民族精神與武術教育的研究緣起
縱觀歷史的畫卷,武術深深根植于民族民間的沃土之中,其地位在某種程度上象征和描繪了國家的地位與實力,蘊藏和彰顯了國人的精神面貌、意志品質和文化意識,不僅展現了中華民族獨特的生命力和特殊的創造力,更是中華民族身份的象征。20世紀初,武術被正式納入學校教育體系,作為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還肩負起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時代使命。換句話說,通過學校武術教育,一方面對學生進行身體規訓以實現外在行為與內在觀念意識的高度契合,進而使民族精神內化為學生德行,另一方面實現民族精神培育與學生自我認同的統一建構。
(一)民族精神與武術教育的歷史尋繹
春秋戰國時期作為中華文化的軸心時代之一,其文化到達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各思想家們先后發表自己的主張與觀點。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代表主張武學教育,強調文武兼備,其倡導的“六藝”中有兩藝與武術有著緊密關聯。隨后,“秦漢以降,帝王推崇獨裁專政,武化之風日微,至景武之間,武化之風大挫。”[3]“重文輕武”的思想成為了封建社會的主流趨勢,并且逐漸形成“文”與“武”的失衡,“‘武’化教育的失位造成中華民族陽剛之氣的缺失,導致整個華夏民族的日漸衰落。”[4]在此之后,無論從國家政治還是從軍事戰爭來看,中華民族都面臨時局蒼夷的苦難境地,內有蒙古入主中原,外有西方列強入侵。在外憂內患的雙重夾擊下,究其原因其癥結在于“武”化教育的缺失,導致民族脊梁的斷裂,進一步磨滅了民族精神的傳遞。
在這樣動蕩不安的背景下,不乏有志之士尋求振奮民族精神、實現保衛國家的有效路徑。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初,梁啟超作為第一人提出了中華民族衰敗的癥結在于“武”化教育的缺失,并受此啟發撰寫了《中國之武士道》一書,該書強調重塑中華民族精神,重視并重構“武”化教育。隨后,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受梁啟超的啟發并加之自身實踐,深切認識到武術正是恢復民族精神、提升文化實力的最佳載體,因此,孫中山特地為精武體育會寫下“尚武精神”的題詞,由此武術正式進入現代意義的學校教育體系。隨后武術被提升為國術,并從國家層面出發開始創建國術館以及國術體育專科學校,意在廣泛地促進民族精神的培育,激發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試圖使徘徊在危機邊緣的中華民族恢復先秦的雄風。不難發現,以武術培育和恢復民族精神,振奮國人雄心似乎成為了當時武術發展的主流趨勢。
(二)民族精神與武術教育的政策導向
自黨的十六大以來,不少政策導向都指明新時代要堅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習近平總書記也曾在講話中多次提到要從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精氣神,精氣神正是中華民族精神世代相傳的內在源動力。長期以來,中國武術作為表達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在構建和發揚民族精神上有其特有的地位和作用。坦率地說,武術服務于民族精神的培育,不難看出武術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張力與人們對武術文化價值認知具有同一性,這種同一性也彰顯著武術弘揚民族精神的真實意蘊和內在價值。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強調支持中華武術等中華傳統文化代表性項目走出去,并且明確指出將優秀傳統文化全方位融入教育領域。”[5]由此可見,武術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與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過程中扮演著先行者和主力軍的重要角色。
學校作為開展武術教學工作的重要支點和著力點,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武術傳承發展與傳承的重要契機。一方面,中國武術歷經歷史的車輪不斷浸潤傳統文化精神,另一方面武術思想與傳統文化交織滲透意在弘揚民族精神。學校武術教育作為傳承傳統文化與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媒介,蘊含著重要的時代價值。對于當下武術的發展而言,不能僅僅將其定位為傳承傳統文化的媒介和載體,而應站位于國家發展層面,將其從傳統體育項目的一種身體技術形式,提升為武術文化與武術精神。進一步“重塑‘剛健自強’精神的實踐載體,培育人的‘武’化精神的實踐途徑,”[6]并利用學校體育這一有效途徑,積極契合宏觀層面的國家發展,培育青少年民族精神,努力推動個體發展并大力開展武術教育,構建合理的互動體系,跳出武術原本的技擊價值,從而最大限度地挖掘和發揮武術內在的文化價值。
二、互動儀式:構建民族精神培育與學校武術教育融合的動力機制
當柯林斯在構建互動儀式鏈的過程時便強調了“人”這一重要關注點,同時人們的一切互動都發生在一定的情景之中,理應從情感這一因素出發研究行為傳播的初始動因。“互動儀式過程中,情感能量是一重要驅動力,互動儀式產生一種共同關注的焦點,”[7]通過身體在場進而形成群體的情感共鳴并將他們符號化。學校作為儀式產生和開展的特殊場域,將武術蘊含的特定民族精神,以學校為載體發揮其獨有的傳遞功能和教育功能,更能清晰地闡明其中的道理和文化,同時更容易使受教者產生情感共鳴。
(一)情感建立:利用學校體育有效傳遞武術彰顯的民族精神特質
無論是涂爾干提出的社會分工論,還是韋伯研究的社會沖突論,其核心概念都暗含了情感。毫無疑問,情感在社會學研究領域中占據重要地位,同時也是“互動儀式鏈的核心組成要素和結果”,[8]當我們試圖更加精準地研究社會概念時,我們不難發現許多重要的概念都依賴于情感建立和產生的過程。當下學校教育已從讀、背、算等硬技能的傳統模式中抽離出來,轉而對學生情感能力的培養做出重要探索。從具體學科來看,武術課程“除了促進身體健康這一基本目標之外,還包括促進社會與情感能力的發展,”[9]以及加深對于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的認識和培養。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經典代表之一的中華武術,“所蘊含的文化基因、展現的文化性格,以及具有的功能價值,實現的不只是身體的強壯,更是完成中華優秀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以及民族精神的延續。”[10]民族精神的延續以及傳統文化教育依托學校為載體,以武術所蘊含的傳統文化信息為主導,通過文化自身的誘發作用和感染力,借助學校特殊的教學場域使參與者分享并體驗武術帶來的共同情感狀態,成功建立起情感協調,弘揚民族精神。同時,根據學生身心發展的規律以差異性適當增加和融入武術元素的情景化課堂能增強學生“在場感”[11]的培育,從源頭加以修訂,加強對民族精神的深度滲透,建立積極的情感能量,讓學生真正感知中華文化的核心精髓,并從中真切體會到民族精神。
(二)身體在場:通過武術教育實現民族精神由認同到實踐的轉化
“互動儀式理論的核心機制是通過身體的協調一致相互喚起參加者的神經系統產生高度的關注跟高度的情感連帶,”[12]而學校作為學習武術技能與傳遞傳統文化的重要場所,強調身體的在場,“即用身體去感知、體味、體驗與獲得,以‘整體性’身體為主體而產生的身體感覺。”[13]在此基礎上所產生的肉體與心靈完美的融合,暗示了身體才是使身心合一的主要途徑。“就中國武術身體觀維度而言,在學校武術教育的場域中這種身體是無聲的語言,”[14]通過學生身體主導的武術實踐活動,以親身的反復體悟,再經歷長時間的跨度和沉淀后,身體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會喚起受教者神經系統與身體主體的某些靈感與情感共鳴,由此產生武術與受教者之間某些內在的聯結與思想的情感的碰撞。對于武術而言,其不僅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而且“還承擔著培育民族精神的特殊任務,凝聚中華民族精氣神的特殊育人任務”[15]。中華武術呈現了精神教育的重要資源,已不再只注重于“高難美新”的表現型技術,而更多是立足于其技擊的本質屬性,展開點到為止的對抗性技藝,從實踐途徑重新認識傳統武術的內在魅力。同時,強調道德對于塑造人格的重要作用,武德在一定程度上與民族精神有著共通點,映射出民族精神與武術文化價值層面的認同。不僅如此,在教學實踐過程中勇敢拼搏,迎難而上、堅韌不拔的武術精神與民族精神相呼應,將民族精神牢牢濡化在傳播過程中,進一步形成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撐。
(三)情感輸出:結合武術教育構筑情感歸屬與民族精神信仰符號
傳統社會下“以農耕文明為主體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促使情感、信仰等價值觀念融入到武術文化之中,進而形成具體的禮儀、意志和精神影響武術習練者的行為和認知方式。”[16]當下,中華民族處于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青年學子并沒有親身體會認知當代中國的發展,此時發揮互動儀式鏈中參與的情感建立與身體在場的能動作用顯得尤為重要,將武術教育折射出的民族精神潛移默化地融入到學校教育體系中,產生明確且強烈的情感輸出。也就是說,在構筑民族情感的實踐空間里,學生作為行動者,是情感空間里的基本單位,以教育實踐輻射出多元化結構,促成傳統文化的發散性傳播,進而構筑中華民族精神的信仰符號。“民族精神美的塑造與培育始終是學校武術教育的終極價值追求,”[17]從本質上看,學校教育作為特殊的儀式形式,以具象化的方式表達并展示了武術教育的內在意蘊與現代價值,意欲強調價值觀念以及民族信仰,使傳統文化觀念得到傳遞并延續民族精神,與此同時產生強烈的歸屬感。雖經歷了時代的變遷和文化的重構,但武術文化所塑造和包含的民族精神與時代信仰仍然根植于武術文化記憶中,具有民族信仰和情感的中國武術哪怕經歷了時代的輪回與交替,也始終將承載的民族文化符號一如既往地向下傳遞。時至今日,武術的發展仍然符合時代的步伐,以“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實踐目標,堅守民族精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三、發展路徑:建立民族精神培育與學校武術教育融合的傳播策略
將學校看作是互動儀式發生的重要場域,把武術教育當作產生情感互動的關鍵紐帶,不僅是民族文化符號和民族精神形成的樞紐,更是促成民族精神培育和傳播實踐的重要推動力。“中華武術是一個價值多元的文化叢體,不同角度具有完全不同的社會價值,”[18]通過獨特的技術體系所呈現出來的深沉精神價值才是當下教育的急切所需。基于以上需求,可以從情感共鳴、場域互動和集體意識三個層面形成民族精神的有效傳播策略。
(一)共建情感共鳴:共同意識形成和筑牢民族精神記憶力
“互動儀式鏈作用的有效發揮,除了認知情境與相互關注的焦點,還有一個重要的驅動因素就是共享的情感狀態”,[19]武術不僅僅是一項身體技術,更蘊藏了豐富的精神文化,由幾千年來的各民族文化集體賦予,彰顯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識。當下,在學校這一特殊教學場域中,通過語言、行為等引起受教者對于武術所產生的相同情緒和行為,由此引發情緒感染效應,并進一步形成獨特的共同意識。受教者通過武術的體悟過程所形成和構建的價值趨向以及共同經歷的文化熏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學生擁有共同意識和情感,往往可以使學生能更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同時使蘊藏在深處的民族精神得到喚醒。當受教者在回溯武術歷史,共同感受著中國武術與中華文化的互融共生,在冷兵器時代的奮勇殺敵,其不僅融攝了儒、道、墨等思想派別的文化因子,還涵蓋了中醫、哲學等領域的文化精華,從不同時空為武術營造出認同感和歸屬感,并形塑了對于武術民族精神的集體記憶和共同意識。互動儀式鏈正是通過這些情感意識,反復將這些短暫情感元素轉化為情感能量儲藏,并建立情感共鳴,進而促使一些歷史記憶的重現和精神符號的形成。當下武術作為中華民族特有的標志性文化符號,“被當作為精神教育、情感教育的一環,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被進一步喚醒”,[20]并成為和平年代表達國人精神與民族自豪的工具,也成為了民族精神的時代強音。
(二)共享場域互動:身體認知促成和培育民族精神傳播力
身體參與作為認識并了解一項文化內涵和外延的邏輯起點,在武術發展的領域中得到了較好的驗證和展開,而學校體育正是為武術的身體認知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共享場域,是以文化空間而構建。“武術的身體教育實踐,是武術人之所以能夠長期習練的心理基礎與精神動力,”[21]以武術教學為載體用身體共在的方式使受教者進入互動儀式的情景和空間,通過身體認知感受該場域下傳統文化體驗和民族精神渲染。傳統文化中武術承載著“內隱的文化價值漸大于外顯的技擊價值”[22],利用學校場域開展武術教育的目的之一便是要實現“以武化人”的目的。“情感可以通過身體的互動而放大,”[23]在武術教學中,強調用具象的身體認知實現與抽象的心理聯結,通過自己的身體形態,全方位調動神經狀態,用觸覺、視覺等感官元素重塑和構建對傳統文化的正確認識,促成和培養對民族精神的理性認知,增強文化記憶,進而形成對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效傳播力。在身體和文化互動的學校場域中,不同個體的身體技術、行為習慣和思維模式交織在一起,通過情感的交流和碰撞構建出共同的感知體系,幫助受教者彼此之間形成并加深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社會關系,構成受教者與傳統文化對話以及民族精神培育的多重傳播空間。
(三)共筑集體意識:武術教育擴大和發揮民族精神影響力
學校教育作為受教者共筑集體意識的原生場所和驅動力,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民族情感的轉化過程。武術教育強調從受教者身體規訓出發,“達到外在行為與內在心理、觀念意識與情感體驗的契合,讓國家意識、民族精神真正內化為學生的德行,”[24]構成民族精神與學生認同的統一體。在武術教育領域中,武術之所以能開發和啟迪受教者的內在智慧,不僅是身體技術簡單的外在演繹,而是一種通過身體的不斷體悟誘導身體內在語言的理性表達,進而達到啟發心靈,培育健全人格,發揮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從受教者個體出發,通過武術教育對傳統文化的認知和認同,在一定程度上對于培育民族集體意識構建了循環的路徑,從整個受教者群體來看,亦是鑄牢民族精神的有效模式。武術在歷史的長河中,靠的不是外在華麗的包裝和宣傳,而是內在深厚文化內涵的影響力,一招一式都散發傳統文化的魅力,以有形的身體教育手段,表達出潛藏在載體中的無形教化。換句話說,武術作為培養和弘揚民族精神的重要媒介,在現代教學體系中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武術教育作為培育民族精神傳播中華文化的形式和載體,一方面增強了受教者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和集體意識,實現了傳統文化的價值表達和延續,另一方面,擴大的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同時,用中華民族的集體意識最大限度凝聚了受教者的青年力量,使其對民族強烈的認同感轉化為民族精神指引其今后的行為。
四、結語
如何在武術教育中真正構建起民族精神力量,弘揚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不難發現,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揚更應該從參與者的視角進行構建,將武術教育作為激發和整合受教者情感需求的邏輯起點,從受教者不同成長背景和情感需求出發,依靠民族自帶的內在凝聚力,建立起二者間溝通與共享的情感能量,并構建情感互動儀式鏈。落實以學校場域塑造的情感、意識等重要元素符號,依靠武術特有的內在底蘊形成受教者共同關注的焦點,并升華群體的情感體驗,強化自身的集體意識。在周而復始的教學環境中,實現凝聚民族精神,發揮傳播傳統文化的積極作用,同時發揮受教者的主觀能動性作用,將心理認同轉化為實際操作,進一步促進民族精神的培育和發揚,形成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