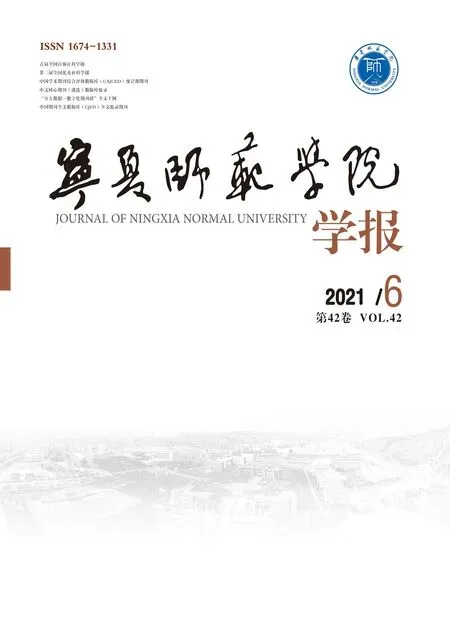文學期刊與詞典體小說的開拓
2021-12-31 20:40:04李曉禺
寧夏師范學院學報
2021年6期
李曉禺
(西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自韓少功《馬橋詞典》發表以來,文壇出現了許多文體特征類似的詞典體小說及部分具有詞典體小說特征的亞詞典體小說,小說“詞典化”已成為一種值得重視的文學現象。[1]在詞典體小說“自主”文體變革與當代社會“他律”之間,文學體制在某些具體的環節上起到了直接的決定性作用。20世紀末,隨著經濟改革進程的加快和深入,意識形態熱點問題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作者群與讀者群持續分化,文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自由”狀態。但是,文學掙脫了政治的“束縛”之后,又再次面臨市場經濟的擠壓和體制的改革以及影視文學、網絡文學等新媒體藝術的“圍攻”。文學、文學期刊不僅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邊緣化狀態,部分期刊甚至出現了難以維持的局面。很多人認為這是文學的“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幾乎是同時,《大家》《莽原》《中華文學選刊》《花城》等期刊相繼提出了“凸凹文本”“跨文體”“無文體寫作”“實驗文本”等口號,“文體”似乎成了最后的稻草。《大家》主編李巍麾下的“凸凹文本”是一個“文學怪物”,打破詩歌、散文、小說、戲劇之間的人為界限。李巍指出:“我們希望,在文體的表述方式上能以一種文體為主體,旁及其他文體的優長,陌生一切,破壞一切,混沌一切”。[2]著名作家、《莽原》主編張宇認為,跨文體寫作興起的主要原因是: “文體像牢籠一樣局限和障礙著寫作的自由”。[3]其實,無論這些期刊高調宣揚了多少關于文學的“獨特”看法和“宏論”,“凸凹文本”“跨文體”寫作等口號的提出,首先是文學期刊的一種自救行為,以改變求生存。……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文苑(2020年4期)2020-05-30 12:35:30
制造技術與機床(2019年10期)2019-10-26 02:48:08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電子制作(2018年18期)2018-11-14 01:48:06
小學生作文(中高年級適用)(2018年3期)2018-04-18 01:24:47
小學教學參考(2015年20期)2016-01-15 08:44:38
少兒科學周刊·少年版(2015年4期)2015-07-07 2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