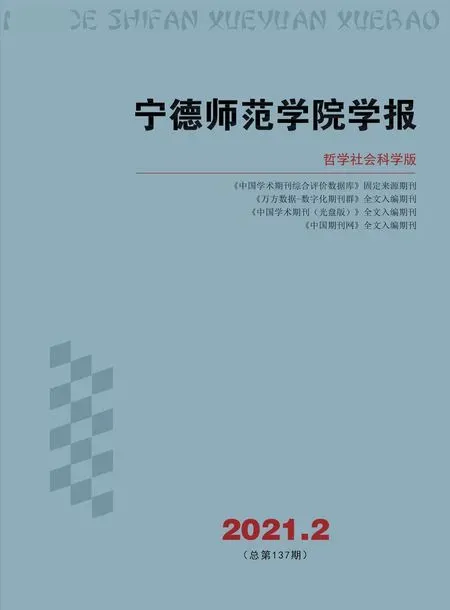建國后西洋合奏音樂創作發展分期及其藝術特征
陳 習
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后,改變了之前我國文化事業自發性的發展狀態,開始以國家的力量給予音樂藝術事業應有的關注與支持,使得我國器樂的發展條件大大優越于以往的各個歷史時期,包括中西方樂器獨奏、合奏在內的各種姐妹藝術如魚得水般地獲得了迅速的成長。在這樣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建設事業復蘇中,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相繼建立了相當規模的專業西洋交響樂團:“中央樂團”(1952 年)、“上海樂團交響樂隊”(1952 年)、“中央廣播交響樂團”(1956 年)、“廣州樂團”(1957 年)等等,有力地促動了中國西洋樂器音樂的創作發展。
西洋合奏音樂正是于建國后,隨著我國作曲家創作探索的不斷擴大與深入,逐漸壯大起來的一種常規合奏音樂形式。它不同于我國傳統的民族樂器合奏、也不同于著力追求單一樂器性能與表現力的獨奏音樂形式,而是大膽地、有選擇地將20 世紀后進入中國人視野中的各類西洋樂器匯聚在一起,作了室內樂重奏性或管弦樂隊合奏性組合的探索。這種源自西方的合奏音樂正開啟著凸顯中國生活、中國情感、中國精神為己任的新征程。它是自20 世紀初首次東西方音樂藝術的激烈碰撞后,又一次深化音樂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重要產物。而根據我國社會歷史與藝術事業發展的原因,建國后這一階段西洋合奏音樂發展經歷了建國十七年間的“探索期”、文革間的“曲折期”,到改革開放后的“發展期”三個階段,呈現出其歷史發展與邏輯認識逐步向深層次延展的基本態勢。
一、探索期(1949-1966):“西體中用話山河”
中國管弦樂團和專業音樂教育的建設,以及建國后較為活躍的音樂表演活動,為中國作曲家大膽探索西洋樂器合奏音樂創作奠定了可靠的基礎。當然,畢竟是探索時期,最早的創作嘗試從小型的室內樂合奏曲開始,繼而中小型單樂章管弦樂合奏曲出現,逐步到大型協奏曲、交響音樂的探索,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廣泛性與多元化特點。
室內樂合奏曲是這一時期西洋樂器合奏音樂最早涉及的創作領域。當時就讀于上海音樂學院的俞麗娜與幾位同窗,他們為探討西洋弦樂演奏和創作的民族化問題,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學派實驗小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弦樂四重奏《梁祝》為伊始,促發了我國早期室內樂合奏作品的誕生,如弦樂四重奏作品:《烈士日記》(何占豪曲)、《弦樂四重奏》(吳祖強曲)、《G 大調弦樂四重奏》(瞿維曲);其他重奏作品:鋼琴三重奏《在臺灣高山地帶》與管樂五重奏《幸福的童年》(江文也曲)、《木管五重奏》(馬思聰曲)等。此外,還有不少小提琴齊奏曲也帶來了一定的社會反響,如王家陽以青海民歌改編的《四季調》、丁芷諾以同名電影主題曲改編的《洪湖水浪打浪》、沈西蒂等人以彝族民歌編創的《姐妹歌》、司徒華城以廣東民歌改編的《旱天雷》,還有唐德昂等以新疆民歌改編的大提琴與低音提琴齊奏曲《送我一支玫瑰花》等。這些合奏作品大多數直接取材于各地的民歌小曲,均采用了移植編創手法,雖然在主題延展、和聲運用與織體構成的邏輯思維方面較為稚嫩,有著明顯的模仿痕跡,但是中國作曲家大膽借鑒西方的創作經驗,積極探尋具有中國特色的合奏音樂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實踐,為當時乃至其后我國西洋合奏音樂的創作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參照。
中小型管弦樂合奏曲在這一階段煥發生機,出現了不少高質量或深受人民喜愛的優秀作品,如《瑤族舞曲》(劉鐵山、茅沅曲)、《黃鶴的故事》(施詠康曲)、《嘎達梅林》(辛滬光曲)、《歡樂的草原》(秦詠誠曲)、《貔貅舞曲》(王義平曲)、《汨羅沉流》(江文也曲)、《紅旗頌》(呂其明曲)、《人民英雄紀念碑》(瞿維曲)、《馬車》(葛炎曲)、《保衛延安》(羅忠镕與鄧宗安曲)、《煙波江上》(江定仙曲)、《節日序曲》(施萬春曲)、《渡江交響詩》(徐振民曲)等。這些作品雖然大多是單樂章的交響詩或序曲,但創作題材豐富多姿,從描繪自然風光到表現民俗風情,從捕捉民間生活現實到感悟世俗情態,皆有涉獵。同時,它們都有著動人的主題旋律、鮮明的音樂形象、簡潔干凈的配器手法等,將我國西洋管弦樂創作水平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協奏曲創作作為大型合奏音樂體裁之一,其寫作需要更為精深的藝術創造力。而這一階段的協奏曲數量雖少,但是就作品質量而言,則有了較大的提升。比如,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何占豪與陳鋼曲)、《我的家鄉》(許元植曲);大提琴協奏曲:《A 大調大提琴協奏曲》(馬思聰曲)、《嘎達梅林》(王強曲);還有圓號協奏曲《紀念》(施詠康曲)等。《梁祝》無疑是新中國成立后最為出類拔萃的一部管弦樂作品,至今仍然活躍于國內外的各類音樂舞臺,保持著長久的藝術魅力。該樂曲的創作主線圍繞著我國家喻戶曉的民間傳說故事藍本而展開,運用了傳統章回體小說的陳述方式來設計單樂章多段標題音樂的結構布局。同時,汲取中國傳統越劇唱腔的音調語言,與西洋奏鳴曲式、和聲、復調等音樂表現形式相融合,并大膽地借鑒了我國民間傳統樂器:二胡、古箏、三弦、琵琶等獨特的演奏技法,融貫古今、中西,是近現代探索中國管弦樂創作實現民族風格與西洋協奏曲寫作規范相結合的成功范例。
除了單樂章的協奏曲外,這一時期大型多樂章體裁創作也有了質的飛躍,比如,管弦樂組曲:《新中國組曲》(丁善德曲)、《歡喜組曲》 與 《山林之歌》(馬思聰曲)、《中國民歌組曲》(李偉才曲)、《春節組曲》(李煥之曲)、《康藏組曲》(陸華柏)、《云南音詩》(王西麟曲)、《漓江音畫》(鄭路曲)、《魚美人》(吳祖強、杜鳴心曲)、《四川組曲》(羅忠镕曲);大型交響曲:《浣溪沙》與《在烈火中永生》(羅忠镕曲)、《英雄海島》(李煥之曲)、《抗日戰爭》(王云階曲)、《長征》(丁善德曲)、《東方的曙光》(施詠康曲)等等。這些作品絕大多數以標題音樂寫成,對各類西洋管弦樂手法進行探索和嘗試。而在題材方面,既反映了祖國各地的壯麗山川與民俗民風,也深入記載了在這一特殊時期中國人民艱苦而卓越的歷史戰爭與革命歷程,對大型交響曲創作的“現實性”、“民族性”與“通俗性”的相糅合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二、曲折期(1966-1976):“樣板移植譜頌歌”
“文革”時期,西洋合奏音樂也受到了催慘性的打擊,非“樣板”類的管弦樂藝術大多被取締。而那些以“樣板戲”、革命歌曲、傳統古曲與民歌為基礎音樂材料加以移植的“改編式”創作,因題材內容上容易符合當時的“歌頌性”藝術評價標準,題材音調取材上擁有較廣泛的群眾基礎,故而成為大多數中國作曲家在這一時期西洋合奏音樂創作的“夾縫”中尋求突破口的一種普遍嘗試。根據其素材淵源,主要劃分為三種改編樣式:
其一,“樣板戲”改編樣式,代表性作品有:管弦樂組曲《白毛女》(瞿維曲)、重奏曲《白毛女》(朱踐耳、施詠康曲)、《海港》(譚蜜子與林恩蓓曲)、《窗花舞》與《都有一顆紅亮的心》(林銘述等曲)、小提琴齊奏《甘灑熱血寫春秋》(顧冠仁曲)、《快樂的女戰士》(阿克儉曲)等。
其二,革命戰地歌曲改編樣式,代表性作品有:鋼琴協奏曲《黃河》(劉莊與儲望華等曲)、弦樂四重奏《翻身道情》(阿克儉曲)、《游擊隊之歌》(隋克強曲)、小提琴齊奏《井岡山上太陽紅》(夏宗荃曲)、《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梁壽琪曲)、《我們是青年突擊隊》(崔義光與金勝吉曲)等。
其三,傳統古曲與民歌的改編樣式,代表性作品有:弦樂合奏《二泉映月》(吳祖強曲)、弦樂重奏《漢宮秋月》(梁建志曲)、《牧歌》(祝恒謙曲)、《歡樂舞曲》(靳延平曲)、小提琴齊奏《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劉奇曲)、《沂蒙山之歌》(丁芷諾曲)、《八月桂花遍地開》(舟波曲)等。
上述這些改編曲,幾乎原封不動地引用了原曲的經典唱段與文學標題,在音樂內容與情感格調上也保持著與原作相一致的歌頌性與通俗化傾向。而在各自的創作方式上也基本是將原作主題旋律在樂器上進行忠實復述的基礎上的擴充、延展或加花,很難真正發揮管弦樂器自身的性能與表現力。當然,其中也有較為出色的作品,如根據樣板戲《白毛女》改編的同名弦樂四重奏與管弦樂組曲,脫出簡單形式轉換的巢臼,在探索用室內樂及管弦樂組曲形式表現母本音樂意蘊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寫作上也比較精致細膩[1]。而移植同名二胡曲的弦樂合奏作品《二泉映月》,也基本沿襲著原獨奏曲滄桑、凝重的音樂基調。在復調手法與聲部織體寫作上,較為充分地發揮了弦樂隊的藝術表現力,并以精簡而雋永的音樂筆觸,塑造出泉清月冷、余韻綿長的中國式意境。
這一時期,真正屬于原創性的西洋合奏音樂作品數量較少,主要產生于“文革”中后期。代表性的作品有,管弦樂曲《忠魂篇》(李序曲)、《北京喜訊到邊寨》(鄭路與馬洪業曲)、小號協奏曲《草原頌》(魏家稔曲)、鋼琴協奏曲《南海兒女》(儲望華與朱工一曲)、《錦繡祖國》(黃楨茂曲)、小提琴齊奏《愉快的小牧民》(李自立曲)等等。
三、發展期(1976-2000):“融匯多元化中西”
“文革”結束后,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全新的面貌,也迎來了西洋樂器合奏音樂煥然一新的發展態勢。在西洋管弦樂隊建設上,不光集中在幾個大城市,而是全國的重要城市都有管弦樂團組建。同時,以1981 年“全國交響音樂作品評獎”活動為伊始,極大地促發了我國各類音樂創作的活躍開展,出現了西洋樂器合奏音樂空前繁榮、且個性多元的重要景象。
室內樂合奏曲隨著我國80 年代前后的“重奏音樂熱”的推動,產生了眾多質量頗高、風格創新的優秀作品,成為這一時期創作發展中最為突出的領域。代表性作品有弦樂四重奏:《風、雅、頌》(譚盾曲)、《琴曲》(周龍曲)、《川江敘事》(郭文景曲)、《邊寨素描》(李曉琦曲)、《第二弦樂四重奏》(羅忠镕曲)、《兩個時辰》(何訓田曲)、《苗歌》(許舒亞曲)、《弦樂四重奏》(賈達群曲)、《村祭》(莫五平曲)等;鋼琴五重奏:《桃花塢木刻年畫》(林華曲)、《賦格音詩》(曹光平曲)等;鋼琴三重奏:《玉門散》(張慶祥曲)、《C 大調鋼琴三重奏》(丁善德曲)、《鋼琴三重奏》(黃安倫曲)、《為鋼琴三重奏而作的四個樂章》(盛宗亮曲)、《長城敘事曲》(陸培曲)等;管樂五重奏:《管樂五重奏》(羅忠镕曲)、《版面集》(王西麟曲)、《春江花月夜》(劉莊曲)等。此外,還有鋼琴弦樂四重奏《思變》(吳粵北曲)、單簧管和弦樂四重奏《易》(陳其鋼曲)、《太行山音畫》(王西麟曲)、《空弦與聯想》(金復載曲)、《弦樂隊慢板》(譚盾曲)、《秋天的等待》(許舒亞曲)、《塔什庫爾干印象》(劉莊曲)、《定》(周龍曲)、《蜀韻》(賈達群曲)、《龍門石窟印象》(周虹曲)、《四重奏——為長笛、圓號、大提琴與鋼琴》(曹光平曲)、《大擺對》(高永謀曲)、《四重奏》(王西麟曲)、《云》(施子偉曲)、《馬九匹》(葉小鋼曲)、《春夜喜雨》(陳怡曲)、《祝福》(馬水龍曲)等室內樂合奏曲。
這些作品既能多方位地汲取民間音調素材、或挖掘我國傳統文化之意蘊,又不落于俗套;既善于運用各種近現代技法、或突破常規器樂手法產生不同的音色音響,但又不刻意追逐孤立、標新立異的新穎效果。如《風、雅、頌》廣泛地吸收了我國民間戲曲、廣西瑤族民歌與傳統古琴曲等多種民間音調中富于特色的調式、旋法與節奏,以及“中國風格的音樂陳述方式與多樣化的民樂演奏技法,并巧妙地將之與泛調性、十二音序列技法等現代作曲手法相結合,以獨樹一幟的中西合璧之理念為我國現當代室內樂創作打開了新天地”[2]。而《琴曲》則在演奏技法上,既借鑒了古琴、琵琶等民間彈撥樂器特有的“吟、揉、輪、拂”手法,同時又突破西洋弦樂常規演奏技法,發展了碼后拉奏、指尖撥奏、指甲彈側板、手掌拍板等多種新技能,造成合奏音響音色上的強烈對比與反差,賦予突出的戲劇性效果。
同時,在這些室內樂合奏曲的體裁創作上,也不拘泥于傳統的重奏樣式,而尋求開放的、多元性的表現途徑,對一些非常規的西洋樂器組合形式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如為長笛、單簧管、小提琴、大提琴與鋼琴而作的《春夜喜雨》,樂曲“從主題旋律、整體曲式結構設計、織體發展及配器安排上都使用了西方現代創作技術手法,使中國民族傳統音樂與西方現代音樂技術相結合,以現代風格和形象出色地弘揚了中國文化”[3]。此外,還有為小提琴、大提琴、單簧管與鋼琴而作的《四重奏》,為兩把小提琴、鋼琴與打擊樂而作的《蜀韻》,為單簧管、打擊樂和低音提琴而作的《定》,為小提琴、大提琴與豎琴而作的《祝福》等等。
自70 年代末以來,大型協奏曲體裁已然呈現出強勁的多元發展勢頭,其創作題材與技法方面涌現出的大膽出新,令我國西洋樂器協奏曲創作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比較突出的鋼琴協奏曲有:《降B 大調鋼琴協奏曲》(丁善德曲)、《山林》(劉敦南曲)、《鋼琴協奏曲》(譚盾曲)、《春之采》(杜鳴心曲)、《鋼琴協奏曲》(徐紀星曲)、《降D 大調鋼琴與樂隊》(郭祖榮曲)、《音詩》(瞿維曲)等;小提琴協奏曲有:《抹去吧,眼角的淚》(李耀東曲)、《小提琴協奏曲》(杜鳴心曲)、《鹿回頭傳奇》(宗江與何東曲)、《土韻》(郭文景曲)、《最后的樂園》(葉小鋼曲)、《小提琴協奏曲》(許舒亞曲)、《王昭君》(陳鋼曲)、《火天堂》(趙曦曲)等;中提琴協奏曲有:《弦詩》、《山與風》(陳怡曲)等;大提琴協奏曲有:《第一大提琴幻想曲——獻給我的父親》(周虹曲)、《地圖:尋回消失中的根籟》(譚盾曲)、《索》(許舒亞曲)等;管樂協奏曲:《雙簧管協奏曲》(陳鋼曲)等。其中,許舒亞《小提琴協奏曲》展示了古今、中外創作手法熔于一爐的自由吸收與恰當發揮:作品中涉及了十二音體系、序列音樂、點描音樂與非常規器樂演奏手法等現代先鋒派作曲技巧,同時五聲性音調基因在樂曲中有機貫穿,民間樂器“彈、抹、勾、挑、滑”等特殊技法的理性借鑒,共同營造了意象交融的中國古典詩歌意境。
這一時期的大中型管弦樂合奏曲創作也表現出大規模發展趨勢,而總體寫作水平,無論是音樂內涵的深度、題材的廣度,還是技巧運用的精度,都較之前有了明顯的提高。比較突出的作品有:《交響幻想曲——紀念為真理而獻身的勇士》、《黔嶺素描》與《納西一奇》(朱踐耳曲)、《云南音詩》(王西麟曲)、《第二交響曲——清明祭》(陳培勛曲)、《北方山林》(張千一曲)、《第二交響曲》(盛禮洪曲)、《布依組曲》(唐建平曲)、《長城交響曲》(杜鳴心曲)、《三峽素描》(王義平曲)、《山鬼》(鐘信民曲)、《地平線》與《釋迦之沉默》(葉小鋼曲)、《和平的代價》(楊立青曲)、《第一交響樂》(瞿小松曲)、《蜀道難-為李白詩譜曲》與《樂隊劇場Ⅰ》、《樂隊劇場Ⅱ》(譚盾曲)、《楓橋夜泊》(徐振民曲)、《交響狂想詩——為阿佤山的記憶》與《土樓回響》(劉湲曲)、《2000》(趙季平曲)、《交響舞詩》(趙曉生曲)等。這些大中型合奏曲,雖然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現代音樂觀念的影響,但在創作技法的運用上更多地體現了以傳統為基石,積極地探索了將民族調式和聲、傳統復調手法與現代西方多調性、泛調性乃至無調性創作技法相融合,在其整體藝術構思、主題音調特色與風格韻味上仍然保持著與我國傳統文化、民族意蘊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系,突出體現了強烈的時代感與民族性。如朱踐耳《黔嶺素描》與《納西一奇》這兩部作品力圖表達我國西南少數民族民俗生活與精神面貌,廣泛提煉了“脫胎”于我國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民間音樂中固有的特性因素:苗族的“飛歌”音調、蘆笙的四五度和聲、侗族小歌的調式音列、侗族大歌的二度疊置、民歌演唱的即興吟誦、民族拉弦樂器的遠距離滑音、傳統戲曲的散板節奏等等,并努力開掘這些獨特音樂品質與多調性疊置、線形和聲調式等現代作曲技法之間的聯系,力圖將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創造出了凸顯民族精神氣質的蘊含時代感的成功之作。
結束語
西洋合奏音樂創作雖早已萌芽,但由于20 世紀上半葉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方面的諸多桎梏,至建國后隨著文藝政策的復興,才獲得了全面而切實的迅速發展。可以說,建國以來西洋合奏音樂創作究其歷史演進,呈現出“馬鞍型”曲線發展。除了十年“文革”造成音樂創作發展不可避免的空間局限與成果銳減,建國后十七年與改革開放二十年則帶來了創作數量與質量不可估量的迅速積累與提升,對推動中國當代西洋合奏音樂乃至其他形式的中國音樂創作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深遠影響。
而這一階段,作為藝術創造的一個完整時期,西洋合奏音樂創作在題材方面從單一的“現實性”或“歌頌性”走向“多元化”;體裁方面從中小型的“室內樂”或“單樂章協奏曲”走向大型的“多樂章協奏曲”與交響曲;創作思維方面,從對歐洲古典室內樂創作技法的追尋,到民族性與現代性相融匯的多元追求,等等……,無一不彰顯我國西洋合奏音樂發展向縱深遞進的銳氣與活力。
注釋:
[1]居其宏:《共和國音樂史》,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 年,第142 頁。
[2]陳習:《中國小提琴音樂創作史研究》,福建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
[3]吳家軍:《繼承傳統、扎根民間、中西融合——對陳怡創作混合室內樂五重奏<春夜喜雨>的分析》,《樂府新聲》2008 年第2 期。
[4]王安國:《現代和聲與中國作品研究》,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年。
[5]汪毓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1840-2000)》,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8 年。
[6]胡郁青、趙玲:《中國音樂史》,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年。
[7]梁茂春、陳秉義:《中國音樂通史》,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7 年。
[8]梁茂春:《音樂史的邊角》,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5 年。
[9]李吉提:《中國當代音樂分析》,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