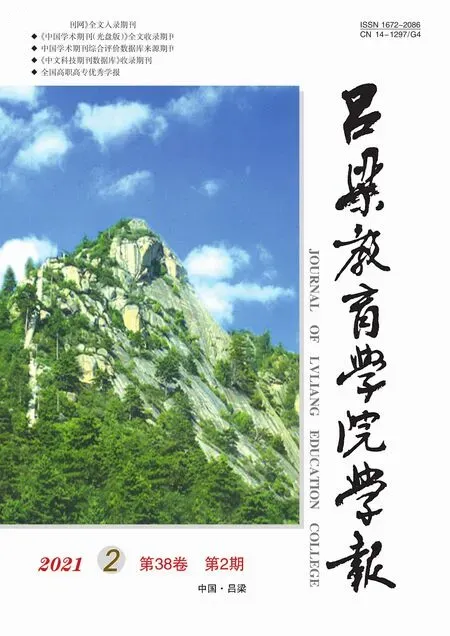數字媒體時代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例
李夢瑩
(安徽大學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數媒時代的到來使動畫電影愈來愈趨向于視覺刺激,從而忽視了作為故事本身的故事性特征。《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簡稱《哪吒》)是當下動畫電影中的一股清流,電影中以中國傳統故事中哪吒為人物原型,在此基礎上對人物故事進行改造,使其呈現出全新面貌,為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方法和思路。《哪吒》在故事層、言語層以及文化層都對原有故事進行了改良和創新,其創作手法和藝術思路值得探討,以期對當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有所啟發。
一、內容充實化——情節與人物
在敘事性作品中,故事層指故事整體,其中情節與人物是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敘事學將其歸納為兩種觀點,一種為“心理性”人物觀,即認為人物是作品中的首要因素;一種為“功能性”人物觀,即認為情節是作品中的首要因素,而人物要依賴于情節。影片《哪吒》作為一部敘事性作品卻沒有偏重于“人物”或“情節”,而是將兩者共同展開,兩者體現出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
(一)可濃縮為一個陳述句
《哪吒》以中國傳統神話故事為出發點,講述哪吒幼年時期的成長經歷,即魔丸哪吒因被施了天劫咒,三年后中天劫咒而死的故事。影片從整體上遵循的是線性發展結構,情節的發展前后連貫且體現出作為一部敘事性作品其情節的“陳述句”式展開模式。
20世紀西方敘事學認為,“敘述作品是一個大句子”[1]83,敘述型作品要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使前后連成一個有機整體,這與動畫電影以故事貫穿始末不謀而合。動畫電影的完成需要一個完整故事的支撐,而一個完整故事則是由若干個小故事組成,在“句子”的定義中,論及句子是由主謂賓構成,且能夠表達一個相對完整的意思、有特定語調的語言單位。用分析句子的方法來分析一部敘述作品有其合理一面,往往能夠對故事內容抽絲剝繭,使故事脈絡清晰可見,從而檢驗出作品各個成分間是否能夠形成一個有機整體,是否能夠顯示出一種不可錯亂的結構關系。
在國產動畫電影《哪吒》這個故事中,哪吒成為主語,而這三年間發生的事情則成為了故事的謂語。將故事細分,我們就能發現,這一敘述句是由若干小的敘述句組成,將若干個小故事串聯起來就形成了有序的前后因果關系。每個陳述句都可看做是一個小故事,故事與故事之間環環相扣,前者的果構成了后者的因,而每個小故事均起到了轉折的作用,使整個故事看起來既緊湊自然又扣人心弦。用分析句子的方法來分析《哪吒》,我們可以看到《哪吒》在講述故事時的成功之處:在敘述作品時要將整體觀念灌入其中,即整個故事要能表達一個前后連貫的因果關系,并能夠圍繞故事的核心思想為其設計恰當的故事情節,且作為分子的各個小故事要做到彼此之間環環相扣,同時契合整體故事的主題,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句法結構”。
(二)用矛盾凸顯人物心理
《哪吒》在情節的安排上構思巧妙,環環相扣,然而卻并沒有遵循“功能性”人物觀的觀點,即“將人物視為從屬于情節或行動的‘行動者’或‘行動素’,”[1]46《哪吒》在講述故事時,認識到情節的展開必定是建立在人物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人物不是事件發生的決定者,那他會是什么呢?如果事件不能展現出人物來,那事件又是什么呢?”[2]《哪吒》對人物進行了重新塑造,擺脫了傳統故事中固化的角色設定,從而擁有了深層次的心理內涵。
哪吒與敖丙形象的顛覆為構建人物內心增加了厚度。一直以積極正面形象示人的哪吒在這里被塑造成了魔丸轉世的魔童,而一向處于邊緣化的敖丙成為故事的核心人物,對兩人形象的突破使其有了更大的塑造空間,人物從平面走向了深度;對傳統角色的重新設定,不僅給故事內容增添了新意,也讓人物形象更加飽滿,更加貼近生活,其情感的真實流露能夠與當下人產生深刻的共鳴。其次,為了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活立體、更富有真情實感,故事制造了多層人物間的矛盾沖突,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碰撞上推進人物性格向更深層次發展。例如,哪吒與敖丙本是同根所生,而兩人卻由于代表不同的家族利益而走向了反目,作為一體的兩面,兩人通過矛盾的碰撞從而實現了自身性格的互補。
在《哪吒》故事中不僅有自我對自我身份認同之間的矛盾,還有自我與他人認同之間的矛盾,矛盾的迸發促進了情感的激發,同時也借助矛盾進一步刻畫了更為鮮活立體的人物形象,正如金圣嘆評《水滸》時所說:“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3]。
二、 敘事要素多元化——蒙太奇與全齡化
話語層與故事層相互依存,在一部敘事性作品中既要關注故事層又要注重話語層。所謂的話語層指的是故事如何被講述,即探究其采用何種情節設計或藝術視角等。通過分析故事的內部結構特征,進一步為如何講好故事提供指導。《哪吒》在講述故事時,運用多種蒙太奇手法和全齡化視角,使其在話語層面呈現出獨特的藝術魅力。
(一)老少皆宜的全齡化視角
《哪吒》沒有陷入“低幼化”的主流之中,而是采用了全齡化視角。所謂全齡化視角,指的是一種適合各個年齡的敘事視角。《哪吒》使用全齡化敘述視角展現了童真童趣,而且還加入了深層次的情感表現,體現出成人的兒童化和兒童的成人化兩方面的特點。
成人的兒童化,首先體現在在人物塑造上,略帶油膩感的肥胖大叔——太乙真人;調皮搗蛋的鄰家熊孩子——哪吒;工作孩子兩頭忙的都市白領——哪吒之母。原本題材嚴肅的哪吒傳說加入了這些貼近生活的角色后,變得詼諧幽默,使成年觀眾產生了強烈的身份認同感。在語言的表達上,《哪吒》大膽使用了方言、口語、打油詩等,使整個故事呈現出輕松自然的色調。在情景的安排上,指點江山筆勾畫出帶有現代意味的游樂場,激流勇進、水柱過山車等充滿了童真童趣。由此可見,觀眾所期望的不僅僅是充滿科技感的玄幻鏡頭,更是“一部能解放心靈,帶領他們返老還童的動畫電影”[4]。
動畫電影“低幼化”帶來了動畫電影在制作上的粗濫、表達情感上的簡單乏味等,忽略了兒童在審美和情感上的需求。《哪吒》在這些方面做出了進步和超越。故事在情節的安排上緊湊得當,畫面呈現精益求精、場景安排栩栩如生、鏡頭特效酷炫十足等都體現出影片對質感的追求。在情感的表達上,故事并沒有以僅供娛樂的結尾收場,而是通過影片一層層鋪墊,引出了親情、友情、天命等具有深度的哲學思考。
《哪吒》獲得觀眾認可,全齡化成為關鍵因素。在全齡化視角的使用中,宮崎駿是“第一個將動畫電影上升到人文高度的思想家”[5],在華特·迪士尼看來,“我要在工作中努力實現并表現天真,讓它可以顯示出笑聲的健康,生活的快樂,顯出人性”[6],可見全齡化視角使動畫電影跳出低幼化、淺層次、娛樂化的桎梏,為其展現富有深度的人文思考提供了切入點。
(二)會說話的鏡頭語言
《哪吒》中多種蒙太奇手法并用,體現出敘事的多樣性和構思的巧妙性,在話語層次中的匠心獨運使得它在國產動畫電影中脫穎而出。敘事蒙太奇是一種“通過對故事情節的發展流程以及前后關系的切分來重新組合段落場景”[7]的敘述手法。故事沒有停留在平行蒙太奇的舒適區,而是力求創新,巧妙插入平行、交叉、倒敘等多種蒙太奇手法。
《哪吒》將平行蒙太奇與交叉蒙太奇手法并用,構成了多種矛盾交織的張力結構。故事以同時異地發生的兩條情節線索的并列表現,同時又將同一時間不同地域發生的數條情節線迅速而頻繁地交替剪接在一起,兩條線索相互影響,最后匯合在一起。一方面,海底煉獄與陳塘關李家在平行敘事中形成了一種對比,原本應降生在名門可堪大用的靈珠化身成異類——龍王之子,而本應被摧毀的魔丸卻成了李靖之子,展現出魔丸與靈珠錯位的人生,形成了兩者之間強烈的矛盾沖突,另一方面,又將哪吒與敖丙同樣不幸的命運通過鏡頭的交叉放到一起,使兩人身不由己的命運悲劇感得到加強。
倒敘蒙太奇,即用倒敘的手法將結構打亂,并依照故事內在邏輯將故事的過去與現在組合在一起。倒敘手法在故事中起到了畫龍點睛之用。風火輪使哪吒看到了三年前父親代自己受天雷之劫一事,使過去與當下的情節互為補充和說明,讓哪吒看到了隱秘而深沉的父愛,從而使哪吒對父親的誤會解開,自以為缺失的親情其實是父母背后的默默付出,從而將劇情推入了高潮。
《哪吒》在講述故事時,將連續蒙太奇、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倒敘蒙太奇并用,形成了敘述的多樣性,從中我們也能看到多種蒙太奇的靈活運用能夠達到故事處處轉折、起伏跌宕的藝術效果,激起觀眾對未知情節的觀賞興趣。
三、 不同文本間的對話——互文性
數媒時代的到來為各類文本間的自由對話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哪吒》借鑒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實現了跨文本間的對話,主要表現在故事的話語層次以及客體世界層次上。
(一)話語層次的互文及藝術效果
《哪吒》能夠獲得獨特的藝術感染力離不開話語層次上互文的使用。“話語層次”指的是構成敘事性作品的語音、語義層以及句子與句子所組成的意群層,其中,成語、典故、詩詞、歷史典故等進入文本并產生原文本所不具備的新的藝術效果,即實現了文本間的互文。對于以影片形式展現故事的《哪吒》而言,語音、語義以及句子與句子所形成的意象群在這里轉化成了會說話的圖像。
首先是將中國傳統文化元素融入到人物形象中。故事中的結界獸并非創作者憑空臆想而來,而是借鑒了三星堆青銅器的造型,兩個結界獸的原型取材于金面罩青銅頭像、青銅鷹形鈴和青銅獸面具。加入青銅形象,一方面符合故事發生歷史語境,讓影片充滿時間的積淀感和歷史認同感;另一方面,通過藝術的再加工,青銅結界獸以呆萌的造型和語言為影片增加了喜劇性,緩解了故事的緊張氛圍,使故事氛圍在緊張之余又充滿趣味。
其次將歷史典故組織進故事情景中。哪吒與太乙乘槎形小舟在水中自由穿行則是借用“仙人乘槎”這一典故。據晉代張華的《博物志·卷十》中記載: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8]“仙人乘槎”這一典故與山河社稷圖中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和美輪美奐的場景相吻合,不僅帶來了視覺享受,同時挖掘了傳統文化的藝術價值,增加了故事的文化底蘊和藝術韻味,使中國傳統文化潛移默化地融進了當代藝術作品中。
在故事的講述中,《哪吒》對中國傳統文化元素進行了吸收和創新,使其帶有中國特有的文化印記,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貌。互文手法的使用,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下仍有強大的生命力,傳統文化元素的運用使故事充滿古色古香的歷史感,加深了觀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同時也彰顯出中國故事特有的文化風采。
(二)客體世界層次的互文及藝術效果
客體世界層是話語層次的外在顯現,因此具有比較形象和完整的意義,可以與故事形成互文的材料包括上古神話、歷史文集、志人志怪小說、古代小說等。《哪吒》則使用了中國傳統神話題材——哪吒傳說,它將新的故事思維融合進神話傳說當中,體現出經典改編的創新性。
首先對于神話故事題材——哪吒傳說而言,它本身具有很強的可塑性,即進行再創造的空間很大。《哪吒》以哪吒為人物原型,一方面表明其題材的可塑性強,另一方面體現出當代電影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歸以及傳統文化借助當下數字動畫技術仍然具有巨大生命力。
《哪吒》故事對傳統神話題材的使用,并非是要對經典的完整重現,而是借此來表現具有時代特點的形而上思考。雖依托于傳統故事,但其表達內容主旨卻與當下緊密相連,“改編一方面通過對文學或歷史細節的小心重建來組織過去的文學經典,另一方面又明確地表明它們需要獲得當代觀眾的認同。”[9]《哪吒》與之前同樣屬于經典改編的動畫電影相比較而言,展現出了一種更復雜、更深厚、更多層次的現代性思考。《哪吒》將經典中哪吒與敖丙的善惡對立轉變為一體兩面的混元珠轉世,由此兩人自出生起便帶上了被注定的悲劇命運,這種無法擺脫的宿命論、成見論不僅對故事中的人物產生了影響,甚至引發了當代人對自身生存狀態的思考。在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上,《哪吒》并沒有遵循以往“削肉還母、剔骨還父”的設定,而是將父子間的矛盾沖突消解,從而建構起自我與命運的抗爭,“我命由我不由天”反映的是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自我主體的認同。
故事中由于互文手法的使用,使傳統與現代建立起了緊密聯系,無論在話語層次還是在客體世界層次,《哪吒》都有意識地將傳統與現代結合,使舊題材呈現新面貌,為故事增加了新內涵的同時又富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風貌。
四、對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美學思考
講好中國故事面臨著講什么和如何講的問題,尤其是當下以科技為載體的視覺文化興起,使得創作越來越追求一種奇觀效果。面對“讀圖時代”的到來,我們更應該注重加強對自身故事內涵的建設,從而有效抵制淺層化、碎片式的閱讀,使大眾在具有深層次的審美內涵中構建起豐富的精神文明世界。《哪吒》積極向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資源和創作靈感,使其為故事注入了中國色彩和中國力量。在全球文化不斷交流融合中,踐行“多元文化主義”已成為共識,而中國故事要講的好,講出國門,加強自身文化的建設是當下首要任務。“實際上,全球化和本土化是辯證統一的關系。……而新時代的全球化則更大程度地尋求著本土文化特征的進一步發展和融入。”[10]中國故事要在中國文化中孕育和產生,才能培養我們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自信,這樣故事才能具有源源不斷的生命力,才能彰顯中國故事的美學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