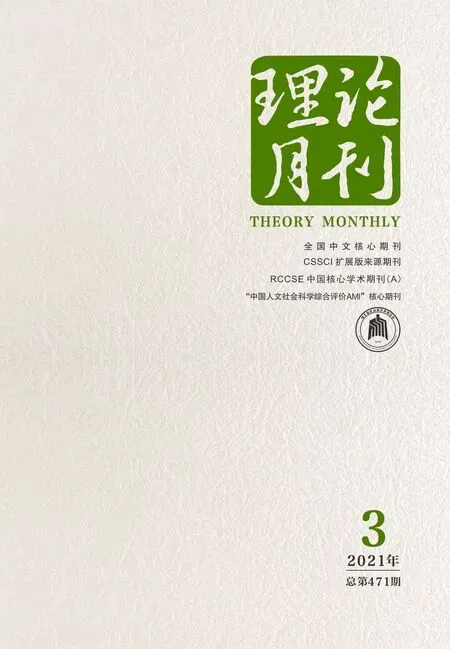鄉村文化建設的媒介傳播與振興策略
□劉 洋,羅小洪
(1.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550025;2.中共貴州省委組織部,貴州 貴陽550002)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為構建中國精神、中國價值和中國力量的引航燈。文化的重要性歷來為學界重視,華裔學者林毓生(Yu-sheng Lin)關注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主張“將中國傳統中的一些符號、思想、價值和行為模式選擇出來,加以重組或改造,使之成為有利于革新的資源,并在這一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1]。德裔漢學家墨子刻(Metzger)對林毓生的觀點持有異議,他認為從語義而言,轉化是根本改變,屬革命派思維,調試是漸進更迭,屬改良派思維,“傳統的轉化”不能解釋“轉化”和“調試”[2]。錢穆、費孝通等中國學人更為務實,“文化本來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環境里得到的生活,就會形成什么方式,決定了這群人文化的性質”[3](p14)。實踐驗證了其觀點,“文化回歸”和“堅守傳統”均難以實現現代化的“自主性適應”,唯有以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文化自覺”回應“文化主體性”的訴求。以此而言,緣于鄉村生活和生產空間的平面性與城市生活和生產空間的立體性的不同,鄉村文化建設涵括的道德信仰、民俗節慶、文化價值、生態倫理等不僅是回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地生根的價值追求和行動策略,也是本土文化遺產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密嵌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訴求和依賴路徑。
鄉村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底色,凝聚著鄉土人文之美。2021 年2 月3 日至5 日,習近平總書記到貴州考察慰問,強調“脫貧之后,要接續推進鄉村振興,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4],指明了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方向。事實上,“三農”問題的中國獨創性實踐證明,農村文化建設與農村社會文明程度呈正相關性[5](p14-23),經濟社會愈發展,文化內涵愈豐富,文化作用愈強大。具體來講,理解鄉村振興戰略與鄉村文化建設,需要理解鄉村振興由鄉村產業振興、鄉村人才振興、鄉村文化振興、鄉村生態振興、鄉村組織振興組成[6](p15-18),其中,鄉村文化建設的“文化”強調的是“文化持有人的持有文化”[7](p17-21)。理解鄉村文化建設與媒介傳播,需要理解5G技術、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引領的技術變革加速嵌合日常生產生活,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也對鄉村文化帶來了深刻影響,以口頭媒介為核心的示現媒介系統、以書面媒介為核心的再現媒介系統、以表演媒介為核心的機器媒介系統共筑的鄉村文化媒介系統及融合策略,可以為鄉村文化振興提供思路。
二、鄉村文化媒介傳播的三種邏輯
美國傳播學家漢諾·哈特(Hanno Hardt)將傳播媒介分為示現媒介系統、再現媒介系統和機器媒介系統。示現媒介系統,即人們面對面傳遞信息的媒介,由人體本身的感覺器官來執行,比如口語、表情、姿勢、眼神等,不需要依賴任何機器手段[8]。示現媒介系統通過“人”連接信源與信宿實現傳播,這種傳播方式并不局限于聲音媒質和口耳相傳,還包含姿態、動作、環境、交際等富有文化寓意的輔助媒介元素,“人”在其中既成為一種媒介,又作為一個主體完成信息傳播,因此“人”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融入自我情感和價值取向,并產生二次創作,實現文化再生產,導致示現媒介系統具有口頭藝術創造的功能。
(一)活態性與交互性混溶的示現媒介系統
原初社會,人類主要依靠口耳相傳來傳遞信息,口語、動作、表情、姿態等非語言符號(表演)成了信息交流與傳遞的基礎媒介,文化的傳承傳播亦是憑借示現媒介系統完成的。
示現媒介系統具有活態性。文化作為一種非物質形態,其傳播主要依靠口語傳遞完成,口語傳遞決定了示現媒介系統的活態性,離開口語,示現媒介系統的活態性便不復存在。傳播者的口耳相傳并非情感刺激,而是理性行為,諸如愉悅消遣、傳承教育等。鄉村文化作為群眾的精神生活,歸根結底都是日常生活的呈現,不同的時空中,傳播者的話語不是一成不變的,表達方式會隨時變化,這是人作為高級物種所具有的特質,且在傳播過程中,他們即興創作,從這個層面來講,他們既是傳播者又是講述者。因此,伴隨生產方式和生存環境的變化,文化也在持續變異。如苗族史詩《亞魯王》在貴州麻山地區活態傳承,至今仍有1700 余名傳承人,這些傳承人唱誦的《亞魯王》并不一致,會因個人經歷、思維方式不同而略有差異[9](p135-143)。同時,傳播者在傳遞過程中會在講述中輔以語調、肢體、表情等多種表達方式,接受者在表演場域中可以更為立體地感受其活態魅力。如川劇變臉在展演場域中強調多種形式的交互,此種交互亦成為活態傳承且影響力不斷擴大的核心要素。
示現媒介系統具有交互性。示現媒介系統至少需要兩個行為主體方能完成傳播過程,即傳播者和接受者,兩者缺一不可。示現媒介系統傳播路徑中,傳播者和接受者須置于同一時空,傳播者在傳播過程中能清晰地了解到接受者的反應,以便其能對他的講述做出適時的調整。同時,接受者針對講述中的疑問可以即刻向傳播者求得答案,還可圍繞傳播內容與傳播者進行交流互動和評介,實現對文化內涵的深層次解析,這是較為有效的文化傳播路徑。流傳于湖北江漢平原的彩龍船民俗,傳播者(表演者)走村串寨,每到一戶便祈福表演,戶主則供給一定的物資。在這一過程中,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有著明顯的互動。同時,不少地區至今都還保留著對歌習俗,如恩施民歌、廣東雷歌、湘西盤歌等,人們在一唱一和中抒發情感,傳播與接收在這一過程中交織并進。傳播者與接受者通過有聲話語和無聲言語彼此交互,彰顯出“人”作為媒介所具有的生命活力。
(二)長久性、靜態性、跨區域性及聯想性混溶的再現媒介系統
再現媒介系統,即通過繪畫、文字、印刷和攝影等信息媒介的互動。在此類系統中,對信息的傳播者(生產者)來說,需要使用物質工具或機器,但信息接收者則不需要。
再現媒介系統使得信息傳播不再依靠“人”作為聯結,物質工具或機器成為“人”感官功能的延伸。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直言,“媒介即是人的延伸”。在實踐中,再現媒介系統使得鄉村文化的傳播實現了長久性、靜態性、跨區域性、聯想性的混溶。再現媒介系統彌補了示現媒介系統的局限,增加了鄉村文化的傳播路徑,尤其是對那些失去傳承人或瀕臨消亡的文化而言,其價值是顯著的。這緣于再現媒介系統對鄉村文化的傳播和保護具有長久性和靜態性。相對于示現媒介系統,再現媒介系統不會受講述者的約束,亦不會因為講述者的消失而中斷傳播。
再現媒介系統具有長久性和靜態性。文化通過繪畫、文字、印刷、攝影等刻制在某一物品上后成為一個靜態的物品,且深深烙上時代印記,只要保存得當,便能長久傳承。再現媒介系統的長久性和靜態性特征,決定了其所傳遞的信息不會因時間、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這對于研究鄉村文化賴以生存的社會風貌和流變規律具有積極意義。諸如黔西縣化屋村的苗繡與蠟染,將苗族人民對歷史與自然的記憶織繡在一張張繡片上或印染在一匹匹麻布中。苗族婦女在制作百褶裙時,為了銘記先民的遷徙歷史,用繡線在裙身上織成五條平行的線條以記錄曾經跋履山川所經過的“黃河(渾水河)、武罩山、風雨關、長江(清水河)、毒蟲沖”[10](p114)。
再現媒介系統具有跨區域性和聯想性。鄉村文化通過再現媒介系統,可以實現跨族際、跨區域的傳播,不受時空限制,更為重要的是方言差異等阻礙迎刃而解。長期的歷史演進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不同地域的人民群眾創造了源于生活的代表性文化,但因自然條件的阻隔和不同區域間思維差異、語言差異,導致基于示現媒介系統的傳播路徑難以實現互通,再現媒介系統解決了困擾人們已久的難題,傳播者只要拿到文本,便可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同時,再現媒介系統是傳播者與文本的對話活動,閱讀過程中,文本可以勾起傳播者的記憶,讓傳播者產生聯想,實現對鄉村文化的深層次認識。諸如信天游從陜北傳遍大江南北,東北二人轉從北方傳到南方,京劇立足中國走向世界,都與再現媒介系統的傳播路徑密切相關。
(三)傳播手段與傳播介質革新的機器媒介系統
機器媒介系統的出現,既汲取了示現媒介系統和再現媒介系統在傳遞信息中的優勢,又彌補了示現媒介系統和再現媒介系統在傳遞信息中的局限。機器媒介系統以其融合性、協同性、個性化、多樣化的傳播手段和傳播介質,對鄉村文化的傳播和保護無疑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尤其是以音樂、舞蹈、曲藝、戲劇、雜技等為代表的具有展演特性的鄉村文化,因其特殊性,示現媒介系統和再現媒介系統難以很好地將其“音、形、義”全方位、直觀化、具象化地呈現在接受者面前,機器媒介系統彌補了這一缺憾。具體來講,電話、電報、唱片、電影、廣播、電視、手機等媒介實現了時間和空間、靜態和動態的突破。相隔千山萬水的人們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借助唱片、電影、廣播、電視、手機等機器媒介實現聲音與動態圖像的信息傳遞和交互,同時,在接受者參與遠距離的實時傳播中,大規模的復制重播能讓接受者再次接收信息,唯一的缺憾在于傳播者與接受者相對孤立,無法即時交互。
數字技術為鄉村文化建設帶來了新的可能。數字技術整合了信息采集、存儲、制播、傳輸等諸環節,實現了信息的交互性、實時性、協同性和集成性,信息的參與方均能實現掌握信息、傳遞信息和編輯信息,并在此過程中完成連續性傳播。數字技術的融合性,既有通信系統的廣布性,又有計算機系統的交互性,還有電視媒體的真實性,將圖像、文本、聲音、文字、視頻等信息全覆蓋,實現了時間與空間的協同,保證了信息傳播的及時與真實。對鄉村文化的文化持有人而言,機器媒介系統能夠確保及時感悟并參與鄉村文化建設全過程。對其他群眾而言,機器媒介系統能夠確保多渠道系統了解鄉村文化信息,不僅能強化自身文化知識,還能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
數字技術將傳統媒體、網絡媒體以及通信系統等全方位融合,關注諸種媒體的互動、互補與互溶。從面上看,數字技術可以實現更宏觀、更大體量的信息展示,但針對受眾的不同,數字技術又可以提供更為細致和個性化的信息服務,這基于受眾關注點的不同而產生的分類和調整,當然也是基于多平臺的展演方式。事實上,媒體平臺的增加使鄉村文化可獲得的展示機會得到增加,諸如通過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App 進行直觀的展示,以便于受眾參與互動性的在線虛擬模仿唱誦或者觀看學習鄉村文化技藝。
三、鄉村文化媒介傳播的三重局限
在鄉村文化建設的實踐中,由于單獨的媒介系統有較大的局限性,諸種傳播媒介是交織并行的。
(一)示現媒介系統的局限性
示現媒介系統是鄉村文化傳播的基礎方式,受時空限制與言語交流等因素影響,有傳播內容消逝快、傳播方式斷裂快、傳播受眾群體少等局限性。
傳播內容消逝快。示現媒介系統的活態性決定了其流動的易逝性。主要表現為示現媒介系統中,鄉村文化傳播主要依靠口語交流完成,這一過程中,傳播者實質上對鄉村文化進行了二次創作。源于個體差異,不同的傳播者會根據自我的價值取向和接受者的審美取向,增補刪減傳播內容,增強傳播內容的吸引力、觀賞性及實用性。此外,以口頭文學為代表的鄉村文化多為傳承人掌握,由于傳承人的言語表達具有獨一無二的特征,一旦這些傳承人離世,那么他們所具有的特色鮮明的口頭藝術表達會隨之消逝。
傳播方式斷裂快。在較長時間內,鄉村文化的傳播依靠口耳相傳,局限于特定時空,橫向傳播空間范圍小,縱向傳播變異程度大。人作為傳播主體,受外界環境、經濟狀況、價值觀念等影響,傳播方式呈現不同程度的斷裂,即斷崖式斷裂或藕斷式斷裂。諸如暢通的橫向社會流動在推動經濟社會急劇發展的同時,也消解了“人”在鄉土社會文化傳播中的主體作用,鄉村文化因無人承繼失去傳播機會。被譽為明朝文化活化石的安順天龍屯堡代表性文化——“花燈”,因無人表演、無人參與,僅留存于人們的記憶之中[11](p63-73)。
傳播受眾群體少。鄉村文化通過傳承人展演、群眾口傳,盡管傳播者和接受者在口耳相傳中實現了傳播者和接受者的角色轉換,增加了傳播的效度,但由于口耳相傳的特征,導致傳播范圍只能局限于某一區域內或某一群體內。諸如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等因地域性較強,受眾較少,傳播較難突破時空限制,受眾亦較難跨越族群。諸如水族的斗魚民俗,因斗魚品種僅存于三都縣蓋賴村和打魚村等水族村寨,流傳范圍狹窄,受眾也較少[12](p386)。
(二)再現媒介系統的局限性
再現媒介系統解決了示現媒介系統傳播中傳播內容易逝、傳播受眾少等問題,但面臨傳遞信息的機械性,難以讓讀者體悟到口頭語言的藝術美等局限性。
再現媒介系統傳遞信息的機械性。再現媒介系統的靜態性決定了其機械性,其承載的信息遠低于口語或動態圖像所承載的信息量。因為再現媒介系統是對示現媒介系統的記錄,換言之,通過繪畫、文字、印刷和攝影等印制的信息,是對傳播者和接受者面對面交流時的口語、動作、神態等的記錄。這些口語和動作、神態一旦被轉變成文字和圖像,其內容就被固定,面對面交流中聲音的高低起伏和神態的喜怒哀樂無法在文字和靜止的圖像中呈現,這就導致傳遞的信息量沒有口語的多,接受者的臨場體驗感也受到限制。如同一部戲曲,人們通過文字記錄獲取的信息必定不及人們在現場觀看表演中獲取的信息多,且獲得的體驗感也不一樣。
再現媒介系統難以讓讀者體悟到口頭語言的藝術美。眾多文化元素被搜集、整理出版后,展現在接受者面前的是書面語言,盡管搜集、整理過程一度強調要“忠實記錄、慎重整理”,但文本的整理必須符合言語規則,加之一些方言與普通話讀音之間的差異,所以書面語言難以實現方言所展示出的質樸美。如川南山歌《槐花幾時開》“高高山上(喲啊)一樹(喔)槐喲,手把欄桿(啥)望郎來喲喂”,其中“山”“樹”“手”要發成平舌音“san”“su”“sou”,否則就破壞了此曲的意境,因為四川方言中沒有平舌和翹舌之分,普通話中的翹舌音一律被讀成平舌音[13](p62-64)。
(三)機器媒介系統傳播的局限性
機器媒介系統以其融合性、協同性、個性化、多樣化的傳播手段和傳播介質,成為鄉村文化傳播的中堅力量,成為民眾了解鄉村文化的主要依靠。但回歸鄉村文化的生存場域,仍顯示出機器媒介系統在傳播中的瑕玷性。
數字技術為鄉村文化建設提供了技術支持。必須注意,基于圖像、聲音、文字的文化建設或信息交互僅是流于表面的技術變革,對鄉村文化振興的目標而言,并無直接聯系,如何保存、如何延續、如何刺激鄉村文化產生新的生命力才是鄉村文化建設的重要突破點。諸如“安順地戲”被譽為“中國戲劇的活化石”,它是屯堡人長期戍邊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娛神與娛人相結合的儀式性文化活動。在時代的發展中,地戲中娛神成分逐漸消退,娛人成分不斷增強,這實際上也是很多鄉村文化在歷史進程中獲得新生命力的縮影,但“安順地戲”的這一新生命力卻削弱了愛國戍邊的文化精神。同時,必須避免數字技術導致的鄉村文化異化,不能根據點擊率、收視率評判其價值,這緣于信息傳播中接受者的主體性被高度重視,傳播者可能為迎合某種需求,篡改文化現象。具體來講,鄉村文化多是俗文化形態,無論從觀賞角度還是從再生產角度,較多依賴接受者的理解與參與。當人物形象塑造、敘事結構、敘事內容、敘事模式、時空建構等均以觀眾為核心時,原本是反映某一時期某一特定區域群體智慧結晶的鄉村文化可能偏離了原本的意旨,讓鄉村文化的傳播傳承陷入尷尬境地。
此外,從示現媒介系統發展到再現媒介系統再到機器媒介系統,也是人體的信息功能不斷向外擴展,體外化信息系統獲得相對獨立性的過程。在機器媒介系統成為鄉村文化傳播的中堅力量,帶給人們極大的個人獨立空間的同時,人們不再受制于傳統媒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規約,任何時候、任何場域,只要拿出電子設備,就可以獲得自己想要了解的文化信息,物體作為媒介的屬性逐漸被開發出來,媒介的主體從“人”變換成了“物”。
當人類沉浸于個人世界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也被隔斷,從人類的發展層面來說無疑是悲劇的。這緣于網絡工具代替人類的感官系統完成信息的傳輸時,人類的感官系統功能必將被弱化,“技術層面的媒介對人體官能的延伸在終極意義上取消了回歸人類本性的可能,媒介替代了人,人被媒介控制而喪失了生態系統上的諸種本能”[14](p64-69),鄉村文化的生存場域已由人轉向機器,由活態轉變為“復述”,鄉村文化可能由于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文化環境而失去生命活力。但智能化和移動化的技術變革帶來的“萬物互聯”和“萬物皆媒”,為鄉村文化建設提供了新的諸種可能。“萬物互聯”促使平行走向的諸種媒體開始嘗試交織與融合,加速媒體傳播手段變革的同時,催生出新興的傳播形態。“萬物皆媒”改變了以人為主體的媒介傳播方式,物體媒介化、平臺多樣化在改變社會行為的同時,改變了媒體生態環境。
四、鄉村文化建設的媒介融合和振興路徑
媒介融合通過信息增殖與信息增值、跨界傳播與跨界融合、編碼排版與資源創新、數字文化化與文化數字化賦能鄉村文化建設,打開了鄉村文化振興的突破口,成為數字中國建設的生動實踐。諸如多元主體參與的鄉村直播,通過線上線下的立體媒介營銷,實現了產業鏈、數據鏈、價值鏈的三鏈合一[15](p125-131),產業效果、產業效率、產業效益的三效合一,做優存量、做大增量、提升質量的三量合一,在傳播鄉村文化技藝的同時,留住了鄉村文化記憶,推廣了鄉村文化產品,成為農民致富和鄉村振興的范型。
(一)信息增殖與信息增值
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由美國馬薩諸塞州理工大學E.B.浦爾教授(E.B.Pool)提出,指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16](p382),后美國新聞學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C.尼爾遜(A.C.Nielsen)重新定義了媒介融合概念,他認為媒介融合指“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17](p57)。媒介融合孕育于數字技術,并延伸出兩種可能——傳統媒介的數字化轉型和新型數字媒介業態,媒介融合的關鍵在于要素融為一體、傳播合而為一,融合絕非簡單疊加,而是優勢互補呈現出來的帕累托最優。
媒介融合是鄉村文化繁榮的關鍵,信息增殖與信息增值則是其支撐。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因主題的復雜多元,信源結構需要重新洗牌,曾經的信息受眾可能轉變為信息生產和傳播的主體,信息接收的過程也由傳統的被動接收轉變為主動選擇,傳播主體的增加也加速了信息源的產生,信息量的無限增殖反過來推動媒介融合的效度。諸如針對某種信息的多元解讀,在快速傳播的過程中實現了信息增殖,也可能導致信息增值,這是因為信息量的增加并不意味信息價值的增加,但信息量是前提,也是基礎。從產業層面來說,媒介融合催生的新型業態帶來了新的產業集群,并以此推動IP 矩陣實現長尾效應和蜂巢效應,促進了產業鏈的延伸,帶動農業、手工業等多種業態的線上線下聯動,并在事實上成為助推鄉村產業升級的有效手段。諸如以李子柒為代表的致力推廣鄉村文化的短視頻創作者,成為中國農村青年致富的帶頭人和推廣大使,被認為“沒有一個字夸中國好,但她講好了中國文化,講好了中國故事”[18]。
(二)跨界傳播與跨界融合
媒介融合的重要特征是跨界傳播[19](p58)。數字技術改變了媒介生態,這種改變本質上就是跨界傳播。跨界傳播被認為打破了傳統媒介固有的業態邊界,包括傳播者角色、傳播渠道、傳播內容、產業資源、媒介市場的跨界等[20](p1)。當前,跨界傳播已成為常態,媒介融合下的跨界傳播正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蔓延并產生影響。從跨界到融合,媒介之間的界限變得虛化甚至被消解,媒介作為社會獨立的信息系統的地位也正在被解構。當媒介跨界傳播擦除了邊界,傳統媒體組織結構的功能也會隨之消失,從積極的方面來看,邊界的擦除有利于形成多元傳播氛圍,但從消極的方面來看,則可能產生泛娛樂化和低俗化。
媒介融合是鄉村文化建設的關鍵,跨界傳播與跨界融合則是其手段。考慮跨界傳播與跨界融合的消極因素,需主動預判風險,把好價值關。媒介的融合與發展是以技術為前提的,只有創新文化內容才能實現技術與價值的雙重驅動,在眾多關注和傳播鄉村文化的短視頻創作者中,多是以鄉村美食、鄉村風景、鄉村人事、鄉村風俗為內容,旨在為用戶提供一種視覺享受和心靈的共鳴,從用戶的反饋(評論)中可發現,對于鄉愁和鄉村的向往事實上是一種對家的眷戀,以及對美好的一種寄托。山中雜記(元樸)自2018年入駐抖音平臺以來,以鄉村生活為題材創作了467 部作品,獲贊2066.7 萬次,收獲196.7 萬名粉絲。其中一條視頻下,有用戶反饋“因戀你家鄉的山水美景而關注你,又因你們的純樸而非常想去住一段時間”,繁華都市與寧靜的鄉村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5G+4K/8K、5G+VR 等技術的支持下,為疲于生活的都市人增強沉浸式觀感的同時,促進了線上的深度交流與互動,也帶動了線下的生產與消費。同時,要強化核心技術的驅動力,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開發新產品和新內容,搭建產品矩陣,在大數據的支持下實現技術的跨界融合,促進場景應用與用戶的深度互動,借助全息技術強化用戶黏性和沉浸式體驗效果[21](p90-93)。
(三)編碼排版與資源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充分運用新技術新應用創新媒體傳播方式,占領信息傳播制高點[22](p9-12)。從媒介融合上看,內容創新、形式創新、手段創新都重要,但內容創新是根本的[23](p22-29),傳統媒體將不再是直接生產內容的主體,而是進行創新數據的挖掘處理,進而創新媒體產品生產模式的引導者[24]。
媒體的數值化在19世紀80年代已被關注,彼時是運用于電視系統的標準化生產,大量的模塊化和可復制性成了傳統媒體的特征,新媒體則強調的是個體性,非大規模的標準化生產。所以,新媒體是基于創新而產生和發展的,其新在于多變,而其多變性是由數值編碼和媒體對象的模塊化結構所帶來的結果。也正是這種多邊性造成新媒體對象產生大量不同的版本,而非復刻本,這些版本在某種程度上是由計算機基于新媒體的模塊化自動組合而成,數字化的存儲將個體元素進行保存并在程序控制下進行各種排列組合,亦可分解成許多離散的樣本,并在需要時進行重新組合。如果將這種法則運用到文化上,將意味著賦予文化產品獨特性,每一個選擇都具有永久的開放性,其內容、細節、顏色、節奏等維度都可成為變量,用戶可自由修改和重組實現創新[25](p36-44)。
媒介融合是鄉村文化振興的關鍵,編碼排版與資源創新則是其手段。媒介融合需要關注內容編排的創新和媒介資源的創新。創新基于傳統,而文化亦非一成不變,如何在人們習以為常的鄉村文化生活中抓住文化的內核,才是創新的關鍵,這就需要對傳統媒介進行反思,在形式上創造出新意。資源是媒介企業的根本,媒介資源指的是能夠自由支配并利用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技術等資源形式的集合,媒介產業與旅游業、農業不同,它更依賴的是社會資源,依靠新技術、人才和創意。因此,創新是其生命,一旦創新缺失,媒介企業也就不可能再繼續發展,隨著技術的更新與人們對信息需求的增長,當下的媒介資源創新不再滿足于對原有資源的創新應用,更體現在對全新媒介資源的開發上[26](p114)。
(四)數字文化化與文化數字化
媒介融合是應對鄉村文化持續變異和相對穩定的關鍵,數字文化化與文化數字化則是其手段。文化數字化指傳統文化以數字化的形式表現,數字文化化則是“從IP 到IP”的產業鏈以數字的形式進行創作,比如地戲的數字化是傳統文化的數字化,但地戲人偶以及漫畫的數字化是數字化文化。簡單來說,數字化的文化產業依托于網絡,根植于技術,發展于創意,其指向是文化的消費市場。本質上,沒有文化的消費市場就沒有文化的數字化。傳統文化的數字化就是一個過程,傳統文化的任何東西都可以存儲成數字化的東西,這本質上是資料形態的改變,這種改變意義更多在于保存和傳承,而忽略了發展。所以,在說媒介傳播的時候要強調平面化的互動,轉向立體化的交融。一對一、一對多的單向傳播模式轉向為多對一、多對多的互動,以及多場景互動。
數字化復原和再現技術為文化的保存和傳承提供了保障,其快速生成的情景實現了文化的虛擬再現,使人們能夠在足不出戶的情況下逼真體驗和了解各種文化,激發文化活力,達到文化傳播的目的。通過數字技術,接受者不再局限于傳播者的個人體驗,而是以一種全知視角的形式去觀察和體悟,甚至在這些畫面中可以觀察到更為細微的細節和變化,強烈的參與感與真實感增強了觀眾的共情能力,觀眾對真實的體驗范圍已然從外在真實延伸到了內在真實[27](p61-66)。
數字技術帶來的感官刺激和體驗享受促使技術的快速更新,但在消費者滿足于技術帶來的好處時,也應該看到并思考媒介傳播無界可能會帶來的危害,比如為了博眼球獲取流量,制作一些比較低俗的視頻進行傳播。具體來講,數字技術帶來的融合和跨界促進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容易使人忘記了媒介的道德和文化使命,在“流量為王”“經濟為王”的利益主導下,道德倫理應當成為媒介傳播的安全閥,在人人都是傳播者的時代,要更加重視傳播者的意識形態問題。無論媒介如何跨界與融合,必須阻止對社會倫理、正義和善良的消解,將媒介傳播置于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中,才能保證其可持續、健康地發展。
五、余論
數字技術變革升級、知識產權意識增強、網絡支付習慣養成等引發了鄉村文化建設從內容到結構的系統性變化。理解示現媒介系統、再現媒介系統及機器媒介系統的互動關系,汲取不同媒介系統的優勢,規避不同媒介系統的局限,是鄉村文化建設需要關注的。特別是鄉村文化建設越發嵌合經濟社會發展,圍繞鄉村文化建設的IP 矩陣在產業鏈上愈發靠前,媒介融合成為助推鄉村文化建設、鄉村文化繁榮、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手段,理應成為鄉村文化建設的新引擎和新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