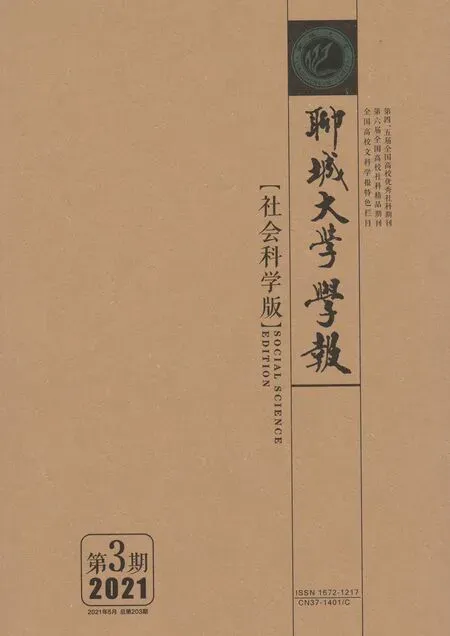20世紀90年代小說中的婚姻倫理敘事
宋 雯
(五邑大學 文學院,廣東 江門 529020)
中國小說中的婚姻倫理敘事,是從五四開始才漸漸增多的。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和“人”的發(fā)現,讓知識分子們看到了腐朽封建制度和家族制度的相通之處,因此家庭生活開始成為這一時期小說家們的重點審視對象,以往被作家們忽視的婚姻生活也開始成為主要的敘事對象。
在封建社會,進入婚姻的女子往往被視為“傳宗接代”,打理家務的工具,地位低下。現代文學時期的很多小說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對女性的迫害。此外,現代文學時期還出現了一批書寫“新女性”婚姻悲劇的小說,它們的敘事模式多為沖破家庭阻力,自由戀愛——進入婚姻,美好幻滅。這體現了作家對封建制度和婚姻的深層次思考,是否推翻了封建婚姻制度,擁有了自由戀愛的權利,就一定可以擁有美滿的婚姻生活呢?五四時期的作家給出的答案多是否定的,美好幻滅的結局反映了作家們的悲觀態(tài)度,也反映出這一時期有關婚姻的思考局限。
“十七年”時期的到來中斷了作家們對婚姻倫理敘事更深層次的探索。因為這個時期,政治革命話語取代啟蒙話語成了文學主流,小說中的婚姻倫理敘事也被賦予了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色彩,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現代文學作品所沒有的“女強男弱”的模式,夫妻關系也都類似于革命同志的關系,婚姻倫理敘事中私人性的一面被完全摒棄。
經過了個人空間被公共空間極度擠壓,政治意識形態(tài)統(tǒng)領一切的年代,有關婚姻生活的書寫在新時期才重歸大眾視野。這一時期的人們剛從文革中走出,面對舊價值秩序崩潰,同心圓式的社會結構碎裂的現實,人們急需建立新的價值秩序,撫慰內心的創(chuàng)傷。這個新的價值秩序包括傳統(tǒng)性別規(guī)范的回歸,因此在這一時期,傳統(tǒng)的賢妻良母型女性又大量出現在作家筆下。不過,新時期小說中的婚姻倫理敘事強調的最多的,還是愛情及兩情相悅的重要性。因為愛情是人道主義話語的良好載體,而人道主義話語正是新時期的主流話語。戴錦華曾評價寫于這個時期的《天云山傳奇》(魯彥周):“這是一篇典型的‘倫理小說’,作者的旨趣不在控訴‘文革’對人性的戕害,而在于歌頌一個為了愛情放棄一生的物質享受和政治生命,至死不悔的女人。”①戴錦華:《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6頁。
此外,新時期小說中顯現得較多的還有職業(yè)女性的婚姻困境。這種女性在十七年時期被稱為“鐵姑娘”,那個時期的小說對她們大加贊賞,她們的婚姻生活雖然沒被具體展示出來,但總體來說都比較幸福,因為社會地位的提高也無形中提高了她們的家庭地位,至于家庭生活和事業(yè)的沖突她們也不必擔心,因為遍地開花的互助組和合作社減輕了她們在養(yǎng)育兒女和打理家務上的負擔。而到了新時期,人們對虛假政治口號和“鐵姑娘”式的人物形象已經感到厭倦,職業(yè)女性家庭事業(yè)雙肩挑的困境就被真實呈現出來。
總體而言,新時期以婚姻和夫妻關系為主題的小說數量猛增,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作家們對于婚姻、愛情及夫妻關系有了更深層次的思考,不過,由于80年代的主流話語是以理想主義、人道主義及啟蒙話語為主,所以新時期小說中的婚姻倫理敘事還是承擔著過多的能指意義。
20世紀90年代的政治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比80年代更加寬松,商業(yè)大潮來襲,文學的地位逐漸從中心滑向邊緣,隨之滑落的,還有文科知識分子的啟蒙者身份和精英地位。這樣一個時期,經濟文化都在經歷著劇烈的轉型,小說中的婚姻倫理敘事又會發(fā)生一些怎樣的變化呢?
一、“過日子”與平凡之美
在以婚姻為題材或主題的20世紀90年代小說中,我們能看到大量有關婚姻日常瑣碎的描寫,此前雖然也有不少小說寫到了婚后生活,可是很少像90年代小說這樣,如此不厭其煩地描摹著婚姻生活中的一個個平凡場景。有學者認為,這類作品“似乎少有文化蘊含,都是日常生活的“一地雞毛”,但其實他們抓住普通人的生存境遇,關心他們如何去解決身邊一個個迎面撲來的矛盾和尷尬,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視角。”①汪政、曉華:《新寫實與小說的民族化》,《文藝研究》1993年第2期。
《太陽出世》(池莉)開篇就從趙勝天和李小蘭的婚禮寫起,重點描繪了他們的婚后生活。新婚不久的意外懷孕,讓這對小夫妻不知所措,因為養(yǎng)育小孩對于他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不過,兩人在經過思想掙扎后決定迎接這個挑戰(zhàn),小說著重展示的,就是這對小夫妻如何在生養(yǎng)孩子帶來的系列挑戰(zhàn)中,逐漸走向成熟,生孩子在這里具有了成人禮的象征。《紙婚年》(方方)中,維揚和如影的婚姻始于維揚對如影的一見鐘情,可是婚后,最初的新鮮感很快過去,原本你儂我儂的兩人常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爭吵。不過在生活過一段時間之后,他們卻發(fā)現,婚姻生活雖遠不如想象中的美好,卻能給人帶來安定的感覺,尤其在見識了朋友轟轟烈烈卻分分合合的戀愛之后,他們更加明白了平凡的可貴。從拒絕平凡到接受平凡,這是20世紀90年代婚姻題材小說的一個常見模式。
關于婚姻和愛情的關系探討,20世紀90年代小說也表現出不一樣的特質。在20世紀80年代的小說中,愛情作為人道主義的一個絕佳承載體,是超脫凡俗的詩性存在。因此80年代很多小說都表達了無愛婚姻的痛苦,認為“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是隨著商業(yè)大潮的來襲,實用主義、拜金主義在社會盛行開來,人們對婚姻和愛情的看法也發(fā)生了變化,如果說80年代小說中的婚姻倫理敘事普遍隱含著一種對此岸的排斥和對彼岸的憧憬,那么90年代很多小說中的婚姻倫理敘事則認可了此岸的庸常,認可了不夠浪漫卻充滿煙火氣的人生。在80年代的很多小說中,沒有愛情的婚姻是難以忍受的,無論是作者還是主人公似乎都堅信愛情的存在,而在90年代的很多小說中,婚姻里有沒有愛情并沒有那么重要,作家們對愛情是否存在也持懷疑態(tài)度,踏實“過日子”,似乎就是婚姻的全部,如《不談愛情》(池莉)中的莊建非和吉玲,雖是因自由戀愛走到一起,可他們之間并沒多少愛情可言,吉玲打算利用婚姻實現階層跨越,而莊建非結婚的原因竟是出于性欲。莊建非的知識分子父母對媳婦很不滿意,小兩口之間也小摩擦不斷,可是當吉玲在一次爭吵后賭氣回到娘家后,莊建非的生活陷入混亂,因為吉玲雖有時會使使小性子,可是總體來說還算賢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條,這種平凡卻實際的溫暖就像白開水,不能給人提供特別的驚喜,可是沒它又不行。此外,在中國的社會環(huán)境下,一個人社會形象的好壞與其婚姻狀況有很大關系,若是婚姻出現問題,這個人的社會形象就會大打折扣,莊建非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出國機會很可能因為離婚而被剝奪,因此一直瞧不上親家和媳婦的莊建非父母,為了兒子的前程,會放下身段去親家家里賠禮。婚姻的重要意義在這里顯現出來,它是一個供人休憩的港灣,也是個人形象的一個重要部分。那些事業(yè)有成的精明男性對此認識得很清楚,他們明白,只有平凡的過日子式婚姻才能提供給他們所需的安穩(wěn)和溫暖,因此在選擇妻子時,他們摒棄了愛情的因素,把賢惠、順從當成首要的擇偶標準,他們希望妻子能夠犧牲自己的追求,以他們的前途和事業(yè)為中心,所以我們看到,在《首席》(張欣)中,野心勃勃的江祖揚拒絕了兩位才貌雙全的優(yōu)秀女性的追求,選擇了一個極其平庸的妻子,“以安家事,為的是不受瑣碎之累專注于大事。”①張欣:《愛又如何,恨又如何》,西安:陜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第108頁。《紀念》(殷慧芬)中的狄仁,不但事業(yè)有成,在情場上也是春風得意,可擁有不少情人的他,妻子卻老實普通,對情人,他調情手段高超,對妻子,他也哄得很好,這不僅是因為婚姻出問題會影響仕途,還因為他的確需要一個讓他感到安穩(wěn)和放松的棲息地。在這些小說中,婚姻都具有很強的實用意義,愛情的缺失并沒讓婚姻中的雙方感到痛苦。從作家的平民立場以及他們在小說中流露出的敘事態(tài)度上,我們也能感受到他們對這種雖缺少愛情,卻踏實安穩(wěn)的婚姻狀態(tài)的認可。婚姻是秩序的一部分,婚姻的穩(wěn)定代表著秩序的穩(wěn)定,對安穩(wěn)婚姻的認可和贊賞,也是對秩序的禮贊。
二、“愛情神話”的建構與解構
20世紀90年代小說中的婚姻倫理敘事,大都從浪漫彼岸降落到了現實此岸,似乎大家都接受了這樣一個現實:婚姻,不過就是搭伙過日子。可是,依然有一些作家在凡庸的婚姻生活中努力找尋愛情的身影,他們似乎想要印證,愛情不一定都是驚世駭俗的,不一定只存在于詩意的彼岸,在煙火氣十足的此岸,在平常的一粥一飯中,同樣可以有愛情的存在。遲子建就是一個這樣的作家,《親親土豆》中,秦山和李愛杰這對勤勞的農民夫婦夫唱婦隨,把小日子過得有滋有味,可厄運突然到來:秦山患癌了。妻子并沒有退縮,而是要找“看病最好的醫(yī)院”給丈夫看病。秦山心疼妻子,找借口向妻子要了幾百塊錢,偷偷為妻子買了條漂亮旗袍,之后就獨自離開了醫(yī)院。過冬的時候,秦山把旗袍拿了出來,給了妻子一個意外的驚喜,“秦山說,‘明年夏天你穿上吧。’‘明年夏天——’李愛杰傷感地說,‘到時我穿給你看。’‘穿給別人看也是一樣的。’秦山說。”②遲子建:《親親土豆》,《遲子建小說》,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275頁。簡單樸素的幾句對話,卻蘊含了夫妻熾熱深厚的情感。《清水洗塵》中,夫妻間的故事都是在兒子天灶的眼睛中展開的,夫妻感情在兒童視角下顯得含蓄又有趣,村里有名的風流寡婦讓天灶父親幫忙去家里修理東西,天灶母親不樂意但又不好直接表現出來,直到丈夫很快回家后才放下心里的緊張,而她的緊張正來自于對丈夫的愛。作者在最后用含蓄的手法寫了天灶父親回家后和母親在洗澡桶里的恩愛場景,使得小說中洋溢著一種愛情的暖意。這些小說中的愛情都是構建在凡庸婚姻生活上的“愛情神話”,與那些轟轟烈烈的愛情相比,這樣的愛情顯得不夠浪漫詩意,卻自有一種溫暖妥帖,這些作品告訴我們,簡單平凡的日常生活,也是可以滋養(yǎng)著愛情的,就像不起眼的土地,也能開出美麗的花朵。
遲子建小說中的 “愛情神話”都建立在此岸的日常生活之上,平實安穩(wěn),充滿著煙火氣,而另一些作家,譬如北村,則固執(zhí)地堅持“愛情神話”只存在于浪漫的彼岸,認為真正的愛情是天塌地陷,轟轟烈烈的,與一地雞毛的瑣碎日常毫不相關。不過這樣的“愛情”因為太過理想化而顯得脆弱不堪,它只適合生長在純凈的彼岸,一旦被移植到現實此岸,它就會像水土不服的嬌艷花朵一樣迅速枯萎。《周漁的火車》中,美人周漁和電工陳清的愛在物欲橫流的社會顯得超凡脫俗。在這個美女們紛紛想著嫁大款的年代,周漁卻義無反顧地愛著資質平平的普通電工。這種超越功利的愛是生長在彼岸的“愛情神話”,比80年代小說中的愛情都顯得更純粹。80年代小說中的人們可能在相愛和結婚的時候不看重金錢和名利,但是崇高的人格和優(yōu)秀的品質仍是他們所注重的,而周漁對陳清的愛似乎沒有任何理由。與那種婚前愛得死去活來婚后就激情褪去的婚姻不同,周漁和陳清在婚后依然延續(xù)了他們的愛情。陳清意外身亡之后,周漁仿佛也跟著死去了,如果不是陳清的情人李蘭意外浮出水面,陳清和周漁的“愛情神話”恐怕會永垂不朽了。可是隨著李蘭的出現,陳清的另一面被揭開,我們發(fā)現陳清和周漁的愛情并沒有看上去那么美好,李蘭一語道破天機:“那種看起來非常偉大的愛情是經不起輕輕一碰的。”①北村:《周漁的火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58頁。《瑪卓的愛情》中,班花瑪卓之所以選擇其貌不揚的劉仁,正是因為劉仁的浪漫。劉仁曾在三年間給瑪卓寫了一千多封情書,并在一個下午,坐在山上,把情書一封封讀給瑪卓聽,這成了他們愛情的開始,也成了他們一生中最寶貴的記憶。可是,當他們修成正果走進婚姻后,他們卻發(fā)現兩人的關系變得尷尬,從婚后第一夜起就變得無話可說,婚姻生活中的做飯、買菜等日常事務好像對浪漫愛情構成了巨大的破壞,那個坐在山上讀情書聽情話的美好下午再也回不來了。正如劉仁對兩人婚姻的分析:“我們仿佛是兩個只適合于在山上過愛情生活而不適于在房間里過婚姻生活的人”。瑪卓也對二人關系做了反思:“他的信一停止,我們的新婚之夜立刻出問題,看來,我們是無力生活的人,我們生活在紙上,生活在猜想中更合適一些。”②北村:《周漁的火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103頁。作家在這些小說中思索了這樣一個問題,不受世俗污染的浪漫愛情,究竟真實存在,還是人們心中的美好幻象?從故事的發(fā)展和結局來看,作者顯然更傾向于后一種解釋。
與上述小說相比,20世紀90年代一些小說中的“愛情神話”被摧毀的原因顯得更加具體,這與90年代文學更加注重和現實的對話有關。90年代的中國,經濟飛速發(fā)展,物欲泛濫,拜金主義盛行,那些擁有愛情基礎但缺乏物質基礎的婚姻,在這樣的社會顯得不合時宜,曾經海誓山盟的愛情,在實實在在的物質面前,脆弱得不堪一擊。《冬至》(張欣)中的“小米”和“大胡子”情投意合,他們的婚姻有著深厚的感情基礎。兩人原本都是超凡脫俗的理想主義者,信奉“愛大過天”,可是貧困使得兩人的婚姻生活落魄狼狽,“小米”也不再相信“有愛就有一切了”,因為窘迫的經濟狀況讓他們無法維持一種有尊嚴的生活,因此這個曾經愛情至上的“小米”真誠告誡自己的女性朋友:“有錢會出現兩種情況,幸福或者不幸福,沒錢就只有一種情況,不幸福。”③張欣:《張欣作品精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7年,第36頁。
在這節(jié)所列舉的小說中,只有遲子建構建的“愛情神話”延續(xù)到了最后,這或許源于作者對愛情的日常屬性的認可,而其他小說的作者就像一個玩積木的人,先是用五顏六色的積木搭起了一座輝煌巍峨的“愛情”城堡,然后再毫不留情地將其推倒。
三、各式各樣的“圍城”困境
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壇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自由倫理個體敘事”增多,與“看起來圍繞個人命運,實際讓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的“人民倫理大敘事”不同,“自由倫理個體敘事”“只是個體生命的嘆息或想象,是某一個人活過的生命痕跡或經歷的人生變故”。④劉小楓:《沉重的肉身——現代性倫理的敘事緯語》,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6頁。因此比起以往,20世紀90年代以婚姻為主題和題材的小說不僅數量頗豐,而且在敘事形式和敘事內容上也顯得更加多元,我們從中可以窺見各式各樣的“圍城”困境。
(一)“皮格馬利翁”與理想伴侶的塑造
《逐鹿中街》中的英語教師陳傳青,38歲才經人介紹和喪偶的市建局干部古子銘結了婚,在外人眼中,陳傳青賢惠能干,她把房間收拾得窗明幾凈,丈夫的穿著打扮也在她的精心設計下越來越有風度。最初,古子銘對這樣的日子很是享受,可慢慢他就感到了不對勁,因為妻子似乎把婚姻做成了一個光鮮的模子,他的一切都要與這個模子吻合才行。他有種被控制的感覺,開始有意識地反抗,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樣,到點就回家,寧可和單位里的小姑娘呆在一起互訴衷腸。控制欲旺盛卻仍想保持自己賢妻形象的陳傳青和覺醒了的古子銘開始了一場“逐鹿中街”的好戲,陳傳青的跟蹤和古子銘的反跟蹤好像變成了一個夫妻間心照不宣的游戲。從歲月靜好到風聲鶴唳,這場婚姻的最大問題,在于陳傳青過于想把古子銘塑造成她心目中的理想伴侶,可是她忘了,丈夫不是一個任由她雕塑的泥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大活人。
《周漁的火車》(北村)中的陳清也是一個外人眼中的模范丈夫,雖然相貌和能力都平平,可是深愛周漁。周漁也知道陳清不夠出色,但對于把愛情看得重于生命的她來說,有情飲水飽。周漁習慣了陳清對自己的愛和付出,要求陳清按她的方式好好愛她,做個她心目中的理想丈夫。陳清出軌李蘭,實際是他對周漁一直要求他扮演的理想伴侶角色的厭倦和反抗,就像他對李蘭吐露的:“光靠我一個人是做不成好丈夫的,是周漁使我這樣的,是她把我塑造成這樣。”①北村:《周漁的火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57頁。他之所以跟李蘭在一起,是因為他可以卸下沉重的“理想丈夫”假面,享受做回真實自我的感覺。
《逐鹿中街》中的陳傳青和《周漁的火車》中的周漁實際上都在不經意間充當了希臘神話中的“皮格馬利翁”,她們對丈夫的想法和喜好毫不關心,只想把丈夫塑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樣。由于一直活在妻子的塑造和期待中,一直活在模范丈夫的面具之下,丈夫的“原始自我”被深深壓抑,這必然會導致最終的反抗。
(二)平波水面,波瀾深藏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中國從一個“熟人社會”慢慢轉變成一個“陌生人社會”,人們的婚戀行為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在過去的“熟人社會”,婚戀雙方大都互相知根知底,而隨著“陌生人社會”的到來,人們對自己的婚戀對象可能了解并不多,周邊同事的撮合或一次意外的邂逅,就能匆匆促成一段婚姻,他們結婚可能不是因為愛情,而是為了符合世俗的期待,他們往往善于掩飾自己的情感和好惡,就算真實的婚姻狀況千瘡百孔,也要維持光鮮亮麗的表面。
《云破處》(池莉)里的金祥和曾善美,是一對公認的模范夫妻,在同一家單位工作,在外人眼中,他們琴瑟和鳴,就像“一列安全行駛了十好幾年的老火車。總是在同一個時間開動,”②池莉:《云破處》,《花城》1997年第1期。可是命運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曾善美意外發(fā)現金祥是多年前毒死自己父母的兇手,籠罩在他們婚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隨之揭下,兩人多年來積壓的對對方的不滿像沉寂多年的火山一樣爆發(fā)了出來,可是到了白天,他們依舊一起上班,一起在外人面前扮演著模范夫妻的形象。
《藤之舞》(黃蓓佳)中的陳兆華從表面上看,是一個富有奉獻精神的能干賢妻,她幫汪齊云從一個小資料員一步步轉變?yōu)橐粋€受人尊敬的副教授,“文革”期間她也不畏艱辛陪丈夫下放,并主動承擔了大部分體力活,可是這種從一開始就不平等的“女強男弱”式婚姻讓思想傳統(tǒng)的汪齊云倍感壓抑。他們回城后,汪齊云成了風度翩翩的大學教授,陳兆華卻風光不再,并因操勞過度成了一個外形粗糙的黃臉婆,兩人在婚姻中的地位顛倒了過來,汪齊云開始反抗妻子對自己命運的操控,在柔弱女子李小娟身上找到了作為強者的自信,開始了他的“第二春”,與此同時,他和妻子開始暗藏機鋒互相攻擊,兒子一語中的:“你們是兩根糾纏在一起的藤,彼此盤繞,又彼此依附,彼此仇恨,卻彼此從對方吸精吮汁。”①黃蓓佳:《藤之舞》,《鐘山》1992年第3期。汪齊云和陳兆華的婚姻,在外人眼中可能幸福美滿,因為他們患難與共,妻子沒嫌棄丈夫比自己出身低微,還一直盡心盡力幫助丈夫,而丈夫發(fā)達后也沒把這個“糟糠妻”休掉。可是在表面的風平浪靜下,卻積蓄著丈夫多年來的不滿和怨恨。
《云破處》和《藤之舞》中的婚姻告訴我們,風平浪靜或許只是表面現象,不管下面暗流如何劇烈翻涌,作為岸邊人的我們都不得而知。很多人為了符合世俗的期待,紛紛戴上面具扮演模范夫妻,甚至在家里,獨自面對伴侶的時候也不摘下來,可是一直被壓抑著的不滿和矛盾都在雙方心里越積越深,一旦達到極限,定會像火山一樣爆發(fā)。但是他們的爆發(fā)也有可能是悄無聲息的,因為他們習慣了偽裝和掩飾,再痛苦,也不想讓外人看到他們千瘡百孔的婚姻現實。
(三)欲望的壓抑
在經濟不夠發(fā)達的從前,人們普遍把生活視作人生的目的,把賺錢視作手段,而物質充裕的現代社會卻將之顛倒了過來,工具理性戰(zhàn)勝了人文理性,人們的生命力也在無形中被“閹割”了。如果婚姻中有一方是這樣的人,而另一方依然保有生命活力,那么這樣的婚姻注定不幸福。《雙魚星座》(徐小斌)中卜零和韋的婚姻就是如此。卜零是個富有浪漫氣息的女子,和這個充滿商業(yè)氣息的世俗社會顯得格格不入。丈夫韋在有錢有權之后,就越來越厭煩這個仿佛不食人間煙火的妻子,比起夫妻間的精神交流,他覺得跟歡場女子直截了當的交換更加輕松。卜零處境很尷尬,在外人眼中,她是養(yǎng)尊處優(yōu)的闊太,可在家里,她不但沒有掌握經濟大權,還伺候男權思想嚴重的丈夫。小說特意寫到韋性欲貧弱,沒有生育能力,他在家經常做的不過是看看電視,這其實象征了韋的生命力被閹割。面對這樣的丈夫,生命力旺盛的卜零是痛苦的。小說細致描繪了卜零的性心理及被壓抑的情欲,她之所以會對年輕帥氣的司機動心,出現殺夫的幻覺,都是情欲被極端壓抑的表現。
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婚姻題材小說中,作者多借婚姻傳達自己對社會問題的思考,對于婚姻中“性”的問題卻多避而不談。而隨著90年代逐漸寬松的社會環(huán)境和文學環(huán)境,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思考“性”與婚姻的關系。對于現代人來說,婚姻中的“性”絕不僅是一個傳宗接代的手段,它關系著夫妻關系的和諧與否,關系著人的正常欲望是否得到合理釋放。不過,一些人已習慣了壓抑自己的本能欲望,他們的婚姻也因此受到影響。《桑煙為誰升起》(蔣子丹)中的蕭芒深愛丈夫寧羽,可他們在性事方面并不和諧。因為蕭芒幼年喪母,沒人對她預先進行婚前性教育,少女時期的朋友小賴的那些給她留下骯臟印象的描述,便成為蕭芒對這類生活的全部認識。這導致在做愛的時候,她總是帶著一種難言的犯罪感。她“習慣了在黑暗的掩護下恪盡妻子的義務,除此之外她幾乎從來沒有沉醉其中。她只是靜靜地躺著,聽任丈夫動作。”②蔣子丹:《桑煙為誰升起》,《收獲》1994第1期。這樣的性生活完全不能滿足血氣方剛,對“性”充滿熱情的寧羽,這正是他在外面找情人的緣由。可以說,“性”的不和諧是破壞他們婚姻的最重要原因,而這又是由蕭芒對自己本能欲望的極度壓抑所引起。小說清晰呈現了蕭芒是如何一步步壓抑自己的欲望,被傳統(tǒng)性別規(guī)范的。她一直想維護自己的純潔好女孩形象,殊不知這樣的形象實際上是她的“偽自我”,她的“原始自我”已被壓抑到她自己都看不到的地方。
(四)為自己畫地為牢
隨著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傳入,20世紀90年代的作家們對“女性解放”這個問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中國的“女性解放”歷來都不太徹底,“它始終與超越性別的民族、階級的革命實踐相伴生,”③楊永明:《女性解放的社會怪圈》,《海南師范大學》2006年第3期。雖然新中國成立之后,女性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可很多女性的主體意識還沒有真正覺醒,她們不但認可男權社會的性別規(guī)范,還把這些加諸在她們身上的規(guī)范都視為內心的道德律令。如《殺人》(萬方)中的鄉(xiāng)下女子六團,在父母做主下稀里糊涂成了親,成親后,丈夫很快回城打工去了,把六團留在鄉(xiāng)下伺候自己的母親。六團黑天白夜小心服侍婆婆,認為這是媳婦的本分;懷上的孩子不小心掉了,則把一切責任都歸到自己頭上,更加忘我地為這個家干活。丈夫鞠生從來都沒有愛過六團,可是當他向六團提出離婚,六團卻堅決不肯。因為世俗道德、輿論和娘家人都不允許她這么做。來自她身邊的聲音都是這樣的:“這方圓百里的誰不知道老鞠家的六團,活得多有名分。”“就是死,你也要死在鞠家。”①萬方:《萬方文學作品選》,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年,第141頁。在這樣的聲音下,“六團”像個狂熱教徒一樣,將封建禮教視為最高信仰來捍衛(wèi),她認定,活著或死都要當鞠生的媳婦。雖然她的婚姻早已有名無實,可為了一個“正室”的名分,她寧愿守活寡也堅決不同意離婚。六團對名分的執(zhí)著,害了自己的一生,也害了丈夫的一生。
都市女性同樣面臨著女性意識尚未覺醒這個問題。如《冬至》(張欣)中的葉冰琦是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一個白領,可是她的思想和那些舊式女子并沒有太大區(qū)別,她認為女人最重要的價值就是青春和美貌,最重要的人生目標就是結婚生子,雖然她婚前就明白未婚夫是個愛流連花叢的花花公子,但她還是義無反顧和他結了婚,一是因為她依賴性強,認為婚姻可以滿足她的物質需求和情感需求;二是因為她把世俗輿論看得無比重要,認為沒有婚姻會讓別人看不起。婚后的她溫柔賢惠,卻被花心的丈夫嫌棄不夠野性,她的第一次婚姻就這樣以失敗告終,可是她并沒有醒悟,又匆匆嫁給一個有錢的香港老男人,卻沒想到他在香港還有家。在小說最后,當葉冰琦的另外兩個女性好友再次見到她時,她已不復當年風采,表面的風光下是無盡的辛酸。
上述小說中的婚姻悲劇都是因女性把男權文化規(guī)范內化為自己內心的道德律令甚至信仰而引起,她們缺少的不是外在的自由,而是內在的自由,因此她們在婚姻里給自己畫地為牢,是那些把籠子打開,也不肯飛出去的鳥兒。這些小說深刻表明,若女性的主體意識不覺醒,“女性解放”永遠也不可能徹底。
文學和時代從來都密不可分,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催生出不斷繁榮的大眾文化與都市文化時,世俗意識開始走進歷史舞臺”,②梁鴻:《重回語文學——地方、空間、詞語與當代文學》,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106頁。以市民為主體的“個人生活”已經不再是某種“被遮蔽的空間”,因此我們看到,20世紀90年代小說中的婚姻倫理敘事擺脫了意識形態(tài)重負,以往小說中被忽略或一筆帶過的日常瑣碎和各類婚姻困境被放大凸顯了出來。這些作品沒有負載過多的能指意義,卻充滿了對平民真實生活的人文關懷,具有很強的現實指涉性,折射出時代的變遷和社會心態(tài)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