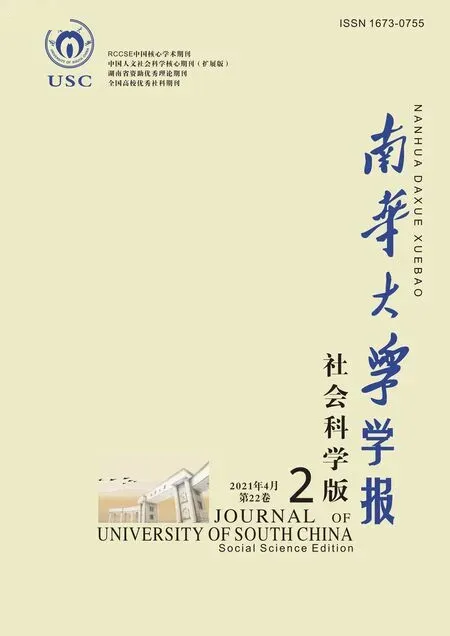律法焦慮與政體健康:體液理論中的莎士比亞問題劇《一報還一報》
陶久勝,郭夢娜
(寧波大學 外國語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外研社英文主編喬納森·貝特在給《一報還一報》撰寫導言時指出,這部莎士比亞的問題劇被記載的首次演出是1604年12月26日,英國新君詹姆士的圣誕慶典之上,“盡管劇中的公爵并非喻指詹姆士”,但其中關于神學和道德爭論,對權力隱秘源泉的探尋都映射了當時英王詹姆士在國會和教會關于律法問題探討的論辯中的態度[1]4-5。一直以來學界都十分關注劇中的法律與道德的問題,一些批評家從公爵文森修的角色扮演角度闡釋一個社會體系中恢復司法的重要性[2],也有學者從法律與宗教的關系出發,研究詹姆士一世對待清教主義的立法提議所采取的政策[3],喬納森·戈森則研究了其中的政治神學,探討基督教思想是如何與當時的法律相互滲透結合以達到服務于社會治理之功效[4],但實際上古典醫學的動態體液平衡理論與政體和人體的大小宇宙類比關系已經成為早期現代英國社會暗指和理解國家法律和政體健康的有效途徑[5]。因此,本文擬從古典醫學體液理論角度出發解讀劇中的維也納城邦的性欲糜爛所導致的社會秩序失衡和法律名存實亡的現象。首先,根據體液理論闡述劇中維也納市民和“暴政”的執法者安吉魯“體液過剩”的狀況。其次,分析法律在劇中的政體健康隱喻、執法者對法紀的陽奉陰違和公爵文森修利用“政治方面的種種機宜”[6]262撥亂反正最終恢復國家政體健康。最后,解析莎士比亞在劇中表達的對英國法律現狀的憂慮和對英王詹姆士能否激發法律的“克制”作用,恢復英國政體健康的焦慮,并解讀法律在其中作為“不過我們的刀刃雖然銳利,/用起來卻要小心,/不可大砍大殺,/要人性命。”(彭譯,II.i.5-7)①之中所隱含的道德層面的因素。
一 古典體液理論與疾病化的維也納
文藝復興時期醫生數量非常少,人們需要自我醫治,因此當時的戲劇中總是以醫學術語來呈現人物,所以當時的醫學話語已經不是一個專業術語而是作為一個通用語言存在[7],而莎士比亞的戲劇《一報還一報》中就涉及了一系列明說暗指的醫學話語,如醫學上常用于治療梅毒的“發汗”之法與雙關語“法國絲絨”(法國病暗指梅毒[1]14)和“骨頭都空了”(骨頭脆是梅毒晚期的癥狀[1]15)等詞對性病侵染后果的暗喻,這些醫學話語的使用一方面說明了市民荒淫縱欲以致患病的狀態,另一方面映射了維也納國度的健康隱患。
在劇中,公爵文森修指出,由于他“放縱人民”(彭譯,I.iii.38),整個城邦充斥著“年輕人如火的熱情”(彭譯,I.iii.5),維也納的“禮儀法紀都蕩然無存”(彭譯,I.iii.32),但是“若因為他們干出我默許的行為,/勢已難改,/再去騷擾打擊他們,/我就成了暴君。”(彭譯,I.iii.39-41)當時的維也納公民因為色情商業的高度發展和律法多年束之高閣,早已無法自制,導致整個國家法紀陷入一種“癱瘓”狀態。公爵將維也納法紀和秩序崩壞的現狀與城內年輕人體內的“情熱”聯系在一起,實際上是暗指由于“體液過剩”引發的過旺情欲而導致個人身體健康受到影響,進而影響整個社會法紀的健康且危及國家政體健康。實際上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將自己視為一種包含著各種液體和蒸汽的海綿式的容器,人體內部的不平衡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造就了他們的情緒和性格,且兩者處于永恒的流動之中,而這個思想又是建立在古典體液理論之上的[6]。因此,當這種縱欲心態由個人身體的體液不平衡中產生、擴散并與外在環境進行交換時,必將危害政體健康最終使整個國家陷入疾病狀態。
由古希臘著名醫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Cos)提出的“體液學說”對早期現代醫學的影響巨大,而由伽林醫生提出的“體液平衡學說”是其重要的醫學理論之一[8]62。盡管后來證明了有其他體液的存在,但在16世紀時,只有四種體液的觀念已經成為真理般的存在[9]136。莎士比亞的戲劇特別是復仇劇就經常涉及體液與醫學相關的術語,喜劇與問題劇中也不少。而根據希波克拉底的“體液學說”,人體內有四種體液:膽液質、血液質、粘液質和黑膽質,它們之間的平衡是相對的。而當其中一種體液占據主體地位時,身體和心理傾向就會受到影響,從而使身體產生病態:異常膽液質、異常血液質、異常粘液質和異常黑膽質[9]38。維也納城中泛濫的性欲和善熱就是由于膽液質占據體液主導地位引起的,而這種體液不平衡就會外化為個人的一種病態。第一幕中,路西奧和兩位紳士的對話中就提及疾病與性欲的相關話語。路西奧是城中的紈绔子弟,與女主人公的弟弟私交甚篤,“他就把凱特·吉普東小姐弄大了肚子,/答應要娶她。/到今年五月一日,/那孩子就該有一歲零三個月了”(彭譯,III.i.428-430),并且反過來到處說幫助他養孩子的老鴇歐弗東太太的壞話,如果說莎士比亞將整個維也納視作一個自然身體,那么路西奧的存在就是導致國家內的疾病傳染的“病毒”即過剩的體液。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可是芒刺,/粘住就不放”(彭譯,IIII.iii.164-165),而芒刺除了有“草木莖葉、果殼上的小刺”之義,還可以引申為“隱患”的含義,此外,舌生芒刺也和縱欲一樣,在中醫看來這是熱毒內伏,心肺火盛所致。由此可見,如路西奧這般患有“體液過剩”之病的市民就是危害維也納政體健康的“芒刺”,是國家疾病的內熱來源。
四種體液決定著人的思維方式,而喬瑟琳也曾將自己的尿液形容成含有“過多的白色的粘液”以此說明自己體內充滿了“冰冷的水質的體液”。根據伽林醫學理論,粘液質包含冰和水的特質:寒冷和潮濕[9]136。這就與路西奧對攝政王安吉魯的指控相互映證。路西奧借用體液修辭來說明攝政王安吉魯行事嚴苛不講情面的性格,他宣稱安吉魯“撒尿的時候,/尿出來的都是冰。”(彭譯,III.i.354-355)連德高望重的大臣愛斯卡勒斯也認為安吉魯是一個“一絲不茍”“嚴謹”的人。他能結冰的尿和冰冷的血液足以說明此人的性格沉穩,不近人情,根據體液理論,當粘液質在體內占據主導地位時,自然身體與思想便受其影響,進而表現出性子沉靜,身體濕寒的狀態,顯然他體內的血液質都已經受其影響失去了原本的活力。但這違反了伽林的體液平衡學說,顯然攝政王安吉魯體內的另一種體液過剩,才使安吉魯呈現一種“嚴謹”的狀態,但是“嚴謹”一詞原本就是與偽善的清教徒連接起來的[1]2。由此可見,代理執政者安吉魯本身就是國家另一類疾病的存在。而當安吉魯見到伊莎貝拉之后,他也感染了城市中的熱病,萌生了玷污這個即將成為修女的求情者的想法并在之后付諸行動。“實際上,古典醫學的體液理論是一套涉及人體、政體和天體的病理理論和修辭話語......和諧與完美為至高狀態。然而,當這種秩序被打破時,紊亂和疾病就占主導。”[10]當這種熱病傳染到攝政王的身上時,必然感染到他所代表的法律的健康即政體健康,從而使維也納陷入疾病狀態,而劇中的公爵從一開始就通過各種政治和宗教手段想方設法使維也納恢復到法治狀態之下,并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二 法律的政體健康隱喻和公爵的“凈化”之法
柯爾律治曾經給予了《一報還一報》極高的評價,將它視作“莎翁劇作之大成”,因其所包含的話語之廣、內容之復雜和詮釋的多義性。正因如此,我們才得以在古典醫學理論的框架下闡述,而維也納的社會弊端既然已經顯現出來,那么統治者公爵文森修便用道德責任去遏制這種風氣的滋長,作為劇中的“操刀”者,必須給社會“放血”以達到恢復城邦體液平衡的目的。
早期現代醫學還有一種觀點,疾病的起因不僅僅是由身體內部的體液不平衡造成的,外部污染也會導致身體內部健康的體液受到污染,使體液呈現病態或者直接感染健康的體液[9]38-39;136-137。英格拉西也指出,“傳染病蔓延的真正原因”是健康人和被感染者的混合體[11]291。劇中紈绔公子路西奧曾稱自己在老鴇歐弗東太太家“買了不少病”(彭譯,I.ii.41),也說過“以后我總要挑頭向你敬酒,/以免落在你后邊,/染上臟病。”(彭譯,I.ii.26)與體液話語相映襯,此處的敬酒行為映射了外部污染源梅毒的傳染性,為了防止梅毒從他人身體傳染給自己,因此要先給對方敬酒避免患病。和路西奧一樣,劇中因犯通奸罪而要被處死的克勞迪奧也曾形容自己為“馬刺”(彭譯,I.iii.139),認為安吉魯將“城邦大權當做胯下之馬”(彭譯,I.ii.137),又在后面提及嚴刑峻法就是攝政王所謂的“城邦大權”。可以從上述言論中看出,身為“馬刺”的他和路西奧危害的是法律健康,而內部“體液過剩”也正是相當于他們身體健康的“芒刺”,最終致使他們和城邦都感染熱病。此外,路西奧與另外兩位紳士言談之間便隨意地抹去了“十誡”中的一誡“汝勿偷盜”(彭譯,I.ii.10),這也就說明了以他為中心的這一群人對于國家法律的不尊重。他們所產生的罪惡最終都影響到了個人和社會的健康,但普通法能夠讓每一件事各歸其位,找到其最適宜的位置[12]。如果將法律做身體化處理,那么它在劇中隱喻的就是一個國家政治身體的健康。
戈森指出,17世紀的新教神學強調將神圣性從教會教庭轉移到國家身上,因此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是否道德高尚就顯得十分重要[4]。劇中的兩個擁有執法權的人都被不同的人指控“殘暴”“暴政”“發瘋”或“瘋頭瘋腦”,原本“嚴刑峻法”的嚴格執行者安吉魯因受魔鬼的誘惑而墜下了“城邦大權”之馬,自恃德高望重的公爵也被自己的臣子當做“瘋了”,由此可見,他們在公民的眼中也是疾病化的,一定程度上德行有虧。而即使部分言論是來自他人的惡意詆毀,劇中各處無不在暗示著國家司法體系中存在安全隱患。考克斯也指出,盡管公爵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無法凈化整座城市的精神污染[13]。但公爵利用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權謀先是以安吉魯的嚴法維護了國家政體健康,又以國教“公開懺悔”的形式根除國家的痼疾,使律法恢復健康狀態,這一舉措也暗含了詹姆士一世對通奸罪所采取的政策[3]。
馬基雅維利《君主論》關于政治統治強調:“人只有在強制下才會向善;如果人能為所欲為,秩序必將蕩然無存。”[12]劇中公爵文森修也發表過相同的觀點,“淫亂之刑太過泛濫,/必須嚴厲糾正。”(彭譯,III.i.346)也就是說,城中的法紀崩壞,道德風尚受損必須讓國家重新恢復到法治狀態之下,才能夠讓政體恢復健康,修復蕩然無存的秩序。早期醫學的治療方法基于對抗療法的基礎之上,即熱病當配以寒性藥物[9]38。借由愛斯卡勒斯對公爵的形容,市民們無法像他一般“淡泊克制”(temperance)導致維也納城中人“患上一種急于做好事的熱病,/非得把好事變壞,/這種病才能治好。”(彭譯,III.i.449)體液理論針對此類疾病的排解之法包括:放血、排便、發汗、嘔吐等[9]140。戲劇伊始,公爵便開始了對維也納的“凈化”。一方面他將國內實權暫時移交給安吉魯,啟動城中的法律以整頓風紀。但單論道德問題,安吉魯就不適合執法。其實公爵早已知道安吉魯拋棄過瑪利安娜,而這一點從公爵毫無猶疑地向伊莎貝拉提出“床上計”就可以看出,且他離開距事發不過一日,根本沒有時間去打聽這方面的事情,而且無論是論資歷還是論道德品格,德高望重的大臣愛斯卡勒斯都是更加合適的人選,那么“明知一個人是惡棍還要擢升他,其意自然不在于‘考驗’他了”[14]。公爵此時就是將他當成一個如劊子手一般的操刀者,關于這方面愛斯卡勒斯也曾提示過安吉魯操刀需謹慎行事,刀鋒足夠銳利,但不需致人性命,只需適當“放血”,實際上劊子手這個職業在早期現代英國算不得什么光彩的工作,無人愿意接手,一般都由囚犯“代理”[15]。而安吉魯在得到權力后立即在城中實行了嚴刑,使其居民“發汗的發汗,/有的上絞架”(彭譯,I.ii.72-73),并且判定克勞迪奧死罪。但是他本人卻也知法犯法,貪圖肉欲,面對大臣的勸誡時,他卻聲稱“你不能因為我有類似的毛病,/就減輕他的罪過。”(彭譯,II.i.27-28)但他卻以權謀私,認定即使伊莎貝拉說出事實真相也不會有人相信,置法律于腐敗之地。據此看來,公爵不過知曉安吉魯的冰冷性格與當時社會盛行的性欲正是對立面,利用了古典醫療中的對抗療法來讓安吉魯在城中實行了“發汗”之法,意在使維也納重歸法治健康狀態。另一方面,他暗地里偽裝成修士,聆聽罪人們的懺悔,使他們重獲健康。懺悔也是劇中的關鍵詞之一,具有宗教和法律的雙重含義。懺悔既是一種宗教儀式也是作為一種法律補充形式存在。伊麗莎白·福勒指出,早在13世紀,懺悔就正式地被當做是教會法庭司法權的一種外部補充之法,用以根據犯罪的嚴重程度的一種可選之途[16]21。懺悔是通過教會法庭,使人的靈魂獲得拯救,被視為一種個人再生之法[13]。類似于“發汗”的療效,犯罪的克勞迪奧和瑪利安娜還有安吉魯通過對“神父”公爵的公開懺悔獲得了新生,洗清了身上的罪惡恢復健康,并且在“神父”的主持之下,幾對新人雙雙成婚,使其原本不合法的關系重新走回了合法軌道。公爵既通過安吉魯震懾了市民,整肅了社會上的道德問題,又親自推翻了所謂的“暴政”,使用“懺悔”和“發汗”使維也納最后恢復到法治軌道之中。
三 對英王詹姆士一世的暗指和莎士比亞對新王統治的焦慮
劇中安吉魯曾下令“維也納郊區的窯子一律拆除”(彭譯,I.ii.78),以整治城中糜爛的風氣。婚姻之外的性行為是不合法的,但是由于過剩的體液驅使,家庭框架之內的性已經無法滿足泛濫的愛欲,而妓院作為一個魚龍混雜的地方,梅毒等性疾病是司空見慣又具有傳染性的,如劇中就曾提到妓院常備的零食“梅子”就是用來治療梅毒的,這足以看出梅毒在妓院的盛行狀況。通過性交行為,男女雙方發生接觸互相感染了病毒,又由各自的家庭向外擴散,最終致使整個城中道德問題橫生,社會陷入了無序狀態。塞繆爾和約翰指出,1575—1578年的瘟疫在造成社會混亂、暴動和法律失衡方面有著自己的“得天獨厚”的影響并且當初多個地區如佛羅倫薩、米蘭等都針對瘟疫的流行和如何處理流浪漢等制定了相關法律[11]265;286。而實際上在1603—1604年這段時間內,英國又爆發了一次黑死病,超過25000倫敦人死亡,倫敦劇院也因此于1603年3月18日關閉,直至1604年8月8日才重開[13]。該劇于1604年12月26日在宮中上演,與劇中的梅毒盛行話語相互映襯。希爾多也曾在他的小冊子中指出,這種骯臟的妓女與嫖客之間相互感染的疾病不僅可以通過躺在一起感染,而且可以通過呼吸和接觸感染[13]。且劇院與妓院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是人群聚集之地,是容易受到外界污染并由此滋生更多疾病的媒介場所,且劇院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不利于國家安全,是反叛與犯法行徑頻發的場所。雖然劇中的場景設置在維也納,也容易讓當時英國民眾聯想到意大利。《一報還一報》就是折射出詹姆士新政黑暗面的鏡子[13]。但從劇中的梅毒話語出發,觀眾不難聯想到早期現代英國瘟疫頻發的現狀并不自覺地將劇中的維也納想象為倫敦,而劇中所傳達的法律道德思想也不免化為大英帝國的道德理想。
在伊麗莎白后期,關于君王的政治統治等問題便不允許在劇院中再現,而莎士比亞的劇團在女王去世幾周后便被重新命名為“國王劇團”,從《一報還一報》中,我們不難發現其中關于英國和英王詹姆士的影射。劇中公爵所采用的宗教遏制政策與詹姆士對清教采取的政策一致,均是為了穩定國家大局[3]。而新教神學就是“尋找那些神圣的存在或可能被重建的地方”,它將神圣性從教會、其官員和它的圣禮轉移到國家,從而將后者的管轄權擴展到精神和個人領域[4]。無論這個神圣的領域是在統治者或者更廣泛的國家之中,統治者的道德責任意識就至關重要。而這一信仰鼓勵像詹姆士一世這樣的基督教保皇黨人,讓他的法院系統嘗試用教會的悔罪和恢復性方法來取代國家傳統的刑罰和懲罰性刑事司法,其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而是為了拯救個別罪犯的精神[4]。因此劇中公爵所采用的“公開懺悔”的懲治形式正符合莎士比亞時代英國的世俗法律,通奸等性道德問題通常是由英國教會也就是國教“交納罰金或者公開贖罪”來進行懲罰,這也符合詹姆士一世的政治理念[16]6。并且劇中公爵所采用的馬基雅維利式的君王政策和探索權力源泉的態度與現實中詹姆士一世所闡述的統治思想一致,公爵提出“我愛老百姓,/但不愿受萬眾矚目,/展現自己”(彭譯,I.i.72-73),詹姆士一世也不喜歡像伊麗莎白女王那樣“通過盛裝游行展示君主權威”[1]4。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斯通發現,十六、十七世紀時期的英國并不穩定,那時候的人們由于缺少“管制”導致“脾性暴躁不安”,且人們總是隨身攜帶武器,在此期間英國法庭的訴訟大幅增長[17]。而當時在英國王庭之中,貪污腐敗現象也甚囂塵上,屢禁不止。瑪麗蓮·威廉姆森注意到,早在1603年,詹姆士的宮廷就已經道德敗壞,地方當局也肆意揮霍,他們經常對亞文化的非法活動視而不見,并參與其中[18]。此外,詹姆斯國王1603年9月17日的《斯圖亞特王朝宣言》中聲稱“流氓、流浪者和閑置放蕩的人”都是治安法官和其他官員的“過失”[19]。由此可見,早期現代英國也正是缺乏律法的約束導致社會風氣敗壞,道德紊亂,國家不安定,這正與劇中法律不嚴導致的秩序失調現象相呼應,表達了莎士比亞對當時瘟疫橫行,律法不嚴所帶來的社會混亂以及對新王詹姆士是否能夠處理好現存問題,把握道德與法律的尺度以還英國社會安定的焦慮。并且,莎士比亞希望詹姆士一世發現自己與文森修公爵的相似之處,并且受這個“道德”公爵考驗和教化臣民的激勵[13],并以此參與到政治討論之中,希望詹姆士一世可以像劇中公爵合理處理國家所面臨的道德困境,遏制國家司法體系腐敗現象并維持英格蘭的政體健康。
17世紀初,新王詹姆士繼位,各種社會道德問題逐漸顯現出來,英國國教徒與清教徒關于如何懲治通奸者的爭端也愈演愈烈,而身為執法者則必須對司法的嚴謹性負起相應的道德責任。從古典醫學的體液理論視角出發研究《一報還一報》,可以發現劇中文森修公爵的一系列維護城市安定之舉措取得了整頓社會亂象,恢復國家政體健康的效果。通過維也納的疾病化,莎士比亞意在刻畫社會亂序現狀并參與政治討論,向詹姆士一世傳達他的政治理念與道德理想。
注釋:
①參見莎士比亞《一報還一報》,辜正坤主編,彭發勝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年版。本文中該劇引用此版本譯文時隨文注出彭澤,Ⅱ.i.5-7分別表示澤者、原文的幕次、場次及行數(下同)。本文所用的全集版本為S.GREENBLATT etal. eds,The Norton Shakespeare (New York:W.W.Norton,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