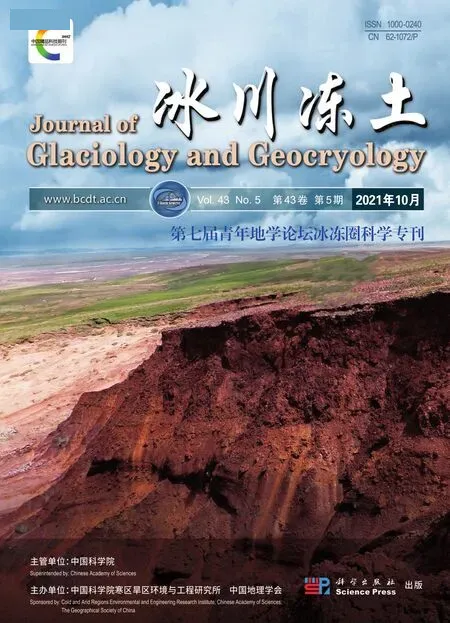高海拔多年凍土區路基工程行為對低溫多年凍土長期影響的監測研究
范星文, 林戰舉, 羅 京, 劉明浩, 尹國安, 高澤永
(1.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凍土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甘肅蘭州 730000; 2.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
0 引言
青藏鐵路是內地連通西藏的生命線工程,是我國高海拔多年凍土區修建的第一條鐵路。青藏鐵路采取了“主動冷卻路基”的設計理念,2006 年全線建成通車,目前已安全運營超過10年。青藏鐵路格爾木至拉薩段(簡稱格拉段)全長約1 100 km,沿線平均海拔約4 500 m,穿越大片連續多年凍土區段約550 km,其中年平均地溫大于-1 ℃的高溫多年凍土段約占50%,體積含冰量大于20%的富冰多年凍土段約占40%[1]。
由于多年凍土含有冰,對熱擾動非常敏感。修建在多年凍土之上的鐵路、公路等線性工程都不可避免的會對地表條件造成改變,導致地表輻射能量結構與地表熱量收支發生變化,進而引起路基下部及坡腳附近多年凍土活動層厚度增加、凍土溫度升高,甚至多年凍土發生融化,最終導致工程構筑物穩定性下降,路基沉陷、裂縫等病害發生[2-3]。
溫度是判定多年凍土是否穩定的主要指標。鐵路路基下部及坡腳附近溫度場的變化主要由自然因素(包括:全球尺度或區域尺度的氣溫、降水、地表覆蓋等)和人為因素(包括:工程施工、人為熱源、鐵路運營等)兩方面引起[4],在這兩類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多年凍土可能會變暖,從而引起凍土區面積減小、低溫凍土向高溫凍土轉化等問題[5-11]。
為保障青藏鐵路的正常運行,大量學者及工程技術人員通過監測路基下部溫度場變化來評價路基穩定性狀況。其一是地域差異條件下路基下部凍土變化研究,對青藏鐵路沿線如西大灘、北麓河、風火山、唐古拉山等地區進行監測,發現凍土活動層厚度不斷增加,多年凍土發生不同程度退化,鐵路路基病害主要表現為多年凍土退化之后易發生融沉[12-16];其二是不同路基結構的降溫效果研究,如對塊石路基、遮陽棚、熱棒等路基結構的長期研究表明,路基結構在保護凍土、減緩凍土退化、減少路基病害方面發揮重要作用[17-20]。這些研究也證實了路基穩定性與其下部多年凍土條件密切關聯。
同時也發現,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路基兩側能量平衡分析計算、多年凍土地氣熱收支分析、溫度與路基沉降等方面[18-24],也特別關注高溫多年凍土區路基下部及坡腳地溫場的變化及其與工程的相互作用,但缺少根據較長時間序列的實測地溫數據,來評價工程行為對低溫多年凍土的影響研究。短時間序列的工程行為對多年凍土影響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足以準確評估鐵路路基穩定狀況。
鑒于此,本文基于青藏鐵路K980+000段2008—2019 年的長期地溫監測資料,分析了鐵路工程運營對低溫多年凍土的長期影響過程,包括路基下部多年凍土地溫變化趨勢、路基上限變化趨勢、天然地溫變化趨勢等,研究結果對準確評估青藏高原凍土環境變化以及維護青藏鐵路安全運營具有重要意義。
1 研究區概況
1.1 區域地質地貌條件
青藏高原位于我國西南部,南自喜馬拉雅山脈南緣,北到昆侖山-祁連山北側,縱貫約13 個緯度,南北寬達1 532 km,面積約為2.6×106km2,約占我國陸地總面積的26.8%[25]。青藏高原也是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大部分區域平均海拔超過4 500 m。較高的海拔導致空氣稀薄、太陽輻射強、平均氣溫較低、日較差大等氣候特點。現代冰川、凍土發育、冰緣地貌、寒凍風化作用普遍[26]。
研究區(圖1)位于昆侖山南坡青藏鐵路里程K980+000 路基西側處,距昆侖山埡口約3 km。南接楚瑪爾河高平原,海拔約4 700 m,屬于昆侖山大-中起伏高山地貌單元,大部分地區為冰水沉積或湖相沉積帶,少部分為河流階地,地形相對平緩。海拔5 100 m以上發育著現代冰川、石冰川[27]。

圖1 青藏高原及研究區位置[26]Fig.1 Location of study site in Qinghai-Tibet Plateau(QTP)[26]
1.2 區域氣象條件
研究區位于青藏高原北部,氣候干旱,多風少雨,屬于典型的內陸高原氣候特征。研究結果顯示[28-29],距研究區南約50 km 的清水河地區1957—2011 年多年平均降雨量517.8 mm,年蒸發量1 163.3 mm,年平均風速4.5 m·s-1,最大風速31 m·s-1,最大積雪厚度15 cm。同時,根據2014年布設在該場地的HOBO 系列氣溫傳感器監測結果(表1),研究區2015—2018 年多年平均氣溫-5.5 ℃,極端高溫20.2 ℃,極端低溫-32.8 ℃,平均凍結天數為247 天,凍結指數為2 490 ℃·d,融化指數為523 ℃·d,凍融指數為4.76。

表1 研究區2015—2018年氣溫情況Table 1 Air temperatures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15 to 2018
1.3 區域植被與凍土發育情況
研究區位于高寒草原區,主要植被類型為高寒草原(alpine grassland),原生建群種為小嵩草(Kobresia pygmaea)和紫花針茅(Stipa purpurea)[30-31]。且植被稀少,蓋度不足20%,植株高度<15 cm。
研究區凍土基本呈大片連續分布,局部有融區。據前期調查,昆侖山南坡連續凍土下界在4 450~4 560 m[32]。多年凍土厚度約為60~120 m,天然上限深度約1.5~2.5 m,垂向上2~3 m 深度易受影響的區域發育著質量含水量超過50%的含土冰層,屬富冰或飽冰凍土區,3~8 m 為富冰或飽冰凍土,含水率約20%,13 m 以下為強風化泥灰巖區,發育飽冰或富冰凍土,部分區域有層狀冰[29]。凍土冷生構造為網狀、水平層狀和裂隙脈狀。
1.4 研究區路基結構
塊石路基廣泛應用于青藏鐵路路基。塊石路基可分為塊石基底路基、塊石護坡路基、以及U 型塊石路基。研究區的路基結構為塊石護坡路基,屬于開放式塊石路基。路基高度約為4 m,塊石護坡厚度約為1 m[圖2(a)]。塊石路基能有效抬升多年凍土上限,降低下部多年凍土溫度。
2 研究方法
2.1 監測設備布設
2007 年10—11 月進行現行路基單側鉆孔[圖2(b)],垂直路基布設鉆孔5個,鉆孔深度均為15 m,1號孔距離鐵路路基坡腳約為30 m,可近似認為是天然孔,鐵路運營對該處的多年凍土基本沒有擾動,或者擾動很小。2號孔距離鐵路路基坡腳約為5 m,3 號孔距離路基坡腳約為3.6 m,4 號孔距離路基坡腳約為2 m,5號孔位于路基坡腳處。每個鉆孔安裝高精度熱敏電阻溫度傳感器25個(由中國科學院凍土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制作,標定測溫精度為±0.05 ℃),用于實時監測凍土溫度。從地面向下第1 個溫度傳感器安裝深度為0.5 m,0.5~10 m 深度,每隔0.5 m 安裝1 個;10~15 m,每隔1 m 安裝1個溫度傳感器。

圖2 K980+000段地溫監測孔布設示意圖Fig.2 Map of ground temperature monitoring holes in section of K980+000:subgrade structure and ground temperature holes at the study area(a);surface conditions at the study area(b)
地溫數據用美國Compbell 公司生產的CR3000數據采集儀采集,數據采集開始時間為2008 年1 月1 日,實施自動連續采集,采集頻率為每天4 次。本文分析數據截止日期為2019 年12 月31 日,其中2013年2—4月的數據缺失,缺失數據通過前后兩年同期數據內插補足,缺失數據小于全部分析數據的2.3%,對平均值的計算影響很小。
2014 年10 月,補充安裝了一套HOBO 系列外部溫度數據記錄器HoboPro v2(U23-004),氣溫傳感器被保護在太陽輻射罩內,安裝高度為2.0 m,地表溫度傳感器埋設在地表以下5 cm 深度,標定的測量精度為±0.21 ℃,適用環境溫度為-40~100 ℃。數據從2014 年10 月5 日開始記錄,每30 分鐘連續記錄一次。本文分析數據截止日期為2020 年2 月29日。
2.2 數據分析方法
2.2.1 平均氣溫、平均地溫計算
年平均溫度是指一年內365(或366)天的平均值,本文年平均氣溫是指每年1 月1 日至12 月31 日的17 520個(2個/小時×24小時×365天)氣溫數據的平均值。不同深度土體年平均溫度是指每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的1460個(4個/天×365天)地溫數據的平均值。月平均溫度是指每月溫度的平均值。
2.2.2 冷暖季平均溫度計算
青藏高原四季不分明,通常分為冷暖兩季。在全球增溫的背景下,區分不同季節的增溫,有利于采取不同的措施,更好的保護鐵路。本文選取將5—10 月份作為暖季(地表溫度為正溫,處于融化狀態),11 月—次年4 月作為冷季,分析冷暖季不同的增溫趨勢。冷季與暖季的增溫率均為年均冷季/暖季增溫率。在進行計算年均增溫速率時,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計算。
3 結果分析
3.1 凍土上限變化趨勢
凍土上限一般指0 ℃等溫線在土體中達到的最大深度,是多年凍土區凍土融化最大深度[32-33]。利用線性插值方法,估算了各個監測孔的凍土上限(圖3)。結果表明2008 年監測初期,1 號孔、2 號孔凍土上限相差不大,均約為1.8 m,5 號孔上限深度為1.26 m。到2019 年監測孔凍土上限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4號孔凍土上限深度達到2.27 m,下降了56 cm,在所有的監測孔中最大,5 號孔凍土上限約1.67 m,在所有的監測孔中為最小,下降了41 cm。

圖3 凍土上限隨時間變化(2008—2019年)Fig.3 Annual variations of permafrost table during 2008—2019
監測期(2008—2019 年)所有監測點的凍土上限都在波動中下降。2010 年和2016 年有一個“跳躍”(兩個年份的凍土上限下降量超過10 cm),可能由于極端氣候的影響或者是地下熱量累積后產生突變,其余時間下降趨勢都比較緩慢。同時,從下降率來看,5 個監測孔凍土上限下降的速率大體一致,1 號孔、2 號孔、4 號孔凍土上限下降幅度均大于4 cm·a-1,3 號孔、5 號孔凍土上限下降幅度約為3 cm·a-1;但5號孔(靠近路基的孔)維持了較淺的凍土上限,表明非氣候源的擾動可能在此處很小,并且塊石路基很好的保護了上層多年凍土,使其處于放熱大于吸熱狀態,保持了較淺的凍土上限深度。
3.2 地溫年均升溫趨勢
對地溫數據進行分析,將兩年溫度的平均值做成一個系列的數據,繪成地溫剖面圖(圖4)。結果顯示,在同一深度,盡管土體年平均溫度可能存在一定波動,但總體呈現出增溫的趨勢,上層增溫大于下層增溫。1 號孔2008—2013 年的淺層平均地溫接近,從2014 年以后,地溫顯示出明顯的增加趨勢。2 號孔的地溫逐年遞增,2014—2015 年地溫在這10 年中表現出最暖(-7 m 以上),外界環境(氣溫、降雨、熱擾動等)的影響大,但總體呈現出波動增溫的趨勢,-7 m 以下,受外界環境影響很小,地溫同樣表現出隨時間增溫趨勢。3 號孔、4 號孔、5 號孔溫度變化趨勢與2 號孔相同,即2014—2015 年平均地溫表現出反常的高溫(-7 m 以上),但其下部的地溫也隨時間不斷增加。同時,對-7 m 以下深度的地溫進行分析,2 號孔、3 號孔、4 號孔、5 號孔下部溫度增溫速率不同,2 號孔2008—2015 年增溫較大(表現為年平均地溫曲線間距較大),5 號孔2008—2015 年增溫較小(表現為年平均地溫曲線間距較小),但2016—2017 年的地溫均表現出了一個“跳躍”(與氣溫變化一致),即所有監測鉆孔深部(-7 m到-15 m)溫度相較前幾年顯著的增加。根據地溫曲線,所有的監測孔地溫曲線逐漸由“穩定型地溫曲線”變為“退化型地溫曲線”,這一過程隨時間推移不斷加劇。

圖4 監測孔地溫剖面隨時間變化(一個地溫曲線代表兩年的平均地溫)(2008—2019年)Fig.4 Ground temperature profile at five boreholes during 2008—2019(A profile represents the average ground temperature in two years)
利用線性回歸分析方法,計算出每個觀測點不同深度每年的升溫率(圖5)。該區域的地溫整體表現出升溫的趨勢,升溫率隨深度的增加呈現出遞減的趨勢。將-0.5 m 處地溫看作活動層上部,-1.5 m處看作是活動層下部,-2.5 m 處看作是凍土頂部,-5 m、-10 m、-15 m分別看作是淺、中、深三個不同的凍土深度,計算了它們的年均升溫率(表2)。地溫年均升溫最顯著的為活動層(表現為所有監測孔-2 m 深度以上年均增溫比-2 m 深度以下大),在-2 m 深度以上,對應的最大年均增溫值1 號孔約0.048 ℃·a-1,2 號孔0.108 ℃·a-1,3 號孔0.108 ℃·a-1,4 號孔0.135 ℃·a-1,5 號孔0.042 ℃·a-1。5 號孔增溫趨勢較1 號天然孔快,4 號孔靠近路基,在-2 m深度以上,增溫趨勢較快,在-2 m 深度以下,增溫緩慢。在-10 m 深度以下排除局地因素的差異以及儀器的誤差,1~5 號孔表現出相似的增溫趨勢,并且距離路基越近增溫幅度越小。

圖5 研究區各鉆孔11年年均增溫隨深度變化趨勢(2008—2018年)Fig.5 Annual increase rate of ground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depth at each borehole during 2008—2018
監測數據表明,研究區地溫在冷季和暖季表現出不同的增溫趨勢,全年表現出不均衡增溫狀態(圖6)。暖季,5 個監測孔地溫都表現出增溫趨勢,隨深度增加,增溫幅度下降。路基孔年均增溫較天然孔小,天然孔與2 號、3 號孔表現出大致相等的增溫幅度,靠近路基的4 號監測孔在0 m 到-2 m 深度顯示出較強的增溫趨勢,-2 m 以下,各監測孔表現出大致相等的增溫幅度。在冷季,5 個監測孔同樣顯示出增溫趨勢。-2 m 深度以上所有鉆孔都顯示隨深度增加而增溫率逐漸增大;-2 m 到-3 m 深度,增溫趨勢最大;-3 m 深度以下,隨深度增加增溫趨勢逐漸減小;-8 m 以下,增溫趨勢大致相等。綜合來看,暖季與冷季表現出不均衡的增溫趨勢,暖季增溫趨勢在0 到-2 m 深度時較冷季大,-2 m到-10 m 暖季增溫趨勢較冷季小,-10 m 到-15 m 深度,冷季與暖季增溫趨勢大致相等,相差±0.001 ℃。

圖6 暖季與冷季不均衡增溫趨勢Fig.6 Unbalanced warming in warm season and cold season,warm season(a)and cold season(b)

表3 不同深度年均增溫速率以及對應的相關系數(R2)Table 3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increase rate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t different depths
4 討論
4.1 地溫變化及其對路基影響
在監測時間內,計算了地溫的年際增溫趨勢、季節增溫趨勢,這兩種趨勢都表明地溫是在緩慢增加。不同監測孔、監測孔的不同深度年際增溫率不同,但這種增溫都導致活動層厚度的增加,多年凍土層部分融化,路基以及天然孔面臨著沉降的風險。增溫的原因是氣候變化和工程擾動的雙重效應。
氣候的變化直接影響著多年凍土的發展。全球氣候變化主要以氣候變暖的形式出現,IPCC的報告指出,過去100 年來全球地表溫度升高了0.3~0.6 ℃,自19 世紀90 年代以來全球變暖幅度明顯升高,預計未來100 年內全球氣溫可能升高2.5 ℃,可能的范圍為1.4~5.8 ℃[34]。青藏高原作為全球氣候變化的指示器,其升溫速率會高于全球平均值[35-36],從1981 年至2010 年期間,青藏高原氣溫平均升高率為0.04~0.05 ℃·a-1[37],同時,1995 年至2007 年期間,青藏公路沿線的多年凍土活動層厚度持續增加,年平均速率為4.5 cm·a-1[35]。從研究區來看,其活動層的厚度持續增加,天然孔年平均增加速率為4.2 cm·a-1,略小于1995—2007 年的4.5 cm·a-1;路基孔的活動層厚度年增加速率為3.3 cm·a-1,遠小于沿線的活動層厚度的年均增加率。與之相對的,3 號孔活動層增加速率4.0 cm·a-1,4 號孔4.6 cm·a-1,2 號孔4.7 cm·a-1。塊石路基減緩了多年凍土活動層厚度的增加速率,但活動層厚度增加趨勢仍會持續。
氣候變暖下,大部分地區的工程熱擾動的疊加作用加速了工程下部多年凍土的退化[38]。多年凍土區的路基工程改變了地表物理性質,破壞了原有的能量平衡特征,其下部的凍土熱狀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研究區域,活動層厚度不斷增加、凍土溫度升高。
4.2 路基地溫隨距離的變化特征
路基一側的5個孔,1號孔離路基最遠(30 m),5號孔在路基坡腳處。圖7 列出了1~5 號孔2008—2019 年年平均地溫。2~5 號孔,測溫孔的年平均地溫隨離路基距離的增加,存在顯著增加趨勢。5 號孔(路基孔)的年平均地溫在檢測時間內顯著小于2號孔。

圖7 測溫孔年平均地溫Fig.7 Annual mean ground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boreholes
從總體上看,離路基越近,多年凍土年平均地溫越低。為進一步研究不同深度這種變化的差異性,選取深度為-0.5 m、-1 m、-1.5 m、-2.5 m、-5 m、-10 m、-15 m 各層的地溫數據作為因變量,以到路基的相對距離為因子等級分別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來研究路基一側地溫隨路基不同距離的變化特征。
從表4方差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在深度為-0.5 m時,5 號孔與其余4 個孔不存在顯著性的差異,即在該層上工程帶來的熱作用不明顯。隨深度增加,在-3 m 時,5號孔與4號孔土體溫度開始出現差異;此時,5號孔與3號孔以及2號孔出現極顯著的差異,與1號孔出現顯著性差異。極顯著的差異在-5 m以下時表現明顯。因此,地溫雖然在一定范圍內隨路基距離的增大而逐漸增大時,各深度的增大速率并不一致。路基的大致影響范圍在2.0~3.6 m之間。
塊石路基夏季通過隔熱降低路基下部土體的溫度,而冬季通過對流換熱來儲藏冷量,起到了“熱半導體”的作用[39-40]。因而,在凍土上限附近(-3 m)、-10 m 處,路基以及相鄰區域的土體溫度較天然孔低。在監測的深層(-15 m),天然孔的平均地溫比路基孔以及受路基影響的孔(2號孔、3號孔、4號孔)要低,但升溫較快。相反,5號孔升溫較慢(圖8)。

圖8 不同深度處的土體溫度Fig.8 Soil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depth
5 結論
(1)長期的監測數據表明,過去12 年(2008—2019 年)低溫凍土活動層厚度不斷增加,冷卻路基監測孔的活動層厚度增加最小,且年均增加較小。
(2)所有監測孔都顯示出長期的增溫趨勢,增溫不僅體現為年際增溫,也體現為季節性不對稱增溫。路基孔的增溫小于其余的孔,天然孔的增溫小于受路基影響的監測孔。
(3)氣候變暖以及工程熱擾動的疊加導致路基一側的凍土地溫增加,年平均地溫不斷升高。工程建筑物的影響局限在一定的區域,并減小了氣候變暖的影響,使路基附近的地溫增加較小且趨勢較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