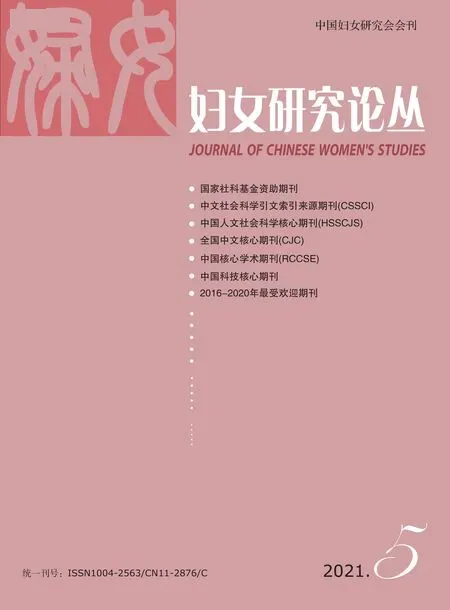法律如何定義對婦女的歧視*
戴瑞君
(中國社會科學院 國際法研究所,北京 100720)
一、引言
1995年,在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上,中國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把男女平等作為促進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我們堅決反對歧視婦女的現象”[1]。2005年修正后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婦女法》)第2條第2款寫入“實行男女平等是國家的基本國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此外,中國數部法律包含禁止“歧視”、禁止“性別歧視”的一般原則,但是沒有一部法律界定何謂“歧視”。2019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譚琳提出修改《婦女法》的議案,建議明確將“歧視”婦女的定義寫入總則,規定國家禁止對婦女實施一切形式的歧視[2]。
事實上,在國內法中對歧視作出定義也是國際人權機構對中國落實國際人權條約義務提出的具體建議。中國于1980年批準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消歧公約》)(1)《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249 UNTS 1,1981年9月3日生效。。該公約在第1條即對“對婦女的歧視”作出定義。負責審議締約國履行《消歧公約》狀況的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以下簡稱“消歧委員會”)(2)消歧委員會是根據《消歧公約》第17條成立的條約機構,負責監督締約國履行《消歧公約》的情況。注意到中國法律中“沒有確定歧視婦女的定義”,建議中國依照《消歧公約》第1條的定義通過立法明令禁止性別歧視(3)《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的報告:第20屆會議》,UN Doc A/54/38/Rev.1,1999年8月20日,第283-284段。另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的結論性意見:中國》,UN Doc CEDAW/C/CHN/CO/6,2006年8月25日,第9-10段;《關于中國第七和第八次合并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UN Doc CEDAW/C/CHN/CO/7-8,2014年11月14日,第12-13段。。
本文將在分析《消歧公約》規定的歧視定義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參考域外經驗,對為什么中國法律有必要定義歧視以及如何定義歧視作出初步回答。
二、《消歧公約》中的歧視定義
定義“對婦女的歧視”是《消歧公約》的根基,因為該公約的締約國承擔的核心義務就是要消除這一歧視。因此,明確界定歧視,是締約國履行義務的前提和基礎。《消歧公約》第1條規定:
為本公約的目的,“對婦女的歧視”一詞指基于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享有和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一)為何聚焦“對婦女的歧視”
從《消歧公約》的定義來看,它不僅禁止基于性別的歧視,而且明確禁止“對婦女的歧視”。這表明“《消歧公約》不是性別中立的”[3](P 12),而是聚焦于消除對婦女的歧視。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
國際人權法上,從《聯合國憲章》到《世界人權宣言》再到“人權兩公約”(4)人權兩公約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999 UNTS 3,1976年1月3日生效)和《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999 UNTS 171,1976年3月23日生效)。都不乏男女平等和禁止歧視的規定。《聯合國憲章》在序言即宣布“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第55條(寅)項規定聯合國應促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聯合國憲章》確立起男女平等及在促進人權和基本自由方面不得基于性別作出歧視的原則。《世界人權宣言》(5)《世界人權宣言》,UN Doc A/RES/217 III (A),1948年12月10日。第2條重申這一原則“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載之一切權利與自由,不分……性別……或其他身分”。《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第1款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并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性別……或其他身分等等,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第3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本公約所載一切公民及政治權利之享受,男女權利,一律平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第2款及第3條規定了類似的平等原則,只是將確保享有的權利指向該公約所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然而,誠如《消歧公約》序言所言,盡管有這些文件,“歧視婦女的現象仍然普遍存在”。這是因為,人權兩公約及之前的國際文件盡管以性別中立的語言寫就,但是“其僅關注在形式上建立權利平等”[4](P 116),其假定損害的性質是基于男性的生活經驗的,當女性的生活經驗與男性經驗不同時,這些文件中所包含的平等或非歧視模式就不再奏效。例如,懷孕、生育、墮胎是婦女獨有的經歷;家務勞動和照料工作的主要承擔者是女性,但這些工作的價值普遍被否定或被嚴重低估;家庭暴力、性騷擾等暴力行為的受害者主要是女性;等等。上述種種男性基本上無需面對的情形卻是導致女性地位低下的重要因素。
以往國際人權文件中所規定的“男女平等”或“禁止性別歧視”只是以一般的生理性別來處理歧視問題。雖然權利平等的法律規定是通向性別平等道路上的重要一步[4](P 116),但這種“對稱性保護路徑無法承認對婦女基于性別的普遍歧視”[3](P 68)。實現實質上的男女平等需要識別出婦女的獨特經歷及由此帶來的不利處境,并采取專門針對婦女的措施。《消歧公約》的制定者認識到,“婦女獨有的特點和她們易受歧視的特點理應得到法律的特殊反應”[5](P 4)。消歧委員會指出,雖然許多國家和國際法律標準與準則都禁止性別歧視,“但《公約》的重點是歧視婦女問題,強調婦女只因其是婦女便一直并且繼續遭受形形色色的歧視”(6)消歧委員會:《第25號一般性建議:〈公約〉第四條第1款(暫行特別措施)》,第5段,載UN Doc HRI/GEN/1/Rev.9 (Vol.II)《各人權條約機構通過的一般性意見和一般性建議匯編(第二卷)》,2008年5月27日,第364頁。。這正是《消歧公約》的使命與價值,也是該公約聚焦于“對婦女的歧視”的主要原因。
(二)“對婦女的歧視”的要素
一般認為,歧視由區別對待、禁止的領域、禁止的事由、不利后果、因果關系等要素構成[6](P 9)。《消歧公約》第1條對婦女歧視的定義,也可以分解為以上諸項關鍵性要素。
1.事由:基于性別
《消歧公約》的用語是“性別”(sex),指向生物學意義上的分類。20世紀70年代該公約起草時,社會性別(gender)尚不是一個被當時的國際人權法所理解的概念[3](P 20),但這并未妨礙公約的起草者敏銳地發現并揭示在生理性別基礎上造成歧視婦女的社會和文化因素。正如《消歧公約》第5條所體現的,“基于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于男女定型任務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是導致婦女受歧視的根源,要消除這一根源必須“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
因此,歧視定義中的性別包含雙重含義,既指男女的生理差異,更指向社會和文化造成的兩性差別,即社會性別。消歧委員會在第28號一般性建議中對社會性別給出了定義:
“社會性別”一詞指的是社會建構的男女的身份、屬性和作用,以及社會對這類生理差異賦予的社會和文化含義。正是這類生理差異導致男子與婦女之間的等級關系,還導致男子在權力分配和權利行使方面處于有利地位,婦女處于不利地位。婦女和男子的這種社會定位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宗教、思想觀念和環境因素的影響,也可以通過文化、社會和社區的力量加以改變(7)消歧委員會:《關于締約國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二條之下的核心義務第28號一般性建議》,UN Doc CEDAW/C/GC/28,2010年12月16日,第5段。。
消歧委員會對社會性別的理解澄清了“性別”并不等同于“婦女”,它的關注點是關系,是男女之間的權力分配關系[3](P 21)。《消歧公約》要解決婦女僅僅因為是婦女就受到的歧視,特別是要解決對婦女基于社會性別的歧視。
此外,《消歧公約》第1條還提及婚姻狀況——“不論已婚未婚”。婦女的婚姻狀況往往成為她們遭受歧視的一個原因,有時是因為已婚,有時又因為未婚。《消歧公約》的起草歷史表明,起草者的意圖是使已婚婦女與已婚男性相比、未婚婦女與未婚男性相比免于遭受歧視性待遇[3](P 80)。但在某些情況下,基于社會性別的刻板印象,已婚婦女和未婚婦女也可能面臨被區別對待,結合《消歧公約》第5條,因婚姻狀況而存在于婦女之間的歧視也應納入第1條的歧視范圍之內[3](PP 79-80)。
2.行為:區別、排斥或限制
區別、排斥或限制是多項國際文書定義歧視的共同要素。
“區別”是指明顯基于性別而對男女的不同對待。它是基于形式平等(相同的情形以相同方式對待)和實質平等(不同的情形以與其不同點相適應的不同方式對待)兩方面的要求作出的判斷。當一項法律、政策或做法未能以同樣的方式對待男女之間的相似利益,或者未能以充分尊重差異的方式對待男女之間顯著不同的利益時,就構成區別[7](P 108)。例如,一項就業政策禁止雇傭或提拔已婚婦女,而對已婚男性沒有類似的禁令。又如,法律或政策允許或默許忽略只有婦女才需要的保健服務,如未能為婦女在懷孕或分娩時提供相應的保健服務。
“排斥”是指剝奪婦女獲得男子可以得到的機會或權利的信念及社會實踐模式(包括性別刻板印象)[3](P 77)。當一項法律、政策或做法旨在排除婦女卻接納男性時,如拒絕為婦女提供男性可以獲得的福利、機會或權利,即構成排斥。例如,某些政策或法律將婦女排除在兵役之外,或禁止她們在服兵役時履行某些職責,或直接拒絕婦女進入提供軍事培訓的教育機構。這些排斥性做法的共同點是“阻止婦女進入或參加某些政治、社會、經濟或文化領域”,不將相關領域的職位授予婦女[7](P 109)。
“限制”是指僅對婦女享有或行使某些權利施加限制,或施加比男子享有或行使相同的權利更加嚴苛的限制。有學者認為,僅讓婦女承擔某種負擔,如在涉及強迫生育的情況下,使其無法充分享有和行使依法保障的權利和自由,也構成“限制”[7](P 110)。
有必要指出的是,“基于性別”而作出區別、排斥或限制,并不是說一項歧視行為“必須明確提及”性別或與性別相關的特征。基于性別既包括明確以性別作出區別的直接歧視,也包括表面中立的標準或做法但實際對婦女產生顯著不利影響的間接歧視。
3.不利后果:妨礙或否認
判斷是否構成歧視的實質檢驗標準是受到質疑的行為或做法是否對婦女產生“不利影響”,這種不利影響表現為對婦女認識、享有或行使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妨礙或否認。而確定是否構成“妨礙或否認”的一個辦法是檢驗某一項法律、政策或做法是否剝奪了婦女的福利,是否給婦女施加了某種負擔,是否貶低了婦女的價值、貶損了婦女的尊嚴或使婦女處于邊緣地位[7](PP 60-68,P119)。
不利影響標準把某些有利于婦女的差別待遇排除在了歧視范圍之外。根據《消歧公約》第4條,締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采取的暫行特別措施,不被視為第1條所指的歧視;為保護母性而采取的特別措施,亦不被視為歧視。
4.因果關系:影響或目的
“影響”指向客觀效果,“目的”指向主觀意圖,“或”表明二者只要具備其一即可能構成歧視。這一短語明確了《消歧公約》的歧視定義既包含直接歧視,也包含間接歧視。
一方面,有妨礙或否認婦女享有權利的目的或意圖的做法當然構成歧視。這種歧視是直接歧視,其特點是公開的、明目張膽的,因而也是法律所明確禁止的。另一方面,意圖又不是構成歧視的必要因素—— 一項沒有明顯歧視意圖、看似對女性和男性無任何傾向的做法,實際上如果產生了妨礙或否認婦女享有人權的客觀效果,也構成對婦女的歧視,即間接歧視。
因此,一項持有歧視意圖(目的)的做法,或者雖然沒有明顯的歧視意圖但在實際上產生歧視效果的做法,都是《消歧公約》所禁止的歧視行為。
5.適用領域:任何方面的權利和自由
對于在哪些領域禁止對婦女的歧視,《消歧公約》使用了“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措辭。其中,“任何其他方面”的用語使得《消歧公約》的適用范圍超越了該公約明確列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只要是公約締約國締結的其他條約所確認或是被習慣國際法所確認的人權或基本自由,國家就有義務消除婦女在享有和行使這些權利時可能遭受的歧視[3](PP 80-81)。而這些條約包括國家在批準或加入《消歧公約》之前締結的,也包括在此之后締結的。這就使《消歧公約》成為一個動態的、發展的公約,可以隨時納入國家所接受的新的權利或自由。這樣的理解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的目標是一致的。
(三)“對婦女的歧視”的特點
《消歧公約》并不是第一個定義歧視的國際文件。此前,國際勞工組織《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8)Convention (No.111) concerning Discrimination in Respect of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362 UNTS 31,1960年6月15日生效。該公約第1條對公約所言的歧視作出定義:“基于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見解、民族血統或社會出身等原因,具有取消或損害就業或職業機會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的任何區別、排斥或優惠。”此一翻譯也參考了國際勞工組織網站提供的中文譯本。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取締教育歧視公約》(9)Conven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429 UNTS 93,1962年5月22日生效。該公約對歧視的定義是“基于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經濟條件或出生的任何區別、排斥、限制或優惠,其目的或效果為取消或損害教育上的平等待遇,特別是:(甲)禁止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接受任何種類或任何級別的教育;(乙)限制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只能接受低標準的教育;(丙)對某些人或某群人設立或維持分開的教育制度或學校,但本公約第二條的規定不在此限;(丁)對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加以違反人的尊嚴的條件。”此一翻譯也參考了聯合國公約與宣言檢索系統提供的中文譯本。都對“歧視”做過定義。《消歧公約》更多受到1966年通過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以下簡稱“《消除種族歧視公約》”)(10)《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660 UNTS 1,1969年1月4日生效。中“種族歧視”定義(11)根據《消除種族歧視公約》第1條,該公約所稱“種族歧視”,是指“基于種族、膚色、世系或原屬國或民族本源之任何區別、排斥、限制或優惠,其目的或效果為取消或損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權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之承認、享受或行使”。的影響和啟發。與之前的定義相比,“對婦女的歧視”定義有自身的特點(12)對婦女歧視的定義也對《消歧公約》之后通過的人權文書中的歧視定義產生了積極影響。例如,2006年通過的《殘疾人權利公約》(2515 UNTS 3,2008年5月3日生效)對“基于殘疾的歧視”的定義也沒有將優惠作為歧視對待,也適用于包括私領域在內的“任何其他領域”,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2條。。
1.某些“優惠”不屬于歧視
不論是《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取締教育歧視公約》還是《消除種族歧視公約》,它們所摒棄的歧視做法都包含基于性別的“優惠”。換言之,優惠也構成某種形式的歧視。
但根據《消歧公約》的定義,特定情況下對婦女的某些優惠并不構成歧視,這集中體現在公約第4條對特別措施的規定上。該條第1款要求締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采取暫行特別措施。這些措施顯然要求區別對待婦女與男子,甚至給予婦女優惠。因為沒有哪種偏見比性別刻板印象帶給社會期待和社會行為的印記更深刻,第4條第1款即建立在承認阻礙婦女實現平等的文化和制度障礙的頑固性的基礎上,認識到消除障礙的緊迫性,明確規定要“加速”實現實質平等。而暫行特別措施作為協助、補償和糾正的促進措施,是實現男女事實上平等的內在方面和必要戰略[3](P 164)。
第4條第2款要求國家為保護母性采取特別措施。這一規定讓與女性生育相關的保護性措施合法化[3](P 163)。生育,包括懷孕、分娩和哺乳,代表著客觀的生理差異,為此需要對婦女采取持久的特別措施。
不論是暫行特別措施還是保護母性的持久特別措施,都是實現婦女在事實上的實質平等的必要手段,是《消歧公約》中的平等和消除歧視概念的固有含義,而不是歧視的例外。認為特別措施構成“反向歧視”“積極歧視”“歧視男性”的說法是對特別措施的目的的曲解[3](173),公約明確規定這些措施“不得視為歧視”。
2.私領域的歧視也是歧視
傳統人權法主要在公領域運行,即在政府、政治、經濟、職場等傳統上屬于男性的領域運行,關注的是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關注公權力對個人權利的侵犯。保護家庭制度和隱私權的法律不鼓勵國家直接介入家庭生活。但對婦女最普遍的傷害恰恰發生在家庭內部,發生在私領域的密室中。“由于家庭是許多嚴重侵犯婦女身心健康的場所,任何對家庭制度和隱私權的無條件遵從都會給婦女帶來災難性后果。”[8](P 127)家庭等私領域的不平等也削弱了婦女進入和享有職場、政治等公共領域的權利。由于多數對婦女人權的侵犯不能被完全歸為政治性的,也不僅僅是由公權力造成的,而是來自私人,來自她們生活的社區和家庭,因此公私兩分,特別是人權法僅關注公領域人權的事實,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對婦女的歧視。
所以,與《消除種族歧視公約》將種族歧視的適用范圍限定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不同,《消歧公約》對婦女的歧視適用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13)兩處著重號為本文作者所加。。前者旨在消除發生在公共領域(14)《消除種族歧視公約》英文作準本更直觀地反映了這一點:in the political,economic,social,cultural or any other filed of public life。的種族歧視;后者不限于公共領域,而是致力于消除所列舉方面及“任何其他方面”(15)比較《消歧公約》英文作準本第1條的相關規定:in the political,economic,social,cultural,civil or any other field。存在的對婦女的歧視,當然也包括發生在私領域的歧視。
事實上,《消歧公約》多處體現了其對私領域歧視婦女問題的關注。例如,該公約第5條規定締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措施“確認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第16條全面規定了締約國“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系的一切事項上對婦女的歧視”的義務。作為一個譴責對婦女的歧視的文件,《消歧公約》能夠“成功的關鍵在于,不局限于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垂直關系,還應通過國家機制,適用于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水平關系”[3](P 13)。因此《消歧公約》第2條(e)項要求締約國“采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
3.揭示結構性歧視
社會性別視角幫助人們識別并理解歧視婦女的根源。“對婦女的歧視”定義的首要要素——基于性別,即包含了基于社會性別的區別對待。因此,消除歧視、實現平等要求解決《消歧公約》第5條所描述的根植于父權制的男女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基于男女定型任務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的結構性歧視。該公約序言強調,“為了實現男女充分的平等需要同時改變男子和婦女在社會上和家庭中的傳統任務”。《消歧公約》的目標就是從根本上消除歧視性的社會結構和傳統做法,轉變人們頭腦中阻礙實現男女實質平等的對男女兩性的刻板印象。
綜上所述,《消歧公約》中“對婦女的歧視”定義是一個內涵和外延均十分廣泛的概念。它既包含直接歧視,也包含間接歧視;既否定基于生理性別對男女作出區分的歧視,也否定基于社會性別和男女定型任務的歧視;既要求男女平等的對稱性保護,也要求承認差異基礎上對婦女特有需求的保護;既要解決面向未來的歧視婦女問題,也需通過暫行特別措施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讓婦女實質上具備與男子平等享有和行使權利的能力。
“對婦女的歧視”定義揭示了歧視婦女的根源,打破傳統人權法的公私二分,豐富了各項人權的權利內涵,對建構事實上的“普遍”人權產生了有力影響(16)鑒于國際人權法和普遍人權理論并未充分反映婦女的主張和經歷,有學者指出,“國際人權法應稱之為國際男人權利法。除非婦女在造法一開始就能獲得平等的代表性,否則國際人權法將無法主張它的普適性”。[9](P 105)。
三、國內法定義歧視的必要性
中國在根據《消歧公約》提交履約報告時坦言,中國法律沒有專門對“歧視”下定義,但認為這“并不影響中國在法律和實踐中遵守《公約》規定的各項義務”(17)《中國關于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就審議中國第五、六次合并報告所提問題單的答復》,UN Doc CEDAW/C/CHN/Q/6/Add.1,2006年6月8日,第1段。。根據中國最新一期履約報告,《消歧公約》關于消除基于性別歧視的規定已充分體現在憲法、婦女法、選舉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相關法律中;雖然現行法律沒有“對婦女的歧視”的專門定義,“但通過單行立法嚴厲禁止對婦女可能出現的直接和間接歧視”(18)《中國根據公約第18條提交的第九次定期報告》,UN Doc CEDAW/C/CHN/9,2020年12月15日,第16段。。
不過消歧委員會認為,缺乏歧視的定義會限制國家對《消歧公約》各項義務的充分理解和落實,因此反復建議中國在國內法中作出符合公約第1條的歧視婦女的全面定義(19)例如,消歧委員會在審議中國第五-六次履約報告的結論性意見,UN Doc CEDAW/C/CHN/CO/6,2006年8月25日,第10段;消歧委員會《關于中國第七和第八次合并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UN Doc CEDAW/C/CHN/CO/7-8,2014年11月14日,第13段。。包含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在內的全面的歧視定義,將為在實踐中打擊對婦女的各種顯性或隱性歧視提供基礎和指導。反之,欠缺歧視定義,將影響識別和解決現實中的直接和間接歧視婦女問題[10](P 85)。在國內法中明確定義什么是對婦女的歧視,是識別歧視、預防歧視以及救濟歧視的前提,也是履行中國《消歧公約》義務的要求。
(一)識別歧視需要明確的歧視定義
就對婦女的歧視而言,平等不等于非歧視,男女平等原則無法涵蓋歧視婦女的所有情形。一般來說,形式上或法律上的男女平等需要通過尋找比較對象來實施,實際上往往是以男性作為比較基準的平等。“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的立法模式以男性享有既定權利,婦女應享有與男性同樣或同等權利來實現男女在形式上的平等。在承認兩性差異的前提下,形式上或法律上的男女平等不足以實現兩性實質上或事實上的平等。一方面,客觀的生理差異決定了懷孕、分娩、哺乳等女性的獨特經歷沒有對應的男性標準,而這些獨特經歷恰是歧視婦女的重要事由,形式上的男女平等對此類歧視婦女問題難以發揮效力。另一方面,基于生理性別而塑造的婦女的社會性別角色通過政治、文化、經濟甚至法律制度而體制化[11](PP 5-6)。通過法律固化、正當化、合法化的性別角色定型和刻板印象更為隱蔽和不易察覺,因此,如果不能明確指出“性別”概念中的社會性別層面,而一味遵循現行法律,有可能非但無法消除對婦女的歧視,反而會進一步固化歧視婦女的社會制度。
由于欠缺歧視定義及對歧視的認定標準,在很多情況下抽象的平等原則無法識別歧視的存在,也無法解決事實上的歧視問題。例如,2019年河南省某地在公開招聘教師過程中,一位考生總成績第一名,卻因懷孕不宜做胸透檢查,被認定為“體檢不合格”,最終被拒絕錄用。當事人質疑當地教育部門以體檢項目缺項變相歧視孕婦,但有關部門辯稱不存在主觀刻意阻撓或設卡以阻礙孕婦入職的情況[12]。此事例中,一項表面中立的要求實際上僅使孕婦群體承擔不利的后果,但有關部門稱自己并無歧視的主觀故意。這是典型的間接歧視的例子,但運用現有的男女平等或禁止基于性別歧視的原則,較難證成歧視的存在。由此可見,平等原則之外,我們仍需要界定什么是歧視。
(二)預防歧視需要明確的歧視定義
2020年中國提交給消歧委員會的第九次定期履約報告稱中國“按照《消歧公約》對性別歧視的全面定義,通過法規政策性別平等審查機制,嚴格審核相關規定內容,確保已經制定的法律條文、行政法規、規章制度和規范性文件不存在歧視婦女的規定”(20)See Ninth Periodic Report Submitted by China under Article 18 of the Convention,CEDAW/C/CHN/9,15 December 2020,para 17.。預防、阻卻存在于法律、法規、規章及規范性文件中的制度性歧視是法規政策性別平等評估機制的核心要義。而包含直接歧視、間接歧視、揭示和識別制度性歧視的“對婦女的歧視”的全面定義,將為各地評估機制準確檢視政策法規中存在的歧視婦女問題提供一把“標尺”。
實踐中對婦女的制度性歧視集中指向就業領域的一些保護性立法和和教育領域的某些限制措施。在就業領域,《勞動法》《就業促進法》對“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的一般原則作出例外規定:“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除外。”《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明確列舉了適用于所有女職工的禁忌從事的勞動范圍。這些以保護女性為初衷的立法,因為“忽略了女性群體的不同就業意愿和個體之間身體素質的差異”而實質上產生了限制婦女職業選擇權的效果[13](P 129)。對一項限制權利的規定,不應作擴大解釋。因此所謂“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應嚴格限于《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明確列示的范圍之內。不僅如此,國家還應當參照科技知識,定期審查保護性法律,必要時加以修訂或廢止(21)這是《消歧公約》第11條第3款關于工作權對締約國提出的要求。。否則,不必要的強制性保護不僅會將婦女排除在特定的工作或任務之外,還會使“婦女是需要保護的對象”的消極刻板印象更加根深蒂固[3](P 399)。
在教育領域,《教育法》第37條第2款確立了“保障女子在入學、升學、就業、授予學位、派出留學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的一般原則。然而《婦女法》第16條第2款對這一原則作了除外規定:“學校在錄取學生時,除特殊專業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取女性或者提高對女性的錄取標準。”可以說這一規定為教育領域限制婦女權利打開了方便之門。2012年教育部對何謂“特殊專業”作出解釋,具體包括與特定職業要求緊密相關,且職業對男女比例有要求的專業,如軍事、國防、公共安全類專業;從保護女性的角度,適當限制女性報考,如航海、采礦等專業;個別招生數量有限且社會需求有一定的性別均衡要求的專業,包括部分非通用語種專業、播音主持專業等[14]。顯然,這幾類“特殊專業”已超出女職工禁忌從事的勞動范圍,是對婦女受教育權的不合理限制,卻成為有關部門和個別學校限制婦女受教育權的依據。例如2003年,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和司法部法規教育司聯合印發一項提前錄取專業招生辦法,明確六所政法院校提前錄取專業錄取女生比例每校不超過本校招生數的15%(22)教學司[2006]16號,《中國政法大學 西南政法大學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華東政法學院 西北政法學院和中央司法警官學院提前錄取專業招生辦法》2003年3月11日,第9條。。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教育部答復人大代表的一段話具有典型性:“男生和女生在專業選擇上確實存在差異,這是男女生理差異所致,不僅中國如此,世界各國概莫能外……我們認為這一現象無可厚非。”(23)教建議[2017]第259號,《教育部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39號建議的答復》,2017年9月21日,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ghs/201801/t20180116_324806.html,2021-06-20。
由上可見,職業性別隔離已經從就業領域延伸至教育領域,并通過法律和政策的形式加以固化。限制婦女權利的性別刻板印象被認為理所當然,現實中存在有關部門行歧視婦女之實卻不自知的情況。究其原因,仍在于缺乏包含對婦女基于社會性別的歧視的全面定義,缺乏明確的歧視認定標準,導致在立法者、執法者中出現了諸多認識誤區,從而侵犯到婦女的合法權利。如果有歧視婦女的定義,性別平等評估機制將更可能在事前或事后的審查中識別出并剔除法律政策中歧視婦女的規定,從而阻卻實踐中發生歧視婦女的問題。
(三)救濟歧視需要全面的歧視定義
由于欠缺全面的歧視定義,不明確歧視的構成要件和判定標準,一些明顯的性別歧視事件無法獲得應有的司法救濟。
2005年11月,周香華訴中國建設銀行河南省平頂山市分行強制女職員55周歲退休案開庭審理。在這起要求男女平等享有同齡退休權的勞動爭議案中,原告周香華主張,被告中國建設銀行平頂山分行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況下僅僅以原告系女性,年滿55周歲為由,自行終止與原告訂立的勞動合同,而對相同條件的男性職工則可以繼續聘用至60周歲,此種做法致使相同條件下女性職工早于男性職工5-10年退休,違反了中國憲法第四十八條確立的男女平等原則,損害了原告作為婦女所享有的在經濟領域內同男子平等的憲法基本權利和平等參加及退出工作,即退休的權利,已經構成對婦女的歧視[15]。然而,法院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認為被告根據國務院相關法規為其辦理退休符合國家政策和法規,并無不當。相反“原告認為被告為其辦理退休手續的決定違背了憲法關于男女平等的原則,要求予以撤銷的理由無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16]。此案中,雖然《憲法》《婦女法》等位階在國務院行政法規之上的法律都規定了“男女平等”原則,但是審判機關并不認為原則性規定可以成為審判依據,由于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什么是“對婦女的歧視”,很大程度上導致法院認為原告的主張“無法律依據”。
司法實踐中,由于對構成性別歧視是否需要有主觀故意的認識不一致,致使受害人難以獲得有效救濟[17](P 48)。此類問題的出現同樣源于法律無全面的歧視定義,導致司法者沒有勇氣處理間接歧視問題。
(四)履行人權保障義務需要定義歧視
在國內法中對歧視婦女作出定義是《消歧公約》對締約國履行人權義務的具體要求。《消歧公約》第2條(b)項明確規定締約國承擔“采取適當立法和其他措施,包括適當時采取制裁,禁止對婦女的一切歧視”。中國作為《消歧公約》的締約國,有義務通過立法和其他適當措施,禁止對婦女的歧視。中國現行法律體系未明確賦予《消歧公約》以國內法上的直接效力,因此該公約中的歧視定義能否被國家機關和個人直接援引以主張權利是不明確的。一般認為,中國通過制定國內法的形式落實《消歧公約》的各項規定(24)1992年《婦女法》出臺之際,全國人大關于《婦女法》制定的必要性的說明中明確指出“制定婦女權益保障法,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履行的國際條約義務”,因為《消歧公約》要求“各締約國根據本國情況,制定法律,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的發展與進步”。參見鄒瑜:《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草案)〉的說明》,1992年3月27日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而明確何謂“對婦女的歧視”,是締約國履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的義務的前提。出于切實履行國際法律義務的考慮,中國有必要在國內法中對歧視作出定義。
四、國內法如何定義對婦女的歧視
(一)比較法上的歧視定義
首先,“歧視”定義是各國、各地平等法或反歧視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為消除對婦女的歧視、促進性別平等,不同國家或地區制定了專門的性別平等法或反性別歧視法,或是將性別歧視的規定寫入一般性的平等法或反歧視法中。例如,英國《2010年平等法案》在第二部分將“歧視”作為平等的關鍵概念詳加規定(25)See UK Equality Act 2010 (Chapter 15),part 2,Chapter 2。。中國臺灣地區制定的《性別工作平等法》專為保障工作領域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而制定,其第二章專門規定“性別歧視之禁止”。澳大利亞制定專門的《性別歧視法案》,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性別歧視條例》,皆是直接從反歧視的角度進行立法,兩部法律都對什么是歧視作出詳盡規定。2018年生效的挪威《平等和禁止歧視法》在第1條明確:本法旨在促進平等、預防基于性別、懷孕、與分娩或收養有關的休假、照料責任等事由的歧視;并在后續條款中對直接歧視、間接歧視、基于懷孕,分娩、哺乳等事項的合法的區別對待以及法律允許的積極的區別對待作出規定(26)See Norwegian Equality and Anti-Discrimination Act,entry into force on 1 January 2018,articles 1,6,7,9-11.Available at https://lovdata.no/dokument/NLE/lov/2017-06-16-51,last visit on 20 June 2021。。可見,不論法律的名稱是“平等法”還是“反歧視法”,“歧視”都是一個繞不開的、需要明確界定的核心概念。
其次,通常而言,各國、各地的立法在定義歧視時,都包含直接歧視、間接歧視以及實現平等的特別措施等要素,有些立法還專門對懷孕、哺乳等基于母性的歧視作出界定(27)See UK Equality Act 2010 (Chapter 15),Articles 72-76;Australia Sex Discrimination Act 1984 with Amendments through 2013,Articles 7,7AA.另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性別歧視條例》(第480章)第5-8條分別定義了對婦女的性別歧視、對男性的性別歧視、對已婚等人士的歧視、對懷孕女性的歧視,并在第6部對歧視的一般例外情況做了具體列舉。。例如,芬蘭《男女平等法案》(28)Finland Act on 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 (609/1986;amendments up to 915/2016 included),unofficial English translation provided by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Finland.Available at https://finlex.fi/en/laki/kaannokset/1986/en19860609_20160915.pdf,last visit on 20 June 2021。第7條明確規定“基于性別的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均被禁止”,緊接著對直接歧視、間接歧視及不構成歧視的情形作出規定。根據該法,基于性別的直接歧視是指:(1)基于性別區別對待婦女與男子;(2)以懷孕或分娩為由區別對待某些人;……。基于性別的間接歧視是指:(1)通過一項看似不分性別的規定、標準或做法來區別對待某些人,但該舉措的效果是人們實際上可能發現自己處于基于性別的不利地位;(2)基于父母角色或家庭責任區別對待某人。該法第9條列舉了不構成歧視的行為,包括因懷孕或分娩對婦女的特別保護;以及旨在促進有效的性別平等以及旨在實現本法目的的有計劃的暫行特別措施。
眾多立法實踐表明,不論是對歧視的一般性界定還是對“歧視婦女”或性別歧視的專門界定,《消歧公約》的歧視定義是重要的立法基礎和指引。同時,各國通過修法不斷豐富并廓清歧視的具體情形以及不屬于歧視的情形,為實踐提供具象指南。
(二)中國國內法關于“歧視”的立法現狀
中國國內法傾向于從平等角度規定婦女地位,多部法律法規規定了“男女平等”原則。一些地方性法規在規定性別平等評估機制時使用了“性別平等”的概念,但未作界定。相當一部分法律法規使用“婦女與男子平等”“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等短語闡明在享有具體權利方面男女平等。如《憲法》第48條規定,“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勞動法》第13條規定,“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農村土地承包法》第6條規定,“農村土地承包,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
同時,中國法律中不乏禁止基于“性別”作出區分的規定,如《憲法》第34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性別……,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個別法律法規使用了“性別歧視”的措辭。如《廣告法》第9條規定,廣告不得有下列情形:“(九)含義民族、種族、宗教、性別歧視的內容。”
不論是婦女與男子平等的規定還是不因性別而受到歧視的規定,都沒有給“歧視”下定義,更沒有一部法律法規采用“對婦女的歧視”這一用語。
目前,現行法律體系中僅有一部地方性法規——《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對“性別歧視”做了定義。根據該條例第5條:
本條例所稱性別歧視,是指基于性別而作出的任何區別、排斥或者限制,其目的或者后果直接、間接地影響、侵害男女兩性平等權益的行為。但是,下列情形不構成性別歧視:
(一)為了加速實現男女兩性事實上的平等而采取的暫行特別措施;
(二)基于生理原因或者因為懷孕、分娩和哺育,為了保護女性而采取的特別措施;
(三)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這一定義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消歧公約》的歧視定義以及該公約第4條對不構成歧視的特別措施的規定。但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將歧視的后果規定為“影響、侵害男女兩性平等權益”,不夠準確和周延。其中“影響”是一個中性概念,并不一定是一種否定性判斷;再者將落腳點放在“男女兩性平等”而非婦女的合法權利,易于忽略婦女的獨特經歷,難以實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的目標。其次,將“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作為不構成歧視的兜底條款,實際上擴大了不構成歧視的情形范圍,這會潛在地豁免隱藏在法律法規中的制度性歧視,從而阻礙實現實質上的平等。
盡管如此,這一地方性法規的開創性探索為制定全國性法律積累了有益經驗。鑒于該條例的適用范圍僅限于深圳經濟特區,仍需在法律層面確立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歧視婦女的定義。
(三)《婦女法》宜以《消歧公約》為藍本定義歧視
世界范圍內歧視婦女問題的普遍性使《消歧公約》第1條的歧視定義獲得了普遍接受。截至目前《消歧公約》共有189個締約國,沒有一個國家對第1條提具保留(29)參見聯合國條約數據庫網站(treaties.un.org),統計截至2021年6月20日。。事實上,《消歧公約》提供的只是最低標準的保護,根據該公約第23條,締約國的法律或已對締約國生效的國際條約如載有對實現男女平等更為有利的規定,其效力不受該公約任何規定的影響。有鑒于此,在中國國內法尚欠缺歧視定義的情況下,《消歧公約》的定義應當成為優先參考的藍本,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例也為中國法律定義歧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豐富經驗。盡管公約中歧視定義的各要素在當下中國的語境中都能找到相契合的例證,但是中國法律在定義歧視時仍需結合中國國情、語境及立法技術進行適當的本土化。
《婦女法》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全面保障婦女權益、促進男女平等的基本法律,可以說該法在事實上扮演著中國男女平等基本法的角色,因此是規定對婦女歧視的恰當載體。目前,該法第2條對男女平等及消除對婦女歧視的一般原則作了規定:
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
實行男女平等是國家的基本國策。國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婦女權益的各項制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
國家保護婦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權益。
禁止歧視、虐待、遺棄、殘害婦女。
該條雖然明確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的基本原則,但是沒有規定什么是對婦女的歧視,致使這一原則很難落地、落實。只有明確了什么是歧視,進而消除歧視,才能實現實質上的男女平等。考慮到明確歧視定義對于實現平等的重要意義,又鑒于“歧視定義”已經成為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性別平等法或反性別歧視法的必備要件,中國《婦女法》對歧視作出定義是必要而適當的。
除欠缺對歧視的定義外,當前《婦女法》第2條各款均有完善空間。第一,第1款“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的措辭帶有明顯的形式平等的傾向,有以男子為標準來界定婦女權利的范圍之嫌,可以考慮借鑒《消歧公約》中“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這一用語。此外,“享有”權利的表述不夠全面。“享有”只是表明一種資格和機會,而實現實質平等需要在事實上有機會、有能力“行使”權利。第二,第2款“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的措辭顯然限縮了《消歧公約》對締約國“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采取一切適當措施”的義務要求,亦無法應對歧視婦女問題的頑固性和消除這一歧視的緊迫性。第三,第3款“婦女的特殊權益”一語由于其用詞的籠統性,未能限定“特殊權益”所涉的具體領域,易給人以婦女享有“特權”的印象,不利于促進男女平等工作的開展。第四,第4款中禁止“歧視”與第2款重復;“虐待、遺棄、殘害婦女”指向人身權利等具體權利,宜在分則中加以規定。第五,作為總則中的核心條款,第2條除應對歧視作出定義外,也應對不得視為歧視的特別措施作出具體規定。
有鑒于此,參照《消歧公約》定義歧視的幾項核心要素,在借鑒比較法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本文建議將《婦女法》第2條修改為:
1.男女平等是國家的基本國策。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和行使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家庭生活的及任何其他方面的權利。
2.國家采取一切適當措施,完善保障婦女權益的各項制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禁止:
(1)任何法律、政策或措施基于性別作出區別、排斥或限制,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依法享有或行使各項權利;
(2)或者,任何法律、政策或措施雖然沒有明確基于性別作出區分,但其施行會產生妨礙或否認婦女依法享有或行使權利的后果。
3.國家采取特別措施,依法保護婦女與生育相關的特殊權益。
4.國家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采取的暫行特別措施,不被視為歧視。
五、結語
2020年10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紀念北京世界婦女大會25周年高級別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保障婦女權益必須上升為國家意志”,“我們要消除針對婦女的偏見、歧視、暴力,讓性別平等真正成為全社會共同遵循的行為規范和價值標準”[18]。這一講話表達了中國政府消除對婦女的歧視、促進性別平等的堅定意愿和決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再次強調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促進男女平等和婦女全面發展的目標,為修改完善《婦女法》提出了新要求。2021年4月1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明確將修改《婦女法》納入2021年度立法工作計劃[19],為完善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提供了重要契機。
解決什么是對婦女的歧視,是消除歧視、實現平等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步。借此次修法之際對“歧視婦女”作出符合中國國情、滿足國際義務要求的全面定義,是增強《婦女法》的可執行性和實效性的必要步驟,將為實現男女在事實上的平等和婦女的全面發展提供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