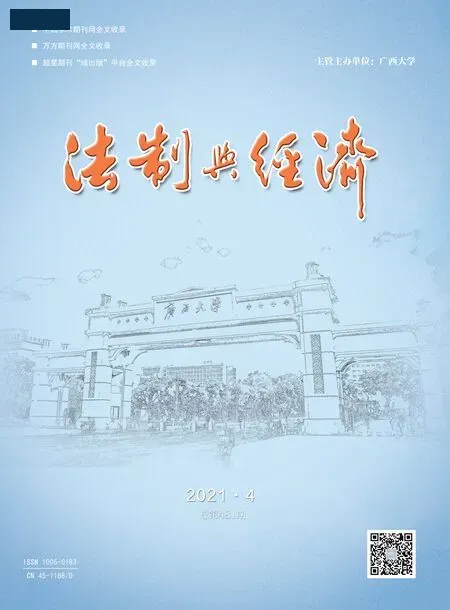過度維權與敲詐勒索罪之界分
王一帆
關于消費者維權索要天價賠償的行為究竟屬于民事范疇還是構成刑事犯罪在理論界頗有爭議,司法實務界也出現“同案異判”的現象。天價索賠案之所以存在罪與非罪的認定困難,原因在于其與通常的敲詐勒索案有著較大的差異。天價索賠案中,被索賠人通常有錯在先,并且索賠行為本身也是消費者在行使權利,是一種正當行為,僅是數額超出了社會一般人的觀念。筆者認為,僅有正當的權利基礎并不當然免罪,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要回歸構成要件本身,當過度維權行為符合敲詐勒索的構成要件時,刑法便有必要介入。
一、過度維權行為與敲詐勒索罪之定性
消費者過度維權并不是標準的法律術語,通常指消費者在與商家發生違約或侵權糾紛時,消費者企圖通過媒體曝光、網絡傳播負面信息等方式向商家索取超出應得賠償以外的高額賠償的行為。過度維權案件之間又有細微區別。如黃某向華碩公司索賠一案中,黃某僅受到了財產損害,但以揭發事實為由相威脅,黃某未憑空捏造新的事實。而李某峰向今麥郎索賠一案中,李某峰夸大并捏造了自己的損害事實。一般而言,對于夸大或捏造損害事實的案件認定為敲詐勒索罪并無太大爭議,理論界爭議較大的是黃某一案,故筆者也主要討論此種類型的過度維權案件。
消費者過度維權一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消費者享有權利基礎。權利基礎包括事實基礎和法律基礎[1]77。事實基礎即消費者與商家確實存在相應的合同或侵權糾紛,如若消費者捏造或過分夸大不存在的侵權事實,則沒有事實基礎,自然也沒有權利基礎。法律基礎即針對糾紛,法律明確賦予了消費者行使權利的資格。二是維權手段的脅迫性。在過度維權案件中,消費者并非通過向法院起訴、請求消費者協會協助等方式進行維權,而是通過私力救濟的方式進行,且手段并不符合平等、溫和的社會觀念,反而帶有一定程度的脅迫性,即向媒體曝光企業的負面信息,或通過網絡發帖等方式將信息快速傳播等。三是權利內容的不確定性[2]44-45。根據權利內容能否確定,權利可以分為權利特定和權利不特定。權利特定即行為人行使權利的內容是特定的,數額也是被法律明文確定下來的。而權利不特定則是指法律賦予行為人相應的權利,但未對權利的具體內容、具體數額作明確規定,當事人之間通常也未提前約定,是可以協商的。在消費者維權案中,雖然法律規定了相應的懲罰性賠償,但對賠償數額的上限未作規定,故過度維權案中權利的不特定是其一大特點。
根據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構成該罪,需要符合兩個標準:一是行為人對他人財物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行為人采用威脅或脅迫手段,且對方因其手段產生恐懼心理或心理強制。若過度維權行為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且沒有違法阻卻事由,應當認定為犯罪。根據消費者過度維權行為的特點,理論界對其是否構罪也爭議頗大。英國學者Williams率先將這種現象總結為敲詐勒索邏輯“悖論”,即兩個白色(合法行為)相加卻得到黑色(犯罪)結果[3]57-58。當下我國實務界對此問題也存在較大爭議。關于過度維權行為能否構成敲詐勒索罪,可以從非法占有目的之認定、手段行為的脅迫性認定、過度維權是否具備法益侵害性之認定等方面進行。
二、非法占有目的之認定
(一)非法占有目的否定說
否認消費者過度維權構罪說一般認為消費者索賠是具備權利基礎的,具體數額取決于當事人之間的協商,屬于意思自治范疇,不能因為數額較大便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張明楷教授認為:“因為行為人的手段與目的均具有正當性,至于賠償數額,則取決于雙方的商談[4]1018。”熊琦教授認為法無禁止即自由,純粹的乞討行為都有合法的可能性,漫天要價這種有權利基礎的行為不應認定為非法[3]。且敲詐勒索罪作為財產犯罪,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說是通說。在財產類犯罪中,例如盜竊罪、搶劫罪等,數額較大或巨大僅僅是量刑情節,并不以其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若僅僅在消費者過度維權的案件中用“數額巨大”來認定非法占有目的之存在,缺乏理論的一貫性,不應當認定索賠數額與非法占有目的之間具有直接聯系。
(二)非法占有目的肯定說
認為消費者過度維權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的學者肯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即消費者的巨額索賠遠遠超過其實際損害,可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尤其是在當事人并無人身損害僅有財產損失的情況下。例如上文案例的黃某,其電腦價格僅為2萬元,卻索要500萬美元的巨額賠償,明顯超出其受損數額,應認定為非法占有目的。陳子平教授認為此種行為可以成立恐嚇取財罪[5]。
消費者維權本質上是民事維權行為,而民法中的損害賠償請求權遵循填平原則,即無損害則無賠償,這也符合民法基本原則之一的公平原則。民法雖未禁止高額索賠,但也不意味著對巨額索賠持保護態度。刑法中的財產犯罪,非法占有目的一般是指行為人對他人的財物并沒有合法權利,卻希望排他性地占有,屬于行為人的主觀內容。我國司法實踐也持此觀點:李某峰一案一審判決便認為被告人索要的數額明顯超出其可能實現的債權范圍,且手段系脅迫手段,不具有社會相當性,應當認為被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①河北省隆堯縣人民法院(2015)隆刑初字第258號刑事判決書。。
維權行為屬于不特定權利的行使,法律沒有明文禁止高額索賠,認定行為人所求賠償是否具有合法權利,在司法實踐中對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并無統一標準,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兩點進行判斷。
1.通過客觀事實推定主觀心態
在財產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采取“推定”態度在當前已經普遍存在。我國2019年發布的《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將惡意制造違約、藏匿證據等行為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001年發布的《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議紀要》[6]也通過某些典型行為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例如財產隱匿、抽逃資金等。在消費者過度維權中,部分消費者對法律不了解,對于自己能獲得多少合理賠償可能并沒有明確的認識,由于“無知”而提出天價索賠并不能當然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非法占有目的屬于行為人的主觀內容,經常存在行為人誤以為自己的行為具有充分的權利基礎之情形。在司法實踐中,可以根據索賠者采取的行為手段、雙方的交涉過程等進行判斷[1]。在交涉過程中,若行為人愿意平等、理性、合理地協商,其索要數額和行為方式必然符合社會相當性,即在一般人標準所認同的范圍內。雖然法律對賠償數額沒有上限限制,但根據社會一般理念也具有一定的“度”和“量”[1]79。通過與經營者充分磋商以及對過往相似案例的了解,行為人對于自己索賠的數額是否明顯超過社會一般觀念所認同的標準,應當有所認識。此時若行為人依然堅持索要巨額賠償,則對超過其應獲賠償以外的數額,可以推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非法占有目的之舉證責任倒置
因消費者過度維權所行使的是不特定權利,造成實體權利的大小難以認定,有學者指出可以通過舉證責任倒置的程序設計來認定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2]45。維權行為本就是民事行為,在民事訴訟中遵循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當消費者索要巨額賠償時,應當就巨額賠償的合理性承擔舉證責任。若行為人對巨額賠償無法做出有效證明,但又堅持要求經營者償付的,可認定其對他人財產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上文提及的黃某一案中,無論是通過客觀行為推定主觀心態,還是通過舉證責任倒置,黃某都沒有合理理由來支撐其500萬美元的巨額賠償要求,故應當認定其具備非法占有目的。
三、手段行為的脅迫性認定
向媒體曝光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中的脅迫行為,也頗具爭議,其本質在于合法的手段行為能夠成為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理論上主要有肯定說和否定說兩種。
(一)脅迫手段否定說
否定說學者認為,消費者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采取多種方式進行維權,向媒體曝光并未被法律禁止,甚至是法律賦予消費者的權利,只要曝光內容客觀真實,不存在捏造、歪曲或夸大事實的行為,便屬于正當的維權手段。持此觀點的學者有陳興良教授、柏浪濤教授等。陳興良教授認為此種情形下,雖手段不正當,但屬于事出有因,可以主張索賠權,不應認定為財產犯罪[7]。柏浪濤教授認為若恐嚇手段僅是向媒體曝光,是能夠為社會所容忍的,具有“相當性”,不應認定為敲詐勒索罪[1]78。否定說學者認為雖然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列舉的五種維權方式中并無媒體曝光,但此種方式作為私力救濟也是法律所允許的,其作為一種中性的維權手段,在性質上與向法院起訴、向消費者協會投訴等并無區別,不具有任何違法性。
除上述理由外,也有學者以手段行為不具有法益侵害性來論證其合法性。敲詐勒索罪侵害的法益是被害人喪失個人意志自由下的財產損害,故個人意志自由的喪失或減損是構成敲詐勒索罪的必要條件。但有觀點認為,向媒體曝光等合法手段行為并沒有減損被害人的選擇,反而給被害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故該行為非但沒有侵害法益,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保護與提升了法益[3]58。類似的觀點還有區分“脅迫”與“開價”。敲詐勒索罪中的“脅迫”以刑事犯罪為標準,與日常商業談判中的開價有所區別。如何區分脅迫和開價,諾奇克提出了底線理論:“若行為人的提議使得他人可期待的處境變差了,該提議就是威脅;若該提議使得他人可期待的處境變優或至少沒有使他人的處境變差,該提議就是開價。”[8]140在消費者過度維權中,向媒體曝光本就是消費者的權利,即便經營者不支付任何對價,消費者也可以實施該項權利,“不曝光”并不是經營者應有的期待結果,故消費者以曝光相威脅并未使經營者的處境變差,其行為應定性為開價,而不是敲詐勒索罪中的脅迫。此種觀點本質仍認為曝光行為并未增大法益損害,故向媒體曝光的行為不能認定為敲詐勒索罪中的手段行為。
(二)脅迫手段肯定說
反對過度維權行為構罪的觀點指出,由于維權行為的目的和手段行為均為合法,故不能構成刑事犯罪。但在敲詐勒索罪中,當前大部分學者認為手段合法并不排除敲詐勒索罪的成立。黎宏、劉明祥、張明楷教授均持此觀點。張明楷教授認為:“……此外,并不要求惡害實現的自身具有違法性。例如,行為人知道對方的犯罪事實,以向司法機關告發進行脅迫勒索財物。盡管向司法機關告發是合法的,但依然成立敲詐勒索罪[4]1018。”向媒體曝光本身是合法的中立行為,但法律賦予公民這一權利的目的是揭露企業的不良問題,維護廣大消費者的權益。此權利并不是財產權利,也不具有財產性質。而行為人行使這一權利已然違背了該項權利設置的初衷,使曝光行為成為向企業施壓的工具[9],目的不是為了維護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非法占有。當合法行為因為非法目的而失去合法性時,完全可能觸犯刑法,構成刑事犯罪。在過度維權案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向媒體曝光,說明行為人行使權利并不是為了“維權”,而是借此做要挾以獲得巨額賠償,本質上是一種脅迫行為。但也有學者對此觀點進行了反駁,認為脅迫與非法占有目的本就是敲詐勒索罪的兩個獨立構成要件要素,脅迫在于行為對被害人的意志進行了壓制,這種壓制與目的無關。但在上述論者的邏輯中,脅迫成為依附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要件[8]143,割裂了實行行為與法益保護之間的關聯性[10]。
筆者認為,采取向媒體曝光的手段做威脅,嚴重程度已構成敲詐勒索罪中的脅迫。即便具有合法的權利基礎,但對權利的濫用和主觀要素的超過,已經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當今社會,媒體的傳播速度較快,范圍較廣,對商家聲譽造成的影響較大,足以對企業產生強制效果,完全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筆者認為消費者過度維權要求巨額賠償的行為,應認定為敲詐勒索罪,司法實踐中之所以存在將其認定為不構罪的案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當前入罪態度的謹慎,以及法理上對非法占有目的、脅迫手段的認定困難。
四、對過度維權行為不構罪的觀點反駁
(一)過度維權行為不具備民事合法性
贊成過度維權不構罪的觀點認為目的和手段行為都正當,應屬民法調整范圍,刑法不應介入。且依據法秩序統一原則,民法上具有權利基礎或民法保護的行為,刑法不能認定其為犯罪,否則便侵犯了我國的法秩序統一。而消費者過度維權要求巨額索賠的行為是否屬于民法的保護范圍,筆者持否定態度。筆者認為,消費者過度維權索要巨額賠償,已構成民事權利濫用,民法不再保護。
民事填平原則是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基本原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懲罰性原則是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例外,雖然民法并未規定索賠數額的上限,但不代表民法要無限度地保護消費者的巨額索賠。索賠是消費者具有的權利基礎,在民法保護范圍內行使權利,自然不構成刑事犯罪,但超出民法的保護范圍,則會構成民事權利濫用,完全有可能成立刑事犯罪。關于權利的行使是否符合民法中的民事權利濫用,我國《民法典》第132條規定了禁止權利濫用原則。關于民事權利濫用的認定,王澤鑒教授認為,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構成權利濫用,而違反比例原則便可以認定為違反誠實信用原則[11]。梁慧星教授認為,當行使權利故意使他人合法權利受損時,構成權利濫用[12]。上文案例的黃某因微小的民事損害向華碩公司索要巨額賠償,并以媒體曝光手段相威脅,企圖使華碩電腦公司遭受巨大財產損失,應當認定為民事權利濫用。民事權利濫用的情況下,自然不受民法保護,其行為若同時構成刑事犯罪,則不可以法秩序統一為說辭阻卻犯罪的成立。
(二)索賠數額可協商之反駁
以索賠數額可協商來反駁巨額索賠案不構罪,缺乏說服力。若因為索賠數額可協商便可不構成敲詐勒索罪,則可以反推敲詐勒索罪是不可協商的。但實際上典型的敲詐勒索罪中,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仍可以就數額進行協商,雖然法律未明文禁止巨額索賠,但也沒有持保護的態度,屬于民事意思自治的范疇。筆者認為,不能僅因民法沒有明文禁止,便認定其一定是合法的,其中存在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間。巨額索賠是否合法,應當取決于相對人的態度。若經營者答應了消費者的巨額索賠,應當認定為當事人之間達成了合意,即雙方約定了合同,該約定可以使其具備民事法律的合理性,依據私法自治原則,索賠是合法的。倘若經營者拒絕了消費者的巨額索賠,則雙方沒有達成合意,除此之外也無其他的合法性依據,故其索賠是不受民法保護的。協商要在雙方自愿、平等的情況下進行,而通過媒體曝光強制對方同意巨額索賠,不符合協商的基本條件,此時的“可協商”成為空談。故不能僅僅因為索賠數額是可協商的,便認定消費者提出的任何巨額索賠都是合法的,是否合法,取決于消費者的提出方式,即是平等的請求還是以脅迫手段壓制,同時取決于經營者是否是自愿真實地與消費者訂立合法有效的賠償合同。
(三)不具備法益侵害性之反駁
否認過度維權構罪的學者提出,向媒體曝光的行為并沒有對經營者造成法益侵害,因經營者對不曝光并沒有期待可能性,故該手段行為不構成敲詐勒索罪的客觀要件。對此有學者提出可從經濟法的角度來理解消費者維權。消費者維權的經濟法基礎不同于民法基礎,經濟法的特征偏向于社會公共性,強調整個社會即市場經濟的整體秩序,與民法的個人本位、私權至上、意思自治有所區別[13]51。故消費者權益法除維護消費者個人權利之外,還維護宏觀的、整體的公平交易秩序。有學者認為消費者索賠的權利來源是經濟法意義上的社會公共秩序特別是公平交易秩序,反之,消費者索賠的邊界也應當是這一社會公共秩序,若消費者索賠破壞了了社會公共秩序,可以被認定為權利濫用,當然具有法益侵害性[13]51-52。
五、結語
綜上所述,不能僅將消費者過度維權行為評價為一般的民事糾紛,其非法占有目的和脅迫手段已經對經營者構成了極大的威脅,維權行為已演變成另一個侵權行為。不能僅因為維權“事出有因”和手段行為合法就將其置于民事法律的“保護圈”內,以非法目的而為的權利行使同樣不具有合法性。在個別過度維權案件中,其索賠數額之巨大及脅迫手段之強烈,已經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對他人合法權益造成了損害,刑法應當及時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