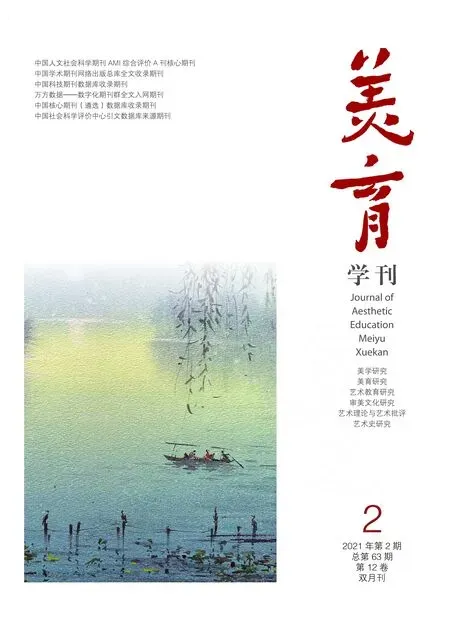《海上樂事》的“另類”敘事及其意義
顏景旺
(中國藝術研究院,北京 100029)
近代以來,上海作為較早被迫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頻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促使其職能發生了深刻變化,一躍成為國際性的大都市。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這一標志性的節點與地域備受關注,尤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層面,更是熱議話題。西洋音樂作為“西學”的有機構件,在這種獨特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傳入,繼而導致“新音樂”的崛起。在音樂史學界,20世紀90年代就已有學者意識到寓滬外僑音樂活動的重要價值,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囿于種種原因,這些研究涵蓋面較窄,呈現出碎片化的研究樣態,僅是聚焦于那些具有典型意義的音樂社團與音樂機構,且在時間維度上,大抵不超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二三十年,缺乏一種從宏觀上、整體上審視“上海開埠”至1910年前后中國近代音樂轉型過程的敘事。
新西蘭華裔學者宮宏宇自1988年起,先后在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音樂學院、奧克蘭大學攻讀民族音樂學、翻譯學碩士和漢學博士學位,之后任教于奧克蘭理工大學、國立尤尼坦理工學院,現兼任寧波大學音樂學院教授、福建師范大學兩岸文化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由于豐富的學術經歷,他長期致力于中西音樂交流、五口通商后西人在華音樂生活、來華西人與中國音樂等領域研究,并取得了豐碩成果。就“晚清樂史”而言,較之既有成果,他的《海上樂事:上海開埠后西洋樂人、樂事考(1843—1910)》(以下簡稱《海上樂事》),無論從切入視角、史料內容、結構秩序來看,抑或從敘事范式、批判立場、具體結論觀之,均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它的出版,不僅使中國近代音樂轉型的歷史過程在大量史實支撐下得以清晰地還原出來,將中國古代音樂與“新音樂”之間長期缺位的歷史鏈條相貫通,更為當下近現代音樂史書寫提供了一種知識范式的參照,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因此,該書一經出版便受到廣泛好評,如美國北伊利諾伊州大學終身教授韓國鐄評價道,“可以想象此書給日后的學者開啟了一條大道。而研究上海樂史,正如研究維也納、倫敦、紐約等藝術重鎮,對于方興未艾的‘上海學’有著無與倫比的刺激,厥功至偉。特別慎重推薦”[1]20;新西蘭漢學家、翻譯家鄧肯認為,“迄今為止,在有關中西這段文化交流與對話的多層面、多取向的研究中,對中西音樂間互動的研究是最欠缺的,更遑論對中西音樂互動有足夠且深入的理解與認識。該書填補了目前研究中的這一空白”[1]25;我國音樂史學家劉再生指出,“該書對于‘晚清樂事’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史學意義和價值”。筆者近讀該書,不揣谫陋,謹以心得記之,就教于方家。
一
一項研究,從啟念醞釀至成果問世往往需要經歷一個層層遞進的探索過程。在音樂史學領域,如果說,對史料的有效搜集、整理、爬梳等一系列規范性操作是檢驗音樂史學從業者的一項基本標準,那么,如何在占有大量史實、文獻的基礎上體現出音樂史學家個性化的理論品格,即對研究對象采用何種史學觀念,應是考驗治史者功力的一個更高要求。一般而言,歷史敘事應包含史料與史觀兩個關鍵要素,二者互為表里。音樂史的書寫,史料并非漫無目的的羅列與堆砌,而是在史觀的引領下有邏輯、有組織、有秩序地整合史料,將史實相對客觀地還原出來,做到邏輯與歷史相統一。宮宏宇的《海上樂事》是一部別具新意的近現代音樂史著作,該著探討的是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寓滬西僑以及來華西人之間的音樂活動。他將研究對象牢牢鎖定在“晚清中國音樂轉型過程”這一特殊時段,敏銳地注意到“晚清”和“上海”作為中國近代文化熔爐的重要作用,試圖將上海置入全球視野的整體觀之下,來關注上海音樂與世界的相互聯系,既注重“他者”對上海音樂文化所帶來的刺激與影響,又關注到上海在吸收、調適“他者”音樂文化時產生的變化。這種內外“互通”的觀照理念,體現出作者的史學智識。
翻閱《海上樂事》,首先感受到的是史料、文獻的翔實與厚重,這從全書的腳注中就能深切地體現出來。有學者說“史學就是史料學”,傳統的治史路徑倡導一種“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即“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故掌握史料的多寡直接決定了“話語”的深度與廣度。《海上樂事》在史料的搜集上可謂詳盡廣博,既含音樂資料,又有非音樂資料;不僅著眼中文文獻,亦聚焦外文文獻。在既往的近現代音樂史著作中,有關晚清西洋音樂活動的論述并不多,這導致了該時段的大量史實長期處于遮蔽的狀態。而宮宏宇在梳理、統籌既往有關上海音樂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史料更多地聚焦于晚清新聞媒體所發行的多種外文資料上,如英文周報《北華捷報》,《北華捷報》日刊版《字林西報》,美國在華的《大陸報》《上海雜記》《上海差報》,法文《上海日報》以及“亞洲文會”會刊《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刊》等報刊、檔案、雜記來掘證西洋人在上海的音樂活動。這些材料是國內多數學者無法看到的“景觀”,它們的開掘與既有成果的匯通,為晚清西洋音樂活動的整體“出場”以及作者所提出的大量創新性觀點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基礎。
在確立史觀并占有大量史料的情況下,如何將這些“自由文本”轉化成“體系性文本”,即采用何種方法將這些史料結構秩序化,涉及一個敘事體例或編寫邏輯的問題。唐人劉知幾曾言“夫有學(史料)而無才(方法),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楠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2],倡導史料要融于方法之中,而方法須化于史料之內。縱觀既有的一些“近現代音樂史”成果,由于文獻局限,研究者僅是著眼于某國、某一人物的音樂活動與典型的專業音樂團體,并未系統地涉及來滬外僑的其他音樂活動,且在敘事體例上多沿用以時間為序、以典型音樂家、音樂事象或作品為內容的編寫模式。而《海上樂事》另辟蹊徑,突破了這種敘事結構,創新性地采用了一種時代加主題或類型的詮釋體系,力在繪制一幅外僑“在滬”音樂活動的多彩勝景。全書九章:上海開埠后教會音樂活動;早期外僑社團演劇中的音樂;寓居上海的外僑業余樂人、音樂組織及其演出活動;來上海造訪的各國軍艦及當地駐軍的音樂活動;寓居上海的外僑專業樂人;“貝多芬”在上海(1861—1899);外來專業音樂家在上海舉辦的音樂會;外來演出團體、歌劇團;寓居上海的西人與中國音樂研究。各章以同一時間流程為經,以主題或類型作緯,在“全景式”年代框架下分主題或類型予以展開敘述。這樣的體例結構不僅能夠使材料有效地服務于各個主題,體現出各自的發展軌跡與特點,還易于集中探討某些針對性的問題。因此,這種體例模式是對以往近現代音樂史書寫體例的一次突破,在敘事范式上給學界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與啟發,具有重要的創新價值與范式意義。此外,《海上樂事》在正文之外,以大量篇幅記述了上海開埠后的音樂大事記以及參考的核心文獻,不僅給讀者了解書中內容提供了便利,還為讀者了解相關學術觀點及深入的再研究提供了必要路徑。
二
《海上樂事》名為“西洋樂人、樂事考”。“考”即考證、推求、研究之義。錢穆在論及“史學”類型時,將其劃為三種:“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一是‘論史’,事實利害得失,該有一個評判。一是‘著史’,歷史要能有人寫出來。”[3]無論“考史”“論史”“著史”均以大量史料為支撐,只有建立在眾多史實基礎上的“考論”才能“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4],以供資鑒。因此,“考”意味著“以史出論”。《海上樂事》不僅是一部音樂敘事著作,其本身還帶有較強的理論價值,具有正本清源的性質。作者所具翻譯學的學術經歷,使他能游刃有余地利用一系列常人難以窺見的史料,其考辨所得之創見,有較強的探索性、前沿性與引領性,將這些所得匯結成典,實乃填補研究空白之舉。
若前述是從《海上樂事》的宏觀方法、范式特色來闡釋的話,以下便是對其具體考證所得某些創見之舉隅。首先,19世紀的教會活動對西洋音樂的引進與傳播具有重要作用。此前研究雖已意識到教會活動之于近代音樂教育的意義,緣資料所限,論述甚少亦欠深入。作者通過梳理認為,在教會音樂教育方面,無論是在“激發中國民眾對西方音樂的興趣上,還是在音樂基本技能的培訓及音樂教科書的編纂上,傳教士都做出了相當重要且具有歷史影響的貢獻。即使是對中國本土音樂傳統的介紹、基礎研究和興趣啟發等方面,傳教士也擔當了先驅者的角色”[1]41。以往,在談及教會學校教育時,一般可追溯至基督教美國長老會傳教士范約翰夫婦于1861年創辦的清心女校。而作者立足史料,認為“上海教會學校的音樂活動似以天主教學校為先。1850年所辦的徐匯公學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系統教授音樂的教會學校”[1]27。值得注意的是,他還對傳教士與其他外國人在華音樂活動的性質與目的進行了區分:“從傳播對象來講,他們所面對的是中國的民眾而不是自己的同胞。這無疑有助于西樂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傳播。從傳播目的來講,他們的音樂活動是為了更有效地傳播基督教義,而不像其他外僑那樣純屬自娛。”[1]41
其次,晚清西洋軍樂隊的在華問題一直是近現代音樂史學者所樂道的命題。既往研究主要聚焦于上海工部局樂隊以及赫德、袁世凱的樂隊,較少提及來滬造訪的各國軍艦及當地駐軍的音樂活動。實際上,早在1880年北洋軍樂隊組建前,中國就已有多國列強軍樂隊出現,且在實際功能、音樂曲目、面向群體等方面與前者不盡相同。列強軍樂隊“除了承擔儀仗之職外,還參加當地外僑的各類音樂活動,并且都有意識地通過音樂來凸顯本國的文化……早在19世紀50年代初,……軍樂隊就已開始為外僑劇社演劇活動和寓滬西人社交舞會提供音樂伴奏……舉辦音樂會……為各類慈善或公益活動募捐……就音樂曲目而言,……不僅僅是儀仗進行曲、國歌、舞曲,也有大型的宗教儀式音樂、歌劇選曲、序曲等……也不乏德奧作曲家的經典作品。……外國軍隊所奏的音樂雖以租界外僑為主要對象,……特別是宗教儀式性音樂,……中國的信眾也得以耳聞目睹”[1]105-106。此外,學界一般將1885年赫德組建、訓練的軍樂隊視為晚清西式軍樂隊的起源。其實,教會學校在進行器樂教學時,就已成立過軍樂隊:“徐匯公學可能是最早教授器樂的教會學校:……蘭廷玉神父根據人們的愛好辦了一個樂隊,從法國運來了銅鼓、喇叭等樂器……”[1]29這些都突破了先前研究的局限,使在滬的各國軍樂活動得以系統展現。
再次,出于需要,在滬外僑的演藝活動亦多姿多彩。關于演藝活動,《海上樂事》將其分為演劇、聲樂、器樂、歌劇,并劃分出業余與專業兩種性質。更難得的是,作者基于史料還對各國演藝團體的水平進行了評判。有關西僑劇社演藝活動的研究,過往一般將1866年成立的“愛美劇社”視為中國現代戲劇的開端。而作者指出,早在1850年就已有所謂的“新皇家劇院”,并成功地上演了劇目,反響熱烈:“上海最早的演出劇社出現在洋涇浜以北、李家廠以南的英國租界……,在1850年……就有一幫英國人戲劇愛好者將一個廢棄了的舊倉庫改為臨時舞臺,將之堂而皇之地命名為‘新皇家劇院’。在同年12月12日……‘成功地’演出了兩出戲。”[1]44在眾多業余演劇與歌詠團體中,他還據當時樂評記載從側面突顯了德僑較高的演藝水準,如“當晚雖然天公不作美,寒風襲人,但沒有保暖設備的蘭心大劇院仍座無虛席……對德僑演員的演技之高贊美有加”[1]59,“在滬的西僑業余音樂社團中也不乏水平比較高的業余歌唱團,特別是德國僑民的音樂組織”[1]79。
除業余樂人、團體演出外,在19世紀50年代,也有歐美專業音樂家抵滬舉辦音樂會。“最早的音樂會是在1856年9月19日舉辦的。……由來訪的法國音樂家阿里和上海當地的業余樂人一起舉辦的”[1]176;有關中國近代史上首場以職業鋼琴演奏家演奏的音樂會,既往將其定位于1874年抵滬的英國女鋼琴家戈達德,其實“早在1859年2月22日,順卜恩就與寓滬的西僑音樂愛好者一起,在‘新皇家劇院’舉辦的一場音樂會”[1]180。以蘇伊士運河通航為標志,來滬獻藝的專業音樂家逐漸增多,尤其是戈達德、克勞斯、孔特斯基等享有國際聲譽的音樂家在滬舉辦音樂會的實例,從音樂視角反映出:上海至19世紀末,就已確立了國際大都市的地位,成為西人音樂會巡演的必選之地。或許是西樂外來刺激所致,研究者更多關注于“他者”的影響,并未從接受美學角度來關注中國觀眾對來訪劇團演出的反應問題。其實,隨歌劇活動的開展,20世紀初中國觀眾就對歌劇表演產生了濃厚興趣:“《孽海花》的作者曾樸對法國作曲家作品……的耳熟能詳……上海音樂會發起人張若谷的《歌劇ABC》”[1]8等都是力證。上述都是一般研究所忽略的問題。
第四,《海上樂事》還論述了一個饒有趣味的主題,即貝多芬在中國的接受問題。“貝多芬在中國”曾被學者多有論及,其人何時被國人所知、其作品何時在華土首演,一直是中西方音樂史學者共同關注的前沿話題。就目前所見,有關“貝多芬在中國”大都遵循廖輔叔所提出的以“李叔同1906年在《音樂小雜志》刊登的貝多芬炭畫像和他三百余字的《比獨芬傳》為起點”[1]151,而作者以周密的史料對《比獨芬傳》之前,貝多芬作品在上海演奏的“史前史”進行了細致考證。他以十年為單位,詳述了貝多芬各類音樂體裁在滬的演出情況。其中,最能彰顯價值的就是確證了“貝多芬在中國”的具體時間。他認為“貝多芬在中國”最早應歸功于1861年來滬的專業音樂家羅比奧。“在1861年12月26日,來上海巡演的意大利小提琴手阿高斯逖瑙·羅比奧和上海當地的愛樂者一起舉辦了一場音樂會。……音樂會以貝多芬早期(1792—1796)創作的《降E大調三重奏》開始”[1]152。之后,貝多芬的作品如室內樂、鋼琴奏鳴曲、小提琴協奏曲等體裁相繼在滬演出,演奏主體既包括寓滬專業、業余樂人和教會學員、學生,還有赴上海巡演、享有世界盛譽的頂級音樂家。
與其他主題性質不同,《海上樂事》最后還涉及寓滬西人對中國音樂理論的研究。除傳教、娛樂之外,寓滬西僑中亦存有許多對中國音樂深感興趣并利用業余時間來研究、翻譯音樂理論的傳教士與任職人員。他們對中國音樂頗為了解,研究內容主要涉及中國古代樂論、傳統音樂理論、中國民間樂器等,為近代中外音樂理論交流做出了貢獻。作者通過文獻既詳述了這些譯書的具體內容,還對他們如何翻譯及其對中國音樂文化所持的態度進行了闡釋。如麥都思翻譯《書經》,為保留原貌,采用直譯法,“即每個漢字或詞后緊跟著英譯,關鍵詞輔以詳細的腳注”;裨治文的《中國文獻錄釋》“每頁分三欄,左邊是英文翻譯,中間是漢字本文,右邊是羅馬字母廣東話拼音,在下面的注釋中則附有詳細的解說”;帥福守的《論中國人的記譜法》載“中國有一種很可尊重的記寫音樂的體系的存在。這種體系與希臘人用的那種體系相比,也毫不遜色”[1]251;慕阿德在《中國音樂》中說“與當時大部分西人對中國音樂充滿鄙夷的完全排斥相反……。‘我們絕不能用我們的標準來評價東方’”[1]274。這些都體現出寓滬外僑在音樂研究上所持的“去歐洲中心論”之意識,高揚著一種文化“多樣”的理念。總之,寓滬外僑對中國音樂理論的研究有著較高的歷史與學術價值,亦為海外漢學研究提供了寶貴史料,至今仍常被引證。故這些珍貴的史料遂成為近代中西音樂理論方面存在互動的有力印證。
三
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領域,對上海工部局樂隊的研究無疑是備受關注的焦點話題。鑒于目前有關上海工部局樂隊的研究已多有成果問世,故《海上樂事》并未“循規蹈矩”,“除討論前人所未涉及的細節外,將不重述其成立過程”[1]9,把目光投向了工部局公共樂隊創建初期的歷任指揮,這為我們了解工部局的早期發展與歷任指揮的專業水準、管理理念提供了珍貴史料。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敘述的五位指揮,即雷慕薩、維拉、斯坦伯格、瓦蘭扎、柏克,在行文體例上并非平鋪直敘,而是靈活地采用了一種“音樂傳記”式寫法,并在敘述每位指揮之前在標題中都給予他們頗為中肯的總結與評價,如“租界早期音樂活動的靈魂人物”“最令工部局失望的指揮”等。
“傳記”是一種文體形式,亦是一種歷史方法,有自傳與他傳之別,在史學與文學領域頗為盛行。“傳記”重視人的主體地位,系在每個歷史人物名下記述個人事跡。因此,其是以“個人生命歷程為主線,記述和描繪個體一生的經歷、作用和貢獻”[5],從而透視出某一時代的社會內容。那些較好的傳記作品,既關注人物的生平、事跡,又注重人物心靈和思想的表現,從而上升到一種傳評或傳論的層次,誠如培根所言“如果傳記的寫作能夠在表現某個人物時運用審慎的思考和判斷,并把該人物的大小、公私行為融為一體,那么該人物就必將能夠獲得更加真實、更加自然、更加生動的表現”[6]。作為一種撰史形式,傳記體在中西方都有深厚的歷史傳統,如司馬遷《史記》、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都是早期的典范。傳記體進入藝術領域最早似從美術領域開始,文藝復興時期的美術史學家喬爾喬·瓦薩里于1550年出版的《意大利藝苑名人傳》就是一部記述意大利13至16世紀的美術家列傳集成,涉及200余位藝術家與作品,被公認為西方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美術史著作。較之瓦薩里早了近千年的中國唐代畫家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亦采用這種體例,收入自軒轅起至唐會昌元年(841)近400位畫家的小傳,以時代為序,分等級列之,包括姓名字號、籍貫生平、擅長、著述以及前人評論與作品著錄等。相對于其他領域而言,“傳記”介入到音樂范疇尚晚,直到18世紀真正意義上的“音樂傳記”才得以興起,后來受19、20世紀各種方法與觀念的影響,“音樂傳記”的內容才逐漸豐富起來。
“音樂傳記”與音樂史關系密切,亦可被視作音樂史書寫的一條路徑。在既往的近現代音樂史著作中,“以人為本”的傳記體寫作除了詞典中的“詞條”、為代表性音樂家或音樂學家專門立傳的著作以及音樂史中涉及某個典型音樂家的貢獻之外,還有一些對某位杰出音樂人物的音樂創作、音樂研究、音樂活動、音樂思想等進行深探的研究型文章也會涉及“傳記體”的高級要素,即凸顯出對研究對象的評或論。雖然傳記是近現代音樂史中一種常用的文體或方式,卻亦有流弊,即純粹的傳記式寫法會有失客觀,對真相有所遮蔽,缺乏在更大的時空中對音樂史呈現的音樂風格、音樂精神以及音樂家與作品淵源的全面揭示,同時亦可導致一件史實被割裂且同一史實被不斷重復的現象。事實上,任何文體都存在某種缺陷,但其中蘊含的某些合理性方法值得借鑒。《海上樂事》在許多地方都滲透了“傳記”要素,尤其在第五章對寓滬外僑專業樂人的論述中。作者對工部局樂隊早期歷任指揮的敘述,并非嚴格按“傳記形式”以生卒經歷鋪陳,而是擷取人物來滬之后與在工部局樂隊任職期間的這段“特殊”履歷予以展開,為所述專題服務。換言之,在工部局公共樂隊這個團體的維系下,將音樂有關的人事關系置于這個特定的歷史空間,從歷時性的角度來記述歷任指揮在工部局樂隊的任職情況及其組織、開展的音樂活動,可避免傳記形式在共時層面的弊端,即割裂同一史實并不斷重復的現象。在記述的具體層面,從整體觀之,雖然每位指揮來滬與任職經歷大體按時間的連續性來進行,但作者不落窠臼,巧妙地以人物的主要“事跡”作分類,依時間序列予以展開,即先歸納再演繹,遵循“以史出論”的原則,呈現一種“事跡專題”的“總(歸納)—分(時間序列的史料支撐)”模式。在這種原理下,宮宏宇依據史料對每位指揮的專業能力、組織能力、管理能力、薪酬待遇、在職貢獻及其曲目風格偏好、樂隊編制調整、樂隊改革、離職原因等方面進行了細致的描述與闡釋,充分地將他們來滬、任職期間的一系列音樂活動清晰地展現出來。綜上,在大力倡導深挖傳統人文資源并對其進行現代性、創新性轉化的當下,在音樂史中靈活地運用“傳記體”要素并將其創新性地內化于材料之中以服務所論之主題,應是值得大力倡導與大膽實踐的。音樂史的書寫模式不僅需要多元化的發展,同時這種體例還應是融合性、綜合性的,即綜合多種體例來服務于敘事需要,以便將音樂史的內容更好地“出場”,將它們在所論主題中得到合理的利用、歸置與闡釋。《海上樂事》作為一部“音樂主題史”,其模式結構也就為這種“多體”敘事提供了較大的張力與空間,具有靈活性與包容性的特征。
四、結 論
21世紀之初,“重寫音樂史”的思潮席卷了中國近現代音樂史領域,這場對近現代音樂史基本原理予以自覺反思的集中探討,從最初的“去意識形態化”問題,逐漸轉向了對音樂史料建設、音樂史學觀念、人物評價標準、書寫范式轉換等更具原理與本質意義的方面。因此,對“近現代音樂史上一系列未為人知而又非常重要的歷史事實進行梳理,對已有的歷史研究成果中被歪曲的歷史事實進行重新整理”[7],如何從研究方法與知識范式的視角來思考“重寫音樂史”的問題并將之敘寫成著,便成為音樂史學界孜孜以求的共同學術使命。從新世紀伊始至當下的20年間,從數量上看,有關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著述可謂洋洋,內容豐富。而細觀之,從學術觀念與書寫范式的層面不斷變換視角來超越前人的成果仍問世較少。《海上樂事》以“音樂主題史”的獨特面貌出場,是一部從音樂史觀與敘事范式的反思層面來展開敘史的佳作,既是對“重寫音樂史”思潮來反身學科發展的一種積極回應,更是探索音樂史學方法論與書寫范式的有力踐行。其次,在目前中西文化交流層面的整體研究中,有關中西音樂互動的探討尚顯薄弱,尤其是關于“中國近代音樂轉型過程”的整體敘事更是長期游離于中國音樂史的主流敘事之外,尚無人深入挖掘。宮宏宇以其特殊的學術背景,另辟蹊徑,運用晚清新聞媒體等一系列“另類”史料,將該時段被歷史長期遮蔽、忽略的眾多史實較為客觀地再現出來,修復了中國古代音樂與“新音樂”之間長期斷裂的時空橋梁,具有重要的“補缺”與“去蔽”意義。其基于“前沿史料”在具象敘事與考證研究當中所提出的新創見,改寫了前人囿于資料所定論的某些史實,彰顯出厚重的學理價值。其三,鑒于上海自近代以來的特殊地位,有學者從音樂視域出發,將上海音樂視為一個專門的學術研究領域,提出了“音樂上海學”的概念,即“以城市音樂人類學為依托的一個特定城市音樂研究的地方性知識的體系化、結構化、學理化研究”[1]16。《海上樂事》作為“音樂上海學叢書”之一,屬該學閾的一項基礎性研究,其上述價值對于方興未艾的“音樂上海學”而言無疑在較大程度上促進了它的建設與發展。此外,洛秦在闡釋“‘音樂上海學’所面對的問題及其思考時”指出,“大多數近現代音樂史論的20世紀40年代之前的內容很大程度上是上海音樂史,但單獨以上海音樂為內容的編年史至今尚未出現”[1]13-14。上海城市音樂文化研究作為一項極具價值的區域音樂社會研究,對其編年史的撰寫理應被納入當下的研究議程。而《海上樂事》中的豐富史料與后面的“上海開埠后音樂大事記(1943—1910)”為上海音樂文化編年史奠定了良好基礎,值得參考、借鑒。當然,任何敘事體例都有其不足之處,《海上樂事》亦概莫能外,但本文意在將該書的價值鉤沉出來,以供學界資鑒。總之,《海上樂事》的學術價值是多方面的,愿這部著作能在讀者的思想中起到更大的“發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