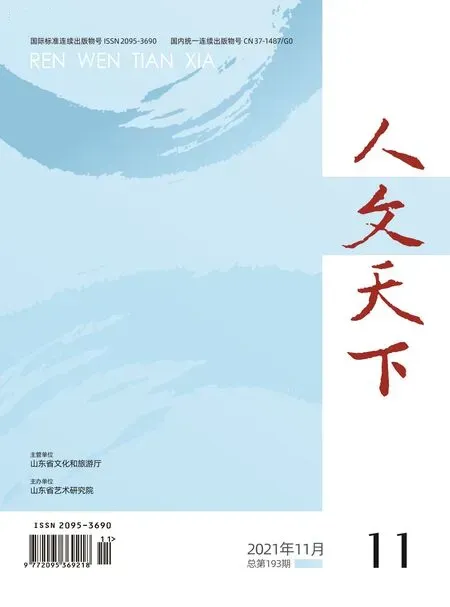回歸本體,讓小戲“小”起來
——觀第十二屆山東文化藝術節小戲展演有感
■孟 璇
小戲作為戲曲的分支,因短小精煉、形式靈活廣受歡迎。近年來,隨著專業院團對小戲創作的日益重視,涌現出一大批新創小戲作品,這些小戲劇種豐富、內容多樣,為戲曲繁榮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在第十二屆山東文化藝術節上,就有專門針對小戲設立的新創作品評比展演(以下簡稱“藝術節小戲展演”),共有12 個劇種的18 臺小戲分4 場先后亮相。此次展演是山東全省范圍內第四次新創小戲作品的集中展示,總的來說,相較過去既有可喜的成績,也顯現出若干不足。
一、追溯小戲源頭,看題材選擇
追溯小戲的源頭不難發現,小戲最早來源于民間的歌舞和說唱,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因此,小戲從形成之日起,就帶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反映的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或表現對命運的抗爭,或抒發對勞動的熱愛,或詠嘆對愛情的向往。可以說,小戲真實、深刻地記錄了人們的喜怒哀樂,甚至積淀了我們的民族文化,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里,小戲題材選擇上的自由和靈活遠遠優于“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的正統大戲,正因如此,它受歡迎的程度之高和施展魅力的能力之大也尤其明顯。當然,伴隨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革,小戲也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如封建教化、統治導向、政策宣傳等,流傳廣、出新快的特點似乎使小戲更容易迎合諸如此類的題材內容。到了今天,小戲所承載的內容早已超脫出單純的情趣娛樂,而是更多地被賦予了明確的思想主旨。
此次藝術節小戲展演最為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題材扎堆、過度關注熱點,扶貧作品幾乎占了一半,以“新農村建設”“青山綠水”“紅色故事”“抗擊疫情”等熱詞為題材類型的作品又占據了另一半,小戲題材的豐富性大打折扣,幾個作品連著看下來觀眾興趣索然,不禁要問:小戲到底要表現什么樣的故事?小戲應該怎樣選擇適合的內容?這其中縱然受當下創作導向的影響,有其他因素的干擾,但藝術創作者要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從小戲的源頭尋找答案。
以四平調《公雞過壽》和山東梆子《清澈的愛》為例。四平調《公雞過壽》用公雞過壽這個荒誕的故事表現村長整治隨禮陋習,人物不多,事件集中,風格是輕松幽默的,語言極具鄉土味,舞臺上演得雖然夸張,觀眾卻感覺親切。山東梆子《清澈的愛》描述了邊防戰士英勇戍邊的故事,有精彩打斗的武功展示,有感人肺腑的母子情、戰友情,有不同時空的轉換,有斗爭激烈的場面,但觀眾看戲有游離,雖有震憾卻較難入情。其實,無論移風易俗還是歌頌英雄,都是值得寫的好題材,關鍵在于以何種形象立上舞臺。
小戲創作當中的題材選擇,首先要正確認識小戲的“小”,這不單單是指不超過30 分鐘的容量,而是要以小見大,并非以小載大。《公雞過壽》就講了一個公雞過壽的小事,通過攀比禮金鬧下笑話達到教育目的,有發生、有發展、有高潮、有結果,故事完整又節奏緊湊,與小戲氣質相符,而《清澈的愛》切入點很高,英雄故事的講述很宏大,卻是小戲無法承載之重。由此可見,由戲說理既然是當今創作無法逾越的問題,就需要花些巧思去布局和謀劃,具體到小戲上,多回顧其產生的源頭,找準小戲表達所長,更有助于選取合適的題材。
二、放大戲曲特色,滿足審美需求
在藝術節小戲展演的舞臺上有幾部優秀作品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些戲中有的創作觀念先進,不落俗套;有的作品具有獨特點,讓人過目不忘;有的看下來很是過癮,唱腔夠味道,身段夠精彩。其中就有山東梆子《我們的指導員》和漁鼓戲《鬧婚》。
《我們的指導員》故事情節非常簡單,甚至有些“無趣”:長征路上過草地,老戰士和小女兵互為依靠,在“把指導員留下的‘秘密文件’帶出草地”這一神圣使命的鼓舞下走出了草地。空曠的舞臺,兩個演員,很難想象這個戲怎么演。相反,《鬧婚》的劇情則很熱鬧,一對貧困戶結了婚卻發現因成為一家而少了一份救濟款,村干部提出為他們安排工作增加收入,二人卻因懶惰成性而不愿接受,想通過離婚再得雙份救濟,卻又有感情上的不舍,上演了一場鬧劇。
兩臺小戲劇種、題材、風格各有不同,但都抓住了戲曲特色充分發揮,使其成為閃光點,靠回歸本體增強戲的感染力,牢牢地抓住了觀眾的注意力。《我們的指導員》因勢利導,不演劇情演情境,為“過草地”這個行動設計了一系列的身段,摔撲、翻滾、跪搓,全在程式里表演得恰如其分。熟悉戲曲的觀眾都知道,程式性動作在舞臺上往往代表固定的含義,“什么情境做什么動作”在傳統戲里已成定勢;而新編現代戲則不同,紅軍過草地則更不同,需要一戲一式地去創造,需要根據想象身臨其境地去找手段。于是我們看到,一老一少兩個角色,依靠一根拐棍時而兩相牽引,時而單獨成舞,時而探地前行,時而受挫拋甩,將草地的泥濘難行、危機四伏和兩人之間的互讓互保、互扶互助都表現了出來,讓觀眾跟著戲的情境走,明知這兩個人不是真的在過草地而又愿意相信他們是真的在過草地,完全投入到戲曲假定性里。除此之外,山東梆子高亢渾厚的唱腔也為情境助力,它大氣又細膩、直白又婉轉的聲腔特點用于表現該情境中的頑強、奮勇、信念、絕望等情緒和感情貼切而又準確。
再看《鬧婚》,非遺劇種沾化漁鼓的發掘和恢復是近十幾年出現的情況,沒有人能清楚地說出它該怎么演、如何唱。所幸編劇和導演對這個劇種是熟悉的,他們準確地抓住了小劇種小戲的特點,創作出與之相適宜的人物、情節、身段、表演。比如兩夫妻騎車、結親、悔婚、舍情等細節的處理,特別具有生活化的鮮活感,既是鄉土的,又是清新的,還是貼近時代的。通過看這臺小戲,我們對漁鼓戲的表演特點、唱腔特色認識更清晰了,會不自覺地認為漁鼓戲就應該演這樣的故事,就應該這樣來演故事,體現了戲和劇種的密切貼合。
總之,由戲曲特色發展出來的新創小戲,保留了戲曲韻味和劇種特質,看這樣的小戲不只是“看熱鬧”,還能看出些許門道,提高審美水平。
三、精細藝術創作,提高呈現品相
小戲創作要講究巧思,要好聽、好看、好玩,要“一事一線結構緊湊”,要劇本、導演、演員互相成就。就創作層面而言,小戲確實不小,且戲曲是綜合藝術,從劇本到導演,從音樂到表演,加上音、服、道、效、化,現代觀眾的眼光越來越高,走進劇場的期待也越來越多。但也有一種戲,作為綜合體來說它并不完美,卻能夠給觀眾帶來滿足感,這次藝術節小戲展演上的山東梆子《村口風波》就是這樣的戲。
《村口風波》故事內容并不出彩,疫情暴發,年輕女護士要奔赴一線,娘家媽前來阻攔,與村口值守的公公產生了沖突,最終公公說服了親家,女護士在公公的支持和媽媽的理解下出發了。相信疫情期間有很多類似的作品搬上過舞臺,那為什么這個小戲就能脫穎而出?因為演員,因為“人保戲”。
一個新編小戲的推出,創作意識貫徹始終,作為綜合藝術形式的每個組成部分都需要進行藝術創作。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這里所說的藝術創作區別于簡單的完成呈現,是需要創作者在充分解讀題材故事或劇本文本或導演意圖的基礎上,以藝術的眼光、技巧、手段、方法盡最大可能地完成自己所擔負的任務。如前面所說的《村口風波》,飾演男主角的演員表演水平就很高:他把一村之長在疫情面前的使命擔當處理得舉重若輕,沒有絲毫臉譜感;當看到親家母到來,從最初的躲到被動面對,再到主動說服,他的表演層次相當分明;特別是他規勸親家母的那一大段唱,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聲音控制和情感流露也很得當,內容雖是村長做工作,效果卻像是親戚間話家常,不刻意卻著力,入耳入心。《村口風波》因為這位男演員出色的藝術創作,把觀眾的注意力牽引到戲上,實現了共情。
再說《公雞過壽》,它在呈現形式上的藝術創作體現得更為明顯和全面,比如人形大公雞造型,村長和兩村民的鮮艷服裝,以及滿場流線式的舞臺調度和夸張的肢體動作,處處充滿設計感。更別說《公雞過壽》在劇本創作階段就確保了精巧構思,如地方色彩濃厚的兩夾弦唱腔、明快的表演節奏和喜劇的處理風格,認真對待小戲的每一處細節,進行藝術創作,呈現時必將反饋驚喜。
結語
綜上所述,小戲創作應回歸本體,讓小戲“小”起來。一次評比展演,涌現出幾個好戲并不是最終目的,通過集中展示分析作品的得失成敗,為今后的創作明確方向、厘清思路才意義深遠。小戲從其產生之日起就帶有民間色彩,回溯本源看題材,讓小戲的思想含量回歸“小”是創作根本;把握戲曲特色,找回戲曲之本,讓情趣和意味發出“小”光芒,未必不能獲得審美之樂;藝術追求精細,回到規律端正態度,把創作往“小”處抓提升呈現,讓觀眾更愛這方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