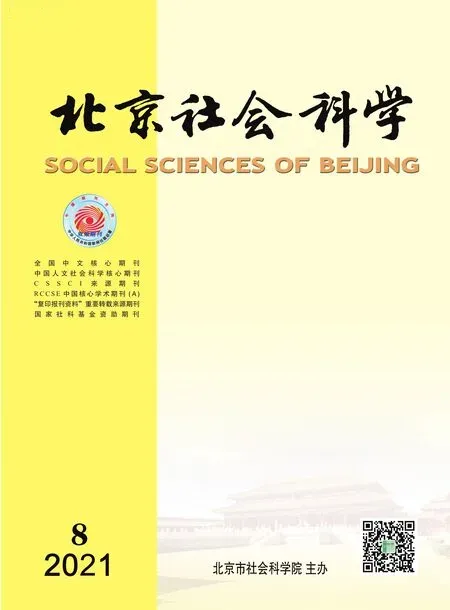近年來鄉村空間研究回顧
林 磊
一、引言
列斐伏爾指出,空間概念在歷史進程中的演變邏輯是從“空間中的生產”到“空間的生產”。[1]近年來,伴隨著中國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大量農村人口流向城市,推動城市規模不斷向外擴張,城市空間日益向鄉村延伸。在此背景下,城市空間結構發生重組,鄉村空間也很難維持其固有形態,而是被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勢能所裹挾,不斷被卷入空間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中。但是,一些研究者仍習慣于從傳統的政治學或組織學分析框架對鄉村進行研究,忽視了空間因素對于鄉村研究的意義。事實上,鄉村與城市一樣,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其不僅僅是人類生活的“場域”和容器,同時也是社會(權力)關系生產和再生產的產物。而伴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城鄉一體化的趨勢愈發清晰,由此,權力、市場、資本這些與空間生產密切相關的要素對鄉村的影響日益深刻起來。近年來,一部分研究者已經意識到空間之于鄉村研究的意義,嘗試將空間理論引入中國鄉村研究中,探尋鄉村治理的空間邏輯,引發了當前中國鄉村研究的空間轉向。但是,作為一種新的分析視角,兼之不同學者對其有不同的研究取向及興趣差異,致使當前這些空間視角下的鄉村研究呈現出不同的形態表征。有鑒于此,本文試圖通過檢視和回顧相關研究,以研究者對空間理論內涵的不同理解及由此形成的對鄉村研究的取向差異為依據,將彼此交織又呈現明顯區別的相關研究歸納為兩種研究類型:鄉村空間變遷的機制與邏輯的研究和多元范式下的鄉村空間研究。并以此為出發點,對近年來空間視角下的鄉村研究文獻進行總結和梳理,以助理解不同空間視角下的鄉村研究在路徑上的差異,同時借此過程對相關研究進行學理上的反思。
二、鄉村研究空間轉向的認知基礎:鄉村空間變遷的機制與邏輯
空間理論是一項以空間為主要分析維度的社會理論,它致力于發掘和提煉空間與權力、資本及權力的運作邏輯之間的關聯性。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就是用時間消滅空間的過程。”[2]列斐伏爾沿襲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經典解析,以社會空間作為概念工具,探尋空間的社會建構意義。他不僅明確指出“空間是一種社會產物”,而且認為社會空間包含著三重主要意蘊,即空間實踐、空間表征和表征性空間。[3]列斐伏爾對空間的三重意蘊的界定強調空間生產的社會性意義。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總結了空間生產的邏輯,即社會性空間的出現是由空間中的生產轉變為空間生產的結果,因此,“空間生產的實質是建構符合人們需要的社會空間”。[4]而這一建構過程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和存續的一種內在機制,正如列斐伏爾所指出的,“統治階級把空間當作一種工具來使用,讓空間服從權力,控制空間,通過技術來管理整個社會,使其容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5]列斐伏爾的論述不僅揭示了空間的社會建構性特征,也啟示我們在研究中需要關注空間同時作為治理資源和治理技術的兩重屬性。基于上述回顧可以看到,空間對于鄉村的意義不僅在于“改造”和“規劃”,而且具有重要的治理意義和價值。空間與鄉村治理之間存在著哪些聯系,相互之間又是如何發揮影響及作用的?這是把空間視角引入鄉村治理分析過程的前提性問題。在此問題意識下,一部分學者認識到空間對于鄉村治理研究之重要性,主要在于鄉村空間在國家轉型期發生巨大變遷,因此,對鄉村空間變遷機制及其邏輯進行分析,不僅是辨識空間在鄉村治理中作用的關鍵性因素,還是透視轉型期鄉村治理變遷邏輯的基礎性條件。循此思路,許多研究者將研究的重心聚焦鄉村空間變遷的過程,期望通過對鄉村空間變遷的內在動力及主導力量的辨析來透視轉型期鄉村空間變遷的機制與邏輯。
(一)鄉村社會空間變遷的主要動力及表現
在很多研究者看來,市場化帶來的社會轉型驅動了鄉村社會空間的變遷。首先,從鄉村物理空間上來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市場化進程引發了村莊物理空間的巨大變遷,在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的背景下,每年都有數量巨大的自然村、行政村消逝。市場推動的工業化、城鎮化使村落空間結構從宏觀上趨向于規模增大、數量減少、錯落密度變化差異顯著,在空間配置中,空心村與一些超級村并存。[6]其次,從社會關系空間上來看,物理空間的巨變與市場的嵌入共同引發了鄉村社會關系空間的變革。市場化促進了農民的理性化,瓦解了過去基于鄉土關系及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公共道德空間、社區政治空間、社區文化與儀式空間等。例如,閻云翔等人的研究表明,傳統的鄉村公共道德空間在市場化浪潮的沖擊下崩潰,破壞了原有的鄉村公共事務處理體系。[7]與此同時,隨著村落精英的外流,村莊公共空間衰敗。[8]此外,造成公共空間瓦解和萎縮的原因不僅僅是市場化所引發的人口外流,人口流入同樣會對鄉村公共空間造成影響,流入的人口難以和本土村民之間共享和共建村莊集體記憶,導致村莊公共空間難以發展。[9]
當然,市場化對社會關系空間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宏觀的公共空間、政治空間等領域,還表現在微觀的人際關系空間中。村莊中家庭關系、鄰里關系等微觀社會關系也隨著市場化產生變革,次級關系取代基于鄉土觀念所形成的初級關系,農民個體趨向原子化,由此,村莊中家庭關系的變化也構成了農村空間變遷的議題。閻云翔通過對東北某村莊的考察發現,市場化驅動的鄉村物理空間變遷引發了家庭內部居住空間的變化,父母與子代之間已經形成分離的私密性空間,這種代際關系變動在空間的投射引發了家庭關系的變化,個體家庭關系的疏離使農民進一步個體化,導致“無公德的人”出現。[7]遵循這一思路,一些研究者也發現,鄉村空間的重構促使農民家庭代際關系發生變遷,如子代外出打工而父代留守家庭,形成了“半耕半工”的撤分式家庭分工空間。[10]
與此同時,市場化所帶來的技術變革同樣引發了鄉村社會空間的變遷。現代交通技術與新型傳播媒介不斷進入村莊,改變了農民的日常生活模式,促進了農民日常生活空間和社會關系空間的變遷。具體而言,大規模的鄉村道路改造以及現代交通設備的進入,促使鄉村生活與消費模式產生了顯著的變化。例如,汽車消費在農村的普及化,給農村社會關系互動與家庭關系造成了沖擊。[11]鄉村空間的消費屬性日益突出,生活空間日益資本化,鄉村空間在消費主義的引導下成為資本增值的工具。[12]現代媒介涌入鄉村,例如電視引發農村社會空間秩序的變動,給村莊人員關系交往帶來了重要的影響,[13]智能手機等媒介也給鄉村生活帶來了多方面的變化,現代技術不僅改變了時空距離,成為農民獲取信息以及與外界聯系的主要手段,而且交流途徑的多樣化也形塑了當代農民新的交往模式。[14]而網絡發展帶來的“空間延展”重構了鄉村公關交往空間和治理空間,為農民交往和互助提供了便利的“虛擬空間”,從而強化了農民在鄉村治理中的主體性。[15]
(二)鄉村空間變遷的機制與邏輯
從推動我國鄉村空間變遷的主導性力量看,其本質上屬于“政府推動型”的空間變遷。這種空間變遷不是“長期自然演進的結果,而是一個壓縮式快速推進和規劃的產物,是一種由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外生轉型”,[16]因此,正如吳瑩所指出的那樣,“在空間敘事的國家視角與地方視角之間,國家的空間邏輯始終居于主導地位”。[17]
與國外發達國家市場主導的鄉村空間變遷不同,在某種意義上中國鄉村空間變遷的主要驅動力來自于政府主導的城市區域擴增,正如李強等人指出的,中國城鎮化推進模式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導、大規模規劃、整體推動。[18]政府經營城市的結果是近郊地區農村出現了大范圍的撤村并居、“村改居”及農民上樓等空間變革現象,而居住空間的變動也影響著村民的社會關系互動、社會關系網絡等社會空間變遷。[19]政府規劃所推動的物理空間變革帶來了治理空間的重構,“村改居”及農民上樓等空間變革中所需的治理模式,在治理對象與治理方式等方面都與傳統的治理存在著較大差別,公共空間的規劃、公共事務的處理以及矛盾糾紛的調解方式都因為空間的變動產生治理策略的變動。[17]
這種政府主導型的鄉村空間變遷,在早期表現為地方政府常常以城市擴張和土地財政的工具性思維來對農村空間進行規劃和開發,這不僅造成了城鄉之間新的不平等,同時還引發了圍繞土地利益為核心的諸多矛盾和沖突。這種現象實質上是一種“空間資本化”邏輯主導下的“非均衡”城鄉空間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20]這種空間變遷在現實中引發的矛盾及其帶來的鄉村治理困境,促使國家在近期從空間角度調整了以往的鄉村治理政策,一方面對城鄉規劃、拆遷補償等方面的相關政策與規定進行了調整和改善,另一方面通過各種“鄉村建設”措施來改善鄉村空間環境與社會關系。但在現實中,這類鄉建工程往往被異化,最終難以獲得預期效果。之所以產生這種結果,一方面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在鄉村建設和規劃過程中行政主體地位過重,在某種陳舊發展思維的支配下,常常在規劃過程中大包大攬,導致這些工程淪為政績工程。[21]任曉莉指出,在鄉村建設及改造過程中,自上而下的行政權力過度干預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會性參與不足,而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績的邏輯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農民的利益。最終,這些建設工程不僅未能達到應有的效果,還造成農民的消極抵制。另一方面則在于,地方政府在鄉村空間改造過程中對作為發展主體的農民意愿缺乏重視和考察。[22]李增元、周平平的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常常以主觀意愿為基礎對鄉村進行空間構造和資源配置,忽略了對農民主體意愿的尊重和考察,導致這種民生工程脫離農民的實際需求,往往難以達到預期效果。[23]
此外,還有部分研究者從空間生產視角指出,在資本下鄉過程中,空間資本化的邏輯主導了鄉村空間重構的過程,鄉村空間變遷淪為隱形的“資本空間的生產”。[24]例如劉林等人通過對銅川市幾個村莊的調查發現,在鄉村的發展過程中,政府、企業和村集體形成了利益聯盟,這種形式形塑了一種“混合經濟下的空間生產邏輯”,導致村莊物理空間改造呈現出混合結構,但在這些結構背后的實質是資本通過“隱蔽”的方式實現了對鄉村空間的侵占。[25]朱靜輝對一個沿海村莊空間改造案例進行分析發現,鄉村空間規劃背后的“土地資本化”邏輯不僅導致村莊社會結構日益分化,還導致部分農民在村莊結構中被“脫嵌”,由此引發了村莊的治理問題。[26]
綜上所述,既有研究已經從多個方面揭示了當代中國鄉村空間變遷的動力機制,為辨識鄉村空間變遷的邏輯及從空間視角建構鄉村治理模式提供了豐富的研究基礎。但是,既有研究傾向于從某一單向維度來解釋鄉村空間變遷的機制,或關注市場或關注政府與資本,并且上述研究多半未能清晰區分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之間的關系。質言之,鄉村空間變遷是多種動力共同推動的結果,不可能僅僅局限于某一單一因素,以上研究只是從某個特定視角展現農村空間變遷的發生過程及其影響,這種碎片化的研究無法從整體上認識當代鄉村空間變遷的邏輯與機制。換言之,要整體透視當代中國鄉村空間變遷的邏輯與機制,必須看到:當代鄉村空間變遷的推動機制來自于市場、資本、權力、技術等多重機制的相互嵌入和融合,在這種嵌入與融合的過程中,“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彼此相互影響與相互型構,共同構成了鄉村空間變遷的內在機制。此外,隨著城鎮化的加速,交通、媒介等技術革新也影響著農民主體的空間認知與空間感知。多重機制共同作用于農民主體,改變與重塑了農民對空間的意義建構,也重塑了鄉村治理的基礎。
三、探尋鄉村治理的空間邏輯:鄉村研究空間轉向中多元視角的引入
如前所述,在部分研究者聚焦鄉村空間變遷機制與邏輯議題的同時,另一些研究者則試圖通過多元理論視角來闡釋社會空間變遷對于鄉村發展的功能與意義,并以此來透視國家和社會在轉型期的行為邏輯與特征。因此,在此思路之下,一些經典的理論范式被引入鄉村研究之中,形成目前鄉村空間研究的多元化特征。
(一)國家—社會視角下鄉村空間研究
作為一種經典的研究范式,研究者將其引入鄉村空間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過對鄉村空間變遷過程的分析來解釋轉型期國家與社會關系重構的基本邏輯。許多研究者注意到在鄉村社會空間變遷的過程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經歷了從“總體性支配到社會化整合”的演進過程。[27]例如,劉擁華從歷時態的視角考察了鄉村空間的變遷史,在將“鄉村空間”視為決定鄉村社會自主性的關鍵性變量后發現,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傳統農業社會空間變遷的停滯性導致了鄉村社會的內卷化。新中國成立后,鄉土空間出現了大規模的空間生產和重組,鄉土社會被國家意識滲透,確立了一個與全國整體上并無區別的政治空間。[28]改革開放以后,鄉村社會空間政治性控制逐漸消退,以市場發育為基礎的草根力量從生存空間向發展空間演變,并在20世紀90年代開辟了新的資本空間。[29]而鄉村社會自主化程度的加強不僅緣于市場化力量的發育和國家權力在鄉村空間中的“退場”,還在于國家正在努力“營造社會”。例如梁晨認為,在當代農村社會治理實踐過程中,鄉村社會空間的拓展是政府與社會共同締造的結果,農村社會空間的自主性成長實質是政府對社會的“營造”。[30]同時,網絡技術的發展也拓展了鄉村社會空間的成長,新的交往方式和治理技術的興起,促進了村莊的“微自治”,網絡技術所塑造的新型治理空間兼具“國家”和“自治”雙重面向,強化了村民的治理主體性。[15]
雖然從歷史的發展階段看,農村社會空間的自治組織與自治理能力正在興起,高度政治化的社會空間逐漸弱化,社會空間呈現出“去政治化”的過程,[31]但是也有研究者發現,近年來在國家社會治理能力加強的同時,國家權力呈現了再度“下沉”的趨勢。[32]一些研究者從政府推動型的“城鎮化”實踐中發現,農村社會空間存在著“再政治化”的現象。王春光通過對“村改居”過程的研究發現,行政力量對農村社會空間的主導性支配是一種“萬能型”能力。[33]鄉村社會空間再政治化的邏輯隱藏在“村改居”的實踐邏輯之中。在“村改居”的特定場域中,社會空間仍然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預與支配,很難獲得自主性,國家與地方政府通過各種形式滲透到農村社會空間中,形成了國家與社會相互嵌入的鄉村社會空間結構。對此,程鵬飛等人指出,鄉村治理應該注重行政領域和社會領域之間的協調和耦合,從而重構鄉村治理的政治空間格局。[34]
(二)日常生活范式下的鄉村空間研究
日常生活實踐,這一由米歇爾·德·塞托提出的概念大大豐富了人們對現實社會活動的理解。按照塞托的理解,人們的經歷、接觸、關系和斗爭構建了空間,空間就是一個被實踐的地點。[35]日常實踐就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吃穿住行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交互行為,人們在空間范圍內的生活實踐構成了農村社會空間的主要內容。因此,在這一分析范式下,有研究者首先注意到居住空間變化所導致的人們實踐行為的變化。例如范成杰等人通過分析農民“居住空間”變化對鄉村代際關系產生的影響發現,“農民上樓”打破了“代際居住空間既有的生產過程和邏輯,代際之間的居住空間受到擠壓,在此有限的空間中形成的剛性結構加劇了代際之間的張力,加深了父代對子代的依附關系”。[36]雷望紅則同樣注意到“撤村并居”后農村居住空間變化所帶來的老年人群體生存狀況改變,即空間商品化導致老年人無力購買居住空間而被排斥到空間的邊緣地帶。[37]從這一研究范式出發,也有研究者看到空間變遷改變了人們的互動實踐形式與內容,從而影響了農民的社會關系網絡與社會資本的運作。具體而言,鄉村人口的外流及村莊改造,導致村莊熟人社會中穩定的社會關系網被破壞,社會互動開始減少,農民交往的空間隔離、鄰里關系淡化。[38]
(三)治理理論視角下的鄉村空間研究
傳統鄉村空間有著相應的穩定的治理機制,通過權力的文化網絡,利用地方性宗族、地緣社會組織以及保護型鄉紳等資源和主體進行治理。[39]這一空間治理模式作為近年來學界關注的熱點理論也被引入了鄉村空間研究。因“治理”范式與社區治理研究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所以,治理理論范式多應用于鄉村社區研究中,特別是“村改居”研究領域,許多研究者試圖通過對鄉村社區轉型過程中各種治理主體的研究來透視城市化進程中社區空間轉型所面臨的治理問題。
一部分研究者從“多元主體治理”模式出發,認為當前“村改居”社區治理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作為多元治理主體的政府與居民在社區空間轉型中的行動邏輯及空間適應出現了問題。具體表現為:基層政府在現實治理過程中主體地位過重與社區居民難以適應新型社區空間。例如,吳瑩的研究發現,在鄉村社區向城市社區的轉型過程中,因為空間形式與內容的變革、空間治理結構與治理方式的變動,基層政府往往通過新的空間網格式管理與原有治理資源相結合的方式來對社區進行治理,但在社區公共事務治理以及社區新的公共空間的生產過程中,作為治理主體的社區居民仍然存在著空間不適應。[17]何艷玲等人也認為,在“村改居”過程中,村莊原有的治理基礎因為空間變動而消退,地方基層政府作為治理主體之一,其行政力量過度介入社區導致轉型后的社區社會空間難以整合,同時,社區空間變動所引發的利益分配矛盾加劇了社區居民之間的分化與沖突。[40]與上述觀點不同,鄭中玉、梁本龍則認為“村改居”社區空間治理問題之所以產生,主要原因在于作為治理主體的地方政府往往秉承一種“線性進化論”式的社區治理理念,導致社區居民空間適應速度落后于社區物理空間的變遷速度。[41]因此,“村改居”社區空間治理的難題不僅在于舊的農村社會空間治理資源在轉型中消解,新的治理模式依賴行政介入,無法有效組織與動員作為治理主體的社區居民,社區居民對現有治理體制無法認同,形成了“過渡性”治理的尷尬處境;[42]還在于在“村改居”過程中基層治理主體過于強調傳統與現代、落后與進步等一系列二元論式的線性治理模式,忽視了地方性空間和知識的多樣性。即,“村改居”社區空間治理問題的產生不僅僅是因為治理資源的匱乏,還在于治理主體理念及行動所導致的“結構性約束”。
與上述側重治理主體的研究不同,另一部分研究者則認為,治理指向的應是如何在鄉村空間轉型過程中建構起合理的空間秩序。例如,黃曉星、鄭姝莉認為空間秩序是村落秩序的一部分,本質上是一種社區道德秩序,是資本、信仰與村治交融互動的結果,空間安排承載了社區秩序再造的功能,因此村落空間的安排與建構才是鄉村空間治理的核心。[43]沿著這一思路,部分研究者將注意力集中于鄉村空間轉型過程中“空間秩序”的重建。例如,呂青的研究發現,由于基層政府過度介入社區治理,導致社區空間難以整合,同時,社區轉型帶來的空間利益競爭加劇了社區治理主體間的沖突和分化,因此,轉型社區的空間秩序正處于一種過渡性形態中。[44]也有研究者認為社區空間失序的根源在于鄉村社會空間解體之后,農民對新的社區空間無法形成有效認同。[45]當然,更多的研究者認為,去政治化后的鄉村社會整合應該通過對鄉村公共空間的重構來實現,鄉村公共空間的弱化是鄉村公共文化弱化的結果和體現,所以,要重構鄉村社會秩序,就要從鄉村公共文化與公共空間的建設等方面著手,[46]“使傳統文化和社會資本成為促進社區空間治理的可動員資源”。[41]
(四)既有研究的述評與反思
既有研究將多元分析視角引入鄉村空間研究領域,為我們提供了鄉村空間轉型與變遷的豐富認知。但總體上而言,這些研究同樣未能徹底厘清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之間的關系,它們或關注鄉村物理空間,或關注鄉村社會空間,導致這兩類空間糾纏在一起,使得研究缺乏足夠的理論穿透力。具體而言,國家—社會范式下的鄉村空間研究雖然注意到隨著鄉村空間的改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正在經歷重構的現實,但沒有深入辨析這種重構究竟是由鄉村物理空間變化所引發的,還是由鄉村社會空間變化所引起的。同時,在國家—社會范式的分析圖景之中,盡管有研究者注意到,國家正在努力“營造”社會,但大多數研究者還是有意或無意地將國家置于社會的另一面,或多或少地將兩者置于一種充滿張力的二元關系之中,導致研究陷入“國家權力下沉”或“鄉村社會自主性呈現”這種非此即彼的勾勒和刻畫中,忽視了轉型期鄉村空間變化的階段性,也忽視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互嵌入性。
日常生活范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國家—社會范式所引發的宏大敘事危機,但同樣未能擺脫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之間的糾纏關系。質言之,在日常生活范式分析圖景之下,既有研究雖然關注到了物理空間變化對代際關系等社會空間的影響,但未能足夠關注代際關系的影響是通過居住條件等物理空間表現出來這一實質。進而言之,在這種分析圖式下,物理空間影響社會空間,而社會空間的變化卻簡單地表現為人所占有的物理空間的變動。所以,雖然相關研究已經呈現了豐富的案例,但其理論啟示和穿透力卻陷入個人或群體占有的物理空間變動表征社會空間變遷的簡單刻畫中,忽視了日常生活的豐富性和社會關系的多樣性、深刻性。
與前兩種范式相比,治理理論范式在本體論預設上屬于實踐論,它將研究重心放在鄉村空間變遷治理實踐過程中的治理主體及治理指向上,由此來揭示鄉村空間變遷治理實踐過程中所展現的種種復雜的、模糊的和不確定的空間關系。從總體性上而言,既有研究雖然發現了基層政府作為治理主體地位過重,忽視了對其他空間治理主體的動員和組織,且在治理目標指向上過于強調秩序,忽視了治理目標多樣性的問題;但是,在這一范式的具體應用中,很少有研究能在鄉村空間治理的敘事過程中從——預先存在空間治理結構條件、空間轉型的時機條件以及各個治理主體行動的偶變性特征——三個層面同時展開,進而通過對復雜的治理過程的描述來理解和解釋各主體在鄉村空間治理變遷中的行動邏輯與機制,同時,對基層政府在空間治理中的政策行為的研究仍然沒有達到“國家和政黨研究的層次”。[47]因此,既有研究只能從“治理資源匱乏”或“結構約束”等方面來闡釋鄉村空間變遷過程中所產生的治理問題,無法從更深層次揭示各“治理主體”的行動邏輯及由這些邏輯所形塑的空間治理機制。
四、結論與討論
綜前所述,近年來空間理論被引入鄉村研究領域,引發了鄉村研究的空間轉向,由于對空間理論的內涵及其應用存在不同理解,形成了鄉村空間研究取向上的差異。但是,在實際研究中,這兩類研究并非涇渭分明,而是呈現出彼此交融的形態。總體而言,鄉村空間應在國家層面通過調整空間政策來實現良性“規劃”,在治理主體層面通過加強基層協商民主來實現“空間公正”,通過公共空間建設等途徑來促進村民空間感知轉型,通過空間治理來實現鄉村共同體的整合和團結,最終達到城鄉空間融合的“善治”目標。這也是諸多研究者的共識。同時說明,鄉村空間研究雖然在取向上出現了類別化的差異,但研究者對鄉村空間變遷與重構目標的理想類型建構在取向上是類似的。
列斐伏爾指出,空間具有社會性,空間彌漫著社會關系,空間不僅被社會關系所支持,也生產著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生產。[48]所以,在筆者看來,鄉村空間研究實質上應是以物理空間為載體的社會空間研究,在這一意義上,無論是鄉村空間變遷機制與邏輯的研究,還是多元范式下的鄉村空間變遷研究,其本質上都是一種基于物理空間變遷的社會空間研究。而社會空間主要由各種社會關系、社會要素所構成,正如李強所指出的,社會空間以物質空間、地理空間為載體,承載了“社會關系、社會要素與社會含義”。[49]但是,社會空間同時又被物理空間所承載和生產,因此,兩者實質上是相互嵌入和相互影響的關系。盡管既有研究選擇了以空間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但鄉村空間變遷涉及理論上的生活空間、制度空間、文化空間及現實中的物理空間。如何建構這些空間的整合框架?只有從兩者“互構與互嵌”的視角出發,才能在分析中厘清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之間的復雜關系。
雖然當前鄉村空間研究呈現了豐富的成果,但總體上而言,這些研究還只是處于理論借用階段,并且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地理規劃等學科領域,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鄉村空間往往只是作為經驗材料來驗證已有理論,未能從不同空間“互構”的視角來闡釋空間的變遷過程,也忽視了鄉村空間重構之于鄉村治理和振興的意義。此外,不同于城市空間研究領域對空間作為治理技術特征的重視,既有的鄉村空間研究往往只注重了空間作為治理資源的屬性,而忽略了其同時作為治理技術的另一屬性。因此,未來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推進鄉村空間研究。
(一)從空間“互構”與“互嵌”的視角來分析鄉村空間變遷
新城市社會學派把空間看作社會空間與物理空間的互構,物理空間限定與制約著社會關系、社會要素,但同時人們感知和調整物理空間以促成互動,互動中人們本身又要與周圍環境與人群相調和,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的互動構成了社會空間的辯證法。因此,研究鄉村社會空間,就要切入到不同空間“互構”與“互嵌”的視角中,不斷揭示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雙重變動之間的影響。家庭居住空間的變動以及村集體物理空間的改造無一不影響著村莊社會空間,同時,社會關系、社會要素的變動也會影響村莊物理空間的型構。因此,只有從不同空間“互構”與“互嵌”的視角入手,才有可能厘清空間概念的多層次內涵,進而明確社會空間融合之于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的意義。
(二)關注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空間
雖然既有研究表明推動鄉村空間變遷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市場、資本等主體,承受空間變遷影響的主體主要是農民,但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既有研究忽視了農民在空間變遷中的空間感知與空間行為,只是關注了鄉村空間的宏觀變遷,極少有研究真正關注空間變遷過程中農民的切身感知與實踐邏輯。例如,在村莊改造或者“撤村并居”的過程中,隨著農民空間居住的變革和原有村落空間的消逝,農民是如何感知空間變遷的意義的,他們對空間變動的社會反應邏輯又是怎樣的?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討的議題。
同時,鄉村空間變遷研究還面臨著“空間正義”的問題,基于現實鄉村空間變遷過程及城鄉空間之間在資本、權力、社會關系等方面存在張力的事實,應如何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城鄉空間資源分配模式?如何改變“村改居”過程中單向度的城市社區建設模式?因此,要實現鄉村空間正義,“消解城鄉空間在資本、權力、社會關系等方面的懸殊,打造一個城鄉平等、共同的正義秩序空間”,[50]在具體的鄉村空間變遷過程中,不僅要尊重農民主體的利益,還需要尊重農民的生活方式與習慣,尊重鄉村社會空間的傳統,而不是簡單地以線性進化的二元思維將城市生活模式移植到鄉村社會中去。這需要國家關注空間作為治理技術的一面,設計出在新發展觀指導下的良性空間治理技術。
(三)提煉鄉村社會空間變遷的中層理論
現代化發展的“中國方案”形塑了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歷程,為創新和推進農村社會空間研究提供了豐富的養分和獨特的資源。如何通過借鑒西方社會空間理論,同時植根中國農村本土實踐經驗,推進具有中國主體性的社會空間理論研究,是當下鄉村空間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既有研究中,極少有研究嘗試從本土經驗材料中提煉出能夠聯系微觀與宏觀的中層理論,即國家、市場與社會等多種力量是如何在鄉村社會變遷過程中相互作用,并進一步影響農村社會空間變遷的?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需要展現“諸力量的斗爭細節及新力量的再生機制”,[47]在此基礎之上,對空間變遷的機制與影響進行提煉與升華,從而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空間中層理論。
總體而言,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鄉村空間正在面臨整體性的變動,從日常生活空間到宏觀的城鄉空間,社會互動、社會關系以及社會網絡與物理空間都產生了變動,兩者之間既相互嵌入又相互影響,共同推動著鄉村空間發生變遷。這種現象之于鄉村振興有何意義?正如吳越菲所言,“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重構一種關系型的鄉村治理體系,其對象不再簡單是‘人’或‘物’,而是涉及城與鄉、本地與全球、人類活動與自然社會系統等不同空間尺度之間的空間關系”。[51]因此,在當前鄉村振興的語境下,如何建構鄉村空間變遷機制的整體性解釋框架,進而探尋鄉村治理的空間邏輯?如何在把握鄉村治理的空間邏輯基礎上,從多學科融合角度出發,制訂良性的鄉村空間重構政策,促進城鄉之間空間的融合?這些問題對于鄉村振興而言意義重大,未來將成為鄉村振興研究領域中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