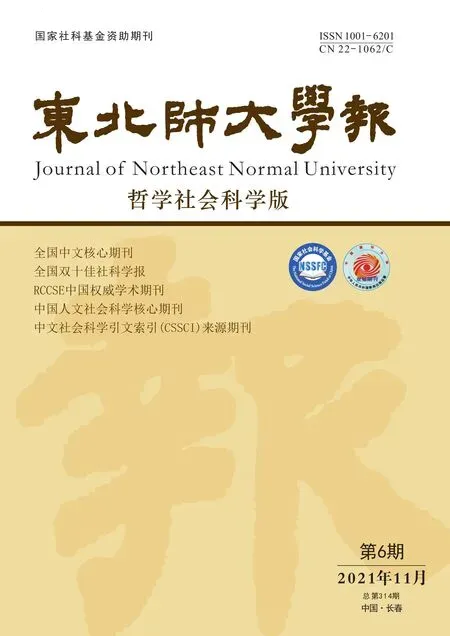漢語復合詞的形象色彩與具象化造詞方式
曹 儒,張道新
(遼寧師范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9)
在有形象色彩的詞語結構類型中,與附加式(如“冷冰冰”)、重疊式(如“嘩嘩”)以及有比喻義的成語(如“藕斷絲連”)相比,復合詞的形象色彩問題要復雜得多。對復合詞的形象色彩,盡管高名凱[1]、劉叔新[2]等許多學者已有研究成果,但仍有需要探討的問題,主要是:“形象”能否全面反映復合詞形象色彩的條件類型?除了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五種外覺還有哪些條件類型?復合詞形象色彩的判斷依據是什么?形象色彩與復合詞詞形、與漢民族造詞方式的關系如何?等等。這些問題不僅涉及復合詞形象色彩的識別,還涉及具象化造詞方式,以及漢語復合詞教學方法設計等問題,所以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文中例詞主要取自《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用例的同音詞、義項的序號與該詞典一致。
一、對“形象色彩”的再認識
(一)“形象”與“具象”
“形象色彩”作為漢語詞匯學和語義學的術語,自高名凱提出以來已使用了半個多世紀。對形象色彩的內涵、表現方式、條件類型以及功能的看法基本形成了共識,不過,仍有些問題值得探討。
1.目前對形象色彩的定義有局限性
對形象色彩的定義,眾家的表述盡管有些許差異,但本質是一致的。高名凱認為,“詞所引起的人們對現實中某些形象的聯想”[1]296;劉叔新認為,“很多詞語除代表一定的對象這種理性意義之外,還同時含有關于該對象的某種形象感,這就是形象色彩”[2];楊振蘭認為,“在詞的形象意義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感性的聯想色彩”[3];黃伯榮、廖序東認為,“具有形象色彩的詞,除了理性義之外,還使人有某種生動具體的感覺,即所謂形象感”[4]。各家都認識到形象色彩的功能是“有助于具體認識事物對象”[2]。這一點不存在爭議。關于“形象色彩”產生的條件則有值得商榷之處。劉叔新認為“詞語的形象感,以視覺形象居多,也有聽覺、嗅覺、味覺、動覺等形象感覺”[2],而邢福義[5]、賈彥德[6]、張志毅和張慶云[7]、黃伯榮和廖序東[4]等也都集中在這五種外覺上,由此可見,最初之所以命名為“形象色彩”,很可能是因為視覺形象居多,至于把其他四種外覺也補充進來,應當是后來的事。作為一個術語,外延擴大而名稱不變本是正常的,然而“形象”在《現代漢語詞典》中釋為“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動的具體形狀或姿態”,這就使得考察條件類型的視野受到限制,除了權威學者列舉的五種外覺,其他“有助于具體認識事物對象”的條件類型似乎很難被考慮進去。下面的幾組復合詞,是否也有這個功能呢?
A.重視 輕視 強化 弱化
B.心疼 心癢 心酸 痛癢
C.暈了 醉了(網絡語言)
D.分寸 十分 萬一 萬眾 顏值 回頭率 重量級
A組中用輕、重、強、弱等運動覺表達事物的性狀、程度等;B組用疼、痛、癢、酸等機體覺表示事物狀態;C組用屬于平衡覺、知覺的暈和醉表達驚訝程度;D組用數量說明程度。這些詞的表達對象都是抽象的,而“有助于具體認識事物對象”的表達效果無疑是存在的。不過,內覺和數量等并不屬于“形象”,因而這類詞事實上已被排除在形象色彩之外,劉叔新、張志毅、周薦等權威學者的文獻中均未見這幾類例詞。如果按照“有助于具體認識事物對象”這個功能來看,“具象”要比“形象”更有概括力。與“抽象”相對的“具象”,在《現代漢語詞典》中釋為“具體的,不抽象的”,所以“具象”與“形象”雖然只是一字之差,卻在對具體感、生動感的概括上有重大差異,不僅能概括目前已有的類型,而且能將內覺、數量等條件類型涵蓋進來,從而使更多的現象得到更合理的解釋。
2.形象色彩與其他附加色彩的地位不同
形象色彩一直被視為與時代、方言、語體、感情等色彩并列的附加色彩。從與理性義的關系角度看,這是無可厚非的,不過就本質而言,形象色彩與其他附加色彩的地位并不平等。原因有二:第一,形象色彩是造詞活動追求的表達效果,而其他色彩則是自然結果。例如,鼠標器的英文名是mouse,中文學名是“顯示系統縱橫位置指示器”,而俗名有內地用的“鼠標(器)”,港臺用的“滑鼠”,名稱雖不同,但不同地區的俗名都追求形象色彩。因此,形象色彩是造詞活動中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追求,是有意而為之的,相比之下,其他幾種色彩則是由時代、地區等差異自然形成的。第二,形象色彩隱含著不同時代、地域的造詞者共同使用的具象化造詞方式,是具象化造詞方式的產物,只要希望“有助于具體認識事物對象”,那么有時代、地域、語體等色彩的詞就必然會采用具象化方式來造,也注定產生形象色彩。總之,形象色彩是在其他幾種附加色彩之上的具有造詞方法論價值的特殊附加色彩。
(二)形象色彩的判斷依據
對于復合詞形象色彩的判斷依據,學界盡管有過討論,但結論并不很明確。復合詞的形象色彩是通過詞形呈現出來的,目的是以“具體的,不抽象的”方式表達抽象對象。因而,構建詞形的語素或整個詞表達的不應是本義而是轉義,即表示對象及其屬性自身的語素或詞均無形象色彩,盡管它們會引起形象聯想,但不屬于形象色彩,而是對事物的心理表象[8]162。例如,“牛皮”指稱一種實體對象時沒有形象色彩,而在“牛皮紙”中則借助牛皮的強度、顏色等特征,能使人產生對紙的質地的具象聯想,這個詞就有形象色彩。同理,“三萬五千噸”與“萬水千山”的“萬、千”,前者表位數,后者則表量大的程度,所以前者無而后者有;“潮流”若指稱“由潮汐引起的水的流動”時則無,若指“社會變動發展的趨勢”時則有。所以,復合詞形象色彩的判斷依據是語素或詞,不是自指而是他指,即不表示對象及其屬性本身,而是以轉義表達其他對象。
綜上所述,復合詞的形象色彩是以具體、生動、直觀的表達為目的進行造詞的結果,只有在語素或詞表達其他對象的某種特征時才產生;條件類型不僅有五種外覺,還有三種內覺和數量等。盡管我們重新解讀了“形象色彩”,但因這個概念已被廣泛采用,所以本文仍然使用,而討論的思路在“具象”上。
二、形象色彩的生成條件是事物的具象性
復合詞的形象色彩是借助語素或詞的所指對象的具象特征而產生的生動、具體的聯想,而產生具象感的條件應具有為語言社團全體成員所共知共識的特征。下面,我們按照這個特征來分析物體、感覺和數量的具象性。由于人對事物的認識、感覺往往有一定的綜合性,因而劃分的條件類型有的相對獨立,有的存在交叉。
(一)物體的具象性
物體包括自然物和人工物,對于人的認識而言是最“具體的、不抽象的”具象性對象。現有文獻列舉的形象色彩條件主要集中于人對物體對象的五種外覺,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對物體及其屬性的認識卻缺乏系統性,以致未能明確提出內在規律和機制。在此,我們著重討論物體名詞和表屬性的詞在復合詞中的具象作用方式,以期找到基本規律。
1.物體名稱與屬性的相指關系
亞里士多德認為,“被認識的東西是作為被某種東西即是被知識所認識的東西來說明的”[9]38。即物體對象是用已知屬性來說明的。此論斷的啟示是:物體名詞與對象的各種屬性形成了一個知識整體,由名詞可聯想到某些屬性,而由表屬性特征的詞可聯想到該對象。在語言上,名稱與屬性的這種關系表現為“名屬相指”的邏輯機制[10]225,即用物體之名表達屬性,或者用表屬性的詞來指物體對象。
借助物體而產生形象色彩的復合詞存在這種機制。第一,用物體之名來特指某屬性。例如,“雪白”的“雪”作為語素并非指雪之物,而是特指其顏色,語素義是“顏色如雪”;“潮流”是“由潮汐引起的水的流動”的名稱,在短語“歷史潮流”中則以潮流的方向屬性比喻“社會變動發展的趨勢”。第二,由表屬性的詞聯想物體對象,進而表達其他對象的特征。例如,“流”表示河水的運動屬性,在“物流、客流”中是以“流”聯想河水,進而產生連續性過程之意;“上、下”表物體空間屬性,而在“上級、下級”中以上、下聯想物體對象的相對位置,進而產生社會等級之意。
因此,由“名屬相指”機制可推導出物體具象性作用的基本方式:物體之名并非指稱對象本身,而是特指某些屬性特征;表屬性的詞并非表達自身,而是通過對物體對象的聯想來表達其他對象的類似特征。
2.物體具象條件的系統性和范疇性
對于以物體充當形象色彩的條件問題,盡管現有文獻已關注,但缺陷有二:一是憑借個人經驗來列舉,缺乏統一標準,張志毅、張慶云列舉了“形態、顏色、聲音、動態、味覺、嗅覺、觸覺”等七種[7]42,而黃伯榮、廖序東列出“形態、動態、顏色、聲音”等五種[4]221;二是僅從五種外覺來考察物體的具象條件,如劉叔新、賈彥德[6]296等,難免缺乏概括性。這兩點缺陷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對物體具象條件的認識缺乏系統性和范疇性。如果以物體的知識系統為參照,那么考察視野會變得開闊一些。
亞里士多德認為,對實體對象的認識存在“實體(即類屬)、數量、性質、時間、地點、狀況、姿態、活動、關系、遭受”等[9]11十個屬性范疇,可概括為“實體—屬性”的邏輯框架。如果以此框架來觀察復合詞的形象色彩與物體屬性之間的關系,就不難發現一個基本規律:物體知識系統中的每個屬性特征都有充當具象條件的可能,并且每個條件都有與特定屬性相對應的范疇性。下面選擇幾種在復合詞形象色彩中表現最明顯的屬性來說明。
第一,狀態屬性,是實體自然呈現的外在形態,主要是通過五種外覺感覺到的。視覺感知到的有顏色、明暗、形狀、聚合態等。例如,“香蕉人”用香蕉的皮和瓤的顏色表達某些西方華裔的心理和文化特征;“黑道、黑幫”用黑暗來表示非法性質;“工字鋼、T臺”用漢字、字母形狀表達其他對象的形狀;“水銀、鋼水”用水的液態屬性表達液態物質。聽覺感知到的有音質、音強、音高、音長等物理特征,如“雷鳴、蜂鳴器”等用雷、蜂的聲音表達其他對象的聲音特征。嗅覺感知到的有香、臭、腥、臊等,如“芳名、臭棋”等用嗅覺表達積極和消極評價。味覺感知到的有酸、甜、苦、辣、咸等,“嘴甜、辛苦”等用味覺表示人或事物的積極或消極特征。觸覺感知到的有冷、涼、溫、熱、軟、硬等,如“暖男、熱情、硬漢、軟著陸”等用觸覺特征表示人或事物的某些特征。
第二,類屬屬性,是指物體對象在知識系統中的類屬。在復合詞中具體表現為用一種物體之名以比喻方式表示其他對象的類屬特征。例如,“水槍、射釘槍”所指不是一種單兵武器而是發射工具的類屬。再如,“心路、思路”所指不是道路而是過程、方式的類屬。
第三,數量屬性,包括物體的長度、面積、體積、速度、溫度、硬度、強度等。例如,在人的觀念中,海洋、天空等有廣大、高遠等屬性,因而海、天等通常被提取出巨大這一數量屬性來造詞,如“海碗、天價”表達碗之大、價之高。再如,“冰冷、冰涼”用冰的溫度屬性表示溫度低的程度。
第四,時間屬性,包括時點、時段、時序。有些物體的時間屬性被提取出來成為造詞的語義材料。例如,古人認為龜、鶴、松有壽長屬性,“龜年、鶴壽、不老松”等即是提取相應物體的時間屬性而造的詞。
第五,空間屬性,包括位置、方向等。例如,“天花板價、地板價”是用物體的相對位置表示價格變化的上下限;“腦海、心地”是用海、地的物理空間來表達心理空間,使記憶、道德、情緒等具象化;“表親、外戚”等用物理方向的“表”和“外”來表達心理空間。
第六,運動屬性,是實體自身的運動方式。有兩種情況:(1)用表物體運動屬性的詞表示其他對象的運動特征。如“客流、物流”是用河水的運動表達其他對象運動過程的連續性。(2)用物體名詞表達其他對象的運動特征。如“水席、水牌”用水的運動表達其他對象的流動變化特征。
第七,性質屬性,是物體因構成元素及其結構關系不同而形成的自然特征。如“骨氣”用骨頭的堅硬表達信念不變的特征;“玻璃心”用玻璃的易碎表達內心脆弱的特征;“皮實”是提取皮革的性質,并以物體之名表達其他對象性質的。
第八,結構屬性,是物體構成元素的狀況。用作為構成元素的物體之名來指稱整體,屬于借代造詞法。例如,“江山”用江、山等指代國家;“槍手、寫手”則用手指代有某種技能的人。
第九,評價屬性,雖非物體本身的自然屬性,卻也是概念內涵的一部分,因而當表達某種評價時也用典型物體之名象征。如,“金貴、珍惜”等的“金”和“珍”有高貴的評價意義,“草民、白菜價”等的“草”和“白菜”有低賤的評價意義。
由上述不難發現:對物體進行系統性和范疇性的認識,能夠為源自物體的形象色彩條件類型展現更寬廣的視野,為條件類型的識別梳理出清晰的邏輯思路,從而避免經驗性列舉所造成的認識局限。
(二)感覺的具象性
五種外覺和三種內覺對于任何身體健全者而言,都有器官功能相同、對刺激反應相同的特征,而這兩方面使感覺獲得了充當具象條件的資格。漢語古今造詞者充分意識到了感覺反應的共性,并用以表達抽象意義。
以劉叔新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形象色彩的感覺條件主要是五種外覺,沒有關注運動覺、機體覺和平衡覺,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形象”一詞以及早期認定的條件類型所致。事實上,三種內覺已經充當了造詞的具象材料。第一,運動覺感知到的是重量、強度等力的特征,對用力大小的感知是人所共識的,因而有具象作用。“重視、輕視、重用、看重、輕而易舉、拈輕怕重”等實質上是利用人對輕重的反應而造的詞。第二,機體覺感知的是饑、餓、痛、癢、酸、脹、麻等,也是人所共有,自然有具象作用。“渴望、渴求、渴盼”等詞以及成語“如饑似渴”,用對無法抗拒的饑渴感來表示程度高的意義;“痛癢”用痛、癢等感覺來表示某些問題;“麻木”用麻痹的感覺表示思維反應的遲鈍。第三,平衡覺是對身體平衡與否的感覺,主要是暈的感覺,目前雖尚未見于復合詞,但在網絡論壇中常用“暈”來表示震驚、無奈等的程度,有具象作用。總之,形象色彩的條件除了五種外覺,理應包括三種內覺。
(三)數量的具象性
數量的具象作用與三種內覺一樣未被關注。事實上,用數量表達抽象的程度意義是漢語作品或造詞的傳統表達方式。就歷代詩文來看,用數量表達程度意義是基本方式,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詩經·豳風·七月》),“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離騷》),“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李白《秋浦歌》),“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木蘭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毛澤東《沁園春·長沙》)。就詞語來看,存在大量表示程度的數量詞語,如,“一再、再三、百姓、萬眾”等復合詞,“九死一生、百依百順、萬眾一心、千恩萬謝”等成語,“十分優秀”“把握十足”“八成會下雨”“萬分焦急”“以防萬一”“百分之百滿意”等自由短語。當代話語也在延續這一傳統,如“爆表”“顏值”“滿意度”“回頭率”“重量級”“輕量級”“幸福指數”“說了N次”等。
數量,作為人最基本的知識和思維能力,量差、比率、度量衡單位以及“極數”都是基本常識,因而對于表達抽象對象有具象化作用。例如,“十分、八成、萬一、百分之百”等是用比率表達程度;“分寸、毫厘、分文、千鈞、千里、萬丈、萬頃”等是用度量衡規制表達程度;“一、三、九、十、百、千、萬”等在漢語中有極數意義[11]112,“一點兒”“十分”“百姓”“千萬”“萬萬”“萬歲”等表達的也是程度。用數量表達程度的成語更為豐富,如“如隔三秋”“九死不悔”“千恩萬謝”“萬死不辭”“九牛二虎之力”等等。總之,數量的常識性質使之在表達程度意義時極易產生具象感,應歸屬于“形象色彩”的條件類型之中。
三、具象性詞形是形象色彩的介質
復合詞形象色彩的呈現,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以部分語素的結構義呈現,二是以詞形整體呈現。
(一)以部分語素呈現形象色彩
這類情況在復合詞的五種類型中均有分布。如:主謂型的“心酸、心硬、心寒、心軟”;動賓型的“遇冷、發燒、揭短、跟風”;聯合型的“強硬、軟弱、痛癢、辛苦”;述補型的“洗白、捧紅、抹黑、搞活”。與這幾種相比,偏正型較復雜,有兩類:(1)修飾限制性語素有具象意義,如“雪亮、重視、流動、暖男、U型管、十字架”;(2)中心語素有具象意義,如“浪花、火柱、思路、腦海、面條、歲尾”等。這些語素的結構義都由本義衍生出來,并由所指對象的特征而使詞語產生形象色彩。在這幾類中,偏正型中的名素的結構義最復雜。名素都有特定的所指對象,并包含著對象的各種語義特征,因而在復合詞中往往呈現出多義性,這個特點影響到對語素結構義的理解和對形象色彩有無的判斷。以“雪”為例。首先,語素結構義不同,“雪亮”表雪的光彩屬性,“雪白”表雪的顏色屬性,“雪糕”表雪的質地屬性,“雪人”則指雪這種物體,四者的結構義迥異;其次,形象色彩有無不同,前三個詞中的“雪”表達其他對象的特征,因而有形象色彩,而“雪人”的“雪”指物體,只產生該物質的心理表象而非形象色彩。
復合詞中起具象性作用的語素,根據具象性義位的固化與否,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有固定具象性義位的語素。有些語素在《現代漢語詞典》中除本義外,還有具象性的轉義義位。首先,有一部分是表物體形態的體詞性語素,如“柱、環、餅、塊、丁、條、片、團、球、珠、丸、板、包、盤、帶、絲、線、網、花”等表示幾何形狀,“散、粉、末、沙”等表示四種固體狀態,“液、水”表示液體,“醬、泥、膏”等表示半固體,“氣、霧”等表示氣體。它們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已經存在獨立的表形態的義位。如:“柱”的“?像柱子的東西”;“環”的“?圓圈形的東西”;“塊”的“?成疙瘩或成團兒的東西”;“片”的“?平而薄的東西”;“花1”的“?形狀像花朵的東西”,“沙1”的“?像沙的東西”;等等。它們充當復合詞語素時可直接引發具象感,如“面條、粉條”可想象到條狀物。其次,還有一部分是表屬性的謂詞性語素,如“白、明、亮、黑、暗、陰、冷、涼、溫、熱、軟、硬、強、弱、韌、皮、脆、甘、甜、苦、辣、辛、澀、香、臭”等。這些詞或語素都衍生了比喻義位。如,“黑”的“?秘密的;非法的;不公開的”,“暗”的“?隱藏不露;秘密的”,等等。像“明白、陰謀、陰通、暗娼、暗號、黑飛、黑社會”等復合詞,都是以光的明暗來表達某種心理狀態或存在方式等意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大、小”的具象性。這兩個詞在充當復合詞語素時,可表示多方面的程度意義,如“大事、小事”表重要程度,“大人、小孩”表成年與未成年,“大病、小病”表嚴重程度,“大雨、小雨”表數量多少,等等。在一定意義上說,“大、小”是具象化表達程度意義的“萬能詞”。
第二類,臨時被賦予具象作用的語素。如“雷鳴、蜂鳴器、柳葉眉、櫻桃口、日光燈、草綠、雪白、冰冷、水席、工字鋼、T臺、鼠標”等,這些語素并沒有固定的具象性義位,其具象性作用是臨時的。對這類語素的結構義的判斷是感受形象色彩的基礎,也是準確理解詞義的前提。例如,“柳葉”包含形狀、顏色、結構等多種屬性,而在“柳葉眉”中的結構義則只表形狀,只有由“柳葉”聯想到柳葉之形,才能感受到形象色彩,并準確理解詞義。因而,前文所述的形象色彩的判斷依據,對這類復合詞尤其有價值。
(二)以詞形整體呈現具象意義
劉叔新認為有轉義的一些詞也有形象色彩[2]。我們同意這種看法,因此不再贅述。我們要補充的是由內覺和數量類語素構成的有比喻義的復合詞,如內覺類的“痛癢、心疼、頭疼、疲軟、麻痹、輕重”等,數量類的“八成、十分、萬一、千萬、萬萬、分寸、毫厘、分文”等,這些詞的形象色彩也十分顯著。
(三)詞的形象色彩的淡化與滅失
毫無疑問,對形象色彩的判斷要借助對詞形語素的理解。然而,如果對語素或整體詞形的本義或基本義不知曉,那么就會無視形象色彩的存在,甚至會導致其淡化、滅失。
我們曾測試過人們對一些詞的形象色彩的感知度。例如,“很潮”的“潮”有時尚的意思;“極”(本字為“極”)用做程度副詞,表示最高程度。不過,絕大多數人不知其理據,自然無法判斷出形象色彩,這就意味著這些詞的形象色彩被淡化,甚至有滅失之象。
導致詞的形象色彩被淡化乃至滅失的原因主要是:(1)人們使用復合詞時往往只使用詞義,而忽視語素義和理據。例如,“渴望、渴求”等只整體性地使用詞義,而對語素“渴”并不在意,這必然導致形象色彩的淡化。(2)一些語素或詞的轉義與本義之間的衍生關系在現代漢語中被割裂。例如,“極(極)”的本義“棟也”(《說文解字》),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根本不提,以致今人難以感受到形象色彩;再如,“企”的“抬起腳后跟站著”之意如今已廢,“企盼、企及”等的形象色彩很可能滅失。因此,復合詞形象色彩感的強弱,與人對詞的形義關系的認識程度有關。
四、形象色彩是具象化造詞的動機和結果
形象色彩本質上與具象化造詞方式相關,這種認識不僅涉及形象色彩這一問題,還涉及漢民族具象化表達方式的問題。在對外漢語詞匯教學中,揭示具象化表達方式對漢語學習者掌握漢語詞匯、了解漢民族的表達智慧等具有重大意義。因而,形象色彩與具象化造詞之間的關系不可忽視[11]。總體上看,能夠產生形象色彩的具象化造詞方式主要有以下五種:
(一)空間化
空間化是用物理空間表達時間、等級、程度、心理等抽象或不易感知的對象。例如,“光陰、時光”等用光影的位置變化來表示時間;“上司、下嫁”等用方位表示等級;“深情、心寬”等用空間量表示程度意義;“天下、海內”用天空下或四海之內的空間表示中國的概念。
(二)物化
物化是用物體特征表達抽象或不易感知的對象。首先,用比喻的,如“耳目、心腹”用器官功能表達人的社會功能,“斷崖式”用斷崖的陡直形狀表達變化的急劇性。其次,用借代的,如“須眉、巾幗、江山、刀筆”等用人或事物的結構元素指代對象的整體。
(三)運動化
運動化是用人的動作和物質運動形態表達抽象對象。首先,以人的運動表達。例如,“徘徊”用人在一個地方來回走,表達事物在某個范圍內來回變化而無更大發展的抽象特征;“收手”用人收回手的動作來表達停止某種行為。此外,“瞬間、彈指、煎熬、負擔、吊打、殺青、收入、下海、上臺、回首”等都是利用人的具體動作來表達抽象的行為、心理、程度等特征。其次,以物質運動表達,“死”“活”表示生物體的兩種運動,被用來表達其他事物的類似特征。例如,“死敵、死黨、死結”的“死”是由“失去生命”的意義衍生出固定、不活動的事物特征;相反,“活1”則表示活動的、可變的、靈活的特征,如“活結、活版、活期、活火山”。其他,如“崩潰、流浪、開關、冷淡、平靜”等的本義都屬于物質運動范疇,它們的轉義義位無疑都有形象色彩。
(四)感覺化
感覺化是用人人共有的感覺反應表達抽象或不易感知的對象。例如,“黎明”是指天快亮了的時段,造詞時以天色的黑暗(即“黎”之義)與明亮并存的視覺狀態稱之。其他的,如“重視、輕視”是用重量感表達人對事物價值的認識程度;“抹黑、捧紅”用顏色表達名聲毀譽行為;“熱情、熱愛”用高溫表達感情程度;“苦悶、郁悶”等用憋悶感表達情緒狀態。
(五)數量化
數量化是用人的數量認知來表達抽象或不易感知的對象。漢民族自古以來對數量認知就十分深刻和普及,因而數量化是漢民族具象表達的傳統方式,不僅詩文普遍使用,造詞也廣泛采用[12]112。如“十分、百姓、百業、千張、萬分、萬幸、萬頃、萬丈、萬向、萬象、萬能”等使用數量結構表達程度,“萬一、八成、顏值、爆表、回頭率、滿意率”等用比率表達程度[13],“分寸、毫厘、分文”等用量詞表達處事的尺度、極小量等。
這些具象化方式,在造詞動機上是為了使抽象對象易于理解,而在客觀上就形成了詞的形象色彩[14]。由此可見,形象色彩既是一種詞的附加義,也是一種造詞方式,更是中華民族反映客觀世界的一種表達智慧。以上的具象化方式都是建立在人人熟知的事物、共有的經驗基礎上的,不僅有利于漢語言語社團的人相互交流,也有利于使外國外族的漢語學習者把握漢語與母語之間的思維異同,從而更有效地掌握漢語詞匯的理據,提高學習效率。
五、結 語
詞的形象色彩在學界被視為詞的附加義,是對詞義認識的深化,但研究的不足也是明顯的。形象色彩問題由于受到“形象”內涵和外延的局限,一方面使條件類型偏窄;另一方面使之在詞匯教學中缺少完整的、機制性的認識。在“形象色彩”的術語下,用具象化來重新解讀,無疑會使研究進一步深化,尤其是從中歸納出的具象化造詞方式,不僅有利于探尋形象色彩的形成規律,也有利于在漢語教學中將漢語與其他語言在造詞方式上進行比較,這對本體和教學研究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