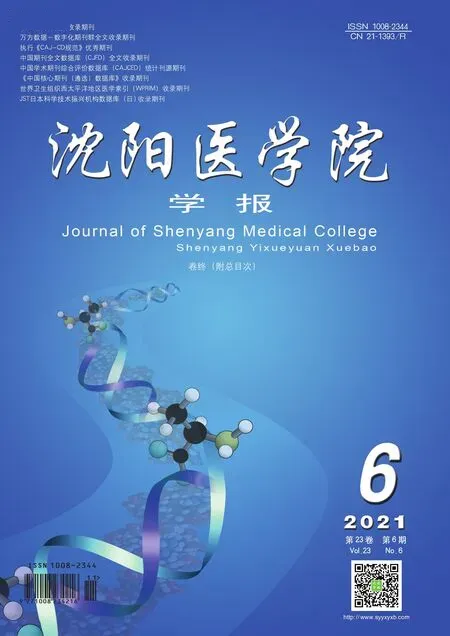COVID-19疫情期間臨床一線護士焦慮、抑郁現狀調查及影響因素分析
葉娜,汪大祝,吳贊芳
(皖南醫學院弋磯山醫院護理部,安徽 蕪湖241001)
自2003年SARS以來,中國接連發生了甲型H5N1和H1N1禽流感、汶川地震、中東呼吸窘迫綜合征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臨床一線醫護人員作為救治的主要參與者,面臨巨大的工作壓力和心理壓力[1]。王亞東等[2]調查研究顯示,在應對SARS的臨床一線護士中出現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高達16.8%。楊玉紅等[3]調查研究顯示,在應對HIN1的臨床一線醫務人員的健康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發生后,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性強、潛伏期長、人群普遍易感、病死率較高[4-6],武漢市首批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醫護人員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心理問題[7]。本研究對武漢市某三甲醫院3個分院中的隔離病房、重癥監護病房、急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房等疫情一線護士(含外省支援護士)的心理健康現狀進行調查并分析影響因素,為進一步開展護理人員心理培訓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20年2至3月,采用方便抽樣法抽取武漢市某三甲醫院3個分院中的隔離病房、重癥監護病房、急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房等疫情一線護士(含外省支援護士)作為調查對象。納入標準:(1)取得護理專業畢業證書;(2)取得護士執業資格證書; (3)征得其同意,自愿配合調查。排除標準:(1)外院進修護士;(2)調查期間外出學習和進修的護士; (3)產假、病事假和離退休的護士。
1.2 調查工具
1.2.1 一般資料調查表 采用自制的一般資料調查表,內容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工作時間、夜班頻率、護士層級及是否有參加過突發應急/公共衛生事件的經歷。
1.2.2 焦慮量表 采用由張作記[8]編制的SAS量表,該量表由20個條目組成,采用4級評分制,焦慮嚴重程度與得分成正比,每個項目相加的總分乘以1.25倍得到標準分。50~59分為輕度焦慮、60~69分為中度焦慮、69分以上為重度焦慮。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49。
1.2.3 抑郁量表 采用由張作記[8]編制的SDS量表,該量表由20個條目組成,采用4級評分制,抑郁嚴重程度與得分成正比,每個項目相加的總分乘以1.25倍得到標準分。53~62分為輕度抑郁、63~72分為中度抑郁、73分以上為重度抑郁。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75。
1.2.4 簡易應對方式量表 采用由解亞寧[9]編制的簡易應對方式量表,該量表由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2個維度構成,包含20個條目,其中積極應對方式維度包含13個條目,消極應對方式維度包含7個條目。采用4級評分制,0~3分依次表示“不采取~經常采取”。本研究中積極應對維度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98;消極應對維度的Cronbach′sα系數為0.687。
1.3 預調查 采用便利抽樣法對20名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臨床護士進行預調查,得出問卷填寫的平均時間為176~1 243 s。通過預調查可以得知臨床一線護士能夠理解問卷的條目并按照填寫要求進行填寫。
1.4 資料收集方法 選取護理部的護士作為本次調查的調查員,在調查正式開展之前均進行了統一培訓。培訓過程中向參與數據收集的調查員介紹本次調查的基本情況、調查問卷的基本內容以及調查中一些注意事項等,以便在進行調查的過程中護士對問卷提出疑問時,調查員可以進行解答。向同意參加調查的護士介紹本次調查的目的、意義,提高調査對象的依從性,減少無應答偏倚。采取方便選樣,在取得護士的知情同意后,再向其發放電子問卷表。同時,問卷還設置了斷點續答功能,護士因各種原因在中途退出后,還可繼續返回做答。由2名調查員負責數據收集,問卷收集后根據專業排查,剔除非調查對象,將數據收集不全的問卷予以剔除。研究者通過問卷星后臺進行填寫數據的觀測、收集,并雙人核對提取資料,確保資料的完整性。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4.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采用[n(%)]進行描述。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和四分位間距表示。采用單因素分析影響護士焦慮、抑郁的因素,采用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有意義的變量,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的一般資料 共收回問卷381份,剔除10份無效問卷(因答題時間少于本研究規定的4份,因問卷填寫人員高度被懷疑為非護理人員的6份),最終共獲得有效問卷371份,有效率97.4%。見表1。
2.2 抑郁、焦慮情況及各量表得分情況 調查對象中有焦慮癥狀者100人,檢出率為27.0%,其中輕度焦慮74人(20.0%)、中度焦慮20人(5.4%)、重度焦慮6人(1.6%)。有抑郁癥狀者132人,抑郁檢出率為35.6%,其中輕度抑郁101人(27.2%)、中度抑郁24人(6.5%)、重度抑郁7人(1.9%)。研究對象的積極應對、消極應對維度得分M(P25~P50)分別為1.92(1.46~2.31)分、1.14(0.86~1.43)分。
2.3 不同人口學特征護士焦慮、抑郁總分的單因素分析 文化程度、夜班頻率和護士層級是影響焦慮癥狀的重要因素(P<0.05);婚姻狀況、夜班頻率和護士層級是影響抑郁癥狀的重要因素(P<0.05)。見表2。

表2 COVID-19疫情期間臨床一線護士焦慮、抑郁得分的單因素分析[分,M(P25~P50)]

續表2
2.4 護士焦慮、抑郁水平影響因素分析 自變量賦值見表3。以臨床一線護士焦慮總分為因變量,以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3個自變量與積極應對方式和消極應對方式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文化程度、夜班頻率、積極應對方式和消極應對方式是影響護士焦慮癥狀的重要因素(P<0.05),見表4。以臨床一線護士抑郁總分為因變量,以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3個自變量與積極應對方式和消極應對方式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積極應對方式、消極應對方式是影響護士抑郁癥狀的重要因素(P<0.05),見表5。

表3 回歸變量賦值

表4 護士焦慮癥狀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表5 護士抑郁癥狀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3.1 臨床一線護士焦慮、抑郁現狀 本研究結果顯示,武漢市371名一線護士中有27.0%出現焦慮,35.6%出現抑郁,焦慮水平高于蒲佳等[10]調查四川省臨床一線護士。這可能與武漢作為COVID-19疫情重災區,由于首次出現該病毒,且傳播途徑廣,傳染性極強,臨床護理人員缺乏對該病毒的認知,內心充滿恐懼與焦慮。同時,自疫情暴發以來,武漢實施最嚴格的“封城”隔離,支援一線的護理人員無法與家屬及親朋好友見面,因此會產生焦慮情緒。與張文慧等[11]調查杭州市某一定點收治COVID-19患者醫院的臨床護士相比,武漢市臨床一線護士的焦慮、抑郁水平較高。武漢市當時的COVID-19患者最多,有26.1%~32.0%的COVID-19患者需要進入ICU進行精細化、個體化的治療和護理[12],對于一線支援護士而言,由于各自專業不盡相同,缺乏急危重癥護理經驗,突然面對充滿巨大挑戰的工作時,工作壓力和心理壓力也會增加,使護士處于應激、緊張狀態,從而導致不安、煩躁等負性情緒,進一步加重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
3.2 影響焦慮的因素分析
3.2.1 文化程度 本研究顯示,隨著文化水平逐漸升高,護士的焦慮得分逐漸下降,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文化程度較低的人應對重大應激事件時往往缺乏正確認識,或者對信息正確性的判斷能力較弱,卻對事件可能造成的威脅比較敏感;而文化程度越高,越能準確把握事件訊息,而且其心理承受能力也相對較強,因而焦慮、抑郁的程度也較低[13]。
3.2.2 夜班頻率 本研究結果顯示,每周夜班頻率越多,焦慮評分越高。在調查的371名護士中,194名護士平均每周2~3個夜班,占52.3%,18名護士平均每周4~5個夜班,占4.8%,過度頻繁的晚夜班,使護士正常的生物鐘節律被擾亂,進而導致了護士睡眠質量的下降[14];長此以往,護士會出現心情煩躁、體力透支等亞健康狀態,若亞健康狀態沒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和治療,會進一步加重護士焦慮狀況。
3.3 應對方式是影響焦慮抑郁、抑郁的獨立因素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積極的應對方式有利于減輕護士焦慮水平,消極的應對方式容易增加護士焦慮水平,與丁玲等[15]研究結果一致。積極樂觀的護士,在護理COVID-19患者或其他應激情況時,更傾向于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正確地面對新型冠狀病毒,做好隔離與防護,從而減輕應激造成的焦慮等不良情緒[16]。當護士采取消極的應對方式,例如害怕、恐懼、退讓等面對新冠疫情時,則會加重焦慮和抑郁,這與譚敏等[17]研究相一致。研究顯示積極的情緒調節對護士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意義[18-19]。
綜上所述,武漢市臨床一線護士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焦慮和抑郁。其中,不同的文化程度及夜班頻率對一線護士的焦慮水平起著重要影響,而積極應對方式和消極應對方式同時影響護士的焦慮與抑郁水平。因此,相關責任人應有針對性的調配人力資源,合理安排班次,避免臨床一線護士過度勞累。啟動心理干預機制,積極引導護士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正確面對COVID-19疫情,從而減輕其焦慮、抑郁,進而促進抗疫工作的順利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