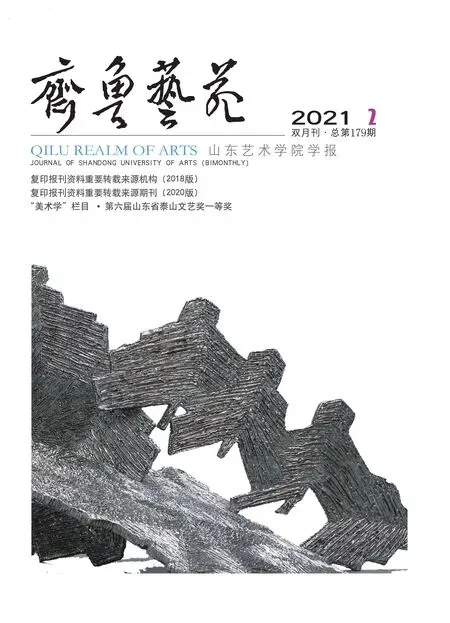呂溫《樂出虛賦》中樂“象”問題的美學思考
張高寧
(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上海 200031)
呂溫是中唐時期的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其家學深厚,自小飽受儒家文化熏陶,文化素養極高,其文章被劉禹錫所稱贊:“文苑振金聲,循良冠百城,不知今史氏,何處列君名”。《樂出虛賦》是其眾多文章之中的一篇賦,載于《文苑英華》。從文學角度來說,此賦的成就并不算高,然而從中國傳統音樂美學思想的角度而言,其對音樂之“象”特征的討論,在中國音樂美學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時至今日,其中所涉及的對于音樂之“象”的論述也值得深入探討。
本文試從《樂出虛賦》中所涉及到的關于音樂之“象”的論述進行分析,通過對音樂之“象”的思考,探索《樂出虛賦》中音樂之“象”的美學內涵及其審美體驗。
一、解讀樂賦
《樂出虛賦》篇幅不長,按照其行文邏輯,可大致劃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呂溫道出了音樂之“象”的基本狀態及其基本的音樂本體觀念。
《樂出虛賦》開篇曰“和而出者樂之情,虛而應者物之聲”,呂氏認為和諧地表現出來的是音樂之中的情感,而從虛空之中做出反應的是樂器的聲音,只有“去默歸喧”“從無入有”,才能奏得理想的音樂。音樂“因妙有而來,向無間而至”,呂氏反復提出了一個觀點,即認為音樂產生于虛空之中,是“無中生有”,從寂靜中發跡,不知為何,不知如何,所謂“虛”“妙有”“寂寂”“玄關”“方寸”,都很好的表現出其神秘的性質。而這正是呂氏的音樂本體觀:他認為音樂是神秘不可知,來源于無形虛空之中,奧妙只在“方寸”之中。隨后他又提出“于是淡以無倪,留而不滯。有非象之象,生無際之際”,這是對來自虛空之音樂的評價,呂氏認為這音樂靜而不止,恬淡和氣,有并非實像之像,在那看不到邊際的邊際……。對音樂源起及其玄妙的論述,正是他音樂本體觀的最好體現,所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第一章)[1](P1),呂氏正是用這種遞進否定的方式闡釋了音樂之“象”的基本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呂氏在闡述了音樂“空虛無滯”的寂靜本質后,進一步為我們理解這種音樂觀念進行了解釋。“故圣人取象于物,觀民以風。辟嗜欲之由塞,決形神之未通”,通過“取象于物”“觀民以風”,使得欲望滿足、形神相同,在此,“象”與“物”、“形”與“神”都成為兩個層級的概念,當由“物”至“象”、“形神”想通后,便出現了“與吹萬而皆唱”的“可聽”的音樂。這種認識觀念涉及中國傳統文人的審美趣味及思考方式,他們不只注意到現實生活的世界,更注意到精神的世界。他們抱有一種超越的心態,不滿足于對物象的表面闡釋,而是尋求上升到精神層面的“神”,追求得意之“象”,正如我們古人對于技與道的追求,我們不滿足于形而下的技,只有超乎技,入乎道,才能算是真正的得道者。而此時,“虛空無滯”“妙有而來”的不可言說的音樂,也正是尋求一種如此的闡釋方式。
第二部分則是對之前所呈現問題的一種思考與升華,既然音樂“從無入有”“妙有而來”“根乎寂寂”“有非象之象,生無際之際”,自虛空中來,無所不至,又不知何以至,因而討論音樂如何于虛空之中產生并如何與作為欣賞者的人建立聯系尤為重要,故而此部分提出“是故實其想而道升,窒其空而聲蔽”,充分表明了從虛空之中所產生的音樂,需要充分發揮想象,通過想象,音樂之“象”才能作為一種審美經驗深入人心。之后則是對音樂經由想象獲得實際功能性特征的論述:“波騰悅豫,風行于有道之年;派別宮商,雷動于無為之世,杳杳徐徐,周流六虛”。而如此音樂則“如是則薰然泄泄,將生于象罔”,表明了他對于音樂本質的認識。
可見,《樂出虛賦》中關于音樂之“象”的美學觀念,一方面包含著對于音樂本體與音樂本質的認識,另一方面其認識方式和認識觀又體現出他對于音樂的審美經驗和美學理想。呂溫的根本觀點就在于認為音樂之“象”來源于“虛”,涉及的是音樂本體觀的虛實之論,而他提出的音樂經驗要依靠審美想象,則涉及到了音樂的審美經驗問題與接受問題,最終將音樂與“象罔”聯系起來,道出了其對于音樂本質的根本認識,因此,呂氏《樂出虛賦》中音樂之“象”的美學內涵,無外乎包含在“象”“虛”“音樂想象”“象罔”這幾個核心概念的內涵延伸及其相互關系之中。
二、音樂之“象”
從字義上看,關于“象”,《周易·系辭》有言“象也者像也”“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2](P543)《韓非子·解老篇》有明確的解釋:“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圣人執其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3](P52)前者“象”為動詞,有模仿、摹擬之意,而后者則是以借大象稀少罕見,只能得其象骨,并通過“想”來重現“象”的故事來喻“道”,以至于“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當人的思維進入到構建“大象”的邏輯之中,此“象”便具有了形象、形式等意思。可見,“象”是中國古老的一種認識方式、審美范疇,根據它的不同詞性,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音樂之“象”的分析:
首先,“象”作為模仿、摹擬之意時,其“比類”之意在中國音樂美學思想中體現出來,人們通過物形、動作和一定實踐進程的再現來認識音樂,可以說是一種最早的對音樂進行的“比類”。如在孔子之前,就有史伯對音樂與天、人、社會萬物之間“同構”關系的認識;《呂氏春秋》中時空統一、包羅萬象的宇宙系統圖式,則是將五音十二律與五時十二月,與五方、五色、五味及其相應的自然及人事的變化、活動相聯系,這也是比類的一種具體體現;儒家音樂美學思想則是更多的將音樂與政治、道德相互比附,其“禮樂”思想正是以樂“比德”“象德”的具體體現。漢代諸家之間相互結合,形成兼采法、道的新道家、統攝法、道的新儒家,皆帶有濃厚的陰陽五行色彩,以致發展為讖緯神學。在這種文化趨勢下,音樂與天、道德之間的聯系更為密切,以音樂類比陰陽、五行、十二支干,形成了復雜、牽強、神秘的音樂觀,《新語》《新書》《淮南子》《樂記》《漢書》等等皆是如此。馬融的《長笛賦》中,在其聽笛聲悠悠之后寫到“爾乃聽聲類型,狀似流水,又象飛鴻”[4](P437),將長笛之樂聲“類”為流水淌淌,飛鴻漸漸,其意在比類,但卻營造出了立體的音樂境象,其描述過程是比類,其形成結果卻是第二種角度的音樂之“形象”。所以說當類比、模仿之“象”經由審美想象,脫離了原始的道德比附,而是試圖構建出音樂的形“象”時,其具備的審美意味顯然更濃。
從第二種角度看,“樂象”這一概念早期在《荀子·樂論》中被提及,“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故鼓似天,鐘似地”[5](P180)。蔡仲德先生指出“其‘象’并非藝術加工的產物,而指鐘鼓等樂器所發音響的狀態、相貌,所以還不是藝術之‘像’”[6](P627)。但很明確的是,這里的鐘鼓樂之“象”,是指形象。鐘與鼓作為天地之象征物,當鐘鼓齊鳴時所顯現出的原始磅礴氣象,便是樂的“形象”。蔡仲德先生雖說此處之“象”并非藝術加工的產物,但是經由天地鐘鼓而鳴發的樂象,本身就具備了鬼斧神工的藝術造詣,是非藝術加工,卻具備藝術張力。同時,音樂之“象”作為藝術之“象”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是一個藝術自覺的過程,也是審美意識自覺的過程;《老子·十四章》說“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7](P30),《二十一章》又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8](P44),則是將“象”與“道”聯系起來,以“象”喻道,這里的“象”,其本該具備的形象是無法言喻的,只能作為對“道”的一種描繪,這種解釋方式,對我們理解《樂出虛賦》中所謂“有非象之象,生無際之際”的音樂之“象”含義有著重要意義,并可以看出后者深受前者的影響;而集儒家音樂美學思想之大成的《樂記》中提到的“聲者,樂之象也”[9](P285),實際上是探討了音樂表現手段的特征,認為聲音是音樂的表現手段,這里的“象”,顯然也具備“形象化”的特征,作為聲音這一基本素材只有通過“文采節奏”之飾才能成為“樂”,才能成為有“意”之“象”,成為藝術之“象”。
通過兩個角度的分析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樂出虛賦》中“有非象之象,生無際之際”的音樂之“象”,應屬于第二個角度。是對音樂“形象”的描繪,這種描繪同老子對于道之描述“惟恍惟惚”“恍兮惚兮”[10](P44)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沒有直接告訴人們“道”是什么、音樂之“象”是什么,而是用形而上學的“負”的方法,告訴大家其不是什么,然后讓人們自行領悟,這也是中國美學中極富特色之處。《樂出虛賦》指出音樂之“象”,是“取像于物”而來,但是不占空間,不在目前,存在于“無際之際”,并非實在之形象,所以稱為“非象之象”,是“象”外之“象”。而這種看似虛無飄渺的描繪,對于只能聞其聲,卻看不見、摸不著的音樂藝術來說,在當時無疑是相當合理的一種認識,體現了古人對于音樂現象的一種樸素又富有意味的思考。
三、樂從“虛”來
《樂出虛賦》中反復強調音樂來自虛空,“虛而應者物之聲”“因妙有而來”“根乎寂寂”等意思皆是如此,故而“虛”在這里對于理解音樂之“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頃,音聲相和,前后相隨”[11](P4)這些相輔相成的范疇一樣,虛與實也是長久以來被相對而論的一對審美范疇,在此我們主要對“虛”的內涵進行探討。顧名思義,“虛”作為一種審美范疇,應是一種玄之又玄且不可說、冥冥之中的非客觀存在,是一種抽象的、需要感性思維來體會的“意味”。從詞源考析來看,《說文解字》將“虛”字列入丘部,“虛,大丘也。昆侖謂之昆侖虛。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謂之虛。”[12](P242),《康熙字典》中除“丘”義之外,另有“虛”“孤”“水”之義。可見,“虛”字含有中國傳統美學的“陰性”特征,“更加傾向于道家哲學”[13]。而對于“虛”這一范疇的探究,我們除了在一向主張“致虛極,守靜篤”的老莊思想中找到契合點之外,更可以追溯到魏晉玄學的發展。玄學是魏晉時期開始流行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玄學在早期道家思想的基礎上更加廣泛地吸取了時代的精神特征,形成了道家文化的新發展,其基本特征是略具體而深究抽象,也可以說是道家之學的一種新的表現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稱。“在其理論上表現為‘有無’‘本末’之論,目的是在于論證名教與自然的統一”[14](P256),文人士大夫對于現實的不滿,企圖性歸山野,卻又為凡世雜務所束縛,既不得全性逍遙,又不愿安居廟堂,在這種矛盾下,人們企圖尋求兩者之中的平衡統一,而玄學所談“重虛”“重遠”“重求之不得”,滿足了脫離生產實踐的上層階級的精神追求,形成了終日談玄的社會風氣,越是神秘不可得,越是百思不得解,越是“惚兮恍兮”越能刺激到他們那已不再對世俗事物敏感的審美神經。故而玄學的形成和盛行如同一針興奮劑,雖然不利于唯物元氣說的進一步發展,但無疑以其玄而又玄、離奇深奧、妙不可言的表現方式,形成了中國傳統美學中極為瑰麗的獨特審美韻味,對音樂、繪畫等各類藝術的理論發展也形成了深刻的影響,形成了對“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追求、探討。《樂出虛賦》完成于中唐,魏晉的哲理思辨精神早已融入到新的時代風潮中。佛教的興盛,形成了儒、釋、道三足鼎立、互相制約又互相發展的局面,而佛理中“不可說”的要義,“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全晉文》)[15](P593)的主張,另如《金剛經》中大量極具辯證性的句偈“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16](P77),對于《樂出虛賦》的“虛空”音樂觀,從其重“空”“虛”的精神內涵來看,很難說不受到影響。另外,從宏觀的審美意識的發展角度來講,正如人們常談的意境產生的三個階段:“莊孕其胎,玄促其生,禪助其成”[17],唐朝佛教文化繁榮,呂溫生于唐代宗大歷七年(公元772年),而這也正是安史之亂后的中唐時期,在這一特定的時期,國家內憂外患,佛教的出世觀點一定程度上對當時的文人階層產生了影響。現實世界的不穩定使人們轉向語言所不能及的思維深處,不可見、不可說、卻可聽的音樂成為了玄理延伸的對象。通過這種思考,我們可以對“虛”有如此理解,即前面所說從審美角度而言,魏晉以來,有重“虛”不重“實”的審美傾向,重“虛”則有“得意忘言”之趣味,雖未說出音樂到底來自何處,卻能使人意會到音樂的“玄妙”體驗,更加使人傾慕于音樂的神秘而向往之,符合當時的審美趣味,使人們能夠接受。
可見,音樂來源于“虛”與用形而上學的“負”的方法談論音樂之形象實際是相輔相成的,前者是在通過“不可知”追求“玄而又玄”的審美體驗,后者同樣是以“象外之象”“物外之物”“際外之際”去嘗試描繪無影無形的音樂之“象”,兩者共同形成了《樂出虛賦》的音樂本體審美觀。
四、“象”由“想”出
上文解釋了音樂之“象”本身的基本邏輯內涵及其來源于“虛”的本體觀念,這是《樂出虛賦》前部分所呈現出來的基本內容,而在《樂出虛賦》后半部分中,他提出“是故實其想而道升,窒其空而聲蔽”,則是將玄妙不可得的音樂玄學逐漸轉為具有實際功能性趣味的音樂思考。
呂溫認為音樂之“象”的產生醞釀,必須要通過自由的想象,也只有通過想象才能使來自虛空的音樂不至于流于虛空。呂氏認識到音樂的“空虛”本質,所以強調經人的主體能動作用,充分發揮人作為審美主體的想象力,在欣賞此“根乎寂寂”的音樂時能夠將自己的主觀情感、想象付之于音樂之上,從而使音樂具有了人文“意義”,達到其所謂的“道升”。在此,音樂從虛空無盡之中通過人的想象,與社會、國家產生了聯系,音樂的實用性趣味開始出現:
“波騰悅豫,風行于有道之年;派別商宮,雷動于無為之世。杳杳徐徐,周流六虛。信闐爾于始寂,乃嘩然而戒初。鏗鏘于百姓之心,于斯已矣;鼓舞于一人之德,知彼何如。是則垂其仁,有其實,樂因之祖述;究其形,實其質,聲因之洞出。”[18](P574)
當音樂從虛空之中進入到人間,經由想象獲得“人文意義”,就能在百姓之中廣為流傳,增強他們的信心,宣揚彼此間的美德。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樂出虛賦》在音樂本體觀念上深受佛道影響,但是在音樂的功能性認識上還是以儒家的“入世”思想為根基,強調音樂的社會功能,彰顯出“以文化樂”的中國音樂傳統。
同時,此處針對于音樂之“象”的想象,涉及到了音樂審美的心理特征,在《莊子·大宗師》中,“游心乎天地之一氣”所表達的就是——審美離不開“想象”,“游心”即指自由想象,也涉及到了藝術審美的心理特征,表明無論是莊子還是呂溫,都深刻的認識到了藝術的特殊性,而音樂藝術其所具備的非實體性、時空流動性,以及表現手段的不確定性,也使音樂審美成為一種超功利而自由,“是感覺、知覺、感情、理智、想象諸因素的交融,是以滲透理性的感情與想象達到主客一體,物我同一,‘無言而心說’的境界”[19](P174)。如此,“有非象之象,生無際之際”的音樂之象,于想象之中散發,才能“波騰悅豫,風行于有道之年;派別商宮,雷動于無為之世。杳杳徐徐,周流六虛。”,成為樂之典范。
五、歸于“象罔”
《樂出虛賦》最后所述“如是則熏然泄泄,將生于象罔”,是整篇樂賦的總結,其關鍵在于“象罔”二字。“象罔”取自《莊子·天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20](P197)這個故事以“玄珠”喻“道”,以“知”“離朱”“吃詬”“象罔”四個虛擬形象比喻四種不同的求“道”方式。前三者分別代表明善于思慮者、察秋毫者、聰而善辨者,他們三人求“珠”(道)卻不得,而“象罔”卻求得,那么“象罔”為何物?關于“象罔”的含義,郭慶藩注:“象罔者,若有形,若無形,故曰眸而得之。即形求之不得,去形求之不得也”[21](P5),呂惠卿注:“象則非無,罔則非有,不皎不昧,玄珠之所以得也”[22](P113),王先謙集解引宣云曰:“似有象而實無,蓋無心之謂。”[23](P116)。通過歷代大家的注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象罔”是一種不可言說、沒有確定形式、若有若無、似象非象的范疇,其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矛盾體,正如前文所述“有非象之象,生無際之際”一樣,是對音樂本質特征的描繪。
但是,我們還要注意到,“象罔”與前面所論述的音樂來源于“虛”的認識有一定的不同,“象罔”作為一個矛盾統一體,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一種陰陽和合、無所不包的概念。呂氏最后將音樂歸于“象罔”,極可能是音樂在本體特性及其功能特性上恰好包括了兩個上下維度的視野,在其本體性質上,音樂體現出“象罔”中的“無”之意,而在其功能性特征上,音樂則體現出“有”的內涵,依此理解,呂氏將音樂的本質歸于“象罔”是一種較為客觀、理性的認識。
六、結語——樂“象”之美
對于《樂出虛賦》中所論述的玄而又玄的“音樂之象”本體觀念的審美體驗到底是以什么樣的方式進行的呢?《中國美學思想史》中指出:“玄則有味生。淡味,指的是審美感受的一種多層次的深厚境界”[24](P257),這種“味”從最早的飲食感官等直接的審美味感不斷地銳化、深化,逐漸向內心體味轉移,這是以“玄理的抽象化掉具體的五行,將五色五聲從五味的黏連中剝離出來,而且也將‘道’的體味與具體的養生氣化分解開來,從而使味成了對本體的體驗玩味,成為離具象的理性窮盡,并進一步移入理性的審美”[25](P257)。可見,在魏晉玄學、佛教禪理的影響下,“有非象之象,生無際之際”的音樂之“象”,有了合理的思想基礎.。而我們所進行的審美體驗,正是在此思想基礎上進行的,這種審美體驗方式正如千百年來文人雅士對象外、言外、筆外、音外之情、理、含蓄之美的不懈追求、不斷玩味一樣,形成了獨特的中國意味的審美特點。而這種方式正是在繼承中國傳統審美方式的基礎上,對傳統審美范疇在當時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進行“切實際”的“感同身受”體驗,就如同“玄則有味生”,以這種方式去體驗那種玄之又玄、無法言明的獨特審美韻味。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注意到,呂氏對于音樂之“象”的論述,在具體的邏輯上是十分清晰的,其音樂本體觀有著較為合理的思想內涵,并非局限于不可言說的審美范式。呂氏在澄清其具有玄學意味的音樂本體觀后,毫不猶豫地肯定了音樂經由人的想象而與現實社會產生的關聯,所以,音樂之“象”,正在于其“象罔”之本體特性上,一方面具有樂之起源于“虛”的形而上氣質,另一方面也是指其與現實社會交融后所具備的形而下之社會、道德屬性。儒道佛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互相吸收融合的特點,在《樂出虛賦》對于音樂之“象”的論述中深刻的體現出來。
中國音樂美學作為中國美學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進行研究的方法論上應該大膽借鑒后者,特別是中國傳統音樂美學因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保存音響少之匱乏,以至對其音樂思想的美學剖析缺少可靠的音響資料,而恰恰在中國美學學科語言中,形態化的審美范疇能夠對傳統音樂美學思想的文字表述進行有效互補,從而通過一種文學性的、哲學性、感性的方式,并結合當時時代的風潮與傳承的特點,對音樂美學問題進行綜合性的探析。
本文通過對《樂出虛賦》中“虛”“象罔”等重要范疇的審美分析,意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述音樂之“象”的音樂美學內涵,同時,也對如何進行這種審美體驗做出了一定的思考。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樂出虛賦》中對于音樂之“象”的論述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它是在多種思想文化背景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獨特的音樂“觀”,是中國古代為數不多的從正面論述音樂之“象”的文章,其中的許多范疇都值得用審美的眼光來對待。同時,我們要積極認識到《樂出虛賦》的當代價值,如《樂出虛賦》對于音樂本質來源于“虛”的認識,十分符合音樂本身的特點,音樂美學家蘇珊·朗格曾認為,音樂存在于時間的幻象之中,這似乎與呂氏“妙有而來,向無間而至”的音樂觀點有著某種相似性。可見,《樂出虛賦》中對于“樂象”的論述不僅對于探討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中的音樂本質、音樂本源問題十分的重要,而且也對當代音樂哲學觀念中對音樂本質的思考有所啟發,同時,《樂出虛賦》中進一步延伸出來的要求發揮音樂想象力、音樂功能性的特征對進一步拓寬中國音樂創作中的思想性、文化性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值得進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