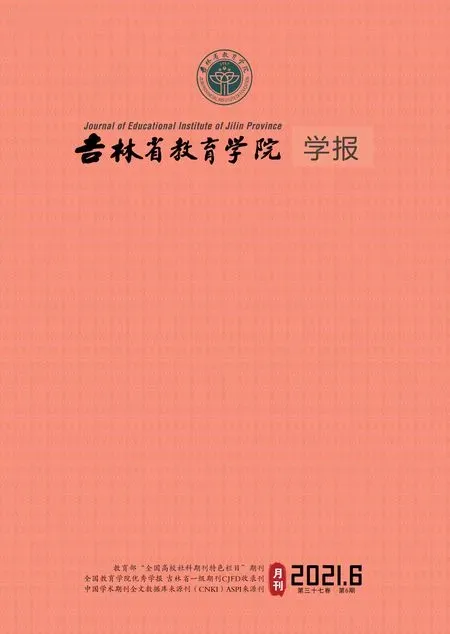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自由思想的規范
——基于中國化早期探索背景的考察
樸耘正
(吉林省雙遼市茂林鎮中心校,吉林雙遼136000)
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自由思想強調的自由性絕不是“全民自由”或“超階級自由”,而是相對自由,相對性是該思想的顯著特征。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出版家對這一特性高度認同,由于身處民主革命的特殊時期,他們將此種“相對自由”置于“革命”的范疇之中加以解讀,注重革命效益以規范自由,換句話說,就是將“革命效益”作為新聞出版自由的限制條件,進而從真實性、革命性等方面考量新聞出版的“革命效益”。因此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自由思想,在自由的相對性方面,體現為真實性、革命性等規范的約束。
一、規范的前提:抵制新聞出版獨裁以獲得自由
馬克思認為“自由是人固有的東西”,新聞出版自由作為人類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的精神特權而非個別人物的特權”[1],也是“自由所具有的英勇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質”[1]的具體體現,一定意義上講,新聞出版自由是人的基礎性自由,意味著人類精神特權的解放。相反,在獨裁體制下,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則“其他一切自由就是泡影”[1],而且新聞出版本身所具有的監督職能也會被剝奪,即“不僅被剝奪了對官員進行任何監督的可能性,而且被剝奪了對作為許多個別人的某一階級而存在的各種制度進行監督的可能性”[1]。可見,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自由思想的基石是自由性,要求人們必須反對新聞出版獨裁,以求得人類最根本的自由,并保障新聞出版固有職能的發揮。
在新聞出版獨裁的環境中,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出版家高度認同自由性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自由思想的基石,并采用借鑒和本土化的方式進行了孜孜不倦的追求。李大釗認為“立憲國之有言論,如人身之有血脈也”[2],應該賦予每個人通過新聞出版自由發表言論之權利,因為無論正確與否,都能使人明辨是非,所謂“果其是也,固當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當使人得非以察是”[2];同時,反對政府對新聞出版實行檢閱制度,強調“除犯誹毀罪及泄漏秘密罪律有明條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且“以嚴禁檢閱制度揭于憲法明文中為宜也”[2],意即憲法應明確人民享有新聞出版自由。在上述新聞出版自由理念的引導下,李大釗對北洋時期的新聞出版獨裁進行了堅決抵制。
首先,為因言獲罪者發聲。
1914 年,北洋政府頒布《出版法》,規定新聞出版不得“妨害治安”,隨之發生了北京《國民公報》的記者孫幾伊因此罪而獲刑的事件,引起社會各界廣泛議論,李大釗深知這是“官吏一人之偏見”,自然“每多失當”,也是北洋政府新聞出版獨裁的表現,甚至認為這“最足為文化之蠢”[2]。于是,他發文為其鳴不平,“今《國民公報》所登載,究竟曾否擾亂社會之安寧秩序,并于社會秩序有無絲毫之影響,事實俱在,實令人索解無從”,并要求北洋政府對“妨害治安”進行普及性解讀,以免自己這種“小民”“時有犯罪之危險,此不特為輿論界之關系,抑亦一般人所不可不注意者也”[2]。其中的諷刺意味顯而易見。
其次,發文直接抨擊新聞出版的相關法規,揭露北洋政府之虛偽性。
針對憲法與行業律令的矛盾之處,李大釗陸續發表《那里還有自由》《爭自由的宣言》等文章,向公眾撕開北洋政府“以新聞出版自由之名,行新聞出版獨裁之實”的丑陋面具,如: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而《出版法》則“把人民著作發行、印刷、出售、散布、文書圖畫的自由交給警察官署或縣知事處理”[2],以致“記者可以隨便被捕,報館可以隨便被封”[2],這就“把宣傳文化灌輸學術思想的工具完全破壞”[2];憲法規定公民也有出版自由,而《報紙條例》及《管理印刷業務例》則“把個人意見和社會輿論的發表權寄附在警察官喜怒之下”“把印刷局的營業自由完全剝奪”[2],以致“印刷局可以隨便干涉,郵局收下的印刷物可以隨便扣留”[2],使得“思想既不自由,輿論也不能獨立”[2]。其結果正如馬克思所言“有這樣的一種法律,哪里還存在出版自由,它剝奪這種自由,哪里應當實行出版自由,它就通過書報檢查使這種自由變成多余的東西”[1],李大釗也疾呼“可憐中國人呵!你那里還有‘約法’!那里還有自由!”[2],以警醒世人。
可以看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出版家有關新聞出版自由的言論以及對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新聞獨裁的反對與抵制實質上是對資本主義“名為自由,實為獨裁”的虛假新聞出版自由的批判與揭露,促使時人對新聞出版自由產生了清醒的認識,并從迷茫、失望的情緒中開始覺醒,也為規范自由提供了前提。
二、以真實性為基礎規范新聞出版自由
恩格斯曾言:“如果禁止報紙報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報刊在每一個有分量的問題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決,如果報刊不管事實是否真實,首先得問一問每一個官員——從憲兵到大臣,——他們的榮譽或他們的尊嚴是否會由于所引用的事實而受到損傷,如果要把報刊置于二者擇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談,——那么,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結了。”[1]他的四個“如果”道出了報刊內容真實性缺失的主要原因,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版自由的完結,可見,真正的新聞出版自由必須用真實性加以規范。
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出版家也紛紛以真實性去規范中國化的新聞出版自由理念。張聞天在《關于我們的報紙》一文中對革命報紙提出了要求,即“我們需要的是真實,……我們需要我們的報紙,如實地反映蘇維埃的實際,真正為黨與蘇維埃政府所提出的具體任務而斗爭”[3];同時,他也要求新聞出版領域的從業者不能做“沉醉于自己美妙的空想家”,也不能做“陷于悲觀失望的無節分子”,更不能對自己工作的缺點與錯誤避而不談,要從現實出發,做一個“依照我們的路線改造這一現實而穩著腳步前進的馬克思主義者”[3]。
惲逸群從“自由”與“真理”關系的角度探討真實性對新聞出版自由的規范。他認為“自由是不能離開真理而獨立存在的”,其中“符合真理的自由才是真自由,是人民大眾所擁護的自由”,而“違背真理的自由則是偽自由,是人民大眾所要反對、所要消滅的”[3]。在民主革命的特殊時期,“自由”“真理”“革命”及“反動”被聯系在一起。在新聞出版中,革命必須掌握真理“為了爭取最大多數人民最大、最長遠的利益而奮斗”[4],也才能得到真正的出版自由;反動則是違背真理,“為了剝奪最大多數人民利益而致力”,得到的只能是危害大多數人利益的所謂新聞自由,本質是反動派的“殺人自由”[4]。
鄒韜奮從實際效果的角度闡釋真實性對新聞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所謂“只有‘開放’真確的消息,才能使人民知道什么是‘謠言’;只有知道真確的策略的人,才有‘鎮靜’的可能”[5]。他的意思非常明確,新聞出版是自由的,但“開放”“指導”的消息、策略只有是真實的,新聞出版自由對人民才有實際效用。從這個意義上講,真實性對新聞出版自由發揮效用具有決定作用,它是新聞出版自由的限制因素。
可以看出,無論是張聞天要求做真實的馬克思主義新聞人并如實報道革命實際,還是惲逸群探討的“自由”與“真理”相輔相成關系,抑或是鄒韜奮所闡釋的真實性的重要意義,都是對中國新聞出版自由的規范,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自由思想相對性的中國化闡釋。
三、以革命性為條件約束新聞出版自由
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出版家深知只有“強有力的言論機關都在這多數人為中堅的政權統轄之下”,才能使多數人享有自由言論的權利[6]。換句話說,報紙、雜志等言論機關只有控制在多數人或代表多數人的政黨手中,新聞出版自由才能夠真正實現。這就要求代表多數人的政黨推翻專制政權,其中蘊含的革命性顯而易見,那么新聞出版“具有煽動的機能,能夠煽動群眾去實現一種行動”的本質屬性,且“具有偉大的力量,發揮偉大的效用”[7],決定了其能夠為此種革命做出自身的貢獻,但前提是其煽動機能必須是革命的。因此,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自由的相對性,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有革命性的層面。
隨著民族危機的逐步加深和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出版家在創刊辦報的過程中,都極其重視革命性,以約束新聞出版自由。瞿秋白認為“真正的解放中國,終究是勞動階級的事業”,但在革命過程中“亦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8]。這種指導是由報刊提供的,因為“在任何一種革命時代,報紙常是站在斗爭的前線”[7]。隨之,他創辦《新青年(季刊)》,作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羅針”,去“與中國社會以正確的指導”,并“與中國平民以智識的武器”[8]。鄒韜奮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在抗戰的特殊時期,新聞出版應“造成正確的輿論,喚起國民御侮的意識與堅決國民奮斗的意識”[9],具體說來,就是“宣傳國策,教育民眾,反映民意,督促并幫助政府對于國策的實施”[9]。在此理念指導下,他創辦《抗戰》具體踐行上述革命性的新聞出版理念。馮玉祥評價其“內容豐富切實,而眼光尤為正確遠大,誠為今日抗戰中之指針”[10]。
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領袖,是倡導并踐行革命性新聞出版自由的集大成者。他認為報紙是“組織一切工作的一個武器,反映政治、軍事、經濟,又指導政治、軍事、經濟的一個武器,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的一個武器”[11],而且強調宣傳要“完全符合于黨的政策”,增強黨性[11]。可見,他把新聞出版從“羅針指針”職能提升到了“革命武器”的高度,換句話說,新聞出版必須是革命的,其自由性也必須是革命范疇內的自由。為了“向反革命派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11],毛澤東倡導創辦《政治周報》雜志,以“為中華民族得到解放,并實現人民的統治”[11]進行革命宣傳。在《中國工人》發刊詞中,他強調:該雜志是為“團結自己和團結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斗”[11]這一革命任務助力;在《解放日報》創刊時,毛澤東指出該報的使命“一語足以盡之”,即“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11]。
可以說,在民主革命時期,瞿秋白、鄒韜奮、毛澤東等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出版家針對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自由思想的相對性進行了中國化的解讀,并付諸創刊辦報的實踐之中。伴隨著民族危機和階級矛盾的逐步加深,革命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一切思想與社會活動都必須順應這一主題,身處其中的新聞出版受其鼓舞,也被其約束,革命性必然成為規范新聞出版自由思想的重要因素。
總之,民主革命時期,在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自由思想中國化進程中,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與革命出版家高度認同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自由思想,并將其引入中國,當然不是“移植式”的照搬照抄,而是結合當時中國的新聞出版實際,對其進行了規范,昭示自由的相對性、真實性與革命性,這既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自由思想中“自由”的精髓,也體現了中國式的新聞出版自由。同時,這樣的早期探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新聞出版領域的集中體現,也為之后中國共產黨人在新聞出版自由領域的探索奠定了基礎,更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