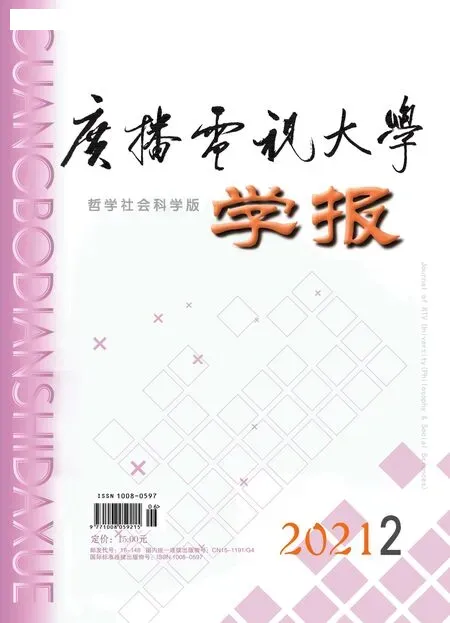氣候小說的“人為”原因與人類中心主義——兼談中國氣候小說
李 珂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200240)
一、氣候小說定義中的“人為”原因辨析
氣候小說(Climate Fiction),也稱氣候變化小說(Climate Change Fiction),是環境危機話語中出現的新文類,往往在科幻小說和生態文本的交叉領域中被討論。關于氣候小說的定義,目前學界側重討論的是對氣候變化的“人為(anthropogenic)”原因。李家鑾在論文《氣候小說的興起及其理論維度》中提到了氣候小說定義的“狹義”與“廣義”之分,他不僅贊同所謂狹義上關于氣候小說的定義——“有意識地、明確地涉及由人類引起的氣候變化的文本”,而且以此為依據論證氣候小說在21世紀初才“正式誕生”這一命題[1]。袁源在《人類紀的氣候危機書寫——兼評〈氣候小說:美國文學中的全球變暖表征〉》中也贊同,“‘氣候變化敘事’不是文學中傳統的氣候主題書寫,而是以人為導致的氣候變化為敘述中心”。[2]然而,真正落實到文本劃分時,這一標準似乎并沒有盡到義務。例如袁源認為,英國作家J·G巴拉德(James Graham Ballard,1930-2009)的《沉默的世界》(The Drowned World,1962-)是首部氣候變化小說,李家鑾則認為這部小說中的全球氣候變暖及海平面上升是由于地球本身引起的,并不能被嚴格劃分到氣候小說的討論范圍中。與此同時,姜禮福在《氣候變化小說的前生今世——兼談人類世氣候批評》一文中主張將瑪麗·雪萊(Mary Shelley,1797-1851)的《最后一個人》(The Last Man, 1826)視作現代氣候書寫的濫觴之作[3],并根據時間順序,將西方氣候小說分為洪水敘事、極寒敘事、全球氣候變暖敘事三類,將氣候小說創作的分布與世界科技中心的轉移聯系在一起,依據是他認為西方氣候小說的創作是基于現代科學發展的。而在這之前,亞當·特雷克斯勒(Adam Trexler)和阿德琳·約翰斯-普特拉(Adeline Johns-Putra)提出,第一部直接描寫人為氣候變化的小說應該是1977年的阿瑟·赫爾佐格(Arthur Herzog,1927-2010)的《熱》(Heat)[4]P187。可見,以“人為”來定義氣候小說,雖然在嚴格意義上縮小了氣候小說的范圍,使其獨立于一般的末日小說和科幻文學,但在實際研究中,仍易造成眾說紛紜的現象,尤其是在跨文化語境中,似乎難以有統一的聲音。
李家鑾等學者所參考的定義——“有意識地、明確地涉及由人類引起的氣候變化的文本”,主要來源于施耐德-梅森(Matthew Schneider-Mayerson)在《氣候變化小說》(Climate Change Fiction,2017)中對氣候小說現狀的概論。施耐德認為,早期的學術研究傾向于將其描述為“以氣候變化為重要主題”的文學,尤其是“以氣候變化——通常是人為的氣候變化——為明確或隱含主題的虛構文本”。而緊接著,他的敘述是I examine only those texts that were consciously and explicitly engaged with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though one might, with more space, cast a much wider net.[5]P312也就是說,他承認我們有更多空間去討論氣候小說,但他本人涉及的研究僅以“有意識地、明確涉及人為氣候變化”的文本為對象,這是他對文本選取的空間限定,并不是定義,這種限定使他在后文更能順利探究氣象小說衍生出的兩個新主題——化石能源枯竭后人類利用智慧實現了能源轉型和美國氣候小說書寫的民族主義困境。再往前追溯,施耐德對氣候小說的定義主要參考的是亞當·特雷克斯勒、阿德琳·約翰斯-普特拉和斯蒂芬·西伯斯坦(Stephen Siperstein)等幾位學者的綜述。亞當·特雷克斯勒和阿德琳·約翰斯-普特拉在論文《文學與文學批評中的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 i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2011)中并沒有將西方文學史上關于全球氣候的文本列入討論,因為作者認為對這些討論的進一步調查是無法處理的,需要涉及對宗教、神話和世界末日文本的敘述,他們僅研究代表人類活動引起的氣候變化問題的小說,因為過去的二十年中,對這一問題進行描述的小說數量暴增,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個問題本身在科學和公眾那里也得到了普遍認可[4]P186。斯蒂芬·西伯斯坦2014年提出,氣候小說是以氣候變化(通常是人為氣候變化)作為顯性或隱性主題的虛構文本,氣候變化的中心問題是未來。而同時,斯蒂芬指出,氣候小說不應該被作為一個僵化的類別來對待,而應該將其作為一個靈活的框架,瑪麗·雪萊的《最后一個人》也應被看作是氣候小說的前身,人們應當認識到氣候變化小說對先前環境話語和其他環境文學流派敘事模式的指向,包括美國自然界對牧民的寫作傳統,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和比爾·麥基本(Bill Mckibben,1960-)等人的生態文本[6]。也就是說,“人為”因素是這些學者對氣候小說文本范圍的一種限定,但在定義上卻無法徹底阻止其本身的“泛化”討論。施耐德甚至認為,隨著氣候變化被廣泛地理解與接收,幾乎所有具有表現野心的敘事都被迫參與到極端天氣事件、熱浪、干旱、海平面上升、環境遷移、大規模滅絕的現實中。在不久的將來,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將成為我們現在所認為的氣候變化小說的一種形式。[5]P317-318另外,研究者自身對這種限定的措辭也會面臨被推翻的風險,如亞當·特雷克斯勒竟認為截至2011年,只有英語小說才涉及了“人為”的氣候描寫。[4]P186
“人為”性的強調,主要突出的是主流科學界認為人類對地球自然的影響越來越深的現實,以此引起生態反思。目前地球正處于從全新世(Holocene,舊稱沖積世Alluvium,該詞現指沖積層)到人類世(Anthropocene)的過渡階段,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似乎越來越大。①在科幻小說里,作家也重復使用人類世一詞來指現今衰減的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以及由人類所開創的地質時代。在分析氣候小說勃興的大背景時,工業革命以來多發的厄爾尼諾現象、臭氧層空洞、全球變暖等世界性氣候事件往往是學者所關注的對象,在公眾視野里,人類的生產發展對氣候環境產生的無意識干預仿佛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將氣候小說及其相關批評視作“生態文化”研究的最新發展的理由之一。作為一種長期存在的、無法被直接感知的慢性災難,氣候變化期待特定的一種文學類型在普及氣候變化知識、激發行為改變方面起作用。2005年,羅伯特·麥克法蘭(Robert Macfarlane)在《衛報》(The Guardian)撰文,“現在人們亟需通過幻想作品來辯論、感知、交流氣候變化的起因與影響。”[7]環境科學家莎拉·珀金斯-柯克帕特里克(Sarah Perkins-Kirkpatrick)認為氣候小說“可能鼓勵讀者改變他們的日常行為”,“與人為引起的氣候變化作斗爭現在為時已晚,或者將永遠為時已晚。”[8]事實上,致使氣候變化的原因有許多,包括大陸漂移、地球運行軌道變化、太陽輻射、溫室氣體排放等,尤其是近些年來,關于氣候變化人為原因的懷疑論與否定論似乎隱隱呈現分庭抗禮的趨勢。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1942-2008)2004年在小說《恐懼狀態》(State of Fear)中表達了對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質疑,并且于文末引入大量的圖表和腳注,以及兩個附錄和20頁的參考書目,盡管他明確表達了自己作為作者的中立態度,但這的確引起了讀者的另一種反思。但更多氣候小說的研究者傾向于認為,氣候變化懷疑論和氣候變化否定論是對氣候變幻的誤解,因為“在人類所習慣的時間尺度上,緩慢的氣候變化過程容易讓人產生一種無動于衷的麻木感”[1]。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來國內學界對全球變暖等問題也出現了不一樣的聲音,如2013年,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教授江曉原在論文《科學與政治:“全球變暖”爭議及其復雜性》中指出,“全球變暖理論”有很大的建構成分[9],2018年,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發表了《氣候變暖的前世今生》一文,總結了三十年以來的全球氣候變暖相關研究,而這之前,占領主導地位的是“氣候變冷”說,從數據上看,對于全球氣候變化來說“永遠不變的是變化”[10]。中國科幻作家鄭軍(1969-)發表于2012年的小說《決戰同溫層》(完書于2005年)和《西北航線》也從非常前沿的視角對氣候災難的人為因素進行了否定,這類小說恰恰也是比《紐約2140》( New York 2140)、《遺落的南境》(The Southern Reach)等公認的氣候經典代表作更為精致的“硬技術”寫作,是在對古氣候學資料的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值得被納入氣候小說的研究范圍的生態文本。對于這一類寫作如果過分強調“人為”原因,其立身的科學依據首先將可能受到非通俗讀者的質疑,在很大程度上將背離氣候小說對現實的責任初衷,更多相關主題的展開和討論也會受到約束。
對氣候小說的定義仍在動態的界定過程中,“人為”性是對它現階段特征的一種明指。事實上,在文本框架內,對氣候小說的研究與解讀仍然存在許多迷宮。2013年,美國記者丹·布魯姆(Dan Bloom)摹仿科幻小說(Sci-Fi)的構詞方式,正式在公眾視野提出Cli-Fi這一概念,但氣候小說究竟是科幻小說的分支,還是兩者存在交叉性目前并未厘清,仍然眾說紛紜;此外,按照國內外學者所接受的現行概念,氣候小說并不單純指描寫氣候災難或是以氣候為主題的文本,中國科幻作品中可以納入氣候小說討論之列的似乎少之又少,諸如劉慈欣斬獲雨果獎的《三體》與贏得電影高票房的《流浪地球》,文本中對三體星球氣候的模擬和地球在逐漸脫離太陽系后發生的一系列氣候變化,是最吸人眼球的情節之一,而在國際上關于氣候小說的討論熱潮中,兩部作品中的氣候描寫并未進入視野。與此同時,國內學術界對氣候小說有意識的研究也是近幾年才有的事,且側重于對理論的概括,而在文本解讀方面僅有零散的對國外熱門作品的解讀,如張慧榮、朱新福《氣候小說〈突變的飛行模式〉的代際正義追尋》、金秋容《超越生態反烏托邦——論氣候小說〈紐約2140〉》,以及臺灣學者陳重仁《“只不過是場災難,放輕松!”麥克尤恩〈日光〉中氣候變遷的探問》等論文,對中國氣候小說的解讀明顯不足。
二、以人類為中心的正面敘事:從《喜馬拉雅狂想》說起
劉興詩(1931-)被譽為“中國科幻鼻祖”,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科幻文學的代表作家,其小說多采用“課題研究”式的寫作模式,往往體現出鮮明的啟蒙意識和實證精神。得益于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的求學背景,劉興詩的小說在考古、地質考察等“硬技術”描寫方面功底扎實,獨具特色。2012年,由劉興詩主編、電子工業出版社出版了“新災變時期科幻三部曲”——《喜馬拉雅狂想》《孤島潛流》《西北航線》,其中《喜馬拉雅狂想》是由他本人創作的中長篇小說,靈感來源于他六十年前公開發表過的一個科幻構思。在故事中,喜馬拉雅山脈隨著印度板塊不停向北方西藏板塊擠壓而持續性增高,阻擋了印度洋溫暖潮濕氣團進入山后,致使中國廣大西部日趨干旱,河西走廊也變成了荒漠,盧孟雄和曹仲安兩位23世紀的未來人為了解決大范圍荒漠化這一難題,試圖穿越時空帷幕,回到古時樓蘭的羅布泊、唐朝的青海腹地、漢朝的張掖古城等地考察來探究人類與氣候變化的關系,隨后借助1000年后的X教授的幫助,通過打通喜馬拉雅山墻這一壯舉改變了這一災變環境。故事結局圓滿,似乎人類只要堅持信仰,充分發揮好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就可以扭轉惡劣的氣候環境以及氣候變化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中國經濟騰飛較晚,改革開放至今,人們還處于享受科技果實的盛宴之時,《喜馬拉雅狂想》中雖已發育出了較為濃烈的環境責任意識,但仍然難掩人類技術自信的膨脹。再往前,如吳顯奎(1957-)1986年斬獲首屆中國科幻“銀河獎”金獎的短篇小說《勇士號沖向臺風》,則更為“明目張膽”地將人類的理性膨脹彰顯到了極致。在小說里,科學家們企圖利用探測器來達到控制臺風的目的,當女飛行員與愛人陸永平一起開飛機馳騁在藍天上時,感慨的是“這是多么美的大自然,多么壯麗的征服大自然的事業呀!”[11]他們甚至想鉆入臺風眼,來獲取臺風動力的真相。遺憾的是,海上的一艘漁船干擾了臺風動向,陸永平最后決定犧牲自己的飛機來啟動光電加速器,利用天空中的閃電能量來摧毀臺風,拯救漁民。吳顯奎有著多年氣象工作經驗,多篇小說的故事設定都與氣象相關,像他的紀實文學《晨星在最黑暗的時候升起》《黑海風暴》《一個傷心的童話》《彼得堡午夜的鐘聲》《涂長望之死》等,主要是寫科學家,尤其是從事氣象方面的專家為了發現真理而獻身的故事,側面貫穿的一直是科學理性與大自然的斗爭這一線索。在吳顯奎的這些故事里,氣象與氣候是大自然里等待著被科學家認知、征服的對象,而《勇士號沖向臺風》提出了一種立場——那些給人類生命財產造成損失的壞氣象,是大自然中的惡魔,它們的存在如果不能加以利用,那么作者傾向于放棄甚至毀滅大自然的這一部分。在這一時期,這樣的行為被普遍認為是正義的,作家進一步可以塑造的就是那種獻身科學、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英雄形象。這類寫作范式也被后來描寫氣候的科幻作家所繼承和進一步延伸。回到《喜馬拉雅狂想》,作家雖然看起來已經開始反思人類的生產活動對氣候變化的影響,但作品內核卻是強調人類在與環境問題較量時重振自信心的必要性,這個必要性的前提是洗刷人類對氣候問題的“罪孽”印象。
《喜馬拉雅狂想》被視為中國氣候小說的代表作品,劉興詩也舉足了證據來說明小說內容考據的可靠性,以此來引導讀者重視氣候變化,這是他對自己論文式科幻創作特點的發揚光大,可以說在科普作品中已屬佼佼。故事的重心雖然在描寫氣候,但真正吸引人的是利用時間機器完成的幾次“穿越”行動。在情節的主線索中,劉興詩一直在提醒讀者,“新黃金時代”已經瀕臨結束,可能持續2500年的“新災變時代”即將到來,其中之一的氣候表現就是大范圍內的反常氣候變化。由于印度板塊不停向北方擠壓西藏板塊,致使新第三紀猶存之古地中海消失,喜馬拉雅山脈出現,并持續性增高,阻擋印度洋溫暖潮濕的氣團入山后,導致中國廣大西部日益干旱,于是小說主人公盧孟雄和曹仲安提出了“打通喜馬拉雅山脈”的構想,引入印度洋氣團,對于山之南印度遭受豪雨的一些地區來說,是一個雙贏的舉措。在小說的“過去篇”中,主人公們企圖利用時光機(故事設定的技術現狀是時光機只能回到過去)穿越回古代去尋求氣候惡化的原因,因為他們認為現實人類所承受的致命打擊,是因為“我們和我們的祖先犯了什么錯”,助長了大自然的肆虐,他們想在可能的范圍之內“調整”一下大自然的進程,本書的立意便是“在有心人的面前,也不是沒有半點回圜的余地”[12]P4。
劉興詩作為地質學家,對地質地理的逼真描述使論述變得自然、合理,具體體現在他描寫漢唐朝河西走廊、樓蘭地貌等細節上,他甚至引入了古詩、史書著述來對比主人公在過去看到的風貌。然而,在故事的前半段,他越是描寫得仔細逼真,就越凸顯了人類的無辜,因為那些歷史上的文明衰竭,并不是龍虎斗爭的結果,而是蟄伏在一旁,“氣候惡魔生出的魔掌”[12]P36。曹仲安從往昔收集了豐富的材料,厘清了過去氣候災難發生的脈絡,以及人類文明的出現、神話的出現同氣候災難之間的聯系,提出在酷烈的全球性災變時期,正應“時勢造英雄”。
劉興詩這種“論文”式的考證方式再次證明,致使氣候變化的原因的確很重要,這是氣候小說應當予以引導的主題內容之一,但原因究竟是不是“人為”導致的,并不像現行氣候小說定義中強調的那樣關鍵。德國學者安東尼亞·梅納特(Antonia Mehnert)在其2016年出版的著作《氣候變化小說:美國文學中的全球變暖表征》(Climate Change Fictions: Representations of Global Warm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中也明確提出,雖然氣候變化的人為原因在關于氣候的辯論中起著重要作用,但已經不可能劃出一條線來區分全球自然(非人為)氣候和人工氣候。[13]對比國外盛行的氣候小說文本,中國作家大都不會主動將“人為”作為人類的“原罪”去書寫,一是無論作為現實主義小說還是科幻小說,人類活動與全球變暖等氣候問題之間的關系,仍然需要獲得更多人、尤其是精英知識分子的信服與支持,這依然是一個需要數據和統計的科學求證過程;二是文學本身永遠面臨審美的訴求與考驗,適度的危機與災難書寫的目的是使人們意識到可能事件的真實性,從而進一步引發對現有倫理秩序和道德框架的反思,這個反思無論是荒謬的、消極的,還是如《喜馬拉雅狂想》那樣充滿信心與斗志的,都是為了成全人類美好而可持續的生存。于是,氣候小說也可以從另一面去體現“人為”性,比如災難過境后人類積極對氣候進行干預,以及人類有意識地利用技術控制氣候達成某些利益等,而不只是體現在導致氣候災難的原因上。
討論人在氣候惡劣的條件下該如何生存,必須依賴一個事實,即影響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巨大力量,依然是科學技術。劉興詩借助幾千年后主人公的后代們提供的最新科技,率先攻破了打通喜馬拉雅山脈的難關,終于促成現實和未來生態的“以肉眼可見速度”地好轉。諸如吳顯奎利用臺風來成全人類繼續進取的野心,在劉慈欣的《球狀閃電》里也有類似的描述,球狀閃電具有摧毀一切事物的神秘力量,可以幫助預測龍卷風,最后被人類技術捕捉到并應用于實戰。這些作家對人類面臨的氣候災難采取了一種“正面敘事”的策略,因為他們都意識到,如果真要彰顯氣候小說的現實影響,如何發揮人類主動性是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歐美氣候小說的強項是書寫人類如何在惡劣的災變環境中舉步維艱地生存,《喜馬拉雅狂想》這樣的技術樂觀主義文本則是將人類理性再次供向神壇,其實兩者都在揭示同一個真相——人類不可能犧牲自己去成全生態,所以氣候小說也永遠否認不了自己立足人類中心主義視角的前提。
三、宣戰生態中心主義:《西北航線》與《決戰同溫層》
氣候小說所立足的“人類中心主義”視角,也是當下生態批評,尤其是環境批評發展的新方向之一。代迅在論文《英美生態批評的三個關鍵問題》中提醒研究者注意“生態”和“環境”的術語之爭[14]。“生態批評”崛起于二十世紀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的英語文學界和理論批評界,目前主要活躍于美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界[15],而“環境批評”是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1939-)的術語,2005 年首次使用。在《環境批評的未來:環境批評與文學想象》(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一書中,布伊爾闡述了以“環境批評”代替“生態批評”的必要性。“生態(eco)”這個詞綴中暗含局限性,其涵義還保留在“自然”而非“人為”環境的層面上。“那些實踐中的所謂生態批評家們的‘生態’更傾向于美學、倫理學和社會政治學,而不是科學,這種傾向自運動的開端就存在,而且還不斷發展”[16]P14。從氣候小說的立場來看,這種逐漸向科學疏遠的術語并不能完成它對人類現實的使命。氣候小說首先要求人們不要幻想與大自然之間保持美學的距離,而是要進行科學的審視,盡管有時這種審視的結果可能會質疑與否定自身。
邁克爾·克萊頓《恐懼狀態》中的人物辯論數據(包括圖表和腳注)和概念,使人們對全球變暖證據的有效性產生懷疑,在小說結尾和公開采訪中作者提供的信息也反映了這種懷疑。不可否認的是,讀者的確可能會從他的書中消除一些傳統觀念上的誤解,甚至有人選擇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情節進行討論,比如作者是如何獲得氣候科學家使用的相同數據并得出全球變暖不是威脅這個結論?“城市熱島效應”會不會導致氣候變暖?克萊頓多次指出冰川在擴張而不是后退,這究竟是事實還是故事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科幻作家鄭軍完成于2005年的《決戰同溫層》與《恐懼狀態》有多處默契,如都寫到了大氣模擬實驗室、反派利用氣象科學進行戰爭、大眾對氣候問題的無知等情節,雖然鄭軍是邁爾·克萊頓的書迷,在早期創作時也深受其影響,但此時《恐懼狀態》的中譯本還沒有在國內發行,鄭軍本人則在2014年才讀到這本小說。在與《決戰同溫層》同一年發表的《西北航線》中,鄭軍同樣否認人類活動對氣候變暖等環境問題的影響,鄭軍認為,他與克萊頓“走了一個相同的思想歷程”,“我的創作主題是自發走到這一步的,主要是大量閱讀了關于古氣候學的資料,知道現在有關氣候危機的言論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②與《恐懼狀態》一樣,《西北航線》與《決戰同溫層》也挑戰了人們對傳統生態文本的閱讀習慣,這兩部作品正式以科學名義向枉顧人類利益的生態中心主義和反科學的環境保護者發出了宣戰。
《西北航線》寫的是,北極圈內極冰融化,浮冰斷裂規模越來越大,成全了人們夢寐已久的“黃金水道”——西北航線③,同時也可以讓人類得以將在北冰洋開采的石油資源運輸出去,但這對于北極圈內的動物來說卻是一場巨大的自然災難,北極熊為了食物不得不向更高緯度遷徙,而來往船只船底下剝落的涂料、可能泄露的石油都可能對海洋造成污染。于是,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生態中心主義者發起成立了“北極衛士”這個組織,企圖以“正義審判”的名義將人類趕出北極圈。《決戰同溫層》講述的是精英知識分子計劃利用氣象武器在世界范圍內發起一場革命,在這場革命里,作者借主人公氣象科學家王樹明之口,從科學的角度闡述了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大自然運行規律與人類活動并沒有直接關系,與大眾的傳統認知相逆,引起了眾怒,這也直接導致王樹明放棄大眾倒向“科學先知”這個由精英知識分子組成的反人類隊伍。
在鄭軍的筆下,生態中心主義者是反人類的,將人類視為自然的敵人,認為人類是所有污染、破壞和腐化的根源。“北極衛士”是極端的生態中心主義,與一般的環保思想相對。一般的環保主張認為是為了人類的利益,只不過是倡導大家重視現實利益之外,也要重視隱性利益,而極端的生態中心主義者則認為世界上的所有生物共同形成一個生態圈,眾生平等、自發運轉、追求自然和諧,為了完成這一目標,可以無限犧牲人類利益。北極衛士有兩個派別,一是正統的“極光幽靈”派,創始人是查爾斯。如果有人在北極探險中遭遇麻煩,便會出現一個身穿白衣的步行者,他不提供給遇難者任何幫助,直到遇難者到達了死亡邊緣,承認在純凈的白色世界中感受到了與自然神靈的心意相通,才會得到“重生”的機會,被頒發一枚藍底三瓣花象征北極上空的徽章,北極衛士認為,在人造的教堂里聽不到主的聲音,它只顯示在讓人炫目的自然景觀中,這種將自然完全視作不可侵犯的神圣,將北極圈的生物視為神靈的思想,其實是一種“媚俗”的產物,在《決戰同溫層》中也有類似描述,在王樹明等中國氣象科學家們的努力下,“晨星一號”飛艇終于成功升入天上,開啟了人類大氣科學研究的新篇章時,“藍天”這個生態組織詆毀的發言是非常詩意的:
當你被困在鋼筋水泥森林中時,你能與大自然做的最快的接觸,就是抬起頭仰望長天。雖然天遠不是你希望的藍,天空也被高樓大廈擠得擁擠不堪,但畢竟,這才是離你最近的自然。你不用盼周末,駕車駛入那滾滾的車流,才能去擁抱它。
然而,當你仰望藍天時,你可能會看到一個怪物,它那近三公里長的身軀在提醒你,無論是極地、深海還是藍天,沒有人類不能去征服的地方。它是人類征服欲的物質象征!而它那深重的陰影,將永遠在已經永不青翠的大地上掠過。飛機雖然早就躍上藍天,但是人們看不到它在大地上的影子。而這個緩慢、高高在上的異物,則拖著它直徑達200米的影子掃過千山萬水。有位讀者發來電郵說,他的奶奶走在河堤上,被那片影子籠罩時,居然嚇得癱軟在地上。[17]
王樹明費盡唇舌,也無法讓“藍天”認識到,他們所贊頌的所謂中國氣象學之大成——二十四節氣是多么粗糙,一代代科學家付出了多少努力才使人們對氣候的認識進步了那么一點點。從另一個角度看,氣候小說也喚醒了人們對生態批評的反思,諸如利奧波德《沙鄉年鑒》(A Sand County Almanac)中 “像山一樣思考”的觀點喚起了人們參與生態美學的渴望,但這種渴望似乎也是人類的一種主觀局限性。布伊爾認為,利奧波德讓我們認識到人類自身包含的生態性,但是,盡管這種以生態為中心、反對人類主宰的企圖中有一些潛在的高尚因素,如果不非常小心謹慎,這種高尚在發展過程中也可以很快變成一種堂吉訶德式的自以為是。[16]P9“北極衛士”還有一支異化得更為激進的分組織,以作家莫德爾為首,他們憤恨所有“南方人”,尤其是破壞北極環境的企業家們,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的刺殺報復計劃。其中,1968年由富豪亨伯贊助的史上最大破冰船“曼哈頓”號測試了西北航線通航可能性,這一事件被鄭軍引用到小說,極端北極衛士綁架殺害了亨伯,讓海洋館中的北極熊對其進行了“正義審判”。
如果說克萊頓將《恐懼狀態》中人們對生態和氣候問題的無知僅指向了律師和政客的陰謀,那么鄭軍則是將生態中心主義者作為徹底的反派來描寫的。生態中心主義者看到了北極圈內的凈土,自認為在這里感受到了神明的力量,所追求的無非是一種加了濾鏡的藝術美感,但事實上,卻如《祝福》中祥林嫂的孩子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一樣,人類與大自然的關系,也許從沒有浪漫過。莫頓(Timothy Morton)的《無自然生態》(Ecology without Nature)一書中用“黑暗生態”的概念,來呼吁人們不要把自然看作遙不可及的美麗幻影,要承認它可能是遭受污染的可怕丑怪,與其創造和逃到一個“干凈”和“比較少毒害”的烏托邦世界,不如“全心投入,與痛苦共處,這是我們的環境、我們存在的地方,要學會正視污穢”[18],而不是像生態中心主義者一樣,企圖將人類作為所有生態問題的替罪羊,鼓動以生態代替人類作為價值主體,最終將走向反生產、反經濟技術的迷途。
綜上,雖然“氣候”這一主題使氣候小說自然而然被納入生態文本討論,讀者也被鼓勵去關注氣候變化及其成因和危害,并積極采取行動來應對,但本質上來說,氣候小說的指向并不是生態主義。另外,目前被熱衷討論的氣候小說《發條女孩》《遺落的南境》《極北》等作品,人為致使的氣候變化描寫也并不明顯,更多的是對工業文明和生物科技的反思,可以討論的人為原因也集中圍繞人類工業文明的興起導致地球升溫、冰川融化、海水將會淹沒濱海城市這些老生常談的話題。相形之下,像《流浪地球》這類描寫人類為求生存而被迫遠離太陽系、遠離自己熟悉的氣候環境去外星系重建文明的情節,在科幻小說與氣候小說的交叉領域內,更能使讀者看到氣候變化對人類活動的影響,從而激發對當下生態環境的珍惜、愛護。而當下所討論的氣候小說文本幾乎不自覺地對氣候問題所引起的心理問題予以漠視,氣候災難的發生,仿佛只是人類征服自然途中的一段失誤風景。正如臺灣學者陳重仁所言,面對氣候變化的困局,不在于抉擇過什么樣的生活,“而是在于自認為有所抉擇的優越心態”[19],如果研究者真要從生態主義立場出發,那么氣候小說的敘事模式恰恰從側面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災害的一種規避和恐慌心理,就如在更早之前,當人們面臨不可抗的天災時,激發了自身無邊的恐懼感,于是開始敬畏神靈一樣,氣候小說想要求助于技術科學,與其別無二致。總體而言,目前學界對氣候變化“人為”原因的強調和對氣候小說的生態主義解讀路徑,仍有可商榷的空間,這或許也并不是作家本人對氣候小說的期待。
[注 釋]
①2019年5月21日,國際地層委員會(ICS)旗下的人類世工作組以29票贊成,4票反對,通過20世紀中葉開始為人類世,但目前尚待ICS和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IUGS)確認。
②摘自筆者2021年5月6日與鄭軍的線上對話。
③指由格陵蘭島經加拿大北部北極群島到阿拉斯加北岸的航道,這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最短的航道。這條航道發現于19世紀中葉,是經數百年努力尋找而形成的一條北美大陸航道,由大西洋經北極群島(屬加拿大)至太平洋。航道在北極圈以北800公里,距北極不到1,930公里,是世界上最險峻的航線之一。一旦能夠進行商業通航,將產生顯著的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