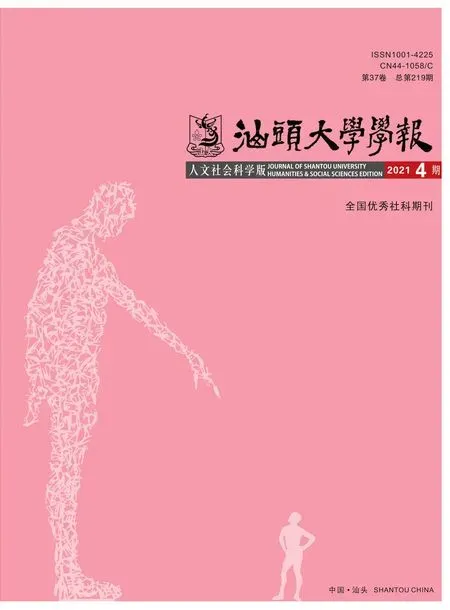“零度寫作”在新寫實小說中的闡釋變異
林 苗
(汕頭大學文學院,廣東 汕頭 515063)
20 世紀80 年代末,在大量引進西方文藝理論的浪潮下,羅蘭·巴特提出的“零度寫作”被眾多的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們青睞,并時常與新寫實小說掛鉤。“零度寫作”被南帆收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批評99 個詞》中,有學者認為:“零度寫作強調由字詞獨立品質所帶來的多種可能性和無趨向性。然而這種無趨向性越來越被狹窄地理解和使用了。在今天的文學現實中,我們無不隨意地用零度寫作來定義那些采用了外部聚焦,行為主義式的敘事規范,新寫實小說就時常不乏貶義地被冠以零度寫作的頭銜。”[1]該論者指出了“零度寫作”這一理論術語的使用被狹窄化的傾向,且“新寫實小說”亦不乏被戴上“零度寫作”的帽子。這反映出將“零度寫作”理論應用到中國文學批評時,存在著理論狹窄化、理論變異的問題,同時也存在著將理論術語不加區分地應用于實際文學批評的問題。另外,文玲更進一步指出,新寫實小說“斷章取義”地理解了“零度寫作”,“僅僅在直陳式、毫不介入的層面上”將“零度寫作”窄化成“零度情感”[2]。該學者從內容上指出了“零度寫作”理論移植到中國大陸所遭遇的變異問題。針對這一特殊的理論闡釋現象,筆者的興趣點在于“零度寫作”理論為何能應用到20 世紀80 年代末的文學批評中?其是如何被闡釋的?其被闡釋的結果又是怎樣的?
一、“零度”闡釋何以可能?
“新寫實小說”這一概念的提出最初沒有經過嚴格的定義與理論說明,它始于1989 年第三期《鐘山》雜志策劃的“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它更多的是一種倡導和號召,將20 世紀末小說創作低谷中出現的“涌動的暗流”加以概括和放大,以期在中國文壇上引領一個“新寫實運動”的寫作潮流[3]。另外,王干在論及新寫實小說的靈魂性時認為:“其實當時說成是‘情感的零度’,還是因為有些忌諱,實質是想要把意識形態抽空。因為在‘新寫實’之前的寫實小說,基本上是意識形態化的,都是用意識形態作為邏輯的體系,然后來模擬人物、組織故事、描寫細節”[4],并指出其創作受到了新小說派羅伯-格里耶和羅蘭·巴特提出的“零度寫作”的影響。也就是說,在20 世紀80年代末,有如王干之類的文學評論家,注意到了小說創作中去意識形態遮蔽的傾向,而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羅蘭·巴特提出“零度寫作”的理論背景相似。王干在《近期小說的后現實主義傾向》中進一步指出,“后現實主義”(“新寫實小說”)“超越了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既有范疇,開拓了新的文學空間,代表一種新的價值取向”[5]。在王干看來,這股“后現實主義”(“新寫實小說”)的文學創作潮流,不止超越了帶有意識形態特征的現實主義,且吸收了現代主義的因子。這種游離于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審美傾向,在一定程度上與羅蘭·巴特搖擺于社會歷史與個人維度之間,追求其中間項——“零度寫作”的審美意圖一致。
巴特在《寫作的零度》中明顯地把寫作界定為“語言結構和風格之間”的“表示另一種形式性現實的空間”[6]10。他明確指出,作家的寫作具有選擇的自由。在社會歷史與個人維度的搖擺之間,巴特以一種解構的姿態,從寫作行為的角度破除“資產階級神話”,卻又跌入“個人維度上的風格魔圈之中”[7]。巴特以其敏銳的批判意識不斷識破社會歷史和個人風格編織的迷夢,企圖尋求中性意義上的“零度寫作”,即主張去除文學作品的外在遮蔽,在語言本體上實現寫作的自由。新時期文學的新寫實小說正是在這一向度上借用了巴特“零度寫作”,在目標的追尋上,以一種自由選擇的姿態不斷掙脫意識形態和個人風格維度上的束縛。
在打倒神話的“零度寫作”上,新寫實小說秉持著巴特對“資產階級神話”的否定姿態。前者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現實主義”,后者則指向了語言。陳思和在《自然主義與生存意識——對新寫實小說的一個解釋》中談到,“新寫實小說”反叛的是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傷痕”“反思”等文學思潮所揭示的現實主義。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多半“混雜著幼稚的道德理想和憤世嫉俗的傷感情緒,成為主觀傾向性極強的現實主義”[8],是狹窄化的“五四”現實主義。可以看到,在新時期“人”的文學潮流中,現實主義演變為對人的價值的無限夸大,即使是“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所反映出的社會“現實”,也不過是人的主觀情緒的泛濫,缺乏對現實必要的反思批判功能。劉心武的《班主任》、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等小說讀來皆充斥著人物內心因時代變遷而變化的大喜大悲。正如王干所言,“把對人的形而上價值的執著探究轉向了對人的形而下生存狀態的關照描寫”[9],新寫實小說正是要打破“人”的神話的迷夢。另外,巴特認為,資產階級的寫作代表了“一種少數派和特權的階級的語言”,這亦衍變為了“一種有關人的本質主義神話學。”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寫作形成了一種固化在人們意識中的語言,他批判性地指出“一種普遍性的古典寫作放棄了一切不穩定的東西以維護一種連續狀態,后者的每一個部分都是選擇,也就是說徹底消除了語言的一切可能性”[6]37。因而,要破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藩籬,語言就成了巴特反思和批判的對象。可以看出,新寫實小說與巴特的“零度寫作”同時具有社會歷史維度上的批判意識,而“新寫實”對“零度”的使用,正是在社會歷史維度上對神話迷霧的破除,尋找自由寫作的實踐。
在個人維度上,巴特以字詞閃爍的“無限的自由性光輝”[6]31打破神話的光芒。但以他敏感的性格,馬上又察覺到作家將不由自主成為“形式的神話之囚徒”[6]49。也就是說,擺脫了觀念寫作束縛的作家,實際上又會受到自身語言范式的制約,成為自身語言的“囚徒”。
對于新寫實小說來說,面對傳統的現實主義與西方傳入的現代主義,小說家們自覺“吸收了可以與現實主義雜交的現代主義表現因子”,但又“小心翼翼地排斥了那種狂轟濫炸式的切割、變形和夸張”[10]。因而,“新寫實小說”自覺舍棄了現代主義式的個人的情感語言,客觀冷靜地道出血淋淋的生存現實。由此可以看出,新寫實小說在面對20 世紀末中西碰撞的文化語境中,保持著巴特的懷疑批判精神,既自覺借鑒新的表現成分,又警醒地覺察是否落入另外一種形式的圈套當中,在生存狀態的書寫中踐行批判的審美訴求。
巴特以其犀利的批判直指資產階級神話、語言形式的怪圈,最后借自語言學的說法,在兩項之間的第三項提出脫離語言秩序的另一種努力——“零度寫作”[6]48。新寫實小說正是在這一向度上,在不斷涌進的駁雜的西方思潮中,不斷破除固有的意識形態的弊端,同時也避免陷入現代主義編織的形式怪圈,最終在人的生存狀態找到了自己的生長點。丁帆、徐兆淮稱其為“奏響了美感的多聲部”[10]。總之,批評家們正是看到了新時期文學這股承接著巴特批判精神的“涌動的暗流”,才得以借用“零度寫作”這一理論術語進行闡釋。
二、斷章取義的“零度”闡釋
羅蘭·巴特提出的“零度寫作”給中國文學批評界的印象是深刻的,在研究、評述新寫實小說的文章中,“零度”一詞被廣泛使用。上文提到,“新寫實”的幕后推手和當事人王干認為,“新寫實”的靈魂性在于“情感的零度”,也即剝離意識形態的“零度”狀態,但這與巴特原本的“零度寫作”的內涵還存在著些許偏差。具體到當時的文學現實,“情感的零度”針對的是“意識形態化的寫實主義”,揭露了作家們消解神圣的同時,轉而投向生存本相的文學真實的寫作策略。自王干之后,批評界開始廣泛使用“零度”這一術語來闡釋新寫實小說。
丁永強在《現實主義與新寫實主義》一文中談到,新寫實小說的敘述語言受“零度寫作”的理論指導,呈現一種“非人格化的敘述方式”,作家“以旁觀者的身份精確地記錄外部客觀世界和人物內心世界”[11],即消除作家的主觀情感。“零度”在這里與作者的情感勾連在一起,作品呈現客觀、冷靜的敘述態度,去除了“為人生”的價值取向,變成了一臺冷冰冰的攝像機,記錄著一個個生活片段。除此之外,孟繁華在論及新寫實小說的寫作特征時,將其概括為“零度敘事”[12],即平實地、冷漠地、不動聲色地書寫簡陋庸常的平民日常生活狀態。冷靜客觀的零度敘事消解了主體的精神價值取向,代之以無處可逃的生活本相。孟繁華是在敘事特征上指出了“新寫實小說”的“零度”特征。另外,趙聯成認為新寫實小說創作是“主體退場”的“零度寫作”,小說文本變成了“一種無調性無色彩的冷面敘述”[13]。“零度”指向了主體激情的撤退與消解,也是對現實的認同和妥協。同時,王和麗將新寫實小說的寫作手法概括為“零情感的介入”[14],即是將偽善的功利主義直接剔除,還原細膩的人性差異和原汁原味的生活。
批評家們借用巴特的“零度寫作”闡釋新寫實小說的“零度”現象,普遍是在反抗神話的社會歷史維度上進行論述的,即是一種去除意識形態遮蔽后的客觀冷靜的“零度”敘事狀態。但在巴特的語境中,“零度寫作”是一種“語言的烏托邦”,寫作的一切意義最終要歸還給語言。當語言不再被意識形態利用,寫作不再被干擾,保持“形式的一種中性的和惰性的狀態”,“人的問題就平淡地被發現和敞開,作家就永遠地成為一個誠實的人”[6]49。也就是說,當神話被消解,“零度寫作”最終要回歸到字詞之間,字詞間閃爍的是主體的自由之思。可以看到,當文評家們急于為20 世紀80年代末文壇出現的這股帶有去除意識形態遮蔽傾向的“涌動的暗流”給出一個說法,卻忽略了巴特提出“零度寫作”的原生理論背景,錯位了“零度寫作”的原意,可以說是一種窄化的“零度寫作”。
同時,批評家們在社會歷史維度上窄化的“零度寫作”,不僅指向“意識形態抽空”,而且也包含了新時期具體文學語境下消解主體激情的成分。前面已經說過,新寫實小說針對的是20 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文學思潮所延續的現實主義傳統,即帶有“為人生”傾向的現實戰斗精神。作家筆下的作品多半是主觀傾向極強的社會問題小說,寫作多是為了針砭社會現實和表達社會理想。而到了新寫實小說這里,“為人生”的意義被消解,價值問題被懸置,擺在作家面前的只有血淋淋的生活。主體的個人情感由高亢的個性主義到低落,最后塌陷到生活的淤泥里。到了作家的創作中,主體的情感始終被控制在理性的范圍之內,新寫實小說家們普遍以觀賞“風景”的寫作態度冷漠地敘述了人間的生存現實,在言語中你感受不到作者對人物的批判與同情,字詞間吐露的只有血淋淋的生存事實。
巴特提出的“零度寫作”,是一種“不在”的狀態,即“主體的地位被消解”[15]的中性寫作狀態。20 世紀80 年代末的文評家們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將“新寫實小說”透露出的冷冰冰的生存現實與“零度”勾連在一起。但不同的是,在“零度寫作”提出的原生語境中,應該還有這一層次的內涵:在取消主體的外在意圖之后,寫作主體就獲得了支配語言形式的最大自由。巴特認為,“字詞是百科全書式的,它同時包含著一切意義,一種關系式話語本來會迫使字詞在一切意義中進行選擇”,字詞本身就蘊含著主體之思,它“被引向一種零狀態”,“其中充滿著過去和未來的一切規定性”[6]32。也就是說,字詞本身是自足的,當主體的意識形態被掏空,就獲得了一種語言形式的自由。
三、“零度”審視下的生存本相
在羅蘭·巴特“零度寫作”的視域下,中國批評家們對新寫實小說的闡釋普遍是一種窄化的“零度”闡釋,即去除意識形態遮蔽的客觀冷靜的敘事狀態。不同于巴特在寫作上對語言的熱切想象,“零度”審視下的新寫實小說,卻呈現出具有新時期時代語境特色的生存意義上的審美。在巴特的理想范式里,“零度寫作”擺脫了意義和目的束縛,寫作的自由得以在語言形式間馳騁;而“零度”觀照下的新寫實小說,“為人生”的意義被消解,人類的生存問題得以被血淋淋地直視。
“零度”審視下的新寫實小說,是生活的“純態事實”,“是當代小說創作中一種土生土長的現象”[8]。20 世紀80 年代末期,中國文壇在經歷了現實主義、尋根、先鋒等小說實驗的銳勢之后,出現了“疲軟”的徘徊狀態,作家的關注和思考自然投射到人的生存問題上。不同于“為人生”傾向的現實主義小說,新寫實小說探討的不是生活的意義,而是生存本身,它把問題往下挖,深入到中國的現實土壤里,追問的是“生存是什么”的問題。而巴特對“零度寫作”的想象,即便他意識到“沒有什么比一種白色的寫作更不真實的了”,作家會重新成為他本身“形式的神話”[6]49的囚徒,但他依然追尋寫作意義上的自由。他認為,“文學的寫作仍然是對語言至善的一種熱切的想象”,“文學應成為語言的烏托邦”[6]55。也就是說,在寫作永遠也無法超越語言藩籬的情況下,巴特依然保持著對語言烏托邦的美好想象,他始終保持著不斷向上的批判姿態;而新寫實小說書寫的生存現實,失卻了巴特那股對自由的寫作的熱忱,它絕望而又無奈地告訴我們生活的真理:這就是生存。
同時,“零度”闡釋下的新寫實小說也不可能指向巴特“語言的烏托邦”,因為時代的生活喪失了對烏托邦的沖動,作家對客體世界產生了不信任,只能抓住自己真實的生命和觸目驚心的生存場域。因此,“零度”闡釋的只能是令人窒息的生活現實,比如池莉《煩惱人生》中對印家厚一天到晚永不止休無法透氣的生活瑣事的刻畫[16],《不談愛情》中莊建飛和吉玲之間沒有愛情,有的只是利益搭建的婚姻[17]。但是這樣的生存現實正好提供了一個精神緩沖的平臺,同時也發展出了一套關于生活的經世哲學。王干在《80、90 年代之間的“新寫實”》中談及新寫實小說對當時人們精神狀況的坡度功能時說道:實際上經過整個20 世紀80 年代的激情燃燒之后,人人都需要降落,“新寫實”正好提供了這么一種降落的功能[4]。也就是說,新寫實小說家們之所以轉向生存狀態的書寫,正好契合了那個年代的精神狀態,如果我們把時間從“新寫實小說”這一點拉到整個中國文化的歷史長河來看,從“五四”以降至新時期之前,人們的精神是充實的、樂觀的、昂揚的。但是20 世紀90 年代初,伴隨著商品大潮的侵襲,人們的精神卻存在普遍的焦慮狀態。因而,在精神上,人們急于尋求一種寄托。而這個時候出現的“新寫實”的寫作潮流,可以說正是抓住了冷冰冰的生活現實,是一點來之不易的希冀。演變到后來,關于生存狀態的文學書寫變成了生活的哲學,一種活命哲學。生活已然是那樣,去奮斗,去以卵擊石,但還是陷在生活的沼澤里,還不如遵從生活的法則,一切都淡化,一切都往后退,活著才是硬道理。再回到巴特,“零度寫作”的提出,更多的是基于對語言、文學、藝術的“烏托邦”的想象,但在當時20 世紀80 年代末的語境,亦不可能發展出這樣的文學樣貌。因而,“零度”闡釋下的“新寫實小說”,只能是冷冰而又真實的生存本相。正因為小說家們所能抓住的只是血淋淋的生存現狀,失去了對“烏托邦”的希冀,“新寫實小說”也顯得笨重而不空靈,作家們既從生存本相中得到了一點依靠,但同時也被禁錮在生存的牢籠里。而“新寫實”最終也走向了一種死循環。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巴特提出的“零度寫作”,是一種語言本體上的烏托邦,始終保持著對自由的寫作的熱切想象;而“零度”審視下的新寫實小說,展現的是生存意義上的審美樣貌。從叩問人的生存意義轉向了人的生存本身,新寫實小說書寫的是關于生活的形而下問題的思考。雖然它筆下的生活本相冷冰冰又血肉模糊,但是對于當時人們的精神狀態起到一定的調節功能。同時,這種“零度”意義上的審美,開出的是特定時期的屬于中國生存現實的經世哲學。
結語
本文重點考察了羅蘭·巴特提出的“零度寫作”對新寫實小說的闡釋研究。首先,著重分析了“零度寫作”運用到新寫實小說批評的可能性,兩者都致力于擺脫意識形態和形式圈套的束縛。恰恰是類似的寫作理想為“零度寫作”在中國批評界的接受和闡釋提供了契機。然而,新寫實小說批評家們窄化了“零度寫作”的理論內涵,其“零度”指向消除意識形態的客觀冷漠的敘事狀態,而忽略了巴特的“零度寫作”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字詞之間,字詞蘊含著主體的全部思考。最后,出于中國本土批評家的闡釋需求,新寫實小說雖然沒有指向巴特的“語言的烏托邦”,但是卻從生存本身而不是生存意義的層面展現20 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的生存面貌,符合當時人們的精神需求,同時也衍變成了一種活命哲學。